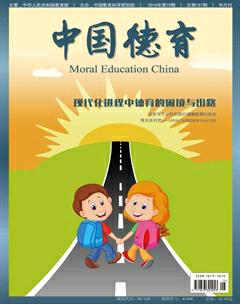论多元文化时代现代道德教育的走向
朱海龙
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现代道德教育赋予了人们理性批判的思维与能力,价值取舍的智慧和勇气,同样也为多元文化在当下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持。
多元文化时代的道德教育已成为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焦点,然而,我们是否该想一想,尽管多元文化的确为促成人精神世界的升华、价值理性的实现带来了难得的生机,但也不可否认,道德教育与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未得到充分的阐释;另一方面,现代道德教育的价值功能虽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回应,但它产生的历史缘起、文化诉求、实现路径与价值追求并未得到足够的逻辑佐证。因此,我们需要正视多元文化时代道德教育的现代走向,探清多元文化健康和谐发展的要旨。
一、道德教育现代性概念分析
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指欧洲中世纪或封建时代之后的时代,它包括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剧烈转型,这种转型是把人从集中权力体系和压制中彻底解放出来的转型,本质就是人作为主体性的自由发展,自我的解放。所以,德国著名现象学哲学家舍勒说,“现代性问题首先是人的实存类型的转变,即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个体的生成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标志。”[1]多元文化与现代性二者之间如同天作之合,多元文化对一元主义的解构和多元价值的宣扬与现代性自由、解放的本质高度契合,可以说,多元文化时代给了“现代性”足够的发展空间,也为道德教育的现代性提供了有利条件。
道德教育的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教育延伸,具备内在的逻辑传承性,因为道德教育旨在促进人自身的解放、人类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道德价值观是价值系统的一部分,它的目的就是促进人的幸福,”[2]这与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作为主体性的人的发展”不谋而合。多元文化时代,正是道德教育赋予人理性的批判、是非选择的价值尺度与方法,使人突破多元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的重重迷雾,找到了价值理性,还原了多元文化时代现代性的本真与美。由此而言,道德教育的现代性对现代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形而上意义,“教育,尤其是健全的教育,能够为各种普遍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主题内在提供并建立较为广泛具体而持续有效的传播方式,解释资源,知识和智力支持,接受机制。这样传播、解释、接受的科学教化机制,是任何其他的文化形式所难于媲美的。”[3]
多元文化时代由于其鲜明的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特色,在对传统社会中的一元主义与集权系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解构的同时,也造成了价值的飘忽不定,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就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这种危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关于这种状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描述,诸如颓废、道德沦丧、抑郁、失落、失忆、空虚、绝望、缺乏值得信仰和值得为之奉献的东西——我们还处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产生的断裂时期。”[4]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现代道德教育赋予了人们理性批判的思维与能力,价值取舍的智慧和勇气,同样也为多元文化在当下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持。
二、现代道德教育的促进力量
追寻道德教育现代性对多元文化时代的理性发展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由于道德教育本身尚未彻底实现人们所期待的现代性,尚未具备赋予主体性的人全部自由的条件和为社会和谐共生提供丰富资源的能力,所以,需要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化自觉为实现道德教育的现代性提供人文环境、价值资源和时代契机,以便促进道德教育的现代性不断升华。所谓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同,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己地位。”[5]由此可见,多元时代的文化自觉正是文化判断、文化选择与文化改造的自主能力,这种能力依靠“拿来主义”无法形成,靠妄自菲薄、自我否定更无法形成,只能靠对一种文化的历史渊缘、当下境遇、未来走向的全面分析才能真正形成。
通过多元文化时代文化自觉的审视与批判,道德教育现代性不足的问题便暴露无疑,这要求我们理清以下几点。首先,当代道德教育的价值理念作为现代性的核心因素还需进一步开放,要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交流中,通过对异质文化的选择与吸收,促进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延续。道德教育价值理念的廓清与重构需要奠基在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以便使我们保持连贯的文化记忆,拒斥文化传统、颠覆文化谱系,只能让人们失去本真的自我。但这并不能成为排斥异质文化价值的道德理由,事实上,“不遵循一个允许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与集团之间相互沟通的普遍原则,就不可能有多元文化的社会。”[6]鲁迅就犀利地指出:“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唱反调。……这才叫保存中国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7]这种做法在当下也颇为流行,本质依然是伪爱国情结。毫无疑问,指引道德教育的价值理念作为教育的主体精神应该具有绝对优势,然而这种优势的获得理应是在开放意识通过对多元文化的比较中寻得的,它理应与各种异质的、多样的文化和而不同、和谐共生,这才是道德教育的最终走向。
其次,道德教育在现代性某些表现因素上尚不突出,需要借助文化自觉的力量进一步反思与革新。道德教育价值理念为“体”,道德教育制度、内容、方法、师资等则为“用”,这个“用”是道德教育价值理性实现的关键载体,应该不断地调整与革新,以适应多元文化时代道德教育现代性的现实要求。困难在于,无论是“用”还是“体”,目前道德教育系统都尚未与多元文化展开良性互动,且“用”,即教育制度、内容、方法、师资等的调整与改革往往滞后于“体”的变化,致使人们感到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难如人愿。然而,多元文化时代的道德教育又是幸运的,它为“体”与“用”的变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人文环境与改革资源。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化自觉,不但警示了当前道德教育现代性的缺憾,也提供了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和全新的教育思维。
三、现代道德教育的价值追求
人是现实中唯一的主体,亦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又是思想意识的主体,是主体性的社会存在者,早在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格拉就高呼“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正是道德教育现代性的价值追求,即人性的自由与发展。多元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多元价值观、价值相对主义、工具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其中不乏对价值判断的不置可否和对人自身价值的无情解构,传统的价值体系被消解,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成建构,道德的权威与人的尊严都受到了挑战。
面对挑战,现代道德教育何以能维护人性的尊严,还原人的价值,表现出人的现代性?审视历史与反思当下,我们仍需回到问题的起点:人的现代性,即人性的自由与发展。为此,康德送来了“道德律令”“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是唯一而同时无可质疑的道德动力,”[8]这成为多元文化社会突破多元价值相对主义的精神利器。需要指出的是,自由仅仅是人现代性中的一个特征,它既非全面,也不牢固。如果认为人类得到了精神世界的自由就实现了人的现代性,现代道德教育也就自然生成,这便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善物,亦不意味着一切弊端或恶行之不存在。”[9]自由与发展的结合才是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而发展则首先要突破功利主义,让人的价值高于物质,否则人变成了纯粹物质的世俗化动物,人的鲜活生态变成了生冷的工具主义,这显然无益于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发展还必须打破个人主义的束缚,因为个体性只是人潜在的和抽象的存在,集体才是具体和自在自为的存在形式,人需要在集体中完成目标任务,而多元文化时代对个人价值的过分宣扬影响了人对自我集体属性的判断,这在一定意义上阻碍了人自身现代性的实现。为此,需要通过道德教育的教化功能弱化人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使人的本性回归集体属性。
四、现代道德教育实现的直接路径
道德教育的现代性理应从道德发生的始点,即生活与多元文化交往中去寻求最终的答案。通过回归生活与多元文化交往来还原道德教育的现代性,并不是观念与现实的倒退,而是现代性意义上的正本清源。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和群体性,脱离了社会性和群体性的人便失去了作为人的自身价值,也失去了道德教育现代性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马克思曾有著名论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所以,无论社会个体或是社会群体,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发生都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不仅从形而上的角度提供了诸如教育理念、教育价值、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育经验等资源,也从形而下的视角提供了教育主客体、教育方法、教学设备等资源,使多元文化背景下现代道德教育的实现成为可能。
然而,回归生活仅仅解决了方向性问题,现代道德教育不会在多元文化生活中自发生成,它还需要多元文化的交往途径,在交往中互通有无,实现道德教育现代性的价值终点——人的自由与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在交往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对社会道德准则、价值标准开始了认知、模仿习得和自主建构过程,对道德的知、情、意、行有了真实的体验,并且逐步形成了自我社会化的道德原型,无论个体道德价值观念的形成,还是社会化的完成,都离不开交往实践。在交往途径的支持下,现代性的价值因素得以彰显。就多元文化时代的交往对现代道德教育而言,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实意义。多元文化时代,就是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的理念、内容、方法、成果、师资等因素只有在国际间交往、流动、借鉴,才能从中发掘其核心价值,多元文化价值只有在交往比较中才能展示出各自优劣。所以,交往已经成为人自身的价值属性和进步发展的必需条件,它与社会生活一起成为实现现代道德教育不可忽视的直接路径。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5.
[2]贝克.优化学校教育——种价值的观点[M].戚万学,赵文静,唐汉卫,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43.
[3]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75.
[4]马斯洛.人类价值新论[M].胡万福,谢小庆,王丽,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1.
[5]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1997(5):15-22.
[6]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M].狄玉明,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27.
[7]鲁洁.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15.
[8]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85.
[9]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13.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56.
责任编辑/李 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