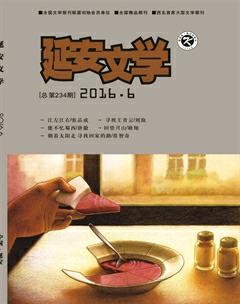石质陕北
刘国欣
小石狮子
我要说的是陕北的小石狮子,不是那种庙宇楼栏之内的石狮子,也跟衙门和墓地肃穆的石狮子不同。我要说的石狮子,是那种可以摆在炕头拴娃娃的小石狮子。它以它的原始性、生命性、鲜活性、自然性、想象性、整体性、泛灵性、直觉性并举,构成了它独特的强大审美能力,甚至可以说,它是陕北人精神的一种象征,体现了陕北人生活方式的一个维度。
石狮子身上,有一种带有人类生命本能的、天然的、经验过的巨大情感库,虽然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变异,汉有汉的姿态,唐有唐的丰赡,明有明的明耀,当今时代有当今时代的谐和,但是它胎里一致的元素和精神是不会改变的,它展现着自身的逻辑层次,于沉默里诉说着自身的审美和情感诉求。原始野性的自由元素,通过石的本质,狮的显像,不加过多雕饰地表现出来,由原始的骨子里的野性冲动与沉沉的石子的睡意结合,表现一种梦幻与追求,表现一种由自然之物经过加工所体现的神性与人性。它是真诚的,也是淳朴的。真诚来自匠人的心眼,淳朴则是对质地和造型的回应。
陕北的石狮子是人对兽性时代的召唤与追思,其绘形、造势各有讲究,传意传神为主,形和相反倒是其次。陕北那种用石头雕刻打制出来的石狮子,笨拙、粗犷、质朴,甚至有点丑陋滞涩。陕北方言说人憨憨愣愣,为木石,石狮子就是一种。但是它的存在又形成一种恐惧和震慑,身子里藏着原始的野,仿佛随时可以起跳、飞跑。一般人根本不敢触动它,甚至家里面也不敢太多地藏有它,尤其庙门的石狮子,即使被盗被偷,也经常在想象里被赋予无尽的能力,偷盗之人会因此丧失他的福分。
陕北没有狮子,整个中国,在汉唐,狮子也是极其少有的。就是现代,我的乡人们,也多是从电视网络看到狮子,但是匠人们的石头狮子却各有特色。这种狮子的创造,立意在先,依石而雕,依形造境,依境传情,为了自由地表达,有些时候,以意为重,舍形舍相,缺眼或者缺嘴,有时眼部并不进行任何雕刻,有时鼻子以下也好像被粗心的石匠给放弃了。以它天性的残疾表现一种智慧,也许这是雕琢者的原意。这样的狮子,我在绥德城郊不远地方一片开发的石头奇相里几次看到过。当然,在村野的尽头,荒草丛生处,也可以看见这样的石狮子,摆放不整齐,完全扑倒在尘埃里,一半身子已经被泥土和青草淹没了,一半露着一只眼,细看,却没有嘴,或者眼是凸出的,还没有完成,仿似纯然的自然物象,但意念已经在那里表达了。它们在意念上穿越今古,超越时空,超越习见的认知。这些像是半成品被人有意或无意放弃的石狮子,简化得太过大胆,太过随意,沉睡在天人合一的自然農耕社会的意境里,却因此显示出了西北黄土高原的狂放不羁和质朴无华之态,显示了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意志,而狮本身,已经脱离其本相,成为一种象征,荡漾出一种无为而往的存在哲学。
炕头拴娃娃的小石狮子,应该算是陕北图腾崇拜的一种。在陕北,人们崇尚石文化,一般的窑洞不算是最好的窑洞,我指的是土窑。平民人家住土窑,真正有钱有势的人家,住石窑。打石窑是要花大力气的,一般人家没那个财力。对石的崇拜自然就转移到了石的佩饰和装饰上,于是,石狮子,作为一种审美和愿望的寄托物,才因此应运而生吧。在陕北,人们心中的狮子高高在上,是和佛家有着密切联系的,而且狮子两眼圆睁、阔口怒张或紧闭,自有一种神威,能驱邪避魔,消灾免难,确保孩子平安,确保孩子受狮子佑护,一路成长起来像只憨状结实的狮子吧。造型狰狞凶猛的狮子,拴在炕头,自有一种威武可爱处,是一种吉祥物。
整个陕北,石狮子以绥德最为有名,绥德的石雕文化最出名。古话有:“米脂婆姨绥德汉,清涧石板瓦窑堡炭”,此话也不无道理。石狮子大规模出在绥德而不是米脂,自有神偶作的美意,和绥德出汉子有一定的关联。力与美在此暗合。
我家有一具小石狮子,在父亲还没出生的年代就被请回家的。祖母在生养父亲之前,已经生养了一些儿女,可是全没有活下来。于是,就请了这头拴娃娃的石狮子回家,希望可以拴住接下来出生的孩子,让他活下来。接着,就有了我的父亲,再接着,我的父亲一路健康地活到了他的中年时代。所以,这头拴我父亲的石狮子,算是功臣一样,一直受着我家的供奉,摆放在我家的窗台上。它大张的嘴巴,作为我们家藏钥匙的一个小处所,在我的幼年,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
拴父亲的小石狮子,口部是横置的花瓣形,狮头身上有两条长而直的线条,里面是一些微间隔的短线条,长短不一。两条长线条交叉围绕起来的那些短线条,应该是头发。花瓣嘴两边,亦有近似头毛的线条,应该算狮子的胡子。狮子的耳部是两条树立的鱼形图,应该象征耳朵。这头狮子是蹲着的,面部较宽,宽于头长,脸部丰满,鼻梁挺直,下颔略圆。陕北人对女性的审美要求以圆脸为主,男性则以阔脸为主,最好是丰满的国字脸。我祖母认为圆脸吃四方,有福,圆圆的脸也象征人生也圆圆满满,她说男人女相有福,如观音长一张女相。也许正因为此,我家的狮子脸型略圆还有点阔。拴父亲的这尊石狮子嘴是张着的,和银行通常摆放在右边那种闭着嘴巴只进不出的狮子有明显的区别。我家的这尊,中间有一小圆球,似豆粒,我那时候经常伸手进去掏,可是探进它的喉咙了,那石珠子还是捞不出。脸部也有很多纹折,弧边三角纹,在头部。面上有两圆点,应该是双目。基座底部也有绳纹,像揉好的馒头用筷子压出的线纹。尾巴是压着的,也是一些弦纹和刺纹,堆砌在一起,疏密度较之脸部更集中。
因为它是拴父亲的炕头狮子,我对它总有一丝亲近,感觉神秘,却又觉得恐惧。当然,这种感受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在我的幼年。而现在,家园破落,它被我叮嘱家人藏了起来,在内心深处,成了父亲的替身的一种象征,它身上甚至有父亲的影子,我固执地认为。它是我前所未有看到的第一只石狮子,也是我生活里的第一头狮子。它连接着原野和今古的气息,它是来自自然的,来自神秘的匠人,也许就来自黄河滩,它曾经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好奇心。现在,在我心里,它也仍然有当时那种永恒的潜在存在的初塑的价值,木讷笨拙,却无可替代,是我黄土高坡上的石狮子父亲。——也许就是这种潜在的情愫让我回头写下这些。
陕北人不像南方人,南方物华天宝,一般人不必为吃穿太过操劳,所以求乐求丽者多,而我陕北,由于土地生产资源有限,从来一直讲究:“居必长安,然后求乐;穿必保暖,然后求丽。”陕北的崇狮意识,应该也是对自然的一种精神呼求,应该也是崇虎意识的组成部分。虎和狮子都是大型猫科动物,就陕北人喜欢给小孩子穿戴虎头帽子虎头鞋,喜欢逢年过节进行舞狮运动,虎相作为一种佩戴,穿上身。而狮子,被赋予了宗教的内涵,成了一种具有圣器特征的圣物。在艰难困苦的生活里,崇尚狮子,并将之雕刻成温顺可爱的样子,何尝不是与自然和内心的妥协?当然,这种深藏的人性意味,也颇值得探讨。
陕北的炕头石狮子,是写实的,形体装饰也是奔着写实的路线,奔着功用隐喻的路线,尽量使狮子的形象在有限之内达到无限的夸张,使生活的真实性与装饰性有机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也相互连贯。中国的建筑,首先讲究坚固耐用,其次讲究美观大方,陕北石狮子的打制,也是朝着天长地久的未来行进的。
石狮子的打制,体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精神意识,荡漾着陕北人对人生的期盼和认知,带有强烈的想象和幻想的色彩。石狮子在被打磨的过程中,就已经消磨了它们凶狠残暴的一面,注重了它们与人生活的亲合与融洽。它们不是创作者表现神性的主体,但是它们作为人陪衬的生活器物,加持了人的本质力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匠人都是普通的,部分石狮子甚至是集体打制,一些人完成狮头,一些人完成狮身。一些狮子呢,在流通中,经过百年之后,再加工,变为另外的样子,但是它们大多是建立在普通人生活的经验之上,在此基础上飞翔、变形和夸张。
炕头狮子是比庙狮、墓狮、衙门狮子、银行狮子等有更多的飞升性的,它们更俏皮,更亲和,更具有人性。我见过很多不同的炕头狮子,在人家的炕上,在收藏者的家中,在一些庙宇殿堂之中,它们摆列着。我现在还记得一头像是猪的石狮子,四蹄下曲,两耳竖立,尾巴翘起来,作跃跃欲奔跑状。因为在泥土里久了,已经出现了苔青色,一头绿色的跃动的狮子,好像随时准备起身,跳出我的视线。
我很奇怪,一些狮子的嘴和眼居然是红色的,是那种砖红色,好像被打过一样。乡下祖母在世的时候,看见我家放在窗台上拴了父亲几十年的炕头狮子变色,嘴角和额头出现釉红色,就会说天气要转了,要阴,要下雨。往往也是如此,天不久就下雨了,就像一种巫术。我现在想,大约是因为石头的色彩和质地可以感知天气吧,然而在客观上,我又会想也许就是一种巫术,石头狮子是通灵的。因为不管人如何喜欢这些狮子,在我乡下,却也很少有人敢去庙里偷这样的石狮子。当然,我在写这篇文章中,认识了家乡一个外号叫做狮子王的人,他收藏有一千多头陕北的小狮子,作为收藏珍藏,也作为一种美术之物器描摹。他的那些狮子,一些极其夸张,眼睛和眉毛似乎在抖动,特别传神。其中有一只,他只留有图片了,长得特别像我黄土高原上另一个收藏有七百多頭狮子的朋友,眉宇之间古里古气,是天赋异禀那种,黑眼珠明显比一般的小石狮子深陷,通过眼睛似乎可以感觉到它的心跳,明显是飞扬的,甚至有点跋扈,不可征服,有类似猴子的狂样、灵样,刁钻纵横样。然而,很遗憾,我看到的只是照片,它被偷走了,狮子王也不再拥有它。很遗憾,这只特别的狮子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以后,我还是要去寻访它的。它是那么多头里最特别的一头,仅仅比我自身用来当父亲的拴过父亲的那头拴娃娃石狮子少一点点特别,因为,这一头是家养的,是连着我的血缘的,在我生命里是唯一,不可复制不可替代,而特别的这被人偷走的一头,我似乎可以寻访到它的替代品。谁知道呢?
大多的炕头狮子打制雕刻古朴,充满着原始意味,但是因为作为拴娃娃的石狮子,又不能有太多的狞烈之气,怕吓着小娃娃,于是,这种石狮子,像猫,让人想到猫,温和俏皮,又不失力的流转。它们以猫的媚态显形,在尘世里坦荡、温顺地活在人家的炕上、窗台上。一些两眼圆睁,尾巴翘起;一些两脚伏地,像家猫一样还戴着绳圈。狮子像猫,明显充满了日常家居生活的情调,而石狮子即便是像猫,也总能透射出一种粗狂的大气,一种原始的情调和意味,其抬腿、扭头、呲牙笑,虽然拙朴滞涩,却毫无做作之态,大约与石头这种明显厚重明显有大地属性的质地有关。为了调节色彩,在一些时日,比如小孩子过生日之时,这些狮子身上就会拴上红线绳,作为一年一度开锁记事的一系列仪式中的一项而被郑重对待。这时候,石狮子分明也是家里的一员,是需要尊敬和照顾的,需要陪伴和嬉戏,与儿童并无二致。
狮子的猫样媚态,甚至是狮身猫头,在陕北的炕狮子中并不少见。在陕北,万物似乎都可以拿来做人的陪衬,然而万物又有灵,陕北是要拿一切来融合的,本就是游牧民族与汉民族融合区,是以前的塞外,是战乱之地,是沙漠与黄河汇合处,是化外也是化内,有“四面边声连角起”的兵器,有堡有寨。这个地方,一切的宗教,都在混合中形成它自己的样子,不是绝对地排斥,又不是绝对地接受。然而,陕北实际是无声的,就如石狮子一样,“石狮子张嘴不说话,什么样的人生都解下。”陕北有这样的禅气与古气,即使陕北的革命红被一遍遍渲染,在陕北人心里,实际另有自己真正的色彩与感受。陕北是习惯将一切化掉的,对狮子的雕刻也是如此。将石狮子请到炕上拴小孩,既是一种供养,又是一种怜悯,是一种分享和承担,并不是作为一种征服进行的,乃是作为一种合作和理想。是的,将狮子请进房间,世界在优美与静穆之间走向谐和,在狰狞与献祭之间走向神性。可以说,陕北的小石狮子,每一只,都洇染着陕北人的期待,都体现了一种理想的深情和企图,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是一种杀戮和征服,而是一种共存脉搏的自由跳动,一种节律,不是你代替我或者消灭我,而是,我与你共存,在一种形体所象征的实相上,我们共同走向自足与静穆,天长地久。
丰富的想象,大胆的构思,以及小巧的身子,使陕北的小石狮子和别处的狮子完全不同,甚至就是与同是黄土高原地区关中的石狮子也不同。关中的石狮子更遵循儒家文化传统的教养,是内敛而稳重的,缺乏飞扬纵横的架势,明明一样的体重,却显得更笨重一些,没有太多的活性。这方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得过去,一方水土养一方石狮子也说得过去。从陕北的小巧的炕头石狮子身上,我们能感觉到一种流淌于狮身的秀美之气,一种矫健之气,混合着慵懒之态,体现出一种自为活着的生活方式。炕头狮子,它的柔美多于它的狞烈,它总体现一副积极面向生活的姿态,无论是低头还是抬头,它都体现一种脉脉情深,并不表现想象的理想狮子的气韵与风格,但它以它的退出自身为完成方式,于取媚中表现自身的怡然自乐。严格说,或者精准说,它确实缺乏一种严峻,但它又并不耽溺于对人类进行谄媚,陕北的石匠没有赋予他们这种气质,他们自己在生活里,也从来不体现这种气质。它是脉脉的,甚至可以说是深情的,但它于这种温顺与静默里,于这种自足的慵懒里,确切地体现着自己的意志,体现着原野与古风,体现着过去与未来。
陕北的石狮子,是在有限中追求无限,讲究留白,虚实相生,不会有太多精雕细刻处,但远远看,却自有一种婉转的灵气与神气流淌,古朴中透露着一种大气。
西方的石狮子和我国的石狮子不同,和我陕北的石狮子更不同。西方有狮身人面像,作为古老文明的象征,它在一步步进化中,逐渐有了自己的翅膀和武器。我说的不是它锋利的牙齿和爪子,而是雕刻时雕出的实体翅膀,以及剑與刀。当然,最近这几年,中国大地上出生的新石狮子,也有一些有翅膀和袭用人面的,那已经不在我要叙述的范围了。我说的那些狮子是古的,过去年代的,相隔了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与现下的时光遥遥相望。
我现在生活的大学校园,文学院的建筑大门前,齐刷刷一左一右蹲着两头汉白玉大狮子。因为大小不一,视觉的感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公一母两头狮子,加之文学院的大门是红色图案纹,砖青色飞檐,让人想起《红楼梦》里那被焦大说成还干净的两头贾府的狮子。但一些同学说,这两头狮子比喻的是陈寅恪和傅斯年。当然,亦有人说,这是为抵消别的院系建筑所制造的煞气,才请来这么两头汉白玉狮子。文学院的建筑和整个学校的建筑一致,但进入里面却自有文学特色,然而外围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不过因了这两头汉白玉狮子,倒是给文学院整座建筑增添了几分空灵之气;人们从两头汉白玉狮子中间走进走出,也似沾了山林之气,沾了一些野气,自然活泛,仿佛别有一种自在,和别的院系形成明显的区别。
写到这里,我想到三个对于陕北石头狮子进行大规模收藏的人,一个即是前面提到的,外号叫做狮子王的人,他有一千多头;一个是我新认识不久的朋友,七百多头,还在不断请进中;一个就是著名作家贾平凹,他不光有兴趣收养活狐狸,他也有兴趣“收养”陕北关中的小石狮子,似乎也是一千多头。想象这些狮子有一天夜半醒来,忽然有了飞跃的能力,想象他们从水泥钢筋打造的建筑里咆哮,冲出,那会怎样的壮观?它们一个个转身,去寻找在岁月流转里一次次拥抱的主人,寻找那些存在或者已经不存在的肉身,寻找在地里掩埋的素朴时代的青苔绿衣,寻找无法道出的前世,会有怎样的哀伤?这几千头石狮子,在我的想象里已经形成风暴。一种收藏所形成的惊惧,一种占有的暴力所体现出的自我屠杀,在我的幻觉里进行。收藏是一种屠杀,这是我在写这篇文字时候一直徘徊的一种感觉,而在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清晰地用“屠杀”这个词,描绘收藏所带来的感觉。于千家万户中,于断瓦残垣里,收藏石狮子,制造了一种分离的紧张,一种岁月的残缺,一种一直在进行的不安。我不是在批判谁,而是描述一种书写产生的想象的痛苦感。几千头狮子,端坐在一起,而它们,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悲怆,它们被拥挤地摆放在几个地方,卧着、睡着、坐着、伏着……对于密集恐惧患者来说,它们以团聚的姿势,制造了一种断裂,深渊在它们团聚的地方,一次次炸开。
我其实并不能准确明白自己写下什么,此刻,我想念拴过我父亲的那头小石狮子,它来自于何方,我并不清楚,在拴我父亲之前,它就已经拴过另一个人了,而我父亲如果活着,现在也已经七十四五岁了。它至少已经百年,甚至比这更久,岁月并没有让它改变多少,然而我想起它,却自有一种亲切。我以我的唯一想念它,以一种不在场想念它,以一种永久之情想念它,它会与我地久天长,海枯石烂。对于收藏石狮子者而言,是存在的;而对于我这种唯一拥有某物的人来说,从来不存在。
石 碾
我的身后是一副碾子。这是一帧照片。我看着身后的这副碾子,看着我自己,想着石头的岁月,我的岁月。
陕北的石文化是个谜,也许连接着汉唐更远的历史,有更久远时代的文明在这里存在过。人类四大文明起始于沙漠地带,而且人类以后的文明,也已经预言要被沙漠地带的文明引领。陕北有毛乌素沙漠,在更久之前,也许还有别的沙漠,沙漠文明在此生发并辉煌,有一定的可能。陕北的石文化是被忽视的,整个陕北文明,也就如一颗被忽视的大石头,是一只有口无法说话的石狮子,是一个被别的文明解释的文明,是一处文化受掩盖的地理。当然,我这是针对近几十年的“红色革命陕北”而言的。了解陕北文化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块地方,不是外界所言的那么简单,它被外来人言语,自间人却是沉默的。而自间人说话,也用的是外来所要用的目光和语言,所以,真正的陕北,从来没有被说出,真正的陕北,却一直存在,并且如同沙漠文明一样,在不断变迁和漂移中。
陕北的石文化,在新时期时代的晚期就已经存在,人们甚至有修建石城的传统,除过绥德大规模的石雕外,在神木的石峁,也发现了大规模的石雕,而在陕北的其他县城,均有各种石雕人面像散落。在我幼年,经常有人来收龙骨等石头,像是石头,但又有骨头的成分在,和部分泥土搅合在一起,说是一种药材。我在田畔山间放羊,也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一些石雕石骨头。人们说起古文明,总是会说到希腊。近年偶有一些历史学家,关注到中国大西南和大西北的一些古文明,有时候我想,我陕北的部分石雕,它是一些部落抵御外敌减少恐惧所制作的吧。我曾经和一个有着自己个人历史版图划分的当地人聊天,他告诉我,在毛乌素沙漠附近,有过更多的部落,甚至一百多个,残杀或迁移、合并,逐渐成了“不精确的总想说清楚”的现行历史教科书的样子,实际上,整个的冰山的真实还在下面。世事本来就说不清,但我每每看见那样的石雕,残疾的,缺眼或者缺耳朵的,嘴巴没有雕刻出来的,总会有一种来自缓慢时光的浓郁惆怅,在我的基因或血液里,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存在过,发声过。那些人借着这些残迹,向我显形,而我却什么都抓不住,一切都无所作为。人,也或者其他的物种,生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时是极其无能的,就长远的时空而言,每个人都是极其无力的,万物无始无终。
亚里士多德说:“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在陕北,也许存在过久远的城邦,开阔辽远的,不断变动的,飞扬激荡的。陕北人身上所体现的那种盲目的自信,那种得天独厚的骄傲感,与现代贫瘠昏黄的高原地貌也许并没有十分必要的联系,而与骨子里那份隐秘的关联相关。在这块以生殖和生存为主要义旨的土地上,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人们的文化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革。在当代,随着西方文化浪潮的袭击,在教育上,全国大部分发达地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和信仰,我们迫不及待地拥抱全球化,进行改革或变革。然而,山川和地理交通的阻隔,陕北倒一直在缓慢地保持着农耕文明的传统,千沟万壑仍然是封闭又开阔的,陕北高原上的人家,苦与乐仍然大多来自土地,根底是柔软和坚韧的,文化里照旧保持着刚烈质朴的一面,有天空的空感,有大地的实感。在这里,人们依然在畅想女娲补天,展开对女娲的石头的思考,展开对引进的西西弗斯的石头的思考。这里的风景、民歌、说书、快板与道情、粥饭与烩菜、一言与一笑,仍然如同农耕时代一样在悠悠荡荡中展开。在这里,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一块砂石上坐下来,在一处废弃了的石碾台上坐下来,在虚想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你仍然可以于车间流水的机械与喧闹外,获得一个大世界,——一个,可能存在的桃源。
我今天要说的,是陕北的石碾文化。石碾,是农耕文明的器具,甚至是圣器;而今,是风景,是碑志,也是墓志铭。对于我刘姓人家,对于我所在的小村,这些都是成立的。
父亲的曾祖父辈,迁移到这个我从小生活的叫做王家墕的村子,大约两百年左右吧,反正至少已经有一百六七十年。那时候,整个村子住着的都是王姓人家,自然村莊属于王姓的地盘。我们作为刘姓人家搬迁而来,古井是王姓的,石碾石磨石碓子,也是王姓人家,自然用不成。
父亲的一个五姥爷(父亲的爷爷以上一辈),人高,壮实,年轻,环眼,好斗。他有匹夫之力亦有匹夫之勇,他在这个村子要住下来,要吃要喝,要刘姓人家生儿育女。于是,他一手提大铡草刀,一手大剌剌赶着高骡子去井口驮水,怒目而视王姓出来拦路的人。就这样,整个王姓家族被他吓倒了,刘姓人家开始驻扎下来。然而,石磨石碾都是人家的,不给用,自然有理由,但粮食需要脱壳,人要吃,牲口也要吃。于是,这刘五老汉,就连夜走石头滩,打了两副碾子和磨盘回来。那以后,我刘姓人家就开始在这村子住下来,分上院下院,上院一副碾磨,下院一副。
我从小就常常听叔伯祖辈说如何在这个村庄扎根的故事,他们一边就着下院的碾道压面,一面说这样的故事。那时候,整个村子里可以启用的碾子,就只有这副了。
在此之前,村子里至少有六七套碾子磨盘。在中国古文化里,碾是青龙磨是白虎,都是圣物,有巨大的煞气,萨满教对碾子,亦尊为圣物,而我陕北,实际上萨满教盛行,只是叫神神而已。婚丧嫁娶,这些碾子都得用红布包起来,煞它们的煞气。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村子里就只用我们刘姓人家这副碾盘。也许是因为我们刘姓人家比较和气吧,对于碾子的修护和维持也比较尽心。其他的几副碾磨,都成了婚丧嫁娶时候穿红衣的青龙白虎,平日里是不启用的。祖母是村庄里她们这一辈最老的老人了,每次,当别人来碾碾子压面,她都会偷偷说起碾盘的故事,说起艰难岁月在一个村子扎根的困苦。到现在,祖母去世多年了,下院快九十的伯父,我假期回乡,在碾盘上相互坐下来拉话的时候,他还说着过去年月的艰辛,哀叹着杂草丛生的碾盘曾经如何连接着整个刘姓人家的命运。他是个勤劳的人,一生辛苦,多儿多女,碾子就在他家土围墙的院落外。对于他,这碾子,曾经如何锣鼓喧天,曾经如何铃铛回响,曾经如何碾盘吱呀,都已经算是过去岁月了。他用浑浊的眼睛打量着碾盘,对我说:“时代变了,碾子老得不用了。我们这最后一茬人,也要废了。”然而,作为刘姓人家在村庄生活并繁衍的标志,这副碾盘,值得被追记下来。
石碾是由碾台、碾砣、碾棍、碾道等组成。碾盘和碾砣大都是采用石头雕凿而成,显出石器时代的沧桑,而碾棍,多由木头做成。我陕北,多是槐树或枣树,因为这两种树木经久耐用。我家的这副碾子,用的是枣树滚。碾砣中间有铁棍。碾砣正中插棍,然后围绕着碾台中心,人或驴骡牛开始推着拉着,就可以转动磨粮食。碾台是圆形,碾盘则如一个车轱辘,碾盘中心凿空装的竖轴子,则像是风车。如果不是因为碾盘笨拙沧桑,整个碾子台看起来,则像是巨型的石头玩具。大人后面跟着小孩一步步推着,碾子滚动,灰尘飞扬,碾子咯吱咯吱发出颤音,小孩子咯咯笑着,没有比这更好的农村玩具了。
牛驴骡拉碾子轧粮食的时候,往往为了不让它们偷吃粮食和感到转圈眩晕,会在眼睛上绑一块布,直包到两耳后面。一般人家,包的都是红布,大约也是出于对碾子的敬畏吧。红色在陕北,有更特别的地方意味,和普遍的中国红还有区别,我以后要专门写关于陕北色彩的一篇文章,但愿我能捕捉到精准的语言,来描绘出这块土地的色彩。
如今,我刘姓人家的碾子,长久地安息在角落里,石台盘上长起了蒿草,我叔叔放的白羊入夜归来,经常跳上跳下地跑,我亦敢于坐在碾子上,仰高脖子望山闲。如果我祖母活着,这样对碾子不敬,是会吓坏她的,她绝对不会愿意看到我大剌剌叉腿坐在碾子上。当然,现在,亦有麻雀鸽子和鹧鸪,经常来这里人一样蹲着,鸣叫歌唱。青苔也已经爬上了碾盘,仿佛要书写岁月的变更。曾经,一年四季都会高歌特殊曲调的碾子,在电器时代的磨面机代替它们之后,长久地休息为一个喑哑了舌头的老人,独自在沉默里,送着黄昏和黎明。大雪纷飞的冬日,人家姑娘出嫁,远远从新村传来锣鼓声,也不必再因了青龙白虎之名,给它们盖上红布单。它们被遗忘在这里,连同那些多半废弃的老房子,以及院落的野猫野虫子,和那些村庄的鳏寡孤独,作为废弃之物,遗忘在废弃的旧村庄。
现在,就是我再怎么想听一曲碾子的自然曲子,也至多只能在记忆里召唤和回想。现实里,不到二十年,甚至不到十年,它们居然就这样沉默地退出了生活。
曾经,村庄的男人围坐在碾台上开会、纳凉,婆姨围坐着碾台上拉话、纳鞋底织毛衣,孩子们围着碾台捉迷藏,鸡和狗,羊和牛,跳上碾台,拴在碾子上,夕阳的光照在碾子上,日子游游荡荡,好像永生永世就必须那样过着,可以那样过着,却忽然间天变了。
我家的这副碾子旁,长满了枣树,都是已经成年的枣树了。秋天来临,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后,打枣,枣子落在碾台碾道上,总觉得更干净,更红润。八月十五献月饼,也多是选择在碾子旁边进行。因为有这副碾子,有这大石器在,人的心仿佛也可以沉下来,是安的。
我最喜欢过年时碾糕面,家里人也是。直到现在,碾糕面用机器加工制作出的年糕,家人仍觉得不如碾子碾出的糕面好吃。只要碾糕面,总会是过年时分。它属于细粮,不容易吃到,而过年没有它,却不算是过年。年糕是陕北过年必吃的食物,寓意是年年高的意思吧。
炸年糕是非常受重视的年节食物,而炸年糕的糕面,最好是新一年秋天打下的。过年时分,为了碾年糕面,碾子就开始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人们尤其怕下雪,因为雪会阻碍村庄人家排队,年糕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年糕的糯米需要头一天晚上泡,泡软了第二天才可以轧。人家磨年糕粉,总是带红柳编制的大簸箕和大笸箩,簸萁箩面,笸箩装细面和粗面。那簸箕和笸箩,每年杀猪时分,都要浸了猪血密密渗一层晒干的,为的是它们不漏面粉。
一般磨年糕都会选择大早上,因为是我刘姓人家的碾子,自然刘姓人家靠前,一大早刘姓人家自然就占了碾道。祖母将泡软的软糯黄米倒在已经扫干净的碾台上,接着,将牛或驴套起,眯了眼睛,就可以赶着它们转圈了。一般都是姐姐在箩细面粉,祖母绕着碾子扫啊扫。那扫帚也是自己家的糜子苗成熟收割之后扎的,上面也有粮食和庄稼的香气。有时候糯米因为泡得太软,祖母就会用锅铲铲一铲,然后再接着让牲口碾,不一会继续扫,一簸箕又一簸箕将粮食装到开着露天口子的笸箩里,让姐姐用粗箩和细箩各筛一遍。祖母喜欢吃细细的面炸的年糕,她一直都爱吃,到临死也爱吃,这份爱她到死都保留着,即使在她死了两个儿子的八十多岁之后仍然保留着。吃到软软年糕的时候,她好像对人生都满足了,好像借着这软软绵绵的粮食,她又生出了自己活下去的力量。因为她喜欢吃细面,所以姐姐就筛得仔细,粗箩细箩各过两道。姐姐这些方面比我好,她是得着整个家族欢悦的,圆圆脸,甜甜的,不太爱说话,总是乖乖的。我也要求筛,也喜欢过年时候凑这气氛,也想着讨好祖母。
我出生的时候祖母已经七十多,算是很老很老了,经常哭,尤其后来死了两个儿子更是每天哭,随时哭。我们都想为她做些事,让她能够顺心些。可是祖母不大喜欢我做这些,她看不上我做这些。她也会给我筛箩,但是很快就没收掉了。她觉得我筛面筛得尘土飞扬,握筛箩既轻又高,总是筛到半空中,面粉都飞掉了,我脸和头发都是粉尘太浪费。她不让我玩筛箩,我总会躲在一面看,心里恨恨的。当然,大多时候我赶着羊群在杨树湾,看她们轧面,筛年糕。现在,祖母死了已经六年了,即使过了六年,我仍然有被抛弃的悲哀。每一次,做饺子或者筛糕面,我就被训斥得远远的。祖母是不放心我的,她不相信我的手艺,她也同样不相信我可以将人生过好。从筛糕面到我整个的人生,她一直有着极其深刻的悲叹,她总觉得我过得轻飘飘的,那双把箩总是拿到高空的手,会将整个的人生,也搬离地面。她一再地用她已经没有多少力气的手,往下压我,压我的筛箩,压我的人生。她总觉得我太轻飘飘了,临死的时候仍然如此觉得,惦记着我,总觉得我瓜不落蒂不熟。
在更早的一些年月,我四五岁时候,爷爷还活着,我也会跟着他碾糕面。祖母围着石碾里里外外扫,爷爷赶着牲口专注磨。爷爷放羊出身,临死前两年在放羊,他的腿就是在放羊时候被过路车碾断的。爷爷在轧年糕面粉的时候喜欢唱山曲子,就如他喜欢打场时候唱曲子一样,他放羊出去独自一人更是喜欢唱。——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会在以后的年月里那么喜欢上山曲子。听到爷爷一边轧面一边唱山曲子,我当时觉得开心。那时候我实在是太小太小了,牛的背要上去,驴的背要上去,骡子的背也要上去。爷爷将我抱上牲口的背,我跟着牲口转圈子,仿佛也是拉磨的畜生了,喊着要眯眯眼,眯眯眼。
最可怕的事,也是这时候发生的。我跟在爷爷的身后轧面,跟着跟着,就动了将手伸进碾子下的心思,我不明白碾子怎么能将颗粒状的米粒儿碾成碎粉,就将手伸了进去。
代价就是,我的无名指和小指立即被碾了过去,血肉模糊,那指尖盖翻着白色的血肉浮出来。我不敢看也不敢哭。我怕他们骂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主动戕害自己。可我并不知道这样会受伤。和后来很多次我受伤了才知道是自找的结果一样,和我总把人生过成颓败失望的结果一样,必须在承担后果之时,我才知道,是我自己最先伸出握向灾难的手。
以后,那两只手指有半年无法正常运作,我变得安静起来。再后来,这两只苦命的手指,还又一次受到了荼毒,是被人家打水井的滑轮截了的。不过,只是被剔除了一些肉和指甲,手指被作为残存保留了下来。为怕祖母担心,我仍然没有哭。那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不再轧面。我对他的记忆,极少极少的。只记得他把我抱在拉磨的牲口身上,我叫着:“眯眯眼,眯眯眼。”那时候,我想做一头拉碾子的骡子或牛,驴子也行,它最乖巧,最漂亮,孩子们最喜欢驴子呀。这碾子连着我的血与肉,连着过年的糕面與祖父母的身影,连着我们家养过的拉碾子的畜生们,就这样第一次于血肉模糊里,被我记住了。
对这碾子最甜美的记忆,除了它可以带来年糕,还有就是它碾过榆树皮。二爹爹砍了一棵榆树,我们一大家子高高兴兴,要吃榆面饸。榆树皮吃起来很香,但必须碾成粉和面拌起来才好吃。我小时候,就已经很少吃到榆树皮了。二爹爹砍了榆树,我们就有了榆树皮,我们就让这大石碾子轧,簸箕笸箩摆好,毛驴拴好,扫帚放好……一家子都很喜悦。一家子都在等着吃榆树面。——那是我关于刘姓家族最为愉快的一顿饮食记忆。爷爷也还活着,祖母也活着,二爹爹和父亲也活着。他们经常吵吵闹闹,但记忆里有过这么一次,他们齐心协力砍倒一棵树,一大家子围着箩面箩粉,笑着说着,等着吃榆树面做的饸。那样快乐的日子,是农耕时代记忆里最幸福的日子,仿佛日子无论怎样过,只要眯上眼睛,咯吱咯吱,一圈圈碾过去,就会碾出精细又惊喜的生活,碾出重复但有序的人生,碾出一种平平静静的安稳。——想不到,多年之后,我仍然过着这样不断重复的碾轧生活,只是,换了碾道,换了碾台的器材,我自己,也不再是山里和驴子骡牛一样呼吸的野兽。
在照片里,我对我身后的这副碾子展开思考,我想象自己的岁月,它的岁月,想象石器时代的岁月,远古的岁月,想象风,想象石头。我的村庄,我的陕北,是一个一再唤我低头思考石头的地方。这里放着西西弗斯的那颗石头,也放着女娲补天的那块石头。而我,在隐秘的世界,不断去确认一个又一个雕刻石头准备补天的人。因此,我返归我的幼年时代,写下这些,我也渴望找到一块石头,补我露天长恨。
栏目责编: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