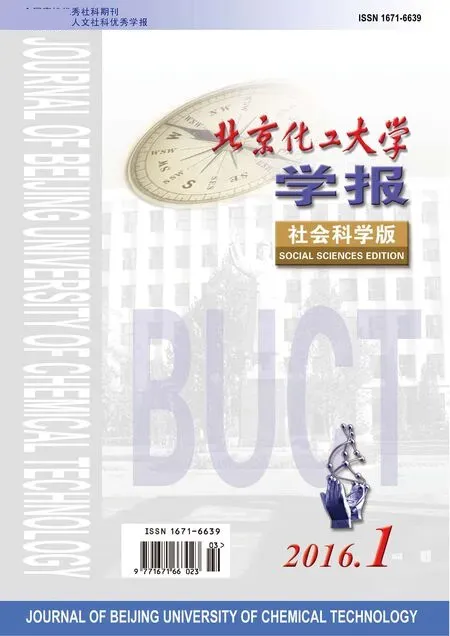维摩手段·娑婆渡舟
——马来西亚居士佛教的形成与发展
陈秋平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
维摩手段·娑婆渡舟
——马来西亚居士佛教的形成与发展
陈秋平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
居士及居士团体在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居士佛教是马来西亚佛教重要的特色之一。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究造成马来西亚居士佛教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以期找出其中的脉络,更清楚地展现出马来西亚佛教的不同面貌。
居士;僧伽;中国佛教;居士团体;经济发展
一、前言
曾任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会长的继程法师认为:“马来西亚佛教近数十年来渐渐的蓬勃发展,其发展之主流不是以寺院为中心的僧团,反而是以在家居士及学佛青年为主的佛教团体。这是与许多地区不同的现象,也许是因我国社会背景,以及我国僧团凋零之所致。”[1]Blofeld也观察到,在东南亚,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许多的在家佛教团体,这些团体的会员都有虔诚的信仰,不但注重个人精神层面的提升,还注重社会福利工作,通过各种管道向年轻人介绍佛教[2]。两人的观察,明确地点出居士和青年在马来西亚佛教发展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居士佛教是马来西亚佛教重要特色之一,是佛教多元性之外的另一个独具的特色。
如果说大部分地区的佛教发展,有赖于佛寺和出家人的推动,而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在家团体所推动①,居士团体在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家信众佛教组织与寺庙一样,更有部分替代了寺院的角色,在拓展佛教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可发现在马来西亚全国各地的大城小镇,佛教活动的推广大都由当地的在家佛教组织所推动,弘法授教的工作也主要是佛教会在做,而寺院很多时候只成为人们膜拜的场所。
居士佛教之所以能在马来西亚顺利发展,且形成一股强有力的佛教生力军,并在独立后的马来西亚佛教发展中有诸多贡献,能与僧伽共事、在各个领域共谋佛教的发展,一起建构蓬勃的马来西亚佛教,是因为居士在马来西亚佛教中的地位是显著的,在很多方面都积极主动寻策促进佛教的成长,因而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马来西亚居士佛教。
但,一向以僧伽为主要拓展动力的佛教,为何在马来西亚会形成以居士为主要推动力的情况呢?
二、居士佛教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马来西亚居士佛教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内部和外部原因与基础。从内部原因而言,包括了历史发展、佛教徒素质、团体发展等原因。而外部原因则包含了社会及经济的发展等因素。无论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因素,都在推动居士佛教发展中扮演角色,内外部原因的有机结合和相互影响,就形成了马来西亚居士佛教的整体发展面貌。下文将尝试说明这些原因。
(一)中国佛教占多数
马来西亚有各种不同传承的佛教,包括南传的锡兰佛教、泰国及缅甸佛教,也包含了藏传佛教和中国佛教。其中,由于华人佛教徒为全国最大的信徒群,因此中国佛教乃马来西亚佛教的主要传统,占有绝对信徒数量以及寺院传统。因此,中国大乘佛教对于马来西亚居士佛教的形成肯定具有影响。
从历史而言,由于大乘佛教的俗化,其中的影响就是在家信徒地位的提高。这可以从菩萨大都以在家信徒的形象出现看出来[3]。强调菩萨道亦为居士,这使得居士的地位大大的提升,居士有了更大且直接的因缘学习佛法,进而贡献佛教。
在大乘诸经典之中,以在家居士为主角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中尤以《维摩诘所说经》中的维摩诘居士和《胜曼经》中的胜曼夫人最为人知,成为了众佛教徒心目中的学习对象①《华严经》和《法华经》中的善财童子和龙女也是备受称道的“居士”典型。。中国佛教历史中,亦不乏王侯、贵族、儒者、文人等在家居士代表人物。自东晋庐山慧远创设僧俗同修团体“白莲社”后,此类团体到了唐宋仍十分普遍流行,而也有相当数量的居士成为此类社团的领导者。到了明代,居士对于佛法修习与传扬研究,大有进展。明末朱时恩更仿效《景德传灯录》编辑了《居士分灯录》。清朝则有彭绍升所著的《居士传》。这样的发展,足见居士修行在中国佛教中已蔚然成风,在家居士可以修行证道,传扬佛法,度化众生亦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
中国在民国初年便出现了以居士为中心的佛教会,福建、福州、厦门等当然也不例外,也有功德林、莲社、佛化社、佛化女社、佛学社、佛化新青年会等的成立[4],许多学者也认为中国民国初年佛教的发展趋势是居士的地位逐渐地被提升[5]。这些风气和进展,都肯定会对学习中国大乘佛教的华人佛教徒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居士们学习佛法的重要依据,以及思考马来西亚佛教未来的重要思想泉源。
南来的华人佛教徒,一直都关心着“祖居国”佛教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尤其是独立前的佛教发展,更是受到中国佛教的极大影响。无论是太虚大师提出的改革佛教思路,还是人间佛教的理论,都极大地影响着马来西亚华人佛教徒。近代又有杨文会、欧阳竞无、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居士积极革新拯救佛教,证明了居士亦有能力改变佛教,促进佛教的现代化发展。如此的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居士积极修证佛法、弘法利生的热忱。这也进而影响马来西亚佛教徒,尤其是华人居士积极入世、超然于传统的形式和教条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居士的地位,并大大地增强居士的社会作用。
相较之下,僧伽罗裔、泰国裔和缅甸裔佛教徒大都以佛寺为中心,他们与华裔佛教徒相比,较少成立以在家人为主的团体,而且他们人口也不多,佛寺已足够应付他们的宗教需求。故,从佛教传承而言,居士佛教在马来西亚的发展,主要还是受到了中国佛教的影响。
(二)僧人不足
如前所述,居士团体的成立,必然受到了祖居国的影响与带动,但这只是其中的渊源,更直接的因缘应该是僧人的缺乏。就以马来西亚北部的槟城为例,1960年,作为马来西亚佛教重镇的槟城州只有56位中国佛教的出家法师[6]。竺摩法师曾记载:“……几年前在某地有僧人因把小庙传给菜姑②“菜姑”指闽南一带带发出家住持的女众佛教徒。“菜姑”投拜皈依某位比丘僧,在佛前举行三皈仪式,也同时摄受《梵网菩萨戒》,便算出家住持。她们舍家庭,独身不嫁,住佛教寺院,布衣素食,诵经礼忏,除了仍挽青丝和留发不剃外,与出家僧、尼无异。闽南一向以来都是中国佛教发达的地区,女子出家人数甚多,但“女众削发出家尼僧少,带发出家菜姑多”,闽南一带女子出家人中95%均为“菜姑”。,官司闹到法庭,法官问他为何不多收出家僧徒,而把小庙传给菜姑呢?他答道:法官!现在马来亚的人,你想叫他出家,即使你把苏丹让给他做,他也不愿意出家呢!所以只好把庙传给菜姑了!”[7]可见当时佛教界,尤其是中国僧人是十分不足的。再加上缺乏宣传与对佛教的认识,普通一般人皆未明出家的神圣意义,视出家为畏途,加剧了问题的存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南来马来亚的僧人,大都未做长居的打算,他们当中有者为了寻求经济满足,而南来当经忏师,又有者前来只为化缘,将缘金带回中国修建祖庭。这些因素都造成马来亚僧人的不足。
而且物质生活相对富裕,僧众的来源渠道因而匮乏,入寺之后的教育也不足以让大部分僧侣建立坚定的、持之以恒的信仰。可是,社会的普通民众又急需佛教等各种宗教资源来满足其心理和信仰需求。在僧团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情况下,寺院和佛教事业就必须借助于有学养、有信仰的居士的力量才能健康发展[8]。
从实际情况出发,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寺庙固然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但若只靠约千人的僧伽来拓展佛教,马来西亚佛教不可能有今日欣欣向荣的状况。所以居士必须配合担当佛教拓展的责任,展现更大的主力和活力[9]。相较于许多的寺院,居士团体也更有活力和生气,带动了区域性的佛教发展。反观,多数寺院已沦为拜拜的场所,毫无活力,且糅杂了许多非佛教的色彩,逐渐失去了接引和度化众生的终极角色。
就算是进入了上世纪80及90年代,甚至于今天,马来西亚还是缺乏僧团的组织力,在僧团没有觉悟需要加强组织力之时,或是僧团组织未健全之前,僧人不如居士容易得风气之先。但是,如果僧团本身已经是一个具有先进理念的开放式僧团,对于化导社会有积极的、自觉的作用,那么,其组织力、信仰力和摄受力,实际上还是远远超过居士团体。可惜的是,虽然已有了全国性的僧人组织,但是却因为多元的传统和各自为政的情况,及个别出家人对组织认同感的缺乏,使得僧团未能得风气之先而快速作出调整,造成了居士佛教更为突出。一个理想的佛教社会,应该由僧团来领导,但其先决条件是僧团本身的佛法认知能与时代合拍,释放出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和摄受能量。基于僧团的先进理念和统理地位,而主动开展或自觉响应引导正信居士的组织,形成僧团与居士系统的相互配合的佛教弘化组织,实现佛教化导社会的目标和理想[10]。
但在马来西亚,现实和理想并不一致,由于严重缺少可以或愿意弘法的出家僧侣,及缺乏强有力的僧团组织扮演领导角色,欲学习佛法的居士便不得不尝试一个新的方式,在法师的协助与指导下成立居士团体,以便可以为大家多提供一些学习佛法的空间。居士也不得不提升意愿和能力,担当起弘扬佛法的责任,利乐有情众生。事实也证明居士们能协助解决缺乏弘法者的困境,他们也愿意投身到弘扬佛法的行列中,向社会各界和各年龄层人士宣说佛教教义[11]。这也即形成了当今马来西亚居士佛教面貌。
(三)僧人素质低落
出家又称出尘,意指辞别家庭眷属、弃舍世务而专心修行佛法。经中云:“出家者,谓持出家威仪相貌,弃舍俗境,受持禁戒,如法乞求清净自活。”[12]这明确指出了出家的意义,即在于远离尘世,持戒求法,过清净的生活。从大乘佛教的观点而言,出家除了为自己求得清净的生活,更要发菩提心,广度有情,是以应当以威仪相貌,上求佛道,下度众生,塑造人间净土。
但,经过长时期的发展,依附之人既多,故由于不真纯之动机而出家者,亦不在少数,其中不可信赖之徒必然也随之增加。只要社会普罗大众仍继续认为这些身穿袈裟、剃须发、诵经念佛、常住寺院的“僧人”是佛教出家僧人,他们就会继续违反佛陀的教义,污蔑僧伽,误导大众[13]。这对于佛教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更有甚者,还形成“僧尼浩旷,清浊混流,不遵禁典,精麤莫别”[14],“并集法门……盖均冒滥”[15]的局面,佛教表面繁荣,但却也孕育着毁佛、灭佛的大危机。
独立前移居马来亚的僧人,一般素质都不高,且多数是经忏师,以打斋度死为业,无法讲经说法,度化众生。他们继续着中国南方佛教的陋习,以及太虚大师所谓的“重鬼”的佛教习俗。这样的僧人,虽然仍能维持三宝存在的意义,却无法对社会带来更正面的影响,不足以带动整体佛教的改变与发展。
对于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僧青年,继程法师有如此的看法:“随着佛教渐渐的兴盛,出家的学佛青年亦会增加,但一方面由于缺少了如在家佛教组织的推动,僧青年发心出家后,反而没有很好的机会接受正规及非正规的僧伽教育,致使僧青年必须靠自己在佛法的修学上摸索,再加上一些僧青年必须在常住或寺院中劳作服务,没有或减少学习佛法、修持佛法的时间,这与出家的志愿往往不符,故而导致了内心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佛门出家的资格没有严格的规定,亦不重视其知识水平之限制,大开方便之门,故出家青年之素质及知识皆参差不齐,这造成了僧团内部的不平衡现象。尤其缺少有系统的僧伽教育,无法使僧才通过教育的方法达到一定的程度。”[16]这道出了这一个时代的僧青年所面对的问题,也说明了居士不得不挺身而出的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不少出家众逐渐的物质化,也让民众对之反感,而失去宗教师的良好形象。虽说在现代社会,适当的物质运用还是必须的,利用科技手段弘扬佛法也是有利的,但关键在于如何适当的利用物质以利自己的身心清净和度化众生,而不被物质“所用”。如果发现僧人对于此世间的物质享受过于热衷,信奉佛教的普通大众自然会觉得尴尬,也觉得灰心失望[17]。出家人本就应该尽量减少物质的享受,将身、口、意净化和提升之后,通过崇高的宗教情操并付之阙如,对俗人和居士的生活样式产生正面影响,必然能使得居士的宗教虔诚得到提升。简而言之,就是在僧人自己得到提升后才能对外发挥引导和影响众生的作用。佛教是注重身教的,而言教是辅助修学者达到身体力行之方针,若只是口令式的布教,对佛教之菩提种子的散播无实际帮助,佛教也永远无法提升人心[18]。
当然,我们并非否定僧人走出寺院介入社会,问题主要取决于参与社会的方式以及参与到哪些领域中去。如果能善于利用现代先进物质对社会的积极关心以提升社会人心道德,不但不会损坏僧人的威望,还会提升社会对佛教的认同感。佛使比丘认为佛教要吸引人民,首先僧伽就必须依教奉行,将治身和治心放在首位。其次,佛教在现代社会,不能仍保持着山林佛教的形象,它必须适应现代的世间需要,为众生解决因政治、经济、道德等所引申的问题与烦恼[19]。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需要出家僧侣提升本身的素质,不但要在修身和修心上下功夫,更要“深入经藏”,让自己“智慧如海”,同时也不应该忽略了对世俗知识的吸收,方能清楚社会的变化,有效地了解现代人的问题与需求,才能做好度众的工作。简而言之,僧人的素质是否提升,在于他是否尽本分地学习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精神。
在佛教史上,每当僧人素质趋于低下或过于庸俗化,僧团日益腐败之际,佛教界必然会出现一些发大心的居士联合某些高僧奔走呼吁,采取各种补救措施以挽救圣教。其中以杨仁山为代表的居士界精英对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复兴与恢复,便是一个典范例子。他们通过各种创新的方式,在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样一支独立于佛教传统僧团之外的令人瞩目的居士弘法队伍,必然也受到了马来西亚佛教在家精英的关注。在僧人素质无法获得提升时,成为了他们学习与模仿的榜样,藉此提出了居士也能发展佛教的主张,并应运而生起各种适合居士弘扬正法的方式,为马来西亚佛教的前程尽心尽力。
概括来说,随着佛教在各地区的演进,民众对佛教和僧人的神秘感及盲目信仰减少,对僧人的修养、学识与处世能力要求却越来越高,这使一般僧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影响力日形减弱。这样一来,居士界纷纷起来弘扬佛法,在进行自我教育的同时,还以不同方式帮助和促进寺院及僧团的自身建设,纠正其种种弊端,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20]。当然,信仰坚定、学识渊博、在僧俗四众中有威信的僧人,能德者居其位,他们抛却世俗生活,以清静比丘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其感染力、号召力要远远大于居士。可是情况却不是如此,因此如果有一批有信仰、有知识、有管理能力的居士,愿意参与寺院的活动,承担拓展佛教的部分责任,即是佛教的大幸。而且处在当今极速变化的时代,过去完全由僧人主导的度化工作,已经需要作出改变。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世俗社会中的许多情况已不如以往的时代,许多方面的工作已不适合僧人,逾越复杂的社会结构也并非是僧人所能完全理解的。
因此,当寺院受政治、经济等力量左右,及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信仰纯正、坚守戒律的僧众数量减少,僧众的佛学素质、人格素养每受诟病之时,居士佛教却逐渐在佛教发展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佛教的发展若除却了居士的贡献,将不会是如今的局面。
(四)团体的大量成立
韦伯认为佛教欠缺“耆那教所创造出来的那种俗人的共同体组织”,而“只有修道僧组织”,乃是佛教未能像印度教那样深深植根于印度文化,“不敌印度教诸正统与异端教派的竞争,在印度本土消失的原因”[21]。姑且不论韦伯的论点是否完全正确①佛教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僧人的宗教,而是出家与在家“四众”兼备的宗教。,但在现代宗教多元竞争形势下,我们尤应吸取这一教训,因为“俗人的共同体组织”(即独立居士团体)与僧团的共同配合,才是佛教的整体,才能适应当代的社会发展。
《六祖坛经》记载:“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这明确地提出了居士也一样能居家修行而达致清净的境界,也是大乘佛教重视心法、积极入世、超然于形式和教条的思想境界的体现,更是居士佛教得以形成的理论基础之一。对于居士团体的设立之必要性与意义,太虚大师有这样的看法:“……都摄正信佛教之在俗士女,期与出家众相辅而行者也。……然正信佛教之在俗士女,所以不可无会者,凡教化之行,皆期普及,出家僧但住持佛教之一种特殊徒众,欲期普及之化,必都摄乎正信佛教之在俗士女而后圆满。…建会以都摄此佛教之正信徒众,庶足以正佛教徒之名而明信佛者之系统。不然者,佛教徒仅寥寥之出家众,其何以见佛化之大,复何以任佛化之重哉?……其利益可得而言矣:杜异道之凌乱,持正信之系统,一也。广佛教之徒众,大佛化之事业,二也。互相资助以收研究切磋发明光大之益,三也。拥卫僧仪,护持佛宇,辅进净德,屏蔽凶邪,四也。和光同尘,遍住于种种流俗之内,宣传正法,讲演真理,以醒世人之迷梦而减人世之恶业,五也。合群策之力,藉众擎之势,以之体正觉之慈悲,行大士之方便,世间现苦,广为救济,六也。”[22]这为居士团体的成立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社会的发展演化,居士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佛教界对居士的地位及其积极作为的认识与态度也产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而且自古以来,居士即占佛教徒的绝大多数。尤其在佛教信仰盛行的国家和地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中都有居士,虽然他们一般不居领导地位,但他们当中有些往往比僧人的影响力更大。佛教向来肯定居士的作用和影响,大乘佛教典籍中以居士身行菩萨道、成圣成贤的内容很多,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居士积极修证佛法、弘法利生的热忱[23]。
因此,除了前述的缺乏僧人和僧人素质低落的原因,再基于在家修行的可能性及居士团体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原有寺院无法满足宗教需求的情况下,居士界逐渐意识到成立团体、组织居士的重要性。加上学佛和修学佛法非易事,需要有一个方便的管道和有利的环境与条件,尤其是对刚接触佛教者,佛学根机不深,修学经验不足,也缺乏坚定信仰与信念,一个可以让他们上课、听讲座、参与活动和共修的环境显得必要。虽说修行是个人之事,但独修孤学,很容易误入歧途,也不容易提起精进心,而容易懈怠,故佛教会在这方面就发挥着亲善知识、相互鼓励、彼此引导的共修力量。佛教会成为了提供这些条件,让大家通过共修的力量,获得启发和鼓励,如实的实践和贯彻佛法于生活中的最佳因缘。许多人通过了佛教会而接触佛教,也同样通过佛教会来贡献于佛教,没有了佛教会,恐怕马来西亚居士就没有今天的面貌。
自1920年代以后,马来亚佛教界开始积极成立居士佛教团体。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居士团体是成立于1920年的释迦院,它是在一批马六甲峇峇(Baba)族群的努力下诞生的。自此,尤其是马佛青总会成立后,将在全国各地协助成立佛教会或居士林列为其中一项首要的工作,许多居士团体纷纷在得到法师和大众的祝福下成立,以应付僧人的不足。从1970年到1980年的10年间,全国各地便成立了约50间的佛教会,如今马佛青属下便有270个团体会员,而全国至少有近300个佛教会或居士林。这些佛教会配合着僧宝一起展开了接引的工作,为广大的群众提供了接触佛教的机缘的同时,也为佛教居士提供了有利的学佛和实践佛法环境,让居士佛教得到了有力的发展契机。
佛教组织也比寺庙更有渗透力。尤其在马来西亚政府对于寺庙的建立有诸多限制的情况下,佛教组织却能在店屋、商场、住家,甚至“居无定所”的操作。而且以佛教会形式出现,也让这些佛教组织摆脱了一些传统的束缚,包括无须出家众当主持,这其实也因此解决了我国缺乏出家人的问题[24]。
(五)经济发展
上世纪50、60年代,是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步入经济现代化的时代,马来西亚在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的优势下,也开始在经济上得到长足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也日渐从乡村的农业经济,蜕变成工商业发达的都市。社会的转型所带来的城市化,面对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性的异化,从乡村移入城镇的人们,不但脱离了本身的家庭和社区,还“住进”了一个物化、工具化、利益化、孤独的社会中,在崇拜物质财富的现实当中,人们陷于无止境的物欲追求。但,经济物质的发展,表面上是繁荣的气象,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生活却失去了依托。80、90年代国家经济成长更是快速,也更全球化,但同时也更加剧了“精神真空”的社会现象。
宗教功能论认为,宗教的功能就在于为其信徒提供各种问题的解释,能有效地以其教义使其信徒处理好种种的社会不稳定和心灵不安。与每一个时代相似,现代社会仍对神圣性有着不减的向往,同样希望寻求一个温暖、祥和的心灵皈依处。而佛法的圆融性、慈悲包容、人文主义以及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等思想,恰可填补“不安者”的心灵和精神真空。
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给马来西亚佛教带来了宽松的社会氛围。除了培育出大批的知识佛教青年,可观的宗教资金让佛教会有更优厚的活动基金,能顺利的运作和推动各式的活动,为无数需要宗教解答处理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佛教发挥其宗教功能、安抚失落的人心的机会。近20年来,由于社会财力增强,很多佛教会得到翻修、扩建,并修建了很多新佛教会,让佛教界在硬体和软体上都得到更健全的建设,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因此,经济发展因素所带来的种种正面和负面效应,都让马来西亚获得成长的契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皈依了佛教,并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佛法。从调查报告显示,华人中佛教信奉者的比例从1990年68.3%上升到2000年的76.3%,就是最好的证明。
经济的发达和社会的转型,促进了政治环境的稳定和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能破除传统的迷信,知识分子逐渐“祛魅”并开始思索、学习一种理性的宗教。而且所培养出的大批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已逐渐地获得了相当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成为社会各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这一批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是宗教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佛教界,也形成了“大专佛青“群体,他们以较深厚的知识基础,更能融会贯通佛陀的教义,也更能适应现代化所带来的变化,因此对佛教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进力量。知识佛教徒的出现,也直接地促成了居士佛教的发展。
(六)时代的需要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制度越趋复杂,并非僧人所能适应,也并非所有层面都适合僧人参与。举例而言,出家众不宜从政,但在家众可以从政,本于菩萨道精神,既可以护持佛教,又可以广积福慧资粮。在多元族群和宗教的马来西亚,也有些场合并不一定适合出家僧人出席,尤其是政治色彩较浓厚以及较为庸俗的活动,但在出家众不适合进入的地区,在家众可以提供资源,举办各类艺文团康活动,方便接引大众学佛。
想要在当今的社会有效地度化众生,掌握复杂社会状况和现代人类心理以便应机说法,是现代僧尼应该做到而且是不少僧尼在努力去做的事。但僧众是专才,对一些俗事可能不太熟悉,就如王雷泉所说的:“出家众平素生活在寺院的单纯环境里,对于复杂社会的状况及现代人类心理的理解,未必能掌握。而入世度众,参与现代社会的种种政治、经济活动,又免不了会妨碍僧人的修行实践,从而降低其在教团中的核心地位。”[25]所以若将这些俗事,如与政府官员交往或筹办火葬场、老人院等事,交给有专业训练的居士来办,成效肯定更好。所以推动居士佛教,善用人才,肯定有助于把佛教与现代社会衔接,使佛教成为有活力的宗教[26]。
在马来西亚,虽然没有制度化的传统佛教权威,但是僧伽本身的修学往往有自己的传统,也就有了一定的封闭性,除了有南传、北传和藏传之别,在修持法门上也各有所依。居士却比较能适应现代化的转变而做出适当的回应,而且较少传统包袱,所以能够有比较多的自主性、创造性和开放性,而有较强的能动性发挥本身的特质和贡献。抛下了这些外在的传统形象,居士就能比较自由开放的选择与参与各传统的寺院和修持活动,可以在南、北、藏传佛教的各宗派之间往来,这对于促进佛教各宗各派的融和,减少山头主义及门户之见大有裨益。
居士团体在弘扬佛法上也有许多的方便,许多佛教会的会员都懂得多种语言,积极参与世界性的佛教活动,出版多种语言的佛教刊物,积极地拉近南传与北传佛教的关系,使各传统佛教间的关系更融洽。由于居士团体的方便,他们可以积极地在政府的各个单位走动和参与非佛教团体所主办的活动,这让佛教得到官方及非佛教徒的认同[27]。
居士佛教是接引群众的有效工具,居士人多,接触社会的层面广,机会也多。推动居士佛教,在接引新人方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僧众当然也能接引群众,但多一份来自居士的力量,何乐而不为呢?在马来西亚,居士团体接引群众的成绩不俗。由居士佛教接引的新人,都会到寺庙亲近僧众。由此可见,居士佛教有其重要性[28]。
在今日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专业化的社会,想要改善多元和复杂的社会,就必须有更多各个方面的人才,各自在相关的领域发挥所长,才能有整体的效果。《杂阿含经》说在家学佛者,应懂得“方便具足”,“谓善男子善女子种种工巧业处,以自营生,谓种田商贾或以王事、军政两界;或以书蔬算画,于彼工巧业处,精勤修行,是名方便具足”[29]。即说是应该学习各种知识、技术,从事对社会和民众有益的各种职业。在家居士学习各类世间学,可以融合世间法与佛法,接引高级知识分子学佛。在家居士也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在政商文教各领域从事各种行业,掌握各种语文,可以更了解身边同事,有针对性的弘法、出版、编译经论、主办各种活动等。人类的学问,也分门别类,各有专才去开拓钻研。佛教的僧众,是多种专才中的一种。这种专才,主修佛学内明,主要的工作是教育群众。其他领域的专门学问与工作,谁来负责呢?当然是要广大的居士来承担了。
而且面对严峻的现实,佛教不论是为了本身的发展,还是为了众生的利益,都必须正视各种社会问题,如政治、教育、文化、经济、宗教等世俗事务和制度,必须关注这些社会现况的制定和发展,必要时更应该直接参与其中和为本身的权益发言,积极争取该有的权利。如果无法参与其中和发言,必然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厄运,同时也会被社会因本身的冷漠而淘汰。因此说,佛教是无法将自己与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和事务隔绝的。
总的而言,居士在当代社会有着出家僧侣所无法达致的优势,对佛教的发展有着积极的贡献,是佛教在面对当今极速转变和转型的社会时,必须重视的一股力量。佛教僧众与居士不同的社会身份,使他们可以更积极和有效地参加社会活动,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发扬佛教的伦理精神,各有针对性地以佛教的根本原则来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因此,有志之居士也本着佛教的根本精神和价值观,推动社会实现更大程度的公正公平,改善并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为建设人间净土筹备资粮。
三、总结
在当今的社会中,难免有部分事情不再适合强调清修的僧人担当,因此“救度”的任务由家人来分担和完成更为恰当和方便[30]。其实从经典而言,这都是有例子可依的。尤其以《维摩诘所说经》中对维摩诘居士的描写便能成为现代居士的典范。该经卷上曾说:“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31]为了完成佛教的发展与普度使命和理想,《维摩诘所说经》便成为了居士们入于酒家、奔走官家的理论依据。也因为居士对戒律的严守的要求,自然没有出家人那么严格,而更为适合在这方面,与在家众携手完成度众的工作。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从长远发展的蓝图来看,僧人素质的提升,僧团的健全及其功能的发挥,仍然是整体佛教发展的必须基础。唯有出现更多有素质的僧人,佛教未来的发展才是光明的[32]。这一方面的工作,不能只落在僧人的身上,无论是个人还是强大的居士团体,都必须给予配合,方能达致效果。
假如居士佛教兴盛,人人在当居士时已打好学佛基础,如果部分良好素质的佛教徒,依于根性,向往出家而加入僧团,在成为僧团成员后,自然也能成为有素质的僧人。当今世界佛教,有不少年轻僧才,就是居士佛教培育出来的[33]。因果是互为影响,佛教社群的各个部分都是互辅相成的。当僧团的素质得到提升,自然的也将提高佛教的形象;有素质的僧伽,也能教育出掌握佛法的佛教徒。
虽然有人担心居士佛教过于蓬勃,将影响僧人的地位,这一点在马来西亚僧界也有人提及。但是印顺法师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要求出家众不要担心在家菩萨僧的发展,他相信:“如果出家众自身健全,深入佛法而适应众生,那一定会与在家佛教携手并进,而且在佛教中,始终会居于领导地位的。”[34]诚如印顺法师所言,出家人如果掌握了高深的学问,具有高尚的品格和慈悲精神,他们仍然是众生的精神象征。
马来西亚现代佛教的发展,从殖民时代至今,居士在其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如此,仍是居士和僧人共同配合的成果。未来的发展,也应该是僧人与居士共同的努力,才能共同成为娑婆渡舟,度化更多的众生,远离此岸的烦恼,获得彼岸的清净。
[1][16][32]继程法师.爱护僧青年,摄受辅导·僧青年自爱,精勤求进[A].建设马来西亚佛教[C].槟城: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文化委员会,1996.p59,p59,p139.
[2][27]John Blofeld.Mahayan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M].Singapore:Donald Moore for Asia Pacific Press,1971. p40~41,p15.
[3]杨惠南.佛教思想发展史论[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8.p86.
[4]陈支平.福建宗教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p255,p267.
[5]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M].廖世德,译.台北:文殊出版社,1987.Welch,Holmes.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64.
[6][7]竺摩法师.荡执成智·真空妙有——五十年来的槟城佛教[A].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C].槟城:光华日报,1960. p229,p238.
[8]孙劲松.略论居士对佛教寺院的监督共管[M].“宗教与法治——宗教组织的管理”学术研讨会,2007.
[9][26][28][33]洪祖丰.居士佛教的时代契机[A].居士佛教面对廿一世纪的挑战——第一届世界居士佛教论坛论文集[C].沙捞越:古晋佛教居士林,2005.p179,p180,p181,p178.
[10]邓子美.超越与顺应:现代宗教社会学观照下的佛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1]Venerable Sumangalo.Sleeping Buddhist[J].无尽灯,1958(7-2):p30.
[12]显扬圣教论(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册.
[13]TeohEngSoon.MalayanBuddhism:ACritical Examination[M].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Ltd, 1963.p44.
[14]魏书·释老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1986.
[15]旧唐书·狄仁杰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1986.
[17]宋立道.传统与现代化:变化中的南传佛教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p310.
[18]释继尊.佛法的现实本质[J].法露缘,1994(17):p2.
[19]转引自宋立道.传统与现代化:变化中的南传佛教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p317.
[20][23]白玉国.马来西亚华人佛教信仰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p103,p103.
[21]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II[M].康乐,简惠美,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85.p371~372.
[22]太虚大师.佛教正信会缘起[A].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p1031.
[24]廖国民.马佛青总会对建设马来西亚佛教的贡献和展望[M].古晋佛教居士林:50年马来西亚佛教论坛,2007.p2.
[25]王雷泉.将终极托付给历史[A].闻思:金陵刻经处130周年纪念专辑[M].南京:金陵刻经处,1997.p49.
[27]John Blofeld.Mahayan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M].Singapore:Donald Moore for Asia Pacific Press,1971.p15.
[29]杂阿含经(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册No.99.
[30]杨惠南.佛教思想发展史论[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8.p86.
[31]大正藏(卷一四),p539.
[34]印顺.教制教典与教学[M].台湾:正闻出版社,1992.p90.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y Buddhism in Malaysia
Tang Chew Peng
(General Studies Centre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Malaysia)
Lay disciples and lay Buddhist organizations play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ian Buddhism.Lay Buddhist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Malaysian Buddhism.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is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order to have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ian Buddhism.
layman;monks;Chinese Buddhism;lay Buddhist organiz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B94
A
1671-6639(2016)01-0048-07
2016-02-25
陈秋平(1970-),男,博士,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助理教授,通识中心主任。①在马来西亚,居士团体一般被称为佛教会或居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