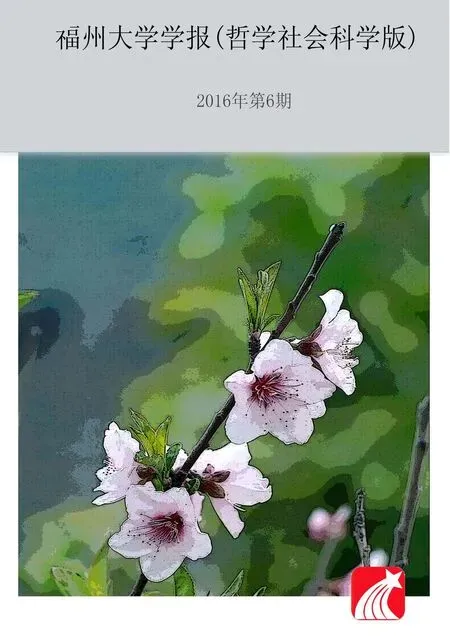“悲情”传统的再叙及其困境——新世纪以来台湾六年级作家小说之认同观察
陈舒劼
(福建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所, 福建福州 350001)
“悲情”传统的再叙及其困境
——新世纪以来台湾六年级作家小说之认同观察
陈舒劼
(福建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所, 福建福州 350001)
新世纪以来,台湾六年级作家在“悲情”主题的历史传统与文学传统下展开新的书写。这批小说较为普遍地调动了隐喻的修辞手段,保持对历史及其叙事的质疑。被质疑的历史得不到认可,又进一步增添了这批小说压抑、怨恨或隔膜的情感。“悲情”叙述陷入认知与情绪的自我循环,有其思想缘由。身份认同兼有历史性和流动性、决定性与模糊性,以及选择空间的理性多元与选择路径感性偏执的可能,要克服台湾“悲情”的偏执乃至“悲情”本身,需要超越个体情感体验的限度,回到完整的中国历史母体之中。
六年级作家; 悲情传统; 台湾文学
“昨日被压抑的一切,他日必定带着更强大的力量反扑。”[1]这句斩钉截铁的判断出自台湾六年级作家张耀升的小说集《缝》,然而不仅是《缝》,其他台湾六年级作家[2]的文本如甘耀明的《杀鬼》《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童伟格的《王考》、许荣哲的《迷藏》、王聪威的《复岛》、纪大伟的《膜》等等,都或明或暗地涉入了这种情绪强烈的昨日重现。群体现象意味着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持续压迫,读过这批文本的读者会迅速联想起台湾文学乃至文化中的一个高频率出现的词汇:“悲情”。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如何理解、如何重述萦绕在台湾文学上空的“悲情”,其重述在何种历史传统中展开,展现出怎样的文本面貌,得到了哪些文化因素的支撑,面临着怎样的认同困境,又拥有哪些可以克服“悲情”的资源和路径,许多问题接连而出、期待回答。
一
通常意义上,“悲情”就是指悲伤或令人悲伤的情感。相较而言,台湾文学文化中的“悲情”更强调这一词汇包含的历史因素及其强大的文化能量,“悲情”往往是表达历史认知的情绪起点,同时也成为认同立场选择的重要参照。有研究指出,“台湾文学的悲情情绪的根源,可以追述到明末”。从明末开始,台湾“一再重演着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对立(明末遗民与清廷的分庭抗礼,1949年以后两岸的对峙),以及南宋时代国土分裂(甲午战败被清朝割让给日本)的悲剧……这一点使得台湾文学始终难以摆脱与民族和政治的双重认同相关的移民或遗民色彩。它一方面背负历史遗留下来的苦难,另一方面为这种苦难进行着充满了悲情的救赎。”[3]经历了荷兰殖民者、郑成功集团、清朝、日本殖民者、国民党政府的更替之后,“悲情”饱含着对历史的质问:为何台湾总是陷于“抗争—失败—臣服—被抛弃”的循环之中?从明末被荷兰殖民者侵占到1945年光复,台湾“悲情”的历史长达三百余年,这其中1895年的乙未割台和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尤为重要,[4]“二二八”事件几乎成为台湾文学历史主题中绕不开的元素。若将“悲情”意识在当代的再生产也考虑进去,那么2000年台湾的政党轮替则是第三个值得注意的时间点,它是“生产遗民—废人或遗民—孤儿反复重现的非常历史时刻”,是明朝覆亡、甲午战败、乙未割台、日本投降、民国沦亡这一系列台湾重大历史转折上的节点。[5]“悲情”涉入了从历史到当下、从情感到认知、从国家到个人等诸多层次,但它归根结底是历史的产物。具体地说,是台湾历史甚至是东亚近代史结构性变动的产物。
乙未割台是“悲情”传统中的重量级事件,许多文本对此作出回应。《杀鬼》尾声时写到,“统领死前要刘金福挖下他的眼睛,放在彰化城墙上,终会看到日寇退出台湾的一天”[6],明显与施士洁《别台作》其三的名句“逐臣不死悬双眼,再见英雄缚草鸡”遥相呼应。但乙未割台首先是近代东亚政治格局大变动的表征,从此以后,台湾与大陆的认同关系日益复杂,并成为冷战在东亚的重要节点,台海关系与中美关系的交错、朝鲜战争中台湾的位置、历史上和现实中台湾与日本的关系等等,都表明了台湾在东亚政治格局中的特殊。[7]造就“悲情”的特殊和复杂源于历史,当这段特殊而复杂的历史移入文学之后,形成了另一种文本的历史,亦即文学上的“悲情”台湾。
追溯台湾“悲情”文学的传统,就不能不提到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这部在当时冒着生命危险而写的、现今看来文学性并没有多么出彩的小说之所以成为台湾文学的经典,还是要归功于其文学史价值。《亚细亚的孤儿》尽量贴近历史原貌的朴素的现实主义观念,至少在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来者的叙述。一是身份认同的焦虑,即“我‘究竟’是谁”的问题。陈映真的《忠孝公园》集中了多种身份的近代史经历者,其中代表台湾政坛主流的蓝绿阵营中的人物都走不出“我‘究竟’是谁”的困惑。有国民党特务背景的马正涛背负着历史的血债,在政党轮替后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全部丧失了意义,“他成了坠落在无尽的空无中的人。他没有了前去的路途,也没有了安居的处所。他仿如忽然被一个巨大的骗局所抛弃,向着没有底的、永久的虚空与黑暗下坠。”[8]相比于马正涛自杀,曾经作为日军中的台湾兵参战的林标最后发现,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群体从来没有得到过日本的承认,从来就没有获得真正的主体身份。小说结尾处,林标哭嚎着反复用日语追问“我是谁呀——”“我到底,是谁呀——”。这撕心裂肺的声音传播开来,在施叔青的《三世人》里产生了回声。参加过“若樱敢死队”的施朝宗毁掉过国民身份证也毁掉过日本姓氏的身份证,他同样是在小说结尾不知栖“身”何处:“他在几种不同的身份里变来变去。‘这个人是我吗?’‘这个人不会是我吧!’”[9]以“朝宗”命名的人不知“宗”为何物,历史的“悲情”悄悄地隐身于揶揄之后。二是来回往返于不同空间的叙述架构。《亚细亚的孤儿》的主人公胡太明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之间来回往返,始终没有找到归宿感,但他的足迹几乎就是近代史上三地间文化关系和政治形势的拓片。在台湾,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可以看成是这种叙述架构的放大,而在大陆,林那北的《我的唐山》也保留了这种历史架构的完整性。1970年代出生的年青作家涉及此主题之时仍然必须尊重该历史架构的主体性,如王聪威的《复岛》尽管启用了后设式的叙述方法,但仍无法跳脱由不同空间构成的历史张力。南方朔推荐《复岛》时更将这种空间/地方间的关系,转化为时间性的隐喻:“它所意指的不就是现在、未来与过去交互影响的那种蒙昧力量吗?”[10]要厘清台湾的“悲情”,文学依旧必须返回这个东亚的近代历史进程之中。此时回头再看《亚细亚的孤儿》,更显意味深长。“吴浊流以‘亚细亚的孤儿’命名台湾的处境,明显的把台湾摆在亚洲地缘政治的架构里,这使得内在的结构性的认同分化更形严峻。因为它们(如统独)拥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却被摆在不可趋及的未来,无限后退的非现在。这样的历史位置,从被殖民状态的中/日夹缝,到韩战后的中/美夹缝,结构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比任何一方民族主义者单纯的政治想象更切实际,也是台湾的忧郁或悲情的历史根源。在亚细亚地缘政治内,祖国认同(中国民族主义),日本认同(殖民皇民遗魂)及八〇年代后的台独认同,难以共量的分歧认同,恰是历史孤儿的处境。”[11]在指明《亚细亚的孤儿》的历史映射功能和认同生产过程中的位置之时,黄锦树的这段话还提醒:到了应该注意已经成熟起来的年青一代作家的时候。
二
进入21世纪,台湾即发生了第一次政党轮替。如前所述,新世纪开启了台湾“悲情”意识的新阶段。许多六年级作家在新世纪跃上台湾文坛,开始形成带有个人风格的叙述美学。“六年级作家”是明显的代际划分观念的产物,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代际划分的方式曾经引发争论。假使承认“将代际研究仅仅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是文学研究多元化的一种体现”[12]的合理性,问题的重心就转移为“为何是六年级作家”?六年级作家是台湾特殊时代的产物。1970年代生人在台湾也被称做“新新人类”,他们基本衣食无忧,摆脱了父辈遭国民党军警围捕的身心压力,在“解严”时代进入大专院校,成长历程贯穿了台湾经济腾飞的黄金年代。[13]他们置身于相对优越的文学生长环境,并展示出在新世纪的十余年中趋于成熟的过程。对于台湾“悲情”的文学考察而言,六年级作家还有着特别的意味。陈映真说,“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斗争,则早在七十年代中晚期就开始了。”[14]六年级作家基本与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的发酵相伴而生,而他们的介入台湾“悲情”的作品已经显现出分离主义思潮之于文学创作的重压,以及重压之下认同的犹疑与徘徊。身处或涉入台湾文学“悲情”传统中的六年级作家,他们看到了什么,又说出了什么?
甘耀明的《杀鬼》《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张耀升的《缝》、童伟格的《王考》、许荣哲的《迷藏》、王聪威的《复岛》、纪大伟的《膜》,这批小说显然不是“后乡土写作”的标签所能覆盖的。它们面相各异,以不同的方式面对台湾的历史传统,而理解台湾的历史传统,又是重述台湾“悲情”不可或缺的要素。大致上,这批小说对它们的前文本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陈映真的《忠孝公园》虽有所继承,但还是开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域。
六年级作家在新世纪的这些文本,较为普遍地调动了隐喻的修辞手段。“参照某种已有的结构来成象、成形、形成概念……用一个具体的东西来比喻不具体的东西是隐喻。”[15]这批小说常常将“悲情”的历史事件隐藏在当代的个体日常生活的背面,并由当代个体日常生活的描摹来勾勒“悲情”历史的内在,凸显“悲情”历史的影响。借由父亲“灵魂衣”的破败和日常生活中对奶奶的虐待,张耀升的《缝》在鬼故事的形式之下隐藏了“如何对待传统”的提问。唯利是图地处理历史传统,却被反噬的传统“缝入现实世界之外”[16],奶奶和父亲的双重悲剧,包含了青年一代对传统被背叛、被割裂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详细地描述了父母对奶奶的厌弃和弃之于阁楼之上的悬置,但并没有交待清楚大逆不道的缘由,这使得隐忧笼罩在历史缺场的情绪之中。相比于《缝》,张耀升的《蓝色项圈》和《友达》这组姊妹小说放手反复渲染国民党在台威权统治所造成的人格扭曲和心灵创伤,“蓝色”和“项圈”这两个高频符号,在台湾政治文化的背景中清晰无比地指向了“悲情”的历史责任主体:在台湾施行项圈般“钳制”的“国民党”。小说里的学校即是福柯笔下的全景监狱,里面每个成绩优秀的学生脖子上都有一条上吊死亡形成的、代表着向鬼魅/专制献祭灵魂的项圈般的深蓝色勒痕。所有的书写/言说,都如阿文信中说的只能写出空白:“笔没水了,每一枝都没水了,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黑的,每一枝都只写得出空白。”[17]甘耀明《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与《蓝色项圈》等相似之处,并不仅停留在同样设置了一个意味着管制和压抑的学校,更要紧的是它们,或者还要加上张耀升的《缝》、许荣哲的《迷藏》、纪大伟的《膜》等等,都将“悲情”置身于具体的历史场景之外,通过种种象征符号及其相互关联的设置来隐喻“悲情”和历史传统的关系。以隐喻的方式回到历史,甘耀明的《杀鬼》似乎是这批小说中的例外,然而其核心意象“鬼”的多重意涵,同样隐喻着“悲情”历史的多层性。
“悲情”的历史是隐喻性的,也是被质疑的。隐喻手段的普遍使用体现了自觉不自觉地与具体历史拉开距离的姿态,这种距离感包含了对历史及其叙述的怀疑和悲观。台湾六年级作家成长的时代,也是西方诸种“后”思潮风靡的时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他们的影响在小说中显而易见。开启了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英美分析哲学奠定了语言的中心地位,在这批六年级作家的小说中,语言成了进入历史的秘钥。“十分明显,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的话,即:对言语所负之责,正是经由想象性的语言,才从纯语言的实体转移到心理的或意识形态的实体上。正因如此,历史‘事实’这一概念在各个时代中似乎都是可疑的了。”[18]当然,是历史秘钥的语言也可能是陷阱,极端而无奈的说法就是许荣哲在《不存在的声音》里说的:“他妈的,我们被骗了一辈子,这是一个诡计……”[19]这批作家的作品中,童伟格的《王考》以质疑历史著称。那个老祖父居然发表了一通明显异于其知识素养和表达方式的宏论:“你还是要记住,文字用你,不是你用文字,因为,文字比你活得久。”当然,文字的记忆也是想象和筛选的结果:“任何畸零不具意义的往事,都自然而然地,被他排除于记忆之外。”[20]这不由令人想起朱天心著名的“我的记忆都不算数”的反问。如果换成《王考》式的思路,那么问题就是,记忆怎么(叙述)才算数?
被质疑的历史得不到认可,没有回声,更添压抑、怨恨或隔膜。如果将历史理解为诸种话语运作机制的结果,那么指向历史的种种质疑、解构或追问就无法产生回声。童伟格《叫魂》的结尾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场景,经历了人鬼相混的乡村魔幻之旅后,吴伟奇将自己的自行车停在象征着历史交汇点的“小路与大马路交接的三叉口”,此时“他看见,远远的地方有个身影向他走来,但天黑了,他辨不清那身影是谁。他扯起嗓门,一一呼唤所有他记得的名字,真实的、虚构的,死的、活的,神、人、鬼、兽,他想,无论如何,那身影,总不会吝于回应他一声”,饶有意味的事情就此发生,偏偏“四周安静极了”,随即“什么东西掉在吴伟奇肩膀上,吴伟奇回头一看,是李国忠的手。”[21]历史没有如吴伟奇坚信的那样回应他的召唤,它无声却主动地找上门来,就像小说中吴伟奇死去的老师李国忠那样,一只手“掉在”召唤者的身上。小说的题目“叫魂”虽可理解成呼唤逝者之魂,但更是呼唤历史之魂。历史模糊不清、频遭质疑、吝于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悲情”。当然,六年级作家小说中的“悲情”主要还是历史无声、或说无法有效进入历史所带来的负面情绪:压抑、怨恨或隔膜。《蓝色项圈》和《友达》的压抑怨恨之情溢于言表;童伟格的《我》中说,“应该觉得轻松快乐的时候,我只觉得,很难过”[22];纪大伟《膜》借科幻的外衣暗示,历史的隔断是形成人与人隔膜、主体记忆偏执化的主因:“她不能真正地与人亲密,有一种非常细微、难以解释的格格不入”,“她厌恶任何牵涉手术的回忆”[23];郝誉翔也指出,甘耀明看似繁复而华美的《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等小说,实质上是“脱离不了死亡的阴霾”的“一座黑色的乐园”[24]。得不到认可又没有回声的历史,进一步加重了“悲情”的文化情绪,从而完成了“悲情”的自我再生产,逐步陷入更深的涡流。
三
六年级作家“悲情”叙述的规模化出现,除了传统惯性的因素,还另有其思想上的缘由。“悲情”问题的核心是身份认同,新一代作家进入“悲情”主题的文学再叙述,某种程度上就是表达身份认同再选择的思考。也正是为此,六年级作家处理历史时的隐喻、质疑和种种负面情绪,就必须回到文学的思想空间中来澄清。大体上说,六年级作家“悲情”文学再叙述的隐喻、质疑和种种负面情绪,至少有这三方面的理解路径。
首先,身份认同兼具历史性和流动性。身份认同始终是萦绕在当代台湾文学乃至文化空间中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分离主义思潮明显抬头并涌入了文学场域。李登辉上台后着力推动分离主义的发展,“与这种情势相适应的是,在台湾文学界中一种新的动向出现了。有人有意强调‘台湾文学’的特殊性,而与‘台独’的分离主义相呼应。这种动向,到90年代愈演愈烈。”[25]对于当时尚处思想成长期的六年级作家来说,分离主义文化思潮是分析六年级作家新世纪文学创作不可忽视的因素。历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做“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原本是个伪命题——台湾人就如同福建人一般属于中国人,这是台湾文学身份认同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和文化基础。当然,台湾身份认同在近代以来产生了很大的流变。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的奴化教育以及国民党政权退入台湾后长期的反共宣传,为台湾分离主义思潮提供了土壤,加上国民党政权自身的弊端,“台独”认同日渐滋长。有研究指出了“台独”认同产生的四个原因,一是国民党迁台后统治集团与台湾人民的矛盾被阐释成“省籍矛盾”;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台湾人民在特殊历史境遇中形成的本土认同缺乏理解和尊重;三是国民党政权“法统”地位饱受质疑,公信力不足之后民众就容易为分离主义所诱导;四是海峡两岸长期隔绝,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都差异明显。[26]虽然日本殖民等文化影响的确客观存在,但不能就此否认更为源远流长、广阔宏大的中华文化传统。确切地说,由日本殖民文化影响而产生所谓的“台湾主体性”更是荒谬的。“当代语境中的所谓‘台湾主体性’与现代台湾为摆脱台湾殖民性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非但没有历史的联系,而且更是以割断或扭曲这一联系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台湾在美国冷战体制中的战略地位的转变为契机,通过承认‘双战’构造造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为前提的。”[27]克服冷战与内战“双战构造”下顽固的台湾分离主义意识,不仅需要更宏观清晰的历史构架,而且需要超越个体生命长度的大情怀。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六年级作家,如果不能跨过个人生命体验而进入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文化的整体近代中国史,就只能满怀犹疑地用隐喻和质疑来试探着进入历史。
其次,身份认同兼有决定性与模糊性。所谓决定性,是说身份认同事关“我是谁”的自我识别,这种识别不仅用于区别自我和他者,它还为自我价值的实践提供依据。“我们必须努力给我们的生活以意义或实质,而这意味着不可逃避地我们要叙述性地理解我们自己。”[28]查尔斯·泰勒就认为,认同问题构成了社会与道德哲学的中心。弄不清“我是谁”的问题,就难以进入公共文化空间的讨论,并在话语中呈现清晰的伦理立场。但与此同时,这种至关重要的身份认同又不是每时每刻都必须挂在嘴边的。回避身份认同的历史政治面相的文学作品不在少数,大陆文坛1990年代后出现的身体写作、情感写作、物欲写作等等,都刻意逃离历史政治的叙述框架,无论这种逃离是否最终落入另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偏激。与此相似的是台湾社会近年来流行的“小确幸”观念。“小确幸”是面对历史沉积产生的无意识反应:既然历史总是带给台湾“悲情”体验,那么避开历史的阴影而投入现实的细琐与自娱,就显得顺理成章。“小确幸”暂时隔离了“我是谁”的认同烦恼,在摆脱“悲情”意识后不断自我膨胀,最终顺畅地滑入了自恋的幻境,“当恋物者恋着自己的所恋甚至恋着自己的恋的时候,恋物的文化便成为自恋的文化。”[29]然而,这种隔离就像不考虑疏通水道的筑堤防洪,只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再次,身份认同拥有理性的多元选择空间,却往往落入感性的执守。吴浊流一代的“悲情”浓缩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悲剧,沉重且深刻。数十年之后,台湾六年级作家不约而同的“悲情”却多少显得偏执,这些文本聚焦于日本奴役时代的“殖民进步”、国民党统治后的“威权”与“恐怖”、“本土”与“外来”,却忘记了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中更有身份认同决定性意义的史实。忽略中华传统的文化母体,台湾六年级作家的“悲情”就像老太太固执的絮叨。随便举一个例子,陈映真认为“‘二二八’蜂起的原因,不是什么日本制的‘现代化’台湾和‘前现代’的农业的中国社会的矛盾,而是战后全中国人民呼唤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反独裁新民主主义国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30]为什么这批六年级作家的文学叙述放弃了这种“悲情”之外的认知可能?童伟格坦言自己在从《假日》到《王考》的系列文本中寻找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我想要知道事情表面底下的线索,我以为,藉由联系这些线索,我也许有机会建立起‘另一种事实’,这种‘事实’,也许当时间都——如您所指出的——‘离散’了,它还在,一直都在。”[31]问题是,这“另一种事实”同样也是后设选择的结果。六年级小说家们的“悲情”看到了“殖民”“进步”的一面,却看不到台湾义勇队和雾社起义。
四
六年级小说家的这批文本,既希望进入历史找到叙述“悲情”的新资源和新空间,却又害怕重返会看到他们“意料之外”的历史,模糊美学、魔幻叙事、解构姿态的流行因此不足为奇。从总体上看,这批文本的“悲情”叙述没有挣脱“新台湾史写作”的意识形态牢笼。“新台湾史写作以省略和扭曲的叙述策略,遮蔽台湾左翼传统的历史脉络及其对民主运动的历史贡献,重构台湾的悲情”,具体而言包括三点:“首先,通过抬高日本殖民统治的‘文明程度’或‘现代化水平’,将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置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对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优越感;其次,通过日本殖民统治与‘二二八’事件的对比,实际上为‘皇民化’开脱,进而将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怀旧’组织到‘台独’的氛围之中;第三,尽管存在少数对中国革命和革命中国持同情和理解态度的人,但用美式自由主义包装冷战与后冷战的台湾政治结构,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切断台湾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连带,却是台湾史叙述的主流。”[32]只有超越个体情感体验的限度,回到近代以来东亚政治结构巨变的历史现场,回到冷战与内战“双战构造”生成的历史逻辑,才能完整地挖出“悲情”历史性的根源,找到克服“悲情”的可能。就此而言,六年级小说家可能碰触到了某些历史节点——但也仅仅停留在“触碰”的程度上,甘耀明的《杀鬼》就是典型。
反映1940至1947年间台湾殖民史的《杀鬼》,其被“魔幻”叙述包装的“悲情”不过是用于佐证割裂历史后的“分离主义”意识形态表述。比尔·阿希克洛夫特等人认为,“后殖民”一词涵盖了自殖民开始至今所有受到帝国主义进程影响的文化,而它关注的是“自我与地方关系中的有效身份认同和恢复”。[33]然而,“有效身份认同和恢复”的关键还是在于回到历史的结构和真相之中。在此意义上,被视为新世纪以来台湾六年级作家写作中“后殖民”文本的《杀鬼》,其含混而充满魔幻气息美学风格值得让人驻足。主人公帕1940至1947年间经历的展开过程中,日本殖民几乎全是正面的历史遗产。艾勒克·博埃默眼中的后殖民写作带有强烈的历史批判色彩,力图在对殖民统治及其象征符号体系的铲除中恢复被扭曲的自我认同:“后殖民”文学并不是帝国“之后才来到”的文学,而是指“对殖民关系作批判性考察的文学。非殖民化的过程不仅是政权的变更,也是一种象征的改制,对各种主宰意义的重铸。后殖民文学正是这一改制重铸过程的一部分。后殖民作家为表现殖民地一方对所受殖民统治的感受,便从主题到形式对所有支持殖民化的话语——关于权力的神话,种族的等级划分,关于服从的意象等统统来一个釜底抽薪。因此,后殖民文学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它对帝国统治下文化分治和文化排斥的经验。”[34]《杀鬼》虽回到了“悲情”诞生的历史现场并直接介入了“二二八”事件的再描述,也的确展示了“帝国统治下文化分治和文化排斥”的经验,但正如赵刚所追问的“在过去十多年间,何以众多的所谓‘去殖民’书写,都那么轻松、无理地把日本给放掉了”?[35]《杀鬼》有展现台湾乡土经验、抵抗情节的一面,这一面总是充满“奇观性”地令人发笑;《杀鬼》更有展现日本殖民现代性的一面,而这一面无论是东瀛器物的功能还是人物的精神,都令人艳羡、晕眩和拜服。帕明确地表达过自己的认同困惑与“悲情”:“多桑,我那么努力当个日本人,努力当你的儿子。好的时候就是好,可是,为什么做错事,我就变成清国奴,就是支那猪?难道再努力,我在你眼里还是永远成不了日本人?”[36]在这样的背景下,“杀鬼”这个标题就很不一般。“杀”的是什么“鬼”?表面上看,帕既杀了象征着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鬼中佐”,也杀了作为抵抗军头领的“鬼王”,然而“鬼中佐”是“形散神不散”,而一直作为非物质形态存在的“鬼王”却魂飞魄散了。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杀完“鬼”之后的帕仍然不知所措,被动地等到“天亮才起身”,“可是离天亮还很久呢!”[37]甘耀明自白:“这鬼不是阴魂之类,而是内心的迟疑与彷徨”[38],但至少帕的行为表明,这“鬼”至少目前杀不了。
陷于“悲情”无法解决问题。“从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寻找台湾人重新再作中国人在历史上、现实上、以及心理上的的合理性”,“才能心安理得地作台湾人”,[39]抚慰此起彼伏的“悲情”。换句话说,摆脱“悲情”需要有“一种进入自身实际所从出的历史来理解自身的能力。”[40]文学是这种能力的表现场域,也是这种能力建构的重要渠道。文学叙述所携带的认同不是高端武器,无法产生即时的威慑,可认同一旦深根,又绝非高端武器所能夷平。有时看似记忆“在和你玩捉迷藏”[41],但历史总在那里:“一再地改造或修补过去的历史,然而当现在被挖掘开来了,或是崩塌了,就会重新露出过去的事物陈迹,无论现在是如何的遮盖,均无法掩饰过去,无论是实体的纪录或是人间的想法与概念。”[42]克服被意识形态偏见所挟持的“悲情”,虽然迟到,但终究会来到。
注释:
[1] 张耀升:《洞》,《缝》,台北县新店市:木马文化出版,2003年,第195页。
[2] 所谓“六年级作家”或“六年级生”是台湾文学界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的称谓,同样的说法还有“七字头作家”等等,都是从论述方便的角度而言。
[3] 黎湘萍:《文学台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3、44页。
[4] 朱双一认为:“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却是所谓台湾‘悲情’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源头是乙未割台)。”见其论文《光复初期台湾社会诸种矛盾辨析——从文学看台湾民众的“悲情”和认同》,《穿行台湾文学两甲子:朱双一选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
[5] 黄锦树:《游魂——亡兄、孤儿、废人》,《文与魂与体:论现代中国性》,台北市: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342页。
[6][36][37][38] 甘耀明:《杀鬼》,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第398,92,414,418页。
[7] 孙 歌:《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30页。
[8] 陈映真:《忠孝公园》,《忠孝公园》,台北市:洪范书店,2001年,第220页。
[9] 施叔青:《三世人》,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269页。
[10] 南方朔:《一本不要轻估的地志风土作品》,王聪威:《复岛》,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7页。
[11] 黄锦树:《游魂——亡兄、孤儿、废人》,《文与魂与体:论现代中国性》,台北市: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336页。
[12] 文学研究“代际视角”的讨论,可见洪治纲的《文化视野中的代际差别》,该文归纳了学界对代际划分的诸种质疑,并给出了三条为“代际划分”辩护的意见,详见洪治纲:《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30页。
[13] 心 言:《台湾新崛起的“新新人类”》,《华人时刊》1996年第1期,第27页。将70年代生人划分为“新新人类”的说法还可见朱双一:《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战后新世代”文学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0页。
[14] 陈映真:《论“文学台独”》,薛 毅:《陈映真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45页。
[15]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3页。
[16] 张耀升:《缝》,《缝》,台北县新店市:木马文化出版,2003年,第24页。
[17] 张耀升:《蓝色项圈》,《缝》,台北县新店市:木马文化出版,2003年,第129页。
[18] [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59-60页。
[19] 许荣哲:《不存在的声音》,《迷藏》,台北市:宝瓶文化,2002年,第198页。
[20] 童伟格:《王考》,《王考》,台北县: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21页。
[21] 童伟格:《叫魂》,《王考》,台北县: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49页。
[22] 童伟格:《我》,《王考》,台北县: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66页。
[23] 纪大伟:《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24] 郝誉翔:《华丽而幽暗的童话国度》,甘耀明:《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台北市: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第9页。
[25] 赵遐秋:《评台湾文学中的分离主义倾向》,《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1期。
[26] 刘登翰:《“台独”文化理论评析》,《海峡文化论集》,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7-308页。
[27][32] 汪 晖:《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3,11-12页。
[28] [加拿大]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 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29] 江弱水:《陆客台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30] 陈映真:《警戒第二轮台湾“皇民文学”运动的图谋——读藤井省三〈百年来的台湾文学〉:批评的笔记》,薛 毅:《陈映真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62页。
[31] 童伟格:《暗室里的对话》,《王考》,台北县: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202页。
[33] [澳大利亚]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34]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 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3页。
[35][40] 赵 刚:《以“方法论中国人”超克分断体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4期(2009年6月)。
[39] 郑鸿生:《台湾人如何再作中国人——超克分断体制下的身份难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4期,第96、135页。
[41] 许荣哲:《迷藏》,《迷藏》,台北市:宝瓶文化,2002年,第39页。
[42] 王聪威:《复岛》,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76页。
[责任编辑:陈未鹏]
2016-03-18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台湾文学研究”(FJ2015JDZ020)
陈舒劼, 男, 福建长乐人, 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文学博士。
I206.7
A
1002-3321(2016)06-006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