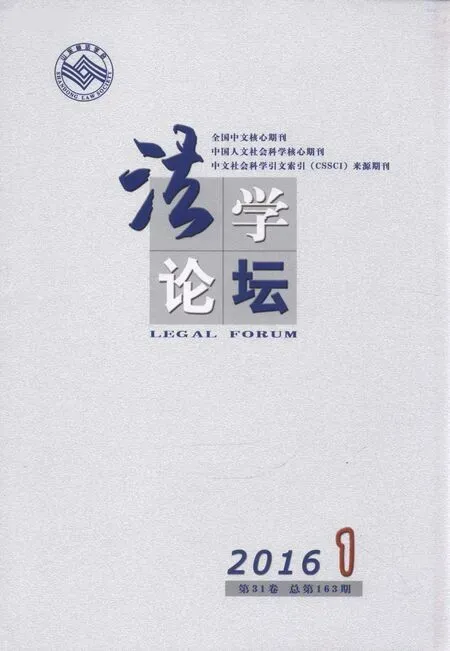晚清两个《人权宣言》汉译本的考察
程梦婧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5)
晚清两个《人权宣言》汉译本的考察
程梦婧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5)
摘要: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自晚清传入中国以来,各个时期出现了不同的中文译本。1903年“小颦女士”的译本,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是《人权宣言》。但在晚清,有两个全译本极为重要,即1907年的“川”本及1908年的林万里、陈承泽本。通过比较,两个译本在序文、名称及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其中,“川”本不乏一些“误译”的内容。“误译”的原因是多样的,译者“川”可能受到语言能力、翻译目的及社会需求的影响。然而,即使“川”本存在“误译”,晚清两个《人权宣言》汉译本的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人权宣言》;晚清;翻译;误译
西方思想、学术与制度、法律在晚清的输入,是与译书直接关联在一起的。一个国家、民族,要想了解、学习和研讨别的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经典和法律制度文本,必须借助于翻译这一极为重要的工具。在晚清中国,面对1840年以来国门洞开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危象与困局,一些敏锐的学者深刻认识到:“当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然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言互异,欲利用其长,非广译其书不为功。……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吾国于强盛之域。”*周树奎:《译书交通公会序》,载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7页。因此,“译书之宗旨”,就在于“输入文化挽救衰亡。”他们指出:“两群相遇,欲互换其智识,则必译书。……然则今日之支那,其以布帛菽粟视译书也审矣。”*《论译书四时期》,载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2、60页。而梁启超尤其将翻译西方著作视为救国启蒙的一大关键。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法国《人权宣言》(特指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被逐步译介到晚清中国,从而让中国人得以见识《人权宣言》的真实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原则。笔者目前所见,《人权宣言》在晚清主要有两个汉译本:其一,1907年,署名“川”的人将《人权宣言》译为《法国宪法人权十七条译注》。 “川”不仅对《人权宣言》逐条进行翻译,而且对其作出了自己的注解。其二,1908年,林万里和陈承泽将《人权宣言》译为《人权及国民权宣言》。该译文系德国耶利内克之著作《人权宣言论──近代宪政史研究析论》第五节的内容。美浓部达吉先将其从德文译为日文,后由林万里及陈承泽转译为中文。
本文旨在对《人权宣言》在晚清的两个汉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当然,每位译者对《人权宣言》的翻译及用词都各不一样,且各具特色。因此,本文的内容并非是对两个晚清时期的翻译文本的简单罗列,而是致力于比较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体现出两个文本各自的价值。其中,甚至不乏一些“误译”的内容。对这些误译,本文也加以讨论,目的在于将这些误译与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相联系,挖掘其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在此之前,笔者先进行一个纠误,即人们对1903年上海支那翻译会社出版“小颦女士”所译的《法兰西人权宣言》的错误认识。史料证明,该译本并非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
一、“小颦女士”译本并非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
从目前所知所见的材料来看,晚清士人对《人权宣言》的翻译,集中出现于20世纪初的十一年(1900年至辛亥革命前)间。不论是零散的译介,还是全本的汉译,在这十余年中,都有前所未见的突进。这当然与这个时期发生的新政、预备立宪、宪政运动、人权观念的发展以及更大规模的译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人权宣言》的第一个译本是何时出现的?对这一问题,史学界有一个普遍的判断,即从“小颦女士”1903年所译的《法兰西人权宣告书》谈起,认为该译本就是《人权宣言》。然而,“小颦女士”译本是否就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从而成为了《人权宣言》的第一个全本汉译本?对这个问题,不少论著存在误判。章开沅先生在《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一文中说:张于英所编《辛亥革命书征》中有《译文四种》(1903年,内有《法兰西人权宣言》)。*参见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载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72页。这个《译文四种》,就是“小颦女士”所译的《政治思想之源》。而熊月之先生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也非常肯定地认为,1903年上海支那翻译会社出版“小颦女士”所译的《法兰西人权宣言》,就是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该书指出:在《政治思想之源》一书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独立檄文》和《法兰西人权宣言》”。该书进一步解释说:“《法兰西人权宣言》,通称《人权宣言》,全称《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1791年《法国宪法》列为序言。”*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339页。这一判断并未明确认定“小颦女士”的译本,即为《人权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汉译本,但显然认为它是《人权宣言》的汉译本。由此,研究者们在涉及《人权宣言》在晚清的情况时,无一例外地都从“小颦女士”的译本谈起,如冯江峰说:“1903年支那翻译会社印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些西方著作和法律文件的翻译对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精神上的震撼……。”*冯江峰:《清末民初人权思想的肇始与嬗变(1840─19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兰梁斌在《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中,引用方光华的《戊戌变法与中国近现代学术》(《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70页)一文中的叙述,也说在1902至1903年,《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以及各国历史书籍,被大量译成中文(第96页)。这些论文虽未指明其所说的《人权宣言》译本,但可能仍然指的是熊月之著作中提到的小颦女士所译的《法兰西人权宣告书》。熊著说“小颦女士”所译即《法兰西人权宣言》,冯江峰认为其为《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显然都是将“小颦女士”的译本视为《人权宣言》的汉译本,或者认为“小颦女士”所译即为1789年的那份《人权宣言》。
然而,据笔者考察,章开沅先生、熊月之先生以及其他学者的著述,的确判断有误。*笔者在《法国〈人权宣言〉在晚清》一文(《现代法学》2013年第5期)中,也按照章开沅、熊月之、冯江峰的说法,认为“小颦女士”所译即1789年《人权宣言》。笔者的初稿正文中提到:“经过多方搜寻,笔者至今未见中译本《法兰西人权宣告书》”,并注有一个解释:“检索显示,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有《政治思想之源》一书的索引,但却被告知:或者“无法提供”,或者库中无此书。经请陈刚教授协助查询,在所查日本的一些图书馆中,未见该书。此外,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吴运筑及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任洪涛在中国台湾交流期间,在一些图书馆查找,亦未见该书。”但这个注解在论文正式发表时,未予保留。十分幸运的是,其后在图书馆朋友的大力帮助之下,终于在2014年搜集到“小颦女士”的译本。第一,该译本收录在“小颦女士”的翻译作品《政治思想之源》一书中。该书封面列名《美利坚独立檄文》(即《独立宣言》)、《法兰西人权宣告书》、《玛志尼少年意大利章程》以及《噶苏士戒国人书》四篇。其第二篇的名称标为“《法兰西人权宣告书》”;在其书内(第7页),名称为“《法兰西民主国民权宣告书》”。由此可见,其名称并非章开沅先生、熊月之先生所说“《法兰西人权宣言》”和冯江峰所称“《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二,更重要的是,“小颦女士”翻译的《法兰西人权宣告书》,实际上是1793年法国宪法中的“人权宣言”部分,由“序言”和35条构成。而且,其《政治思想之源》的第7页,已经在“《法兰西民主国民权宣告书》”标题下,明确标明其时间为“1793年”而非1789年。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时期,关于人权的宣言书频繁公布,所以法国被誉为“人权宣言”的故乡。在这个时期,“且不计影响较小的人权文献(如在人权宣言制定过程中提出的草案),值得充分重视和研究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权宣言至少有四个,即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791年《妇女与女公民权利宣言》、1793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和1795年《人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这四个文献同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并成为大革命人权思想和原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马胜利:《法国大革命中的四个人权宣言》,载《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其中,1793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由雅各宾派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起草的。*罗伯斯庇尔的著作《革命法制和审判》,收录了《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除“绪言”外,共有37条(赵涵舆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6─140页)。1793年7月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共35条,比罗伯斯庇尔的草案少两条,但内容并无大的不同。尽管该宣言吸收了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一些内容,但两个宣言显然各有不同。由此可见,“小颦女士”的《法兰西人权宣告书》或《法兰西民主国民权宣告书》译本,绝非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译本,当是确定无疑的。
二、晚清两个《人权宣言》汉译本的问世
既然“小颦女士”所译的《法兰西人权宣告书》并非《人权宣言》的汉译本,那么,《人权宣言》全译本的出现,还得继续往后追查。仅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这个全译本在1907年诞生了。这就是《法国宪法人权十七条译注》(以下简称《人权十七条译注》)。该译注的作者署名为“川”,译注全文刊登于1907年2月的《申报》。*《人权十七条译注》分三次刊登于光绪33年(1907年)的《申报》,分别为2月17日(西历3月30日)第9版(译序及前言、第1至5条)、2月19日(西历4月1日)第9版(第6至11条)、24日(西历4月5日)第9版(第12至17条)。下文引用该《译注》时,不再注明。“川”在译注之前对翻译《人权宣言》作了一个说明:“地球各国之宪法,除英国外,大半取则于法国。而法国宪法之纲领,全在人权十七条。此十七条人权,系于七百八十九年由国会投票决定而宣布者也。故名之曰人权之宣告。人权者,犹言人人应有之权利也。此权利系天赋者也。既为人,既为国民,皆有此权利。今特释之如下(原为‘如左’,今改为‘如下’──引者注)。”这一译文的译注者“川”,到底是什么人,无法加以查考;译文是从法语直接翻译为中文,还是由日文或其它语言转译,也无从知晓。但是,这一译注无疑是中国人权史上极其重要和十分珍贵的史料。
1908年,又出现了另一个《人权宣言》的全译本,即《各国宪法源泉三种合编》第一编“人权宣言论”中所含的《人权宣言》条款。*全部条文见[德]挨里涅克原著:《各国宪法源泉三种合编》,[日]美浓部达士原译,林万里、陈承泽重译,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版。根据该书日译者美浓部达吉博士的“原译小引”,该书为德国公法学教授挨里涅克(美浓部达吉译为“哀犁难克”,今通译“耶利内克”)的原著。其中,《人权宣言论》(全名《人权宣言论──近代宪政史研究析论》)发表于1895年,尽管只有“五十三页”,但所论“皆为前人所未发”。中国福建侯官的林万里和闽县的陈承泽,又将美浓部达吉的日译本译为中文,名为《人权及国民权宣言》。由此可见,中文本《各国宪法源泉三种合编》所含《人权宣言》,历经三次转译:一由耶利内克从法文译为德文,二由日本的美浓部达吉从德文翻译成日文,三由林万里和陈承泽从日文译为中文。中国吴县长洲的潘承锷作为校订者为中文本撰写了《〈各国宪法源泉三种合编〉序》,序文说:“反诸吾国近政之情状,信此书重译之不可少。”这一再三转译的译本,也是本文立论的一大史料基础。
鉴于读者难以查找两个译本以及下文比较的需要,特将两个译本全文抄录如下:
川:《法国宪法人权十七条译注》(1907年)
林万里、陈承泽:《人权及国民权宣言》条文(1908年)
宣告之纲:人权宣告(Dé Claration Tes Aroits de L'homme et Ctoen)国会中之人民之代表,考见国民之涂炭,政界之腐败,皆由于不知人权,或遗忘人权,或忽视人权之故。今特将此天然应有之人权、不可卖蔑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之人权,明白宣布,俾全国社会中人,念兹在兹,虽瞬息之顷,勿忘此相当之义务;俾立法行法之人,梦寐之间,均当以人权悬于心目。凡有作为,皆当与此目的相符合;俾全国民之一举一动,时时以维持宪法为责任,时时谋全国民之利益,而不可一刻偶忘此大义。
职是之故,国会特将此人权十七条宣誓于吾同人之前,皇天后土,实共鉴之。
(川)第一条 人之生长与居处,皆有自由平等之权利。惟因公共利益之故,乃有社会上之区别。
(林)第一条 人于出生及生存,有自由平等之权利,舍公共利益外,不得有不平等之处置。
(川)第二条 各种政会之目的,无非保全此天赋之人权,保全此永久不蔑之人权。此人权者,何也曰自由也,曰安全也,曰财产之主权也,曰压制之抗力也。
(林)第二条 一切政治结合之目的,在于保持人之天赋不可让之权利,如自由,所有权,安全之手段,对于压制之反抗是也。
(川)第三条 大权仅在国家,苟其事非由国家之大权而出,则无论何人,无论何会,均不能行其私权。
(林)第三条 全主权之渊源,必存于国民,团体及个人所行使之权利,必为出诸于国民者。
(川)第四条 凡不妨害他人者,人人皆能为之,此即所谓自由也。如天赋之人权,人人皆当享有。则此人自行其人权,必以他人之人权为界限。此界限何由而定,乃以法律定之。
(林)第四条 凡人之行为于不侵害他人范围内,得以自由,盖社会各员之自然权利当同等,非依法律,不得有他限制。
(川)第五条 法律只有一权。此权维何,防御有害之事是也。凡非法律所禁者,无论何人,不能阻止之。凡非法律所令其行者,无论何人不能强迫之。
(林)第五条 法律限于对有害社会之行为,有禁止之权利,法律之所不禁,当放任之,法律之所不命,不得加以意外之强制。
(川)第六条 法律者,全国人之志愿与代表也。凡系国民,均当争相协助,或则直接出其身以任其事,或则举代表以任其事。所任之事维何,即编制法律是也。法律所当保护全国人共受此保护,法律所当责罚全国人共受此责罚。凡系国民,皆能居于执行法律之任。盖其位为公位,其务为公务也。惟视其人之才德何如耳。才德之外,无他事可区别其能否胜任。
(林)第六条 法律者总意之发表也。凡公民有选代表者参与立法之权利,法律之与以保护及定其罚则,要当均一。法律视公民皆为同等,故公民除按其己之价值及技能外,均得受一切宠号,任公之地位及职务,无所区别。
(川)第七条 惟为法律所规定者,始能逮捕,始能拘留。若有人自发其擅夺之令,目行其擅夺之令,或助人为擅夺之事,或受人指使而为擅夺之事,法律皆当罚之。但国民若遇法律上之唤召,若遇法律上之逮捕,亦当暂时敬从。若或反抗,是自取戾也。
(林)第七条 非由法定及法定形式,不得提起公诉,及为逮捕与拘留。求发专恣之命令及发专恣之命令者,与执行者,与命执行者,皆罚之。然各公民对于适法之召唤逮捕,为抵抗者罪之。
(川)第八条 法律只值确系万不得已,显系万不得已,乃能行其责罚。凡轻罪之当受责罚者,必在法律已经编定布告之后,且必法律已经正当施行之后。
(林)第八条 法律非绝对必要者,不得滥定刑罚。无论何人非依犯罪前制定公布及适法之法律,毋得处罚。
(川)第九条 无论何人,当罪案未定之先,与无罪之人无异。审判之后,罪案已定,凡严刑之可以删除者,皆当竭力删除。
(林)第九条 各人未宣告有罪时,皆当推测为无罪,虽有时必须逮捕,苟非必要之暴力,而拘束其身体者,法律必严禁之。
(川)第十条 苟不紊法律所定之公共之秩序,则各人意见不当妥而不发。
(林)第十条 凡人之发表意见,凡在无害于公共秩序之范围内,其意见皆无为其妨害者,宗教上之意见亦如之。
(川)第十一条 思想之交换,意见之交换,此为各人最宝贵之权利。故国民可任意著作,任意印刷,惟有为法律所限制者,不能妄用其自由。
(林)第十一条 思想及意见之自由交换,人之最贵重权利中之一也。故各公民依其法律之所定,得自由言论、著述及出版,但对于滥用其自由者,负法律之责任。
(川) 第十二条 欲保护人权,不可不有公共之勇力。然则公共之勇力者,为公共之利益而设,非专为私人之利益而设也。
(林)第十二条 保障人及公民之权利,要有公之权力。此权力者,为公众利益而设,非为受此权利之委任者之特别利益而设也。
(川)第十三条 欲维持公共之勇力,欲维持施行政事之费用,则纳税为万不能免之事。凡系国民,皆当纳税,而又量其力之所能,以为区别。
(林)第十三条 为维持公之权力及行政之费用者,不得免公共之课税,其课税从各公民之能力平等分配之。
(川)第十四条 凡系国民,皆有决议税则之权,或躬亲其事,或举代表以任其事,承诺与否,悉出于自由。匀担如何,支配如何,征收如何,期限如何,均视应用之数以为准。
(林)第十四条 凡公民由自己或其代表者,认公之课税为必要时,得自由同意,有检其用途与定其性质、征收、交纳及继续期间之权利。
(川)第十五条 种种社会,均有向官员查账之权。
(林)第十五条 社会对其行政之公代理人,有问其责任之权利。
(川)第十六条 若无宪法,则权限不分,而种种社会均无自保其险。
(林)第十六条 不安固社会之权利保障,且不确定权力之分立,其社会非为有宪法者。
(川)第十七条 财产之王权神圣不可侵犯,惟为公益所必需,则可要索之,但须依公正之条约,而预给其价。
(林)第十七条 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之权利,故非由法律认为公之必要,且与以相当之赔偿者,不得夺其所有权。
三、晚清两个《人权宣言》汉译本的比较
晚清对于《人权宣言》的翻译,作为晚清宪法史和人权史的重要事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而且会展现出译者对原文的汉语表达。因此,有必要深入比较分析其译本,从而既揭示其文本本身的内容,又能透析出当时的历史背景及思想观念,尤其在几种不同文本之间做比较性分析,更能展现译者的不同思想观念与翻译技巧。在此,笔者选择将《法国宪法人权十七条译注》与《人权及国民权宣言》两个译本进行比较。
需要明确的是,因晚清的文字仍偏重于古文,故而笔者的比较与评述,主要是看上述材料对《人权宣言》所作的“译”,在涵义、内容、精神上是否符合原文。对于字、词的使用,笔者只会提及对涵义及内容有较大影响,以及在选词上产生较明显分歧的用词,不会过多地纠缠一般字词的使用。
(一)两个译本对“序文”的处理
“川”本全文翻译了《人权宣言》的“序文”(引言)。但是,林万里、陈承泽的译本则未见这一“序文”。据耶利内克的原著,该“序文”被称之为“特空理的及政治心理之说明”。*参见[德]挨里涅克原著:《各国宪法源泉三种合编》,[日]美浓部达吉原译,林万里、陈承泽重译,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版,第4页。这里所谓“特空理的及政治心理之说明”,李锦辉的今译本译为:“一个属于政治形而上学纯粹理论的教条式声明”([德]格奥尔格·耶里内克:《〈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现代宪法史论》,李锦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3页。)这一“声明”,当指《人权宣言》条文之前的序言。耶利内克的著作之所以未录入这一“序文”,其原因可能是他认为,对于其研究而言,只须讨论《人权宣言》的各个条文就够了,而其“序文”并不重要。他自己就明确指出:“法之《权利宣言》前文中(即序文),有所谓‘于最高神庇下,断然承认此人类及国民之权利,且为此宣言’之语,亦与美之合众国及各州宣言之意义无所异。今略其前文,但对照所列举之权利。”*[德]挨里涅克原著:《各国宪法源泉三种合编》,[日]美浓部达吉原译,林万里、陈承泽重译,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版,第4页。故此,林、陈的转译本,独缺这一“序文”。从这一点来看,林、陈译本也并非完全的译本。而“川”显然没有耶利内克那样的考虑,所以很自然地保留了“序文”。
(二)两个译本的名称比较
“川”翻译的《法国宪法人权十七条译注》,有一段“译者序”(见上文)。这一“译者序”,简明地表达了译注者之所以要译注《人权宣言》的基本动机,也阐明了他对人权的理解,以及关于人权与宪法关系的见解,同时解释了“人权十七条”的由来。而译注者将《人权宣言》称之为《法国宪法人权十七条》,可能是因为该宣言已成为法国1791年宪法的一部分。因此,就两个译本的名称而言,林万里、陈承泽译为《人权及国民权宣言》更为准确。
(三)两个译本的内容比较
从内容上看,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渉及多方面的问题。
其一,两个译本中的个别条款之意义有巨大的差别。例如第三条,“川”所译的意思体现“主权在国家”,而林万里、陈承泽则将之译为“主权在民”。第十六条,“川”将其译为“若无宪法,则权限不分,而种种社会均无自保其险”,这一译文实际上强调了宪法的重要性。相较之下,林、陈将其译为“不安固社会之权利保障,且不确定权力之分立,其社会非为有宪法者”,实则强调了权利的保障及分权的重要性。第十七条,林、陈的翻译为“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之权利”,而“川”译之为“财产之王权”。“王权”与“所有权”实为不同的概念。
其二,就条文的语序而言,“川”有时使用“肯定之语序”,而林、陈则有时使用“否定之语序”。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第七条及第八条当中。对于第七条,“川”的译文表现了在何种情况下,能够“逮捕”、“拘留”,而林、陈的译文,采用了在何种情况下不得“逮捕”、“拘留”。同样,对第八条,“川”译为“凡轻罪之当受责罚者,必在法律已经编定布告之后,且必法律已经正当施行之后”。林、陈则译为“无论何人非依犯罪前制定公布及适法之法律,毋得处罚”。
其三,就条文的用词而言,“川”在第六、七、十一、十三、十四条中使用“国民”一词,而林、陈对此有所区分。其在标题及第三条中使用“国民”一词,此后的第六、七、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条中,使用“公民”一词。此外,在第六条中,关于公职人员的素质,“川”将其译为“才德”,而林、陈译为“价值及技能”。第八条中,林、陈使用“犯罪”一词,而“川”译为“轻罪”。第十一条中,“川”将“出版自由”译为“印刷自由”。第十五条中,林、陈将其译为“有问其责任之权利”,而“川”则译为“查账之权”。
其四,就条文内容的完整程度而言,两个译本也有所区别。例如,第七条中,林、陈提及“公诉、逮捕或拘留”,而“川”只翻译了“逮捕或拘留”,缺少“公诉”的意思。第十条中,林、陈提及“宗教意见”之表达,而“川”并未提及此处。第十一条中,林、陈具体罗列了“自由言论、著述及出版”,而“川”只提及了“任意著作,任意印刷”。
经过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就晚清时期对《人权宣言》的翻译而言,林万里、陈承泽的译本是极为准确、精炼的,属于上乘之作。林、陈的译本之所以精准,一个推测性的解释是,无论是原译(从法文译为德文)者耶利内克,还是再译(从德文译为日文)者美浓部达吉,是德、日的法政大家。而转译(从日文译为中文)者林万里和陈承泽,也具有良好的法政知识素养。因此,他们对于《人权宣言》的翻译,虽然几经转译,但仍较有可能表达其原意。
四、“川”本中的“误译”
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误译”是很常见的现象,甚至是无法避免的现象。毫无疑问,晚清士人对《人权宣言》的翻译,只能是初步的。而“川”的《法国宪法人权十七条译注》对一些条文的翻译,不乏精准之处。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误译的问题。翻译本是一桩极难的事情,再加上晚清对域外文本的翻译,不过数十年历史,而合格的翻译人才也不多见,所以晚清的译书,往往出现不少错讹。与此同时,因中西语言文字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容易导致译者错误理解域外的文本所表达的涵义、观点与思想。翻译大家严复曾经指出,译事有三难,即信、达、雅。而这信、达、雅,肯定不是每个译者都能做到的。晚清士人对《人权宣言》的译介,也存在着“误”即不“信”、不“达”的问题。
(一)“川”本的“误译” 之处
在以上晚清中国的两个《人权宣言》汉译本中,林万里、陈承泽的译本较为准确。因此,“误译”主要集中于“川”所译《法国宪法人权十七条译注》这一文本。这里所指的“误译”大致有如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误译”,是指翻译上的“失误”,如个别条文的内容有所缺失,漏掉了原文中的某一含义,所以翻译并不完整。例如,第七条中,“川”只翻译了“逮捕或拘留”,缺少“公诉”的意思。第十条中,“川”并未译出“宗教意见之自由”的涵义。第十一条中,“川”只提及了“任意著作,任意印刷”,而未译出“言论自由”。虽然,在“川”的译本中,“川”对大部分条文作出了自己的注解,注解中有对条文涵义的补充。例如,在第七条的注解中,“川”解释了“公堂也,民自立而民自入焉,有何不可也”。第十一条的注解中,明确指出“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印刷自由,此三者具而立宪之根基始立”。然而,无论在注解中如何解释条文的涵义,在条文本身的翻译中,缺失部分信息,都将被视为对条文翻译的不精准。至于为什么会在条文中省去这些内容,其原因往往难以考察。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漏译。
第二种“误译”,即翻译上的“错误”,即“错译”。通览《人权十七条译注》全文,可以看出,译者所对条文涵义、内容及精神造成误译的条款,有第三、十一、十五、十六及十七条。
在第十一条中,“川”将“出版自由”译为“印刷自由”,并不准确。印刷与出版并非同一事物。第十五条译为:“种种社会均有向官员查账之权。”但原文为“社会有权要求其管理部门的一切公务员报告工作。”“报告工作”与“查账”,显然不是一码事。
第三、十六条涉及一些较为严重的误译。第三条译为:“大权仅在国家,苟其事非由国家之大权而出,则无论何人、无论何会,均不能行其私权。”按《人权宣言》第三条:“全部主权的源泉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任何团体或者个人都不得行使不是明确地来自国民的权力。”这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确认。而“川”的译文,没有译出这一原则,反而译成“大权仅在国家”。实际上,晚清士人对《人权宣言》第三条的误译,显然不仅仅只有“川”的译本。就其“误译”而言,前引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所录《人权宣言》第三条的译文,与原文的差异之大,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原文规定的是人民主权原则,说明一国家权力的来源。而梁启超所录则变成了国家主权问题,指国民全体或一部分不得由外国人管辖或者不可被分割于外国,这不免偏向了民族主义而非人民主权。而《湖北学生界》发表的《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一文,也同梁启超如出一辙。*译自《支那论丛》并由《湖北学生界》刊载的《痛黑暗世界》有言:“土地者,国民之所有权也,东西各国君主,未有敢以国民之土地而擅送友邦者。法兰西革命之《人权宣言书》曰:‘国之全体或一部分不可分割于外国。’”这里所谓“《人权宣言书》曰”,最有可能指的是其第三条的规定。该文认为,这即是民族主义的体现。“自此主义一出,而各国民虽粉骨碎身,不肯奴役于外种人覊轭之下。此十九世纪,所以收民族主义之成功也。”(《痛黑暗世界》,载《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4期。)可见这一“误译”,在晚清并非个别现象。
“川”的误译,尤其体现在第十六条的译文上。通行的标准译文是:“任何社会,如果在其中不能使权利获得保障或者不能确立权力分立,即无宪法可言。”然而,“川”却译为:“若无宪法则权限不分,而种种社会均无自保其险。”《人权宣言》原文所揭示的是宪法之所以为宪法所必备的内容与精神,即只有“权利获得保障”和“确立权力分立”,才有宪法,否则就没有什么宪法。该条着力强调的,是“权利获得保障”和“确立权力分立”对于宪法存在与否的重要性。而“川”的译文,则是强调宪法的意义,说没有宪法就不会有权限划分和社会保障。这就颠倒了“权利获得保障”、“确立权力分立”与“宪法”之间的关系。他还在注解中说:“所谓权限者,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是也,如君权、民权之界限是也。”这又在权力(三权)分立之外,增加了“君权、民权”的划分,也不合原文之意。实际上,“权限”与“分权”也是不同的概念,不可混用。
最后,第十七条的译文,“川”将“财产之所有权”译为“财产之王权”也并不十分准确。虽然,从“王权”一词,可以看出“川”想强调财产之所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但“王权”一词也并不能直接对译“神圣的所有权”这样一个在法律上较为专业的词汇。
(二)“误译”的原因
既然出现了“误译”,那么“误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它是否也具有一些价值?要对此问题进行探析,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误译”的存在是否是合理的,亦或是不可避免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追问,完美的翻译是否是可能的?早在晚清中国,就有一些翻译家对“好”的翻译设立了标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严复曾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对“信、达、雅”进行详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载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然而,严复虽明确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并对其有着深刻的认识,但他的翻译作品也并非完全达到“信、达、雅”之标准,且被后人认为是“非正法”之作。严复中期的译品为“正法”,即本义上的翻译,道地的翻译,信、达、雅三善具备;而初期和末期的译品多属于“非正法”翻译,即变义上的翻译,是“达旨”,或“译述”(即译中有评、译中有释、译中有写、译中有编、译中有“附益”、译中有删削、译中有案语),甚至采取一种全新的译法──“引喻有更易”。*参见王秉钦:《20世界中国翻译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3页。因此,要到达“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极为困难的。
许多翻译家或语言学家同样认为,完美的翻译是难以实现的。十七世纪法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佩罗·德·阿布朗古尔(Perrot d’Ablancourt)的翻译原则是:“一个翻译人员能领会词义就够了,因为要想把所有的词都译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作者的著述,从他本人的东西翻译成我们的东西,只能表达出原意的大半”*转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7页。又如,埃德蒙·里奇(Edmund Leach)描述说:“语言学家早已告诉我们,所有的翻译都是困难重重的,而完美的翻译通常是天方夜谭。然而我们也知道,出于实践的目的,某种差强人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不管‘原文’多么佶屈聱牙,毕竟不是绝对不可翻译的。语言是各不相同的,但还不至于不同到完全无法沟通的地步。”*转见刘禾:《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宋伟杰译,载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由此可见,语言虽是各不相同的,但仍然具有可沟通交流的空间。所以,即使完美的翻译难以达成,但翻译本身是可能的。
正是由于完美的翻译难以达成,才使得翻译中出现“误译”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而造成“误译”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可能是由于语言能力的缺乏,亦或是翻译技巧的不娴熟。但是,它还可能受到时代背景、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可以包括很多方面,例如翻译机构或出版社、作者、原作、翻译的目的、目标语读者的需求和认知语境、目标语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译者等等。*董明:《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这里,笔者将着重从语言及翻译目的两方面来分析误译的原因。
其一,误译可能是由语言本身造成的,包括翻译者的语言能力、翻译技巧及其水平的局限。毫无疑问,晚清中国是译介《人权宣言》的初始阶段,对外文的掌握及翻译技巧的运用不够娴熟,都有可能导致误译。此外,译文是否是由法语直译而来,亦或是像林万里、陈承泽一样经过多种语言的转换,由法语到德语到日语,最后译为中文,也可能造成翻译的偏差。而“川”之语言能力,译文是由何种版本译来,均无法考究,就此难以总结“川”之误译受到语言本身的多大影响。
从“川”本存在的误译来看,除去个别条文内容上的缺失,还有个别误译源自用词精准度的缺乏。例如,第十一条中,“川”将“出版自由”译为“印刷自由”。又如,第十七条的译文,“川”将“财产之所有权”译为“财产之王权”。这都有不确之处。梁启超曾在《论译书》中说:“译书之难读,莫甚于名号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书既与彼书异,一书之中,前后又互异,则读者目迷五色,莫知所从。”*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载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所谓“名号”,如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度量衡等。那么,是否由于“名号不一”,或“非外语不足以表彰新颖之名词”而导致误译呢?实际上,每当谈及翻译中用词的问题,都不得不考虑译出语与译入语的对应性。换言之,外文中的语词、概念或涵义是否能用完全与之对应的中文予以表达。通常而言,人们认为,如果无法用中文词语精确地表达外文的含义,一定是缺乏对等词。然而,从相反的角度思考,即无法用中文词语精确地表达外文的含义,并非一定是缺乏对等词,而是由于对等词太多。如果说汉语仍旧是最难翻译的语言之一,那么可能的情况是,这种难度恰恰在于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假设的对等词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不在于缺少这种对等。*参见刘禾:《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宋伟杰译,载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这一点,似乎能够很好地解释“川”误译的原因。
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曾写道:“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开。”*严复:《与梁启超书(三)》,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9页。严复这一论述的意思是,在中文里仔细考究,终能找到与西字对应之词。“川”的“误译”,即以“印刷自由”代替“出版自由”,以“财产之王权”代替“财产所有权”,且以“国民”代替“公民”及“人民”,并不在于其创造了与西字不相符合之词,从而显示误译是由于中文的语词及概念中缺乏与西字相对应之词。因为无论是“印刷自由”还是“出版自由”,“财产之王权”还是“财产之所有权”,“国民”还是“公民”及“人民”,都是已经存在的中文词汇。由此可以认为,“川”的误译,实际是由于汉语与其他语言间存在大量的对应词,从而使“川”在已存在的与西字相对应的语词中,选择了并非精确的词汇。
其二,在以上这些业已存在的语词中,“川”选择了并不完全符合原文意义的词汇,这当然与“川”对文本的理解极为相关,同时也多少受到语言之外的因素的影响,例如时代背景、翻译的目的及社会需要等等。
如果结合两项翻译理论及晚清的时代背景和格局,似乎就能够找到一些思考线索。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宏志所述,首先,不得不提到伦敦大学Theo Hermans教授提出的“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学说。这一学说提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a rewriting of the original),且是译者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对原文进行的操控(manipulation)”。换言之,译者在翻译时会对原著作出各种各样的修正、改写以及整理,从而凭借具有很大“重写”成分的“译文”,来达到他原来所设定的目标。由于译者和他的译文所面对的是译入语文化和译文读者,因此,他所设定的目标、他的改写和操控,都是针对着译入语来进行的。其次,安德鲁·利弗威尔指出:“翻译并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Translation is not done in a vacuum.)。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位译者,由于使用跟原著不同的语言,面对完全不同的读者群,在不同的文化范畴下运作,受到各种各样主观的或客观的环境条件所制约,因而在翻译时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考虑,根本不可能翻译出跟原文一模一样的译文来。*参见王宏志:《一本〈晚清翻译史〉的构思》,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2期。这些观点,对我们解释“川”的误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回到晚清的情景中来看,一方面,晚清士人正着力进行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各种立宪运动蓬勃开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宪法的重要性。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表明,“1900年以后,‘宪法’的使用次数明显增多,并分别形成了1906、1913年两个高峰。”*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1900年,梁启超谈到“宪法”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时说:“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旨也。西语原字为THE CONSTITUTION,译意犹言元气也,盖谓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又说:“宪法者万世不易者也,一切法度之根源也。”*梁启超:《立宪法议》,载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407页。而在1906年清政府开始廷筹备立宪之后,“宪法”一词就更常常出现在不少大臣的奏折之中。这些表明,晚清士人对立宪与宪法,是何等的向往。因此,“川”在翻译《人权宣言》第十六条时,可能带着宣扬宪法的目的,从而在译文中强调“宪法”的意义,也就不难让人理解了。另一方面,晚清中国正经受外国列强的入侵和欺压,处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急需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和民族认同意识。实际上,在1895至1900年之间,梁启超曾主张“人民国家”:“使国家成为人民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然而,到了1905年以后,在与革命派的辩论中,梁启超倾向于“国家主权说”,并提出了“开明专制论”。*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54页。由此看来,对《人权宣言》第三条的翻译,无论是“川”本所译“大权仅在国家”,还是梁启超所译“主权在国”,都反映了晚清士人追求国家强盛与民族独立的愿望。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的一些重要翻译家,把翻译当成改良社会、救亡图存的政治工具,所以在翻译动机和选材上将社会政治因素放在首位。因此,清末的翻译往往重意译,即注重原作思想、观念的传输,不太在乎原文语言形式上的表达。从这一角度而言,似乎能够接受并包容“误译”的存在。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现有的各种翻译标准大多过于强调忠于原文或原文的某些方面而忽略了译文面貌的其他影响因素,尤其是目标文化、翻译动机、译文用途、译文读者”。*参见杨平:《翻译的政治与翻译观念的再思考》,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王克非:《近代翻译对汉语的影响》,载《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2年第6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将目标文化、翻译动机、译文用途等要素考虑在内的对翻译优劣的评价,都必须考虑到法律文本对严谨性的要求。法律文本及其翻译,尤其是法律条文的翻译对严谨性的追求,与文学等翻译有本质性的区别。在法律文本的翻译中,任何用词以及表达的出入都将改变整个条文的涵义。因此,即使将晚清翻译法国《人权宣言》的目的、社会需求考虑在内,也不能化解翻译中存在的误译所造成的误解。
除此之外,“川”误译的另一个原因,可能还在于,其译注文本并非法国《人权宣言》单一完整的译本,而是将译文与译注相结合的文本。由于这一方式,“川”在心理上觉得,即便在翻译时使用了并不完全精准的用词,但可以用注解的形式来加以补救。
(三)“误译”的价值
当然,即使是像法国《人权宣言》这样的法律文本在晚清的翻译中存在着“误译”,这些“误译”也并非一文不值。如果说精准翻译原文本来的含义,传递原作者本身的思想,是翻译的基本目的和意义,那么“误译”也能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正是由于“川”的误译可能包含了历史大背景及社会需求等各项复杂因素,这样的“误”才更值得深入挖掘,从而更深入了解晚清士人对《人权宣言》的不同解读。而“川”对于“平等”、“自由”、“国民”、“权利”等各种名词的使用,也构成了晚清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说,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一张由各种新名词为网结编织起来的立体多维的观念之网。几乎没有哪种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是由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作为网结构造而成的。因此,要认知各种近代新思想,测量其社会化程度,就不能不从总体上考虑这些新思想所包含的各种重要的新词汇、新概念的形成、传播和社会认同问题。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川”的误译,不可绝对否定。
与此同时,根据“川”的误译,人们似乎能够提出许多超出翻译本身的更为深刻的思想性问题。例如,晚清中国如何理解“国民”、“公民”、“人民”这三个名称的内涵?是否缺乏对三者涵义的分辨?以及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川”将“任何社会,如果在其中不能使权利获得保障或者不能确立权力分立,即无宪法可言”,译为“若无宪法,则权限不分,而种种社会均无自保其险。”那么,晚清中国是如何看待宪法与权利以及分权的关系,又是如何看待宪法的地位的?这些都是晚清人权思想发展过程中极具价值的问题。
总而言之,在《人权宣言》的两个译本中,“川”的译本存在一些误译和偏差,这当然是由于完美的翻译是难以达成甚至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川”的翻译可能受到时代背景、翻译目的及社会需要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存在一些误译与偏差,但也多有精准之译,这些都是人们了解和认识《人权宣言》的基础。不同的译本,对用词、语序、句式的选择,无论精准或错误,都蕴含了晚清士人对《人权宣言》的独特理解。毫无疑问,这些翻译对《人权宣言》在晚清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王德福]
收稿日期:2015-10-21
基金项目:本项研究及论文获得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0903005203298)资助。
作者简介:程梦婧(1987-),女,重庆人,法学博士,重庆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与人权史。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16)01-0151-10
Subject:On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uthor & unit:CHENG Mengjing
(Law School,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Abstract:Since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was brought in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everal Chinese translations appeared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Ms. Xiaopin’s translation in 1903 is actually not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as people usually thought. Two other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Déclar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re important, which is Chuan’s version in 1907 and Lin Wanli and Chen Chengze’s version in 1908. To compare those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Déclaration, differences are found in their prefaces, titles and contents. Besides, there are some mistranslations in Chuan’s translation. The reasons to mistranslate are various. Chuan might be affected by his language ability, translation purpose and the social need. Nevertheless, even though some mistranslations are in Chuan’s translation, the values of both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Déclar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all not be ignored.
Key words: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ion; mistrans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