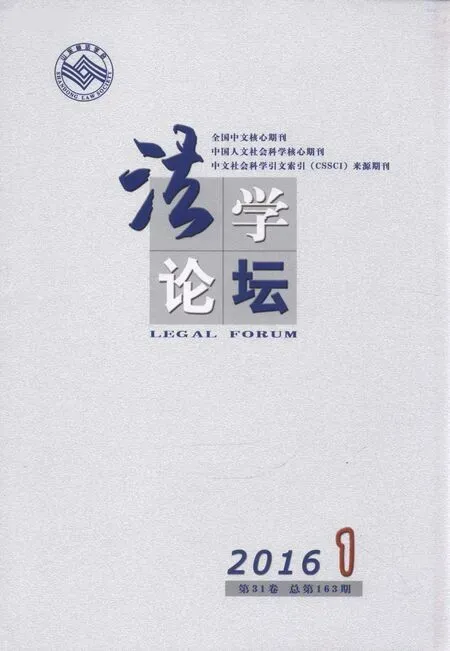科技、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司法检视
——以“宜兴胚胎案”为例的分析
张婷婷
(中国政法大学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8)
科技、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司法检视
——以“宜兴胚胎案”为例的分析
张婷婷
(中国政法大学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8)
摘要:在疑难案件中,法律与道德的巨大冲突很容易掩盖科技的“除魅”特性。科技不仅革新了法律纠纷的产生和鉴定方式,还重塑了传统道德的取舍范围。而道德则依赖人生与社会认同的优势,又为科技发展和制定法设定了伦理准则。“宜兴胚胎案”的两种裁判就证明,在制定法缺失的情况下,科技与道德将以隐性和显性的方式分别作用于法律解释,并在相互制约中影响司法裁判。然而,受国家法治意愿的影响,法官只是有选择性地接受科技与道德的引导,并最终将裁判结果限缩于法律框架之内。
关键词:科技进步;道德市场;法律进化;司法裁判
作为法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命题,“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时下中国法学研究中极具回暖之势,四川沪州遗赠案、陕西黄碟案、南京换偶案以及南京彭宇案等案件引发的法律与道德论争便是鲜明例证。除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之外,上述案件也引发了学界对于道德问题的深思:随着国家现代化推进,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道德的退化?法学界与伦理学界不约而同的将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的干预,如社会转型、价值多元以及公民意识觉醒。不得不说,上述因素的确打破了人们对于传统道德的信仰——例如“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观念的弱化。然而,外部因素的干预只能证明国家强制力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影响。传统道德为何一再退化、如何退化以及化解路径何在,仍是一个尚未厘清的问题。事实上,以法律和国家公权力机关为代表的国家强制力只能肯定和迎合“道德退化”这一趋势,而无法对其产生阻力。若双眼完全蒙尘于法律的力量,则不利于我们厘清道德退化、法律进化背后的物质基础。吊诡的是,新近发生的“宜兴胚胎案”(以下简称“胚胎案”)却削弱了人们对法治的崇拜,并为法哲学家们重新审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命题提供了形而下的视角——科技*日本学者樱井邦朋认为,“科学和技术(可以)看作是同质的东西,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把科学技术归拢在一起使用”。[日] 樱井邦朋:《现代科学论15讲》,东京教学社1995年版,第1页。笔者赞同这一观点,故不对“科学”、“技术”加以区分,而以“科技”作为统称。此外,这里的“技术”不仅包括与自然科学相关的技术,也包括与社会科学相关的技术。参见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视角。该案件的两次判决不仅凸显出科技对于法律、道德的影响,也体现出法官在疑难案件裁判上的内在规则。本文无意于考察科技发展史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微观意义,而只试图围绕“胚胎案”进行“一种独立于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解释”*桑本谦:《科技进步与中国刑法的近现代变革》,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5期。,以期探明司法审判中科技、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机理以及其中内含的裁判规则。
一、隐含的科技因素与法官的裁判逻辑
在司法领域中,科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检视必须深入到具体事例中进行推衍。吊诡的是,面对形而下学研究路径上的案例缺失,伦理学家们虽然未能寻找出完美的事例展开分析,却臆造出一种“司法公正与道德评判”思维困境——“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Philippa Foot. 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 Oxford Review , 1967(5): pp.5-15.。该事例虽然是假设的,但却较好地反映了科技、法律与道德难题产生的现实根源,即科技发展造成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标准差异。然而,“胚胎案”*2004年,我国曾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例。在该事例中,丈夫遇意外去世,妻子王X要求医院移植冷冻胚胎而未获准许。后经多次协商,在国家卫生部召集专家论证后才允许王X移植该冷冻胚胎。由于该案未进入司法程序,因此不宜作为科技、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典型例证。的出现却为伦理学家与司法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难题:法律应当如何平衡科技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为了便于说明这一问题,本文选取“电车难题”与“胚胎案”作为观察对象。其主要目的是:(1)通过假设案例与真实案例的鲜明比较,凸显科技因素在法律与道德关系上的作用过程;(2)“电车难题”、“修正版电车难题”以及“胚胎案”形成了有效的渐变序列,便于观察科技因素与道德因素分别在何种情境下影响司法裁判。现将三个案例作以简述。
电车难题:假设一辆有轨电车飞速驶来,即将撞上前方轨道上的5个检修工人,并且他们已来不及逃跑,但备用轨道上却有1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岔道工是否可以通过牺牲这一个人的生命而拯救另外五个人。
修正版电车难题:路人A站在天桥上,看到有一辆飞速驶来的电车。而在轨道前方的5个检修工人却不晓得电车冲来。这时,路人A发现,身边的路人B恰好体形巨大,可以挡住电车,让电车出轨,从而救下5个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路人A是否可以把路人B从天桥上推落,以拯救那五个工人。
胚胎案:2010年10月,沈杰与刘曦登记结婚。婚后二人因“原发性不孕症、外院反复促排卵及人工授精失败”,在南京市鼓楼医院进行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手术,并获得受精胚胎4枚(尚未移植)。2013年3月,沈杰与刘曦因车祸死亡,遗留受精胚胎4枚。之后,死者双方的父母因受精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发生争议,并诉至宜兴市人民法院。南京市鼓楼医院作为诉讼第三人参与诉讼,并宣称胚胎属于特殊的物,涉及人性伦理问题,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为此,一审法院以“有违社会伦理和道德”、“合同履行不能”等法律规定为由,判决驳回沈新南、邵玉妹(二者系沈杰的父母)的诉讼请求。二人不服一审判决,随后上诉至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伦理”、“情感”等道德因素构成公民权利的基本组成部分,上诉人在不违反法律、公序良俗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可以获得4枚受精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
上述三则案例中关于道德难题的论争,是任何企图探讨法律道德性难题的学者都无法回避的。同样的,其中隐含的科技因素也成为诱发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立法者一方面谨守法律的道德底线,另一方面又迫切地将新兴技术运用到法律中去,理由则是“顺应时代发展”。这样,一些早期传承下来的道德观念在现代科技面前不得不被重新审视,这也导致富勒的法律道德主义学说亟待修正。然而,一个反潮流的经验事实却表明,国家虽然倡导并以立法形式保障科技革新,但却始终坚守法律道德主义的核心立场。道德在立法、执法以及司法领域的膨胀也印证了这一论断,如见义勇为条例、文明执法以及南京彭宇案等。那么,这种现象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行为逻辑呢?或许三则案例的论证能够为该问题提供一定的解答。
其一,科技能否成为道德的阻却事由。Philippa Foot 创设的“电车难题”虽然旨在表明道德选择的两难性,但却无意中预设了一种科技前提,即“电车无法立刻停止”。既然如此,道德问题的产生就必须优先虑及科技因素的适用场域。在科技因素的介入下,人类道德可以区分为两个等级:(1)满足社会有序化要求的基本道德,如避免伤害、诚信以及尊老爱幼等;(2)增进人类发展、提升社会福利总量的高尚道德,如无私、博爱、利他等。*参见[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页。显然,前者属于先验的人性检验范围,后者则导致人类道德产生了等级差异,即拥有财力或工具优势的人比普通人更易于彰显道德,如社会捐助、善意搭载路人。假设“电车难题”所衍生的道德难题被移至司法机关,那么显然,在撇除法律功利主义以及法律道德主义的前提下,科技因素势必将成为司法裁判的重要考量部分,*Tamara Garcia & Ronald Sandler认为,生命科技的强大有可能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其理由在于:经济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低收入人群难以接受生命科技的治疗,从而引发医疗待遇的不公平。Tamara Garcia, Ronald Sandler. Enhancing Justice NanoEthics. 2,2008(3):pp. 277-287.毕竟岔道扳手的设计增加了人类道德选择的难度。由此可以获得定理Ⅰ:科技能够成为道德的阻却事由。
其二,道德能否成为科技的阻却事由。倘若“科技可以成为道德之阻却事由”的论断得到认可的话,那么,道德论者们在面对“修正版电车难题”时,势必需要考虑如下问题:道德究竟在何种情境下能够成为人类行为的评判标准?言下之意是,在科技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具体情境的变化能否改变道德的作用方式。“电车难题”与“修正版电车难题”的比较分析表明,行为的合法性与否形成了不同强度的道德选择难题。在“电车难题”中,岔道工的行为属于合法的职业行为,只是在生命选择上存在取舍难题。因此,合法行为诱发的道德难题只具有弱谴责性;而在“修正版电车难题”中,路人A的行为本身便具有违法性,无论其行为目的如何,都会遭受强烈的道德谴责。进而发现,行为合法性、正当性的考量对定理Ⅰ进行了修正,分别获得以下判断:科技因素只在弱谴责性道德难题中能够成为道德的阻却事由(命名为“定理ⅠA”);而在强道德谴责下,其影响力迅速降低,并弱于道德批判(命名为“定理ⅠB”)。该论断对于司法裁判同样适用。在司法机关看来,道德行为的可谴责性意味着该行为的可惩罚性和惩罚必要性。对于弱谴责性的不道德行为来说,司法机关不会动用昂贵的国家机器进行制裁,毕竟道德规范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行为评判标准。但对于强谴责性的不道德行为而言却不同。由于该类行为的增加有损社会稳定,即便科技能够容忍这类不道德行为,并且法律也未预设制裁措施——如“代孕”技术已经能够实现对冷冻胚胎的异体孕育——道德仍将谴责该行为。由此得出定理Ⅱ:道德只能在强谴责性下成为科技的阻却事由。
其三,科技与道德能否影响司法。也许有学者认为,假设的案例只能提供理论学说上的分析,其实证效果难以得到测度。但“胚胎案”却鲜明地佐证了前述定理。在该案中,“人工授精技术(in vitrofertilization)”与“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通常来说,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属于一种新型的人工助孕技术,它主要是“通过人工的方法,将精子和卵子在体外结合形成受精卵并使它们发育成胚胎,在植入子宫前通过基因检测筛掉有遗传疾病的胚胎,并将健康胚胎植入母体子宫的技术”。田野:《“设计婴儿”的法律思考》,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凸显了科技对于法律与道德的重塑性、批判性,并构成了法律与道德之间、司法裁判与道德评判之间的巨大冲突。*拉伦茨认为,法官既需要在法律中获得裁判依据,同时也需要兼顾正当的伦理要求。并且,对于法官而言,正当化的伦理要求恐怕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解释法律都需要兼顾这个要求。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页。二审判决虽然支持了上诉人沈新南、邵玉妹的诉讼请求,但在4枚受精胚胎的处置方案上,*参见周华:《论类型化视角下体外胚胎之法律属性》,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却是延续了一审法院的裁判策略:“不得违反法律、公序良俗”*美国发生过一起类似案例,即Hecht vs. Kane案。在该案中,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认定,死者生前储存的的精子属于可继承的“财产”,应当归配偶所有。Mason, McCall Smith. Law and Medical Ethics. London: Reed Elsevier (UK) Ltd, 1999. p.487.。隐藏在其中的行为逻辑是:司法机关在面对“精神慰藉”的强情感需求时,选择了道德优先于科技因素;而在面对“受精胚胎孕育”的弱道德性(也可能是不道德)需求时,司法机关谨守了法律与公序良俗的底线,否定了上诉人潜在行为的道德性。这种事实性判断对价值性判断的挑战,型构出科技因素在道德与司法审判中的又一规律,即定理Ⅲ:在疑难案件中,科技属于隐性影响因素,而道德则构成法官裁判的评判准则。
虽然司法裁判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制约下做出的,并且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显然不是肆意而为的——它仅构成理论研究中的极端例证——法官的任何裁判方案却都需要科技、法律与道德基础作为现实支撑。一旦超越了社会所能容忍的道德底线与科技水平,即便法官依法裁判,该判决也未必能够得到公众认同。因此,我们可以将定理Ⅰ、定理Ⅱ、定理Ⅲ归纳出一个原则性论断,即定理Ⅳ:
在司法审判中,司法裁判既要尊重社会的道德底线,也要顺应科技的发展水平。
二、科技扩张、道德内省与法律要素的结构性分立
传统上,科技与道德的相互阻却现象(定理Ⅰ与定理Ⅱ的混合结果)被“归因于古代科学的不发达、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以及科学和技术都还仅具个体意义而未充分社会化”。*孙莉:《在法律与科学技术之间》,载《科学学研究》2007年第4期。然而,在科技水平极度发达的今天,司法裁判中科技与道德的阻却现象已经难以用“科技水平低下”来评判。因此,法学家们有义务去探寻司法裁判背后的真实逻辑,以明析科技与道德相互阻却的内在原因。
遵循科学学的思维路径,科技被视为人类四肢和头脑的延伸,*刘可风、朱书刚:《哲学的应用与创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页。并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立法过程以及法律制度的存在业已证明,科技的此种实用性能够解决立法争端,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也被某些利益集团运用于司法领域,以应对机会主义诉讼。*参见David S.Caudill.Law and the Science Wars:Introduction to the Forum.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23,1999(3):pp.545-554.科技对司法的影响主要源在于人类理性与经验的关联性。苏力在论证科技与法律的关系时指出,科技通过实验观察方法发现的因果联系,能够影响法律制度(包括司法制度)中的责任分配方式。*参见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一个显见的例证就是,古代社会中神明裁判、刑讯逼供等现象在证据技术发展过程中逐渐消除,而现代科技成果一旦产生也将迅速内化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增强法律的实效性与可操作性,如DNA鉴定技术、指纹鉴定、笔记鉴定、录音录像技术等。
虽然法哲学家们以法律的道德性指责科技扩张的无序性,并坚信道德构成制定法的社会基础。然而,理性、严谨的科技因素却成为传统道德难以逾越的法治障碍。即使法官承认道德构成法律必不可少之组成部分,科技在司法中的运用仍逐步侵占了道德的生存空间。加之社会转型以及城乡一体化的飞速进行,传统道德所依赖的“熟人社会”日益为法治社会所取代。由此,法律中的科技愈发强势,道德因素却日渐式微。法律道德主义的回暖也只是立法者应对道德退化现象的无奈之举,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湖南省见义勇为条例》等。造成此种“此消彼长”之势的原因在于:科技的实用主义观念反映的核心命题是“是”与“不是”的关系问题,而道德却反映的是“应该”与“不应该”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关于“是”的事实判断并不能必然推出关于“应当”的价值判断,任何由“是”向“应该”的过渡都应当是基于充分论证而得,否则该过渡便是不合法的。*参见潘丽萍:《法律的道德批判与法的价值理念的发展》,载《东南学术》2010年第1期。这样,在现代科技的作用下,人们愈加明白传统道德的“应当”是难以自我证成的、存在愚昧成分的,甚至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从而导致科技进步在引领人类走向文明的同时,也削弱了人们对于传统道德的信仰。
然而,广为道德论者诟病的是,科技所体现的实用主义观念极易导致法律的形式化、技术化,却难以提供价值判断。恩吉施就认为,“传授实现具体目的的手段,不对目的本身进行道德性讨论,这是整个现代技术的特点。……技术在道德上是中性的或吝啬的,它从其可能服务的目的之道德性和非道德性那里获取它的道德含义。”*[德]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9页。显然,恩吉施批判的即是将科技视为“司法裁判的决定性要素”的观点,并认为道德性目的才应当构成司法裁判的归宿。因此,在道德论者看来,即便科技有助于司法运作,但它与人性价值、精神关怀等道德因素的背离,显然是不为现代法治所倡导的。为此,道德在司法领域中选择了一条有别于实用主义的表达路径——伦理主义。
事实上,道德论者对科技的反击并未走远。在伦理学界,伦理主义并非是一个恒定且无异议的概念,它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是普遍伦理主义(ethical universalism),即“存在某些客观的普遍适用的伦理准则,这些准则虽然植根于某种文化,但同样能适用于其他社会”;*参见[美]安妮·玛丽·弗朗西斯科、巴里·艾纶德:《国际组织行为学》,顾宝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二是相对伦理主义(ethical relativism)。它认为,伦理是基于社会与文化状况来确定的,不存在适用于任何社会状况的普适准则。概念上的差异导致道德融入司法的过程极具风险,并最终引发相对伦理主义在司法领域中的灭亡。佐证这一判断的理由有二:(1)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法律是一种具备普适性特征的国家规范。而相对伦理主义影响下的道德,明显欠缺此种普适性特征;(2)经验性事实证明,法律与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合性,如:“不得杀人”、“诚信”、“公平”等。反观相对伦理主义坚持的恒变论,缺乏法律所必须的稳定性。因此,在司法领域中,道德只能依托普遍伦理主义来干预司法裁判。任何企图扩大普遍伦理主义范围的立法或司法尝试都将遭遇法治危机*戈尔丁认为,“从道德上谴责一种做法,到认为应从法律上对其加以禁止,还是有很大一段距离的。”[美]戈尔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3页。。由此观之,伦理主义的反击不但未能抑制科技的司法扩张,却限缩了道德的司法空间。由此抽离出裁判规则Ⅰ:司法机关在裁判疑难案件时要有选择地接纳道德规范。
当然,道德论者的反击并未就此而止。以法律道德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自然法学成为道德论者的另一个证立路径。众所周知,自然法学派历来强调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并宣称法律规则应当体现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英国自然法学家史蒂芬就认为,法律的强制性旨在实现美好的目标,即“确立、维护并授权于立法者所认定的良好道德体系或标准”。*[英]詹姆斯·斯蒂芬:《自由、平等、博爱:一位法学家对约翰·密尔的批判》,冯克利、杨日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124页。这种自然法理论甚至已经作用于司法领域,以至于有学者认为,隐含于法律规则背后的道德价值应当成为司法裁判的指导目标。*参见孔祥俊:《法律方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由此可见,道德因素寓于法律之中的是伦理秩序和价值判断。这是被自然法理论视为“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系统”。*Lon.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New Haven:Yale University,1969. p.46.
依照这一理论假说,道德与法律和谐与否,除了关系到司法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之外,更是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问题。然而,管窥“胚胎案”二审判决书的说理、论证部分可知,自然法理论中“神圣化”的道德在司法实践中却产生了行为悖论:基于伦理与情感原因获得的“胚胎监管权和处置权”却不得违反法律与公序良俗进行处置。显然,自然法学家们的直观判断会是:该裁判是专断的,有违道德的。但理性的读者会发现,法官在此将“人工授精技术”视为合道德性且合法的,肯定了科技对生命延续的积极意义;而对于后续的“代孕”行为则持否定态度,将“代孕”视为破坏基本的家庭伦理关系的不道德行为。*参见Robert P.George.In Defense of Natural Law.Clar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86.因此,在司法领域中,支撑道德因素的自然法基础是有边界的,它只能在普遍伦理主义的范围内适用,超越普遍伦理的道德规范难以获得制定法的支持。由此产生一个疑问,道德论者的反击为何抑制了道德的司法空间?
事实上,道德内省所导致的抑制性结果反映了一种“除魅(Entzauberung)”时代需求。科技进步明晰了法律中的因果关系,并将过去因缺乏科学证据和技术支持而归结为不道德的错误因果关系予以了纠正。*颜厥安认为,生命科技的发展导致法律制度在设计上产生了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参见颜厥安:《鼠肝与虫臂的管制——法理学与生命伦理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由此发现,科技带给司法两个直观变化:一是实现了科技的司法扩张,这在司法证据审查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二是增强了因果关系认定的客观性。当然,无论是科技的司法扩张还是法律因果关系的变化,它们都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真理性仍是毋庸置疑的。例如在胎儿继承权问题上,南宋的宋慈以“呼吸观测法”探测新生儿是否为“活产”,但现代科技则以“肺浮扬试验”和“胃肠浮扬试验”来测试新生儿的存活时间。*参见[宋]宋慈:《〈洗冤集录〉今译》,罗时润、田一民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显然,在南宋时期,宋慈创立的“呼吸观测法”属于先进的测试技术,并且在当时能够获得公众认同。但该技术在当下却将饱受质疑,甚至被归于无效证据。因此,凯尔森认为,“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凯尔森显然看到了科技赋予法律的进化动力,也觉察到道德的历史局限性对于法律的桎梏。科技的“除魅”功能在此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命令”、“规则”,它强制性地要求人们服从某一客观事实。*参见[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例如:当前亲子关系争端中,法官、陪审团、当事人以及律师显然不会试图以“滴血认亲”的方式来挑战DNA鉴定结果。*参见邓雪仁等:《DNA鉴定——亲子关系争端之解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尽管科技仅为司法证据审查提供了技术、形式支持,而不涉及价值判断,但科技的“除魅”效应确实引发了司法领域中科技与道德的分立。
事实上,司法领域中科技与道德的分立是必然的。虽然科技与道德都凝聚着人类理性与经验,是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产物。但是二者所依赖的哲学基础却有所不同。科技主要借助数理逻辑和实验观察,逐步抽象出以工具理性和事实判断为特征的哲学基础,而道德则将人类生产、生活中产生的互助关系与协作精神,逐渐凝练出以价值理性与价值判断为特征的哲学基础。这也引发了法哲学视域下科技与道德的两种分立:
其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立。自“休谟法则”*休谟在讨论道德问题时指出:“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然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了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需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9-510页。提出以来,道德问题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问题上便产生了分野。按照休谟的主张,事实判断不经证明无法转化为价值判断,言外之意是,价值判断在缺乏事实证成的情况下未必为“真”。进而可以推知,在道德问题上,事实判断构成了价值判断的阻却事由。吊诡的是,在司法领域中,科技显然已经内化为一种事实判断,并且具有“是”与“不是”的强客观性特征。当科技面对价值判断时,其客观性不会因法律人的主观愿望而发生变化。因此,科技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参见Maja van der Velden. Design for a common world: On ethical agency and cognitive Justice.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1, 2009(1),pp. 37-47.而道德则不然。道德属于价值范畴,会受社会共识性观念的强烈影响。它仅在部分范围内同法律保持同质性,并且该范围伴随国家意志的变化而变化。凯尔森将法律与道德在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性区分为“客观价值判断”与“主观价值判断”。他认为,法律对于行为合法性的判断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或情感而转移的,只有依据法律规范来裁判人们的行为才属于客观价值判断。这是司法裁判得到认可的唯一方式。*参见[奥]凯尔森:《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换句话说,司法裁判只遵从同法律保持同质性的那一部分道德。因此,对科技与道德对立之解读,应当建立在法官的客观价值判断之上。倘若一位法官按照个人好恶裁判案件,显然不构成科技与道德的司法对立,而属于枉法裁判。由此总结出裁判规则Ⅱ:司法裁判能够容忍的仅是客观价值判断,而人的主观意愿与情感则将为科技所阻却。
其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立。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研究最早从德国法学家马克斯·韦伯开始。他将黑格尔哲学中的“理性(reason)”概念改造为法学、社会学中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并建构起“工具—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学说体系。韦伯认为,近现代理性观念的重心正在由实质理性向工具理性演变,这其中既与科技的迅速发展有关,也与价值理性的历史性相关。在社会发展早期,正是由于价值理性对价值与目的的清晰界定,才给予了以科技为主的实践手段的可持续发展。当技术手段(工具理性)发展成熟后,便获得了独立性、自主性,并逐渐成为与价值理性相对立的主体。*参见陈振明:《工具理性批判——从韦伯、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载《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基于法律进化论的大胆推理,理性的发展显然不会到此止步。有学者就辩称,“人类理性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重视整体理性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分离,再走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过程。”*何建华:《发展正义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3页。法律作为一种理性建构的产物,便是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结果。然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司法领域中的融合,并不能说明二者已经完全脱离了“分立”的状态、失去了独立性。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这种合理性的分立,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的。*霍克海默认为,合理性必将分裂为不同的有效性层面,如规范正确性、正直性、真实性等。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360页。韦伯亦赞成此一论断,并宣称:“这个趋势包含了用合理性的东西把合法行为的感情和传统的模式作为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东西而从生活中加以取代的过程。其结果是,……理性是它自身的必要性的立法者。”*[英]唐·责克雷:《世界热潮的中心人物:韦伯》,赵立航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由此证明了定理Ⅰ的正确性:科技可以成为道德的“枷锁”。
三、科技界限、道德市场与国家法治意愿
司法裁判同立法一样,都应当凸显一种社会激励效应,即维护社会稳定、激励社会进步,促进人类和平相处。即便对于具有强惩罚性的刑事类案件而言,保护人权、维护正义才是其根本目的,惩治犯罪仅构成一种手段。因此,对于抑制科技的司法扩张而言,任何规范化的立法设想都是无望之谈。它既不符合科技发展的历史潮流,也违背社会进步的意愿。我国科技类法律法规的总体面貌便印证了这一结论。审视我国《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条文设置,激励性条款与鼓励性话语充斥其中,但科技研发方向指引与科技负面影响的抑制措施却较为鲜见。倘若纯粹地看待科技研发而忽略科技用途的话,立法者如此规定确无不妥之处,毕竟科技研发的积极意义在于推动人类进步。但根据定理Ⅰ的推衍,科技最终可能将替代道德。道德论者乃至社会公众显然难以接受这一反经验论断。事实上,前述推衍只是一种无外力作用下的完美演绎,司法实践中的科技扩张历来承受着两种抑制:一是内部抑制;二是外部阻却。内部抑制便是科技对于自身的抑制效用,而外部阻却则是法律(包括司法)的道德性*参见秦策、夏锦文:《司法的道德性与法律方法》,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对于科技的阻却,两种抑制方式的交叉影响致使科技始终朝向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前进,却无法导致道德消亡。
在司法领域中,科技的自我抑制效用表现在彼此之间的可验证性,即科技融入司法中的程度受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该抑制效用的两个早期例证是我国清代末年的“法律移植”和墨西哥移植美国法的失败。有学者将两者失败的成因归纳为“社会文化差异”。*参见[美]布赖恩·Z·塔玛纳哈:《一般法理学:以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为视角》,郑海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但这一结论却忽视了两个输入国的科技发展水平问题。按照清代中国以及20世纪末墨西哥的科技发展水平,两个国家的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显然缺乏支撑现代司法制度运行的科技条件。而新近的一个重要例证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一方面,该制度推翻了“口供中心主义”的举证传统,对证据的真伪性、证据链的完整性提出了更高的鉴定标准。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必须掌握最新的证据鉴定技术,如笔迹鉴定技术、声纹与指纹技术、录音与录像鉴定技术、血型鉴定技术以及DNA鉴定技术,*有一项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发生的多起错判案件是由于DNA鉴定技术缺失,而另有多起错案是由血型鉴定误差所致。参见陈永生:《我国刑事误判问题透视——以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以便应对各种证据鉴定需要。相比于古代社会中“滴血认亲”的科学性,显然,现代科技的发展提升了司法的证明标准;另一方面,法院将录音、录像的获取渠道纳入到证据审查中来。这意味着,侦查机关不仅需要证明录音、录像本身所载有的内容属于真实信息,也需要对录音、录像来源的合法性予以证明。正如桑本谦所言,科技在提升法律的可操作性、降低法律实施的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法律对行为的规范标准,缩小了法律推定的适用范围。*参见桑本谦:《疑案判决的经济学原则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设想在录像鉴别技术缺失的前提下推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有多少录像能够被排除在法庭之外。这说明,司法领域中的科技扩张会受到自身发展水平的巨大限制。科技融入司法的种类、多少、程度不仅需要满足人类道德的审查,还需要经受其他科技成果的检验。由此归纳出裁判规则Ⅲ:司法机关对科技的认可与适用,是按照科技之间的彼此可验证性进行选择的,并非任何科技成果都可以转化为司法审判的工具。
而道德对科技的抑制效用源自于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这不仅成为法律道德主义者宣扬道德永恒性的一个反向佐证,同时也为道德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市场。在司法领域中,无论是基于法律规则还是基于裁判说理,道德总是能够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司法裁判需要道德作为其内在支撑,以增强裁判的说服力。尽管科技是价值中立的,或者说是无价值表征的,但其工具属性却是要经受人性道德的考量。因此,科技的司法扩张并非是毫无界限的,它会受到道德的制约(定理ⅠB)。这一论断充分说明了一个显见却被忽略的事实:缘何科技的飞速发展未能消除人类道德的生存空间。理由在于: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技都带有一定的领域属性。那么,职业伦理与人性道德就构成科技研发人员的一种约束力量。尽管这种道德约束力对科技研发仅具有主观批判性,缺乏对客观研发行为的有效规制,但职业伦理的谴责以及职业共同体的抵触同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科技研发、适用的阻却事由。然而,法学家们对职业伦理的阻却效用充满疑虑。他们认为,单纯的依赖道德约束无法抑制科技的扩张性。因为道德约束仅是一种心理上的软约束,对于缺乏职业道德的科学家而言,这完全是不足够的。并且,解构定理Ⅱ可以发现,将强道德谴责性视为科技的阻却事由,只是在人性心理层面上得出的静态分析结论。它只能证明在纯粹的科技与道德对立情况下,人类对道德情感的可接受性优先于科技带来的便利性,而无法保证在第三方因素介入的情况下,二者的对立关系、优先规则同样适用。因此,单纯的将道德视作科技的阻却事由仍是有缺陷的。
按照上述分析范式,定理Ⅱ确实难以成立。但一如前述所言,科技与道德的对立关系并非静态的、孤立的对应,第三方因素的介入极易打破这种平衡。道德同法律的衔接便是典型例证。实际上,强道德谴责总是与法律保持一致,强道德谴责性同时也意味着违法性,某些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也违背职业伦理。例如:道德与法律均将杀人、盗窃、强奸、抢劫等行为视为“不得宽恕之行为”。因此,尽管强道德谴责性只是一种主观层面的心理约束,但现代法治的发展已经实现了法律与伦理、道德的有效衔接,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享受道德生活的环境,也通过法律来指引人们过有德性的生活。*参见H.L.A.Hart. Social Solidarity and the Enforcement of Moral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Review, 35 (1967): pp.1-13.可见,国家推动“道德法律化”的理想愿景在于实现道德秩序与国家秩序的统一,减少(更愿意“消除”)公民之间因行为标准差异所导致的无序行为。假设某人的不诚信行为能够从集体诚信中获得利益,那么,随着这种投机行为的增加,集体诚信将逐渐缺失,甚至不复存在。显然,国家并不希望此种有序化的人际约束机制就此消失。为此,强制化规范措施是国家必然采取的防范机制。*参见Patrick Devlin. 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Clar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p.17.正如霍布斯所言,只有国家公权力的强势介入,才能够有效缓解个人的投机行为,并解决该类投机行为的泛化危机。*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8-129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继承制度、赡养义务、非书面契约制度能够为我国法律所规定,而见义勇为、“常回家看看”等行为不适宜由法律强制规定。即便科技在司法领域内能够持续扩张,但由于国家公权力的支持,道德仍然会持有巨大的法律市场。这既是道德论者反击科技论者的主要理由,也是道德市场持续勃兴的真谛所在。由此我们将获得裁判规则Ⅳ:在司法审判中,国家的法治意愿将保证道德市场的兴盛。
四、“胚胎案”的司法效应
“胚胎案”的两次判决引发了强烈的公共讨论。*“胚胎案”的两次判决,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关注,社会公众、媒体、学者以及法官纷纷现身说法,表达不同见解。例如徐隽:《冷冻胚胎究竟该归谁》,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日;杨立新:《一份标志人伦与情理胜诉的民事判决——人的体外胚胎权属争议案二审判决释评》,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1期;张圣斌、范莉、庄绪龙:《人体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权归属的认识》,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1期;杨立新:《人的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及其继承问题》,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13期虽然社会公众与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但在案件审理的主要症结上却大致形成了共识,即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问题。即便法律形式主义者认为一审判决更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也仅是出于尊重和保护法律权威的考虑(违背了裁判规则Ⅰ、Ⅱ)。或许一审法官的确是如此思考的,但这显然不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因此,该判决虽然合法却难以“服众”。如此,一起简单的“物权纠纷”或“合同纠纷”,由于冲撞了公众的道德共识,而演变为一起民事疑难案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安抚公共舆论的道德谴责,伦理道德就堂而皇之地成为司法裁判的“挡箭牌”。而且二审法官发现,这一“司法脱身术”*参见桑本谦:《疑案判决的经济学原则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十分有效,不仅定纷止争,而且稳定民心。但是,当有心者细心比对一审判决与二审判决时就会发现,二审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既饱有司法裁判的“合法性”成分,也化解了科技、法律与道德的激烈冲突。在此,笔者将“胚胎案”中法庭各方的观点予以对比、解读,以探讨该案件对中国司法的历史效应。
(一)谁是赢家:科技抑或道德?
根据当前的舆论走向,伦理道德无疑成为了“胚胎案”的最终赢家。然而,基于定理Ⅳ及裁判规则Ⅰ的指引,二审判决却未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何在案件当事人胜诉的情况下,却被要求“遵守法律且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和损害他人之利益”。这不免令人深思,公民权利的司法限制究竟是否合法?其根源来自何处?这里,假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审法院在“诉讼主体结构安排”上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诉讼程序及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故本文也不对此问题进行深究。依照法律规定享有胚胎的监督权与处置权,那么,“监督权”与“处置权”属于何种权利呢?按照《继承法》第3条的规定,继承人所继承的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一般来说,财产所有权分为物权与债权。显然,由于胚胎具有发展为“人”的特性,它既不应当被视为“物权”,也不得被视为“债权”予以继承。由此发现,一审法院的判决在现行法律体系之下是行得通的,但在情理面前却是行不通的。法理在情理问题上遭遇了阻碍。故此,二审法院在法律与道德面前遭遇两难选择:若依法裁判,可能会降低司法公信力,引发公众不满;若服从伦理道德,则可能迫使法官超越法律裁判。更加危险的是,受精胚胎的后续处置将引发一系列的道德与法律难题。
显然,上述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均不是依法官职权所能解决的。但是坚持实用主义理念的法官会发现,“胚胎案”显然是一个偶发性事件,倘若以个案正义的偶然牺牲换取法律的可预测性、司法的公信力以及社会的稳定性,明显是一笔有益的司法尝试。这看似有违形式法治,但未必不是一种司法智慧的体现。事实上,二审法官的确遵循着这条实用主义的思维路径。在二审判决书的表述上,他通过司法言辞技术的巧妙运用,将“伦理”、“情感”、“特殊利益保护”修饰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借“于情于理是恰当的”的论证,宣布道德的胜利。
如果司法技术的运用、社会效果的忧思未能减弱法律道德主义者的胜利喜悦的话,那么,生命科技的法律限制则将展开另一重意义上的反击。在“胚胎案”中,二审法官显然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舆论事实,即社会舆论只关注司法机关如何裁判受精胚胎的归属问题,却丝毫不在意胚胎的后续处置问题。而后者恰恰才是法律的根本性难题;二是裁判假象。倘若仅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享有胚胎的处置权,可能给社会公众造成一种假象,即法律允许“代孕”。细致观察可以发现,舆论事实与裁判假象问题的交集在于胚胎的后续处置问题,也就是“代孕问题”。在我国,代孕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其次才是一个科技问题、法律问题。因此,尽管二审法院给予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道德上的支持,但是,“代孕”的技术问题与法律问题,甚至是道德问题都成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后续难题。由此观之,二审法院的裁判策略不仅成功规避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问题,而且将法律与道德的矛盾转嫁给案件当事人。这看似是伦理道德获得了胜利,但从裁判的实质结果来看,道德的司法界限并未得到扩张。同时,“体外受精技术”、“代孕技术”的法律规制仍然被严格限制在现行法的范围之内。不得不说,此判决彰显了二审法院杰出的司法智慧。
(二)“胚胎案”确立了什么?
“胚胎案”的审结,给予普通民众的是更为新奇的谈资,但在法律人看来,该案件的意义似乎远不止于此。由于科技水平以及其他制度性条件的差异,我国的个案裁判并不会产生美国法官眼中的“判例法”。即便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在试图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但在繁复且缺乏恒定标准的案例筛选机制面前,“胚胎案”最终未必能够产生制度层面的效用。因此,当下对于“胚胎案”裁判智慧的探讨,适宜从偶发性案件的层面出发,来探究该案件在中国司法文明史中的贡献。当然,按照德沃金的“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之分,“胚胎案”显然属于典型的疑难案件,即无明确法律规则的案件。那么,我们可以将前述4个定理以及4个裁判规则加以融合,凝练成为疑难案件裁判的3个指导原则。
1.对于司法裁判而言,生命科技的发展水平及其运用策略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却只能发挥隐性的作用。上文的论述已经表明,社会公众同法官的思维并不总是一致的,同理,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司法公正也非是严格形式意义上的“依法裁判”。 在“胚胎案”中,将生命科技视为上诉人道德的阻却因素(定理Ⅰ及裁判规则Ⅲ),只是对于法官裁判思维的主观描述。而且判决事实证明,这一主观描述只能存在于法官思维过程中,而无法表露于纸面或言辞上。社会公众难以在心理上接受科技对人性道德的限制(尽管理性思考后的结果确实如此)。在社会公众看来,司法裁判对公平正义的追寻,只是法律人或者国家臆造出来的“正义守恒”假象,真正令案件当事人(也可以包括旁观的社会公众)所服膺的是将被打破的正义纠正到可接受状态。即便无法回归到诉讼双方关系的原初状态,能够令胜者“心生痛快”往往也能够息讼止争。但是科技作为一种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工具或手段,显然难以产生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当然也就不会成为道德两难案件的正当裁判理由。因此,虽然科技在司法裁判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作为裁判理由而言,它的说服力尚有待商榷。值得注意的是,法官们似乎历来具有一种职业默契,即无论科技如何影响证据鉴定或司法裁判,它都不构成判决书中的纸面理由。科技的司法效用必须修饰为法律理由才得以进入判决书。这其中虽然不无法律解释技术的功劳,但如果忽略人们对法律与道德的信服力,那么该判决显然也难以服众。所以,科技的司法意义往往掩盖于法律与道德的智识性解释之下,这也使得法官的判决获得了国家与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2.疑难案件的裁判应当与公共判断相协调。“胚胎案”的一审判决表明,导致疑难案件出现的原因之一在于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然而,这种判断仅构成疑难案件的表层原因。事实上,我们对“胚胎案”的一审判决与二审判决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是依“法”裁判,但导致的判决可接受度却明显不同,而且法律适用错误并不构成二审法院改判的合理理由。那么判决可接受度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又应归于何处呢?实际上,“疑难案件”概念本身便给予了我们需要的答案。案件之所以疑难,是因为法律并未对某一类型的案件作出具体规定,因而就需要法官依据自由裁量权进行裁判。但是,问题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利弊参半”的双刃剑。对于法官而言,自由裁量权可以使得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个案正义为原则,适当地修正法律;而对于社会公众而言,自由裁量权则是法官个人偏好的法律表征。尽管法官代表的是神圣的司法机关,但裁判行为可能是在掺杂个人偏好的基础上作出的个体性行为。因此,疑难案件所反映的司法与公众矛盾,实质是个人判断与公共判断之间的矛盾。也恰是因此,在“胚胎案”中,一审法官的裁判结果被认为“不通情理”,并引发社会公众的强烈非议。二审法官则意识到,在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的情况下,法官的正义判断仅构成个体判断,是一种可能偏向原告或偏向被告的或然性判断,而社会的整体正义观念却是由社会公众共同持有的,任何违背社会公众直觉和道德认知的判决都将遭受来自公共判断的压力。因此,“司法裁判不能是法官基于个人偏好做出的,也不能是缺乏正当理由的任意决定。”*陈景辉:《同案同判:法律义务还是道德要求》,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3期。即便一审法院的判决于法有据,二审法院的裁判也需要与公共判断相协调,并在坚守法律的权威性与司法的公正性的基础上,承认法律规则、法官判断同公共判断是相一致的。
3.疑难案件的裁判应当维护法律权威。在一定程度上说,疑难案件的裁判体现了法官高超的司法智慧。他不但需要凭借判决书的制作来平息社会公众的非议,更需要在缺乏有效法律指引的前提下维护法律权威,保证法律的稳定性、有效性。对于法官而言,后者的意义显然重于前者,这是法官彰显其身份价值的核心要素。因此,“依法裁判”的法定职责势必给法官提出一个权衡难题,即如何在公共判断与法律权威之间获得平衡。事实上,法官在“胚胎案”中采取了两种策略来解决这一权衡难题:一是运用反向论证策略树立法律权威。二审法院分别基于《合同法》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规定,否定南京鼓楼医院享有受精胚胎的处置权,从而反向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依法享有胚胎的监督权与处置权;二是将伦理道德进行法原则处理,承认道德是法律原则的构成性要素。进而将合理但不合法的“道德裁判”纳入到司法领域中,并辅之以禁止性规范(即“应当遵守法律且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和损害他人之利益”)来强化法律权威。按照这一裁判逻辑,疑难案件的判决不仅是智识性的,更是策略性的。而且,法官作为司法者的身份属性迫使法官必须维护法律权威,而无论他采用何种司法策略,如解释、修辞、论证等。在此亟需澄清的一点是,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维护法律权威仅具有形式层面上的意义,或者说仅需要在纸面上或说辞上证立法律权威的存在即可,实质层面的判决仍是需要依从公众意见和法律原则进行判断。
结语
国家现代化与道德退化的悖论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除魅”效应是传统道德无法抵御的,法律亦不能阻挡这一趋势。尽管科技赋予了法律体系一整套的操作方法,而国家意志和国家机器给予法律的强硬的外壳,但社会发展所凝聚的道德规范才是真正构筑法律制度的社会基础,法律也需要从社会道德中汲取公共说服力。因此,无论是道德的回暖还是退化,它都会以一定的形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但科技则不然。在司法领域中,科技的力量必须以隐性的方式展露,它能够戳穿但不能明目张胆地指责传统道德中的“愚昧”——即便事实确实如此——国家需要道德维护社会稳定。倘若以发达或落后的科技作为司法裁判的理由,当事人很容易将国家科技水平视为败诉的原因,这既不利于国家维持自身的强大形象,也难以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所以,在理性分析无法言明的地方,法律制度的设计就需要与公共直觉相一致,而科技引发的直觉冲突则需要保持隐蔽性。当然,本文所讨论的科技、法律与道德的复杂关系只是局限于疑难案件,而未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论证。这就导致前述定理、裁判规则以及原则的普适性受到广泛的限制。当然,目前也未有哪种理论可以自信地宣布,它能够解决疑难案件中的所有难题。*波斯纳认为,试图完美的解释整个经验世界的理论并不存在,它实质上只是对经验世界的一种描述。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2, p.17.因此,本文对于科技、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司法检视,虽然在研究范围上有所局限,但却基本明晰了疑难案件中科技与道德的作用方式。至少我们对于国家现代化与道德退化悖论的起因不再混乱。
[责任编辑:刘加良]
收稿日期:2015-12-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法律冲突的适用方法研究》(11CFX0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婷婷(1987-),女,河北滦县人,中国政法大学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刑事诉讼法学。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16)01-0133-11
Subject:On Judicial Inspec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Law and Ethics——Take "Yixing Embryonic Case" as example
Author & unit:ZHANG Tingt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The nature of “disenchantment” of technology is usually disguised by the strong conflict between las and morality in hard cases. Technology not only renovated the ways of gener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of legal disputes, but remodeled the scale of alternation of traditional morality. Whereas morality set the ethical criteria for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statute law through the preponderance of humanit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 two different rulings of "Yixing Embryonic Case" show that when there is lack of statute law, technlolgy would act on legal interpretation as implicit while morality explicit, and exert influence on judicial judgment in mutual suppression. However, affected by the will power of rule of law from the state, the judges alternatively accept the guidance of technology and morality, and eventually restrict the judgment withing the frame of law.
Key words: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ethical market; legal evolution; jud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