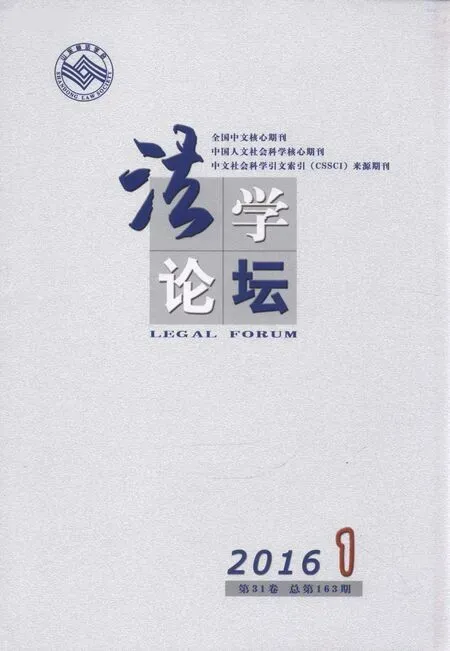死刑合宪性解释:从立场到路径的比较与反思
黄晓亮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死刑合宪性解释:从立场到路径的比较与反思
黄晓亮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摘要:站在宪法的立场上考察死刑妥当性问题,对于死刑的存废具有终极的社会意义。世界上主要存在着4种死刑合宪性解释的路径,但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人权具有普世价值,在生命权的保护上不应该存在任何例外,以人权作为死刑合宪性解释的立场对于形成一种尊重生命和人格的文化,引领公众对死刑树立起理性的认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废止死刑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增加所有国民的人权。政府应以此作为设定政策和措施的出发点,重新审视死刑在控制犯罪中的意义。从削减和废止死刑、保障人权的角度考虑社会的防卫才是合适的社会演进之方向。
关键词:死刑;人权;合宪性解释
就当前保留并适用死刑的国家或者地区而言,从宪法上考察和分析死刑的妥当性,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已经成为确然的作法。不过,语境的不同,对死刑问题进行宪法考量的深度和广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存在违宪审查的国家,关于死刑的合宪性解释,会自然延伸到违宪审查制度之中。但是,在不存在违宪审查的国家或者地区,死刑的合宪性解释就有局限性。有论者指出,我国的合宪性解释是从司法的层面上展开的,因为其并不属于违宪审查制度的内容,而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就死刑而言,同样也是如此。对死刑的合宪性解释,在实质内容上是对其是否符合宪政的价值进行反思,但是,在形式上,却仍是在司法的轨道内进行的。换言之,不管在审判活动的何种层级上进行死刑的合宪性解释,解释主体都无法舍弃具体的案件,即在案件所限定的问题类型之下,从宪法规范和精神的角度考察、衡量和分析死刑适用于具体案件(以及案件中具体的被告人)的合理性,死刑适用于该具体案件所代表之特定类型的社会现象的合理性,有时候甚至会溯源至刑法立法本身,考量将死刑规定为某种具体犯罪之法定刑的合理性。当然,不管是否从违宪审查制度的角度考量,死刑的合宪性解释都有可能关涉死刑的存废,只不过在合宪性解释包含于违宪审查制度之国家的法治中,死刑的合宪性解释会牵涉是否从根本上废止死刑的问题;在合宪性解释作为宪法之外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国家或者地区,死刑的合宪性解释同样会涉及具体犯罪或者特定社会现象之死刑废止的问题。所以,合宪性解释与违宪审查制度的关系本身对死刑存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我们可以在不过多地考察违宪审查制度的情况下比较和反思不同国家或者地区在死刑之合宪性解释方面的具体情形。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死刑进行合宪性解释,就是思考死刑的存废问题,进而可能涉及死刑的终极社会意义。
一、死刑合宪性解释的立场
人和人类社会最为根本的价值,不能不说是人权。人权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的普世性价值。*参见张旺山:《由韦伯价值哲学的观点论“人权作为普世价值”的意义》,载萧高彦主编:《宪政基本价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9年版,第85页;另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其他的社会价值,只有从人权的角度出发才有意义。*有论者从人权的角度分析反恐之措施的妥当性问题,其实也揭示了这一点。参见廖福特:《即使战争,也要人权》,载《欧美研究》2009年第39卷第4期。因而从人权的角度考虑死刑的正当性问题,是对死刑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唯一立场和路径。*有论者指出,刑罚的报应论和功利论均应受到人道主义的制约。参见李念祖:《刑罚功能与报应论均应受人道主义制约——对死刑维持论的答复》,载《司法改革杂志》2003年第47期。另参见马加福:《国外死刑存废之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考察》,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但是,在该方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其中,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的就是:为了犯罪人的人权而废止死刑,是否严重地侵犯了被害人的人权,或者因将社会公众置于严重暴力犯罪的危险境地而侵犯了公众的人权?
(一)在生命权的保障上不存在例外
生命是一切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基本载体。没有了生命,就谈不上人权问题。因而生命权是首要和基本的人权。不可否认,杀人这样侵犯他人生命权的行为,也是对被害人人权的严重侵犯。但国家以报应或者预防的名义杀死犯罪人,难道不是对第一位基本人权的否定?国家一方面宣传尊重和保障所有的生命权,另一方面却否定犯罪人的生命权,这是否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换言之,关于生命权,国家能否在生命权问题上设置例外原则?*相近分析,参见李仰桓:《联合国与废除死刑》,东海大学法律学院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笔者认为,不应当设置例外原则。既然是普世性价值,就在本意上排斥例外原则。一旦设置例外原则,那么,无法保证这样的例外原则不会变成普遍的做法,从而损害乃至替换了人权这种普世性价值。*在康德看来,正义就必须维护所有人的人权,不论远近疏远,只因为他是人,有理性,他就值得尊重。参见[美]迈克·桑德尔:《正义:一场思辨之旅》,雅言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39页。有论者从人权入宪的角度分析了《刑法修正案(八)》削减13种死刑罪名的重要意义,并从贯彻人权保障之原则的角度,主张从立法上进一步限制或者减少死刑的适用。*参见周道鸾:《人权入宪与死刑限制》,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10期。延伸该论者的思路,完全可以从人权保障原则的角度考虑全部废止死刑的问题。
(二)基于生命和人格的尊重
基于人权而反对国家设置和适用死刑,是从国家与犯罪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所提出的主张,提倡国家不要将死刑作为应对严重暴力犯罪的手段,即死刑既不应成为国家报应犯罪的手段,也不应成为国家预防犯罪的手段。
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的发生,从根本上看,与犯罪人蔑视他人生命和人格尊严的罪过态度有关。*“对某人的爱或者对某国的爱、对自由的狂热都可以做到的事,贪婪、憎恨、嫉妒怎么就做不到呢?几个世纪以来,死刑时常伴着一种野蛮的文雅,并试图与犯罪对抗;然而,犯罪却无法禁绝。”参见[法]Albert Camus:《思索断头台》,Utopia无境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8页。很多情况下,犯罪人在杀人后仍抱以冷漠的态度,也表明在意识上未确立对他人生命和人格的尊重。没有生命和人格的尊重,不仅不可能在每个人的精神和意识上确立克制情绪、反对犯罪的防线,而且无法让犯罪人在内心启动悔悟和忏悔。在这样的情况下,处死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也不过是消灭了个体的恶,却无法清除根植在社会文化中的恶,完全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而未治本。死刑在此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唤起犯罪人的人格觉醒,对社会公众的健康人格塑造也未必起到积极的作用。相反,死刑本身的存在和适用,将所有本来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淡漠化,使得政府制定任何措施的出发点并非保证有生命的每个人的人格尊严,使得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忽略了其责任更在于形成公众相互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文化。有日本学者就指出:“承认死刑制度,这只不过是刑事政策之贫乏的显著佐证”。*参见[日]尾后贯庄太郎:《死刑之去向》,转引自[日]长井圆:《死刑存废论的抵达点——关于死刑的正当根据》,载《环球法律评论》1999年第1期。我国也有论者主张生命权入宪,并强调同时对死刑的限制适用作出规定。*参见上官丕亮:《生命权的全球化与中国公民生命权入宪研究》,载《金陵法律评论》2004年春季卷。
经济转型但民主未转型的国家或者地区,固守死刑的制度,并非是为了恪守社会基本的正义,而是将统治的秩序置于首要位置,将公民(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人格和尊严作为维持自己秩序的代价。只要维持统治的秩序,即便是牺牲公民的生命和人格,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此背景之下,这些社会中的统治阶层对关于死刑的民意,固然能看得清楚,但也并不一定予以积极的引导,相反,迎合或者利用这种刑罚民粹主义,以死刑的保存和适用,制造自身维持社会正义的光辉形象,*参见[美]David Garland:《控制的文化——当代社会的犯罪与社会秩序》,周盈成译,巨流出版社2006年版,第5章。并不考虑生命和人格尊重之社会文化的建构问题。而这样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要抛弃上述对民众恩赐式的表面正义,就要考虑修复式正义的问题,从修复社会关系、恢复社会信任和尊重的角度考虑刑事措施的正当性,考虑制定合适的措施,而在此背景之下,死刑并非是必要的刑事制裁方式。
完成政治转型的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例如南非,都经历了对死刑的冷静思考,放弃规定和适用死刑,根本的意图并非为了废止死刑而废止死刑,获取良好的国际名声,恰恰相反,他们更要在全社会彰显一种生命和人格尊重的文化。换言之,废除死刑是国家尊重生命和人格的举措之一,也是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和措施之时尊重和保障生命和人格的表现之一,是一个起点而非重点,是一个契机而非最终成果。政府有必要将生命和人格尊重作为所有措施、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三)民众在道德情感上接受死刑的保留
韩国宪法法院曾分别于1996年11月、2010年2月两次做出了死刑不违宪的判决,*参见赵炳宣:《实质性废除死刑困于希望与绝望之间——韩国死刑分析》,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5期。而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院也曾以大法官会议解释的形式阐明死刑并不违宪,应予保留。*参见台湾地区当局“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于1999年1月29日所做之第476号解释。其中,他们所提到的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死刑的保留符合社会民众的道德情感。根据民众的道德情感阐述死刑在宪法上的正当性,是对“社会现实价值”的承认。*参见黄舒芃:《“价值”在宪法解释中扮演的角色》,载廖福特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六辑)》,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筹备处2009年版,第196页。但在笔者看来,上述对死刑不违宪的看法都有将刑罚民粹主义作为宪法解释根据的嫌疑。民众对死刑的态度,来源于对严重暴力犯罪的本能性恐惧和防卫态度,即便形成汹涌的民意(public opinions),也并不一定能真正地包含对死刑的理性分析。而且,当严重暴力犯罪频发,死刑也不能有效抵御这种趋势时,民众便呈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显然,民众并不深刻地追问死刑对防御犯罪的实际效果,并不考虑如何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建构预防犯罪的体系,只是产生“乱世用重典”的本能性情感反应。民众的这种本能性反应表现为坚决反对死刑废止的态度和情感。基于这种态度和情感,民众要求政府无条件地接受并予以实施,甚至不容许有妥协和让步。例如,2010年10月,台湾地区当局“法务部”部长一职被迫易人,新任部长迎合民情,依法行政,批准执行多名犯罪人的死刑。其实,与其说民众一贯地坚决支持死刑,不如说是对政府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御犯罪所表达的无奈和必然反应。*有论者指出,如果政府废除死刑、“优待”罪犯,未能保障守法公民最低限度的安全,在危害人们生命、财产的暴力犯罪日益增加的形势下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在被害人遭受暴力犯罪侵害之后不能有足够的措施抚平其肉体与心灵的创伤,那么普通人除了基于天然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罪犯的报复心理产生使用死刑的冲动之外,还能要求他们有什么“更理智”的判断呢?参见黎宏:《死刑存废的理念之争与现实判断》,载《人民日报》2010年8月31日“环球走笔”栏目。政府为了对付民怨,就将执行死刑作为民愤的发泄口,转移民众对政府预防犯罪和治理社会政策的失败或者疏漏的批评和指责。
但问题是,民众可以不理智、不理性,政府却不能不理性,司法力量更不能借口民众情感而为保留和适用死刑给自己提供理由,放弃对民众的理性引导,不考虑公共理性的塑造与发展问题。其实,加强对社会公众关于生命和人格的教育,形成社会成员相互尊重生命和人格的文化,唤醒每个人尊重生命和人格的内心意识,并基于生命和人格的尊重和保障,制定各种社会政策,建构各方面的社会制度,是比死刑更为有效的犯罪预防手段。*参见王玉叶:《 美国联邦主义与民意对美国废止死刑之影响》,载《欧美研究》2005年第4期。而且,唤醒犯罪人内心对生命和人格尊重的意识,从本心上产生罪错感和忏悔心,才能使得被害方从犯罪人身上实现对罪刑的真实报应,从根本上得到情感的弥补,抛开仇恨的情绪,以获得修复的精神状态维持一种较为安定的生活,而非永远生活于无尽的痛苦和悲伤之中。*有论者认为,犯罪人未必会真心的悔悟,但也对被害方很有作用。参见林立:《台湾的一些死刑论述之哲学检视》,载第十四届儒佛会通暨文化哲学学术研讨会《死亡作为刑罚?跨文化、跨视野的对话》会议论文集,第190页。否则,即便是处死了杀人的犯罪人,也未必消除被害方内心的仇恨,反而在加害人近亲属的内心世界里树立起了对国家、社会甚至被害方的怨恨,与被害方间又处于一种紧张、危险的关系中。此时,所谓的正义只是国家在特定案件上所宣传的符号而已。显然,真正理性的民众并不欢迎这种所谓的正义。
我们应当相信民众的理性判断。不管是我国大陆地区还是我国台湾地区,乃至其他国家,例如日本、美国,在保留并适用死刑的情形下,早就有各自的刑事法学者分别就死刑存废问题进行过民意的调查。绝大部分的民众在废除死刑,但对严重暴力犯罪适用不得假释和赦免的终身监禁的问题上持认同的态度。可见,对于普遍而毫无例外地实现人权,同时又尽可能严密地预防犯罪,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民众并非不能走上理性的道路。在普遍实现生命和人格尊重的社会环境下,形成对死刑的公共理性认识,并非是遥不可及的痴人说梦。*有论者指出,每一位公民的道德直觉,除了民主政治文化素养之外,也有来自于更高层次的信仰(罗尔斯所称之“整全性学说”),假如这些信仰与信念并不违背民主政治的公共文化,则只有通过理性与沟通才有可能改变、内化某些政治价值成为我们民主生活的一部分。参见萧高彦:《死刑:政治思想与哲学的省思》,载《思想》2010年第17期。
二、死刑合宪性解释的路径选择
当前,纵览世界上保留死刑之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机构对死刑的认识,以国家的名义公开发布有关死刑政策的模式多种多样,主要有:(1)宪法法院解释模式。如前所述,韩国宪法裁判所曾分别于1996年11月、2010年2月两次做出死刑并不违宪的判决;(2)最高司法机关解释模式。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于1972年判决死刑违宪,但于1976年恢复死刑,认为死刑并不违宪;(3)国家立法机关解释模式。对于中国大陆地区来说,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享有对法律的最高解释权。但这只是对死刑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模式,并未实际发生;(4)国家元首或者最高行政首长解释模式。例如,2003年底,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颁布了暂停执行死刑法令, 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地方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标志着哈萨克斯坦向着彻底取缔死刑迈出了决定性的积极步骤。*参见蔡桂生:《死刑在印度》,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页。根据对上述情形予以反映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了解保留死刑之国家或者地区进行死刑合宪性解释时所因袭的路径。
(一)以社会保护为路径阐述死刑的合宪性
台湾地区当局“司法院”第六届大法官会议于1999年1月29日作出第476号解释,在总体上认为“关于死刑与无期徒刑之规定,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因而“无违宪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与宪法第十五条亦无抵触。”换言之,台湾地区“司法院”认为,死刑的存在是以法律的形式,为了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且确有必要限制公民的生存权。该解释尽管也考虑到了基本人权问题,但在死刑存在的理由上却强调了社会保护的问题,即从秩序价值的合理性以及与人权的关系等角度来分析死刑的合宪性问题,因而其分析的路径并非人权,亦非公民的自由及权利。尽管其分析考虑到了宪法比例原则,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就死刑合宪性的解释说辞没有过大的差异,但在人权价值已经深入人心,接受基本文化教育之现代人均尊崇人权的情形下,上述解释丝毫不直接提及死刑是否违背人权的问题。因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增进公共利益”的必要性,与死刑是否侵犯人权,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有着不同的思维进路,无法相互替代。因而以国家的现实需要本身为根据而设置侵犯人权的刑事处罚,正当性究竟在哪里,底限又是什么,如何防止这种死刑立法模式的肆意妄为呢?上述解释完全予以回避,在阐释上显得过于笼统和含混。
(二)以国民情感和国情为路径阐述死刑的合宪性
韩国大法院于1962年10月19日对某案件辩护律师所提出死刑违宪审查发表意见,认为“现在考虑我国实情和国民的道德感情等因素,作为国家刑事政策,为了维持秩序和公共利益,刑法、军刑法等即使规定了死刑这种处罚种类,也不可以认为是违宪条款”。此后,大法院在多个有关死刑的判决中重申上述认识,将“实情和国民的道德感情”作为在刑事政策上保留死刑的根据。韩国宪法裁判所在1996年11月作出判决,将上述所谓的“实情与国民感情”予以具体化,认为死刑是“对犯罪报应心理的一种必要的‘恶’”,是“为了保护与犯罪人生命和价值相同的他人或其它多数人生命的不可避免的选择”,且“从文化水平和社会现实来看,促使死刑完全无效是不妥当的”。*参见[韩]全智渊:《大韩民国的死刑制度》,载京师刑事法治网http://www.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showpage.asp?pkID=21778。这种论述同样是没有从人权的角度展开分析,判断多于有理有据的阐释,显得粗疏。而且,在笔者看来,宪法裁判所将死刑是否违宪的判断寄托于国民情感,似乎是期待从公共理性的角度寻找根据,但这似乎找错了路径,普通国民的情感与公共理性完全不能等同,相反,二者可能大相径庭,民众情感的随意性特征很容易民粹化,使得死刑的认识陷于民粹主义之中,企图以大多数的非感性力量驱退人权路径上的死刑认识。
(三)以死刑与生命权、人格尊严关系的路径阐述死刑合宪性
韩国宪法裁判所于2010年2月25日所做的死刑判决,比较全面地从死刑限制生命权、人格尊严的必要性、正当性以及是否违反比例原则的问题,主要内容有:(1)生命权也属于《宪法》第37条第2项所规定的法律保留对象;(2)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对这些极其严重的犯罪,处以与其违法程度相适应的严厉刑罚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非常必要的手段,死刑正是其欲实现社会正义的必要的手段之一;(3)死刑是仅适用于那些极其严重犯罪,而且死刑制度本身都具备了立法目的的正当性、手段的适合性、损害的最小性、法益均衡性等因素,所以在限制生命权方面,不违反宪法上的比例原则;(4)死刑制度是仅针对那些无视刑罚,实行极其严重犯罪的罪犯在罪责刑相适应的范围内适用的,是犯罪人自己残忍实施犯罪行为的自食其果,所以,不应当认为此种刑罚制度只是为了追求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把罪犯当做客体侵犯其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而违宪。*该判决载于韩国宪法裁判所官方网站:http://www.ccourt.go.kr/home/view2/xml_content_view02.jsp?seq=22893&cname=??&eventNo=2008??23&pubflag=0&eventnum=25378&sch_keyword=&cid=01020002。可以看出,韩国宪法裁判所是从人权的角度全面地分析死刑是否违反比例原则、生命权是否为法律所保留、死刑是否侵犯人格尊严等问题,尽管其要比1996年11月所做的判决更为详尽和深入,但其答案却都显示出死刑并不违宪的意思,似乎是在预设死刑不违宪这一目标的情形下进行死刑支持论者的论证,其中颇多矛盾之处,如承认生命权的绝对性,属于先验于宪法的自然权利,但却认为宪法可以对该权利进行法律的保留,给予宪法的限制,因而受到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参见[韩]赵炳宣:《实质性死刑废除困于希望与绝望之间——韩国死刑问题分析》,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5期。
(四)以死刑是否属于残酷刑罚的路径阐述死刑的合宪性
对死刑是否属于残酷刑罚而侵犯人权来分析死刑合宪性问题的国家主要有美国和日本。其实,日本的最高法院更早地对其死刑是否属于残酷的刑罚、是否违宪的问题通过具体死刑案件的判决来进行阐述。日本最高法院在1948年3月12日针对一起杀害近亲属并遗弃尸体的案件作出判决,并在其中指出,生命为一切之基础,因而死刑属最为严厉之刑罚;剥夺生命之行为本身并不视为残虐,但死刑执行的方式则涉及残虐性,肉体的痛苦来自于执行死刑方法本身;日本的死刑执行并不存在精神层面、肉体层面的不必要痛苦,因而并不构成残虐的刑罚。*参见赖文荣:《日本国死刑废止论之研究——以日本国宪法与自由权公约第六条为核心》,淡江大学日本研究所2006年6月硕士在职专班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而美国则较晚,其于1976年通过Furman v. Georgia案考察和反思死刑是否属于残酷与不正常刑罚(cruel and/or unusual punishment),暂时性地认为,当时美国的死刑不符合人性尊严;死刑非防卫社会必需,是过度的刑罚,存在歧视性、随机性适用的情形;死刑适用达到了罕见的程度,无法达成阻赫犯罪、满足报应需要后者其他刑罚目的,因而是过度的刑罚。*参见王玉叶:《欧美死刑论述》,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8月版,第102-103页。比较日本和美国最高法院不同的阐述,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存在认为生命权有绝对性因而死刑作为最严厉刑罚是合理的这样的矛盾性质,且决断性地认为,死刑即便是对有绝对性之生命权的剥夺,但并不残虐,因而并未不当限制基本人权,从而具有合宪性。而美国最高法院上述死刑判决却保留了一定的开放性,认为死刑之所以侵犯人格尊严,之所以非常残酷,是因为存在不当的适用,即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
果然,在1976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Gregg v. Georgia以正当程序原则,认为“谋杀罪判处死刑并非必然在所有情况下均为违反宪法增修条文第八条及第十四条,关键在于死刑不得武断或者恣意地适用,要符合这样的要求,可以透过周密订定的法律,确保审判机关获得适当的信息与指导”,*参见王玉叶:《欧美死刑论述》,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8月版,第122-123页。从而在实际上恢复了关于死刑合宪性的认识。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最高法院以正当程序来拯救了其死刑在美国宪政中的地位,或者是通过死刑案件来完善正当程序原则的不足,也就是说,对人权的保护,并不希望通过废止死刑来完成,而是希望通过其不断修补正当程序原则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该1976年刑事判决延续了1972年判决之开放性特征。不过,不同的是,1972年判决所保留的开放性是死刑因正当程序原则和规定被完善而可能合宪,1976年判决则保留了随着成熟进步社会演进的适当标准(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而宣布死刑逐渐不合宪应被废止的可能性。正是基于该演进的适当标准,美国最高法院在2002年通过Atkins v. Virginia案认为对心智障碍犯罪人执行死刑,属于“残酷且不寻常刑罚”而违反宪法;在2005年通过Roper v. Simmons案认为,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在适用最严厉刑罚的极端可责性(extreme culpability)的范围内,演进的适当标准须与时俱进,因而对未成年人适用和执行死刑是违反宪法的。这种根据演进的适当标准来判断死刑是否属于残酷且不寻常刑罚的思路,其实将死刑是否侵犯人权的判断寄托于利伯维尔场经济下民主社会的民意,未必不是一种刑罚民粹主义的思路。*有论者认为,“把死刑判决与民意结合在一起,在增加了死刑判决合法性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也把死刑制度置于一个开放的民主决策体系之中,不肯越过民主程序一举废除死刑。因此,就未来而言,如果民意倾向于废除死刑,美国就有可能废除死刑,如果民意支持更多地适用死刑,也有可能保留死刑,甚至增加死刑的适用。”参见张守东:《美国死刑制度的宪法法理及其未来——以Kennedy v. Louisiana案为例》,载《法学》2011年第3期。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更多的还是从人权的角度探讨死刑是否残忍地侵犯了生命权、人格尊严的问题。
当然,在理论上看,有关的分析在路径上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即综合多种路径来分析死刑是否在宪法上有正当性的问题。如有论者认为,对于侵犯生命之犯罪的死刑,无论是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人的尊严的根本性维护的层面上,还是在对具有现代建设性意义的社会契约理论的承袭上,抑或是对民众意见的现实考量上,都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而非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犯罪的死刑,却缺乏这些基本的宪法正当性。*参见范进学:《论我国死刑的宪法正当性》,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综合性的路径却避免不了在基本人权问题上的缺漏,将配置死刑作为法定刑的犯罪区分为严重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和非严重侵犯生命法益的犯罪,本身就是以国家、公共利益为路径有选择性的安排和决断,在死刑是否侵犯人权的问题上作出两种不同的回答,其实也是以两种不同的标准来对待和保障人权,因而其局限性自不待言。
三、以人权为立场进行死刑的合宪性解释
上述有关死刑合宪性阐述的路径选择,并非都体现出人权的立场。在笔者看来,前两种路径就没有体现出人权的路径,因为其所主张的理由和根据并没有放在人权的天平上进行全面和详尽的衡量,根本就没有围绕人权体系中最为基本的范畴——生命权、人格尊严进行必要的分析和阐述,更遑论对死刑与生命权绝对性的关系、死刑是否侵犯人格尊严作出蛛丝马迹的解释,因而虽然是纯粹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却丝毫没有体现人权的色彩。也正因为这一点,其却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受到反对废止死刑论调的赞同和拥趸。至于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倒不是作为知识精英的宪法法院工作团体,缺乏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和人权价值观念,而是因为面对理性与非理性混杂的公众选择时,他们担心政府被民意所抛弃,不得不做出全面的退缩,连去疏导引领公众趋向死刑的理性认识也顾不上了。即便是在对支持死刑的民意进行疏导,也可能面临死刑保留论者的反驳和批判。*参见于志刚、曹晶:《美国的死刑保留政策与新死刑保留主义———当前死刑存废之争的域外答案》,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
后两种路径自然是从人权的立场出发,对死刑与人权之基本范畴的关系问题作了分析和响应。但是,依据后两种对死刑合宪性作出肯定结论的不同国家却在分析逻辑上体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韩国宪法裁判所在2010年所做的判决,认为生命权属于法律保留的对象,不具有绝对性;死刑因其所适用之犯罪人的最严重罪行而具有内在适当性。尽管该判决是从人权的角度作出的,但是,其却明确、断然地得出了死刑不违宪的结论,对死刑与生命权绝对性、人格尊严之关系所做的答复也具有决断性,因而与1996年的判决相比,反而失去了开放性,毕竟1996年死刑判决将死刑不违宪的根据放在国情和国民感情上,至少给未来依国情变化和国民情感改变而改变死刑合宪性之认识留下了可能通道。同样,日本最高法院1948年刑事判决所做的死刑不违宪之论也具有这种封闭性,不必再做赘述。但是,值得称道的是,美国针对死刑所做的几个判决,在死刑合宪性的问题上却具有开放性——尽管这种开放性并非完全为了寻找死刑废止的根据。在其1972年判决中,仅有两名法官(Brennan、Stewart)认为死刑“否定了人类的尊严”,“弃绝了人道的观念”,其他人则认为无法证明该刑罚的功效,且存在不公平适用的情形,因而死刑是“残酷且不寻常的刑罚”;后来1976年判决藉助上述适用的正当程序问题,根据各州死刑制度改革而认为死刑适用基本上是按照正当程序进行的,进而认为死刑不违宪,同时,又确立了“成熟进步社会演进的适当标准(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来考察死刑是否属于“残酷且不寻常的刑罚”,从而又保留了一种开放性,但除了提出不同意见书的Brennan法官指出死刑有损人类尊严外,均未对死刑与生命权绝对性、人格尊严的关系作出任何分析。从其2002年判决、2005年判决来看,美国最高法院依据上述开放性标准来考察死刑是否属于“残酷且不寻常的刑罚”而应废除,其实,所主张的是“不符合正当程序的死刑有违于宪法”,采用了渐进式的死刑废止策略。
显而易见,在死刑的合宪性解释上,必须正面应对死刑是否侵犯人权的问题。对此,以笔者之见,从我国当前的法治语境出发来分析死刑的合宪性问题,应注意如下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刑罚的文明发展要求按照人权的路径去考量死刑的合宪性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刑罚经历了从残酷到文明的过程,即便是文明的刑罚,其判断标准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朝着更为人道的方向发展。清朝末年沈家本的刑罚改革,只不过是将多种多样、以残忍为特点的死刑执行方式予以唯一化,实现死刑执行方式的唯一性,却被认为是中国死刑的重大进步,就是因为在死刑执行方式上体现出保障人权的意味。但我国关于死刑制度之文明进步的认识却并未停滞,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从制度上倡导和推行死刑缓期执行,又将死刑执行朝着人道和文明向前推进一步。而这一切其实都是围绕着更好地保障人权的问题展开的。《刑法修正案(八)》削减13种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将死刑制度又朝着文明的方向提高到一个新的程度,在人权保障的制度发展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法治价值。*参见高铭暄、黄晓亮:《削减死刑罪名的价值考量》,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12期。《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削减死刑罪名,有九种之多,且开始涉及暴力犯罪,尽管是非致命性的,但仍是对死刑制度文明程度的提升,是对宪法中人权保障之原则的贯彻。*参见赵秉志:《中国死刑立法改革新思考》,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从上述立法举措来看,国家立法机关废止大量非暴力犯罪之法定刑中的死刑,在思维逻辑上,自然是认为死刑适用于这些具体犯罪,不符合刑罚的文明标准,在根本上侵犯了人权。因而刑罚的文明标准在于人权本身,刑罚之文明程度的提升,体现为对人权越来越高的重视和保障,国家在刑罚的残酷性方面逐渐退缩。延续此思路可以进一步认为,对暴力犯罪规定并适用死刑,其实也有违于人权,因而不符合宪法的规范和精神。
(2)刑罚的文明程度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不存在停滞的标准来判定死刑,或者适用于暴力犯罪的死刑,就必然合乎宪法。刑罚是人类社会现象的一种,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刑罚的文明程度也必然不断提升——尽管在一定的时期,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刑罚在文明程度上参差不齐,甚至大相径庭。如前所述,即便是在美国,联邦法院后来提出保留并适用死刑,但也没有完全断绝死刑制度之文明发展的可能性,对废止死刑的州也并不判定违宪,相反,其所提出的“演进的适当标准(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保留了死刑可能违宪的认识可能性,而这符合人们对人权之性质、内容、范围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更新认识的客观情形。其实,对于那些以国家或者公共利益、民意为路径分析死刑合宪性的论点,我们无需过多给予批驳和否定,因为他们并未看到,即便是国家或者公共利益、民意,也并不是停滞于一时的;他们以此主张死刑的合宪性,也只不过是没有看到公众尚未达成死刑违宪的共识而已,因为公共利益有一个价值追求的“共识”作为基础,而“共识”的达成在于各方的利益得以协调,*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这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人类社会注定会尽力摆脱消极的人性,向积极的人性发展,在法律上体现出更为强烈和浓郁的人权保障精神。*参见王永宽:《扭曲的人性:中国古代酷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当然,这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更好的社会制度会促进人权保障的进步,人权意识的强化和保障的巩固也会推动社会制度的文明进步——包括刑罚之文明程度、死刑制度之文明程度的提升。
(3)死刑是否侵犯人权的问题,与犯罪同样也侵犯人权(及其集合起来形成的公共利益)的问题,在现代法治语境之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现代社会早已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简单报复型社会,而且,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文化还尽可能压制那些报复性的行为,以国家惩治来替代私人报复,以文明手段替代野蛮举动。因而尽管国家在很多时候代表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但对国家的治理在文明上有更高的要求。毕竟,人们的权利并非国家所赐,相反,国家的权力却是民众所赋。因而国家不能像犯罪侵犯人权那样,以侵犯人权的方式去应对犯罪,对付犯罪人。一旦容许国家以侵犯人权的方式管控社会,那么,权利保障的底线就无处可寻。也因此,国家管控社会的措施,会时时处处面临是否侵犯人权的诘问。我们不难理解,即便是死刑在一定时期在宪法上有合法性,仍需要接受合宪性检查。*参见韩大元:《死刑立法的宪法界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那种以犯罪侵犯人权而认为死刑不违宪的观点,其实是一种缺乏根据和说服力的空洞言说。国家将严重危害行为规定为犯罪,规定相应的刑事处罚,本身就是对犯罪活动侵犯人权之属性的否定,对罪犯不尊重他人权利的谴责,但这并不是国家能够以任何形式、程度侵犯罪犯之人权的理由,相反,国家的惩罚必须具有正当性,才不会肆意妄为,而正当性的判断自然就是对作为罪犯之公民的权利的剥夺或者限制,是否为惩罚犯罪所需。从人权的角度看,该问题同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会有不同的答案,剥夺或者限制之公民权利会逐渐缩减。
综合上述分析,从人权的立场上寻找死刑的合宪性解释路径,必须对死刑与生命权绝对性、人格尊严的关系作出回应,而且,这种回应也不应当是封闭式的,相反,应处于开放状态——哪怕承认国民对该死刑不得有违于生命权的观点有个逐步接受的过程,死刑违宪的最终结论取决于国民对上述观点的接受和信奉。如此看来,死刑问题上的刑罚民粹主义似乎是不得已的选择。美国最高法院的做法体现出务实的风格——问题是,民主程序本身不足以推动死刑之民粹主义的改变,政府应当做些什么呢?在此问题之下,我们应该将死刑废止的问题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即废止死刑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增加所有国民的人权,每个国民相信并尊重生命权的决定性,尊重他人的人格,从尊重自己和他人生命与人格的角度出发设定任何活动的动机和意志,把社会力量而非他人和自己的生命人格实现自己价值的手段。政府有必要从此处设定政策和措施的出发点,将更多的工作落在预防犯罪、减少来自于民众内部之暴力的实处。*废除死刑已经60多年的德国发展出了较为完善的保安处分制度。参见[德]阿弥·弗里奥夫:《德国的刑罚与保安处分》,载台湾地区废除死刑推动联盟主编:《死刑存废的新思维》,元照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9-72页。
结语
生命权之有无绝对性,似乎已经成为不必争论的话题。人权价值的普遍性已经向我们表明了基本的答案。但是,在死刑剥夺生命是否属于残酷刑罚,是否违反宪法比例原则的问题上,保留死刑的少数代表性国家宪法法院却做出了否定的回答,避开了死刑以何为依据剥夺有绝对性的生命权的根本问题,与废除死刑的国家或者地区表现出完全迥异的态度,*欧洲国家逐渐普遍认同生命权的绝对性而否定死刑的存在和适用,但在堕胎和安乐死的问题上对此予以回避。参见廖福特:《生命权与废除死刑——欧洲理事会观点之分析》,载《政大法学评论》2006年8月第92期。根据似乎是以民主为名义的刑罚民粹主义,好像对民主背景下的公共理性有着深厚的信任和依赖。与此类似,中国大陆对此即便不是寄希望于民众的理性,但也往往以国情作为当前保留和适用死刑的理由,*参见《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答中外记者全文》(2005年3月14日),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3/14/content_2696724.htm。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迄今为止国家关于死刑存废的唯一明确公开申明。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至今并未对此公开表示意见。并没有提及人权的根据问题,对通过刑事法治实现社会转型下的司法正义显然存在不足之处,因而有必要从人权视角重新审视死刑在各项政策措施中的意义。也有论者避开生命权有无绝对性的问题,从平等权的角度考虑死刑违宪问题,企图以新的路径讨论我国废止死刑的可能性。*参见刘春花、范国强:《死刑违宪新论——以宪法上的平等权为视角》,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此论虽有新意,但仍偏离了问题的实质,因为不回答包括生命权在内的人权在死刑制度中的位重问题,就仍然难以阐明死刑在宪法规范和精神中的实际意义。所以,在任何社会中,人权深入人心,成为政府和民众行为的圭臬,才能减少乃至消灭来自于国家和社会个体的暴力。从削减和废止死刑、普遍保障人权的角度考虑社会的防卫,似乎才是合适的社会演进方向。
[责任编辑:谭静]
收稿日期:2015-12-0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北京师范大学自助科研基金项目(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刑事一体化的现实建构》(SKZZY201406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晓亮(1976-),男,河南平顶山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刑法、区际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16)01-0093-09
Subject: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Death Penalty: the Comparis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Stance and Path
Author & unit:HUANG Xiaoliang
(College for Criminal Law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It truly has a great ultimate social significance to review the propriety of death penalty based upon the Constitution. There is an inevitable limitation among the worldwide four mainly methods of the death penalty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more or less. Human rights have wide-spread value in the world so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excep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life. Hence, we should review the death penalty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ground of human rights, which may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haping a form of culture that values people’s life and personalities and leading the public to set up a rational knowledge about the death penalty. Government should set the real intention which is to add of human rights to all citizen rather than abolishing of the death penalty itself,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carry out all policies and measures, and rethink the role that the death sentence played in controlling cr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mitation and abolition of death penalty,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social defense is actually regarded as the right direction of social evolution.
Key words:death penalty; human rights;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