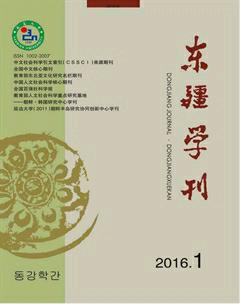在韩延边朝鲜族务工群体的社会适应及其障碍因素
李梅花 郭跃
[摘要]韩国各地有很多中国延边朝鲜族务工人员,通过对他们的个案访谈,剖析其身体、语言、居住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是如何限制其适应韩国社会的,并指出在韩国社会的接纳和排斥之间,朝鲜族务工群体只是“选择性”地适应韩国的社会生活,在深层融入韩国社会方面仍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关键词]韩国;朝鲜族;务工群体;社会适应;障碍因素
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中国朝鲜族发生了急剧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跨国(特别是赴韩)流动人口的增多和膨胀。据韩国法务部统计,截止到2015年6月,在韩朝鲜族总数为616,109人,可以说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一多的中国朝鲜族正向韩国流动。跨国(主要是赴韩)人口流动在延边朝鲜族聚居地区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成为了影响其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总体上来说,朝鲜族在追寻所谓“韩国梦”的过程中获得了物质利益,但同时这种跨国流动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例如,人口流失严重、低生育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农村社会空心化、耕地抛荒、民族教育危机等。现有研究大多关注跨国流动和迁移对朝鲜族社会发展的影响,却很少以跨国流动群体为主体,探讨跨国流动对其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影响。而且,国内学者以中国为出发点研究跨国流动对朝鲜族的影响,韩国学者则以韩国为中心探讨朝鲜族跨国流动群体给韩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这种分别以流出国和流入国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使得朝鲜族跨国流动群体被双重边缘化,其在跨国场景中的行为和心理,特别是在流入国的社会适应和融入,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全面解释。鉴于此,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在中国延边、韩国首尔等地对10多名在韩务工延边朝鲜族进行的个案访谈,以其日常生活经验为主要分析维度,从身体、语言、居住空间、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从微观角度探讨他们在试图实现“韩国梦”、在适应流入地社会过程中面临的壁垒和障碍。
一、工具性身体与社会区隔
身体除了具有生理学或生物学的意义外,还蕴涵着重要的社会性,是获取社会地位的重要工具,同时又是造成社会区隔的核心要素。事实上,人的根本性差异铭刻在身体之上,身体带有社会阶级的印记,身体的差异不仅是各自“身体”的差异,更是表明了身体所处的两个世界的差距。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身体体现为一种资本形式,是区隔权力和地位的独特性符号,不同的阶级或群体往往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身体取向,创造出多种身体形式。在当代社会,身体在权力的实施和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中扮演着非常复杂的角色,身体往往不容辩驳地被打上个体所属社会阶级的印记。他还举例说,工人阶级生产出的身体形式所构成的身体资本,其交换价值要低于支配阶级生产出的资本形式;工人阶级的身体特征(如口音、姿势和衣着)所获得的评价,普遍不如其他社会阶级生产出的身体形式那么高。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也认为,外显于身体的服饰、表情、姿态以及语言等特征,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意义,不仅体现了群体的边界,也成为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身体外貌涉及所有身体表面的那些特征,如包括穿着和装饰模式,而特定个体和他人都可看见这些,并且往往用它们作为线索来解释行动。”
在赴韩务工初期(20世纪90年代),延边朝鲜族粗糙黝黑的皮肤、灰暗土气的服饰、疲倦紧张的神情、粗犷硬气的口音等外在特征,形成了他们身上独有的“朝鲜族味”,让韩国人一眼就能够识别出他们的身份。即使到了现在,朝鲜族在韩国务工的环境和条件相对过去有了很大改善,很多人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乍看起来与韩国人并无不同,但是韩国人仍然能够迅速识别出朝鲜族的身份,并自觉不自觉地对其“分类”,进而调整互动方式。对此,一位被访者这样谈起自己的经历:
我是2007年的时候嫁到韩国的,老公对我很好,我的衣服和化妆品说实话比一般韩国女人高级多了。老公的公司经常举办那种夫妻都参加的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老公同事的老婆们对我都很友好,在她们打量我的服饰的眼神中,我看到了羡慕和嫉妒,心中很是得意。不过,当她们了解到我是朝鲜族的时候,不知为何,态度上有了微妙的变化,她们的聊天内容也不再是我所能参与的,我只能尴尬地坐在旁边。后来,这样的聚会我就尽量不去了。(被访者崔某,女,34岁,2007年去韩国)
很多被访者也表示:“到韩国就是来挣钱的,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干活,穿好衣服太浪费了,好衣服回国的时候穿。再说了,你穿得再好,人家也认为你是来打工的,你的身份就摆在那里。与其在穿着打扮上花钱,不如把钱存起来。”
这表明,朝鲜族务工人员对自己身体的使用大多限于获取经济资本,而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再生产出具有更高价值的身体资本形式,因为形成更高身体资本形式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按照有关身体的社会学理论,体力劳动者和他所属的身体之间存在一种工具性关系,身体成为实现其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朝鲜族赴韩务工人员的身体不仅是他们挣钱的工具,满足“过日子”的直接需求,同时也是体验各种疼痛的物质性存在。他们在韩国大多从事当地人不愿从事的“脏(dirty)、难(difficult)、危险(danger)”的3D工作。那些在工厂或饭店打工的朝鲜族,平均一天要工作11-13小时。例如一名来自图们的朝鲜族,他在一家土特产品加工厂工作,平均每天要在11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内将5吨重的橡籽分放在机器上。由于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很多人虽然挣到了钱,但身体却被严重损耗,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是2002年以研修生的身份来韩国的,在杨平(音译)工业园的一家印刷厂打工。刚开始,一个月只能挣80多万韩币(相当于当时人民币五、六千元)。我为了多挣钱,几乎每天都加班。老板看我工作认真,几乎把印刷厂都交给我了,自己偶尔过来看看。印刷厂的机器一直开着,声音隆隆的,辐射也大,对身体不太好。我在那家厂干了十来年都没换地方,老板也给我涨了工资,每个月能挣个一万多人民币。近几年,我一进印刷厂就浑身冒虚汗,头晕恶心,所以就回国了。(被访者李某,男,54岁,2002年去韩国,2014年回国)
对于在韩务工的朝鲜族而言,由于他们的身体往往被置于传统观念中底层的服务场景中,打工过程中的身体经验,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心理上,都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们是身处韩国社会底层的“他者”。
我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星期天休息。回到自己租的房子,一点都不想动,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酸痛。不过最闹心的是,韩国人对我们朝鲜族的差别待遇。同样是服务员,他们的态度还分个三六九等,对朝鲜族,就是呼来喝去的,小费要么不给,要么给得很少,而对韩国的那些“阿祖玛”(韩语,大婶、大妈之意),他们的态度就很客气,不太使唤她们。(被访者李某,女,52岁,2012年去韩国,2015年初回国)
二、“延边口音”与社会区隔
朝鲜族踏上赴韩务工之旅,这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过程,更是一次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的过程,需要重新调整其心理归属和行为方式。尽管朝鲜族和韩国人“同源同族”,但由于双方长期生活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其价值观、生活模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差异,所以很多朝鲜族来到韩国后都经历了“文化冲击”。赴韩务工朝鲜族为了适应在韩国的生活,往往被迫或主动调整自身的心理和行为,但他们却很难或者说是不愿意接受韩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而韩国社会虽然认可朝鲜族是“同族”,但常常对其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用被访者的话说:“就像对待农村的远房亲戚一般,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瞧不起和怜悯”。
被访者普遍反映,韩国人(特别是首尔人)特别“爱算计、斤斤计较”,“功利主义”,“用得着你的时候呢,就特别热情,用不着你的时候就装作没看见”,“人情非常冷漠,不像咱们延边人那么热情厚道”。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看来,这种所谓的“冷漠”、“算计”,是保护自己不受外部威胁和伤害的理性表现,因为典型的大城市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复杂多样,那么多人聚居在一起,利害关系千差万别,如果不精于计算,他们之间各种往来的有机联系就会被打乱。同时,频繁的流动和瞬息万变的生活特点也迫使城里人矜持起来,他们不可能对所有接触的人做出内心反应,这也往往让来自小城市或者农村的人以为他们冷漠无情。对此,朝鲜族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在韩国遭受的“差别待遇”,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来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是从事底层行业的“在中(国)同胞”。
的确,韩国人对朝鲜族的显性或隐性排斥,更多是和经济因素相关的阶层排斥,因为在韩国人心目中,朝鲜族即“在中(国)同胞”已然被贴上了“来自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劳动者、“从事3D职业的底层劳动者”的标签,从而成为“差别与歧视”的对象。特别是,粗犷、淳朴、彪悍的“延边口音”,成为了朝鲜族在韩国社会被区隔的象征性符号。于是,是否能够说一口标准流利的首尔话,成为朝鲜族适应韩国当地生活的重要条件和资本(在初期更是掩饰他们在韩国非法滞留打黑工身份的重要手段),不少朝鲜族极力让自己的韩国话说得更地道些,以掩饰自己的“在中同胞”身份,但实际上他们的口音(延边话)很难消除。很多被访者表示,本以为和韩国人语言相通,容易沟通,但没有想到,韩国的朝鲜语和延边的朝鲜语在语调、词汇、语法,甚至表达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别,特别是韩国的朝鲜语中夹杂着英语等外来语,所以和韩国人接触的时候,常常因为语言发生一些误会,甚至在感情上受到伤害。
我在国内的时候是护士,所以到韩国找工作的时候,职业中介所好几次都推荐我去当保姆,说是看孩子,但都被雇主拒绝了。他们不要我的理由是,我说的是延边方言,怕孩子跟我在一起学会了延边话。(被访者石某,女,57岁,2008年去韩国)
我刚来韩国的时候,在一家旅馆做清洁工。有一天休息的时候,老板凑过来对我说,想不想在韩国找爱人啊?我很认真地告诉他,我在中国有爱人了。他用很暧昧的眼神看着我说,你在中国有爱人啊?从那以后,他总凑到我旁边,动手动脚的。我把这事告诉了一起干活的韩国大婶,她听完就骂老板不是东西。原来,在韩国语里,“爱人”是情人的意思,而在中国,我们通常把自己的丈夫或妻子称为“爱人”。难怪他用那样的眼神看我,原来是把我当成不正经的女人了。(被访者全某,女,44岁,2002年去韩国)
延边口音作为朝鲜族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身份象征”,之所以在韩国社会被负面性“他者化”建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朝鲜族务工人员缺乏在韩国当地生活竞争所必要的文化资本。大多数赴韩务工的朝鲜族并非精英移民,较低的文化水平、职业技能的缺乏使他们缺乏竞争意识和竞争素养,在精英云集的韩国都市社会里,他们往往被挤到当地人不愿意从事的3D行业中,而底层职业意味着较低的经济收入和社会评价,因此朝鲜族在韩国很容易被当地社会排斥。不过,随着韩国海外移民政策的改善和宽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韩国社会对来自中国的朝鲜族也不得不另眼相待,朝鲜族不用像过去那样在韩国非法滞留打黑工,也不再避讳自己的延边口音,近来在首尔街头随处可见朝鲜族用延边口音聊天。
三、“同胞村”与孤岛效应
居住空间不仅是单一的物理环境,还是识别不同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所言,“空气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城市空问结构实际上体现了城市分层的结构。居住条件的差异,影响着人们的身份认同和心理归属,强化着不同社会群体的边界,进而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志。朝鲜族赴韩务工人员主要从事3D行业,其经济收入主要寄回国内用于各项开销,所以一般不会在韩国的居住条件上投入太多,用他们的话说,“有地方睡就行了”。所以,他们大多租住在廉价的地下室、半地下室,或者滞留在教会的收留中心,或者在诸如饭店、工厂宿舍或者看护病房等工作场所解决睡觉问题。这种迥异于当地市民的“居住差异”(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不仅造成在韩务工朝鲜族和韩国当地市民居住生活上的空间隔离,事实上也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隔阂。
我是2002年来韩国的,没地方住,就睡在公司的集装箱里,公司中午提供午饭,早饭嘛,我头两年都是吃方便面。现在,我老婆和儿子也出来了,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干活,没办法住在一起。我到韩国三个月,就见了我老婆三次。现在家里人都出来了,怎么也得有个团聚的地方啊!所以,我花了500万(韩币)抵押金租了一个房子,每月租金20万。(被访者吴某,男,65岁,2002年去韩国)
我弟弟在加里峰的工地上干活,他和老婆、孩子一起住在出租房里。我休息的时候,我弟弟一家都在上班干活,所以我一个人住在他们家的时候多,倒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感觉,但怎么说都不太好。这里也有我同学和老乡,有时候也住在他们那里。(被访者崔某,男,55岁,2000年去韩国)
我和女儿租了一个半地下的小房子,挺便宜的,十多万韩币,但是见不到光,大白天都要开着灯,不然太暗了,又潮。这里哪能和国内比,我去年在延吉买了100多平方米的公寓楼房,现在空着呢,以后回国养老的时候住呗。我二姐也在韩国打工,主要是看护病人。她根本没有固定地方,有患者看护的时候,就在病房里打地铺,没有活的时候,就到桑拿浴或者教会对付几天。(被访者李某,女,52岁,2012年来韩国,2015年初回国)
我不喜欢国内的朋友到我住的地方,条件太次了,不能和国内的住房条件比,更不能和韩国人比。不过,话说回来,韩国人的住房条件差别也很大,有住公寓、住别墅的,也有和我们一样租房子住的,有的人还没地方住呢,夏天的时候睡在大街上的多了。想住在好地方,何必来韩国呢?(被访者韩某,男,46岁,2007年来韩国)
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受到不同结构性条件的制约,往往会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不同的居住方式。这表现为,在生活质量和居住质量相似的社区里,集中居住着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大体相似的人群。朝鲜族在向韩国流动的过程中,逐渐在首尔的加里峰洞、新大林、南九老等地形成了以朝鲜族务工人员为主的“同胞村”(也有人称为“延边村”),特别是位于首尔南九老区的加里峰洞,因其交通便利、房价低廉、打工机会多而成为在韩务工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区。在这里,不仅有专门以朝鲜族为对象的职业中介所、房屋中介所、货币兑换所,而且还有朝鲜族市场、杂货店、饭店、练歌厅、麻将厅、按摩房、羊肉串店、火锅城等,凡是延边有的,这里也几乎应有尽有。
“同胞村”(或“延边村”)的存在有其积极的意义,它为生活在这里的朝鲜族提供了信息交流、社会适应、情感慰藉、工作机会等方面的条件,但同时也造成了在韩务工朝鲜族居住空间配置上的边缘化和“孤岛化”,使其渐渐成为一种“排他”意义的符号,强化了朝鲜族与当地市民的社会隔离,其实不利于朝鲜族在韩国社会的融入和发展。
四、“跟进式流动”与熟人社会关系网络
赴韩务工朝鲜族怀着对“故国”的想象,来到韩国打工,心中不无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然而,现实却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其实这里是“陌生人”的世界。的确,历史渊源以及作为“同源”民族的语言文化优势,让他们在适应韩国生活方面相对容易一些,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特殊的照顾。在韩务工朝鲜族为了减少跨国流动的成本,通常利用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解决他们最初在韩国的生存和适应问题。一直以来,家族或地缘关系都是支持延边朝鲜族向韩国流动的社会资源,并直接促成了“跟进式流动”。相关调查也表明,以亲缘、同乡、朋友为纽带形成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为在韩朝鲜族务工人员提供了一种安全、稳妥、低成本的流动链条,减少了流动的盲目性,在为其获得情感慰藉、就业信息、金钱资助、提升安全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在韩朝鲜族务工人员大多从事3D行业,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社会资源相对贫乏,加之居住环境相对恶劣,生活方式和语言、习俗的差异,这些都导致他们的社会交往活动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大多数人通常只和家人、亲戚、老乡、朋友、同学等往来,无法或不愿与当地市民进行深入全面的社会互动。
我是2007年8月1日到韩国的,是我弟弟邀请我的。今年(2008年)2月份我三姐也到韩国了,二姐是5月份到的,她俩也都是我弟弟邀请来的。我大姐夫两、三年前用商务签证先到韩国,现在一家工地干活,我大姐和他住在一起。我在仁川干活,二姐和三姐在蔚山的一个工厂干活,现在听说换了工厂。我们偶尔通几次电话,到现在还没见上面呢。(被访者李某,女,55岁,2007年去韩国)
值得注意的是,熟人群体内部之问的频繁互动和人情往来难免增加额外的金钱支出,加之务工人员之间工作竞争的压力、素质良莠不齐,所以在韩务工朝鲜族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我在饭店打工,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如果客人多的话,就更晚了。一周休息一天。每天回家累得要死,就想躺着,哪有什么心情和朋友出去玩。再说了,别人也都一样,累得很,而且出去了还得花钱,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在家休息。(被访者李某,女,58岁,2007年来韩国)
我老公在韩国打工,家里的亲戚和朋友也有很多在韩国打工,但他们一般不来往。都挺忙的,见一次面得吃饭,让谁掏钱都不是事儿,谁掏钱心里都心疼。前几天,我姐姐去韩国出差,问我老公在哪里工作,说要不要去看他,捎些东西啥的。我马上回答,千万不要去!去看啥呀?住的是地下室,跟贫民窟似的。你去看他,他心里更不舒服,怕你可怜他。(被访者李某,女,42岁,老公2011年去韩国)
饭店里的朝鲜族服务员呢,为了讨好老板,给韩国老板打朝鲜族的小报告。你说,都是到韩国打工,给人家干活,都干这种脏活累活,有什么可争可斗的?真是给朝鲜族丢脸!我现在干活的地方,就我一个朝鲜族,挺省心的,没那么多烦心事儿。(被访者李某,女,52岁,2010年去韩国)
不过,随着在韩朝鲜族人数的增多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一些朝鲜族同胞团体也纷纷成立,如“朝鲜族联合会”(2000年成立)、“中国同胞一心协会”(2006年成立)、“在韩同胞联合总会”(2008年成立)。另外,还有一些朝鲜族同胞媒体,如《中国同胞新闻社》、同胞社区新闻(www.dongpotown.com)、在外同胞新闻(www.dongponews.net)等,不仅发行报纸,还开通网络新闻。同胞团体和新闻媒体在为朝鲜族传递信息情报、排忧解难、提升群体良好形象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韩朝鲜族务工人员的“韩国梦”充满了艰辛和苦涩,他们试图改变自身境遇的奋斗与挣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其物质生活带来了改善和提高,但他们在韩国的生活始终与当地人存在深刻的隔阂,这种隔阂不仅是空间上的,更是心理上的,这也使得他们最终选择返回家乡;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决定最终返回家乡,他们不愿意与韩国当地人有更多的交往和联系。尽管生活和工作在韩国,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始终围绕着故乡的亲朋好友,其结果就是在“同胞村”这样的地方形成了新的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在韩国社会的接纳和排斥之间,朝鲜族务工群体只是“选择性”地适应韩国的社会生活,在深层融入韩国社会方面仍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