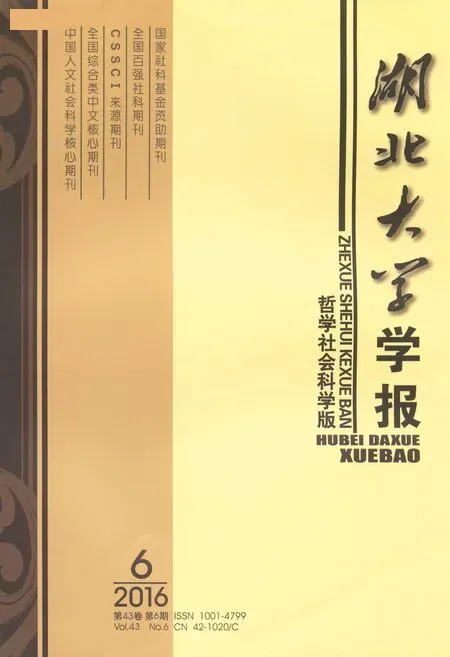CEO股权激励偏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公司治理”介入的视角
张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CEO股权激励偏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公司治理”介入的视角
张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适度水平的股权激励可以促使职业经理人的“尽职尽责”行为,提升其工作绩效水平并带来整个企业绩效的增长,反之(如“非常规股权激励”存在偏高或偏低等现象)则可能提高职业经理“道德风险”和“逆向行为”行为的风险概率。现实中“无效”的股权激励主要表现为“股权激励偏离”,这种偏离会直接导致企业绩效水平的变动,而公司治理机制介入之后,绩效变动的方向或程度会发生变化。通过对21345份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CEO股权激励“正偏离”的概率较大,且收敛到最优水平的速度较慢;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CEO股权激励“负偏离”的概率较大,且董事会调整这种偏离的能力较强,收敛到最优水平的速度较快。公司治理机制不仅对CEO薪酬契约内容及其订立产生影响,而且对CEO股权激励水平的调节起到关键作用。
股权激励偏离;公司治理;股权薪酬;绩效变动
一、引言
随着证券市场的迅猛发展,股票和股权(期权)越发成为职业经理人偏好的一种薪酬激励方式,股票或股权收入成为企业高管总收入的重要组成。但这种CEO偏好的激励方式也逐渐显示出巨大的危害性,“过高”的股权激励水平可能掩盖了CEO的“道德风险”,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很多学者指出了CEO这种行为的危害,但CEO的行为是否完全是股权激励造成的还未有统一的结论。关于此,学者们的观点有四类:一是Hanlon,M.,Rajgopal,S.和Shevlin,T.(2003)认为在企业前五位高管中实施股权激励政策能够大幅度提升企业未来预期绩效,高水平的股权激励更能激发CEO的“尽责”行为,但这种水平一旦偏离基准模型设计出的最优水平,企业后续绩效会被明显拉低,可能还会产生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二是Almazan,A.,Hartzell,J.C.和Starks,L.T.(2005)认为可以通过企业公司治理水平状况来评估和预测CEO股权激励水平的偏离状况和企业未来绩效的变动状况。三是Karaevli,A.和Zajac,E.J.(2013)关于CEO继任与企业业绩偏离之间关系研究,研究认为前任CEO和新任CEO“速胜”动机会强化企业绩效增长趋势,减弱CEO继任决策的负效应。四是宋渊洋和李元旭(2010)关于企业特征、CEO薪酬、股权激励有效程度的研究,研究认为薪酬、股权激励更有利于CEO激励相容机制设计,民营企业中CEO股权激励优于薪酬激励,而国有企业中薪酬激励效果更佳,股权激励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发挥作用。本文在综合以往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细化的验证研究。一是验证“高水平的股权激励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和“非常规股权激励水平”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二是检验在公司治理变量介入下的结果情况;三是“公司治理介入”视角一定程度上补充了Core和Guay(1999)对于“非常规股权激励”跨期持续效应研究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非常规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
相比现金激励,股权激励更具有长远性和持续性,但同时也具有高风险性,尤其是当企业在不合理性的股权设计机制指导下的股权分配,激励结果可能与预期相反,有学者认为高管获得异常高的股票或股权价值,企业收益恰有可能会受损。
在股权激励水平测度方面,Core和Guay(1999)的研究倾向于选择“高管股权比重或绩效薪酬敏感性”,但是由于“高管股权比重”和“绩效薪酬敏感性”都能够独立对CEO的行为产生激励影响,所以实证分析中很难辨清何种要素的作用更大或更小。但他们的观点是最优CEO股权激励水平是一个“平均值”,一般以“股票比重”和“限制性股权”来替代,并以此来衡量现行股权激励水平与最优水平之间差距及收敛情况,且CEO的股权激励水平与最优水平之间的差距太小或太大都会对未来绩效水平有负面影响。
由此得出:
假设1:管理者异常高或异常低的股权激励水平会直接降低企业未来绩效水平。
(二)有效公司治理机制与非常规股权激励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①基于研究目标即在了解企业中董事会及其与CEO之间关系基础上,CEO股权激励水平偏离情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中“公司治理”截取原本含义中的部分内容,具有特殊含义,特指企业的董事会结构特征和董事会与CEO之间的权力特征。结构设计方面会严格监督和把关董事与高管行为,尤其是CEO与董事之间的密切关系,若董事会在观察到CEO股权激励水平出现偏差时及时进行调整,通过逐渐的“次优”到“最优”的调整,CEO的投机行为则可能不会发生,则上述假设1的假设不会成立。因此,可知董事会的决策权力在股权激励水平偏离发生过程中起到关键调节作用。股权激励偏离的发生可能并不是因为CEO股权激励水平本身的偏离,而是由于最优水平的变化,或者CEO股票比重或股权收益的变化。另外,他们还认为董事会会观察到这种偏离状态,继而通过改变薪酬支付形式和调整支付额度来调整这种偏离状态,最终使得CEO股权激励偏离收敛到最优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偏离状态的“股权激励”都不会长期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既然董事会可以进行有效的调整,那CEO非常规股权激励为何还会对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影响呢?实践中董事会如何不进行调整呢?这两个问题就涉及到公司治理状况,一旦董事会权力较弱,其监视CEO及其薪酬支付的程度就会较低,发现非常规偏离的概率较低,因此绩效还会受到这种偏离的负面影响。
由此得出:
假设2:若公司治理机制有效,CEO非常规股权激励收敛到最优水平速度更快。
(三)无效公司治理机制与非常规股权激励
关于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研究都考虑了“绩效—薪酬敏感性”的中介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司治理机制决定了CEO薪酬契约的约束程度和绩效薪酬敏感性水平等。若企业的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绝大多数公司股权,则其对CEO的监管力度会增强,机构投资者会最大程度削弱股东和经理人之间代理问题。若CEO可以决定自身的薪酬形式和水平,他们一定会减少绩效薪酬在总薪酬收入中的比重。李维安、邱艾超和牛建波(2010)认为这种情况也体现在CEO与董事会之间“强弱”比较的情况中,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保证CEO受到董事会的监管,CEO权力弱化;而无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则可能出现CEO兼任董事会主席的情况,董事会的监管“形同虚设”,CEO权力强化。同样,Hazarika,G.J.,Narasimhan,S.K(2008)认为管理权力“集中化”会导致CEO及其管理团队与董事会之间较多的摩擦、分歧较多,继而CEO的非常规股权激励水平可能因为CEO管理权力“集中化”而出现“正偏离”。
由此得出:
假设3:若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无效,CEO的非常规股权激励偏离水平及其跨期持续效应更强。
三、样本、变量与假设检验
(一)样本选择说明
本文样本数据有三个来源:一是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2008—2012);二是中国证监会的年度报告;三是部分的上市公司一线调查(主要通过学校EMBA学员及其所能涉及的同学关系的调查数据来获取)。
1.截取21354份企业年度披露的CEO及各项经营绩效信息,其中CEO薪酬方式都是绩效薪酬敏感性。
2.截取2008—2012年的目的是为了验证CEO非常规股权激励对后续的5年的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
3.通过基准模型计算的最优股权激励水平的数据库则需要一个综合数据库来获取,分别是“年度报告数据库”、“上市公司信用评级数据库”和“证监会上市公司监控数据库”。
4.为了匹配检验估计目的,样本经过逐年的剔除,针对观察到20250家公司年度的股权激励水平与绩效检验目标,并通过年度获取公司2008—2012年的资产回报情况;2008年评估剔除之后的样本量为17383份;2010年剔除特殊的企业之后的样本数为12694份;2012年规范后的样本量8797份。
5.获取12093份专门针对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企业管理数据。
(二)变量选取与释义
1.非常规股权激励。CEO的股权激励往往是与利润挂钩,又称为“基于总利润的CEO股权激励”(用绩效薪酬敏感性来体现),用“Portinc”来表示,主要反映企业市场资本价值变动情况下CEO股权占企业总股权的比重。绩效敏感性则主要通过企业市场价值1%的变动引起的CEO股票持有比重变化价值来测度。本文中CEO的总股权激励水平主要借助于Core和Guay(1999)的界定,最优股权激励水平则通过Black-Scholes的股权定价模型来确定。基于此,“绩效薪酬敏感性”(Portinc)的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Portinct表示企业i在第t年CEO的绩效薪酬与利润分享型的股权比重之间敏感性程度(Core和Guay,1999),体现的是CEO股权比重价值对企业市场价值变动的反映程度。在估计Log(Portinct)之前,BMt,FCFProbt,PP&E/Salest,R&D/PP&Et的样本量的缩尾值分布从0.5%到99.5%之间。数据估计结果显示绩效薪酬敏感性与企业规模、非系统风险和CEO任期之间是正向变动关系,而与企业市场价值比重呈反方向变动。另外,绩效薪酬敏感性与资本敏感性和R&D敏感性之间是负向变动的。估计模型中的残差界定为RESIDt,即“非常规股权激励”。
2.企业绩效。测度企业绩效有两种方法:一是Core(1999)和Ittner(2003)界定股权激励后1、2、3和5年的资产回报收益(ROA)的均值为企业绩效变量;二是Hanlon(2003)研究界定的非股票的会计绩效水平,主要体现股东预期。本文主要选取第一种测度方法。
3.公司治理。根据Core和Guay(1999)等学者的研究,本文将公司治理界定为“CEO所有权比重、外部董事比重和机构投资者比重”的组合情况。当CEO掌握大比重的股票时,CEO对董事会股东的影响较大。当企业的外部董事掌握大比重股票时,CEO薪酬保持固定的概率较小,机构投资者对外部董事的监管力度较大,而规模较小的董事会的监管效率更高。另外,为了减少公司治理各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导致的误差和避免不一致的回归系数,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公司治理的变量进行了筛选。
(三)假设1-3的检验模型
1.假设1检验模型。通过公式(2)的OLS回归模型来估计检验假设1:

其中,ROAt+1,t+h表示t+1到t+h的平均资产回报收益(h=1、3和5),且ROA等于经营收入/总资产;RESIDt表示由回归等式1计算出来的残差表示CEO非常规股权激励水平;SDROAt-5tot-1表示t-5至t-1期间资产回报收益的标准差;Salest-1表示销售总额。本文用非线性模型(RESIDt2)和等式(2)分别对非常规股权激励两种情况进行检验(RESIDt>0,则为正向影响;RESIDt<0则为负向影响)。
2.假设2检验模型。检验假设2的OLS回归模型为:

其中,Abs(RESIDt)指t年的CEO的非常规股权激励的总水平;Board_Strengtht是指主成分分析捕捉的董事会的权力;CEO_Powert是指主成分分析捕捉了CEO控制董事会的情况。假设2假定的是β2<0和β3<0,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是否支持异常高或异常低的股权激励水平,本文又估计等式(3),分别对非常规股权激励两种情况进行检验(RESIDt>0,则为正向影响;RESIDt<0则为负向影响)。

(表1)变量设置与释义①为了便于数据分析,表1中的变量设置了英文缩写的形式,后续表中的英文及含义均与表1所列相同。
3.假设3检验模型。检验假设3的OLS回归模型为:

其中,Ch_Abs(RESIDt)表示t-1到t期间CEO非常规股权激励水平变动的绝对值(如:Abs(RESIDt)-Abs(RESIDt-1));Board_Strengtht是指主成分分析捕捉的董事会的权力;CEO_Powert是指主成分分析捕捉了CEO控制董事会的情况;Abs(RESIDt-1)表示第t-1年CEO非常规股权激励的绝对值(包括了等式4中涉及的高水平非常规股权激励的回归值);假设3假定的是β2<0和β3>0,为了进一步验证在t-1时期内,异常高或异常低的非常规股权激励是否得到支持,本文又用等式(4)分别对两种非常规股权激励进行检验(RESIDt-1>0,则为正向影响;RESIDt-1<0则为负向影响)。
四、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Pearson回归系数结果,与假设1的界定一致的是非常规股权激励的绝对值与年初的ROA之间是负相关(-0.08;P<0.01),与未来3年(-0.06;P<0.01)或5年(-0.03;P=0.00)的ROA之间亦是负相关。与假设2的界定一致的是非常规股权激励与董事会权力之间是负相关,但是与CEO控制董事会的影响之间是正相关。
(二)回归检验结果分析
1.假设1检验结果。通过等式(2)来检验非常规股权激励的影响结果,具体结果见表2-1、2-2和2-3。
表2-1展示的是等式(2)的回归分析结果,即非常规股权激励和未来绩效之间的关系。Part A展示三种ROA形式下的回归估计结果(2008年初、2008—2010三年平均值和2008—2012五年平均值),即三种情况下ROA与最优股权激励水平之间偏差的绝对值Abs(RESIDt)。与预期一致的是,三种形式的ROA测度下的Abs(RESIDt)的回归系数都是负值,表明了短期到中期,股权激励(包括“异常高”和“异常低”两种情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负向的。
由于未来绩效与股权财富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凹”型[10],本文通过回归模型(2)中的RESID和RESID2来替代Abs(RESIDt)(结果见表2-2)。Part B分析结果(剔除了CEO(创建者)的样本)显示了非常规股权激励与绩效的回归系数值是绝对值而非原符号值,表明了非常规股权激励与绩效之间关联性的负向关系可能为“凹”型。部分回归结果中的RESID系数值为负,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当CEO的薪酬支付水平异常低时,企业绩效水平是逐渐下降的。

(表2-1)非常规股权激励与会计绩效(Part A:非常规股权激励绝对值)

(表2-2)非常规股权激励与会计绩效(Part B:非常规股权激励绝对值平方(Residual2))

(表2-3)非常规股权激励与会计绩效(Part C:非常规股权激励的“正”和“负”值)
为了分离“异常高”和“异常低”股权激励对企业未来绩效的影响效用,本文改变了回归模型(3)的形式,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种形式的影响效用(结果见表2-3)用以替代测度非常规股权激励水平的大小的变量(Abs(RESIDt)),且界定了“正值”和“负值”的非常规股权激励水平变量的含义,若为“正向”,PosRESID=RESID,其他情况为“0”;若为“负值”,NegRESID=RESID,其他情况为“0”。另外,若PosRESID为负值,则表明CEO股权激励的水平异常高,对企业未来绩效增长不利;而NegRESID为正值,则表明CEO股权激励的水平异常低,企业未来绩效会更糟糕。
与预期一致的是,PosRESID回归系数为负值且显著,NegRESID回归系数为正值且显著(至年初和三年平均值的结果如此)。在Part A中,本文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对剔除CEO(建立者之一)的样本进行的回归检验,结果在附属样本中也得到强力的支持。上述这种结果恰恰验证了企业在进行CEO股权激励水平调整时,“调高”比“调低”更为容易,CEO群体也比较容易接受“调高”的决策。
2.假设2检验结果。表2第1栏显示了等式(3)的检验结果。非常规股权激励水平高低(RESID)与董事会强度(Board_Strength)之间是显著负相关,但与CEO兼任董事会主席变量(CEO_Power)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表3)有效公司治理与非常规股权激励

(表4)无效公司治理与非常规股权激励
表3第2和3栏显示了估计等式(3)中分别关于“负值RESID”和“正值RESID”的估计结果。结果发现在激励水平异常高或异常低时,Board_Strengh与非常规股权激励水平之间是负相关;当董事会权力较弱时,Board_Strengh与CEO股权激励水平偏离最优水平(异常高或异常低)也是负相关。另外,结果还发现CEO自身变量影响薪酬契约的情况,即CEO_Power变量在影响CEO非常规股权激励水平层面有差异,变量对“异常高”和“异常低”的股权激励水平的影响并不一致。对于CEO有异常高激励水平的(RESIDt-1>0)的企业来说,影响力更大的CEO可能会正向扩大其股权激励水平与最优水平之间的差距。而对于那些CEO掌握较少股权的企业而言,CEO的影响能力并不会拉大这种差距(后续的(4)、(5)和(6)具有类似的特征)。此数据证实了假设2的假定,结果表明了公司治理机制对CEO薪酬影响更弱的情况下,CEO股权激励与最优水平的偏离程度更大。间接说明了当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时,CEO股权激励偏离水平较低,也说明了CEO股权激励水平恢复到最优水平的速度更快。
3.假设3检验结果。表4第1列展示的等式(5)的估计结果,当CEO_Power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时,Board_Strengh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了当董事会权力较弱时,CEO的股权激励水平收敛到最优水平的可能性较小,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很大,此结果说明了当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无效时,CEO股权激励偏离程度较大,且在不同时期内都表现出较大的负效用。如前所述,非常规股权激励的持续性表明了在CEO薪酬契约形成过程中存在一种“摩擦力”阻碍了CEO非常规的股权激励水平(异常高和异常低)快速调整到最优水平。
表4第2栏和3栏展示的等式(5)关于“企业CEO在第t-1年的股权激励水平异常低”(RESIDt-1<0)和“企业CEO在第t-1年的股权激励水平异常高”(RESIDt-1>0)的估计结果。结果发现,两列中Board_Strength回归系数都是显著负值,表明了强势董事会对股权激励收敛到最优水平起到加速作用(包括“异常高”和“异常低”两种情况)。第三列中CEO_Power回归系数为显著正值(RESIDt-1>0),表明了CEO拥有异常高的股权比重和强势CEO都会降低股权激励收敛到最优水平的速度。但当CEO股权激励水平较低时,CEO就很少有动力去阻止董事会给予其更多的股票和股权,且可能以此为借口索取更多股权薪酬。第2栏中CEO_Powe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了当CEO先前的股票激励水平异常低,CEO会通过其影响提升股权激励水平(第4、5和6栏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五、结论与启示
第一,股权激励偏离方向对绩效的异质性影响。在实证数据分析之后发现,CEO的非常规股权激励对企业未来绩效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异常低”的影响高于“异常高”的影响。本文认为“异常高”和“异常低”的CEO股权激励水平都会降低企业未来的会计绩效。后续的检验则体现了这种非效率的股权激励主要体现在CEO薪酬契约订立的过程中,结果发现弱势的公司治理机制与CEO股权激励水平和收敛到最优激励水平的速度都相关。
第二,CEO股权激励偏离对企业绩效存在确定性影响,且体现在CEO薪酬契约机制过程中。先前的研究检验了CEO实行股权薪酬支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混合的,要么是不明显,要么是没有发现“异常高”的股权激励和企业绩效之间的明显关联性。本文的研究结论肯定了Core(1999)关于CEO股权激励水平偏离最优激励水平的理论预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或为正,或为负。实践中,董事会与CEO签订的薪酬契约往往并不能够完全规避CEO因为薪酬激励问题而采取的投机行为带来的绩效损失风险。这也验证了CEO的薪酬契约需要定期修正和动态调整,尤其是在股权激励水平的调整,这一过程中董事会结构变量起到重要的影响。
第三,公司治理机制对CEO薪酬契约订立的影响。本文研究认为公司治理机制不仅仅对高管薪酬契约的设计有影响,而且在调整跨期的高管股权激励到最优水平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另外,在CEO薪酬契约中,公司治理和绩效薪酬敏感性的关联性并非一致为正向,在某些强势公司治理结构的企业中,公司治理可以降低绩效薪酬的敏感性。由此可见,公司治理特征直接影响了CEO薪酬契约中股权激励比重,比重合理性直接影响企业未来预期绩效水平。基于此考虑,董事会非常重视和谨慎与CEO之间薪酬契约的订立工作。
第四,本研究可以让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团队意识到CEO股权激励的重要性以及水平设计不合理带来的负向影响,可以了解不同情境下CEO股权激励偏离产生的条件,并采取相应的实时监控的措施,避免企业的绩效损失。另外,企业在CEO薪酬结构设计是也不能过度倚重“绩效—薪酬敏感性”,即不能将CEO薪酬与绩效“挂靠”过度,若不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最后,公司治理有效性测度中“董事会构成及其权力”变量对CEO股权激励偏离的影响往往需要企业格外关注,一旦CEO兼任董事会主席或者与董事会中部分董事关系密切时,需要及时控制和修正CEO的管理决策,因为此时的CEO股权激励水平更容易出现“正偏离”,结果是企业绩效增长的收益会偏向CEO本身或管理团队。
[附注]本文还得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高管薪酬水平策略及其对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影响研究”的资助。
[1]Hanlon,M.,Rajgopal,S.,Shevlin,T.Are executive stock options associated with future earnings?[J].Journal of Accounting&Economics,2003,36(3).
[2]Almazan,A.,Hartzell,J.C.,Starks,L.T.Active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s and costs of monitoring:Evidence from executive compensation[J]. Financial Management,2005,(34).
[3]Karaevli,A.,Zajac,E.J.When Do Outsider CEOs Generate Strategic Change?The Enabling Role of Corporate Stability[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3,50(7).
[4]宋渊洋,李元旭.控股股东决策控制、CEO激励与企业国际化战略[J].南开管理评论,2010,(4).
[5]Core,J.,Guay,W.The use of equity grants to manage optimal equity incentive level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9,(28).
[6]李维安,邱艾超,牛建波,等.公司治理研究的新进展:国际趋势与中国模式[J].南开管理评论,2010,13(6).
[7]Hazarika,G.J.,Narasimhan,S.K.Corporate Governance,Debt,and Investment Polic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M]//SSRN Working Paper,2008.
[8]Ittner,C.D.,Lambert,R.A.,Larcker,D.F.Th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consequences of equity grants to employees of new economy firm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3,(34).
[9]Hanlon,M.,Rajgopal,S.,Shevlin,T.Are executive stock options associated with future earnings?[J].Journal of Accounting&Economics,2003,36(3).
[10]吕长江,郑慧莲,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设计:是激励还是福利?[J].管理世界,2009,(9).
[11]方军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治理决策[J].管理世界,2012,(11).
[责任编辑:马建强]
F244
A
1001-4799(2016)06-0121-09
2015-06-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5XRK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60328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4M562045
张行(1985-),男,安徽含山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