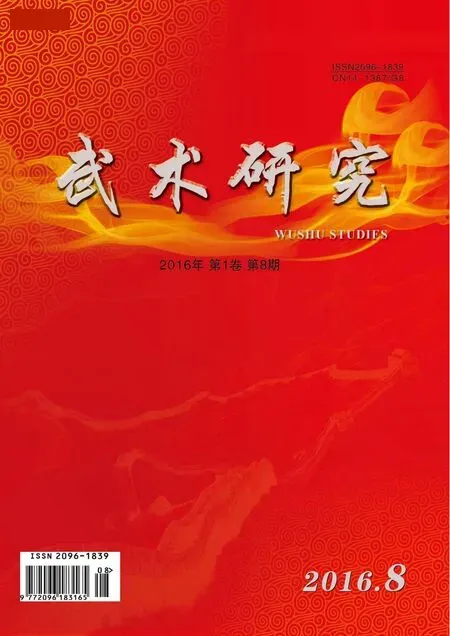武术:促进民族团结的法宝
曹玉冰河南警察学院开封校区,河南 开封 475000
武术:促进民族团结的法宝
曹玉冰
河南警察学院开封校区,河南 开封 475000
中华武术,拳种丰富、文化深厚、传承不息。从古至今,武术对促进各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从武术拳种、武术文化和武术传承三个方面,论证了武术对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价值。
武术 民族团结 拳种 文化 传承
1 武术拳种:促进民族团结的物质载体
1.1 武术拳种门类众多,各民族充分选择
中国武术门派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拳种逾百。各具特色的武术拳种,为各民族的武术爱好者提供了充分的选择,武术拳种也就成了民族间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和载体。
以下仅就回、汉民族间和满、汉民族间的武术交流活动为例,来审视武术拳种活动在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即民族团结方面的积极影响。
1.1.1 八极拳等是回汉民族习武人群的主要选择
在我国,回族人口有860余万人,主要聚居于宁夏,在甘肃、新疆、青海、河北以及河南、山东也拥有大量聚居区,体现出小集中大分散之民族人口居住特点。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其教义与习武强身黯然契合。将尚武视为“逊奈提”(意即“圣行”)的回族,自古以来便崇尚武勇;自然,为数众多的回族武术家在各历史时期均不容小觑。故此乾隆皇帝曾说:“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将种。”[1]回族武术包括八极拳、查拳、心意拳、华拳、洪拳、炮拳、弹腿、回回十八肘、杆子鞭、哨子棍等拳械几十套,其种类之多,传习之广为各少数民族之最。
吴丕清说:“许多汉族弟子投师回族武门,同样受到厚爱,一些回族弟子拜汉族为师同样得到真传。可以说沧州回汉民族的团结,与回、汉武学的交流、融合有着直接关系。”[2]如是举例证明,吴氏开门授艺,“收罗疃李大中,张克明等汉族人为入室弟子,这才使得八极拳在沧州汉族民众中传播开来。”[3]“沧州回族武术家马凤图始受家学,12岁拜黄林彪为师习练通备、劈挂拳法,黄将其毕生之学倾授与他,黄是汉族人。”[3]“回族武术家马登云从师张占魁习练形意拳,张是汉族。”[4]
起源于山东冠县的查拳,被公认为在回民所流传的诸多武艺中习练者最多、流传范围最广的拳种。俗谚云:从南京到北京,查拳出在教门中。民国以前,被称为教门拳的查拳主要在回族内传承;民国以来,中华武术会、精武体育会、武术传习所、国术馆等近代武术组织、学校蓬勃发展,加之军队训练对武术的需要,查拳开始突破民族与宗教的界限,向更多人群、地区传播开来。建国后,竞技武术迅猛发展,许多竞赛套路内容直接来源于查拳,这也从客观上推动了查拳在汉族群体中的传播;民间的习练者除仍在回族寺坊中传习外,部分门人通过参与运动会比赛的形式来扩大查拳的影响;一些查拳门弟子利用在高校进行教学与研究的机会,极大地拓展了查拳的普及范围,如已故的回族查拳名家张文广即为最典型的代表;一些回族查拳传人开始打破“传回不传汉”的旧规,广授徒众,如武贵祥阿訇在阳谷县创办了业余武术队,他二十年如一日地传授技艺,并“打破民族界限,不分回汉,其中90%是汉族的。”[5]更有一些艰辛创业,如常玉光(查拳名家常振芳之子)在开封通许创办查拳武校来推广这一宝贵的名族文化遗产。
心意拳,又名心意六合拳,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心意拳始于山西人姬际可,河南洛阳回族人马学礼习得此拳后,开启了心意拳在河南回族中传承发展的历史。与马学礼同一时代的山西祁县汉族人戴龙邦,作为心意拳的又一重要继承者,传艺于山西,名为戴氏心意拳;随后的河北深县汉族人李洛能改进了心意拳,易名为形意拳,同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形意拳名家,师徒一道使形意拳广传河北、山西。可见,河南回族所传习演练的心意六合拳与现在山西、河北所传心意拳、形意拳属于同源异流,这无疑是汉族与回族武术亲缘关系的历史见证。虽然,与八极拳“开门授艺”的开放式传承迥然不同,河南派心意拳曾经呈现出仅在回族内部传承的特点,然而由于在民国期间宗教传承格局发生了改变,河南派心意拳也渐渐地由乡村传入城市,并通过军队、武术社、教场、码头等,传向省外更多的汉人。”[6]夏志臣、宋国宾、范万明、李洳波等较为著名的传人,均为汉族。
1.1.2 太极拳等是满汉民族习武人群的主要选择
三大内家拳之一的太极拳,如今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流传最广,在海外更是备受推崇。杨式太极拳和吴氏太极拳在历史上都曾和满族有着直接的联系。曾学于陈家沟的河北永年人杨福魁(1799——1872),字露禅,艺成后应邀携次子杨班侯、季子杨健侯到北京教拳。杨露禅受聘于端王(载漪)府,同时任神机营总教练。其所教者多为王公大臣,杨露禅根据这些贵族多体弱不耐艰苦的特点,将高难功架简化,后发展为杨氏太极拳,当时即在京津影响甚大,后经其孙杨澄甫推广,渐发展为习者最多的太极拳派别。同在王府中授拳的杨健侯还曾教授过溥伦贝子和满族人汪崇禄。汪崇禄之子汪永泉也因此得杨家两代三位宗师(杨健侯、杨少侯和杨澄甫)的真传。汪永泉传拳不懈,有不少弟子成为当代汪传杨式太极拳名家,影响甚广。
在杨露禅所教三位著名弟子中,除万春为汉族,凌山及全佑皆为满族。宗师全佑之子吴鉴泉(1870——1942),对其所学杨家太极拳不断发展,最终自成流派,创立吴氏太极拳。其长子吴公仪、次子吴公藻、长女吴英华、女婿马岳梁均为满族籍太极拳宗师,对于传播吴氏太极拳功不可没。
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情况,还要关注学生价值观、情感观方面的变化和进步,关注学生自身的发展。高中地理课堂上,课前引入是融合人文知识最好的情境,通过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转承手段,融合人文知识和学生所学习的知识,让地理知识更加富有感染力和张力。
与杨露禅在王府传拳类似,八卦掌祖师董海川在肃王府当差,其弟子及再传弟子中不乏满族名手,如全揩廷、樊志勇和曾增启(尹福弟子)等,在此不再赘述。
与回族武术传承方式不同的是,武术在满汉互传过程中,并没有太多民族和宗教障碍,汉族著名拳师可以传授满族弟子,而满族拳师也可以向汉族弟子授艺。这主要是因为在清代满族作为统治阶级,并未像回族等少数民族那样遭受宗教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并不像回族那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自强意识。而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汉族文化始终表现出较强的同化能力,也始终是满族统治者学习的对象。
1.2 武术拳种分布广阔,各民族广泛参与
武术拳种分布广阔,呈现出地域特色,也演变出了繁复纷杂的支流门户,扩大了拳种的影响范围,加快了拳种的传播速度,使得各民族的习武爱好者能够广泛接触,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1.2.1 少林功夫遍天下
少林武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从民间汲取养料,从各民族武艺中获得灵感,逐渐吸收融合日益丰富,素有“少林功夫源天下”之说。少林寺是中华武术的交流之地,集散之所;少林武术的传播范围从最初的寺内扩大到寺外,并且能够超越民族的界限传播至全社会乃至外域。中岳嵩山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坐落于此的禅宗祖庭、武学圣地少林寺,亦因此成为各民族各地区武术的融合之所。少林武术拳种繁多,是一个内容庞杂的武术体系。自明代以来,尤其到晚清和民国时期,少林武术的社会传播大为发展,民间多有传习,曾有“天下功夫出少林”的说法。
1.2.2 分布广阔的武当武术
武当山所处的荆楚之地为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地区,武当武术无论是从起源上看还是从流传范围看,均与少数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学术界对于武术产生原因的认识基本上包括原始生存竞争、原始宗教活动、原始战争等。武当山地区山峦叠嶂,溪河纵横,常有野兽出没,生活于此地的各族先民在生存竞争中摸索并总结武技的情景不难想象;居住在武当山地区的各族人民的早期宗教活动、玄武崇拜、民风民俗、巫术与神仙方术等,对于具有鲜明道家和道教风格特征的武当武术而言,均是其产生与发展的文化土壤;而处于鄂、豫、陕、川四省交界区域的武当山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说,在武当山各民族武术内容的交融方面,战争因素起着最重要的作用。《韩非子·五蠹》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这是武术史料中记载的最早最著名的原始部落武舞——干戚舞。甘毅臻认为,发生在武当山地域内的禹之干戚舞的出现是武当山武术诞生的标志。[7]《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人武舞,也就是“巴渝舞”,据甘毅臻考证认为,巴渝舞发源于武当山,因为巴渝舞的展示者为“西土八国”中的彭、濮两族巴人,而刚勇好武的巴人在武当山地区生产生活了两千多年,当时的彭、濮两族巴人实为武当山原始居民。[8]另外,从“武当”一词的来源也可见此地战事不断:一般认为武当者,武力阻挡(当)也。春秋战国之时,在武当山下丹阳所建的楚国与邻近民族和部落征战频繁,楚遂在武当山设防,以抵挡秦、巴南下谋楚。从以上所述可见,武当山武术活动的萌芽与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单独创造,而是以武当山所在的荆楚地区为中心,包括其邻近区域在内的各民族宗教、风俗、图腾崇拜等文化内容与各民族征战过程中的武技文化相互激荡与交融的结果。
1.2.3 遍布巴蜀地区的峨眉武术
以峨眉山命名的峨眉派武术是与少林、武当三足鼎立的中华武林三大门派之一。峨眉武术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发展成熟过程中糅合并融入了各民族文化元素,但关于什么是峨眉武术,学界尚有分歧。清代何崇政(峨眉山湛然法师)在其所著《峨眉拳谱》的开篇诗写道: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由此,峨眉武术的经典分类方法“五花八叶说”流行于世:五花者,即流行于四川的五个武术流派,也就是丰都的青牛,灌县的青城,通江的铁佛,开县的黄陵,涪陵的点易;八叶者,即峨眉派武术的八大门派,也就是僧门、岳门、赵门、杜门、洪门、化门、字门、会门。以此法界定峨眉武术最为流行,然而难免以偏概全。《四川体育史料·武术专辑》(1984年第5期)认为:峨眉二字,广而言之,为古巴蜀之称。因此,无论过去和现在,凡在四川内流传久,根基深,具有地方风格的拳种,均属峨眉武术。[9]拥有类似观点的研究者多将峨眉武术与巴蜀武术互称,仿佛两者并无二致。然而,文化的发展是动态的,是与多重影响因素长期互动的结果,其流传区域和影响范围的边界具有模糊性的特点,是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区划来强行划界的。虽然峨眉武术和巴蜀武术的概念不能完全等同,但毫无疑问,其所指内容会有大量的重合。综上,峨眉武术是“起源于四川峨眉山地区的峨眉山道、僧武术与民间武术,主要流行于峨眉山地区,并广泛流传于整个巴蜀地区乃至其它地区,以峨眉命名的各种拳术、器械、功法和武术理论等武术内容和形式的总称。”[10]也就是说,峨眉武术应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峨眉武术主要指以发源于峨眉山、并与巴蜀地域文化长期互动交融而形成的拳种流派。广义上的峨眉武术更接近巴蜀武术的概念,既包括早期传入四川地域并与其地域文化互相适应、已具有显著巴蜀地方文化特色的外来武术拳种,还应包括从四川传播到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川外其它地域,但具有显著峨眉武术风格、认同并归属于峨眉派的武术流派。峨眉武术,作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文化符号,在促进四川及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有着独特的历史贡献。
2 武术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
2.1 武术文化促进各民族对主流文化的认同
武术文化促进了各民族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因为,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植根于儒释道主流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受其影响和熏陶。儒释道主流文化成为了武术文化的重要基因和显著特色。因此,各民族习武人群在习练武术的过程中,不断的接受着武术文化的熏陶,自然,也就不断接受着儒释道主流文化的影响和教育,其价值观和人生观则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改变或重塑,使得各民族的习武者对主流文化逐渐认同和接受。
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各个武术拳种门派所规定的武德要求。“所谓的传统武术道德…就是传统武术人愿意持守的生活态度和愿意遵循的行为原则”[11],这些武德规矩无不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作为习武者的习武规范和人生信条。因此,习武者,不管来自于哪个民族,都要接受和遵守其所在拳种门派的武德规范,通过对这些武德规范的严格遵守,使得他们对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及其价值理念能够认同和接受。
对道家文化的认同,主要取决于武当派武术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与少林武术齐名的武当武术,是在武当山地域文化、荆楚地区各民族武术文化、道教宗教文化、道家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交融中形成的一大派系,具体而言是指“在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和武当地域文化长期氤氲滋养下,元末明初武当道人张三丰通过道教内丹术与之前少林武术的有机结合,而开创的蕴功法、套路、格斗三位一体的一种养生技击并重的拳术,它包括由张三丰创立,以及经过历代尊张三丰为祖师且有明晰传承的拳师改良完善的各种流派的单练与对练的拳种、器械等传统拳术”。[12]因为道家和道教文化对武当武术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主张练气、练内功、练丹道的内家拳法多皈依于武当,以别于世人所谓外家的少林派。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下设少林门和武当门,并将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列于武当门下。虽然这种分法不尽科学,但充分反映了当时武术界,尤其是习练内家拳的武术人对武当的皈依与尊崇。对文化史“应然”的考证也许并不能左右文化创造者和传承者的内心情感,而文化现象中“实然”的力量却不能小觑:武当门人皈依武当、崇拜张三丰、认同道教和道家文化的隐性力量,既是各民族武当武术习练者的共同心理基础,又是维系和凝聚各民族武当武术习练者的文化纽带。
对佛教文化的认同,主要是禅武合一的少林武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少林武术中蕴含了特色鲜明的佛教文化,无我、我执、真空妙有、明心见性、禅等佛教思想极为巧妙地被融入到了少林武术的拳法套路、各种功法以及擂台战术之中,如此,每个习练少林功夫的人,不论来自哪个民族,必然要受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也就使得他们通过少林武术文化的熏陶和学习,逐渐认同了作为主流文化之一的佛教文化,并由此而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2.2 武术文化促进各民族对他族文化的包容
历史上,草原、森林、江河、大漠、高原、平原等不同的生存环境以及游牧、渔猎、农耕等不同的生存方式,促使各民族的武术内容均颇具其民族特色;同时,由于各民族间军事战争的周期性爆发,以及元、清两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元明清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又促使各民族间的武术多有交叉与融合。各个民族积极学习与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武术内容,使得许多原来只属于某一民族的武术拳种,相继出现在了其他民族中并得以广泛传播,从而促进了民族间相互的理解、宽容与团结。
在驰名中外的武术之乡河北沧州,回族武术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此地传播最广、习者最多的当推八极拳。八极拳全称“开门八极拳”,“开门”之意,一说为技术含义,即“以6种开法破对方门户,”而另一说为则为传承方式之意,即“沧州孟村吴钟受一云游异人及其徒先后传授拳法及大枪奥妙,吴钟学成后,初为吴氏回族家拳,只教本姓亲族,后开门授徒,遂成回汉共练之术。”[13]无疑,在这里,“所谓‘开门’,即有开门交流,汲取众家之长,冲破武林关门习武的神秘传统之意。”[14]可见,“开放”是八极拳传播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应该说,也正是因为其提倡开放交流,反对封闭保守的开放胸襟,使八极拳在全国蓬勃发展、从学者数万。
武当武术产生以后,对整个中国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若以传统的内家拳与外家拳的说法来看,武当派所代表的内家拳派可谓中华武林之半壁江山。“武当”几乎成为了内家的代名词,许多习练内家拳术者都自称其拳术源自武当。但上世纪30年代,唐豪通过考据得出武当无拳的结论,这与武当武术的实际社会影响大相径庭。然而,80年代以来武术挖掘整理数据表明,目前仍在各地流传的武当武术门派就有29个,功法套路共208个,武当不仅有拳,而且其体系之庞大、影响范围之广非某一单一拳种可比。在这诸多门派中,有些内容传承谱系非常模糊,明显不是创自于武当山地区,这一方面表明,武当武术是在与他族、他派武术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而成;另一方面,各派系对武当和张三丰的认同展现了武当武术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峨眉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其所处的巴蜀地区多山地、高原、丘陵,地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秦巴山地、四川盆地等几大地貌。在这片产生并流传峨眉武术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着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傈僳族、满族、纳西族、布依族、白族、壮族、傣族等共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共有490余万。其中我国第二大藏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均在此地。若追溯历史,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尚武传统。如古巴蜀族的尚武之风就可谓源远流长。《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人,前徒倒戈。”武王伐纣用巴蜀之师,足见巴蜀族自古便好习武艺,英勇善战。如今从各民族的风俗活动中,仍然可见武术的踪影。贾奇侠等认为,从丹巴藏族风情节开幕式后的民间娱乐活动、土家族丧葬期间所跳的武丧舞、青羊宫庙会上的武术活动可以看出,巴蜀地区的武术与风俗活动有着密切关系。[15]这表明,主要流传于巴蜀地域的峨眉武术流派,其影响已深入民间,并与各族百姓的风俗活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巴蜀文化是中国最富于包容性的地域文化之一。巴蜀历史上有七次大移民,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群体,使四川成为一个各民族大融合的移民社会,移民带来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和闽南文化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巴蜀文化。峨眉武术正是巴蜀文化的一个缩影。”[16]峨眉武术正是在历史移民所带来的川外异质文化与巴蜀文化的无数次碰撞与融合的背景下,在这个移民社会里被诸多民族共同传习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积极扩大峨眉武术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影响力,发挥峨眉武术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文化功能,是值得峨眉山地方政府和武术管理部门深思的一个问题。
3 武术传承:促进民族团结的生生法脉
3.1 时间上,武术在各民族之间的传承源远流长
从时间上,武术在各民族之间的传承,可谓是源远流长。大多数武术拳种都可以追溯到上百年甚至是上千年前,也就是说,在武术传承的过程中,各民族通过拳种的传承而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形成了一条多民族以拳种为纽带而传承不息的生生法脉。这条武术传承的法脉,使得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贯穿古今,紧紧的团结在了一起。
有很多拳种,它们都追溯到了同一个创始人,例如武当武术中的各个拳种流派都是以张三丰为祖师爷。少林武术中的各个拳种流派都是以达摩为祖师爷。以共同的创始人为起点,形成了各个交错的拳种门户传承谱系,在这样的一个谱系网中,每个拳种传承者所代表的民族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武当武术的一大文化特色就是对充满传奇色彩的张三丰的尊崇与认同,这种来源于祖先崇拜传统的文化上的凝聚力,是能够超越武当山地域界限以及各民族界限的。武当山和张三丰是武当武术的两个重要文化符号,对武当的皈依感和对张三丰祖师的尊崇是凝聚各民族各地区武当武术人的文化向心力。现如今习练人数最多、历史上曾在满汉间互传的杨式太极拳,“虽然从渊源上看与陈式太极拳关系很密切(当今陈式太极拳传人大多宗陈王廷为祖师),但是,杨澄甫先师之子杨振铎在邯郸一次会议上说:“我对太极拳源流没有研究,但是我们杨家历代祭祀的就是张三丰”。[17]广义上的武当武术是包括太极、形意、八卦等内家拳术的,虽然是否所有这些内家拳术都来源于武当山莫衷一是,但现实中众多内家拳习练者自觉地尊崇张三丰祖师、皈依武当门派的文化事实却不可否认。
3.2 空间上,武术在各民族之间的传承百花齐放
从空间上,武术在各民族之间的传承,可谓是百花齐放。因为,几乎每一个武术流派,在其传承发展过程中,又都形成了众多的支流门户。每一个拳种,通过来自各个民族的武术人的传承之后,便不会局限于某一地区,而是被广泛的传播到其他地区,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少林武术庞杂的内容,它是在融合各族各地区不同的武技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的。明代俞大猷将棍法传入少林寺,即为少林武术源于民间之明证。再如,被视为少林武术精华的心意把,若与流传于山西、河北的形意拳以及在河南回族中所传承的心意拳相比,便可发现无论是拳理还是技术风格均有明显亲缘关系。虽然学界关于心意把和心(形)意拳的关系以及心(形)意拳始祖姬际可与心意把的关系尚无定论,但姬际可“在少林寺一住十年,授拳多人(也有和尚),老年返里”[18]表明,少林武术是与民间武术不断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少林武术又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走向民间,从而成为中华各民族所共享的文化瑰宝的。少林武名真正显扬是在明代,尤其是抗倭战场上的辉煌战功使其声名远播。至清代,教门及秘密结社多靠习武发展会众,所吸收会众中不乏习少林拳者,更有甚者如天地会则直接将其所习洪拳认为传自少林寺,借少林之名进行反清活动。清廷对少林寺的态度也因此从支持转为打压,这就迫使少林武术的传播范围从主要在寺内转移到广阔的民间,同时清代教门及秘密结社的习武活动客观上也扩大了少林拳在各民族各地区间的传播。民国时期,直接推动少林拳在社会与民间传播的是以国术馆为典型代表的各种武术学校和组织。中央国术馆初设少林门和武当门,虽不甚合理,但足见少林武术地位之高。新中国成立后,受影视作品宣传的影响和竞技武术的推动,各地少林武术馆校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习练少林拳的各民族武术爱好者不计其数,少林武术在中华各族儿女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更是无可比拟。综上可见,少林武术的内容来源、传播对象和其所承载的民族情感都具有鲜明的超民族特征。
1983年国家体育总局对四川峨眉武术进行挖掘整理的结果显示,峨眉武术目前有68个拳种和门派,1093个徒手套路,518个器件套路,41个对练套路,276个练功方法和14个技击项目。数量庞大的峨眉武术体系绝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产生,绝不可能被一个民族所创造,更绝不会被一种地域文化所孕育,而是在古老丰厚的巴蜀文化的浸染下,产生于道教和佛教的共同圣地峨眉山的武术文化,与由移民等重要因素所带来的其他地域与民族的武术文化相互碰撞、借鉴、交汇、融合,在巴蜀大地各民族习武群体传习演练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的。
峨眉武术发祥地峨眉山及其所处的巴蜀地域,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可以说巴蜀文化发展与变化的历史主线便是移民,而峨眉武术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历史背景也是移民。较为著名的移民活动是“秦汉大移民”“湖广填四川”。秦汉之时,众多西北部和云贵地区移民流入蜀地,使蜀地民族成分变得复杂起来。巴蜀地域文化不断吸收其它民族文化的特质,至宋代,各少数民族与汉人长期杂居,文化上已渐趋融合。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再次改变巴蜀地区的民族版图,大量湖广人(湖南湖北)以及广东、广西、陕西、贵州、河南等地移民入川,清代福建、江西、云南、贵州等地居民亦有迁入,使四川地域文化深深地打上了移民这一历史事件的烙印。移民浪潮对巴蜀地域的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川东(重庆)、川西(成都)两个地区的武术风格有明显不同,即或与两地移民来源显著不同有一定关系。以少林拳为最典型代表的外来拳种随着移民被带入蜀地,并与巴蜀原有拳种互相交流与影响,在巴蜀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下,发生了适应性变革,最终融入峨眉派武术体系之中,大大丰富了峨眉武术的内容,拓展了峨眉武术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如峨眉“五花八叶”中的僧门拳,原系少林武术,在蜀地民风、原有武技、川人身体条件、所处自然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虽仍保持着少林拳的原貌,却已具备了诸多地方特色而与中原地区的少林武术有所区别:如四川僧门拳套路中基本无腿法,而上肢动作较多。这是少林武术与巴蜀文化相融合的历史见证,也是移民文化对峨眉武术文化影响的结果。
[1]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清代)[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99.
[2]吴丕清.沧州回族武术[J].回族研究,1997(1).
[3]《沧州武术志》编纂委员会编.沧州武术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06.
[4]刘汉杰.沧州回族武术文化的内聚与外衍——以八极拳的传承、传播为例[J].回族研究,2005(2).
[5]范景鹏.“中土回人,性多拳勇”——查拳门[D].兰州:兰州大学,2009.
[6]郭春阳,李红卫.河南心意六合拳的传承方式及其形成原因[J].体育学刊,2011(5).
[7]甘毅臻等.武当山武术活动略述[J].湖北体育科技,2008(6).
[8]甘毅臻,王小卫.武当山——“巴渝舞”之源地[J].湖北体育科技,2007(4).
[9]四川武术挖整小组.四川体育史料[M].武术专辑,1984.
[10]王亚慧,代凌江.试论峨眉武术的起源及对“白猿起源说”的质疑[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5).
[11]乔凤杰. 武术哲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1.
[12]龙行年.武当武术文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22.
[13]吴丕清.沧州回族武术[J].回族研究,1997(1).
[14]吴丕清.沧州回族武术[J].回族研究,1997(1).
[15]贾奇侠,沙川华.巴蜀地区环境与武术拳种特色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5).
[16]代凌江.峨眉武术分类问题的现状研究[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8(2).
[17]龙行年.武当武术文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119
[18]陈振勇,温佐惠.论历史移民对巴蜀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7(6).
Wushu: A Magic Weapon to Promote National Unity
Cao Yubing
(Hennan Police College,Kaifeng Henan 475000, China)
Chinese Wushu is rich of boxing styles, rich of culture, and heritage endless. Since ancient times, Wushu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 unity.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from the Wushu styles, Wushu culture and Wushu inheritance three aspect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t value of Wushu to promote national unity.
Wushu national unity boxing styles culture heritage
G85
A
2096—1839(2016)08—0009—06
曹玉冰(1964~),男,副教授。研究方向:武术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