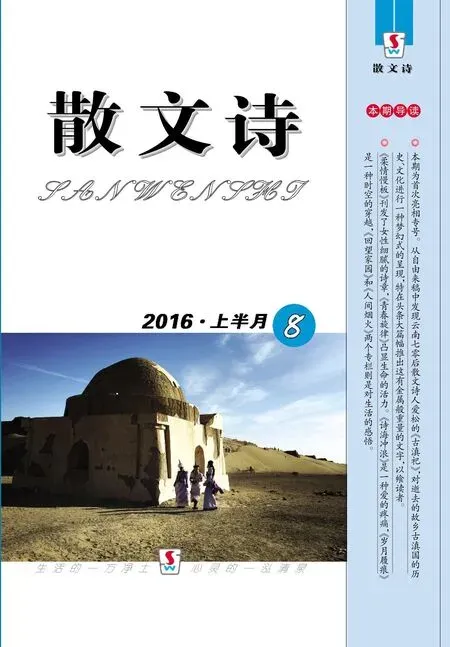倾听:经典的弦律
安徽◎金国泉
倾听:经典的弦律
安徽◎金国泉
岁月履痕/钟道生图
古琴曲:平湖落雁
每一只飞翔的大雁,无论怎样的高远,最终均必须回到地面,回到这片湖,这片秋日里苍茫、宁静而承载一切的湖面。
辽阔得没有边际的天空,允许一切存在,却不允许一切在其中停留。一切只能略过,只需略过。一切均必须在略过之时原路返回,哪怕是一只孤雁!
每一只大雁都是一串音符。每一串音符都在波浪上跳动,在波浪上注解自己。
大雁也在注解天空。
涌动的波浪,既在涌动中消失,又在涌动中生长,在涌动中完成自己的一生。
是哪一只大雁首先发出鸣叫?忍不住的鸣叫在秋日黄昏的湖面响成一片。秋风在吹,在芦苇的深处发出沙沙的水声,此起彼伏。
疼痛。大雁的疼痛被这片湖牢牢锁住!
古琴曲:高山流水
高山总有流水不断向下流淌,流向四面八方,流向江河湖海。
江河湖海总是波浪汹涌,浪花激溅,即便是平静的,也仍然有看不见的涌动,鱼儿溅起的水花仍能让一切不肯止息!
谁在呐喊?我感到是呐喊,而非鸣叫。鸣叫的只有麻雀。任何时代都有的麻雀、总是飞一下停一下的麻雀,是否也是从春秋伯牙那座高山上飞来?
风也在呐喊。风入松,风吹动一枝一叶,卷起尘土。尘土不通音律,尘土只是相反,它将一切包括音律覆盖。是否覆盖了我们的梦?
高山仍然耸立,千年万年。
琵琶曲:春江花月夜
月亮又在升起,圆圆的月亮,从江水中分离出来,从江岸上的野花野草中分离出来,一直上升,一直向天空盛开。
虚无的天空,虚无得只剩下这轮皎皎明月。它投向大地的是否也是虚无?
虚无并非不存在。虚无总是什么也没有地存在着,坚实且坚决。
就像真实的存在着的大地,就像这个宁静的夜晚。宁静才能侧耳倾听,倾听春、江、花、月、夜。
就像这真实地存在着的混浊江水。它一直流淌,一直咆哮,千万年也不肯止息,它要倾诉什么?它是在向这个夜晚倾诉吗?
倾诉就是对抗?它在对抗虚无,它在对抗虚无的同时又流向了虚无,它在流向虚无的同时又在倾诉这存在于虚无中的美妙。
这是春天,春天的夜晚,春暖花开。
一个人在江岸上走过,又一个人在江岸上走过。他们像一朵花,一丛花,他们的身后,尽管黑黑一团,但他们仍然与这月光,这虚无的月光对峙。
保持着一份千年不变的美妙。
古琴曲:广陵散
只能倾听,不能弹奏,千年至此不绝。
聂政如此,嵇康也是如此。
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这远古而来的天籁之音,完美而极致。极致就是死亡。
死亡也有它的反面,那就是永生。这面对死亡的弹奏,只须倾听,只须在沉默中倾听它的永生。这是在广陵?
广陵以外的广陵被弹出,也被隐藏。
我们都身处其外,也身处其中。
古琴曲:梅花三弄
只需三弄,就可以看见皑皑白雪中的梅花,就可以看见梅花枝头的皑皑白雪。
梅花与雪总是相互映衬,相互通过对方找到自己,找到不可能。
而现在,一切都有了可能。一切可能都在枝头,在枝头等待,在枝头仰望。
风也在仰望,风吹白雪如弹去梅花枝头的灰尘。这些冰冷的灰尘、冰冷的美的呼唤,从不回头。它宁愿融化,宁愿消失。
回头的总是我们。我们站在村口如站在某个枝头,在这个枝头上倾听。
一切都在倾听?演奏也是一种倾听。区别仅仅是时间。
而时间没有什么能战胜。我们找到的唯一方法就是与它同行,就像这些不断吹动的风与雪同行,就像这些雪与梅花同行。
古琴曲:胡笳十八拍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系在一个时代的肩头上,相互依存,相互取暖。
但时代总是冰冷,时代不允许一个人在其中取暖,即便是伏在它的肩头上。“冰霜凛凛兮身苦寒,饥对肉酪兮不能餐。”这是怎样的冰冷?怎样的冰冷才能让一个人在既面对饥饿、又面对肉酪时而不能餐?
撕裂的疼痛。撕裂地穿越千年时光也仍然疼痛。
漫天风沙不是美妙的音符,漫天飞雪也不是美妙的旋律。它吹不干一个女人的眼泪,但它却吹干了胡杨,吹干了塞上的黄蒿。
一个女人的眼泪往往就是一个时代的眼泪?
谁能记住这些?这些美妙的旋律与音符与此有关吗?美妙的旋律与音符总是有起有伏。在这起伏之间,我们听到了什么?
琵琶曲:阳春白雪
两千年了,雪一直在下,白皑皑一片,白茫茫一片。
那个莫愁女还在舞蹈吗?
只见舞者,而不见舞者的脚印。一个没有脚印的舞蹈是孤独的悲哀,还是悲哀的孤独?在这亘古的雪野上,反复的脚印被反复降下的雪覆盖。
就在这个雪国,雪同时也在覆盖泥土,也在覆盖人间烟火。但炊烟仍在升腾。在覆盖着雪的屋顶上升腾。
那个舞者是否冻伤?炊烟能温暖舞者的身体,却温暖不了舞者的舞蹈。
没有一朵花在这里开放。即便是雪花,也在凋零。那是不是春天就在不远处?
两只灰喜鹊在叫,就在这个世界的枝头。枝头的下面仍然是泥土。泥土是这个世界“并非唯一但却是永远的朝圣者”①①沈天鸿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