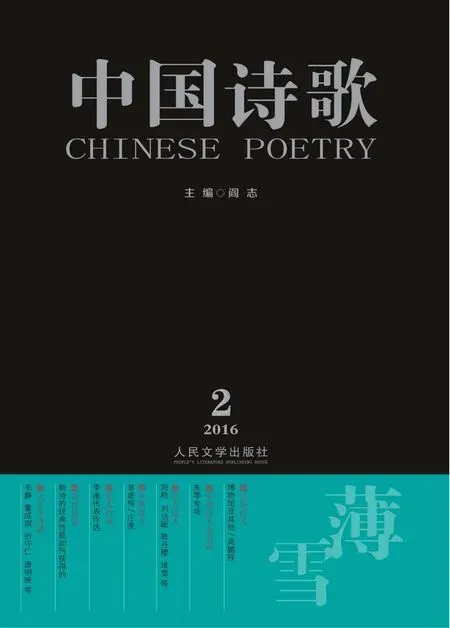诗学观点
□孙凤玲/辑
诗学观点
诗学观点
□孙凤玲/辑
●黄一认为“以物观物”不仅影响创作者的视域以及物象在作品中的呈现,同时规定了在诗歌阐释过程中,读者对诗歌所呈现的物象的释义过程。根源于道家美学的以物观物,使观察者的中心地位被消解,物物互相应和,语言呈现的是“一种类似‘指义前’物象自现的状态”,因此读者阅读诗歌,如同面对空间里并行的物象,不受先在的意义与关系束缚,从不同角度自由出入其间,读者得以对诗歌“作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从而获得对诗歌多层次的感受。正由于道家美学主体虚位以及以物观物的思维程序,诗人在表物的过程中充满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造成文言语法的自由。
(《叶维廉比较诗学的重审与再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4期)
●宋湘绮认为对拘泥于文学表现论、再现论,写“小我”感受的作品,需要饶宗颐先生“落想说”的超拔和提升,需要从实践存在论的角度重新认识王国维境界说。真正意义上创造诗的过程,也是创造人生、创造自我的过程,是生命创意、创造、创世。好的作品不仅仅是个人感受,而且是价值真理的符号表达。经典表达既超出了作者的体验,也超出了读者的体验、批评者的经验,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的境界,具有文学不可或缺的现实根底和理想的维度。“个人”书写要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走向对理想的人性、人生,对理想社会的价值建构,需要重建当代诗词文学创作的价值观。
(《关于当代诗词研究的四个问题》,《诗潮》2015年11月号)
●西川认为有必要书写社会之恶和生命的哀伤,但反对将社会之恶与哀伤简单化。简单化的简单做法就是把生活事件化、标签化、符号化、平面化,即取消恶与哀伤的历史深度。我们现在的写作离地一寸高是时髦,离地一尺高别人就要在网上骂你了,如果离地三尺高你在文学界、诗歌界就没法混了,这就意味着你是在逆行了。精彩的作家往往是逆行的,不是顺着大伙的接受习惯走的,但在当下中国,在写作中摆出一副批判的姿态而且离地一寸高其实不是逆行,而是顺行,因为大家都这么干。这种让人一目了然的写作深度和道德关怀,往好了说(犹豫一下)也许是一种伴随政治天真的文学天真,而可以为“天真”做辩护的最方便的说法是:“我写出了生命!”
(《从写作的角度试谈中国想象之基本问题——2015年4月13日晚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演讲》,《诗选刊》2015年11月号)
●李元胜认为诗人的个体写作恰能及时而准确地表达出敏感心灵的波动。而这个过程最适合在孤独的状态下独立完成——只有孤独能带来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一首诗的旅行才有可能走得更远。不管诗人习惯什么样的风格,偏爱什么样的语言工具,他们的内心是相对不封闭,或者完全开放的,他们的作品不是孤独的,它们和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只是时代的局部造像。诗歌是一种探索性的、上游性的、资源性的写作,敏感的它也许表达并不完整、并不系统,但是它领先。诗歌更关注人们内心的波澜和断裂,它孤独前行,无视商业和名声。
(《诗歌是一种资源性的写作》,《诗刊》2015年11月上半月刊)
●蔡丽认为人与自然生自相通,在相当程度上观望着宇宙生命的永恒。这是历代骚人墨客喜欢登高临眺的缘由。当代诗人,临危崖,望星空,寄情于草木山水的也不少。但当代诗人个人目的性很强,人欲大于天道,目光往往是从一个单向度上接纳自然甚至涂改自然,人与自然物事的相遇通常招来人对物的利用。1950年代诗歌里的青纱帐、甘蔗林接应的是如火如荼的革命生命的隐喻,而朦胧诗时期的舒婷、顾城笔下的峡谷、森林,更是个人内心情绪的映照,甚至是一种观念形态的物化。在这种个人化的有向度的进入和选择中,自然苍白无能,成为人顺手拈来的道具,古人和自然之间平等地活着的无功利交融就变得非常稀罕了。天人合一的物质,在相当程度上就成为现代诗和古典诗的内在分水岭。
(《我给大家散个花》,《诗刊》2015年11月下半月刊)
●谷禾认为童年、少年的经历,让我也过早领悟到了衰老和宿命——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孩子是不幸的,也可以说他是幸运的,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最终成为了一个诗人。其实,所有的写作又何尝不都是回忆?只有贴骨贴肉的回忆,才是通达真实的桥梁。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通过自己熟悉的书写方式,记录下“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歌哭”,让后人或读者看到历史作用于个人的粉碎性碾压和个体生命的承受。如果“诗歌是对真理的热情追求”(米沃什)成立,那么,诗歌的书写者应该能够在他提供的广度里给人以爱和善良的力量。在伟大的历史面前,所有的生命个体都是渺小的,但历史的伟大恰是由这些渺小的生命构成。
(《写诗,失败主义者的事业——关于〈少年史〉的对话》,《扬子江》2015年第6期)
●中国散文诗经过新世纪十多年来的探索发展,在语言的诗性与结构的表现力上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审美高度,许多前辈所孜孜以求的散文诗之“美文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所谓的语言技巧问题在当下散文诗中已经不成为问题了。然而,如果散文诗仅把“美文性”作为其本质,那么,她的发展也许至此就已经到头了,而她的存在也就永远无法摆脱成为分行诗或散文的小情人的境遇。要使散文诗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其叙事性与现代性远比其美文性的追求更为重要。纵观散文诗的历史,那些成为经典的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纪伯伦、兰波、鲁迅等人的作品,莫不是以叙事性与现代性为核心。然而,这些更为重要的散文诗美学要素,究竟被当代散文诗作者继承了多少?这是值得怀疑的事情。我们看得到的是,在“美文性”的倡议与追求下,更为本质的散文诗的灵魂却总游离在许多作者的作品之外。
(《〈诗歌月刊〉编辑部编后语》,《诗歌月刊》2015年11月号)
●谢克强认为,诗的艺术实际上是语言的艺术。诗人的天才就在于他善于将那些平淡的漠不相关的词奇妙地组合在一起,使之结成姻缘并熠熠生辉。
诗的魅力、诗的美的力量,从来是与它的个性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的生命即是个性。诗的个性,来源于诗人独特的艺术感受。艺术感受的独特,也就是他在摄取生活中诗的元素,进行诗的构思,展开诗的联想,捕捉诗的意象等等时,都必须有他的独特之处。一个真正的诗人,他所处心积虑的就是要在百鸟齐鸣的树林中找到属于他自己的独特声音。
(《独白,徘徊在诗与美之间》,《星星》2015年11月号)
●耿占春认为当我们诗歌的感受力要增加其他一些环节,这些环节就是承载感受力的身体,感受力所指向的身体,还有语言,语言也是承载感受力或转换感受力的媒介。因此,就又产生了同样作为承载感受力的身体与语言之间的一种连接。感受力需要一种语言,感受力不会发生在真空中。感受力是我们和社会之间产生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同时指向一种语言。如果一个社会取消了这种感受和表达,堵塞这种感受力向自由的语言、丰富的语言、敏感的语言表达的渠道,限制很多感受、认知不能进入公共语言,不能进入语言的自由交流,那么这种感受力不能转换为社会情感资源,就会被孤独的个人躯体化、肉身化。
(《诗歌与感受力》,《大家》2015年第6期)
●张德明认为在物质化、世俗化的文学语境中,诗歌的消费变得越来越艰难,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随之而来的是,诗人的美学和文化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占数量优势的诗人不再是凡俗生活的代言人,他们甚至对类似话题特别警惕和敏感。他们放弃对商业文化哪怕是最柔性的批判,而醉心于对日常生活柔情蜜意的非对抗性的审美表达,诗人们向现代性集体缴械。他们中的不少杰出分子早已成为官方与商界各种场合的座上宾,徜徉于高档会所与度假村之间,随时领略着物质魔方带去的万般诱惑。许多久经沙场的诗人发现了一种谎言无处不在又极具欺骗性的话语系统,自信地认为自己的沉默和超脱比欲望昭昭之下呈现的各种丑态来得真实、重要、更有利于自保,所以,他们时常因为自己侥幸不在其中而自觉获得了一种偷着乐的快感。
(《常态的性灵书写与非常态的诗歌意义——关于娜夜的诗歌精读与潜对话》,《当代文坛》2015年第6期)
●王士强认为,言外有意、言简意丰、言在此而意在彼是诗歌不变的特质,诗歌从深层来讲是不可说、说不尽的。无论是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诗歌都不可能改变其成为自身的核心特质,诗还是诗!那种认为现代诗歌已经不需要言意结合、以少寓多、含蓄蕴藉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在当前的语境下,强调诗歌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也是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及物性的。当今的诗歌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经营,而仅仅成了“口水”、“废话”的狂欢、宣泄,形成了平白如话、淡乎寡味的现象,这样的诗歌没有“言外之意”,甚至“言大于意”。在另外的方向上,有的诗歌成了一种语言游戏或者修辞练习,仅仅是在语言、修辞的层面上用力,这实际上切断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有效关联,同样形成了“言多意少”、“有言无意”的现象。对诗歌写作而言,这两种情形都是出现了偏差,应该注意避免的。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清明》2015年第6期)
●冯妮认为不可否认“打工诗歌”、“农民工诗人”这类复合名词,确实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么一点因为偏见而导致的错位。尤其最近半年,《我的诗篇》这部纪录片裹挟着一批非常优秀的打工诗人进入了公众的视线,我的一些朋友,以前不怎么读诗的,突然都一下子被那些语句吸引住了,那些强烈的意象甚至让人震惊。但是,这一类诗人、诗歌,往往是以“集体的”、“群像的”方式呈现的,大多数读者并不会特别区分他们之间的异质性或者说个体性,大众媒体在论及这些写作潮流时,也往往在谈论一种“现象”。换句话说,郑小琼对命名的抵触,针对的应该是这些东西,而并非这个命名背后的身份意识与文化意识。(《谈郑小琼》,《名作欣赏》2015年11月上半月刊)
●谢有顺认为当下中国心狠手辣的写作太多了,带着希望、暖意和亮光的写作太少,而我们需要后者。但这确实又是一个无所希望的时代,一个作家,只有把希望藏得越深,力量才可能越大。直白、浅薄地写希望,只会令人生厌。正因为如此,我们刚才谈到,绝望中的希望才是真正的希望。也就是说,没有经过苦难的磨炼,没有付出眼泪和代价的希望,都是轻浮的、廉价的。正如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必须付出死亡、流血的代价,比如耶稣上十字架,就是最好的象征。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没有苦难也就不会诞生任何有价值的希望。
(《还能悲伤,世界就有希望——关于〈篡改的命〉的一次对话》,《南方文坛》2015年第6期)
●朱大可认为在互联网的时代,诗歌有可能“逆袭”吗?表面上看,现在的诗歌很繁荣,很多前诗人都变得有钱了,他们愿意赞助诗歌事业,使得各种“诗歌堂会”非常热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种活跃究竟能对当下诗歌的整体性衰败有多大的抵抗作用?从2005年开始,中国开启了娱乐元年。这一年中国娱乐界贡献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中性人李宇春,一个是芙蓉姐姐。从那个时代开始,丑角登上中国文化舞台,包括凤姐等诸如此类。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大困惑,这个困惑如果不解决,我们就无法去探讨未来的文学。在全媒体时代,我们新的美学原则和方法是什么?这个需要我们一起来思考。
(《聚焦“全媒体时代”,再论“闽派”文学精神——2015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暨“闽派诗歌”研讨会发言摘要》,《福建文学》2015年11月号)
●张者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一项内省的工作,是一个反思的过程,是自我剖析行为,是一场自我教育,自我叩问。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过程,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在作品中寻找另外一个知识分子的过程。真诚地写作,不断地寻找,要把自己的书变成驴圈,一直到老,一直到死。知识分子写作是理性的,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完成一部巨著把自己写死了是一种耻辱;愤怒出诗人,但愤怒只能出差诗人;写作中不能自已,号啕大哭,是开玩笑,而且是低级玩笑。
(《知识分子写作:骑着毛驴找毛驴》,《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