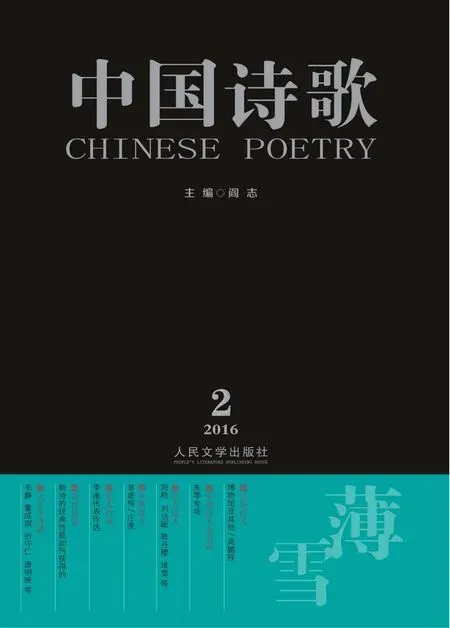新诗经典的三元性
□张用生
新诗经典的三元性
□张用生
说某一首作品是新诗的经典,也不是绝对的,因为经典总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2012年3月11日,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了“首届中国沙溪新诗论坛”,韩作荣、吴思敬、叶橹、唐晓渡、王光明、陈超等三十余人参加。论坛主题为“新诗的经典化问题”。韩作荣认为:“经典是一个神圣的问题。怎样去理解,去遴选经典诗歌,是一个需要时间沉淀,需要后人来评说的事。”唐晓渡认为:“对于中国新诗来说,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尺度。”陈超认为:“百年新诗有两个形象——历史形象与美学形象。”王光明认为:“经典是凝聚于广泛的集体记忆和历史沉淀的文本,文学经典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受文学教育和传播状况的影响。”吴思敬认为:“诗歌经典应凝聚人类美好的情感和智慧,在内容上有永恒性,在艺术上有独创性,而且能穿越现实和历史的时空,经得住不同时代读者的检验。”与会诗人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新诗的经典化作了比较广泛的诠释。本次会议的协办单位《扬子江》诗刊,在半年前向诗人们发出倡议并收回了165份推荐文本,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作品进行评选。短诗、抒情诗是评选的大致范围,“去蔽存真,只重文本,惟好诗入选”,是评选的大体尺度。与会专家慎重评出新诗十九首作为经典作品,它们是:北岛的《回答》、卞之琳的《断章》、戴望舒的《雨巷》、艾青的《我爱这片土地》、洛夫的《边界望乡》、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郑敏的《金黄的稻束》、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曾卓的《悬崖边的树》、张枣的《镜中》、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余光中的《乡愁》、舒婷的《致橡树》、痖弦的《红玉米》、食指的《相信未来》、昌耀的《斯人》、闻一多的《死水》、多多的《阿姆斯特丹的河流》、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这成为了近年来中国诗坛上所发生的一次引人关注的事件。
笔者认为这些诗作不愧为历史的经典,所以能从几十位诗人、诗评家慧眼审视下走出来。这些作品也是在新诗百年中,从短诗、抒情诗这个层面上出现的。笔者在多年的诗歌编辑中接触不少杰出诗人,思考了一些关于新诗经典的问题,在此提出“新诗经典的三元性”与大家讨论。一是背景性:包括时代背景(民族、民间),地域背景(自然、地理),作者背景(个人、家庭);二是慧悟性:作者慧悟(智慧、感悟),偶得慧悟(灵气、偶获),众家慧悟(众识、家慧);三是普特性:普质特质(普性、特性),普乐特质(基调、主调),普鸣性(众鸣、家鸣)。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文明进步、科学飞越、文化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审美观也会变得更情理、更时尚。一百年的新诗经典,会在现有的基调上得到升华。每一位诗人都会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空间里,诗人生存的地域地理背景对于诗歌来说自然是不可少的。假若你生存在植被丰茂,天蓝水清的自然空间,或许会写出清丽的诗句,但也要受其他背景的影响,或许是歌颂或许是逆向。多多1989年带着疮痍的心情来到异国,异国的夜没有给诗人以欣喜,而是让他觉得格外清净,于是就有了一种思念家国的倾泻:“十一月入夜的城市,/惟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突然/我家树上的橘子,/在秋风中晃动,/我关上窗户,也没有用,/河流倒流,也没有用;/那镶满珍珠的太阳,升起来了,/也没有用,/鸽群像铁屑散落,/没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显得空阔。/秋雨过后,/那爬满蜗牛的屋顶,/——我的祖国,/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如果没有那种特定的时空,他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精美的诗句,表达这样真切的诗情。所以每一个人在创作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自然地理背景,它隐藏在诗句的背后,明眼人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并且也只能联系到这样的地理与时代背景,才可能做出独到的解读。
《雨巷》是一首重彩、重象、重情的作品。在它的背后有民国时代的背景,有民间的江南情调,自然更有诗人本身的素质、情采、背景等色调。这表明了诗人的智慧、感悟、灵气,他是在厚积薄发的情境之下,才偶得佳诗。《雨巷》有重彩的普特性:此诗植根于大众情感的土壤里,艺术抒情上具有独立的特质;它的乐感相当强,所以在乐感上有大调的普性,而在乐性上则属于抒情小调。这样的作品朗诵起来行云流水,入乐歌咏犹如独蚕抽丝,有凄婉之美。所以我认为戴望舒的《雨巷》和余光中的《乡愁》一样具有普鸣性,即大众共鸣之力。“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寞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寞的雨巷。/走尽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读着这样的诗句,每一个知识者不得不为之动容,因为它与每一个人的情感相关,与每一个人的心灵相关,除非他对于美无动于衷,或者没有基本的美感能力。
在这次所选出的十九首经典诗歌作品中,背景性(时代背景、地域背景、作者背景)很强,无论哪一首都是这样,诗人和作品的慧艺都能从中解读出来。在慧悟性(作者慧悟、偶得慧悟、众家慧悟)方面,如果我们深知作者较细的背景和经典出炉的背景,慧悟也就能详解其意。十九首新诗有质的普遍性,都植根在人类共性的土壤里,其生长的诗歌各具特性;十九首诗都有普众的音乐感,但每首诗在乐韵色彩上各具特性。余光中的《乡愁》具有普乐特性,普在众感,特在乡愁的独特乐韵色彩。我个人认为十九首新诗经典,能够引普众的共鸣。每首诗各具能引普众共鸣的不同特性,又能感动专家们共鸣。有的具婉约之情的乐韵感人(如《雨巷》、《再别康桥》);有的具壮丽之魂韵动人(如《致橡树》);有的具哲韵喷薄而激情(如《回答》)。
关注人类共性的诗,若在艺术上取得了格外的成功,则更能为时间所检验。杨炼的《诺日朗》、欧阳江河的《悬棺》、傅天琳的《柠檬黄了》、顾城的《一代人》、赵恺的《第57个黎明》,这些优秀的诗歌都不失为一个时代的经典。邹惟山的十四行抒情诗,完全融入了家乡的穹隆意象,所以成就了它少有的格局:“那些圆石与泥沙显然来自于海底/一层层煤炭正为灶王的火种留下/据说高顶寨上从前皆为长街纵横/对面玉皇庙的香火仍然灼痛泪花。”(《俩母山的石头》之四《西海》)笔者认为种种地理因素的融入,会给未来的新诗经典带来不可多得的文学胜景,人类共性元素在此得到了独到的表达。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自然地理是他们生活与生存的根基,所以才会形成地域的文学和地方的文学,诗歌作为文学的一部分也同样是如此。诗人如果注重对于地方因素的发掘,表现人类共有的品质,其作品就更能为读者大众所欣赏、所认可。
新诗的经典性是一个重要的话题,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思考过,就是写出了优秀作品的如上述19位诗人,也不一定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因为诗人看重的是自己的作品,他想写了就写,不想写了就不写,至于作品有没有流传的可能,那是后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