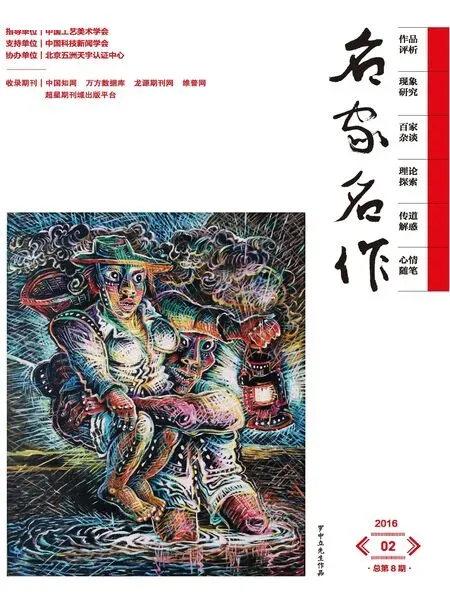论萧红小说“散文化”形式中的深刻意蕴
张凤渝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卫生分院,江苏 常州 213002)
论萧红小说“散文化”形式中的深刻意蕴
张凤渝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卫生分院,江苏 常州 213002)
[摘 要]萧红小说在语言文字、叙述结构、叙述方式和抒情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散文化”特征。这种形式表现了她对生命的深刻理解,深化了悲剧的审美意义,使作品的悲剧意义超出了个体和时代,更具有普遍意义。
[关 键 词]小说;散文化;意蕴;情感
一、“散文化”的小说风格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一位大家,但却是最善于建立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家之一。她惜才如珠,并以开放的胸襟把艺术才华的生命更新建立在探索精神上,勇于打破艺术的陈规,她对文坛的贡献在于凭借出色的才情越出传统小说法规的轨道,以明丽新鲜的笔触、细致的观察和感受,将小说散文化、诗化和绘画化。而其中“散文化”是其小说风格最突出的特征,表现在稚拙清新的语言风格,场景式的结构方式与漫不经心的叙述方式三个方面。
首先进入读者的感官,触发读者感觉的是萧红的文字。她作品中一切情绪、意念等等,无疑是借诸文字而诉诸读者的审美感情。散文相对于诗歌来说,赋予语言表达更大的自由,也更便于负载某些情感。“散文”不只是情韵,不只是结构,也是一种语言形式。
萧红的文字,是一些用最简单,以至于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常常显得不规范。比如:
呼兰河这小城里面,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三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八十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依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1]
几乎是无以复加的稚拙,单调又重复使用的句型,同义反复,在语言学家眼里似乎是费话,然而让人惊异地感到,这种最朴素俗白的文字,经萧红的灵性,而具有某种感人的情调,这也许就是鲁迅所说的“越轨的笔致”。她的文字朴素、平淡,而又新鲜明丽,处处散发出萧红特有的醇厚美。这种语言风格,并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是刻苦追求提炼的结果,而似乎完全出自她天才般的艺术直觉,出自于她对事物的独特感受,一切都是自然流出。她的语言绝对难称“精美”,它们只有构成整个句段篇时,才显示为美;它们不具备修辞学的典范性,甚至出于文法的规矩之外。
与稚拙的“文字”组织相适应的是作品“无结构的结构”。她以自己的美学追求,借助自己的文字组织,有效地使戏剧性淡化了,使情节淡化了,使小说化解为散文。她通常不是依“时”序,而是直接用场景结构小说。如,对于事情的发展过程显得漫不经心,只肯把气力用在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上。久贮在记忆中的印象碎片,就这么信手拈来,嵌在“过程”中,使作品处处洋溢着萧红特有的气息,温润的、微馨的。萧红的叙述中永远有情境,完整地满溢着生活味的情境。这些“情境”散化了情节,浓化了情致韵味。
情致韵味正是散文化的又一个特征,即情绪化。萧红的小说并不以“抒情性”为特征。“抒情”应当是以抒情主体存在为前提的。萧红作品的情绪特征在于那浸透了文字的“感情”,这是一种与文字、与内容不可分离的元素。萧红并没有刻意要抒情,然而,我们读她的作品总能透过她的文字、结构、叙说感觉到一种情感的力量。萧红作品特有的情绪特征、情绪力量主要不是经由主体的发“抒”,而是经由她特殊的文字组织来实现的。
富于魅力的更有萧红的讲述。无论使用怎样的人称,那都是她的讲述,一派萧红的口吻,因而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她最成功的几部作品,如《小城三月》《牛车上》《呼兰河传》,都是由一个独特的“儿童视角”来完成其艺术创作。儿童看世界、思考世界的特有方式,不是诉诸经验与理性,而是诉诸生动的直观,所以才有萧红稚拙清新的语言风格、场景式的结构方式与漫不经心的叙述。
二、“散文化”形式中蕴含的深刻意蕴
评价一种形式的优劣,必须看这种形式是否更好地表现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形式中蕴含的深刻内涵,也就不能对她的风格做出公正的评价。
《生死场》初现文坛,“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惊动”。[2]因其出现在东北沦陷后的1935年,作者为东北流亡青年,作品又是涉及抗战题材较早的作品,于是人们遂将其作为三十年代抗日文学的奠基作品之一 ,并据此批评它描写人民斗争不够坚定,未写出革命主流和党的领导,有悲观情绪。《呼兰河传》的出现,已完全远离了“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大时代”“血淋淋”的现实。于是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个“不可否认的退步,是个人寂寞情怀的写照”。[3]
《生死场》《呼兰河传》在表层的“散文化”叙述之外,隐藏着深刻的主题。《生死场》在将人推到非人的境地,思考其生命活动的同时,也将“生”推到“死”的境地来考察其生命价值。《呼兰河传》是这一审美思考的深入与延伸,写出了为死而生,生不如死。人的生命活动让位于“鬼”的礼仪、祭俗及其阴森统治的种种病态人生相,从而发展了“国民性”思考的历史主题。由于作家着眼于整个民族灵魂的改造,她所关注的中心,就不再是脱出社会常规的个别的、奇特的、偶然的事件和人物,而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瞬息万变的生活现象,特别是人的精神现象,不是沿着一条或数条情节线的传统叙述方式所能载负的。萧红出生于一个开明的地主家庭,在哈尔滨受过现代教育,受着“五四”新文化的深刻影响,后来直接受到鲁迅这位思想巨人的影响,这一切都使她更多地接受了世界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潮、民主精神以及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文化觉醒意识,成为一个根植于现实土壤的“现代文化”追求者和思想先驱。表现在艺术创作道路上,她不囿于传统,勇于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她曾说过:“有一种小说家,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4]
《生死场》着力思考的并不是正面对敌斗争等现实生活的外部关系,也没有戏剧性的英雄乐章般大起大落的艺术情节,而是对民族自立的潜在障碍及其封闭落后而又愚昧陈腐的文化心态进行历史反思。这使其最终舍弃了以情节取胜的新旧艺术传统,而用散文的笔法、“内化”的结构完成其独特的审美思考。她的作品有着细腻悲惋而又敏锐曲致的女性“阴柔美”。不过这已不是传统女性温柔典雅或“犹抱琵琶”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而是“五四”新文化背景下新女性敏慧、犀利、悲惋而又深邃的审美选择。
萧红小说散文化的风俗画卷曾多次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和责难。这是由于其不符合被尊奉一时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审美信条所致。“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得到的紧张的迫力。”[5]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作者从没有硬去按其臆想的因果逻辑关系编织一个完整故事,或是一定让几个贯穿首尾的人物做结构上的行动线索或艺术衔接,而是来去自如,将“环境”当作一个结构线索,一个具有某种性格的主体来描写。使诸多的人物故事只作为这一环境的点缀。使环境成为悲剧的深层内因,从而唤醒人们对于所处环境的自觉认识。萧红小说是深刻的,这深刻性在于她把“环境”的意义从一种衬托性的背景和静态的客体发展为具有主体品格的文化现象。
萧红小说的时空结构里寄托着她对于历史文化的理解。时序的概念对于理解萧红作品的结构有时全无用处。那些作品的各构成之间,往往不是依时序,而是由一种共同的文化氛围焊接在一起的。萧红更注意的,是历史生活中那种看似凝固的方面,历史文化重压下的普遍而久远的悲剧,她用比当时许多作品宽得多的时间尺度来度量这种悲剧。《生死场》写了四时的流转,却没有借时间“推动”情节。占据画面的是信手展示的一个个场景。《呼兰河传》的前半部,更索性使时间带有更大的假定性:是今天,也是昨天或者前天,是这一个冬天,同时也是另一个冬天,是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的呼兰河边的日子。这种时间意识在于强调历史的共时性,强调文化现象、生活场景的重复性。从而由这种历久不变的生活现象发掘民族命运的悲剧性。这样的“时间”当然构造不出通常意义上的“情节”。小说特征在这里也就冲淡了。
时间的假定性势必造成叙述内容的假定性。出现在《呼兰河传》开头的,无论“年老的人”还是“赶车的车夫 ”,甚至于“卖豆腐”的,都是特定的个人。因而,即使“个人命运”,在这里更带有共同命运的意味。时间的假定性,使特定的空间范围(呼兰河)在人们的感觉中延展了。是“呼兰河”的“传”,又不仅仅是呼兰河的。萧红作品中的情境在虚实之间,在具体与非具体、特定与非特定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写实与寓言之间。《呼兰河传》首章中关于大泥坑的故事,就是“呼兰河生活方式”的象征,“意味”又更在呼兰河外,同时也是中国历史、民族命运的象征或者寓言。叙述方式、时空结构又不仅仅是形式,其中更有深刻的内涵。萧红以“儿童视角”出发,平静地、漫不经心地,甚至用一种温和的略带调侃的语调来叙述悲剧,让人感觉不到那种由灾难性的生活变异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痛苦,而是因年深月久而“日常生活化”了的漫无边际的痛苦。后者比前者在美学的天平上也更有分量。
萧红是寂寞的。寂寞地苦苦追寻,寂寞地死在从异乡到异乡的旅途中。她的作品也始终浸透着寂寞情怀,因而有人为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悲凉气氛,一再惋惜。“在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还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至其惋惜一样。”[6]
萧红并没有沉浸在自己的身世之感,她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悲剧感受集中在人类生活中如此“尖锐”的“生”与“死”的大主题上。她尤其一再地写死亡,写轻易的、无价值的、麻木的死和生者对于这死的麻木。
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最惊心动魄的“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就算了。[7]
恬静到麻木,残酷到麻木的,是乡间的生活。这“麻木”在萧红看来,是较之“死”本身更可悲的。流贯萧红创作始终的激情正是关于这一悲剧现象的激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热望,构成了萧红小说有关“生”“死”描写的主要心理背景。
并不尖锐痛彻却因而更见茫漠无际的悲凉感,如淡淡的雾、寂寂的霜,若有若无,无处不在,而又不具形色。它正是萧红所特有的文字组织、叙述方式,也无法由字句间,由叙述的口吻中剥出。
强烈的生命意识,使萧红写“生”写“死”,写生命的被漠视,同时写生命的顽强。萧红是寂寞的,却也正是这寂寞的心,最能由人类生活,也由大自然中领略生命感,一派天真地表达对于生命的欣悦,寄寓她对于美好人生的永远的憧憬和期待。正是这两面的结合,才更见萧红的深刻。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飞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8]
如此亲切体贴富有生命力的自然描写,在萧红的作品里比比皆是,她把“生命感”注入她笔下那些极为寻常的事物,使笔下随处有生命在勃发、涌动。并非有意的“拟人化”,却一切都承有着自己的生命意识,活得蓬蓬勃勃、生机盎然。萧红并不大声呼唤生命,生命却流淌在她的文字里。
天真无邪的生活情趣与饱经沧桑的人生智慧,充满欢欣的生命感、生命意识与广漠的悲凉感,都碰在一起,也才有萧红的淡而有厚味,稚气而有深度,单纯而有智慧。
萧红以自己独特的生命感受和艺术天才突破了艺术表现的常规,选择了最有利的角度切入生活,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个性、最有利的方式来表达她深刻思想,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位置。
参考文献:
[1]萧红.呼兰河传[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05:265.
[2]许广平.追忆萧红[A].张毓茂,阎吉宏.萧红文集[C].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07:376.
[3]葛浩文.萧红评传[M].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03.
[4]聂绀弩.萧红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2.
[5]胡风.生死场(后记)[A]张毓茂,阎吉宏.萧红文集[C].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07:327.
[6]茅盾.《呼兰河传》序[A].张毓茂,阎吉宏.萧红文集[C].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07:12.
[7]萧红.呼兰河传[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05:39.
[8]萧红.呼兰河传[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05:90.
张凤渝,女,汉族,江苏盱眙人,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卫生分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
On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Xiao Hong’s Novels in the form of “Prose Features”
ZHANG Feng-yu
Abstract: Xiao Hong’s novels show distinctive features of“prose features”in the language, narrative structure,narrative style and lyrical aspect. This form shows her deep understanding of life,and deepens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the tragedy, so that the tragedy of the work is beyond the individual and the times,but also has univers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novels;prose features;implication;emotion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8854(2016)02-0008-03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