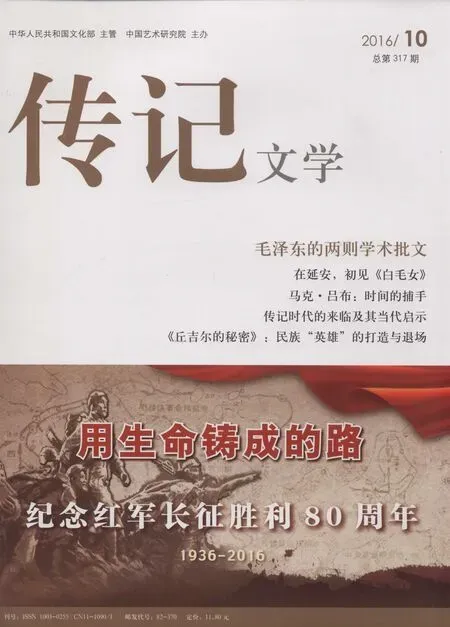传记时代的来临及其当代启示
文|梁庆标
传记时代的来临及其当代启示
文|梁庆标
内容提要 20世纪后期以来,作为主要的非虚构文体,传记迎来了它的时代。传记地位的凸显有多种表现,作品的大量出版是一个方面;传记批评与理论的逐步成熟则是“传记时代”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传记学”进入现代阶段的体现。传记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文类,如今能自成一家,与虚构文学批评、历史批评鼎力相持。从深层角度看,传记对人类自我认知及自我超越的意义非同寻常,是人们认识复杂人性、丰富现代人格、完善理想自我的必要路径。不过,在当代中国,受传统观念及现实利益的影响,传记依然要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这就需要传记家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更强的伦理意识、更深厚的哲学积淀以及更充分的自信。传记的“人生”之途依然艰难、漫长,但充满光明。
传记;成熟;困境;启示
—— 开课的话 ——
1978年,西方第一份传记研究刊物《传记》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创刊,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传记理论与批评逐渐形成独立的话语体系,自成一家,在当代国际学术研究领域已然占有了一席之地,“传记走向了西方文化的前沿”,“传记迎来了它的时代”。
我刊从这期开始尝试开设“传记课堂”栏目,与国内外传记研究机构携手,邀请优秀的教师,开讲传记理论与批评课程,既有理论建构与文本分析,也有宏观评述与微观品读;既回顾总结传记的发展历程,也力图阐明其未来发展趋势。我们的“传记课堂”在“传记的成熟”季节开课,相信在摘得成熟果实的同时,也一定会播下优质的种子。
写得精彩的传记几乎像活得精彩的一生那么难求。①
——〔英〕托马斯·卡莱尔
传记史上的先驱、哲人蒙田曾这样写道:“‘做你自己的事,要有自知之明’,人们通常将这一箴言归功于柏拉图。这一格言的每个部分概括了我们的责任,而两部分之间又互相包含。当一个人要做自己的事时,就会发现他首先要做的便是认识自我,明确自己该做什么。”②显然,终生具有强烈自我意识且以记录、认识自我为要务的蒙田在此表达得非常清楚:自古希腊以来,对自我的认知便被认为是人的首要任务,“知与行”在此结合为同一问题,成为人类存在要面对的一大根本命题。纵观历史,应当可以说,认识人之自我乃至人类本身的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便是传记(life writing,这里乃就广义而言,既包括自传也包括他传)——这一真实人生的载体。因此不难理解,在世界文化特别是在西方文化中,传记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据研究,最古老的自传文本之一是中古王国时期赫梯君主哈图西里三世(前1275-前1245)的自传,该自传以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了他如何获得权力的故事,其中“我”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而且包含了对自我的解释与分析。③在此之后,中外出现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传记作品:柏拉图和色诺芬对乃师苏格拉底的记述、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司马迁的《史记》、绥通纽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等相继开创了这一传统,堪称古代典范;蒙田的《随笔集》、佩皮斯的《日记》之后,约翰生的《诗人传》、鲍斯维尔的《约翰生博士传》、卢梭的《忏悔录》、歌德的《诗与真》、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等则将其发扬光大,使18世纪成为了传记的一个“黄金时代”,闪耀出人性的光辉;经过19世纪的相对沉寂,到了20世纪早期,英国的伍尔夫、斯特拉奇,法国的莫洛亚,奥地利的茨威格等发展出“新传记”,赫尔岑、高尔基、马克·吐温、纪德等则通过文学笔法使自传负载了丰富的政治、伦理等要素,使其进入现代形态,突出了人格书写、主体意识和叙述功能;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传记又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写作者遍布各个社会领域、阶层和学科,如特洛亚、艾尔曼、艾德尔、派因特尔、博伊德、阿克罗伊德、迈克尔·怀特等,就最为凸显的自传而言,就有萨特、波伏娃、罗兰·巴特、阿尔都塞、德里达、罗素、卡内蒂、莱辛、田纳西·威廉斯、纳博科夫、萨义德、格拉斯、马丁·艾米斯等名家,文本形式多样,意图与修辞愈加复杂,甚至有研究者将此称为“传记的成熟”④。
这一说法来自当代英国传记家奈杰尔·汉密尔顿⑤。他长期从事传记写作与研究,在近著《传记简史》中述及传记的现状与发展趋向时明确指出,20世纪末以来,传记的兴盛已是不可阻挡。他用了“传记的成熟”(Biography Comes of Age)作为书中一章的标题,认为“传记终于迎来了它的时代”,并且可以看到,“在20世纪末,传记走向了西方文化的前沿”⑥。进一步说,他甚至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传记‘转向’”。⑦由此,汉密尔顿表达了一个基本判断:传记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了当代文化与学术研究的重心与热点之一。
一
传记的繁荣与地位的凸显有多种表现,传记作品的大量出版、传播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与虚构类的小说相比,侧重真实人生与人性的传记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真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一个角落、每一种肤色、每一种性别、每一种身份,以及几乎每一边缘群落——都可能暴露在传记家的显微镜下,成为持续的兴趣和好奇心的关注对象。”⑧每个人的人生都包含着故事,都有记录和书写的价值,也能吸引不同层面的读者,当代的传记家和自传者们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导致传记作品的大量涌现。正如汉密尔顿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研究所指出的:“在西方非虚构类作品的传播与出版方面,传记已成为最流行的领域。”⑨也有学者通过统计指出,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每期的评论中很少会少于3部传记⑩,可见其分量之重、影响之广。我们还可以看到,除了正式出版物,伴随着电子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在各类自媒体的便利条件下,它已经扩展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网络上的博客、日志、相册、视频等,从而进入到万千普通人的生活之中。教育领域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从事英语文学与文学写作的学生正在学习和写作的他传与自传文本超过了虚构类文本;……在电影学校,传记和自传计划也在数量上超过了虚构类作品。”⑪这保证了传记在未来的赓续和变革的可能。汉密尔顿甚至大胆断言:“事实上,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传记已经与小说互换了位置。”⑫也就是说,传记似乎在逐渐取代小说曾经的主导地位。据此,他对读者提出了建议——“赋予你的生命以意义”(Making sense of your life)⑬,也就是鼓励读者去书写自己的人生,这看起来颇令人激动。
回过头来看,传记的当代境况可以说是某些历史声音的回响,在传记步履艰难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早就认识到了它的潜在价值。有人指出,经过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传记盛世,19世纪初,英国首相狄斯莱利就曾说过一句话:“不要读历史,除了传记外什么也不要读,因为传记才是生活,而且不含枯燥的理论。”⑭这无疑是对传记的极度肯定和推崇,他不仅把传记与历史区别开来,甚至将其置于历史之上。在这直观感性的断语中,我们可以嗅到尊重生命的气息。不过19世纪是小说发展成熟的时代,受到维多利亚时代道德风尚的影响,人们更愿意以虚构的方式呈现自我,真实被蒙上了面纱,传记受到过多限制,虽然体量很大,但过于保守沉闷,创新之处无多。转机发生在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时期,伴随着自我认知的观念更新与个性主义的复苏,传记与小说一起成为作家们的实验对象。1928年,即伍尔夫发表了《新传记》(1927)之后一年,约翰·梅西就指出,在过去十几年间传记开始兴盛,并吸引了人们的广泛兴趣,甚至“在畅销书榜上传记和小说在一争高下”⑮。这与当代的状况也颇为相似。琼斯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传记”在欧陆以及美国盛行开来,“在一年半或两年之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新’传记在美国出版界无疑非常流行而且利润可观”⑯。这说明,传记写作与阅读,用现代的话说即“传记产业”,在当时就成了一种世界性的、至少是西方世界的重要现象,一直是人们的兴趣所在。针对20世纪以来传记与小说的消长关系,在1978年出版的一部传记研究论文集中,丹尼尔·艾伦如此认识与理解:“当批评和严肃的小说世界看起来越来越遥远时,传记可能正提供了一度由小说、诗歌、批评和历史来满足的需求。”⑰世界日益复杂多元,人性愈发捉摸不透,当代人的生存焦虑日趋严重,几乎所有坚固的东西都在“烟消云散”,基于真实与人性基础之上的传记正可以成为人们把握人之自身和世界的方式,由此获得存在的稳定感和现实感,因此说传记成为读者的新宠,在当前出现热潮就不难理解了。
传记批评与理论的发展和逐步成熟则是“传记时代”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传记学”进入现代阶段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传记批评基本呈零散状态,文学家、批评家对传记偶有涉及,但并未形成常态和持久的研究兴趣,因此难成规模与体系。但是显而易见,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记研究论著在西方成倍增加,传记甚至成为学术研究的“最前沿阵地之一”和“热点领域”:“有关传记研究(特别是自传研究)的论著大量出现,一位美国的研究者收集了一些数字以后宣称:对自传的研究已经‘从文学研究的边缘进入了主流’,所出版的论著在25年中增加了2500%。”⑱也就是说,在形式主义、新批评等式微之后,众多的理论家都转向了虚构的反面,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传记这一富有开放性、前沿性和持久生命力的学术领域,从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角度切入传记,丰富了传记理论体系,也深化了人们对传记的认识。对此,王元化先生早有洞察,他在《〈鲁迅传〉与传记文学》(1981)一文中提到:“在我们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内,直到目前为止还留下许多空白点,而传记文学这一课题似乎始终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在国外,传记文学早已成为专门名家的学问。”⑲两相对比,正见出西方传记研究的先行先觉之处。而且西方国家对传记的重视不仅体现在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中,还延伸到了中学教育之中。菲利普·勒热讷就指出,在法国,“从2001年以来,自传成为中学一年级5个必修的文学课程之一。成千上万的老师要向成千上万的学生讲解自传”⑳。自传以系统、专业的方式被传授,实乃前所未有,这一境况充分说明了它的普及性和现实性。
在西方,1978年可以看作传记研究专业化、制度化的一个转折点。美国著名传记家、理论家、《亨利·詹姆斯传》的作者利昂·艾德尔㉑当年在夏威夷大学马诺亚分校创办了《传记:跨学科季刊》(Biography:An Interdisciplinary Quarterly)㉒杂志,这是西方国家第一个从事传记研究的专业学术刊物,它标志着传记研究进入了大学校园和学术殿堂,传记理论停留在传记家的感想和经验总结,或者说由小说家来评价传记的时代已成过去。1985年,在詹姆斯·奥尔尼㉓的支持和帮助下,北美另一个传记研究专业杂志《a/b:传记研究》(a/b: Auto/ Biography Studies)也得以创立,并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逐步稳定下来,至今已有30年。美国自传研究专家埃金也提到,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记才进入北美最大的学术团体“现代语言学会”(MLA)的议题之中。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一批传记学者,承袭了20世纪初期由伍尔夫、斯特拉奇、莫洛亚等人开启的“新传记”传统,清理了从约翰生乃至普鲁塔克发端的传记理念,另一方面,又从20世纪西方文学、史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化批评中广泛吸取养分,对传记理论加以发展。传记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并融入了当代国际学术的潮流,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传记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文类,到20世纪90年代理论研究日益兴盛,至今竟能自成一家,与虚构文学批评鼎力相持。
基于这种现象,英国学者乔利主编了《传记百科全书:自传与他传诸形态》(2001),作为世界传记领域的“第一部百科全书”㉔,此书的出版可以看作传记研究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一,与杨正润教授的专著《现代传记学》相得益彰。它们共同包含了上自古代,下至20世纪末全世界比较重要的传记作品、传记家和传记理论问题,勾勒了一幅传记地图,深具学术性和前沿性,为传记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基于此,21世纪的传记写作与研究具备了良好的出发点。
二
溯其根源,传记在西方的繁盛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关,特别是西方人的自我探索与自我认识传统。针对20世纪以来传记的兴盛现象,汉密尔顿指出:“似乎西方社会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寻找自我的运动。在这里,真实的人的生平故事现在看来更为重要、更真实,也更易得,而且比那些虚构的人物更有启发意义,几千年来艺术家和作家们生产了那些人物,把他们作为善行的模范,并以此来警示恶行。”㉕也就是说,一度由虚构人物承担的政治、道德、伦理等功能,现在由真实的人来完成,他们更为真切可感,也更有效用。
从这一深层的哲学角度来看,传记对整个人类自我认知及自我超越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是对个体生命的记录与解释,其对象是人之自我,尤其是心灵世界这一“微观宇宙”㉖,所展现的正是人类自身的复杂性和自我认知的限度,包含了关于人性、存在的所有命题与困境,可谓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在它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交出自己的答卷。因此说,传记这一“人性迷宫”的巨大魅力就在于,它是人们认识复杂人性、丰富现代人格、完善理想自我的必要路径,它永远铺展在人们的面前,引领着探索者不懈前行。
传记在现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兴盛也符合这一历史趋势。独立自由、自我意识、个性观念等代表现代主体诉求的理念与传记的盛衰密切相关,晚清以来的几次思想启蒙与文化开放都大大促进了传记的发展,在20世纪前期由梁启超、郁达夫、胡适等为代表,在“五四”前后进入了现代传记的一个“黄金时代”;而到了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之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之下,则出现了传记普遍兴盛的局面,传记成为人皆可为的文体,没有很高的门槛和对文学素养的特别要求,真诚就是它的基本标尺和最大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他身体力行,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国人的传记自觉,不光亲自写作多部传记,还开设传记课程,通过演讲介绍传记,并鼓励友朋进行实践,这方面有很多实例。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来成为了历史学家的邓广铭在北大修习胡适的“传记文学习作”课程,他的作业就是一部《陈龙川传》,并于1943年出版。胡适对此书很赞赏,认为是一部“可读的新传记”㉗。胡适对中国传记事业的推动之功由此可见一斑,这背后体现的就是他对人性自由与独立人格的尊重,这使得他非常看重个体在历史中的巨大作用。此后,朱东润也通过他的《张居正大传》等多部传记与专业研究延续了中国的传记事业,并使传记确立为高校的一个研究方向,韩兆琦、杨正润、赵白生等当代学者都是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对传记理论进行开拓的。可以说,就写作实践和理论研究而言,当代中国的传记进入了难得的发展时期。
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回避传记面临的困境。在当代中国,受传统观念以及现实利益的影响,我们依然不得不面临多个方面的挑战与阻碍。其中最明显的是缺乏自觉的传记意识,而且对传记存在误解。比如,多数人依然认为传记是伟人名家之事,自己没有资格留下传记,缺乏个性观念与人权意识;或者相反,受通俗传记的影响,将传记视为低俗的猎奇与窥视,是在满足人们隐秘的欲望,不值得提倡。李广田的女儿李岫提到,早在1948年,有《人物》杂志向李广田约稿写《自传之一章》,李广田没有答应。他后来在《自己的事情》中写道:“‘自传’两个字似乎有点严重,我以为我自己并不配写什么‘自传’之类,即便是‘之一章’也不行。”㉘身为知名作家的李广田还如此看待自己,普通人就可想而知了,这正代表了国人的一种普遍态度。到了21世纪,诗人余光中依然对传记持有很强的偏见,并坚持不写自传,也对他人为自己所写传记的“颂词”并不认同。他说:“朋友劝我写自传,我不想写,也不认为有这必要。我觉得,作品就是最深刻的日记,对自己;也是最亲切的书信,对世界。”㉙显然,他将自己的作品视为了传记,但这是戴着面具的隐形自传,是对自我的遮掩与保护。他承认,退一步说,就算他真的提笔写起自传来,“也不会把什么都‘和盘托出’,将一生写成一篇‘供词’。那样的自传对传主岂非自表‘暴露狂’,而对读者岂非满足‘窥秘狂’?凡此恐怕非纯正的品味”㉚。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传记的理解比较狭隘和通俗,没有真正认识到其背后蕴含的人性与文化价值,过于保守了。当然,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
此种意识也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传记的根本要素——真实性的怀疑。虽然大家阅读乃至写作传记,但都知道其真实性是有所保留的,因此都是半信半疑、虚虚实实,并不那么严肃地对待它。钱锺书早就借助“魔鬼”之口讽刺过传记。“魔鬼”夜访钱锺书,说他因为出了名而被社会关注,许多隐私都被别人拿去发表了,搞得将来写自传就没有新料可爆,因此无奈地说,将来不得不另外捏造些新鲜事实来吸引人。钱锺书吃惊地问,这样岂不与传记精神相悖?魔鬼如此答道:“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作的传。自传就是别传。”㉛这段话真是够辛辣,其实正是钱锺书自己的“反传记观”,在他看来,人们尽可以吃鸡蛋,但并无必要认识下蛋的鸡,他不想暴露在传记的显微镜、窥视镜之下。余光中也说过类似的嘲讽之语:“当你记下自己本来该做的好事,而且删去自己真正做过的坏事——那,就叫回忆录了。”㉜他们都指向了传记写作中的选择性与过滤性问题,这是影响其真实与声誉的根本原因。
如此一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虽然国内每年都出版数以千计的传记,但令人忧心的是委实缺乏传记经典,精品匮乏。很多传记都乏善可陈,写作时畏首畏尾,人性剖析不够深入,人格把握不能到位,敏感隐私不敢揭示,语言叙述也缺乏动人魅力。恰如英国著名传记家、历史学家卡莱尔所说的:“写得精彩的传记几乎像活得精彩的一生那么难求。”㉝这确实值得我们警醒,也让我们想起了伍尔夫在1939年就曾预言性地指出的:“如今传记尚处于其生涯的开端,它还有很长很精彩的人生要度过,当然我们可以确信,这一人生充满了困难、危险和艰苦的工作。”㉞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要面对传记的现代发展这一艰难的任务,其实也就是面对人性中的各种痼疾,要有所革新和演进确实非常艰辛,这就要求我们保持开放的视野,充分吸收传统传记的优点,参照中外传记经典,借鉴现代传记批评理论,推动中国当代传记事业的成熟与勃兴。
三
从中国的传记现状看,迫切需要重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传记写作的专业化。这主要指传记家对传主工作、生活各个方面的高度熟悉,包括其职业、生涯、人格等,尤其当传主的职业具有高度专业化特点(如科学家)的时候,如此传记才能写得到位、不流于表面。这其实要求传记家具备一定的专业才能,单纯的文字能力、文学才华是不够的,还要有与传主相应的研究经历或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传主,进行更深入的对话。另外,专业也带有“忠诚”的意思,要求传记家在这一传主身上付诸超常的努力,耗费相当多的精力与时间,这样的传记才具有活的灵魂。传记史上最经典的就是青年鲍斯维尔的《约翰生博士传》。他从苏格兰跑到伦敦,长期跟随约翰生,并随时进行记录和整理,甚至被嘲讽为“跟屁虫”,但其传记是何等鲜活。英国学者派因特尔从少年时代就喜欢读《追忆似水年华》,后来耗费多年时光收集了关于普鲁斯特的各种资料,完成了《普鲁斯特传》;格林布拉特是莎士比亚专家,博伊德是纳博科夫专家,他们基本都是穷尽毕生心血,将自己的所得融入了传记之中,他们从事的真正是生命传承的事业。或者竟可以说,如同有些作家一辈子只有一部代表作一样,一位传记家一生可能也只能写一部最经典的传记,那是他的使命。
而在写作姿态和主体间关系中,传记家与传主之间要有平等的对话意识、争辩意识,他不能操纵传主,但也不能被传主操纵,这两个世界还要保持必要的张力。比如传记家怀特自称是托尔金迷,大学时连读七遍《魔戒》,但是对于为托尔金作传,他还是非常谨慎,要求自己写出真实而丰富的传主人格,如其私生活(与妻子伊迪斯的关系、与朋友刘易斯的关系)和内心世界,尤其是人性的阴影。针对很多传记将托尔金视为“圣人”这一现象,他大胆地进行了探查和质疑,最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托尔金是一个好人,“但并不足以被当作一个圣人”㉟。怀特为牛顿作的传记《艾萨克·牛顿:最后的炼金术士》也同样破除了关于牛顿的许多传说,尤其是“苹果故事”,认为这是牛顿为了隐瞒自己的炼金秘密而编织的幌子,再由学生和信徒们加以宣扬。他认为,只有还原了真相,伟人的真正伟大才能彰显,而非被颠覆,他说,“我们在解释一个奇迹的时候,不必害怕奇迹失踪”,虽然牛顿的学生将一些资料隐瞒了好几个世纪,“但当这些东西被公诸于世之后,原本学校教科书上的圣人才有了更完整的人性光彩”㊱。
这就需要传记家具有高度的伦理意识,即保证对传记的“事实伦理”的尊重。虽然学者提出了“自传契约”等理论,但传记并非法律文书,写作者也无需为作品中的人生真伪负法律责任,从本质上讲,它乃是一种伦理写作,即使有所谓惩罚,也主要是道德、心理层面的。这就为传记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自我持守的“传德”,避免受到“现实伦理”或“审美伦理”的过度干扰,避免有意甚至恶意的捏造、虚构或隐饰,从而正大光明地呈现真实的人生。英国传记家尼克尔森的《婚姻肖像》可算一个例证。作者的传主是他作为名人的父母,母亲是作家维塔,父亲是外交官尼克尔森。但是作者丝毫没有为亲者讳的意思,将父母的婚姻关系、其间的纠葛与隐私一一披露出来,其“炸弹式”的信息是:他的父母都有同性恋经历,而且维塔是伍尔夫的情人,还是《奥兰多传》的原型。因此汉密尔顿指出:“此传不是那种孝顺的维多利亚式儿子的作品。”㊲不过,他看似是对父母的不敬不伦,其实在更高程度上承担了伦理责任,赢得了读者的更大尊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则采取了死后出版传记的方式来保障内容的真实,因为此时他“再没有什么希求又没有什么恐惧”㊳,因此得以放开手脚大胆陈述他人与自我的缺点,而不是像面对众人时有意做出的虚伪的“表演”。
如果要对传记家提出更高要求的话,那就是最好具备较高的哲学素养。中西传记的一大明显区别就体现在哲理的深度上,这决定了它们对传主人性理解层次的高低以及表现层面的高下。传记家应该能深切地体会到,没有深厚的哲学积淀,就无法走出柏拉图笔下那幽暗而充满假象的“洞穴”,无法透彻地理解人生和人性,就难以写出人生况味的复杂,只能是流于生平的琐碎细节或流水账式的记录,背后的关联和内在意蕴也难以把握,而这种弊病恰恰是大多数传记的表征。堪称世界传记史上最伟大经典的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根本原因在于,普鲁塔克本质上是一位信奉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家,传世的还有一部传记色彩非常浓厚的哲学著作《道德论丛》,二者正可以相互阐发、印证。他熟悉当时众多的哲学流派,如伊壁鸠鲁哲学,并与之争辩,而不同的哲学观恰恰是他笔下的那些帝王将相思想、人格与事业的基础。普鲁塔克因此抓住了要害,传记方能入木三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各种质疑,传记家依然要保持自信。要认识到,许多声称不信任传记、攻击传记的人,反而从传记中受益良多,他们其实是真正的传记热爱者,并能够从中找到自我认同。比如上文提到的余光中,他也曾谈到读《济慈传》的感受,因为发现济慈和他自己一般高,就感到非常亲切;他读了关于艾略特的传记,知道诗人的第一次婚姻并不美满,就对他更加同情,也更好地领悟其诗了。钱锺书虽然讥讽传记,也反对别人探察他的生活与内心世界,但杨绛先生偏与丈夫不同,她不停地书写传记与回忆,记录家庭生活与各种遭遇,从中呈现了钱锺书以及她自己的丰富人格,感人至深。试想想,在这个日益冷漠化、技术化、功利化的苍白世界里,还有什么比真实鲜活的人性与人生故事更能打动人的心灵的?能读到细腻、生动、真实的传记,实乃读者之幸。
当然应该承认,与诗歌、小说等已经高度成熟甚至过了鼎盛时代的文体不同,传记虽然古老,也相对成熟,但它演进比较缓慢,依然处于开放性的发展之中,特别是与当代文化的各种形态之间建立了密切关联,正日益焕发新机。或者可以说,当代文化(尤其是影视、网络传媒)与传记已是不可分割。如经典美剧《纸牌屋》中出现了传记家托马斯,可以看到,传记因素的加入使得此剧的人性深度大大加强,借助这一视角,观众得以进入总统安德伍德夫妇的内心世界与隐秘空间,他们也开始真正地直面自身,认识自己,这形成了巨大的人性张力,令人印象深刻。
当然,由于传记文类的独特、形态的复杂和作品数量的庞大,要想全面地掌握这些材料是不可能的,当前任何传记理论也只能是当代人在可能的视野范围内对传记历史的总结和对传记未来发展的展望与推测。但我们相信,传记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动态发展之中,需要的是一点一滴的持续改进,不可能一蹴而就,如同人性本身缓慢而坚定的演化一样。由此我们可以回应伍尔夫说,传记的“人生”之途依然艰难、漫长,但充满光明。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
责任编辑/斯 日
注释
①转引自傅孟丽,《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②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上),潘丽珍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31页。
③梁庆标选编,《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5页。
④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41.
⑤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英国传记家,曾任教于伦敦大学等。著有《J.F.肯尼迪:鲁莽的青春》(1992)、《克林顿传》(2003-2007)等 多部传记,以及学术著作《传记简史》(2007)等。
⑥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 p.279.
⑦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 p.312.
⑧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 p.239.
⑨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 p.279.
⑩Mary P. Gillis, Faulkner’s Biographers: Life, Art,and the Poetics of Biography, 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2002, p.8.
⑪ 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 p.280.
⑫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 p.283.
⑬ 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 p.287.
⑭ A. O. J. Cockshut, Truth to Life: The Art of Biography in the 19th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p.9.
⑮John Macy,“The New Biography”, The English Journal, Vol. 17, No. 5 (May, 1928), p.355.
⑯ Howard Mumford Jones,“Methods in Contemporary Biography”, The English Journal, Vol. 21, No. 2, (Feb., 1932), p.113.
⑰Daniel Aaron,“Preface”, in Daniel Aaron ed.,Studies in Biography,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viii.
⑱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⑲王元化,《思辨短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7-188页。
⑳菲利普·勒热讷,《从自传到日记,从大学到协会:一个研究者的踪迹》,《现代传记研究》(第1辑),2013年,第42页。
㉑利昂·艾德尔(Leon Edel, 1907-1997),美国传记家、文学批评家,先后在纽约大学和夏威夷大学任教。1976年在夏威夷大学创建了传记研究中心(CBR),并创办学术期刊《传记》,代表传记为《亨利·詹姆斯传》(5卷),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另有《书写人生:传记通则》(1984)、《文学传记》(1957)等评论著作。
㉒这份刊物可以看作当代传记研究史的缩影,本身就体现了传记研究的进程,值得专门梳理。
㉓詹姆斯·奥尔尼(James Olney,1933-2015),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自传研究,著有《自我的隐喻》(1972)、《记忆与叙述》(1998),并主持编译了著名的《自传理论与批评文集》(1980)。
㉔Margaretta Jolly, ed., Encyclopedia of Life Writing: Autobiographical and Biographical Forms,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2001, p.ix.
㉕ 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 p.238.
㉖ Laura Marcus,“The Face of Autobiography”,in Julia Swindells ed., The Uses of Autobiography,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95, p.14.
㉗刘浦江,《不仅是为了纪念》,见《读书》杂志编,《不仅是为了纪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82页。
㉘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㉙傅孟丽,《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第3页。
㉚傅孟丽,《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第3页。
㉛钱锺书,《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见《钱锺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㉜傅孟丽,《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第2页。
㉝傅孟丽,《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第1页。
㉞Virginia Woolf,“The Art of Biography”, in James Lowry Clifford ed., Biography as an Art: Selected Criticism 1560-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33.
㉟迈克尔·怀特,《魔戒的锻造者:托尔金传》,吴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7页。
㊱迈克尔·怀特,《魔戒的锻造者:托尔金传》,第7页。
㊲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 p.236.
㊳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编者导言”,第21页。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自传理论与批评研究”(11CWW01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11&ZD138)之“港澳子课题”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