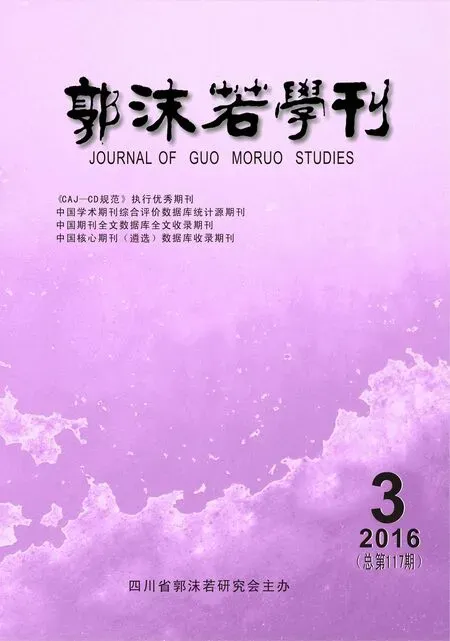郭沫若的公孙尼子及其“乐”论研究
杨胜宽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郭沫若的公孙尼子及其“乐”论研究
杨胜宽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乐山614000)
郭沫若是20世纪开启公孙尼子及其“乐”论研究的引领者,他把公孙尼子的“乐”论思想置于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体系研究比较的平台之上,通过全面分析其关于“乐”的性质、功能与作用、意义与价值内涵,来阐释这些思想主张与儒家社会政治学说的联系及其与墨家、道家立场的差异,并由此确立公孙尼子“乐”论思想在先秦思想史上的贡献与地位。后世许多研究者只把公孙尼子的“乐”论视为音乐理论,是狭隘和不够确切的。
公孙尼子;“乐”论;思想内涵;儒家社会政治学说;《礼记?乐记》
公孙尼子其人、其书、其思想,因为史料的匮乏研究难度甚大。史书上没有关于其时代与身世的确切记载,只有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之类的史书篇章中,著录《公孙尼子》一书时极为简单地提及其名和大约活动年代。因此,要考察此人的身世、著作与思想主张,多通过勾稽相关旁证材料予以分析并得出推论。故而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其他研究者,有关公孙尼子及其“乐”论的研究结论都不能说普遍获得了学术界的全面认可。如他跟钱穆的观点分歧就是如此。即便如此,郭沫若对公孙尼子及其“乐”论的研究,依然是迄今最具开拓性意义且认可度最高的成果。
一、关于公孙尼子及其著述的考察
郭沫若关注公孙尼子的动机,在其《十批判书·后记》中有清楚交代:“就在写完《秦楚之际的儒者》的同一天晚上,我的兴趣被吸引到音乐问题上面去了。因为儒、墨之间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音乐。我须得彻底根究一下儒家方面对于音乐的见解究竟是怎样。因而公孙尼子的《乐记》便上了我的研究日程。研究《乐记》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我曾经参考着《史记·乐书》《荀子·乐论》及其他有关文献,把《乐记》按照刘向《别录》的原有次第加以整理,整个抄录了一遍。一切准备工作停当了,九月四日‘夜,开始草《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第二天也就把它完成了。”[1]465-466这段话揭示了以下值得注意的信息。
第一,郭沫若在1943年的这段时间一直把研究精力放在儒、墨关系上,他之前所作的《墨子的思想》《述吴起》《秦楚之际的儒者》,都以厘清儒、墨的基本思想以及两家思想影响于两大流派人物的思想倾向与社会作用为主要研究目的。他的兴趣被吸引到音乐上面,也是为了分析比较两家“是乐”与“非乐”思想的根本区别。
第二,郭沫若用来与墨家“非乐”思想观念作对比的儒家代表性著作,主要是《礼记·乐记》和《荀子·乐论》。这里牵涉两个相关的重要问题:一是《乐记》关于“乐”的思想理论来自哪里;二是《乐记》与《荀子·乐论》是什么关系。
关于《乐记》思想的渊源所自,首先又涉及《礼记》一书的构成与传承问题。据《隋书·经籍志》所载,《礼记》是由孔子弟子及后学者所记汇编而成,汉初河间献王献于朝廷者计一百三十一篇。西汉末刘向考校经籍,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序之;后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五种合计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记》。而其弟戴圣又进一步删削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礼)记》,汉末马融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为四十九篇,融弟子郑玄传其学,并为《礼记》作注。随即郑注之《礼记》立于国学,得以传世不废。[2]925今天所见,即郑玄作注的小戴《礼记》四十九篇。然而,其中《乐记》三卷列于第十九,人们已经无法弄清保存至今的《乐记》,究竟是马融所定的一篇,还是戴圣删定的《礼记》原本有之。
《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列于儒家,注云:“七十子之弟子。”又有《公孙尼》一篇,列于杂家。[3]1725-1741郭沫若认为,二书的作者“论道理应该是一个人”,但没有解释认定的理由。[4]487其措辞的推测意味十分明显。《汉书·艺文志》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3]1742郭沫若的推论或许基于此说。《隋书·经籍志》将《公孙尼子》一卷列于儒家,注云:“尼,似孔子弟子。”[5]957郭沫若认为,这就是《汉书·艺文志》列于杂家的一篇,且云:“注语与班固不同,当是长孙无忌别有所据。”《隋书·经籍志》的编撰者之一长孙无忌何以将《公孙尼子》一书作者公孙尼从七十子之弟子,改题为“似”孔子弟子,依据是什么,作者并未明示,也许纯属推测;郭沫若认为“当是别有所据”,更属推测之推测。
即使两种史书对于《公孙尼子》一书作者的身份看法不太一致,但在认定为孔门弟子这点上是一致的,差别只在嫡传或再传上。基于此,郭沫若还在《隋书·音乐志》里找到沈约上梁武帝的《奏答》,证明《礼记·乐记》主要取自《公孙尼子》。案《隋书·音乐志上》载沈约语曰:
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6]288
按照沈约的说法,《乐记》有两个传承系统,一是河间献王、毛生等人採《周礼》及诸子言乐事者编纂的《乐记》;二是刘向校书所得的二十三篇《乐记》,其内容与前者大不相同。依照上述《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传世的《礼记·乐记》,是戴圣在刘向校考经籍、戴德删削烦重的基础上确定的篇目,与河间献王等人编纂的《礼记》之传承系统完全不同。迄今研究者关于《乐记》的作者是公孙尼子还是河间献王仍然存在诸多争议,但照沈约的说法,《乐记》的主要内容取自《公孙尼子》,其与河间献王没有直接关系,应该是说得比较清楚的。郭沫若认为:“《公孙尼子》的一部分算在《乐记》中被保存着了。”[4]487这个推断是可以成立的,也可能是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依照上世纪90年代于湖北荆门新出土的郭店楚简所保存的战国文献考察,《礼记·乐记》主要取自《公孙尼子》,《缁衣》取自《子思子》,而《子思子》《公孙尼子》均成书于战国初期,这一事实得到了出土文献的有力印证。[7]这也说明,沈约当时在《奏答》中向皇帝陈述的关于历史文献渊源和传承关系的说法,是有根据且可以采信的。
基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乐记》的思想观念源自孔门,而不是如钱穆所说的出自荀(子之)门[8]573,难以确证的问题只在究竟是孔子直传还是七十弟子之一所传;其年代在战国早期,而非战国末期。郭沫若依据公孙尼子有关“性”的主张与孔子极为相近的情形,认定他就是孔子的直传弟子:“公孙尼子可能是孔子的直传弟子,当比子思稍早。虽不必怎样后于子贡、子夏,但其先于孟子、荀子,是毫无问题的。”[4]492他甚至根据孔子七十弟子中有公孙龙其人,少孔子十三岁,推论此人就是《公孙尼子》的作者公孙尼,且谓“尼者泥之省,名尼字石,义正相应。”[4]491故在他看来,《礼记·乐记》与《荀子·乐论》的关系,是后者杂取于前者,而不是相反。钱穆仅据《缁衣》一篇中某些与《荀子》言论的相近来证明《乐记》抄袭《荀子》,且断言“公孙尼子殆荀子门人,李斯韩非之流亚”[8]573,的确过于牵强,缺乏足够的文献证据和说服力。据郭沫若“追记”,他在完成《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后,于友人处借得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查看有关《公孙尼子》一书的考述,在于9月8日写下一段文字中如此评价钱说:“仅据断残的资料与推臆而欲推翻旧说(案指《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的说法),勇则勇矣,所‘失’难保不比长孙无忌更‘远’了。”[4]505
《隋书·经籍志》所载刘向校书获得的《乐记》二十三篇,前十一篇的内容完整保存于今天所见的《礼记·乐记》中,后十二篇仅存篇目而缺内容。孔颖达《礼记正义·乐记》题解云:“按郑《目录》云: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9]1527这表明,取自《公孙尼子》的《乐记》,刘向所见的二十三篇,梁武帝时代的沈约尚能见其完帙,而至迟到唐代,已经亡佚后十二篇,只有前十一篇得以传世。对于存世《乐记》十一篇的文字内容,郭沫若又对刘向《别录》、《礼记·乐记》和《荀子·乐论》的次第差异与内容异同进行了比较,得出了如下判断性结论:“我认为今存《乐记》,也不一定全是公孙尼子的东西,由于汉儒的杂抄杂纂,已经把原文混乱了。但主要的文字仍采自《公孙尼子》。”[4]490这个判断包括两个方面的主要内涵,一是传世的《礼记·乐记》内容尽管不都是《公孙尼子》的原文,但后者的主要思想理论得以在其中保存了下来;二是传世的《礼记·乐记》经过了自战国中期直至汉代儒者的取舍增删,后世儒家关于“乐”的某些思想理论成分混杂在其中,研究公孙尼子的思想理论,需要进行甄别,把可疑的部分“剔开,才比较可以得到他的真相”。[4]490尽管这样做事实上已经很难,比如刘向所得的《乐论》二十三篇,是不是《公孙尼子》的全部内容,汉儒杂抄杂纂混乱原文达到什么程度,传世的《礼记·乐记》哪些思想理论是公孙尼子的“原版”货,哪些是“拼装”货等,这些问题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委实难以全部还原其真相。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充分肯定郭沫若严肃认真、努力接近历史真实的求实精神和研究态度。
二、公孙尼子的“乐”论及其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公孙尼子》一书的全部内容尽管已经难知其详,但该书主要是阐述关于“乐”的理论问题,则非常清楚。因此,后世研究者大都认为《公孙尼子》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音乐专著,公孙尼子则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之祖。“乐”本是儒家“六艺”之一,其初本意主要指音乐。《礼记·乐记第十九》:“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注云:“宫商角徵羽杂比曰音,单出曰声。”[9]1527说明“音”“声”是人心有感于物而形成的。同时,“乐”在中国古代又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包罗宽广的概念,郭沫若指出:“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岳),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岳)者,乐(洛)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岳)。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大约就因为音乐的享受足以代表艺术,而它的术数是最为严整的原故吧。”[4]492音乐在孔子那里就很受重视,其教育学生时有不少这方面的言论,把其地位提得很高。但几乎同时兴起的道、墨两家,要么反对享乐,要么否定音乐的积极作用,形成明显的理论分歧。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背景下,儒家传人需要系统阐释音乐与人性、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公孙尼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集中讨论“乐”,建立起儒家较为系统的“乐”论思想体系。郭沫若注意到,公孙尼子理论中的“乐”,依然是相当广泛的,“《乐记》中所论到的,除纯粹的音乐之外,也有歌有舞,有干戚羽旄,有缀兆俯仰。但大体上是以音乐为主,比以前一两辈人的笼统,是比较更分化了。”[4]496郭沫若已经看到,公孙尼子作为孔子的再传弟子,其对于“乐”的认识,既源于孔子,又比孔子及其弟子,更加注重阐述“乐”的理论属性和社会作用。
首先,明确“乐”的性质,阐明其与人性本质的关系,并由此建立起“乐”与人性在理论上的逻辑联系。《礼记·乐记第十九》:“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成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返躬,天理灭矣。”(这段话郭沫若引自《乐本》,认为是公孙尼子的观点。‘欲’作‘颂’,容也)[9]1529郭沫若指出:“这和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正一脉相通。”[4]491以上《礼记·乐记》的一段话,重在阐明人生之初,本无情欲好恶;但物来斯感,便会生出欲望喜好;假如不对人的欲望好恶进行适当调节控制,其本初的天性就会随物变化,改变其无欲而静的本性。故后文有“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云云的话。联系上文关于“声”“音”之所由起的论述,声音是人有感于物的必然心理活动,这种声音有了一定的抑扬起伏急速舒缓变化,就形成了人类最初的音乐。故《礼记·乐记》云:“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9]1527因为音乐是人的心声的反映,自然会表现人的好恶哀乐,不仅给表现者带来情欲的释放,使其在此过程中获得快乐或者忧伤的感情体验,而且使闻之者受到感染,在这种音乐活动中获得丰富的感情体验。由此看来,音乐既源于人心,又满足了人性的正常需要,这是音乐的本质属性。
郭沫若对公孙尼子“乐自性出”的观点作了如下分析评述。他说,不少学者(以黄东发、陈澧为代表)以为这是近世理学的渊源,“然而,宋儒的理学是把理与欲分而为二,而公孙尼子的原意却不是这样。他是以为好恶得其节就是理,不得其节就是灭理。所以他说:‘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顺说是真,反说便不真。宋儒却是反说:‘去人欲,存天理’。这是误解了公孙尼子。”[4]491-492对于郭沫若引述的《礼记·乐记》“物至而人化物”等语,孔颖达疏云:“外物来至而人化之于物,物善则人善,物恶则人恶,是人化物也。”“人既化物,逐而迁之,姿其情欲,故灭其天生清静之性,而穷极人所贪嗜也。”[9]1529郭沫若着重强调公孙尼子与宋代理学家在认识天理(性)、人欲(情)上的根本区别,既然公孙尼子坚持认为音乐出于人性,是人表达心情和欲望、寻求感官享受的正常需要,二者在人的生命中被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是人性与人生的基本属性与表现形态,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理论上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而宋代理学家恰恰将二者尖锐对立起来,主张必须通过“去人欲,存天理”的方式与过程,才能保证人性不受情欲的冲击与毁灭,宋儒之所以把人欲视为洪水猛兽,其道理即在于此。郭沫若认为公孙尼子所理解的“乐”的性质是“和谐”,其论述音乐与人性的关系是“顺说”,意在强调合理调节人的欲望,以不致“人化于物而灭理”为度,达成欲望与人性的和谐统一;宋儒认识和对待二者的关系,恰与之相反,认为必须去尽人的一切欲望,天理才得以保全,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这不符合自孔子以来古代儒家对“乐”的性质的基本认识和定义。
其次,阐明“乐”的功能与作用,确立其与儒家社会政治理论的内在关联。郭沫若认为,公孙尼子所认识的“乐”的基本功能是“同化”。并具体解释说:“所以你的声音是怎样的性质,在别人的感情上便可以起出怎样的波动,感情被声音的传达而生感染;同时,知音的人听见你有怎样的声音也就知道你有怎样的感想。”[4]497郭沫若认为,在《礼记·乐记》中,阐述“乐”的“同化”功能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一段话里: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9]1527
这段话主要蕴含以下三方面的内涵:一是明确“六心”非性,而是人“情”的不同表现形式。人之所以会有如此种种的情绪差别与多样变化,是因为心感于物,境遇不同,感受亦不同。二是阐明不同的内心世界,必然在其所发的“声”“音”中真实地表现出来,音乐是人的内在情绪的自然流露。三是证明音乐可以实现其“同化”人心的功能。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感,音乐便可以在人际间实现可以预期的艺术效果。所谓先王用“乐”这种艺术形式来实现“和”与“同”的社会治理效果,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论与实践原理。当然,礼、刑、政也可以实现“同化”的社会治理效果,其目的相同,殊途同归,但惟独音乐可以使人在获得愉悦享受过程中,达到和谐与同化的目的,发自内心而非外砾,潜移默化而非强制,这是其他三种形式不能取代的独特感化功能。故《礼记·乐记》云:“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唯乐不可以为伪。”孔颖达解释“唯乐不可以为伪”一语曰:“伪谓虚伪。若善事积于中则善声见于外也;若恶事积于中则恶声见于外。若心恶而望声之善,不可得也。”[10]1536
因此,“乐”与政治相通,由音乐之“音”可以了解政治的情态得失与社情民意。《礼记·乐记》云:“情动于中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9]1527“乐”与政治存在密切关联,在孔子的言论里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观点,如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1]171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2]142孔子判断天下有道无道,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就看礼乐征伐一类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如果礼乐、刑罚失效或者根本不用,那老百姓的行为就没有准绳可言了。古代儒家极端重视礼乐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在《礼记·乐记》中有不少论述。如言:“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9]1529郭沫若分析认为:“因此音乐又成为政治的龟鉴。为政的人当倾听民间的音乐,不仅可以知道民间的疾苦,也可以知道政治的良与不良,从这儿便可以生出政治的改革。”[4]499
基于“乐”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古代儒家自孔子开始,就注重从整体上设计出一套社会政治理论学说,以规范社会秩序和人的言行,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虽然许多观点和方法一直在调整变化,但基本的政治理念与体制框架,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比如礼、乐作为社会治理及处理人际关系的两大支柱,各彰其能,交互为用,二者不可或缺,这种思想观念无论是儒家学者,还是封建统治者,都始终奉行不悖。儒家这套社会政治理论能够维持中国封建制度长达数千年之久,居功至伟。《礼记·乐记》云: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9]1529
郭沫若对此作如下解读:“乐须得礼以为之节制,礼也须得乐以为之调和。礼是秩序,乐是和谐;礼是差别,乐是平等;礼是阿波罗(Apollo太阳神)精神,乐是狄奥尼索斯(Dionysos酒神)精神。两者看来是相反的东西,但两者调剂则可恰到好处。”[4]500治理天下虽然有礼、乐、政、刑各种方法,并且目标一致,但很明显,礼、乐更注重从人性的本质出发,发挥社会人的内在动力与主观能动性,达到个体自我约束、自我完善,人际调剂和谐、友好相处的目的。礼乐精神发挥到极致,儒家社会政治理想——大同世界也就实现了。故儒家主张齐家、治国、平天下,必始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即时此意。朱熹云:“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13]4前述《礼记·乐记》有“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之说。所以,音乐与社会个体的道德修为,及社会政治理想实现的途径,就这样被古代儒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再次,阐明“乐”的意义与价值,确立其与儒家世界观的一致性。《礼记·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和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相沿也。”甚至把礼乐推至与天地同在、与万物同源的高度,为之抹上无比神秘、神圣的浓郁色彩:“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9]1530郭沫若指出:“到这儿为止我们看到音乐的崇高性逐渐上升,作者的精神也逐渐亢扬,把音乐的赞美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很有点类似希腊皮它果拉斯派的宇宙观。”[4]502郭沫若所说的皮它果拉斯,今天通译毕达哥拉斯,他是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不仅因发明勾股定理而闻名于世,而且其提出的天体和谐理论对柏拉图等西方古代哲学家的宇宙观、美学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就是天体和谐有序运行所形成的音调与旋律,这种音乐被称为“天体音乐”。郭沫若说公孙尼子的宇宙观类似于毕达哥拉斯一派的宇宙观,应该是指此而言。
关于“乐”的意义与价值,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受到重视。如孔子感慨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4]178后世学者对孔子这番感慨的解读,普遍认为是孔子反对注重礼乐的外在形式,强调应该重视礼乐的根本精神与内在实质。孔子还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5]62既表明礼乐对于不仁的人没有任何作用,也表明礼乐对于人而言不可以斯须离,有如空气之于生命般重要。孔子之后,儒家传人对“乐”的意义与价值越来越看重,如《尚书·舜典》(郭沫若认为此篇及《尧典》均为孔子弟子子思伪托所作)有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与夺伦,神人以和。”[16]132把“乐”提升到人、神和谐的程度。《吕氏春秋·大乐》云:“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混混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17]642更把音乐上升到本体论的认识高度,它与天地同体、与万物同生,无所不在,无所不用。战国中后期的儒者,其关于音乐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不同程度地受到公孙尼子“乐”论思想的影响。故郭沫若说:“公孙尼子之后,凡谈音乐的似乎都没有人能跳出他的范围。”[4]503-504
三、郭沫若公孙尼子研究的特点与得失
郭沫若作为20世纪最早研究公孙尼子及其“乐”论的先行者,其贡献与影响甚大,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孙星群《〈乐记〉百年研究回顾》评价云:“郭沫若先生的《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开启了20世纪《乐记》研究的先河,对《乐记》作者、成书年代、认识论评定、学科定位、史籍整理、内容剖析与评价、《乐记》与《易传》《别录》《乐书》的比较、儒墨道的比较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20世纪的研究许多是围绕他的观点展开的,或赞成或诘难,因此是一部重要的影响后世的文论。”[18]其实,郭沫若对公孙尼子及其“乐”论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其把“乐”论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定位,并将其置于当时几大显学比较中评价其作用、意义与地位,既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又摆脱了一般人往往孤立地研究《乐论》并评说其短长的弊端,这无论从研究方法上还是从研究结论上看,都是最具学理性且最有说服力的。其显著的特点也在于此。
笔者对郭沫若上世纪40年代先秦诸子研究著作的出版情况作了统计,显示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形成于1940—1945年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19]而后两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是完全一致的,主要针对先秦诸子思想及学术流派开展研究,《十批判书》是按照研究计划在1943年7月至1945年1月之间共计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的,而《青铜时代》的研究论文,除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周易〉之制作年代》作于30年代中期之外,其他也是在1942—1945年初写成的。应该说,从郭沫若上世纪20年代后期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到40年代中期完成上述两书的写作,其在约20年中对先秦社会及意识形态的关注及研究,占有的资料非常充分,用他自己的话说:“秦汉以前的资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勦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1]468以郭沫若自幼奠定的旧学基础,加上20年间对先秦资料的系统涉猎,再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与多学科融合贯通,其准备之充分、耕耘之勤劳、探究之彻底,的确为一般人所不能及。
郭沫若对于公孙尼子及其思想理论的研究,虽然用了《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的题目,但其切入的角度与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后世严格学科分类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音乐”概念,今天的许多音乐理论研究者,往往站在现代音乐学科研究的立场,去看待和评价郭沫若的公孙尼子及其音乐理论研究,虽然给予的评价已经很高,但并没有准确把握郭沫若研究的初衷及其最突出特点。为了证明这一点,郭沫若有一段话可资佐证,他说:“音乐,我曾经写过一篇《隋代音乐家万宝常》,虽是属于后代的事,但其中也涉历到了古代。古代的音乐,我感觉着我们所固有的东西非常简单。卜辞及金文中所见到的乐器,只有钟、鼓、磬、籥等类。音阶在古只有宫、商、角、徵、羽的五音,其起源还不知道。琴瑟是西周末年由国外传来的新乐器,三《颂》中祭神乐器无琴瑟,《风》《雅》中虽见琴瑟的使用,而是用于燕乐男女之私,足见这类传统不古,没有资格供奉家庙鬼神,也就如一直到今天二胡琵琶还不能进文庙一样。十二律也是春秋时代由国外输入的,有了它的输入才使五音或七音成为了相对的音符。”[1]487-488而在其所提及的《隋代音乐家万宝常》一文里,专门论及古代的“乐制乐论”,却只字未提公孙尼子的“乐”论思想,只介绍了十二律、五音的发展演变问题。[20]144可见,郭沫若当时对公孙尼子与其“乐”论所产生的“兴趣”,完全不在狭义的“音乐”本身,而是其作为先秦儒家社会政治学说组成部分的意涵及其与墨家、道家思想观念的分歧,包括上述的公孙尼子“乐”论的性质、功能与作用、意义与价值等思想理论范畴的问题。
明白于此,郭沫若以下的话语就容易理解了:
人有感官自不能不图享受,故“乐”之现象实是与人类而俱来。然自人类进化到有贵族和奴隶的阶段,则一切享受均不能平均。高度化的享受为上层所垄断,低级者留之于下层,甚至连低级者有时亦无法享有。故尔到社会达到量一阶段的时候,对于这享受的分配便不免有新见出现。
殷周是奴隶制时代,上层的贵族早就有钟鼓磬琴瑟笙等等相当高度的音乐及其它感官的享受,但作为奴隶的人民却和他们有天渊之隔。因此在春秋战国当时,奴隶制逐渐解体的时候,思想家对于这享受的不平衡便有了改革的反应了。[4]492-493
显然,郭沫若关注的重点是音乐带来的享受在春秋战国时代不平均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问题,由于音乐与享受都是与生俱来的人性需要,所以会因此形成激烈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成为加快社会结构解体和阶级分化的重要诱因之一,当时几大显学儒、墨、道都高度关注这一现象,并提出各自的理论观点,形成思想纷争的焦点之一,根本原因即在于此。所以,郭沫若所说“儒、墨之间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音乐”,指的并非音乐本身的技术层面,而是如何看待“乐”的社会作用、意义与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郭沫若对公孙尼子及其“乐”论的研究,横向看将其放在儒、墨、道诸家的对比分析上,纵向看放在儒家自创始人孔子到先秦儒家思想集大成者荀子“乐”论的传承发展上,在这个坐标点上去确定公孙尼子的“乐”论思想价值与地位,其科学性、严谨性与可靠性,构成《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的鲜明特征,除了得到多数学者高度认同的学术理论价值外,其研究方法的先进性,也非常值得今天的学人借鉴。
一分为二地看,郭沫若关于公孙尼子与其“乐”论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毋庸讳言的不足。首先是其使用的“音乐”概念不够严谨。无论是郭沫若还是今天的研究者都同样清楚,先秦时代人们所说的“乐”,跟现代人所理解的“音乐”,其概念的大小差异是不言而喻的。虽然郭沫若在文中对中国古代的“乐”所包罗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罗列,并且强调音乐只是其代表,因为这种艺术最能使人快乐,感官得到享受,但如其题目所示“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容易给人造成公孙尼子关于“乐”的思想理论就只是有关音乐理论问题的错觉。20世纪以来很多研究者都从音乐学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公孙尼子及其“乐”论,就是这种错觉导致的结果和具体表现。实际上,无论是公孙尼子本人的“乐”论,还是郭沫若所关注和揭示的公孙尼子“乐”论意涵,都不局限于音乐本身,甚至也不是今天音乐专业人士所常说的音乐学科性理论问题。郭沫若自己用了不少篇幅论述公孙尼子“乐”论中关于礼、乐并用,充分发挥其人伦教化与社会治理作用的思想观念,努力证明公孙尼子关于“乐”的思想内涵,是“乐”的产生、性质、功能、价值、地位等哲学思想命题。也许用“公孙尼子与其‘乐’论”的题目,可能更加契合郭沫若论文重点表达的思想内容,能够避免其题目与内容间的自相矛盾和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必要误解。
其次是对于使用资料的甄别不够清楚。郭沫若自己说过,研究先秦诸子,最大的困难在于资料真伪的甄别与使用。他在对公孙尼子及其著述进行考证的过程中,采信《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沈约《奏答》等支撑性与说服力较强的资料来证明《公孙尼子》文字内容的存佚与传承情况,这种文献研究方法是科学合理的,今天的学者赞同其研究结论,主要建基于此。但郭沫若提出:“我认为今存《乐记》,也不一定全是公孙尼子的东西,由于汉儒的杂抄杂纂,已经把原文混乱了。……我们要论公孙尼子,就应该把这些可疑的来剔开,才比较可以得到他的真相。”[4]490为此,他专门列表比较了《别录》《礼记》《乐书》有关《公孙尼子》篇目次第的差异,但并未得出哪种文献保存《公孙尼子》原文内容最多且最可靠的结论。在引用资料时,除了《史记·乐书》的一条外,其它几乎全部引自《礼记·乐记》上中下三篇中的上篇,只有一条标明来自《乐本篇》,其他则未加说明。相关引文来自《公孙尼子》的哪些篇章,《礼记·乐记》是否只是上篇保存了《公孙尼子》的原有内容,依据是什么,读者并不清楚。其不引《礼记·乐记》下篇(中篇引用一条),是否表明属于郭沫若“剔开”的文字,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作者并无交代。这样,郭沫若提出要甄别汉儒“混乱”《公孙尼子》原文、想获得其真相的目标,难说得到了很好实现。也许郭沫若确实想解决这一重要问题,无奈文献亡佚严重,资料相当匮乏,导致博学多才的郭沫若也无力完成其预定的研究目标。
再次是个别观点不够审慎。关于公孙尼子其人,究竟是战国初的孔子嫡传弟子、再传弟子还是战国后期的荀门弟子,郭沫若与钱穆观点不一样。从所据的资料及论证的方式看,郭沫若的说法比钱穆更有说服力。但在对公孙尼子身份及其与孔子关系的考察上,郭沫若的观点依然存在明显瑕疵。他比较《汉书·艺文志》说公孙尼子是孔子七十子之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的记载,由此提出公孙龙就是公孙尼的观点,且说:“龙是字误,因有后来的公孙龙,故联想而致误。尼者泥之省,名尼字石,义正相应。子石,《集解》引‘郑玄曰楚人’,《家语》作‘公孙龙,卫人’,那是王肃的自我作古。”[4]491案《史记索隐》:“《家语》或作‘宠’,又云‘砻’,《七十子图》非‘砻’也。按:字子石,则‘砻’或非谬。郑玄云楚人,《家语》卫人。然《庄子》所云‘坚白之谈’者,其人也。”[21]2219《史记》列入孔子弟子的公孙龙,“龙”字在《家语》中作“宠”或“砻”,但没有任何史料显示有作“尼”的,要说“尼”与“石”义相应,那《史记索隐》说“砻”与“石”也算其义相应。“尼”为什么会是“泥”之省,“龙”为什么又误作“尼”,王肃注《孔子家语》何以自我作古把“龙”误作“宠”或“砻”,这些疑问郭沫若并未给出任何文献资料证据或合理性解释。郭沫若既然清楚《汉书·艺文志》明说公孙尼是七十子之弟子,即孔子的再传弟子,却又要强说此人是孔子的嫡传弟子,观点有些想当然的“大胆”,难免误导后学,直至今天还有人信其说而踵事增华者[22],显得不够审慎谨严。
(责任编辑:廖久明)
[1]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M].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一[M].隋书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M].汉书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郭沫若.青铜时代·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A].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三[M].隋书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唐魏征等.隋书·音乐志上[M].隋书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
[7]邹华.郭店楚简与《乐记》[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诸子攟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论语·季氏[M].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论语·子路[M].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论语·阳货[M].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论语·八佾[M].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M].二十二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8]孙星群.《乐记》百年研究回顾[J].中国音乐,2000(4).
[19]杨胜宽.郭沫若学术研究的“疑”与“通”——兼论郭沫若学术精神与蜀学精神的一致性[J].西华大学学报,2014(4).
[20]郭沫若.历史人物·隋代音乐家万宝常[A].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1]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2]田君.公孙尼子与《乐记》新考[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9(3).
中国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符:A1003-7225(2016)03-0041-08
2016-07-02
杨胜宽,男,乐山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