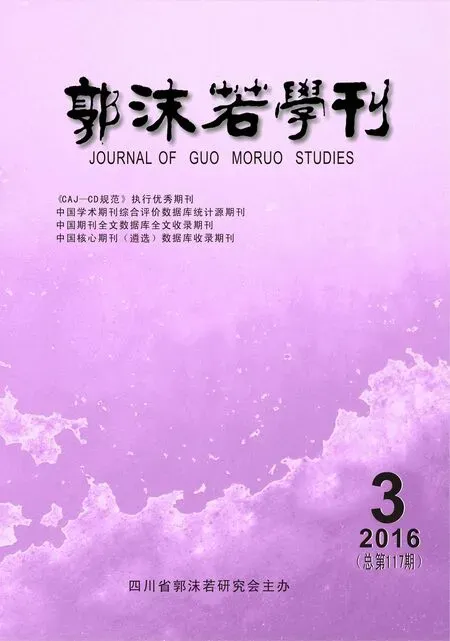郭沫若“孤山去看梅花”考实(外一题)
陶霞
郭沫若“孤山去看梅花”考实(外一题)
陶霞
北京刘勉已在自己编辑的《晨报副刊》1925年2月28日第四版发表了郭沫若半月前自上海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前天跑往西湖去过一次来,因为有朋友相约同往孤山去看梅花。但是今年天气太冷了,孤山的梅花现在还没有开呢。在西湖跑了两天回来……”
上录《晨报副刊》发表的是一封私人“通讯”,应该没有虚构,郭沫若信中写及的自己的行踪可以作为史实载入其生平类记实著述如年谱等书中。郭沫若写信的时间,是自杭州返回上海的1925年2月13日,“前天”便是2月11日。“在西湖跑了两天回来”,这“两天”是12日、13日两天,写信时间是郭沫若返回上海寓所后的当天夜间,这符合34岁的诗人的作派。
之所以这样推算,是因为郭沫若为他1926年1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戏剧集《塔》写的无题自序后的时间有“1935年2月11日夜书此”的明确记载。也就是说,郭沫若在上海寓所编完《塔》、写好短序,便立即坐夜间火车应“朋友相约”前往杭州。了结了一桩文字业务,出外散散心,也是常见的文人习性,郭沫若也不例外。依郭沫若的气质,在上海编完《塔》,当天就赶往杭州,在杭州住处写下短序,也是有可能的。但无题短序后没有“于杭州”之类的字样,就只能作又一种推算了。
郭沫若去杭州西湖,与之“相约”的“朋友”是谁?他在上引写给刘勉已的信中有一句可作为线索来查考:“在西湖有友人汪静之兄交来《李太白及其诗》一篇,明天当邮寄上,以备采择。”
早在1922年3月杭州已有由几个20岁左右的青年以歌咏爱情和自然为职志的诗社“湖畔诗社”,郭沫若信中说的代为转《李太白及其诗》稿的作者“汪静之兄”就是湖畔诗社的重要成员之一,另外几个重要成员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等。在此之前,这个湖畔诗社已于1922年的4月、8月和次年的12月出版了诗集《湖畔》、《蕙的风》和《春的歌集》,就在郭沫若赴西湖“探梅”这一个月,湖畔诗社筹办的后来共出了四期的诗刊《支那二月》第一期即将问世。
与郭沫若致刘勉已信中所述在杭州见过汪静之完全一致,汪静之在稍后的一封书信中也有提及。这就是1925年2月25日汪静之写给已结婚一年多的妻子符竹因的信,该信收在由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飞白编《汪静之情书漪漪讯》一书中。在这封信中,汪静之写道:“我今天又到沫若处去玩来。他问我他在西湖时第二天你没有去同游,你是不是生气了;我已把你解说过了。”
汪静之此次是到保定就任中学国文教员,路过上海借便“到沫若处去玩来”的。那个“又”字也是实情,前一天即24日的去郭宅在这信中也有写及:“昨晚和修人同到沫若家中去,沫若同他的安娜一同做厨子,忙着弄菜做饭给我们吃,吃了一种日本做法的菜。直谈到十点钟才回来……”这里的“修人”即湖畔诗社年龄最长也才仅25岁的应修人,供职于上海福源钱庄做账房工作,工余酷爱新诗,《支那二月》即由他主事。
从汪静之致符竹因的信中,确知郭沫若“有朋友相约同往孤山看梅花”的“朋友”,或许就是汪静之夫妇。汪静之1924年在武汉一所中学担任国文教员,次年又转任保定一所中学国文教员,旧历年底前后返杭州与妻等家人共度春节。传统的正月十五过后邀约长自己十多岁的郭沫若光临杭州西湖并去孤山看梅花,陪了家人再与友人欢聚,也在情理之中。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当地的习俗也是正月十五前主要与家人和亲戚共度,正月十五后再邀友人欢聚。
从汪静之写给符竹因的信中,确切地知道郭沫若在杭州西湖头一天是由汪静之夫妇陪同的。另从汪静之1925年2月26日致符竹因的信中得知,这一回郭沫若与汪静之夫妇杭州的相聚,郭沫若《孤山的梅花》第六节中那位在杭州东坡路开设医院的“友人”没有来。汪静之在信中向符竹因报告他离沪的这天即26日上午等船离岸时,前来送行的郭沫若向他讲:“说杭州医生钱君胥最好,须要他看了才的确。我就叫他介绍,他说回去就写信,信寄你由你转与德桢,叫伊持信到旗下东坡路钱氏医院去看,他当要看得仔细些。沫说看肺病胸前要解开,叫伊不要顾忌。钱君是日本留学生,沫若很佩服他的医学。”信中“德桢”是符竹因的朋友,患有肺病,据郭沫若对汪静之讲,肯定要死去。由这一番话,证明郭沫若游杭州时钱君胥不在场。
上引汪静之信中“沫若很佩服他的医学”的钱君胥即钱潮,曾与郭沫若合译德国作家Theoder Storm的《茵梦湖》(钱君胥自德文译出,郭沫若改译润色)。钱君胥,是郭沫若留学日本去学医时的同学。
郭沫若《孤山的梅花》两次虚构
郭沫若在文末佯称“追记”的《孤山的梅花》,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写实散文。如果三十三四岁的郭沫若在月和日这个写作时间问题上没有“捣鬼”,这篇《孤山的梅花》完成于1925年3月18日。在致刘勉已的信中,郭沫若明确地表示他去杭州因为“今年天气太冷了,孤山的梅花现在还没有开呢”,确指1925年2月12日和其前或其后两天的实况。向《晨报副刊》编辑刘勉已预告了“兴会来时,或可作孤山探梅记呈教”,郭沫若就不敢怠慢了,在“兴会”一旦“光顾”时便“追记”出一篇分为六节再加一个尾声的《孤山的梅花》,有八千字,要算不短的篇幅了。
刘勉已也紧追郭沫若不放,很快就来信索要“孤山探梅记”的文章。1925年3月28日郭沫若收到刘勉已的索稿信时,他的八千字长文《孤山的梅花》已于十天前的3月18日完工,便将自以为“不甚满意”的“早已草就”的文稿“付邮”,还兴致很高地写了近千字的复信。郭沫若这两封书信,都被刘勉已公开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郭沫若《孤山的梅花》除1925年4月上旬分三次于3日、4日和7日在北京《晨报副刊》的发表文本外,1958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沫若文集》第七卷作为“集外”一辑五篇之一收入的文本,据该书卷首说明,是“经过作者修订”的又一个文本。郭沫若去世后于1985年9月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七卷“其他”一辑所收《孤山的梅花》是《沫若文集》第七卷的照排,所谓“有重大改动处加注或附录”编注范例没有体现于该文,因为《孤山的梅花》一篇经核校有“重大改动”,相对于真实的“孤山的梅花”,是又一次虚构。下面对两次虚构的主体内容,试作梳理。
《晨报副刊》发表文本《孤山的梅花》,是郭沫若对“孤山探梅”的第一次虚构,虚构的底本就是他一个多月前的这次“跑往西湖去过一次来”的经历,只不过虚构得面目全非罢了。作品的主人公自然是“我”,但这个“我”在作品尾声“抱节做的”长达30行诗的《西湖——Florence》中又明确地三次写着“啊,沫若”,虚构中又自认是真实的作者本人。这首诗中写着邀请我到西湖去的“余猗筠小姐”或曰“余抱节”这个狂热地爱上“沫若”的年轻女人,从这第一次虚构文本中得知她是一个晚期肺病患者,她在西湖与“沫若”白天攀援宝石山,夜游白云庵,而且还有“钱塘旅社之两眠”。虽然这两个夜晚二人是分睡两张床,但被“沫若”迷倒了的“余猗筠小姐”或曰“余抱节”几乎对“沫若”崇拜得五体投地——有了与“沫若”同游,“杭州之西湖,真的成了南欧当年的Florence了”;“沫若”喝醉了的“发光的面庞以及和衣睡倒”在床上的“率真”,“我愈看愈觉得和Shelley一样……”,作为崇拜“沫若”的“我”即“余猗筠小姐”或曰“余抱节”,自比Keats,被全文抄录的三十行诗最后四行是:
啊,沫若呀!
听说Keats后来就死在Shelley住过的那个房间里的,
你如今走了,
我不久恐怕也要死了。
引用过“抱节做的”30行整首诗,全文作为尾声最末一段为:“这首诗是很真挚而且哀婉的,没有些儿矜持,也没有些儿随意,这和荠次的诗倒真差不多,不过要比我为雪莱,我实在有几分惭愧了。这诗不消说就是抱节做的,不过这抱节是不是猗筠小姐,我想聪明的读者用不着我来点破了吧。”
除了“抱节做的”诗中明写“沫若”与她在钱塘旅社“住了两夜”,郭沫若在抄录全诗之前也有“我在杭州只住了两天,我是二十二的清晨,乘早车回上海的”。“抱节做的”诗《西湖——Florence》,是郭沫若“回上海不久”从杭州寄来的。
郭沫若对二十二三年前的旧作《孤山的梅花》上述最主要的情节的第二次虚构,是为《沫若文集》第七卷所收此文进行的改动。这改动倒也爽快,即全部删掉《晨报副刊》上第六节后用三个圆圈表明的尾声,即含有“抱节做的”三十一行诗《西湖——Florence》和诗前诗后的全部文字,重写近两百字作为第六节最后的四个自然段:
看样子,这也不像是小姐能住的旅馆了。
我问是不是有位余抱节先生来住过,柜上回来说没有。柜上是有电话的,我便打电话到某某女学校去,也说并没有“余猗筠小姐”这个人。有趣,真是有趣。
孤山的梅花呢?还要等两三天才能开。这怎么办?
东坡路上的朋友也不好再去找他了。我折回车站,赶上了当天开往上海的晚车。
1958年8月印行的《沫若文集》第七卷所收《孤山的梅花》的“修订”是从头至尾的,第四节写“我”去不去西湖的犹豫不决的心理活动改得很多,几乎每一处重要的词句都有重新改写,目的是为了重新塑造“我”的形象。好在最初刊载《孤山的梅花》的《晨报副刊》早在1981年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不难见到,本文就不予以论及了。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讯息·书讯
《岷峨诗侣》线装本,以“人自为卷,以齿为序,分缪钺、黄穉荃、马识途、李维佳、何郝炬、刘少平、张榕、曾渊如、文伯伦、滕伟明、周啸天、郭定乾,共十二卷”2016年2月分两函出版,扬州文津阁古籍印务公司印刷、巴蜀书社出版发行,定价捌佰伍拾伍元。
《中国抗战文化编年》文天行编著,2015年6月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定价60.00元。
《抗战文化运动史》,四川抗战文化研究丛书之一,文天行著,2015年9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定价65.00元
黄侯兴先生著《郭沫若与孔孟之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该著全面评述了郭沫若的先秦儒家文化史观。黄先生认为,郭沫若是一位明显尊孔的并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但他的尊孔,呈现出一种波浪式的起伏,即尊孔,批孔,再尊孔。为何会出现这种起伏的现象,正是今天仍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鉴于此,《郭沫若与孔孟之道》对郭沫若的先秦儒家文化史观做了深入的研究,且见解独到。
(魏红珊)
(责任编辑:王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