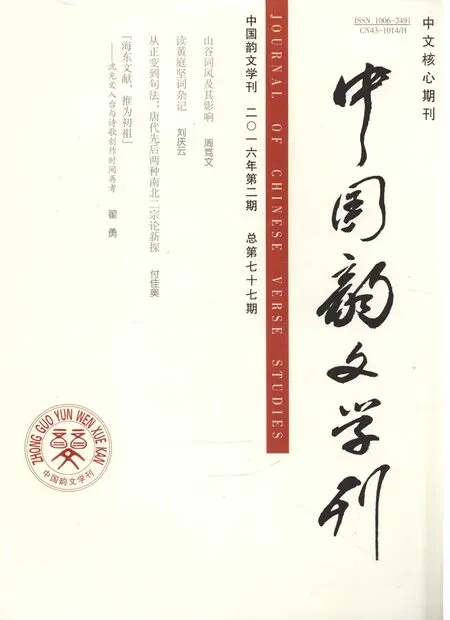张衡《二京赋》的风俗世态书写及其审美趣味
杨朝蕾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张衡《二京赋》的风俗世态书写及其审美趣味
杨朝蕾*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摘要东汉张衡在《二京赋》中对京都风俗世态进行生动摹写,表现出其独具特色的审美趣味。这种趣味在赋中并未直接呈现,而是通过作者的批判式言说间接表现出来,即将感性的审美趣味渗透于理性认识中。其根本原因在于赋家非依赋作而腾达,在与政治权力的适度疏离中,保持人格之独立,使作品成为个人思想自由驰骋的场域,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化审美倾向。
关键词张衡;二京赋;风俗世态;审美趣味
东汉张衡的《二京赋》被誉为京都大赋之“极轨”,其内容宏富、场景壮美、语言腴劲、议论犀利,全面展示了汉代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与多元文化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张衡视角向下的平民意识与对市井文化生活的关注,使《二京赋》具有鲜明的特色。诚如陈庆元先生所言:“班固的《两都赋》,由宫廷而扩大到京都。张衡的《二京赋》,则又由京都的上层生活转而关注市井文化生活的层面。……这是汉大赋由宫廷转向京都之后第一次关注市井的文化生活,给大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气息。”[1](P178)张衡在《二都赋》中对京都风俗世态进行生动摹写,表现出其独具特色的世俗化审美趣味。这种趣味在赋中并未直接呈现,而是通过作者批判式言说间接表现出来,即将感性的审美趣味渗透于理性认识中。这可能出乎作者意料,其对京都风俗世态的感知并未服从于其“极陈汰侈以归于讽谏”[2](P185)之意图,赋家意识到的,未必是其艺术趣味的最真诚表白,而其未意识到的,却往往是其审美情趣最天真的流露。
一异彩纷呈的风俗世态书写
(一)对社会众生相的传神写照
与班固《两都赋》不同,张衡《二京赋》中除了对西京长安、东京洛阳的山川形胜进行具体描摹外,更引人注意的是其对社会众生相的传神写照。举凡皇帝、后妃、宫女、将士、猎手、艺人、商贾、游侠、辩士,无不信手勾勒,栩栩如生,共同构成一幅汉代的社会生活长卷。
《二京赋》大约完成于殇帝至安帝初年间[1](P175),距东汉建立已有80多年,其时吏治腐败,外戚擅权,社会逸乐成风,儒家思想的禁锢有所松动,张衡也就拥有相对自由的写作空间。赋家通过对君主及宫廷生活之内幕的透视,剥去笼罩在帝王头上的“天命”光环,使其一改以往赋家所歌颂的神圣威严、德行兼美形象,还原其愚昧、贪婪、奢靡、好色之本质,深刻揭露宫廷繁华表象下的腐朽与龌龊。在铺叙宫室的富丽堂皇后,指出:“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虽斯宇之既坦,心犹凭而未抒。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3](P37),将其贪得无厌、穷奢极欲的心理入木三分地揭露出来。其讽刺武帝好神仙、求长生而“采少君之端信,庶栾大之贞固。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3](P45),“端信”“贞固”皆微词,之后反言质疑,“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3](P45),将笼罩在武帝头上的神圣光环抹去,无情揶揄其求仙炼药、荒于朝政的可笑可悲可怜心态。作为离宫之最的建章宫,为武帝所营,在述及其营建之因时,《西京赋》言“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用厌火祥”[3](P39)。《汉书·武帝纪》载:“(太初元年)二月,起建章宫。”注引文颖曰:“越巫名勇,谓帝曰越国有火灾即复大起宫室以压胜之,故帝作建章宫。”[4](P199)可见武帝营构建章宫不过是顺越巫之言,以压制火灾,其愚昧无知之形象栩栩于笔下,颇含嘲讽之意。在进行大张旗鼓的畋猎描写后,带叙后宫嬖人“慕贾氏之如皋,乐《北风》之同车”[3](P68),《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5],至此始明武帝“千乘雷动,万骑龙趋”的畋猎不过是为博后宫佳人之一笑,正可谓禽荒色荒,往往相因,欲抑先扬,前后比照,嘲讽意味尤浓。在对穷奢极侈的酒色歌舞进行浓墨重彩的描摹后,张衡指出,“鉴戒《唐》诗,他人是愉”[3](P85)。《诗经·唐风·山有枢》:“子有衣裳,弗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6],讽刺晋僖公不能及时以自娱乐,终使他人受益。张衡借用此典故,剖析帝王今日不恣意行乐而会使他人受益的心理,深刻讽刺其奢侈淫靡的行为。
对后妃与男宠的竞争邪媚、以求荣爱亦以寥寥数笔而再现其神貌,“卫后兴于鬒发,飞燕宠于体轻”[3](P85),卫子夫因鬒发如云而获宠,赵飞燕因体轻善舞而封后,从侧面讽刺皇帝的荒淫好色。成帝不仅沉溺女色,亦迷恋男宠,“许赵氏以无上,思致董于有虞”,《汉书·外戚传》载,成帝谓赵昭仪曰:“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4](P3993),许赵氏天下无出其上者,以保证其专宠地位。《汉书·董贤传》载:“后上置酒麒麟殿,贤父子亲属宴饮,王闳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4](P3738)对男宠董贤竟要效法尧舜禅让,予之帝位,更是荒唐之至。以上诸端,无不显示出张衡对帝王宫廷生活的嘲讽,因其非朝廷要员,自然无所畏惮,所言虽为西京,却又处处给当世帝王以警醒。
较之班固《西都赋》“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的类型化概述,张衡则将更多目光投向市井,以其如椽巨笔揭示出“瑰货方至,鸟集鳞萃”的市肆繁荣下所隐藏的种种矛盾与危机。《汉书·地理志下》载:“汉兴,立都长安……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4](P1642)《淮南子·要略》指出:“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7]《西京赋》对此亦有表现,曰:“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何必暋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3](P50)深刻揭露长安商人弄虚作假、欺伪下士的恶行,语言平易和雅,心中鄙视嘲讽之情以反语出之,更具杀伤力。此处所言虽为西京,实则暗讽东京,范晔《后汉书·和帝纪》载“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8](P186),可见东汉不法奸商巧诈欺市之行径实与西汉相类。若非来自底层的生存现场,又怎能对商贾鬻良杂苦、以假代真之伎俩洞悉无疑?此非俯瞰众生之怜悯,而是代众生在控诉,因为赋家本身即为众生之一员,未尝不深受其害。
西京之尚游侠,亦地气使之然。班固《西都赋》称:“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9](P4),只对其进行概括式、类型化叙述。张衡《西京赋》则进行典型化描摹,“都邑游侠,张、赵之伦,齐志无忌,拟迹田文。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实藩有徒,其从如云。茂陵之原,阳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眦虿芥,尸僵路隅”[3](P52),《汉书·王尊传》载:“长安宿豪大滑东市贾万、城西万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4](P3234),茂陵原涉,“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忍好杀,睚眦于尘中,触死者甚多”[4](P3718),阳陵朱安世等皆为长安游狭中颇具代表性人物。张衡以寥寥数笔将其势力张扬、随从众多、强悍勇猛、好斗嗜杀的特点再现纸上。其实,张衡明写西汉之游侠,实则暗讽东汉豪族豢养爪牙,图谋篡逆。东汉豪族以窦氏为雄,其家族势力十分显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8](P908)。窦宪作为窦太后之兄长,和帝时以外戚专权,官至大将军,其骄横放纵,威震海内,袁弘《后汉纪》载:“是时窦氏骄横,威震海内,其所置树,皆名都大郡,乘势赋敛,争相赂遗,州郡望风,天下骚动,竞侵凌小民,掠夺财物,攻亭殴吏,略人妇女,暴虐日甚,百姓苦之。又擅檄缘边郡突骑善射有财力者,二千石畏威不敢不送。”[10](P259)窦宪爪牙心腹众多,“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其“奴客”仗势欺人,强夺财物,欺凌妇女。后来窦氏居然图谋篡弑,终被逼死。
(二)对民俗风情的生动摹写
张衡深于《周礼》之学,《二京赋》中大量征引《周礼》之语。《周礼·天官·大宰》:“以八则治都鄙……六曰礼俗,以驭其民”,强调以礼俗来驭民。张衡亦甚重视民俗,只要契合礼仪,在《二京赋》中对汉代民俗风情有生动叙写。
汉代乐舞百戏风气盛行,《汉书·西域传赞》载,孝武之世,“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4](P3928)由出土的画像石亦可略窥其一斑。山东诸城市前凉台村墓髡刑、乐舞百戏画像[11](图版104),既有吹箫、吹埙、击鼓、击铙等乐器演奏,亦有伴唱、舞蹈,还有飞剑掷丸、倒立、杂耍、叠案等表演。河南南阳出土的画像石[12](图版109)则表现汉代的象人之戏,其上有四人,其中三人分别鼓瑟、吹埙、击鼓,组成乐队,另一象人戴面具,两臂上举,下肢半蹲,扮成熊罴状。山东沂南出土的墓壁画像[11](图版203)内容更为丰富,除了艺人起舞、飞剑掷丸、顶橦悬竿等杂技表演外,还有龙戏、鱼戏、豹戏和雀戏等。《盐铁论·散不足》称:“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玩好无用之器。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锑追人,奇虫胡妲”[13](P349),亦表明其时民间盛行玩物制作与百戏杂耍的风俗。
在张衡生活的东汉,乐舞百戏仍甚盛行。与其同时而年辈略长的李尤在其《平乐观赋》[14](P1134)对当时“百戏”的演出情景有精彩的描述。西京实质上是东汉社会奢华风气的投影,如赵逵夫先生所言:“在一定程度说,《西京赋》是对《东京赋》的补充;其中所写西京,实为东京的影子。”[15]《南齐书·乐志》载:“角抵、像形、杂伎,历代相承有也。其增损源起,事不可详,大略汉世张衡《西京赋》是其始也。”[16](P195)《西京赋》中尤为人称道的杂戏技乐一段,写得有声有色。既写了扛鼎、寻橦、燕濯、跳丸剑、走索上等杂技,又写吞刀吐火、画地成川等幻术。更精彩的是融歌舞、杂技、幻术于一体的大型戏法“总会仙倡”与巍巍壮观的伪作假形为戏的“鱼龙曼延”:“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海鳞变而成龙,状婉婉以昷昷。舍利飏飏,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3](P78)。这一惊心动魄的幻术场景作为世俗娱乐而登大雅之堂。明代胡广《胡文穆杂著·序戏》云:“大抵此戏本于巴俞,都卢、寻橦、蔓延,其来远矣。所未之见者,以今之伎不能古也。一戏尚然,而况与其它乎?先儒谓太史公叙庞涓马陵事,委曲详尽,观平子之赋,序事亦去曲折周至,可见古人为文章笔力妙处”[17]。可见此戏法在明代前已失传,《西京赋》如实反映了汉代“百戏”演出的生动情景,成为我国古代“百戏”的珍贵史料。若非亲眼目睹,焉能描述得如此详备。尽管此处是作为对君主“取乐今日,遑恤我后”、心奢体忲、贪图享乐的讥讽与批判,实则在对杂戏进行的生动形象的刻画中,表现了张衡对民间游艺娱乐的热衷与喜爱。《潜夫论·浮侈》载:“今民……或以游敖博弈为事;或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排,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18](P123)。东汉民间游艺娱乐之风如此盛行,生活于其间的张衡有意无意中受此影响,亦为自然之事。
为了体现东京的法度之美,《东京赋》着重描绘朝政礼仪,但岁末驱傩一段,充分表现了汉代宫廷傩仪大典的隆重盛大。傩源自远古,形成于商,至汉而盛。现存汉代画像石对傩仪、傩祭、傩戏及傩面具均有表现,与《东京赋》相互参阅,更有助于深入了解汉代的傩文化。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以逐恶鬼于禁中……乘舆御前殿……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櫑、苇茭毕,执事陛者罢。”[8](P3128)《东京赋》正描绘了这一情景:“尔乃卒岁大傩,殴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瘅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3](P148)此乃傩仪的第一环节,驱鬼。赤帻皂衣的童男童女们,手执桃弧棘矢,在“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周礼·夏官·相氏》)的方相氏的带领下,将群鬼驱诸四裔。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方相氏驱鬼辟邪画[19](P174)表现的正是头戴面具、手执法器的方相氏与怪兽搏斗的情景。山东沂南汉墓则出土了十二神兽大傩逐凶图[11](图版188),更详尽地表现了十二兽驱逐群鬼的雄壮场面。傩仪的第二环节是吓鬼,“然后凌天池,绝飞梁,捎魑魅,斫獝狂,斩蜲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慑,况鬾蜮与毕方。”[3](P148)写了对不同鬼所采用的不同的消灭方法,并威胁鬼疫,八灵之神已为傩仪所震慑,何况是弱小衰老的鬼魅。第三环节是防鬼,在将恶鬼驱除后,为防备再来作祟,使性能执鬼的神荼、郁垒二神,持以苇索,执遗余之鬼,使无复疫厉,皆得安善。
《东京赋》写的虽为汉代宫廷傩仪,但上行下效,由此可见傩文化在汉代已成为民俗风情的重要内容。傩仪表层目的是驱鬼除疫,祈福免灾,实则是基于万物有灵的观念,通过仪式沟通人、神、鬼,使阴阳调和、天人谐协,建立起天地人合一的宇宙图式。
毋庸讳言,《二京赋》创作之本意在于提纯朝政典礼,而贬抑民俗事象,对民俗风情的描写不过为了突出东京的礼治文明。尽管如此,《二京赋》对民俗的贬抑恰恰反映了其时人的正常生活状态,生动再现了盛世京都的民俗风情,而对朝政礼仪典雅肃穆场面的描写,表达的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诉求,而非真实的社会状况。
二审美趣味的世俗化倾向
(一)好奇猎异的审美趣味
好奇猎异乃人之天性,对怪奇事物的审美认同是人类自我认识与自我理解的具体体现,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如桓谭奏疏所言,“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8](P959)。汉代人尤好奇谈虚语,《论衡·对作篇》指出:“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20](P1179)在整个社会皆以闻奇言为乐,览虚言为美的氛围中,赋家难免受此影响,“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18](P19)。加之赋体本身有尚奇倾向,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赋概》所言,“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如此方可适应了人们求奇探异的心理。张衡“好学博古,贯综谟籍”“学为人英,文为辞宗”[21](P719),对奇闻异事的浓厚兴趣,使其在《二京赋》中大量征引神话传说、民间轶事与宫廷秘闻,表现出尚奇、猎异、好怪的审美倾向。车永《答陆士龙书》称:“足下此书,足为典诰,虽《山海经》《异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复过也。”[21](P2085)将《二京赋》与《山海经》《异物志》相提并论,亦是将其视为所涉既广、遂多珍异的“博物之书”。
以神话传说入赋,增加了赋的奇美色彩。《西京赋》描述长安的山川形胜曰:“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缀以二华,巨灵赑屃。高掌远蹠,以流河曲,厥迹犹存。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岐、梁、汧、雍,陈宝鸣鸡在焉。……昔者大帝说秦穆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剪诸鹑首。”[3](P21)崤及函谷关、桃林皆在长安之东,“二华”指太华、少华山。巨灵为河神之名,薛综注引古语云:“此本一山,当河水过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开其上,足蹋离其下,中分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迹,于今尚存。”[3](P22)李善注引《遁甲开山图》亦曰:“有巨灵胡者,遍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3](P22)张衡以巨灵擘山的神话来描绘二华山的形成,富于想象力与神奇色彩。“陈宝鸡鸣”则出自《史记·封禅书》:“(秦)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坂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22](P1359)此显然为民间传闻,却也为陈宝地名的来历增添了神话色彩。至于秦缪公梦天帝奏钧天乐,并赐其土地,此意尤奇绝。如此通过一系列神话传说,使长安的山河土地变得非同凡响,成为民间智慧的折射。
张衡史学修养甚高,“雅好博古,学乎旧史氏,是以多识前代之载”[9](P32)。《后汉书·张衡传》载:“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8](P1904)可见张衡对汉朝事故之熟稔。宫廷生活在平民眼中笼罩着神秘光环,宫中逸闻成为百姓饭余茶后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民间流传甚广,“官司案牍流传,仅存故事,民间则耳濡目染,久若定成矣”[22](P968)。在官方意识稍有松动时,来自民间的声音便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来,为其增添新的活力。将民间传闻采撷入赋,表现了张衡创作的平民心态与好奇趣味。《西京赋》描写了成帝的“微行”:“阴戒期门,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怀玺藏绂。便旋闾阎,周观郊遂。若神龙之变化,章后皇之为贵。”[3](P83)《汉书·成帝纪》载“鸿嘉元年”“上始为微行出”,三国魏张晏注曰:“于后门出,从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白衣组帻,单骑出入市里,不复警跸,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4](P316)《汉书·五行志》亦载:“成帝鸿嘉、永始之间,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余,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帻,带持刀剑。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4](P1368)一国之君,放下九五之尊,微服出行,去体验平常人的世俗生活,可见天子对正常人生活的好奇与渴望,亦寓含着张衡对帝王懈于政事的婉言讽谏之意。皇帝的私生活亦在《二京赋》中亦有所折射,如前文所述卫子夫、赵飞燕淫乱内闱,成帝对董贤的情有独钟等,均反映了张衡对帝王好色误国的嘲讽。“丞相欲以赎子罪,阳石污而公孙诛”,则语涉宫闱丑事,《汉书·公孙贺传》载,公孙贺为丞相,子敬声为太仆,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朱安世不能得,公孙贺请逐捕以赎敬声罪。后果得安世。安世遂从狱中上书曰:“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遂父子俱死狱中。[4](P2878)张衡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太仆与公主私通的秽闻写入赋中,其讽谏之意甚明,亦取决于其取材立意的世俗化审美趣味。
(二)崇简尚俗的审美倾向
赋体“凭虚”倾向,自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假设“子虚”“乌有”,已有所昭示。至张衡《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则明示其“凭虚构象”意图。前人对赋体“凭虚”特征,多集中于其“靡丽多夸”“驾虚行危”“语多虚设”上,其实不仅如此,即使在看似写实中,亦不乏“凭虚”表现。何义门指出:“平子《东京》与班氏《东都》不同,班氏全祖《长杨》,以虚运成文,平子却于首尾用虚,中间用实,历言典制,自成一格。”[2](P230)《东京赋》所言典制,均史有所征[23],是谓写实,然其美东京之风俗,亦不乏虚笔。在历叙东京典故后,其文曰:
是以论其迁邑易京,则同规乎殷盘;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禅,则齐德乎黄轩。为无为,事无事,永有民,以孔安。遵节俭,尚素朴。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将使心不乱其所生,目不见其可欲。贱犀象,简珠玉。藏金于山,抵璧于谷。翡翠不裂,玳瑁不蔟。所贵惟贤,所宝惟谷。民去末而反本,咸怀忠而抱悫。[3](P156)
此段总东京之德,“遵节俭,尚素朴”,“民去末而反本,咸怀忠而抱悫”,与西京之逸乐奢靡相反,这无疑是一种虚构、净化、提纯了的理想状态中的京都民俗美。《二京赋》创作之由在于指斥“自王侯之下,莫不踰侈”的风俗之弊,其时奢侈之风屡禁不止。汉明帝永平十二年、章帝建初二年、和帝永元十一年皆下过禁奢之诏,“观此诸诏,知汉世用度,本有程品,特莫之能行耳”[24](P486)。由此可见,这种返璞归真的风俗世态亦不过是赋家凭虚造象而已,反映了其对社会风俗的理性建构与其崇简尚朴的审美倾向。
就娱乐功能言,赋与优语、小说相类,“乘子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介,为赋诵,好嫚戏”[4](P2366),“其高者颇引经训风谕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8](P1996)。赋家有意识地以街头巷语、小说典故入赋,反映了雅俗文学间的杂糅与互渗。《西京赋》写杂戏曰:“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3](P78)这一戏法见于《汉武故事》:“未央宫中设角抵戏,三百里内观其云雨雷电,无异于真,画地为川,聚石成山。”[25](P463)《西京赋》又曰:“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能不救[3](P78),李善注引《西京杂记》曰:“东海人黄公,少时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饮酒过度,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以赤刀往厌之,术不行,遂为虎所食。”[3](P82)前文所言“卫后兴于鬒发,飞燕宠于体轻”[3](P85),《文选》李善注引《汉武故事》:“子夫得幸,头解,上见其美发,悦之”[3](P88)。赵飞燕体轻善舞,《西京杂记》载:“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3](P88),《赵飞燕别传》言:“赵后腰骨纤细,善踽步而行,若人手持花枝,颤颤然,他人莫可学也”。暂且不管《汉武故事》与《西京杂记》的成书年代,可以肯定的是二书中的某些故事已长期流传于民间,甚或已有成文。张衡在《西京赋》中对这些民间流传的故事的采纳,至少表明其对民间文化因素的重视与吸收,而这也是其贴近平民的审美娱乐观的一个重要方面。《西京赋》末凭虚公子言:“鄙生生乎三百之外,传闻于未闻之者,曾仿佛其若梦,未一隅之能睹。”[3](P90)似乎可看作张衡夫子自道,亦隐隐透露出其创作《二京赋》时“闻之于耳”与“闻之于传”,撷取民间口头或书面传说故事之端倪。
更有趣的是《西京赋》在述及天子出猎时,带叙小说,“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3](P62)。此处的“小说”,薛综注曰:“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又引《汉书》曰:“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衣使者。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3](P65)天子出猎而带上《周说》之类,究其目的在于“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3](P65)。这一做法,于史无征,显为赋家虚设,却也由此可见作为后世“小说”雏形的《周说》之类因具有通俗性与娱乐性而在当时颇受欢迎。“千乘雷动,万骑龙趋”“光炎烛天庭,嚣声震海浦。河渭为之波荡,吴岳为之陁堵”[3](P63)的天子畋猎,神圣色彩被消解,赋予其休闲娱乐功能。就此角度言,赋体亦与《周说》具有相似性。赋家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4](P2367),扬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乃随成帝出祭、出猎、行游而作[4](P3522),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得幸,“每行巡守,辄献上赋颂”[8](P1373)。汉代帝王之所以出猎而命文士赋颂,亦是出于娱乐耳目的心理。张衡有意虚设此情节,进一步凸显帝王神圣出游中的世俗乐趣,无疑是出于平民身份下的猜度,颇具嘲戏之意味。
对方言口语的鲜活运用,表现了张衡对世俗文化与时代文化的关注,也是其尚俗审美倾向的重要体现。简宗梧先生指出:“早期那些使用玮字的双声叠韵复音词汇,既不是搜辑群书摘翻故纸所得的古话,也不是卖弄艰深故作晦涩的隐语,却是当时活生生的词汇,是平易浅俗的口语”[26](P45),“这些最浅俗的口语,书之为文字,如果不透过其音韵,就难以知其意义,而语汇常有地方性,又最容易变,所以俚俗的口语,在不同的时空间,就成为最难懂的词汇”[26](P100)。如写其楼台高峻,则“馺娑、骀荡,焘奡桔桀。枍诣、承光,睽罛庨豁。增桴重棼,锷锷列列。反宇业业,飞檐車獻車獻”,馺娑、骀荡、枍诣、承光皆台名,焘奡、桔桀、睽罛、庨豁皆形貌。李善注曰:“焘,徒到切。奡,五告切。桔,音吉。睽,呼圭切。罛,计狐切。庨,呼交切。”[9](P47)可见,以上描写形貌的词,或双声,或叠韵,锷锷、列列、业业、車獻車獻皆高貌,皆为叠字。这些词极有可能来自口语,被张衡采撷融汇至赋中,以描摹台之高峻之貌。再如其写鸟则“翩翻”,摹兽则“駓騃”,状草木之盛则“郁蓊薆薱,橚爽櫹槮”,现曼延之戏则“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囷 。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蝹蝹”[9](P37)。如万光治先生所言,汉大赋中语多联绵是其口语和口头文学的一大特点[27](P409),这一系列的联绵词,无疑是张衡汲取其时口头文学营养来摹物图貌,以增加大赋的生动性与形象性。大赋字多异体亦因“这类口语在当时的运用虽然十分普遍,却与文字的符号尚未建立其稳定的对应关系。赋家依据‘六书’原理,或借字,或造字,其于口语的记录,都还处在探索、实践的过程之中”[27](P411)。“峩峩”首用于《神女赋》,《招魂》用作“峨峨”,厥后相如《上林赋》、张衡《西京赋》皆作“峩峩”,“峩”“峨”异行,并存不害。“彷彿”亦然,宋玉《九辩》用之,《神女赋》用作“髣髴”,张衡《东京赋》仍之。恰当运用方言词汇以增强大赋表现力,也是《二京赋》的重要特色。如其写楼台高峻曰“将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怂兢”[9](P34),《方言》载:“怂,慄也。先拱切。怵,音黜。慄,音栗”[9](P47)。写天子畋猎曰“纵猎徒,赴长莽”,《方言》载:“草,南楚之间谓之莽”[9](P55)。写力士搏兽曰“梗林为之靡拉,朴林为之摧残”[9](P36),《方言》载:“凡草木刺人为梗。”[9](P57)方言口语的表达形式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还蕴含着更丰富的文化指向,不仅真切地表现了作者对灵动的生活语言所具有的艺术生命力的重视与发掘,而且能够复现一种密切的依附于口语的文化现象,体现出作者颇接地气的尚俗审美意趣。
三赋家独立人格对《二京赋》风俗世态书写的影响
所谓“人格”,是指“整体性地呈现于生活中的真实的自我,它包括了外在的气质、风度、容止、行为和内在的哲学——美学理想、精神境界、伦理观念,以及人生各阶段与人格各层面的心灵趋向与冲突”[28](P3)。对赋家而言,其人格不仅表现在生活中,亦表现在赋作里。
赋自武帝时代成为汉宫廷文学的新兴文体[29](P20),《汉书·严助传》载:“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并在左右。……其尤亲信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4](P2775)可见武帝朝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等皆因赋而受宠,作赋以助兴,而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等虽非专业赋家,却亦精通赋之创作技巧,并参与朝中文化活动。作为宫廷文学的赋,其题材、艺术均受制于皇权的审美要求,有着取悦于君主的特定创作目的,“讽一”必然内含于“劝百”中。于是,汉代赋家时常处于尴尬境地,如枚皋所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4](P2367),扬雄亦称赋家:“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4](P3575)。时至东汉,班固作《两都赋》,《文选·两都赋》题注云:“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9](P1)其预期读者仍为皇帝,其创作目的仍为“劝百讽一”,其讽谏效果自然不尽人意。当文士依附或谄事于当权者,或本身即位居当权者之列时,其人格必定被“阉割”,其灵魂必定被禁锢,其情怀必定趋向于狭隘,其作品必定缺乏峻洁的风格与针砭痼疾的锋芒。
张衡“少善属文”[8](P1897),“天姿浚哲,敏而好学”[21] (P719),青少年时代离开家乡南阳,“游于三辅,因入帝京,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8](P1897)。他游历三辅之地,观西京之胜概,览山川之锦绣,又入当时帝都洛阳,进太学深造,研习经学,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熟识京都物态人情,甚至亦如左思“尝从文士问其方俗山川”[30](P116),为《二都赋》的创作搜集丰富的资料,奠定下坚实的基础。“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8](P1897),表现出其青少年时有志于实学而无心于虚名的冲淡情怀,却也表明其身份乃置身于京都“人海”中的一介书生,与那些被统治者以“倡优蓄之”的宫廷赋家不同,亦与班固作《两都赋》时郎官职位虽低,却深受章帝宠幸的身份不同。基于这种平民化身份与来自“底层”的“生存现场”的真实阅历,张衡得以以冷静而犀利的眼光透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平常心去体悟百姓盛世中的艰辛,洞悉统治者奢靡覆盖下的腐朽,富贵遮掩下的龌龊,将世俗生活审美化,使文人感怀平民化,深入发掘出京都风俗世态中蕴含的人生况味与文化意义。
《二京赋》属于一篇私人性较强的作品[31]。《后汉书·张衡传》载:“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8](P1897)可见张衡作《二京赋》目的在于讽谏其时奢侈之风,加之其因“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8](P1897),非依赋作而腾达,如此就与似俳优的赋家区别开来,在与政治权力的适度疏离中,获得人格之独立,也就拥有言论的自主权。其作品成为个人思想自由驰骋的场域,可以不受权势所限,不为身份所碍,不被学科所囿,在博物骋学中将世间万象包罗其中,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化倾向。审美趣味的形成受制于创作主体已形成的审美经验、审美结构与预期读者的审美习惯,渗透着多年积淀下来的审美感受方式与价值取向。《二京赋》表现出的世俗化审美趣味,亦取决于张衡的平民身份与独立人格。其潜意识中深植着的以讽刺为目的的预构审美图式,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得到显示,显示出民间与宫廷审美意趣之异,使《二京赋》成为汉代宫廷大赋走向式微的标志。
参考文献:
[1]陈庆元.赋:时代投影与体制演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清〕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3]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496.
[6]〔清〕方东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253.
[7]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462.
[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南朝梁〕萧统.文选[M].长沙:岳麓书社,2002.
[10]〔晋〕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1]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汉画像石[M].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
[12]王建中.南阳两汉画像石[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3]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4]〔唐〕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5]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J].文学评论,2003 (1).
[16]〔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7]〔明〕胡广.胡文穆杂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彭铎.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韩玉祥,李陈广.南阳汉代画像石墓[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
[20]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1]〔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3]蒋晓光.月令之学与《二京赋》的论述[J].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4).
[24]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5]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6]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27]万光治.汉赋通论(增订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8]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M].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29]〔美〕康达维著,苏瑞隆译.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0]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1]曹道衡.读《文选》札记[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0(3).
责任编辑赵成林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批准号:13YJC751067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5BZW111)。
*作者简介:杨朝蕾(1977-),女,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16)02-01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