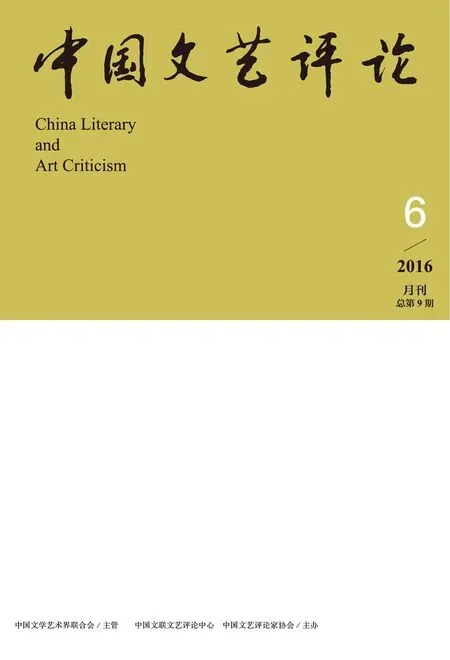增强现实与位置叙事:移动互联时代的技术、幻术和艺术
黄鸣奋
增强现实与位置叙事:移动互联时代的技术、幻术和艺术
黄鸣奋
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正在诸多领域获得应用,其潜能不仅为商业开发所利用,而且为新媒体艺术家所看好。2010年前后,在与位于曼哈顿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打交道的过程中,纽约艺术家斯克沃列克(Mark Skwarek)与荷兰设计师费恩霍夫(Sander Veenhof)对这类老牌机构的排外性感到不快,他们想以某种现代科技手段来挑战它们。这种手段要能穿越它们高高的门槛,要让被它们拒之门外的艺术家自由地发表看法,而且还要让路过它们所在地点的人都能通过移动设备看到这些意见,进行对位思考。为他们所青睐并应用的手段,便是增强现实。如今,增强现实已经不只是让艺术家发表意见的媒体,还作为位置叙事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心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起作用,并且催生了与之相应的新颖艺术形态。
一、增强现实技术与位置叙事的自然环境
如果将自然环境当成实境的话,那么,在计算机技术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虚拟现实是虚境(完全沉浸的封闭或半封闭系统),其特点是沉浸性(Immersive)、交互性(Interactive)和想象性(Imaginative)。[1]Burdea, G, Coiffet, P.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ies.New York, NY:John Wiley & Sons, Inc, 1994,p.4-5.相比之下,增强现实是以现实为依托、以计算机虚拟信息为增强的开放系统,即“第二自然”。我们不妨称之为相对于实境(正题)、虚境(反题)的复境(合题),因为它既是由数据层和现实层复合而成,又体现了螺旋式上升的特点。虚拟现实意味着由计算机营造的数码空间能够给用户以位置感。人们将虚拟现实当成可入、可行、可居的灵境。相比之下,增强现实意味着数据层为现实对象增添新的内容,使之具备在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双重位置。
增强现实技术已经在遗产保护、娱乐游戏、旅游展览等领域获得应用。例如,在欧盟支持下,IntraCam公司运用增强现实技术对古希腊的赫拉神庙遗址进行数字化重建。以此为背景,艺术家将增强现实作为大有潜力的新技术来开拓。2011年,在日裔美籍艺术家蒂勒(Tamiko Thiel)领导下,艺术群体“增强现实宣示”(Manifest.AR)致力于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增强现实介入,以及在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与闪族设计团队(PATTU)的合作。上述介入运用涌现中的移动增强现实技术,通过GPS坐标,将虚拟作品在地理上定位于封闭的展览空间。与物理上的艺术介入不同,这些作品无法由策展人或其他权威所移除或封锁,艺术家想将其保存于这些场所多久就多久。北京理工大学王涌天教授致力于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完成对圆明园的虚拟重建,让在园中散步时戴上特殊三维眼镜的用户可以观览当年皇家园林原貌。在该校光电信息技术与颜色工程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的协作下,中国军事博物馆利用增强现实技术,以红四方面军一个真实故事为原型,再现《雪山忠魂》这一感人场面,让观众感受长征的震撼。增强现实的艺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位置叙事”主要是指以位置为中心的叙事。它将自然环境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基点,在宏观上涉及人在自然界的位置,在中观上涉及社会群体和所处地域的关系,在微观上涉及个人与所在地的关系,因此是有地点的叙事。若按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格拉希(Vladimir Geroimenko)的说法,真实现实为“阳”,虚拟现实为“阴”,增强现实是阳中有阴,增强虚拟(Augmented virtual)是阴中有阳。[1]Geroimenko V.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and Art: The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of Evolving Conceptual Models.2012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Information Visualisation (IV).IEEE, 2012,pp.445-453.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大学谢弗(Nathan Shafer)认为:“时至今日,增强现实已成为我们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人们漫步于其间,并通过发光的屏幕凝视世界。”[2]Shafer,Nathan.Augmenting Wilderness: Points of Interestin Pre-connected Worlds,In Augmented Reality Art : From an Emerging Technology to a Novel Creative Medium.Edited by Vladimir Geroimenko.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4,p.217.从技术上看,作为“第二自然”的增强现实对于位置叙事的重要性正逐渐显示出来。
增强现实相对于位置叙事的价值之一,是基于地点的文化传承。由于旧城改造、乡村城市化等社会变迁,许多携带重要历史信息的景观消失了,许多风俗、仪式不见了,人们只能通过纪录片、博物馆之类的途径去寻觅它们的踪迹。可是,被影片所记录、被博物馆所收藏的对象已经丧失了活力。相比之下,增强现实可以使它们在原来的地点复活,实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衔接。只要人们走过这些地点,网络就自动将相关的视音频作品推送到他们所携带的手机、平板电脑或智能眼镜上,让他们知道这里曾发生过的事件、曾有过的风光。
融合了增强现实技术的位置叙事可称为“增强型位置叙事”。例如,艾弗森(Hana Iverson)实施街坊叙事(Neighborhood Narratives),与特鲁里(Sarah Drury)开发出移动增强现实作品《场所机制》(the Mechanics of Place),让虚拟居民重新入住如今已经面目全非的伊斯坦布尔街道。又如,激进主义艺术家奥格斯特(Brian August)响应乌尔默(Gregory Ulmer)关于建造现代纪念碑以排解当今悲剧和恐怖的号召,用增强现实技术建造了美国世贸中心纪念碑,称为“110个故事”(110 Stories),让观者得以重温关于该中心的记忆,将它们留在自己拥有上述记忆的地方,从而将时间中的记忆和物理场所联系在一起。上述记忆保存在社区可以从应用程序和互联网调取的集体数据库中。
在旅游领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宋扬蔡青等设计出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桂林文化创意旅游及服务系统,让游客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文化旅游信息,看到早已消逝的各个时期桂林古城原貌,亲身体验到古时的桂林人文风情,和桂林名人旧事产生交流、交互等全新的旅游体验(2012)。[1]宋扬蔡青、卜治寒、汤莹:《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桂林文化创意旅游及服务系统》,《科技创新与应用》2012年第34期,第61-62页。
二、增强现实幻术与位置叙事的心理环境
增强现实首先是一种技术,在能够给人提供奇妙感受方面又可称为幻术。例如,增强现实与印刷术的结合,颠覆了书刊报纸给人的刻板印象——只要用摄像头对准印刷品上的标志,相关移动设备上就会呈现出预设的三维图像,效果非常奇妙,对于不了解这种技术内情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增强现实开发商已经和数以万计的出版商、营销商、品牌与代理机构合作,让它们运用专用浏览器开发相关服务,即交互性印刷。它们把虚拟信息和现 实世界联系起来,让读者可从纸质出版物上获得生动的数字体验。国内也有书刊报纸在做这方面的实验。至于电子游戏界,对增强现实早就表示欢迎。
幻术有戏法、巫术、魔术、妖术、奇术等多种含义,在字面上可以理解为致幻之术。关于它与魔术的异同,存在种种不同说法,兹不赘述。我们将幻术理解为高超的魔术。传为战国列御寇所著的《列子·周穆王》说:“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难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2][战国]列御寇:《列子》卷三“周穆王第三”,四部丛刊景北宋本,第24页。引文中强 调幻术以深明物理、随机应变为条件。幻术的类型很多,有断头复续、坐成山河,立兴云雾、呼风唤雨,履火蹈刃、种瓜移井等。从今天的角度看,幻术之所以能够使人信服,好像真的创造了奇迹,一方面是由于施幻者使用了障眼法,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懂得设计和运用各种技术。二者结合起来,就使得幻象被误以为真。
增强现实为我们理解历史上的幻术提供了反向思考的余地。与其说幻术将假象呈现给观众,还不如说它们刻意隐瞒了与特定现象相关的因果关系。只要可知条件和实际结果之间缺失了逻辑推理所必需的某一环节,那么,观众便有可能将这些现象当成奇迹、奇观。从“反常合道”的角度看,幻术与艺术是相通的,或者说幻术属于广义艺术。不过,艺术并不讳言“道”,乐于让受众闻其详、知其理,具备较高的透明性。相比之下,幻术总是向受众隐藏了某种东西。如果和盘托出、一览无余,那么,它就失去了特有的魅力。与一般的魔术不同,幻术比较适宜在现实环境中表演,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今,它经常被视为某种大型实景互动娱乐。
幻术也为我们理解当今增强现实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系。幻术的特点是亦真亦假,真真假假。能够施展幻术的人,总是精通某种常人所不了解的技术,进行某种灵想独辟的设计。作为一种技术,增强现实很适合创造某种现实幻象。如果说虚拟现实是引导人们沉浸到计算机化空间、体验虚拟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增强现实是引导人们瞩目覆盖了幻象的生活环境、体验现实转变为幻象的可能性。当代魔术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例如,美国纽约数码魔术师坦皮斯特(Marco Tempest)用开源软件来开发魔术工具。2012年,他在美国私有非营利机构“技术、娱乐与设计”(Technology, Entertainment,Design)组织的大会上表演“魔术和叙事”,将增强现实与虚拟魔术结合起来,如其所言,“模糊了极度真实与极度虚幻的界限”。[1]Visnjic,Filip.Magic and Storytelling at TED / Collaboration: Marco Tempest, onformative + checksum5.2012.http://www.creativeapplications.net/openframeworks/magic-and-storytelling-at-tedcollaboration-marco-tempest-onformative-checksum5/他的表演具备某种幻术的特征,例如,凭空从掌心生出一个黄色小球来,与之嬉戏,然后将它抛没;又如,在空中映射分别标有“事件”和“情感”字样的两个圆点,然后用手凭空划出一条线将它们连接起来;还有,在讲到参与时,其身体左右各出现一个影影绰绰的人,向他靠拢。在表演的最后,他用手翻舞许多米黄色的粒子,向大家告别。坦皮斯特一边进行肢体表演,一边发表关于魔术、科技和叙事的见解,强调上述图像并非事先录制,而是依靠电脑生成的图像,与现实融为一体。他公开承认魔术是一种骗术,但声明它让人享受,放弃怀疑;与此同时,又强调魔术是一场戏剧,一招一式都是故事。
位置叙事是依托一定的心理环境进行的。这就是说,对实境、梦境和幻境的甄别,是位置叙事的基本前提。实境所提供的景象是通过分析器所能感知,通过神经中枢所能理解,通过效应器所能交互的。相比之下,梦境所提供的景象无法依靠感官来把握,无法依据逻辑思维来辨析,也无法通过四肢与之互动。幻境介于实境和梦境之间,具备亦真亦假的效果。这种效果的制造,大致通过以下三种途径进行:一是引入某种传感技术,使当事人体验到超乎日常五官感觉的刺激;二是引入某种并非逻辑思维所能推导的因果关系,使当事人觉得奇异、奇妙或奇怪;三是引入某种单凭身体所无法控制的交互机制,使当事人的反馈机制和日常经验脱节。
增强现实完全可以通过上述途径作为幻术起作用。这种效果已经在以色列梅—拉兹(Eran May-raz)、拉佐(Daniel Lazo)所拍摄的科幻短片《视象》(Sight,2012)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主人公戴上隐形眼镜,便可以通过意念控制所见的梦幻世界。不论是冰箱所藏食物的多媒体信息,还是墙上所悬挂的油 画或电视机,其实都是增强现实系统所叠加的数据层。这种眼镜不仅可以充当安排约会的“红娘”,而且还能给佩戴者相关的提示,制造出某种善解人意的幻象。但是,如果对方发现你的巧妙应对原来只是增强现实系统的周到安排,那么,幻象就被戳穿了。
如果想要体验作为幻术的增强现实所产生的心理影响,那么,下述项目可供参考:西班牙马德里interactiv os工作室开发的增强现实魔术系统(AR Magic System),可让用户与其身边的人交换头部影像,让自己的脑袋仿佛长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同时也获得了新的面孔。陶氏(S.Dow)等人《奥克兰之声》(Voices of Oakland)将背景设定于墓地,让所葬之人的声音为游客所得闻,以产生基于场所的叙事(2005)。移动增强现实游戏《闹鬼的星球》(Haunted Planet,2012)提供户外神秘冒险,让玩家追踪附近的单一魔鬼(2012)。德国应用科技大学斯皮尔灵(Ulrike Spierling)等人致力于推动面向移动增强现实的位置意识交互叙事结构化,推出“精灵”(SPIRIT)项目,将移动设备转变成为“魔术设备”,让用户可以遇见历史人物的“不安精灵”,即在增强现实中与虚拟人物交互(2014)。
电子游戏经历了电视游戏、控制台游戏、计算机单机游戏、网络游戏等发展阶段,在新世纪和增强现实幻术结合,使广大玩家能够体验到通常只有在魔术舞台上才能见到的亦真亦幻的效果。例如,Sony公司PS3游戏《审判之眼》(Eye of Judgement,2010)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在玩家身边的真实环境中逼真地渲染出3D怪兽等游戏角色。
增强现实让玩家得以在现实环境中体验数码游戏。为此,相关系统必须检测他们的现实运动,匹配他们的行为。玩家则必须带上装备,离开电脑桌,在户内(或者到街上)行动起来,将自身的身体变成游戏角色的代理,将现实空间当成游戏场域,或占领地盘,或射击对手,或寻找宝藏,等等。游戏小世界,天地大舞台,增强现实游戏将二者有机融合起来,让玩家在现实环境中体验到舞台幻象。他们既是现实的人,同时又是游戏角色。作为现实的人,他们与身边伙伴或过往行人进行故事外交互;作为游戏角色,他们与其他参与者进行故事内交互。这种幻象的制造者是负责开发与运营增强现实游戏的企业,是比单个魔术师强大得多的机构。对于魔术师来说,多数观众(除被邀请上 台一道表演的外)只是在被蒙蔽的意义上形成心理幻象。对于增强现实游戏运营商来说,所有玩家几乎都是自觉地共同建构群体性的心理幻象,而且是以自己的行动来建构。
三、增强现实艺术与位置叙事的社会环境
作为技术的增强现实被引入艺术领域,既可能产生供既有艺术作品传播之用的新媒体、新平台,又可能产生泛艺术意义上的新手法、新产品(如前述增强现实游戏),同时还可能产生作为前卫艺术的新开拓、新形态。后者就是所谓“增强现实艺术”。目前,它已经不只是个别艺术家脑洞大开的艺术实验,而是由相关艺术群体所力促、有相关艺术宣言作为理论主张的某种流派。
增强现实艺术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马丁(Julie Martin)1994年创作的《在赛伯空间中起舞》(Dancing in Cyberspace)。该项目由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资助,让参与者与投射到舞台上的虚拟景象交互。加拿大艺术家加迪夫(Janet Cardiff)引导观众在物理空间中遵循她由便携式光盘播放器或摄像机所传达的指令(如“下楼梯”“看窗口”等)而行动,变成她所设计的故事的参与者(1995)。在这一过程中,观众所处的物理空间为信息空间所增强,具备了平常所没有、为故事所赋予的含义。这一作品以“音响散步”著称。澳大利亚技术大学格威尔特(Ian Gwilt)创作了将增强现实与移动通信结合起来的作品《作为_保存》(2007)。他指出:从创造的观点看,增强现实移动艺术的前景是极端广阔的,因为它可以将数码内容赋予物理环境或空间。它意味着艺术作品可以为不断变化的场所和境况而创造。持着手机观看增强性艺术作品的行动将数码技术科学和文化约定联系起来,我们得以观察如何将一种空间加于另一种。从观念的视角看,增强现实 作品不是以一个空间模仿地取代另一个,而是旨在理解二者关系的复杂性。[1]Gwilt,Ian.Augmented Reality and Mobile Art.In Handbook of Multimedia for Digital Entertainment and Arts.Edited by BorkoFurht.London; New York: Springer,2009,pp.593-599.2013年日本艺术家白鸟圭(Kei Shiratori)等人创建了增强现实艺术网站ARart。[2]ARart.http://arart.info/
近年来,可穿戴计算为增强现实艺术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2013年,纽约艺术家卡茨(Samantha Katz)号召30位艺术家戴上谷歌眼镜,将每天各自的生活拍成视频,通过YouTube共享,连续30天。同年,另一位纽约艺术家达图纳(David Datuna)向迈阿密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 Miami)提交了一件装置艺术作品,形态是嵌有许多摄像头的玻璃材质美国国旗。一旦访客戴上谷歌眼镜凑近观看,其形象便被摄像头捕获,作为视频流传送到谷歌眼镜上,形成包含反馈的回路。
同样从事增强现实艺术创作,长驻纽约的伊朗裔加拿大艺术家(Amir Baradaran)看好的不是智能眼镜的小屏幕,而是背靠背的两个大屏幕。2015年,他在迈阿密海滩艺博会(PULSE Contemporary Art Fair)上展示以微笑为激励机制的新作。当两个屏幕前面的参与者都微笑时,相应的系统就被激活,将他们带入增强现实体验——各自的面部作为数据层叠加在展馆空间中,并随着微笑而变化。意大利艺术表演团体ConiglioViola在都灵推出影像艺术展《巴格达蒂诺之夜》(The Nights of Tino From Bagdad)时进行了另一种尝试。其作品叙述蒂诺公主放弃皇家安富尊荣追求诗人之梦的故事,所根据的是德国作家拉斯克-许勒(Else Lasker-Schüler)的同名小说(1907)。展览在30个公交车站广告牌张贴了讲述主人公故事的海报。用户倘若在智能设备上运行以主人公为名的程序,就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这些海报。国内亦有这方面的例子。据报道,2014年厦门文广影音推出《音乐·时光·鼓浪屿》音乐专辑和《乐游鼓浪屿》有声盖章本。这两个为智慧鼓浪屿量身打造的音乐旅游文创新品创造出了艺术的惊奇:游客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媒体的摄像头,就可以体验产品图像上叠加的互动多媒体信息。从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中可以看见,鼓浪屿知名中提琴演奏家杨璟浮现在专辑封面上进行现场演奏(虚拟场景),有声盖章本内页景点地图上浮现了相关景点的信息。[1]伏山:《“听见鼓浪屿”:厦门开创性运用“增强现实技术”再现有声风景》,http://www.fj.chinanews.com/ news/2014/2014-08-04/285961.shtml
如果说增强现实作为技术主要涉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作为幻术主要涉及人与心理环境的话,那么,它作为艺术主要涉及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艺术历来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其起源、本质、特征和功能都可以在社会交往中得到定位。作为艺术的增强现实也是如此。在消费社会中,它面临着顺应体制(走市场化道路)或挑战体制(以批判者自居)的选择。增强现实艺术能否商业化的问题,格拉希已经进行了探讨,他所著《增强现实绘画与雕塑:从实验性艺术作品到商业艺术》(2014)一文基于对作者个人展“潜藏现实”与户外装置“企业拼图”的分析,认为通过二维、三维物体的增强整合起来的特殊类别增强现实绘画是可销售的。他提供了自己用于在亚马逊网站销售的首个增强现实绘画,即《半吻》(The Half Kiss)。[2]Geroimenko,Vladimir.Augmented Reality Painting and Sculpture: FromExperimental Artworks to Art for Sale.In Augmented Reality Art : From an Emerging Technology to a Novel Creative Medium.Edited by Vladimir Geroimenko.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pp.175-188.不过,目前西方增强现实艺术的主导倾向仍是社会批判或激进主义。相关艺术家以绍续街头艺术自居,对公众赋权格外关注。
在西方激进主义者看来,增强现实艺术仿佛是街头艺术的科技版。例如,纽约城理工学院贝克尔(Damon Loren Baker)将增强现实作为“使有抱负的世界破坏者成为可能的技术”来加以考察,并援引激进主义者哈林(Keith Haring)论街头艺术可能性的随笔《灾变》(Apocalypse,1988)作为增强现实艺术的思想渊源。[3]Baker,DamonLoren.Wearable Apocalypses: Enabling Technologiesfor Aspiring Destroyers of World.In Augmented Reality Art : From an Emerging Technology to a Novel Creative Medium.Edited by Vladimir Geroimenko.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pp.305-312.
街头艺术主要包括街头涂鸦艺术、街头行为艺术两类。它们都和增强现实艺术有相通之处。美国丹佛大学麦克加里哥(ConorMcGarrigle)创作了移动增强现实作品(NAMAland),基于Layar平台,运用开放数据将爱尔兰金融崩溃的方方面面视觉化,并加以批判,做法是用一个数据库驱动的数据层覆盖都柏林,从中可以辨认出爱尔兰国家资产管理局(National Asset Management Agency,NAMA)控制下的房地产。这一机构是为消化金融危机遗留下来的810亿欧元银行坏账而建立的(2009)。麦克加里哥创作的关键是运用有关的另类资源,即在匿名网站NAMA Wine Lake1 上找到有关上述机构的房地产信息。据信,增强现实有力量曝光一度安全地隐藏在墙、会议室之类屏障后面的腐败、污染、非正义等信息。例如,斯克沃列克创作了题为“ar OCCUPY app”(2011)的作品。手机用户只要扫描美国大通银行的商标,就能从屏幕上看到华尔街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投入250亿美元巨资救市。此举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用普通纳税人缴纳的税赋扶植这伙资本家。以上两个作品都具有某种街头涂鸦艺术的意味,但不是简单的乱写乱画,而是用高新科技所进行的社会批判。相比之下,与美国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相配合的增强现实艺术作品同样是用高新科技所进行的社会批判,但具有某种街头行为艺术的意味。2011年,有25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用增强现实作品响应上述运动。这些作品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扫描华尔街相关位置来观看,内容包括恐龙吐火、呐喊示威、虚拟爆炸等。这些艺术家未必都亲临现场,通过增强现实作品所进行的抗议不受华尔街警戒线的限制,甚至将抗议由祖科蒂公园移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前面。2012年5月1日,全球增强现实激进主义者又举行了名为#arOCCUPY May Day的占领行动,由42名艺术家在瑞士、日本等二十余个国家实施。
西方激进主义增强现实艺术家不认为占领街道在今天是表达诉求、进行社会批判的有效办法,因为大规模交通阻塞可能危及整个国家。相比之下,运用增强现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小得多,不过是接入网络的费用而已。他们试图通过增强现实将虚拟经验转变为物理经验,赋予大众新的权力,推动社会变革。他们相信增强现实允许人们将所要发布的信息置于地球表面任何指定地点,并且与身处那儿或上了网的其他人共享这些信息。不过,他们也明白这种技术的两面性:大众固然可以因它而获得一度被认为是超人才有的能力,但它也可能被用为剥削、操控和监视大众的工具。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主动介入,可以让增强现实的应用朝有益于大众的方向发展。而且,他们希冀通过网络发挥跨越地域的影响,在群体内外生成对话。被选为增强现实艺术体验场所的经常是公共空间中出问题的地点。走过那儿的人们本来就可能有所感触、有所联想,增强现实作品让他们得以动情和沉思,所想到的一切都可以很方便地通过网络扩散。因此,增强现实艺术实现了本地化和全球化的统一、位置叙事与非位置叙事的统一。
增强现实艺术将用户当成自己的组成部分之一,为公众维权是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例如,激进主义者创作了《苹果商店以富士康工人介入》(The Apple Store Intervention with Foxconn Worker),反映劳动者所处的恶劣环境,并设想将该程序颠覆性地安装在苹果商店的展品手机中,让消费者在买手机时可能偶然地予以体验。又如,2011年土耳其禁止在互联网领域使用“自家制”“热”“性感”等138个词,因为它们冒犯了该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当地艺术家基兹勒玛(PetekKizilelma)等人用增强现实制作了《土耳其的禁词目录》(Turkey’s forbidden words list),将它们变成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涂鸦,以维护公众的言论自由。再如,美国艺术家蒂勒(Tamiko Thiel)专注于探索场所、空间、身份与文化身份的相互作用。她曾经将被当局所监视的艺术家的剪影通过增强现实置于科科伦艺术画廊的墙中。
在增强现实领域,西方激进主义艺术家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之一是使技术民主化,让创作过程简单到任何人都可用智能手机方便地进行。为此,需要相适应的工具,应用程序infiltrAR就是如此。它允许公众以虚拟热气球的形式将推特信息直接发到美国总统办公室、私营企业内部之类普通人不可进入的场所。如果那儿的达官显贵或大腕人物打开应用程序,就会看到绕着自己所在位置飘的气球,这就是公众针对特定地理位置所制造、表达自己诉求的增强现实信息,它们只能在这些地理位置被看到。又如,美国佩彭海梅尔(Will Pappenheimer)所开发的“天空书写”(Skywrite,2012)让公众得以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描绘增强现实云彩。据介绍,人们用移动装置看着天空,以手指在其屏幕上描绘,不仅可以见到一片云彩就这样出现,而且还能听到飞机的声音。这可用于写情书。但作者选择的是白宫、国会大厦、苹果与面书总部这类场所,因此,当要求他们在这些建筑上画点什么的时候,就可能将平常的市民转变成为激进主义者。
除社会批判、公众维权之外,西方增强现实艺术家也将环境保护当成自己关注的重点之一。例如,2010年,斯克沃列克等人创作了《你的家乡的泄漏》(the leak in your hometown),所针对的是英国石油公司(BP p.l.c.)2009年夏天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故。这是用移动性增强现实制作的第一件激进主义作品,特点是“黑”了该公司的蕊状图标,让其花心冒出一根冒烟的排污管来。只要将手机摄像头靠近英国石油公司的任一图标,就可以从屏幕上看到它在排污。又如,谢弗(Nathan Shafer)《退出冰河终点项目》(Exit Glacier Terminus Project,2012)揭示阿拉斯加冰川近年来的后退,揭示全球变暖的吞噬效果。弗里曼(John Craig Freeman)《毒物废料排放》(DechARge de Rebut Toxique)描绘了一个穿过巴黎城区的放射性有毒废物泵,以警示环境被污染的危险。
此外,斯克沃列克等人还创作了一些以国际政治为题材的作品。例如,在《擦除分离障碍》(Erase the Separation Barrier AR,2011)中,增强现实技术被用于创造穿过巴以路障的大洞,让两边的人可以穿过大洞相互张望。它用增强现实移除(而非增加)现实的一部分,什么高墙都不见了。又如,《朝鲜统一项目》(Korean Unification Project,2011)用增强现实技术擦除了军事分界线,试图通过制造和平统一的朝鲜的视野来创造共同背景。
在策略上,激进的增强现实主义艺术家师承当年字母主义国际(Letterist International)和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所谓“异轨”(detournement),致力于挪用现成的人工物,根据自己的意图赋予新义。在社会批判的态度上,他们和黑客存在某些相通之处。不过,黑客之“黑”往往造成被“黑”对象的实质性改变,而激进主义艺术家运用增强现实所实现的“黑”仅仅是为之覆盖在特定条件下可见的数据层。在具体做法上,他们受到涂鸦艺术家在公共空间进行未经许可的创作的启发,但自信靠现代科技可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比如,如果你定位于一家有腐败行为的公司,用增强现实“黑”了它的某个图标,那么,该公司在全世界的所有图标都会受影响,因为只要人们用带摄像头的手机对准它们,就可以观看到它们被“黑”的结果。这类作品和“城市牛皮癣”不同,不会影响市容,只是呈现于赛伯空间。
尽管如此,这类做法仍然可能涉及伦理的、礼仪的甚至是法律方面的问题。激进主义艺术家可以将自己不满的真人形象和公众所熟悉的负面人物形象嫁接起来,例如,将《加勒比海盗》中无恶不作的巴布萨船长(Captain Barbossa)转变成为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执行总裁 CEO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上述做法在什么意义上为社会规范所允许,什么意义上又构成越轨,这类问题都是有待探讨的。激进主义艺术家自己也不无担心。过去的激进主义者担心集会游行被认出,如今的激进主义者则担心使用增强现实会留下可追溯的数码指纹。
根据艺术群体Manifest.AR所发表的《增强现实艺术宣言》(2011),增强现实艺术的革命性可以用影片《电子世界争霸战》(Tron,1982)中的一句话作为引子来认识:“一切可见的必须超越自己并扩展到不可见的领域”。[1]在影片中,这是由休斯(Barnard Hughes)所扮演的电脑监守程序Dumont对安全程序Tron所说的话,允许后者访问自己所守护的输入/输出接头。我们不妨将“一切可见的”理解为物理世界,将数据层的叠加理解为物理世界的扩展,将“不可见的领域”的进入视为增强现实的效果,将“超越自己”看成是增强现实发展的驱力。在艺术领域,增强现实至少具备如下影响:一是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显示器、摄像头等器材对于数码艺术创造力的约束。“增强现实创造了并存的多重空间现实,在其间万事皆有可能——不论在哪里!未来增强现实没有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在未来增强现实中,我们变成了媒体。从停滞屏幕的虚拟获得解放,我们将数据转变成物理实时空间。‘显示的安全玻璃’(The Safety Glass of the Display)被粉碎,物理的与虚拟的统一于新的中介空间。我们正是选择这一空间进行创造。我们正突破神秘的不可能之门!时空死于昨日。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中,因为我们已经创造出永恒的、泛在的地理定位在场。在21世纪,屏幕不再是边界。摄像机不再是记忆。运用增强现实,虚拟的对真实的予以增强、加强,将物质世界置于时空对话中。”二是打破了传统艺术体制对于数码艺术家创造性的约束。“在瞬间虚拟集体的时代,增强现实激进主义者加重与解除了介于所谓纯粹虚拟与所谓物理真实之间的表面张力与渗透压力。如今,一大群联网增强现实创意人士拓展虚拟媒体,以覆盖、然后压倒栖身于物理层系中的封闭性社会系统。他们创造了阈下的、审美的与政治的增强现实刺激,在网上与离线体验的亚同温层触发了技术骚动。我们坚定地立足现实,将虚拟的影响加以扩展,整合并将它映射于围绕我们的世界之上。物体、平庸的副产品、魔鬼想象与激进事件将并存于我们的私宅与公共空间。我们运用增强现实安装、修改、感染、仿真、曝光、装饰、破坏、骚扰与揭示先前由公共的精英承办商把持的公共机构、身份及对象,以及所谓物理真实中的艺术政策。”三是打破了传统艺术观念对于数码艺术创造定位的约束。手机与未来视觉化手段是瞬息维度物体(Ephemeral Dimensional Objects)、后雕塑事件与创新性建筑的物质证人。“我们以我们由病毒引起的虚拟精神侵入现实。增强现实不是一个尚武的前卫取代计划,而是一个生根繁殖、彼此相关与相互整合的附加存取运动。它拥抱一切模式。与奇观相对立,现实化的增强文化引入了全参与(Total Participation)。增强现实是新的艺术形式,但它是反艺术的。它是原始的,这增强了其病毒效力。正是坏绘画挑战好绘画的定义。它出现于错误的地方。它未经许可就占据了舞台。它是自我实现的关系性观念艺术。增强现实艺术是反重力的,它处于潜藏状态,必须被发现。它是不稳定的、非持续的。它是存在与变化、真实与非物质的。它就在那儿,可以被发现(如果你寻求它的话)。”[1]Geroimenko, Vladimir,ed.Augmented Reality Art : From an Emerging Technology to a Novel Creative Medium.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Preface.如果说上述宣言主要表现的是西方激进主义者对增强现实艺术的情感化认识的话,那么,另一些人则从学理的角度加以探讨,像博尔特(Jay David Bolter)等就是如此。
在西方学术界,增强现实已经成为新媒体艺术研究的热点之一。2014年格拉希主编出版了论文集《增强现实艺术:从涌现中的技术到新奇创造性媒体》,为本书撰稿的25位艺术家来自六个国家(美、澳、意、英、罗、德)。格拉希指出:“从人类诞生到20世纪,人类生活于单一世界(我们如今可称为‘真实现实’)。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明增加了新的现实领域——一种复杂的、令人激动的、有用的数码世界。从那时以来,我们生活于两种不同的世界(物理的与数码的),但并非同时,至少就我们的感知与注意是如此。这正是增强现实起作用之处。这种独一无二的技术使作为真实世界与数码世界之混合的新世界的存在成为可能。增强现实或混合现实将数码内容植入物理世界,以增强或增进后者。它使得有可能不离开物理世界就体验数码世界。增强现实是从物理世界与数码世界二元论走向其统一的关键一步,这使得这种技术对未来人类拥有至上价值。”他认为,“增强现实艺术不只是一种新奇的创造性媒体,它注定要变成涌现中的混合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将一种新型艺术作品带到物理世界——位于任何地方、拥有任何尺寸与功能上的复杂性的作品。”[1]Geroimenko,Vladimir.Concluding Remarks: Today’s Vision of an Art Form of the Future.In Augmented Reality Art : From an Emerging Technology to a Novel Creative Medium.Edited by Vladimir Geroimenko.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pp.313-314.国内亦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现。[2]哈尔滨工业大学媒体技术与艺术系权维撰写了硕士论文《基于增强现实的交互式空间艺术构成和审美体验的研究》(2011);杨旺功、赵一飞:《浅析基于增强现实的新空间艺术审美体验》,《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2015年第1期,第46-48页。
上述分析表明:增强现实技术的引入促进了艺术观念的变革。从增强现实的角度看,艺术与环境并非彼此区分或相互对立,而是趋于一体化。大地艺术从实体的角度表明了这一点,增强现实艺术则从虚拟的角度表明了这一点。不过,增强现实艺术的功能受制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从理论上说,这种新的艺术形态在世界各国可能被用于数码抵抗、社会治理或市场营销等多种目的。激进主义者可以用增强现实艺术进行社会批判,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用增强现实艺术推行社会教化,产业界同样可以应用增强现实艺术进行产品推广。
在我国,增强现实技术完全可能和文艺创新结合起来。信息革命带动文艺创新,这是近年以来不止一次发生过的现象。网络文学由附庸蔚为大国,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之一。如今,我们可以预期网络文学与增强现实相结合,成为有地点、可定位、和乡愁相联系的网络地域文学。网络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主要特点是由作为数码媒体的互联网造就的,这就是虚拟化。虚拟化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想象力,使文学创作摆脱了现实环境的制约,朝着时空穿越之类方向发展,并有利于文学作品的全球共享。这样做的消极影响之一,就是淡化了用户或读者对于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的关注和热情,疏远了活跃于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引发了对于网络沉溺的担忧和批判。增强现实本来就是作为虚拟现实的革新而出现的。它有利于文学在现实世界中的立足,有利于凝聚和激发人们建设自己所在的城市、乡村的热情。试想:如果我们将增强现实作为一种观念贯彻于创作,让人们为家园或其他特定场所写的诗文通过网络定位于相应的地点,走过那儿的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终端调用,那么,定居者可以寄托自己的情思,旅游者可以扩展自己的见闻。赛伯情感和现实情感可以统一起来,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就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宋代文豪苏轼曾说:对于杜甫“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这样的描写,“非亲到其处,不知此诗之工”。[3][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七近体诗《子规》注引,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38页。将来,读者要想深刻领略网络地域文学的内涵,予以恰当的评价,也只有亲自到对应的地点才能做到。增强现实不仅有助于推动网络文学与地域文学的融合,而且有益于不同世代文学创作者与文学评论者之间的沟通。他们可以通过相关网络服务共享信息,以特定位置为依托,集成具体作品、创作体会和阅读感受,实现增强现实和位置叙事的相辅相成,并以不断叠加数据层的方式进行历史文化积淀。
黄鸣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史静怡)
编者按: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如何从技术、艺术、评论、产业等层面多维度地认识网络文艺,是文艺界评论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期刊发一组文章,以期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