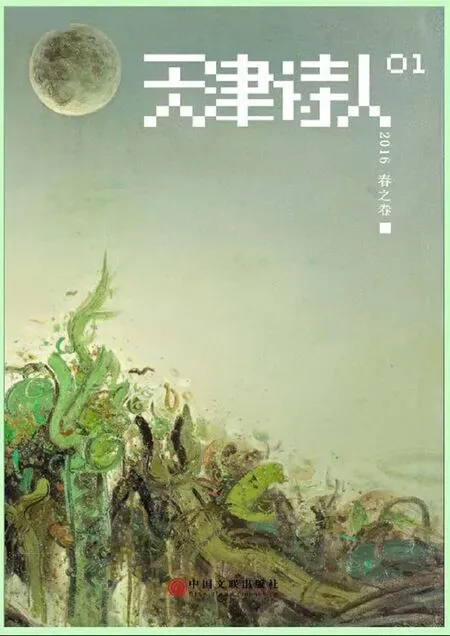美学高于伦理学:汉诗中的“休闲”
方文竹
关于汉语诗歌与现实问题的理论纠缠暗含着诗歌题材比例的一种划分,即诗歌中的现实多些或少些以及诗歌价值本身构成的问题。其实,这只是浅表层次的问题,而暗含中还有另一种暗含,即深层次的问题:与现实镶嵌或隐藏在现实背后或支配着现实运转度的是什么?我想,“休闲”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元素或元素之一,何况目前汉诗写作中已经体现出“休闲”的气氛和品性,休闲也是一种现实,是另一种现实。“休闲”是一种态度,体现为对现代性的穿插、并列、互补,与其对抗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性,或说成为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度假村、别墅、公园、广场、KTV、桑拿、小长假、农家乐甚至明星文化等等的兴盛。休闲是文化消费时代的奢侈和补偿,不休闲也会活得好好的,但休闲却扩大了人生的意义和文化的边界。尤其是当休闲成为休闲文化时,再扩展为文化产业,潜入或闯入人们的现实生存图景,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配置和制作,休而不休,闲而不闲。休闲自然或明或暗地进入诗歌的肌理和创造流程,完全有理由进入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写作的势力范围。不仅如此,由于休闲的潜在强势,非现实类诗歌同样摆脱不了休闲的干系。
“休闲”侵入目前汉语诗歌写作的肌体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说古已有之)。从汉语诗歌现状可以看出休闲的如影随形:想对于50后、60后,70后、80后诗人相对逃离社会负累且生活环境优越,他们的“下半身”本身即“休闲”的产物,这也是“下半身”长期遭到批评的原因。“民间写作”对抗主流意识形态,“游离”即处于“休闲”的互换状态,并以“游离”或“休闲”取胜。当然,“下半身”和“民间”并非无事可做,而是有着做不完的“闲活儿”,只不过不被主流承认和接纳罢。作为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群体,“知识分子写作”对“知识”(这里指非功利性的知识)的吸取必须在“剩余”的可能性中完成,而“剩余”不就是“休闲”么。总起来看,诗人属于有闲阶级(自古而然),试想一想,整天为生计奔波或在战火中冲突能够搭建好词语的建筑吗?
另一方面,休闲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写作对象。且不说任何“闲”不住的人也有休闲状态,就是翻卷不息的波涛、不停地遭到腐蚀的文物、山雨欲来的社会变革、不可逆的时间、随着时代不断被篡改的文本等也有着它们各自的“瞬间”——停顿即休闲。休闲,既休亦闲,似乎无关紧要,小主题甚至非主题反主题,但是,小主题甚至非主题反主题也是一种主题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会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主题。休闲往往化大为小、化整为零、化外为内,处于游击状态,但往往以小胜大、转败为胜,此类作品以车前子为代表。车前子有一种将生存化作修辞的本事,达到了休闲的至境。对于有力的诗歌来说,“写什么”(题材)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写,其实浅薄的人总是弄不明白一个道理:怎样写总是包含着写什么。车前子玩着词语吗?其实是在风云雷电的翻滚中走钢丝,词语的冒险即意义的冒险。
另一位“休闲大师”无疑是柏桦。他的诗与车前子的诗相同又不同,同的是质地,不同的是方向。作为休闲的彻底派,柏桦将“休闲”进化、转化其实是上升为“逸乐”,休闲与逸乐伴生或互生起来——“逸乐”正是一种减法,从而消除了休闲的障碍。柏桦直言:“逸乐作为一种价值观或文学观理应得到人的尊重。”接着转换逸乐的位置:“逸乐是对个体生命的本体论思考:人的生命从来不属于他人,不属于集体,你只是你自己。”这里的“自己”似乎离诗歌更近了一步,你看,柏桦最终轻巧地将布罗斯基的一句话送上诗歌法庭:“美学高于伦理学。”(《2007:我的逸乐观》)
这里,人们难免迷惑:休闲难道不是一种伦理?作为人的一种状态,休闲当然伦理,而且很伦理。同样,“逸乐”也是一种伦理,而且更伦理。休闲和逸乐,皆为现代性内含的布局和意义道场之一,直接为人的服务和灵魂安置提供中转站式的基础保证。问题是,这一切同样为审美和诗歌打开了通道,从而使休闲和逸乐本身通向了审美和诗歌。也就是说,哪里有休闲,哪里就有审美和诗歌。休闲从而成了现代性的一个缺口,这里的“缺口”意即休闲攻破了现代性的整体硬块,成为通向审美和诗歌的通道。大家知道,现代性形成了当今时代的理性和实用的战场,“缺口”一旦形成,人类心灵的空间必会扩大,包括伦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然,休闲也是一种伦理,但是,它是一种审美化的伦理。关键是,只有审美高于伦理时,休闲才真正成为休闲,诗歌中的“休闲体”才会应运而生。
由休闲催生的“美学高于伦理学”不仅呼应了现代性的裂变,直接地接通了诗人的生命体验和个性表达,而且将会带来诗歌性质、主题、题材、风格、语言甚至写作动机、诗人群体等的变化,至少成为观察当代诗歌的一个有效的视角。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休闲不是不要伦理,而是伦理的绕道而行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直面存在和存在本体。典型如近年兴盛于陕西、北京、贵州的《旅馆》诗刊群体最能说明问题。按照我的简单理解,“旅馆”十分贴切、形象,旅馆即休闲。《旅馆》负责人黄土层坦陈:“旅馆主义就是以‘旅’和‘馆’为关键意象构建生命和命运的动静关系,发动一个诗者的真朴气息和锐利思考。所谓‘懒散,春意,方外,喜洋洋’,也只是表象,真正的旅馆主义者的核心最严肃的强盛的存在主义者……旅馆主义本身很松弛,很低调,不打算强制谁,封杀谁。它宽容,懒散,主张草木皆生。”(《旅馆主义是最不像主义的一种主义》)
“闲”,与其相关的有淡、悠、静、轻、小、净、幽、趣而无用等等皆为中国审美境界元素,全诗即实现了诗意的“拢集”,就像海德格尔分析荷尔德林一样:天地神人的融和。真的是闲到了家!最后“青山兀自不动,只管打坐入定”则颇得佛性功夫。处于现代化运动和后现代叙事的夹缝和尘烟里,各种生存压力并置和拥挤,连喘一口气的空隙都难以敞开,我们难得一“闲”,到自然里走一走、看一看、亲一亲。诗人并非质疑现代性,而是主张忙里偷“闲”一下,弄一会“闲”情逸致,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或许能够和平相处。对于亘古如斯的自然还能说什么呢?“不动”“打坐”,这不是寂灭,而是一片生动化机,世界总是处于待定状态,“闲”也就是在此开启了诗人感知世界的天窗。这首诗有力地驳斥了有人将“休闲”看作“个我”“小我”的自成圈套,休闲中的小我其实是大我——休闲中的小我排除功利和现实根绊、精鹜八极、游刃有余、心游万仞,从而超越了自身而与无穷的世界相沟通,可见“闲意思”即大意思。
从写作主体心理学看,作为调节和放松,休闲本身却是诗歌写作的最佳时机,甚至可以说,一首诗不可能不在休闲的状态中产生。鲁迅有个人著名的说法:感情正烈的时候反而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所谓“愤怒出诗人”“最热的时候写诗”只不过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罢,却不符合诗歌写作的实际。只有在休闲状态下,诗人才会有所余裕地进行形上玄思,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同时在词语的森林里冷静地寻觅、掇拾、嫁接,谋篇布局。
休闲的诗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形式的诗,有点语言游戏的意思。其实“形式”或“语言游戏”构成诗歌的必要阶段,尤其对于百年汉诗来说,打破“旧瓶(形式)装新酒(内容)”,必然是“新瓶装新酒”,况且这个“新瓶”还在观摩、描画、制作、实验之中,像一件打磨不尽的玉器,或许永无完美之日。内容只有一个(写什么),而形式却无穷无尽(怎样写),尤其对于汉语诗歌自身所承担的天命而言。休闲不做急就章,草莽章句要不得。尽管“趋时”“载道”派不时地给汉诗套上种种枷锁,仍有一些诗人我行我素、心无旁鹜地摆弄着语言的元件,构建着汉语诗艺的精美建筑,作为汉诗艺术的自觉者、创造者和真正地回到自己的诗歌岗位者,很难说他们中间不会产生未来的大师。
从休闲的内容看,休闲本身即消解,即历史感和宏大叙事的暂时缺席,如语言建筑诗、山水风景诗、个人心境诗、佛性禅境诗、古代宫廷诗、后现代平面诗等多属此类。但是,无意义也是一种意义。如建筑诗以形式反抗内容,带有文本与现实对抗的意味。古代宫廷诗本身即贵族生活的折射。所以这里的“历史感”不是完全没有,只是曲折的反映罢。休闲的诗往往以“不”说“在”,以“空”载“实”,以否定的方式肯定诗歌的意境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