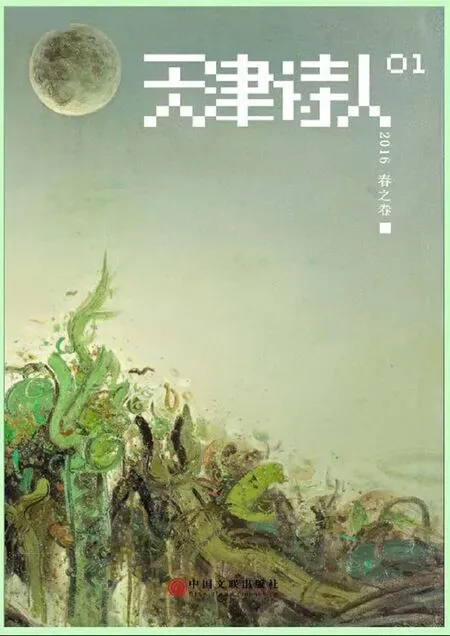诗,何以知天命
李建春
古希腊悲剧由萨提儿剧发展而来。萨提儿,半人半羊神,一个可笑的角色,代表了自然的欲望。按照席勒的理解,萨提儿歌队构成了一个高踞于朝生暮死浮生之上的“理想境界”,表演人的可笑,歌唱神灵的可怕。因此悲剧就是“喜剧之上的喜剧”。但丁把他的史诗命名为《喜剧》,或许也在这个意义上。喜剧是一波三折的进行时,悲剧是高亢的进行时忽然逆转,进入超越之境。在人之上的那个命运,或神,如此可怕,神秘,却是超越的安慰之源。可怕在于,她的非理性,非人间地专横,甚至暴力;神秘在于超出了常人境界;安慰在于若你敬畏顺从了她,你就找到了本然的位置。(这个位置的实质是:虚空。)这是人在蒙昧、骄傲状态下的“知天命”。儒家的知天命,是从十五知学,经过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若你终身在礼法的熏陶中,强学不已,未几也可以达到类似境界(此虚空假有之名,仁义充塞,慎独而能群),乃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过程是快乐渐渐地来,《论语》开篇明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多好啊,对比各种文化对“天命”的理解,方知夫子之道恂为中庸,百姓日用饮食而不知。惜乎这个道,已被现代性全部推倒重来。你把礼法踩在脚下,如何知天命呢?那就进入古希腊的道了:从一场打击开始。对于那特别的少数人,天命会从天而降,众神打断了英雄的高亢,给他以瞎眼为代价,张开了天眼的安宁。现代世界实际是重回蒙昧时代,像埃斯库罗斯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表现的暴力神,普罗米修斯的内脏,每天都要被鹰啄开一次。这个野蛮的景观是真的实现了且翻了无量倍,《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先生作证:那些在大饥荒中饿死的人,相当于内脏遭受了凌迟之刑。诗人张维在他的诗集《母亲的编年》中,反复哀悼了进入凌迟的命运,诗人的祖父,一个地主,(原本是多么崇高的称号,)也是这样饿死的:
从我那年在一朵蘑菇云里出生
我经历的荒诞
比任何恶梦都奇幻险峻
我斗过自己的父亲
也恨过生下来就没有见过面的祖父
因为即使他用肉身喂给了那个饥饿的年代
罪名和血液仍河流一样流下来
这是多么蒙昧、荒诞啊。如果噩梦不得开释,就会凝结于血液。改革开放之后,这位“原罪携带者”又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八十年代,他狂热地写诗。1991年,他编辑出版了海子、骆一禾全集,如果不是同病相怜,慧眼独具,在那个节骨眼上,怎么可能。因此他又对诗起疑,思考人类文明的问题,著有《灵性的时代》和《向》,那么早,那么敏锐。同时经商。“我一个人活成好几个人”,处处都是风口浪尖的人物,“我又为这个时代的欲望建造房屋/把土地炒得越来越烫/使草木无法生长”。参用古希腊人思维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半神”,却有一只手按住了他在世间奔忙的腿,使他成为坐在轮椅上,用艺术修行的人。“善男子。此菩萨及末世众生。证得诸幻灭影像故。尔时便得无方清静。”《圆觉经》诗人的自述,充满了忏悔和幻灭之感:
他们分割我 牵扯我 犹如
五马分尸 沙尘暴
像灵魂在自残在癫狂
直到上苍善意地收起我的双腿
另一个典故:犹太人的祖先雅各伯,在危机关头曾与天使彻夜摔跤,最后赢了,天使临走前捏崴了他的膝盖,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恩典的名字。参照他躁动奇崛的大半生和对上苍的感恩之情,这是吻合的。但何以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历程,竟然站到了两希文化的源头上?这是现代性的结果吗?是一代人宿命吗?无解。
张维的长诗《朗颂,五十述怀》,连同诗集《母亲的编年》,已构成了一个很典型的为了天命而写作的范本。他的语言已具有一种悲剧的品质,崇高,质朴,大理石般质地,在地狱和天恩之间惊人地腾挪却能不着痕迹,用当代口语,又没有日常性的琐碎,不,他实际是写日常的感受,甚至可以说是散文式的,却无一例外地内敛到了命运的维度上,这是接近于古典的风格,是当代汉语出人意料的收获,但也可以说是期待已久的、一个民族的苦难必然的回声。他有一个阿赫玛托娃式的理想:“说出这些苦难的记忆和诗意是我要做的事情”,“要告慰那些至今没有安顿的灵魂,让这个世界安宁”,他负疚于那些死者没有在汉语中得到体面的葬礼,一个安提戈涅式的信念。同时也从自己的身世转向他人的苦难。“我碰到的问题是,苦难转化为文字为何失重了?”这个问题,张志扬也提过,但至今只有张维和他的友人杨键在写作中贯彻。既然是黑暗叙述,失重又何妨,何不一再地调整状态,写!——文革之后,不写诗才是有罪的!何必那么匆忙地转向国家主义。张维也说“我天生就是祖国意义上的爱国者!”原因在于:“我生来就是贵族”,证据是:“虽然我出生在农村,祖父是个地主,父亲是个右派也是个教师,母亲种了一辈子田,” 这是多么有诗意的定位啊。(他并非无据:中国农人历来是士的来源,工、商是无资格的。)让我们张大眼睛,瞧一瞧这人,莫非他真的是当代尼采:“虽然我有时胡子拉碴,衣衫老旧,但我从血液里就有一种使命,保护保存我们民族最高贵最良善最坚贞的品质,在一些昏暗的时刻,做自己民族和时代的眼睛,寻找发现保护蒙难贵族的后裔”,像这种辜鸿铭式的宣言,也只有张维敢发了。想一想他在九十年代初是怎样对待两个天才的遗作。杨键曾把在语言中归来的张维比拟为“门神”:“整个时代物欲第一,门神却有一个心愿:诗人才是这个国家的莲花。要为汉语的天朗气清而守护。”
我认识的张维,是在一个雅集上,神情落寞而友善,扶着轮椅的一只轮子,招待由他出资从全国各地请来的诗友们。中国的贵族我没见过,陀思妥耶夫斯笔下的贵族我倒记得:经过了多少个日夜的颠倒、焦虑、争辩,忽然继承了、或赢了、或不管什么方式弄到手一笔钱,跑到大街上路衢中央喊人赴宴,转眼间挥霍一空,坐在修道院门口。这不是真的。他只是一个中国地主的孙子、右派校长的儿子,从神情到样貌,像极了达摩。我恍然觉得,莫非他真的是达摩化身,连达摩也认为,必须如此化身?必须下到当代中国的深渊中,才能重新达到自己的高度,为他在此世饿死的祖父张学余先生,为好多个陆阿巧,为农民郑艳良、用木工锯锯下自己右腿并咬断了四颗牙齿的人,为从哈佛爱国回来在夹边沟被吃成一副骨架的董坚毅博士,为一个两岁的女孩悦悦、在广东佛山、承受五辆车轮轧过,路人却听不见的血之尖叫,为1959年至今在汉语的大地上跳起、闪耀的黄金和碧玉——而超度!这达摩,在一片肉山酒海、笑语喧天中,行使他的世间法——只是世间法!是化现、权宜之法!而他实际上是在这里:
我已年届五十
朋友们越来越少
我经历的深渊成了自己的高度
站在虞山顶上
看见自己爬过的黑暗时刻
明白在那些恶的时辰里
自己就是一盏灯
一块地下行走的水晶
一部沙尘念诵的《金刚经》
《朗颂,五十述怀》作为一首登高之作,与《望岳》比较的话,也是有一览众山小的气概,杜甫登泰山是想象,张维登虞山是回望。虞山是他家乡的想必不会太高的山。他却已登到自己的年龄之高,生命境界之高。在《母亲的编年》后记中,张维说到随着年龄渐大,他关心的问题已渐小,把精力放在自己家庭和身边小人物的历史命运的书写上。对比他早年只关心人类文明的前途,这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似乎也是共同的趋势。雷平阳在一首诗中写到天底下他只爱他的云南昭通,这个逐渐变小的过程,却耗尽了他一生的精力。五十之年登虞山,开阔之后的回归,着地,意味着一代人的关怀已落到本土和本位上。我们这国家,从企图解放全世界无产者,渐次降到初级阶段等等,实际上在过去一百年中,中国士人谈什么都要以文化批判为借口,全然失了修齐治平的次序,灾难就是这么来的。海子的自杀,何尝不是因为谵妄,张维曾严肃反思过。现在又有了一种谵妄,就是全球化。信息的诱惑,也会使你失去对真实生活的专注。“我经历的深渊成了自己的高度”,但丁要一直下到地狱底部,翻过魔王的身体,才能到达炼狱之山脚下,一步步地升上天堂。《圆觉经》介绍了三个最重要的悟道法门,分别是:奢摩他(止观)、三摩钵提(假观)和禅。张维的这一生,是在假观的范畴之下的,“由起幻故,便能内发大悲轻安”,然后渐次增进,直到幻相永灭。假观还有一个特点:在修的过程中,对真如的感受会“如土长苗”。(注意:这只是比拟,佛教修行是很严肃的。)“大悲”当然是这首诗的主调,“轻安”也表示了:“不再恭候与奉迎/一壶茶在静静叙述”。“如土长苗”:“这深渊等同生死/因此也就无畏生死/十里青山缓缓而来/藏海寺轻轻落在虞山山顶”,这个境界让我由衷地敬畏向往!在现代诗史上,只有冯至的组诗《十四行诗集》在个人经验、历史主题和生命境界上,与张维的《朗颂,五十述怀》恰好构成“对望”,如果展开比较的话,会非常有趣。我这里只略提一下。冯至是在民族危难中,随西南联大迁到云南,回顾他个人的历程和时代的纷纭,他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这组诗虽是回顾,却有一种开来的展望,沉郁的语调中流露出民国时代特有的达观自在。“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以及不祥的“彗星”、“狂风”等,冯至真的准备好了领受吗?历史的真相让人落泪!这个中国的“奇迹”会怎样地开展啊。张维大部分诗的主题,偏偏是七十年来“彗星”和“狂风”的后果,参见《母亲的编年》。除了诗人自己经历的“奇幻险峻”,“五马分尸”,这时代的景象诸如:
我看见人世的大腹便便里盛满饥饿的记忆
他们暴饮暴食 好似复活的饕餮
无非是想在补偿中遗忘
在报复和自残里反复抵达
直到一降痛风刮过身体
他面临的问题是:“这世界 狂躁烦热/因为死者活着/在尘埃和半空游荡/他们没有土地/因而没有语言”。张维的诗之思不经意间又闪了一下,前文提到,他决定用语言给死者安葬,这里,他的思考又进了一步:“他们没有土地/因而没有语言”,为了叙述中国经验,除了解决语言问题,还必须“安土地”!其实安心就是安土地,是这样安的:首先,你要发现自己本善,“明白在那些恶的时辰里/自己就是一盏灯/一块地下行走的水晶”;其次,你要能停下来,“让我在一棵柳树前停下来/让我看见柳暗花明里的故乡”;最后,你还要会流泪,“那一夜 我一个人流泪到天明/泪水滴入深渊/大海瞬间收缩为放生池/在霞光中静静地闪耀”,这就是安土地!在这个三摩钵提式的语言之幻的修行中,大悲轻安,如土长苗,可以一直长到下述的高度:
虞山顶上 蓝天好像一张宴席
我们坐拥万古江山
像古画里的人一样
梅兰竹菊 抱月而醉 拥水而弹
竹林里谁一声长啸 天高地清月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