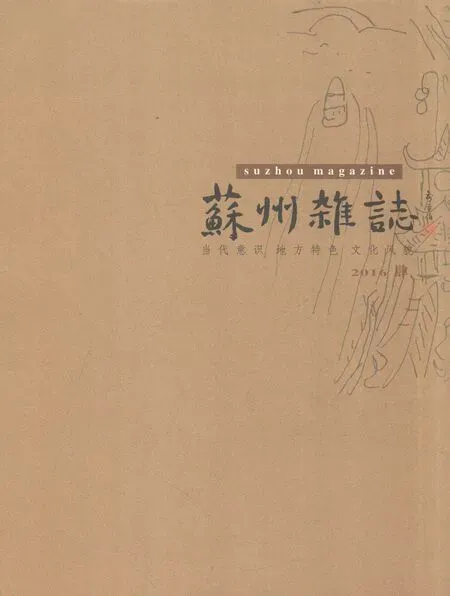从苏州走出去的柯岩
朱子南
从苏州走出去的柯岩
朱子南

说来,柯岩是从苏州走向北京的,由此成就了一位诗人,一位作家。她还是苏州大学的校友。而现在,她走了。早就想写这一篇文章,但心情总是不能平静……
检阅书架上柯岩赠送的《柯岩文集》六卷、《柯岩研究文集》三卷,以及《寻找回来的世界》《癌症≠死亡》等各种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的集子,浓重的茫然涌上心头,各种集子上她的签名手泽仍在,而人走了,走了。人走了,留下的是在文学领域里,由多种体载创作的作品,那是曾经影响过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曾经引发全国热议思考的,而她的报告文学,是连同样以报告文学著名于世的黄宗英也认为是自己强劲的对手。
我想起了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来苏州的情景。她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江浙沪组视察来苏州的,在下榻处给我来了电话约去见面晤谈。我如约去了,离上次见面已过去将近有十年了。但接待的人说,柯岩随视察组出去了,还没有回来。于是,等吧。在休息室里坐坐,又到门口去望望。如此过了大半个小时。去外面视察的人大代表回来了,却没有见到柯岩。可能是听到有嘈杂的人声吧,她从里屋出来了,原来,她并未外出,而是在里屋等我呢。于是她在里屋,我在外屋,互相等着。那时没有手机,联系不方便,便闹了这么个误会,她等得心焦,我也等得心焦。一见面,哈哈一笑,我说她为什么不出来看看,她说这一等可耽误了不少时间,只能长话短说了。本来,她是要同我详细谈谈对近期报告文学创作的看法的,想了解一下苏州以及江苏文坛的情况,还有,那时苏联已经解体,她也想了解民众的反应,毕竟这是一件大事。谈了有半个多小时吧,要吃午饭了,我这才告辞。临别,她送了我苏联解体前思想界出的一本谈苏联学界思想状况的书,还有一张名片,约好了可以随时互通电话。那名片上印了她的5个主要的头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她还有多个头衔,但这名片上的,却已经涵了她主要的社会工作和所从事的主要创作门类:小说、诗歌、报告文学。
我又想起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同柯岩初次见面的情景。1985年11月4日,我收到了她发来的电报。我事先曾去信,约在方便的时候见面对她作一次采访,以写作一篇关于她的报告文学。那时,我已发表了以报告文学作家为写作对象的如黄宗英、陈祖芬、理由、李若冰等的报告文学。现在,她来电约我去上海,说正在上海参加一个诗会。可是,在这个电报里说她在上海参加海洋诗会,并没有说她在上海下榻何处,也没有提及会面的地点,这该从上海这“海”里何处觅柯岩?从近日的报纸上见到消息,说上海电台正举办海洋诗会,于是作推断,上海电台肯定知道来参加诗会的柯岩住于何处。
到了上海,去了电台,电台的人说柯岩住在上海音乐学院招待所。打电话给柯岩,说正在等我,告诉了我住的房号,又关照了一句:不要在招待所门卫处登记,这要在会客室里谈话了,不方便,要我直接进她位于四楼的房间。——她写有著名的儿童诗《“小迷糊”阿姨》,有人见了她也会戏称她为“小迷糊阿姨”的,有时也确实会犯一些迷糊,可现在,又细心了,连怎么进门,都关照好了。
这次谈话,真是谈畅了。我一进门,她就说了,“你提什么问题,我答什么问题。”当然首先谈的是报告文学。她认为,对写作对象的采访,实际上是一种发现,是在原有的素材基础上力求新的发现。这发现,是对人生的发现,而对人生,无法朦胧。她要在采访对象中挖掘出他心灵的春天,对热爱生活的人来说,心里没有冬天。一个文学工作者,只有不断追赶太阳,不断纯洁自己,才能使自己在不断登攀中作出贡献。
其实在生活中缺少的不是美,而是缺少发现。对于柯岩,她不就是要把生活中实实在在存在的美告诉大家么?这或许也是她写作报告文学的契机。而她,热爱生活,心里也确实没有冬天。
我在采访中,提到她是我所在的苏州大学的校友。建国后,高校多次调整,她就读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几经撤并,也并入了苏大。她是在1948年秋从武汉考入社教学院的。在有关柯岩的报道中,都说她原名冯恺,这并不正确,冯恺只是她的曾用名。她原名冯成保。她看到过社教学院印的校友录,“在性别栏里,把我写成男的了,告诉他们改过来吧。”那也是,冯成保,男性的名字,编印校友录的人一时查不到资料,就望名定“性”了。她也确实豪爽,有男儿的气概。曾在苏州市文联工作的段炳果同柯岩在社教学院是都在艺术教育系但不同专业的同学,柯岩在戏剧组,段炳果在美术组。在1985年段炳果同我谈话时还记得,那时的冯成保钥匙圈上挂着的那个银灰色的金属“小炸弹”,居然是她的名章。一个小姑娘用上了炸弹形的图章?她解释:人生就是战斗么!
冯成保变成柯岩,是一个飞跃。她在1949年苏州解放后去了北京,进入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从此开始了她在艺术上新的追求。冯成保也变成了柯岩。她说,“我们中国人把绿绿的小树称为柯,岩呢,是大大的坚硬的石头。岩石上是很难长出树来的,因此,凡是能在岩石上成活的树,它的根须必须透过岩石的缝隙寻找泥土,把根深深地扎入大地。”那“大地”,是人民吧,只有深深地进入到人民中,才能有生命的活力吧?而后,在生活中也有了新的起步,认识了贺敬之。在听贺敬之讲课时,讶异于这位到青艺讲课的曾是《白毛女》的作者是那么年轻。而她作为课代表,也使他们两人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但是,他们的结合,柯岩说来是那么平常,那么没有浪漫,也就是到外面散散步吧,就这么一起走过了近六十年。
这次交谈,真是我问什么她答什么的,包括她的文学观,她的生活历程。
完成了这次采访之后,我写了报告文学《依然追寻、依然追寻——记柯岩》,发表在大型双月刊《女作家》上。但是这篇作品在作为报告文学名家的柯岩看来,并不出色。在发表之前,我曾把文稿寄请柯岩审阅。她回信说:“对这篇文章说点什么呢?写法是新的,材料中也有新的,但是不是介绍得多,发现得少?和以前那篇文章比,我更受益于前者。可能时间太仓促吧?也可能是我谈得太仓促。”还是写报告文学的一个基本要求:要有发现,这发现应该是多元的,而不应仅仅是满足于有这么一点新发现。
柯岩提到了“以前的那篇文章”。那要把时间再往前推了。那是1981年了。那时,我正研究报告文学作家,也同秦兆基先生一起撰写报告文学作家的评论文字。为了了解柯岩走上报告文学创作道路的一些情况,我1981年11月去信,提了5个问题,希望柯岩能作介绍。她那时正病着,1981年大半是在住院治疗,“医生不允许我工作,您的信至今才能给我,迟覆请谅。”看到她回信的开头这一段,该是我有歉意了,打扰了她的休养。在信中,她以小小的字写满了两张纸:
我开始写报告文学,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整整十年被迫与创作绝缘的日子,我急于感受伟大祖国各条战线的呼吸脉搏,除在下边生活之外,我参加了一系列的全国性大会:科学大会、财贸大会、教育大会、科技大会、公安战线积代会……文联全委扩大会、文代会……接触到各条战线的许许多多的实际问题和优秀代表人物。十年来,虽然被揪,被斗,被迫不写只字,但我活着,活在祖国的土地上,活在人民的怀抱里,爱着,恨着,斗争着,在解冻的春天里,这些感情一旦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及人物相撞击,就必然成文。至于,写报告文学而不是写小说,就因为我要把活生生的事实讲给人们听,指给青年看。因此,我的报告文学都是真实的。我怕任何一点失真会在某些本来就悲观失望的青年中更增加思想混乱。因此,我要让我的报告文学都经得起客观实际的检验。……
柯岩以诗化的语言回答了我的问题:她是怎么走上报告文学创作道路的,她对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坚持,她对报告文学功能的定位,她对报告文学作品所注入的爱憎感情……
也有她没有在信中作答的:“您问,‘您的诗人气质是如何作用与影响报告文学写作的?’我想,这是您的,也就是评论家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不应我回答。”她把皮球踢回来了,但这确实是我同秦兆基在写作关于她的报告文学评论时研究、思考的问题。
我把写成的柯岩报告文学评论初稿寄给她审阅,她在1982年6月1日的回信以小字整整写满了5张纸。在信中,她提到了儿童文学创作中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你们用了很大的篇幅谈“童心”、“童趣”……如果我理解得不错,我想你们对我是高度称贺——“不失赤子之心”及“天真的想象”,“坦率的表达”……赤子之心,天真,坦率……都是必需的,但“用孩子的眼光”、“儿童的心理”、——去思考及观察生活,则是远远不够的了。也许因为我同时又是搞儿童文学的,我深知儿童由于年龄特点的局限性及生活经历的浅薄,往往带来他们观察生活及判断事物的幼稚和肤浅,有时——甚至很多时刻,还是片面的及错误的,他们的率真且常常带有缺乏思考的痕迹……因此,不要说写成人世界用儿童的心理及眼光来观察是不应该的、错误的,就是写给孩子看的儿童文学时,也要用成年人的深思熟虑来帮助孩子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事物,丰富他们的想象,并逐步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在儿童文学领域中很严峻的思想斗争之一,就是:是帮助孩子正确及顺利的进入成人世界(当然用的是适合他们年龄特点的艺术手段),还是作者蹲下去说话,把自己降到儿童水平。
因在评论她的报告文学中涉及到关于“童心”的问题引出了她对于儿童文学的一些看法,这对我是一大收获了。柯岩写诗,写儿童文学,写报告文学,我在1985年曾去信问她,在她所从事的这多种文学样式中,哪一种写来最得心应手,哪一种写来则感到有些困难?她在12月6日回信说:
所涉及的各种样式中,我的实践是儿童文学最难,因除了遵循一般艺术创作规律外,还必须遵循儿童的心理学及教育学的原则。儿童越小,其年龄心理差异越大越细微。给较小的孩子写作还需考虑他的辅导者(老师、家长)的心理特点。上乘的儿童文学既要征服儿童还要征服家长,是很难很难的。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的。
她在这一信中还说,“我所涉猎的样式我都喜爱。”我原以为她会说写作报告文学最难,也以为她会最钟爱报告文学。对我这个喜爱并研究报告文学的人,她还是实话实说。
我们修改了这一题为《真诚·诗思·意境——柯岩报告文学的美学评价》的评论,当然也在评论中谈到了她是如何以写诗的才情、诗的意境融化到作品中的。这也是她曾在信中谈到的,诗人的气质是如何作用与影响报告文学写作的这问题,该“是评论家”来回答的。这篇文章在一家大学学报刊发后寄给了她一本。
在与柯岩的交往中——通信、会面,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她的真诚、豪爽。她不像有些成名人物那样,把自己的地址、电话号码保密起来,唯恐人打扰。其实,会有多少无聊的人以攀附为荣呢?她几次来信,都写到了她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要我直接打电话联系或写信寄她家中。或是,“还需要什么,来信。”这十余年来,她几乎都在病中,动手术,休养,但又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忙于各种活动、写作。检阅她的来信,信的开头几乎都是,“因最近心脏病发作,躺了些天,迟复请谅”,或是,“全家都病”,或是“最近身体一直不好,家中还有病人,迟复请谅”。写来极淡定,可那是怎么样的“病中”啊,右肾切除,心脏搭桥!在上海、在苏州的两次见面,也见到她室内的一个小桌子上放满了药瓶,这该是怎么坚持着以病弱之躯还在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在工作着,写作着,接受着采访。应该是我抱歉的去打扰她,而她回信却总是“迟覆为歉”。而1997年2月27日的那封来信,却是为了一件小事:“近来我因身体不好,三年内连续动了两次大手术,与各方均少联系,不知你是否仍在苏州大学任教。昨天托一位老同志打听,才知地址,匆匆写几个字致候。”这一打听,却原来只是为了稿费,“你有一笔稿费寄到我处,现转上。”不多的一笔钱,她都是如此地放在心上,还托人打听了我是否仍在原址。这样的认真,还不让人感动么?何况是在动了两次大手术之后!
柯岩走了,在2011年12月13日那天走了。在柯岩大姐逝世5周年前夕,爰以此文作为纪念了。
——记绍兴市柯岩中心幼儿园 “酷玩柯岩”园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