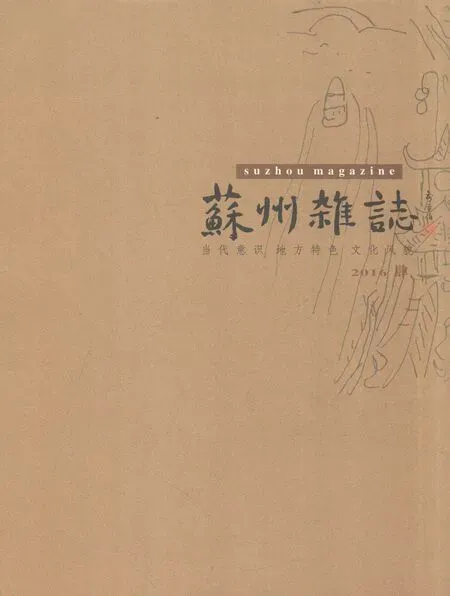梵净山,觉悟者之山
谷之林
梵净山,觉悟者之山
谷之林

万山深处,冬季的表情铅灰阴冷。大山隐在黑暗里,地上没有灯光,天上没有星月光,唯有低处水声喧哗。从长长的廊桥走过时,看见下方河床宽阔,黑墨墨的水流湍急奔泻而下,不舍昼夜。布满河床的乱石滩上溅出银的水光,撞出巨大的响声,越发显出沉默大山荒野深峡的静来。
这河名黑湾河,原本土家在河上拉的是索桥,现在新建的这座新廊桥,黑湾河风雨桥。
这水源自梵净山,今晚就住在梵净山下。
梵净山为武陵山主峰,武陵山脉贯穿黔东、湘西、鄂西和渝东南地区,长度约420千米,是乌江、沅江、澧水的分水岭,主峰梵净山,位于贵州铜仁地区,海拔2500米。地质年龄达14亿年。
我过去从未听说过这座梵净山,却早就知道武陵。是从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得知武陵源这一片亘古神秘莫测之地,王维“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李白“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直接把史书上称为“禹甸之灵境”“赤县之奥区”的武陵山脉,视作世外桃源。“桃花源”从此成为中国人梦中的“伊甸园”。
一路转机,几乎花去一天时间,傍晚才抵达小小的铜仁机场。一道长廊般的平房站台,三角形木屋式拱门。阴霾灰白的天际下,山一浪一浪、一垛一垛。路在千山万岭中延伸,钻入武陵山深深的腹地。接近暮色笼罩下的河口,大山合缝,路从缝中挤出一条通道,甚至是从山肚里钻进钻出。山越来越大越高,从一垛垛连成了一道道、一截截,巍峨成屏、成陵,心里知道,万山都是儿孙,正向武陵深处的最高祖殿汇聚。
就在层峦叠嶂中,住着土家、苗、侗、白、仡佬各族,人在山隙狭窄的谷缝中见缝插针耕作,过着自给自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日子。
当夜入住梵净山麓。山野寂无人声,全体沉入最黑的夜,唯有黑湾河谷大水喧哗,宽河滩水光如黑亮柏油的反光。大水让深山更显寂静深邃。
好像没过多久,窗隙就透出灰白。天是亮了,阴沉沉的。到山前开始飘雨,和平原温润的雨全然不同,是冰冷冰冷的水滴。天色晦暗阴湿,群山隐于雾霭之中。
这样的季节和天气,无人上山。好在缆车照常运行,将徒步需五至六个小时的登山时间,缩短到半小时内。但真正登顶还需继续徒步。
缆车穿云破雾而上。风之手时常搅动原本湿重的灰雾,让它渐渐稀薄透明,群山似隐又露,汪洋大海般的原始森林在脚底,在四周,在头顶朦朦胧胧,时隐时现,如同蒙了一层细纱。一时间,满眼满心,满世界都是它们了。

原本以为,冬季萧瑟,深山气温更低,历经一场场阴雨一夜夜霜浓,恐怕早已是万木凋零。未料还是锦绣之山,虽没有深秋的亮红艳黄,依然是一种老熟的红绿黄褐,犹如熟透的果实将坠未坠,仍在枝头熬着。
天惨白着脸,水珠沙沙拍打玻璃窗。哦,是雪珠!座中一山民说。不是雪吗?众人不信,齐望窗外,果然,撞击玻璃的是细细雪珠。这是今年山里第一次见雪,被我们遇上了。
缆车终点站在2000米的高台之上。一踏上高地就冻得瑟瑟发抖,气温骤降至零下,难怪滴水成冰了。花40元租了件厚厚的黑棉袄套上,拔脚踏上登顶的石阶。
上去要走好多路,天又不好,坐滑竿吧!山民一个劲鼓动。微笑婉谢。路不好走,估计又陡又滑,更不能让人抬着上去了。
水雾冰雪搅在一起。途中,捡了块瓦楞纸举在头顶遮挡密密麻麻降落的雪霰,只听得头顶一片噼啪脆响,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白雾中能见度只达近前,湿漉漉的岩石嵌绿,石缝水亮,数丈外便是灰蒙一片。走着走着,忽有一阵微风轻拂,猛见左侧空濛天幕中影影绰绰显露一柱擎天黑影,再看,即隐。继续上至一平台,右近有土红色的庙宇,仅见海市蜃楼般的轮廓。看得出是新建筑,庙前一道山石残墙倒是旧物,圆门上刻“敕赐承恩寺”几字。穿门入内,各殿上锁,是座空庙,迷雾水汽弥漫其间。前后绕了一圈返回排在第一座的天王殿廊下,凝望前方久之。天雨成霰,除近处残垣尚现,余皆大块昏白。那根天柱刚才已向我透露了踪影,此刻隐在眼前这片充塞天地的厚重白帷之中。当地人说那就是红云金顶。
偶尔,绵白厚帷渐稀变成白纱,它就在正前方透出身形。有时隐约一团随即消失;有时如显影般逐渐清晰,也只让人惊鸿一瞥。更多时间,天边白雾浸润覆盖一切,没天没地当然也没了它,甚至身边的庙群,连同站在殿檐下的我。碰上这样的天气,没有丝毫转机,再待也没用,更不用说继续向上了,更高处只会更阴霾。同伴有的留在缆车站,有的陆续返回,在浓雾湿雨中叫一声:今天啥都见不到了,回吧!钻进雨雾中消失。
山区天无三日晴,入冬更是风霜交加,今天这样的气象根本不可能逆转,返回是对的。这么想着,我仍留在原处继续仰望前方那片白帷。没有理由,没有期盼,天意难测也无需求,仅仅只是再伫立片刻。既来之则安之。
大雾弥天,宇宙犹如洪荒。天地本来无一物了,却在人不经意间不动声色地发动枢机。擎天柱般的红云金顶又开始由浅入深在厚重的白帷中呈现姿影,变幻色泽,由浅灰、浅绛到浅黛,忽隐忽现,若即若离。总有某一刻,蓦地全身兀立于云雾飘渺中。人刚喊一声:看!却又倏忽隐去,如是者二三,峰影隐现,不知为峰抑为云也。
它的真容就是在这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下人窥看见。这座传奇的百米尖峰矗立于2200米高度的崇山峻岭之上,顶尖下劈40多米,以一石拱小桥连接两端,其上各建一殿,左如来、右弥勒。释迦佛寂灭时曾预言弥勒为未来佛,此山为弥勒道场。
奇异的是,它的顷刻一现,也是只身一现。其背景和周下仍是纯白厚重的一片。唯独它瞬间闪现,犹如天地“一指禅”,直指神秘莫测的灰白上穹。九天之外无迹可寻的兜率宫应正是祥云红霓,云蒸霞蔚吧。
白帷重新弥合,纹丝不动。天寒地冻,绝顶阴惨,雪珠绵密,凉湿侵衣。明知此时该返回与同伴们会合,却不知为什么,反而向通往后山的更高处山路望去。往上的路,左通红云金顶,右通老金顶,此时能见度极差,路口都用黄带拦住,上书“路滑危险,封道禁行”。
未假思索,绕过封带,顶风冒雪踏上通往老金顶的石阶。就像当年登京冀边界的灵山主峰一样,我又一次放弃理智和思维,只跟随我的双脚走向更高处。
此去是沿山脊向老金顶而去。高寒之地岩崖累累,虽非寸草不生,也大多是些低矮附崖的灌丛杂桧,偶有一两蓬高不过二三尺的小树。此时,笼罩在密网一般灰雾中的枝枝叶叶根根草草,全成了细细碎碎的冰棱和悉悉索索的雾凇。
山径袒露在天底下,人行其上,便成为一座移动的制高点,餐风饮露,雨雾迷濛。不,这里没有雨水,在这样的高度和温度下,早已是滴水成冰、落雨变雪了。石阶当然成了琉璃道,须步步为营,像太空人初登月球一般。
老金顶,是主峰至高无上之处,传说为燃灯古佛的居所。那里宽谷深壑,奇峰怪崖,皆从绝壑中拔地矗空。灵异谲怪,千姿百态,盘旋罗列,纷至沓来。奇崖怪石如菩萨海会,太子石、蘑菇石、老鹰石、万卷书岩……一层层一叠叠一摞摞,犹如码得整整齐齐的巨型天书,封存着亘古密码。
一片鸿濛中,只见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其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道德经》)
雪霰一直在静静下降。众山之上,无遮无挡,巨风卷起雪粒猛击脸颊,打得脸生疼生疼的,像迎面遭遇一场沙尘暴。手一接触空气,瞬间就冻僵了,几乎拿不住东西。还是勉强掏出手机来拍了张照,不知为何,瞬间大笑。
这就是武陵主峰梵净绝顶啊,普天而降的圣洁的冰珠,透明、无垢、纯净、冰凉。
没有光。凝阴覆合,雾弥水施,冰晶惝恍,天门开合。在这晦暝难明的大混沌中,没有音声,没有思维,没有语言,更无震撼、感动、欣狂、恐惧或孤独之感,只这一刻的相对凝望,竟然与这木石、这天地同体无心。其实,和这些14亿年的高绝大山相比,人不过一微尘,可就在此刻,时间凝固的这一刻,我和它们浑然一体。
独与天地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瞬间等于亿万年。
总是这样,一时心如太古,如众山,如虚空,昏昏蒙蒙如宇宙洪荒,混沌未开,未觉有己,何论思绪、语言和情感?离开幽暗孤峭寒危的极顶,犹如从天界重返人间。途中天色渐亮,下视众山历历分明。
此时万山白雾袅袅似云蒸。十多亿年的亘古山林如从远古走来,撩开面纱,让人一窥堂奥。
有座深持和尚塔悄立于山间一角。他是清朝天庆禅院的创建者。令人感慨的是他对此山的珍惜。虽然筹够了建庙的资金,却与众僧约法:不取山中一木一石,不惊山中一鸟一兽;所有建材,无论大小多少,一律从山外运来。其艰难险阻可以想象。最后,一座矗立在危崖之上、绿海之中的禅院如天降人间,闪耀着人与自然“同体大悲”的佛性之光。
和现今大肆毁山灭林,动辄占地千百亩修建富丽大庙的行为相比,今人缺乏的就是“悲悯”二字。见之一叹再叹。
汪洋大海般的原始森林还未洗尽铅华。虽已入冬季,却依然风华绝代,美不胜收,是一种经霜后熟透的神采,老去的优雅,掩不住的高贵气韵,在自在中任意飘荡。
无边无涯的华美植被覆盖了所有的山体沟壑,偶见白练般的山涧垂挂陡崖,古道掩藏于虬螭结蟠、林木郁苍之中,崇岭之上,但见层峦披锦,云气横天,不见仙梯接斗,万水潜流。
这里是武陵源、桃花源的深邃处,孕育大千世界一切蠢动含灵的母地。绝顶安住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而在远古时期,最早的修行人是苦行僧,他们供奉辟支佛。佛,觉悟者。“俾山川树木,翁静无伤,斯居其地者,咸享平安之福。”“草木者,山川之精华;山川者,一郡之气脉。”古人此等语皆大彻大悟。
梵净山,实乃觉悟者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