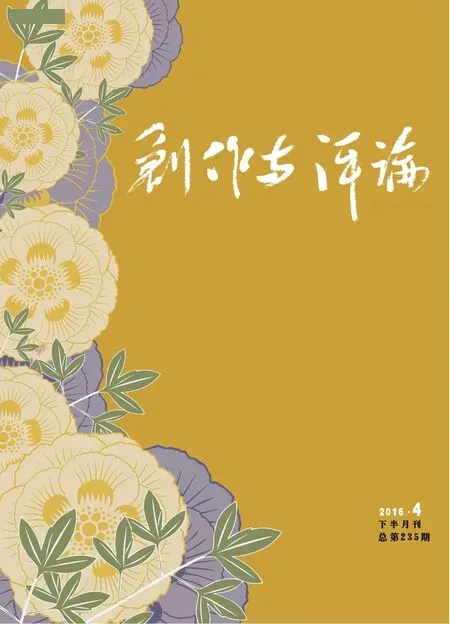王安忆《天香》中的女性生存图景及其价值
○颜敏
王安忆《天香》中的女性生存图景及其价值
○颜敏
写作原本不该有男女之分,但现实是:男性所建构的生活观念、美学观念往往成为时代主潮。在这种境遇中,女性写作就有了“对着说”的整体诉求。然而,正是她们用自己的独特视角,不懈地填补着主流美学尚未关注的空白角隙,巧妙地溶解主流美学中的杂质尘埃,从而使得文学真正能够承担起作为全人类精神家园的使命。王安忆已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似乎比一般的女作家爽朗大气,具有巾帼英雄的气势,但在她的小说世界里,我还是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现代女性试图另辟蹊径、与男性话语对峙的勇气和智慧。在这种“对着说”的女性书写中,王安忆的《天香》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顶点,常被脸谱化的古典女性生存图景,经过她的重构性再现,显现出了更为丰厚、真实而又意味深长的现代性和普世性。
一、天香园:“借”来的女性时空
历代建园,无非是男性权势功名的物化,从皇城到私家园林都承载着绵绵不绝的功名利禄之心。明嘉靖以来的上海,兴建私家园林看似与主流有差异,可依旧是闲散的仕子文人标榜自我、享受富贵心情的行为。天香园的崛起,既与仕途经济有关,也是申家男人们性情喜好的象征。申明世生性张扬,中进士而欲造园,选原本俗艳的桃花又不甘媚俗,故起名为“天香”,园子由民间艺人章师傅精心打造,终成沪上奇观。但这样的精致美丽的园子,可以满足男人们一时的虚荣心,却关不住男人们的尚奇好玩的心,何况上任为官、总得离乡背井。于是乎,这人间奇景,就留给了困守庭院的女人们。女人们,借助这并非出自女人之手,并非为女性而打造的时空而居,在生活的煎熬中慢慢地散逸自己的芬芳,最终将它变成了自己的天地。因此,天香园的主角,就变成了明世的母亲、妻妾、儿媳女儿们。
这一借来的女性时空,其依照的母本显然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大观园为省亲而建,炫耀的是皇权、等级和富贵,一经元妃兰心蕙质的挑点安排,俨然成为了富贵中的女儿国;天香园本是男性趣味的产物,却演绎了闺秀女子的才智和丰采。两者建构方式如出一辙,但大观园的主角是待字闺中的青春儿女,而天香园的主角是已为母妻的妇人们。从女儿到妇人的转换,是意味深长的,显现了王安忆的独特立场。众多论者包括作家本人也都承认,《天香》是向《红楼梦》致敬和挑战的作品,从故事架构、语言表述、人物谱系处处可见《红楼梦》的影子,立意感觉上却另辟蹊径。曹雪芹同情、怜悯并尊重女人,借宝玉之口抛出了“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的惊人之论,却又将女人和女儿作出区别,在他眼里,女孩是可爱的,结了婚的女人却是可憎的。故《红楼梦》里青春儿女最光彩,而婆婆、嫂嫂、夫人们,则多少显得刻板、枯竭,了无生趣。这种“恋童情结”,明显暴露了基于男性本位的视角,未有真正的换位思考。王安忆则有意与《红楼梦》“对着说”,将叙述重心放在嫁入夫家的妇人们身上。未经世事的女孩固然可爱,但用弱小身躯承接家族的重任、经受生活煎熬,活出自我风采的女人才令人赏叹!天香园里的女人在衣食住行的体验经营中,没有了红楼才女们曲高和寡的孤独感,留下了更为真实、鲜活的女性生存图景,于是,大观园里“万艳同悲”“千红一哭”的悲剧性场景转化为天香园里平淡的俗世风景。
显然,王安忆的天香园也会令人联想到《红楼梦》里的天香楼,曹雪芹用隐笔写出了一流女子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结局,她房间的甜香浓艳也被渲染成肉欲的象征;而王安忆的天香园虽是俗世,却非下贱下作之世,女人们只有坦荡荡的痛苦、离别和慰藉,没有偷鸡摸狗与苟且偷生。同样,《天香》也剔除了书写宫廷后院时惯常的勾心斗角的套路,这些在《红楼梦》里也是分量不轻的;如袭人和黛玉、赵姨娘和王熙凤明争暗斗、势不两立;在当下流行的宫廷剧里更是变本加厉。但王安忆策略性地抹平了这些裂缝,如刺绣般将缝隙缀补起来,形成了人性温柔绚烂的画景,所以天香园不是天香楼、大观园,也不是宫廷剧里阴森恐怖的后宫。那些空间看似有强烈的女性特征,但这种女性时空,其实是基于男性视野的戏剧性场景,在起伏不定的时间之流中,它们都会变成废墟尘埃,断壁残垣,成为不堪回首的记忆。而天香园,张扬着那种与生俱来的生命的韧劲和平淡,世代传承,延绵至今。正是这种根植于生活深处的从容和平静,使得借来的女性时空有可能转化为现代女性真正的自我空间,催生像王安忆这样自觉的女性作家。
自然,这种反客为主的策略,多少带有一些后现代的浪漫构思,但王安忆仍能以其朴实、细腻的笔调,将这缕虚空化为实在。带着经历过忧患的过来人的眼光,王安忆将她对现代女性生存空间的沉思化入男性建构的古典楼阁,去反思古典女子自我救赎的可能性,对这种寻找回来的女性时空,我们在感受到希望和慰藉的同时,对作家如何呈现这一救赎过程也必然怀有更大的兴趣。
二、绣阁:绣成自己的房子
西方女权主义一直在争取女性的合法权益,成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被隐喻为寻找一间属于女性自己的房子。①简·奥斯丁的写作只能在客厅里进行,伍尔夫没有办法和长兄们一起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简爱》里的伯莎有了一间自己的阁楼,却已经疯了。王安忆的奇思妙想在于,她既看到了女性要求自我空间的艰难,又认为中国女性有将禁闭的空间转换为自我空间的独特策略。对“绣阁”的这一经典女性生存图景的重写,体现了王安忆对女性化禁锢为自由的过程及策略的深入思考。
绣阁之“绣”意缘起于申明世给儿子柯海建的楠木豪宅。这宅子拔地而起、有些气势凌人,在天性聪慧的儿媳小绸看来,“好像不是给人住的一样”。这意味着个性独立的小绸朦胧中意识到,所谓金屋藏娇,实际不过是将一个个活泼泼的生命变成男人的附属品。果然,丈夫柯海的小妾闵女儿搬进楠木楼,没有得到丈夫深切的爱,还被一大家子所冷落。为了熬过这段岁月,闵女儿在楼上将绣花绷支起来,埋头绣着自己的心事心语,可见“绣”原本起于“怨”。王安忆承认绣与怨的联系,却不相信绣会终于怨,于是,一反古代才子佳人小说里那种具有禁闭意义的绣阁书写,小说赋予了绣阁自由的意味。作者有意让闵女儿将她的绣花绷从楠木楼中搬出,安落在象征着自由自在的白鹤楼上。白鹤楼被形容得如诗如画,自成一体,成为了天香园的奇葩:那里,有来来去去的白鹤盘旋,有同飞同宿的鸳鸯常驻,“四面环窗,虽小却敞亮”②,那里,女人们用“几道屏风,遮挡午前或午后过剧的日光,案上燃几盒香,祛除楼下漫上来的水腥气”③,是一个相对安谧、纯净的女性空间。有意思的是,绣阁还被赋予了“艺术工厂和公共空间”的意味——女人们在那里集会、交流,既孕育这一代代绣艺精湛的女艺人,也共同面对和化解了个人、家族的诸多难题。当然,更重要的是,绣阁还是修心养性之地,女人们投身刺绣之中,才华和怨气都有了寄托之所,于是,恩怨情仇驱尽,平和安定的心境也渐渐生成。一间属于女人自己的房子,就有些意外地在古代闺阁之中出现了。
为了将这种“意外”变成了“情理之中”,王安忆并不是先验性地设定绣阁的自由意味,而是从生活出发,用绵延细密的笔力来呈现这一追求自我的过程,敞开了女人们化解孤寂的艰难过程。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偶尔也会写到庭院女子的孤寂,但在书写女子如何化解孤寂时,不外乎两种方式。或是《金瓶梅》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以排解内心孤寂的方式,或是《红楼梦》里林黛玉式诗书琴画的寄寓、妙玉惜春遁入空门式的逃避。前者太俗,后者过雅。王安忆则在雅俗之间作出了另外的探索。《天香》中有才女,也有资质寻常的女人,甚至有村野之女。但她们并未走向极端,而是回归生活,在生活的磨练中成就并升华自我意识。
《天香》中,小绸是才女,源自书香世家。用情至深的她在丈夫冒然娶妾后,闭门自做璇玑图,将自己的一往情深变成文图的迷宫。这一类璇玑图是曲高和寡的游戏,总归太雅,并非人间女子所应有,带来的也未必是心性的化解、幸福的人生。倒不如寻常机户人家闵女儿的选择。为了打发冗长孤寂的岁月,闵女儿将绣花绷支起来,编织出来的也是密密麻麻的心事,可又是实用暖人的人间之物。小说意味深长地写道:“好像娘早知道女儿出阁要过什么样的日子。”④从娘家带来的针线活,让这个苦命女子有了依托,这便是古典女性在婚姻和情感的困境中,最常见的摆脱方式。在小说看来,选择富有人间味道的刺绣,而不是自言自语的璇玑图,才能使得原本具有囚禁意味的庭院,变成一间女人自己的房子。但是,王安忆也否定了那种过于顺从,没有自我的奴性人格。技艺精巧的闵女儿,在她看来,虽然针法绣法精致,但到底缺少些什么?那就是女人的识见:“不读书的人,张望万物亦不过山是山、水是水,读过书了,便看山不是山,水不是水。”⑤没有书里的乾坤,闵女儿的绣品不过是混沌无度的自然;有了小绸的书意,绣品就成为人文,成了女性发声发音的媒介。
另一位才女希昭听凭命运的召唤,嫁入申家,正情浓意蜜时,丈夫突然离家出走,幸福瞬息消失。像希昭这样保持了自我意识的女子,丈夫的出走足够让她的尊严脸面荡然无存,她只有沉浸在绣画中逃避现实。所幸的是,绣画对她而言,已不仅是化解怨气的途径,也是自我价值的体现。有丈夫相伴的日子里,她也能将男欢女爱暂放一边,学字学画,沉浸于自己的世界。这便是希昭超越婶娘小绸的地方,希昭是心中原本就有乾坤,小绸是被离弃才寻找乾坤。因此,作为女性自我意识隐秘载体的天香园绣,到底是成于希昭,而不是小绸。
将天香园绣发扬光大、远播天下者,则是将自己的头发(情欲)绣成佛像佛经的蕙兰。蕙兰跟希昭小绸相比,少了些书画气息,多了些人间气息。她爽朗直率,敢说敢做,出嫁前就敢于向夫家索求天香园绣的名号,保留了鲜明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的存在使得蕙兰比一般女子更能接受生活的挑战。她的命运与上两代申家女人相比更为惨烈。成亲刚三年,尚未体验到男女之情,丈夫就死了,在清贫中守寡的她,未必没有挣扎徘徊心动,但为了承担家族的生存重任,她以青丝为绣线,以佛像为寄托,用一种超乎寻常的坚韧绣出了一个家族丰盈的未来。更值得敬重的是,由于同情怜悯之心,她设幔将绣艺传授给了和自己一样苦命的乖女、戥子,让天香园绣世代流传下去。
天香园的主角是小绸、希昭、蕙兰,她们是有识见、有自我意识的尘世女子,在遭遇情感困境、婚姻痛楚、生死离别时,她们不是任凭情欲泛滥、选择红杏出墙,而是选择了担当、忍耐,选择了将才情、泪水和心智转化为人间的艺术——绣画、绣佛。所以,面对痛苦、离别和劫难,阁楼里的中国女人没有疯,她们坚韧地活下来,将苦难升华为美,活出了自己的风采。有了这种坚韧和担当,古典的世界才不会完全消失和崩溃,寻找自我的女人才可以一直扶持着走向当代。
三、闺阁钗黛:苦海同舟下的“兄弟”情谊
中国古典小说写男人之间的金兰之义,莫过于《水浒三国》。《三国演义》还带有一点尊卑愚忠在里面,《水浒传》就更多心气相投的豪放了,但古典小说很少探讨女人们之间的情谊。书写的最多是女人们之间的相互践踏,《金瓶梅》里的勾心斗角不用说,就是《红楼梦》也少见亮色,妻妾之间极少和谐的。王熙凤和平儿的关系虽然亲密,但太不平等,平儿始终是奴才。不过,《红楼梦》毕竟还是留下了姐妹情深的空隙,宝钗和湘云,黛玉和宝钗,这些女儿们之间的情谊,为王安忆描写天香园里更为平等相契的同性情谊提供了借鉴,也提供了超越的可能。
王安忆写过《弟兄们》这样的小说,写的是当代女性在家庭之外寻找姐妹淘的喜怒哀乐。那时的王安忆对这种立足于现代女权主义,有点刻意做作的兄弟情谊夹杂嘲讽之意。但当王安忆写古典世界的女性情谊时,却寄托了更多理解的同情。一反人们对于古典世界妻妾妯娌之间争斗反目的叙事基调,呈现了这些被囚禁在庭院里的女人们相惜相怜的一面。
小绸和闵女儿,一妻一妾,原本是对头,但丈夫长期不在,日子长了,究竟还是成了相依为命的姐妹俩,正如小说中镇海媳妇的感叹:“大伯不是在外访山问水,就是忙于制墨,终究还是你们姐妹作伴!”⑥两人之间的情谊,在丈夫娶了第二个小妾之后变得更加坚实,两个苦命人共同抗拒着男权的压迫,令人生出敬意,连丈夫见了她们也自惭形秽,往往落荒而逃。这种妻妾间的情谊被诗化为“双双燕子飞帘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⑦
希昭和小绸的友谊,则是超乎辈分的两个才女之间的相知。最初带些文人相轻的劲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当希昭失去丈夫、小绸上门抚慰时,两人间的隔阂消失了,终于相互赏识、互通有无了。蕙兰和星儿、乖女的友谊,也是同病相怜,甚至婆媳之间在各表心迹之后,也会萌生生死与共的誓约。蕙兰和婆婆之间就是这样,两个丧夫的女人相濡以沫,支撑起其一个风雨飘摇的家族,而家中的男人,死的死,逃的逃,构成了莫大的讽刺。
《天香》中最令人心动的是小绸与镇海媳妇、希昭和蕙兰间的那种情谊。恰如《红楼梦》里薛宝钗和林黛玉,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日常、一个绚烂。或者钗黛本该合一,因为她们代表女性的两个面。像小绸、希昭那样才气逼人、个性十足的非凡女子,终归离不开人间的一点平常心,而镇海媳妇、蕙兰就是人间的平常心。《书香》将《红楼梦》中尚未完全展开的钗黛合一的寓言书写成了一个互补性的友谊结构——林黛玉那样才情绝世的女子必要碰上薛宝钗这样深悟世情的女子才肯降服安定。事实是,对于古代女子而言,不将脱俗的才情个性与随俗顺世的处世态度融合起来,怎么可能求得现实安稳、擦干泪水活下去呢?
同样,王安忆没有凭空设定这种兄弟情谊,小说用极为细腻和朴实的笔调,呈现这些女性化解隔阂的缓慢过程和坎坷心路;当选择将刺绣作为传递、缔造情谊的媒介,则使得《天香》中兄弟情谊的生成格外含蓄古典。因为刺绣既是女人们无限心事的化身,又是她们交流倾诉的秘密语言,只有深谙其道的人才能懂得。小绸和镇海媳妇都是在闵女儿的刺绣中读懂了她的孤独、善良和示好的心。小绸和闵女儿在镇海媳妇的寿衣上绣出的那味鲜艳夺目的当归药料,未尝不是这三人生死与共情谊的隐秘诉说。小绸在闲说希昭绣的竹子时,也慢慢化解了希昭的孤傲与怨恨。蕙兰素淡的字绣在旁人看来过于萧杀,婆婆却边看边流泪,两人就在一绣一看中通了心思,生出些欢喜。
女人间建立起如男人间义胆忠肠的交情,未必是对男性情谊的简单模仿,而是她们在男女欢爱之外寻求寄托的途径与结果。以刺绣作为女人间建立情谊的积极媒介,则体现了现实生活对这种女性情谊的规约性。因为刺绣本是人间之物,既可传情也可谋生,天香园女子做的绣活,不是《百年孤独》里织了又拆拆了又织的裹尸布——那不过是孤独的符号,无益于他人,而是申家女人安身立命、惠及家族的手艺。刺绣在传递彼此心意情怀的同时,也呈现了比男女欢爱更重要的生活根基。意识到了这一点,《天香》里的女人们才能在情爱消逝后不会枯萎、不会陷入彻底的孤寂,而是回归女性世界,凭借同性情谊活出另一种荡气回肠、璀璨自在。
然而,之所以称《天香》里女人们的密切关系为“兄弟”情谊,而不是姐妹情深,仍缘于一些忧虑。一方面,这种以织绣和痛苦作为媒介的闺阁情缘是男权压制的结果,其局限是明显的;我们不难想象,倘若荣宠加身,这种情谊就会淡化甚至消失。另一方面,作者在处理这种关系时的策略值得深思。王安忆有意将之与现代意义上的女同性恋现象相区别,在小说中祛除了女性情谊中暧昧、性感的一面,显示出纯净、淳朴的色质;同时又不自觉地将女子间的感情想象成兄弟前缘的延续⑧,显现了“对着说”时的话语困境。所以《天香》中女人间的情谊,仍有些吊诡的意味。
四、天香:悲悯情怀的灵根再植
很多评论者认为《天香》是在书写上海的地理记忆,但我却觉得她的着力点并不在此。小说名为“天香”,而不是“天香园”,已经说明,小说并非仅写一段上海建筑的历史,而是要寻找这座城市能够存在发展延续的道德根基和心灵归宿,敞开人性的美好。
在王安忆寻找上海这座城市得以发展延续的依据时,跟张爱玲一样发现了上海是以日常生活为底色的。但她书写的女子,不是张爱玲笔下仅供欣赏的“玫瑰”,而是可以硕果累累的“桃花”,不会轻易走向孤独和封闭。《天香》中的女性,小绸、希昭和蕙兰都是沐浴了明代个性解放之风的独立女子,其坚韧、执着中隐含着男子气概,但她们绝非王熙凤一样的泼妇,自私中透着冷酷;也不是曹七巧、白流苏那样过于自我、庸俗的市井女人,生活在唯我独尊的个人世界里。她们都有一颗温和易感的心,能够以牺牲和宽容成就自身以外有情有义的世界。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王安忆对于丑陋和丑恶也有她独特的处理方式。她很少书写彻底的人。或许是读过了当下太多批判社会、言辞激烈的小说,我非常欣赏王安忆的温和。一切伟大的小说一定是宗教的,但中国人的宗教其实就是哀而不伤、百折不挠的精神境界。《天香》里的女人身受苦难,都没有寻死觅活,而是痛定思痛,从头再来。小绸遭遇感情上的至痛,可已为人母的小绸并非日日泣血的林黛玉,就是闭门为情而苦,她也是平平常常过日子的样子。小说写到:“母女俩在太阳地里坐着,丫头的脸贴在母亲膝上,让做娘的掏耳朵。两人都是安怡的表情,不是人们想的孤苦。”⑨《天香》里的男人也未必是西门庆一样的恶俗,他们所做也并非万恶不赦。不过是在情势之下,顺其自然而已,伤害了女人,未尝不是在伤害自己。生性善良温顺的柯海在友人们的怂恿下,因自己的一点冲动娶下了闵女儿,但也为这小户人家的女儿免掉了遁入深宫的命运,算是积功德。而妾娶进家门之后,他不但没有享受到齐人之福,反而深陷在对小绸的愧疚和闵女儿的怜悯中不能自拔,为同时辜负这两个女人而抱恨,不免令人生怜。王安忆不愿将痛苦的原因归诸于制度和人性之恶,相反,她看到了很多误会源于人性的柔软,远非原罪;所以这一切终会化解、冲淡。
对柔软人性所达成的宽宥结局这一过程的书写,王安忆也没有设定戏剧性过强的情节,而是以极为自然的生活叙事来敞开这一点。在王安忆看来,人的天性里本应有的“明德”,会集中体现在某些人身上。如小绸有墨宝、希昭有天涎香,阿施有九尾龟。但这种美好的东西是否能持久,是否能让自己和他人幸福,是要经受生活的千锤百炼的,最终是生活教会我们明了生性,宽容一切,这就是《天香》所持有的一种特别真实的态度。刺绣是最好的隐喻,针针线线,分分秒秒,既是煎熬,也是磨练,心灵的痛苦在刺绣中被呈现、也被化解。《天香》里的女人都曾遭遇过精神上的巨大危机。小绸在听闻丈夫变心的那一瞬间,觉得整个天地都坍塌了。镇海的媳妇在讲述移了心性执意出家的丈夫时,虽是轻描淡写,实是字字泣血。还满脸稚气的希昭在丈夫突然消失时如此惊愕、不知所措,连笑容也来不及抹去。蕙兰满身素缟、从此不着色彩的刺绣中,隐藏了无数心酸和痛楚。但她们最终都在刺绣中释放了痛苦,修炼了心性,不再怨天尤人,而是奋发图强。小绸淡漠了情爱,对柯海不再有恨,生出了几分互尊互重;希昭原本怨恨的心变得平和,容纳了黯然回来的丈夫;素兰在绣佛绣字中抚去孤寂,在设幔传艺中寻求回应。《天香》里的女人们,都是在磨难中懂得了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
天香,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美好。如何在生活历验中捍卫发扬这种美好,将这种美好施与他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命题。当下一些文学作品在极力鞭笞假丑恶时,往往忘记了敞开通向光明的路径,而王安忆的《天香》做到了。在《天香》中,女人们并不是一座供人赏看的园子,在岁月中慢慢颓败;而是慰藉、给予,有不断再生繁衍的能力,如地母般支撑着这个世界,并成就了这个世界。所以《天香》看似为庭院闺阁中的女子做传,实是为现实世界寻求救赎之道。
比起《长恨歌》等作品,王安忆的这部小说得到的回应还不是太多,对之定位也不是特别明晰。但顺着女性写作特有的“对着说”的角度看去,我们或许可以确立它的独特价值。在当代琳琅满目的写作模式中,王安忆通过对古典女性生存图景的生活化呈现,开辟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呈现了她对化解人类生存困境的积极思考。她立足素朴的民间,但在她的笔下,并非神鬼狐怪才是民间,柴米油盐也是民间;她赞美生存的智慧,但在她眼里,并非书画诗文才是智慧,刺绣织补也是智慧。在传奇和不奇之间,作家守候在生活的热潮中,书写人性本然的纯净,既不哗众取宠,也不愤世嫉俗;以平常之心写出了一部绝不平常的好小说。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觉得,王安忆也为自己的写作做了一个总结。在此之后,她可能要歇下来一段时间,因为她以写作告诉了我们,也告诉了她自己如何现世安稳。
注释:
①[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瞿世镜译:《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②③④⑤⑥⑦⑨王安忆:《天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第92页、第61页、第34页、第79页、第79页、第56页。
⑧在与钟红明讨论蕙兰和婆婆的感情时,王安忆更愿意将这种感情看成是兄弟前缘的化身。详见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研究暨史料整理”(项目编号:13CZW08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