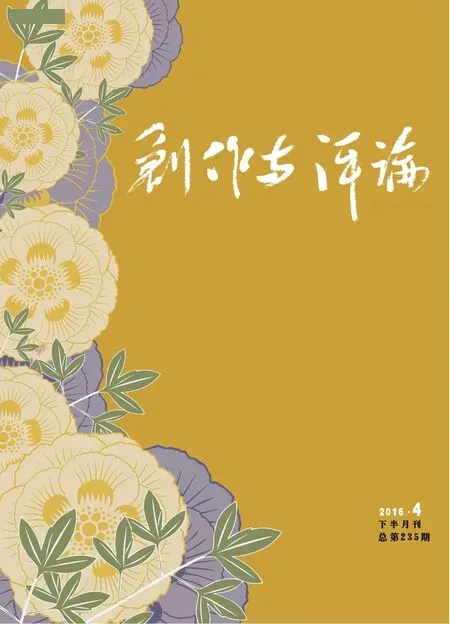由『狂人』到『黑衣人』:『破』与『立』之间的反抗者形象
○武斌斌
由『狂人』到『黑衣人』:『破』与『立』之间的反抗者形象
○武斌斌
“狂人”与“黑衣人”分别是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与《铸剑》中的人物形象,两篇小说分别发表于1918年与1927年,“狂人”是辛亥革命沉寂后的“呐喊者”,而“黑衣人”却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复仇者”。狂人作为启蒙者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其个体的“痊愈”消解了启蒙成功的可能性,而“黑衣人”复仇的决绝最后也变成了狂欢化的表演,奴隶的集体狂欢再次消解了启蒙的意义。提倡反抗的狂人痊愈了,同归于尽的黑衣人被奉上了封建的祭坛。可以说,狂人和黑衣人在启蒙的意义上都是失败者,是悲剧人物的代表。但仔细分辨两个时期鲁迅创作心境的差异,从心理时间上发现鲁迅反抗精神从“立”到“破”的流变,可以体会到先行者不同历史语境下反抗的价值与意义。
一、“改良”而非“破坏”
《狂人日记》作为鲁迅“反抗精神”的发难之作,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令人耳目一新,在新文化运动简化为“文白之争”的僵局里,它的出现的确适时挽救了《新青年》同人“提倡有心,创作无力”的局面,在物理时间上可谓是一阵及时雨,但从作者的主观心理即面对历史语境的心理时间出发,我们会发现《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历史语境中的作用被无形放大了,鲁迅对狂人的描写立足点是在“立”(反抗的呐喊者),即对反抗精神的提倡,而不是在“破”(反抗的行动者)。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曾自言其小说创作的缘起:“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①“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②鲁迅的小说创作缘起并非想把小说抬进“文苑”,而是关注到小说有“熏浸刺提”的能力,主要是希望能借此介绍改良社会的“反抗精神”。介绍“反抗精神”是呐喊者的范畴,狂人正是这样的呐喊者形象,在对《狂人日记》分析之前,应当首先知晓狂人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也就是“反抗精神”表现为何的问题。
《狂人日记》是燃烧封建礼教的熊熊大火,狂人所承载的改良社会的“反抗精神”却早在鲁迅留学日本时期就已埋下了火种,这种反抗精神具体表现为三点:一、对科学求真精神的提倡。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盛言希腊人探寻未知的精神“盖尔时智者,实不仅启上举诸学之端而已,且运其思理,至于精微,冀直解宇宙之元质。”③赞扬科学之桀士“盖仅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④真理的火种只有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的勇士才能盗得。二、对拜伦精神的呼唤。《摩罗诗力说》详细介绍了拜伦之生平及其创作,鲁迅欣赏其“利剑轻舟,无间人神”的勇气。三、对尚武(反抗)精神的提倡。在其早期翻译创作的一篇文言小说《斯巴达之魂》中,鲁迅增译或虚构了一女子形象,张扬此女子激励其夫的故事并不仅仅意欲增加情节的曲折,而更主要地是为了张扬斯巴达之“魂”,此魂为勇为武,其“蛮”与“力”与中国传统社会崇尚文治,以文为美相对立,故此可以看出鲁迅于民族意识中提倡一种“冒险精神”。
但关注《狂人日记》中狂人痊愈的隐喻会发现鲁迅对启蒙的隐忧,这正是其在心理时间上是对历史局势的主观反应。清醒如鲁迅者,由拜伦之“援希腊之独立,而终死于其军中者也”深感“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⑤,由“自意振臂一呼,人必将靡然向之”,而终归乎发出“知自由苗裔之奴,乃果不可猝救有如此也”⑥产生了寂寞的共鸣,“铁屋难破”的事实在主观上动摇了其“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决心。鲁迅只能寄希望于将来,呐喊、呼唤:“救救孩子!”
从心理时间的角度还原《狂人日记》的历史作用并不是为了表现鲁迅的犹疑、怯懦,作为文学书写,不管是呐喊还是复仇,都要看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而《狂人日记》正是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承载起了“反抗者”的内涵:有学者在研究《狂人日记》文言小序+白话日记的体例时曾关注到“叙述者发现某人手稿,经过处理加工以披露的小说结构模式,古今中外均不乏其例”。⑦中国这一体例的显著者即为《红楼梦》,由空空道人的手录而得以传世,西方这一体例主要表现在冒险小说或科幻小说里,体例的渊成只是一种文学书写,在此需要关注的是中西这一体裁模式所承载的思想内涵的相似,即“人”的发现,无论是《红楼梦》中“女子”传奇的发现、“新人”形象的书写,还是西方启蒙主义之后“人”的发现所引起的冒险小说的繁荣,其主旨都表现出一种“冒险(反抗)”精神,此体例与思想的殊途同归以新奇的手法表现了“应时”的精神。但文言小序恰好形成了对白话内容的包围,作者的写作目的也仅仅是为了“供医家研究”而非药到病除,根治疾病。由此也可以发现鲁迅对反抗精神在当时历史语境中提倡的犹疑,故只能“改良”(立)而非“破坏”。此种犹疑正是对启蒙消解的隐忧,这种隐忧不仅表现在《狂人日记》的体例上,而且表现在内容上。
二、炼狱与天国,恐惧与狂欢
从非“破”而为“立”的角度,还原了历史语境中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心态,并不仅仅是因“寂寞”难耐而走向了《新青年》的场域,而是鲁迅扬尚武“反抗”精神的一脉传承。通过将《狂人日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荒唐人的梦》进行比较,可以更加具体而微地从结构与内容方面考查其非“破”实“立”的心境。
鲁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中盛言了陀氏的伟大,但又言明自己“虽然佩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⑧。鲁迅反对用伦勃罗梭式的病理学理论去解释陀氏的作品,切身体会到其“热的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⑨,由此可知过分地用病理学的知识诠释其《狂人日记》也是画蛇添足的。但他不爱的原因为何呢?鲁迅自言主要是中西境遇的不同,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陀氏的忍从可以带着罪业进入天国去修炼天人的功德,而作为中国读者的“我”却深感忍从的“虚伪”与对于同类的“恶”,选择在炼狱停住。
《一个荒唐人的梦》与《狂人日记》虽都为第一人称叙述,但在结构方面却是迥异的。《狂人日记》“文言小序+白话日记”的诸多阐述无论是作“包围论”或“非典型性结构”⑩等都具有合理性,本文着意于以巴赫金的复调——狂欢理论为基础探讨两篇文章结构方式与内容理解的差异。
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狂欢化叙事时曾追述这一叙事模式的根源到西方的“狂欢活动”,而其最主要的形式即为“狂欢节丑角的加冕与随后的废黜”。⑪狂欢是表演出来的游艺性思考,形式上能生成体裁的影响。“交替与转换、死亡与复活的激情”⑫一开始就是双重性的,具有愉快的相对性。根据巴赫金的理论,复调小说最主要的特征为主人公是思想,或思想的人,《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又何尝不是一个思想者呢。但《狂人日记》的狂欢化叙事又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
《狂人日记》“文言小序+白话日记”的形式在结构上形成了“加冕”与“废黜”的模式,但置诸的语境不同,其狂欢的内涵就会形成极大的差异,旧与新,传统与现代,文言与白话,狂人由“觉醒”到“痊愈”,在《新青年》的语境中看来是由“加冕”到“废黜”,但在旧文学的语境中看来却是由“废黜”到“加冕”,此双重形象的模式就不仅仅是“怪诞”与“相对愉悦性”的特征了,而代表的是“传统”与“现代”的截然对立,但关键问题在于鲁迅的情感天平指向哪端呢?指出《狂人日记》的反封建性特征及其破坏作用是后世研究者(包括鲁迅自身)对其先前经验的历史总结,但其创作时的现时心境呢?通过鲁迅的“寂寞”“犹疑”以及上文“非破而实立”的窥探,鲁迅当时的心境恐怕是站在旧文化的立场上犹疑“加冕”的短暂性与虚幻性的。
对比两篇文章的开头更能指陈这种狂欢的差异,进而诠释鲁迅当时的心境:
我是个荒唐的人。他们现在都管我叫疯子。这可是升级了,如果我对他们不是仍然像从前那样荒唐的话。不过我根本不生气,因为眼下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亲爱的人,甚至当他们嘲笑我的时候——我甚至更觉得他们可亲。我自己也会跟他们一起笑,不是笑自己,而是爱他们,如果我看着他们时不是这样难过的话。我难过的是他们不知道真理,而我知道真理。唉,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真理是多么难受啊!但是他们不会理解这一点的。不,他们不会理解。
——《一个荒唐人的梦》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狂人日记》
陀氏笔下的荒唐人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可以说真理与荒唐天生就是二重却一体的,荒唐人因为掌握了真理而“爱”他人,在荒唐人与他人的鸿沟间真理既是阻隔但也是桥梁,真理提供了“爱他们”的可能,“嘲笑”引发的是“觉得他们可亲”,因此陀氏笔下的狂欢形成了一种荒诞但“愉悦”的氛围。鲁迅笔下狂人的觉醒经历了一个邂逅的过程,真理作为可视可见的“他”突然与狂人遇见,瞬间充满了他的灵魂,“狂人”(真理)对自身身份的体认缘自对外界的“恐惧”,更是在他者的窥视里确立了“我怕的有理”的心理认同。两篇文章都揭示了“人”的主题,但“新人”的呈现却在完全不同的氛围中,“愉悦”——“恐惧”,恐怕不仅仅是由于他者态度(嘲弄——迫害)的差异,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主体的情感差异。
正因情感差异的不同,鲁迅笔下的狂人直接进入了“恐惧”体认的确认过程中,即一旦遇到了真理便开始了“梦之危境”;而陀氏笔下的荒唐人却又接受了一次“道德的考验”,对小女孩求助的漠视表达出了对世上一切都绝对冷漠的主题“在我的周围什么都不存在”之后才进入了奔向月球的“梦之幻境”,无论是“梦之危境”的极端“迫害狂体验”还是“梦之幻境”的“月球天堂”体验,实际上都是日常生活或正常人不可能体验的“极端境遇”。“危境”中的狂人经过了与他者无声的心理交锋,有声的质问,发现了历史甚至至亲“吃人”的荒诞性,发出了“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⑬的呐喊。狂人反驳了历史“从来如此,便对吗?”,但正是在历史的考查中却又发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难见真的人”。⑭“梦境危机”以狂人在恐惧中的怀疑始,却以真理对自身的怀疑声中终结,“难见真的人……救救孩子……”,由恐惧笼罩下的觉醒到无力的呐喊,“梦之危境”不是道德的考验而是“恶”的判决。相比之下,陀氏笔下的荒唐人没有历史的因袭,其自我意识的充分性给予了自身宣传人间天堂的自信“……如果说世上有个人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个荒唐鬼,那么,这个人就是我自己……”⑮,“即使这梦永远不可能实现,即使不会有什么天堂(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我还是要去传道。”⑯“幻境”与“危境”,“宗教”与“历史”,在此我们能够了然为什么鲁迅认为陀氏伟大却又不能爱上他的原因了。鲁迅选择的是一条炼狱的道路,宁愿推上峭壁的石头砸下把自己压烂。所以鲁迅式的狂欢不存在道德的考验,只存在“恶”的确认以及面对“恶”的抉择。追溯到历史自我的狂人产生了对“真理”效用的怀疑,鲁迅最终走向了“复仇”变成了《铸剑》中的“黑衣人”,但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对“破”对“复仇”并没有如此的决绝与断然。“我是一个荒唐的人”在明确的自我体认中有愉悦的亮色,而狂人却在恐惧的质疑声中无力呐喊。狂人的犯病是一个短暂的梦,即使在这个“梦境危机”里狂人也不是勇士,所以“救救孩子”的呼唤是“立”的范畴,张扬反抗的精神,呼唤真的人,都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破”与“立”在时间意识里为先破后立,而在情感尺度上,鲁迅的犹疑却更倾向于“立”的张扬,而尚缺乏“破”的决心与勇气。分析“破”与“立”的主旨并非是为了辨析“破”与“立”时序的先后,而是为了还原历史语境中一个反抗者的心态。《狂人日记》站在“新”的立场上为破天荒的作品,站在旧的立场上却是抉择的犹疑,而后者也许更贴近鲁迅当时的情境,非“废黜”而“加冕”,实“加冕”而“废黜”。
三、“奴隶的狂欢”与“狂欢的奴隶”
从《狂人日记》到《铸剑》,从辛亥革命的沉寂到大革命的失败,鲁迅提倡反抗精神的决心逐渐由呐喊的言语者向行动的复仇者过渡。王的废黜并不代表整个封建制度的灭亡,同样个人的“废黜”(狂人的痊愈)也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失败。鲁迅反抗绝望,决心由“立”到“破”,由言语者转变为行动者,但对启蒙消解的隐忧仍如影随形,因为言语者形象下“个人痊愈”的失败也相应地过渡为“集体的狂欢”,启蒙者变成了孤独的“狂欢的奴隶”。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破”亦有其行动的意义。
分析时代语境之中的“破——立”之辨并不是仅仅为了追溯鲁迅的小说创作心态,而是立足于鲁迅自身对“反抗精神”狂欢化解读的警惕与反省,其“破”的指向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即为对“复仇”的犹疑。《铸剑》中黑衣人的成功复仇似乎实现了“废黜”与“加冕”的新生更替,但结尾时众生狂欢的景象,终究使复仇变成了狂欢化的表演,其严肃性被彻底消解,这正是鲁迅对“破”的隐忧所在,在此注意巴赫金追溯西方狂欢节的意义,只是作为特定节日的短暂叛逆,释放被奴役者的压抑情绪,最终只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之一。换句话说,狂欢只是高压氛围的调节剂之一,是一种“刚硬”统治方式的“柔性”补充,其次作为戏谑化的狂欢式表达,废黜的并不是“君主”实体,而只是“奴隶”扮演的“君主”。警惕这一场闹剧的意义在于从头至尾这一狂欢化的文学表达只是一次“奴隶”的狂欢,而复仇者自身或是鲁迅作为启蒙者自身到头来只是众生眼中的一个“狂欢的奴隶”。
早期的鲁迅深受进化论的影响,尚“立”而非“破”,不仅表现了其对反抗精神的传承,而且寄希望于同盟者的出现,至少是“救救孩子”呼声的回响,传统文化语境下“未吃过人的人”作为“群体”的消失,让鲁迅犹疑“立”的效果,张扬个性反抗意识的启蒙者在“立”的层面是看客眼中的闹剧,在“破”的立场上又何尝不是“奴隶”的替代呢。从《狂人日记》开始,在《孤独者》《复仇》《复仇(其二)》《铸剑》《女吊》中鲁迅塑造了一系列复仇者的形象,启蒙知识分子面对庸众陷入了“无物之阵”。鲁迅为敌人活着,从对敌人的憎恶里汲取反抗的力量,其复仇的指向不仅指向了敌人更指向了自我,“破”不仅仅是要成为加冕的王者,而且要指向“狂欢的奴隶”自身,只有在这样清晰的向度里“破”才具有深沉的价值与意义。
《铸剑》中的黑衣人答应与眉尺间联合向“王”复仇,但拒绝“义士”的称呼,明确指出其复仇不是“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⑰的理想化表达,也就是说《铸剑》中的黑衣人不想成为《三侠五义》等传统小说中扶危济贫,反抗强暴的义士,因为“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⑱,这正是其对“立”的犹疑,个人反抗精神终究只会消溺于庸众的无知中,甚至变成“放鬼债的资本”给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功利性指向。拒绝成为义士的黑衣人选择用“破”的方式报仇,此时的黑衣人已经摆脱了“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狂人式失望,而步入了奇诡绚丽的热血式复仇“提起眉尺间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黑衣人决心成为一个真正的“加冕者”,当他看到眉尺间在与王的头斗争中渐出于劣势时毅然决然地自割头颅,跳入水中,眉尺间的头,王的头,黑衣人的头互相经历了一次“废黜——加冕”的仪式,复仇者真正地战胜了“真正的王者”,加冕为“反抗意识”成功的个人者,但这种貌似真正的“革命化”狂欢很快就被消解无遗。小说的结尾经过一夜的商议无果,直到第二次鸡鸣,这才决定了一个最谨慎最妥善的办法,是“只能将三个头骨都和王的身体放在金馆里落葬”⑲成功复仇的黑衣人变成了“祭礼”的“牺牲”,就像猪牛羊一样,甚至自己作为“牺牲”的权利也在众人的狂欢中被彻底消解:
七天之后是落葬的日期,合城很热闹。城里的人民,远处的人民,都奔来瞻仰国王的“大出丧”。天一亮,道上已经挤满了男男女女;中间还夹杂着许多祭桌。……伺候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百姓看她们,她们也看百姓,但哭着。此后是大臣,太监,侏儒等辈,都装着哀戚的颜色,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
复仇在这里变成了一出真正意义上的狂欢,荒谬消解了崇高,嘲讽消解了悲壮,复仇者本身也许直到此时才发现有勇气“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的自我早已被消解或遗忘了,成功加冕的王者在奴隶的狂欢视域下最终也只不过是一个“狂欢的奴隶”罢了,无从“破屋”的鲁迅面对“我的灵魂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已经“憎恶我自己了”。鲁迅的复仇最终指向了自身,但已然远远超越了《狂人日记》中呐喊的狂人形象,因为狂人无力改变事实,只能寄希望于将来,而黑衣人的复仇或者自剖终将唤醒集体。鲁迅虽然停止了小说的写作,但他最终选择了相信群众,由进化论到阶级论。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也由“呐喊者”转变为了“行动者”,而这与作者主观心理由“立”到“破”的转变是密切相关的。由“狂人”到“黑衣人”,不同历史语境下鲁迅的创作心态是差异很大的,从“呐喊者”到“复仇者”,启蒙的隐忧虽然一直困扰着鲁迅,但真的勇士必须直面现实,以“恶”抗“恶”,九死而不悔。
注释:
①②鲁迅:《我怎么作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第527页。
③④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第32页。
⑤⑥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第83-84页。
⑦鲍国华:《“寂寞”“听将令”与“曲笔”——<新青年>视野中的<狂人日记>》,《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⑧⑨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第426页。
⑩王桂妹:《“白话”+“文言”的特别格式——<新青年>语境中的<狂人日记>》,《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
⑪⑫[俄]巴赫金著,刘虎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⑬⑭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第454页。
⑮⑯[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潘同珑译:《陀思妥耶夫斯中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7-558页、第578页。
⑰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896页。
⑱⑲鲁迅:《铸剑》,《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第450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