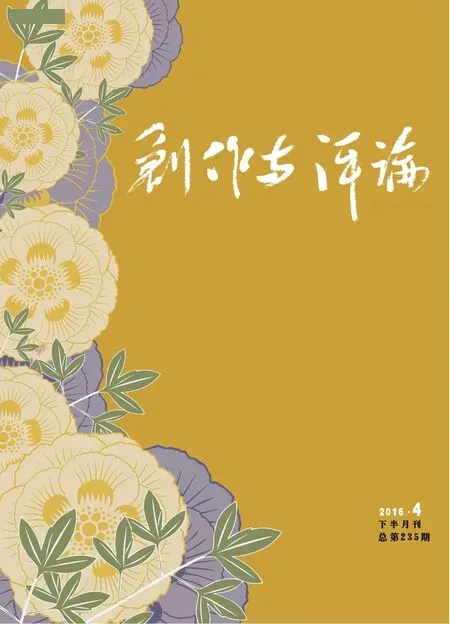现代知识分子的“还乡”叙事
——鲁迅《故乡》与莫言《白狗秋千架》之比较
○瞿心兰杨经建
现代知识分子的“还乡”叙事
——鲁迅《故乡》与莫言《白狗秋千架》之比较
○瞿心兰杨经建
鲁迅的《故乡》是为大家熟知的作品,创作于1921年,讲述作者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重回故地重见旧人的所感所受。1985年,莫言创作了《白狗秋千架》,讲述“我”回到故乡所遇到的诸种人情世态。本文之所以将这两部不同时代的小说放置在一起进行研究,是基于在知识分子“还乡”叙事上,二者既具有某种创作相似性,同时又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
一、对故乡的观照:启蒙立场和民间立场
鲁迅是一名真正的思想革命者,他创作的小说数量不多且篇幅短小,但大多都是惊世骇俗的。鲁迅不屑创作供人们消遣的饭后谈资,他以笔为枪,对黑暗的社会和麻木不仁的国民固执地掷出投枪,经历了“五四”运动的中国,启蒙国民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主题。鲁迅深入地剖析揭露现代中国的社会状况,毫不留情地批判国民劣根性,是现代中国黑夜中的一盏长明灯。
《故乡》是一篇抒情味较浓的作品,这并不是说这篇小说没有鲁迅标志的战斗性。这是一个普通的现代知识分子返乡后又离乡的故事,也是鲁迅的一次精神之旅。鲁迅在这次回乡经历中不断观察着现实的故乡,现实故乡不断地冲击着他,不断引起他的反思。
鲁迅颠覆了中国文学史上传统游子返乡的叙事模式。以往的游子多是怀揣着温情美好的恋乡情节,虽也不乏物是人非、光阴流逝的感伤情调,但这种鲁迅式的对故乡近乎绝望的悲哀,是前所未有的。《故乡》中展现了现代视角下的故乡,是一种“现代的风景”,这种“现代的风景不是美而是不愉快的对象”①。开篇描写作者即将到达故乡时所看到的景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②这不是纯粹的风景,更是作者的心理视界,这种视界透露了作者内心的萧索,并贯穿在他的回乡体验中。瓦楞上枯草断茎当着风抖动的老屋、被浓重封建气息笼罩的杨二嫂和没有了一丝活气的闰土,这些“不愉快的对象”,和作者的情感相互映衬,给人以深深的荒凉绝望的无力感受。
于绝望中诞生希望,是鲁迅的希冀,而实现这份愿望只能通过启民之蒙来实现。曾经的杨二嫂和闰土也是鲜活美好的,那时伊被称为“豆腐西施”,闰土活泼且有灵性,作者离乡的二十多年,他们竟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与其说的自然的变化,不如说是人为的异化。杨二嫂身上笼罩的腐朽气息与故乡封闭的社会环境分不开,长期的不开化和千百年来古老传统和庸俗习俗的熏染,使得她与时代格格不入,作者对杨二嫂的无话可说正如《祝福》中作者对祥林嫂临终“三问”的震惊,都是对封建传统的无声谴责;闰土变成一个合乎规矩的木偶人,多子饥荒,苛捐杂税,兵匪官绅一层层压在他的肩膀上,更可怕的是长久以来的封建等级意识,这些因素的合力彻底摧毁了当年的少年。鲁迅不愿看到闰土“辛苦麻木而生活”,“辛苦麻木”正是当时劳苦群众的生存常态,所以王富仁说“在对闰土的愿望里,鲁迅集中表达了他对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愿望”③。
鲁迅眼中的故乡是和非现代、封建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样的故乡造就了这样慵懒的国民,造就了国民劣根性,这些被“异化”的国民,成为现代中国摆脱尴尬困境的束缚。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提出了“立人”的目标。在对现代社会的绝望中萌生了新生的希望,这是鲁迅特属的“希望”逻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④
不同于鲁迅,莫言的创作体现了一种民间立场,这里的“民间”指的是“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⑤。莫言坚持认为民间写作“就是要求你丢掉知识分子的立场,要你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⑥。他极力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左右,将自己彻底融入民间大地,寻找精神的独立自由。
莫言从来不停留在传统的道德意识层面,也不对民间的人和物做表面的非对即错的判断,张清华曾说:“莫言的意义,正在于他依据人类学的博大与原始的精神对伦理学的冲破。”⑦在《白狗秋千架》中,“我”偶遇旧时女友暖,牵扯出了十几年前暖因被“我”撺掇去荡秋千发生意外而失去右眼的沉痛记忆,“我”又亲睹了她嫁给哑巴后生了三个哑小孩的艰难窘困的生活现状,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愧疚。小说末尾,暖向“我”提出了帮她生一个会说的孩子的请求,她的哀求十分触动人心,令人不忍拒绝。这是一个生活在悲惨境遇中的女人在乞求支撑自己生活下去的希望,这无关贞洁、道德礼仪,或者说所有的道德礼仪在这样的哀求下几乎都是无力的,在这样自由而无拘无束的乡间,人们似乎不能对暖的行为进行简单的是非判断。
莫言的民间立场还体现在他的话语形式上。“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决定了作家们对乡间的叙述采取了知识分子的语言形式,莫言力图突破这种启蒙话语形式,进行彻底的民间狂放式写作。莫言曾经在乡间生活劳作,与普通农民无二,他所获得的丰富农村经验,在他小说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白狗秋千架》有一段关于暑天打高粱叶子的感受描写:“汗水遍身胸口发闷是不必说了,最苦的还是叶子上的细毛与你汗淋淋的皮肤接触。”⑧可以将这种感受描写得如此细致,令人具体可感,非是经历丰富之人是不能做到的。小说人物的语言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和独特性格,要真实地摹写出乡村人,就必须极强的话语捕捉能力和文字表达功底,文中“我”回乡与暖初遇时的一段对话,极其简短,却把暖内心的烦闷和我的窘迫表露无疑。其中暖几句带着粗俗恼怒的话语十分出彩,将一个普通乡村农妇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莫言从不避讳自己是个农村人。他以民间意识观照故土,表达了对故乡的难以言传的悲悯情怀,而不是启蒙视角中那种对故乡的批判性省思。这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是对“五四”启蒙视角的一次调整性反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传统“还乡”叙事的一种现代性回望。
二、何处是故乡:不同景象中的殊途同归
鲁迅在《故乡》中勾画了一个与现实故乡对立的理想故乡。鲁迅笔下的现实故乡,环境萧索、社会闭塞,充斥着旧时代迂腐的封建礼教,人们愚昧无知,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大潮。而鲁迅憧憬的理想故乡,存在于作者记忆中的世界,民风淳朴,人们生活自由和谐,充满着脉脉温情。
童年的回忆是鲁迅写作的一种叙述形式。《故乡》中对童年的回忆在很大程度上经过了他记忆的美化,成为了他心中理想的精神家园,这一现象可以从创作主体的艺术心理来进行解释,艺术家是一个“诗性主体”⑨,而文学创作中作为叙述方式的回忆,因为时间的生成、记忆的淡化与现实生活分离,对往事的获得了远距离的审美观照。这种审美观照使得作家虽依然身处境中,却能做到心于境外,做出超然的审视。在这样的审视下,有关童年的记忆和经验不断地在“回忆”过程中被修改和翻新,“回忆”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幻想的性质。因此,鲁迅童年记忆中的故乡被不断地美化,最终构成了一个与现实故乡完全对立的理想化的故乡。
这样的幻想和美化可以在文本中找出很多端倪。小说的开篇,作者看到萧条的故乡景象时不禁发出疑问:“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随即他又否认:“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是,记忆中的故乡究竟是个什么模样,究竟是怎么个好法,他却又答不出了,“仿佛也就如此”⑩。从这段简短的心理叙述中可见,当鲁迅真正遭遇了现实性的故乡,他心灵构筑的那个世外桃源便渐渐地瓦解了,故乡景象给他的震惊只是这个瓦解过程的开始,真正打破他理想幻境的是成年闰土。回乡见闰土前,作者脑海中浮现的是少年闰土在月下沙地上手捏钢叉刺猹的景象,然而这幅景象是作者未曾亲见的。在小说的描述中,作者和少年闰土的交往实际上仅限于一次新年的短暂时光。作者从闰土的口中得知了很多新奇的事物,仅凭着这些,就在脑海中塑造出了少年英雄闰土。等作者终于再见闰土,时间与现实使他生了残酷的变化,他已然不是作者心中的闰土。这样的现实使作者再也说不出话,内心幻想出的理想故乡在尖锐残酷的现实面前轰然崩塌。
周作人曾直言不讳地说:“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纪念他的故乡,但其实那故乡没有什么可纪念,结果是过去的梦幻为现实的阳光所冲破,只剩下了悲哀。”⑪鲁迅的感受不难理解,故乡不再是旧时的故乡,不是空间的改变,而是时间的推移,毕竟“重回旧地的人不再是那个曾以自己的热情装点那个地方的儿童或少年”⑫。
如果说,《故乡》的魅力在于能够重启人们内心深处重返童年、回归理想故乡的渴望,那么《白狗秋千架》的魅力就在于能够唤起人们直面现实、不忘乡土的勇气。
《白狗秋千架》中莫言所描绘的故乡是异常现实的,没有鲁迅的那种幻想与美化。莫言在叙述他的故乡时态度客观近乎冷峻而酷烈,然而他的深切正在于此:在极端的冷峻之中升腾出了一种悲悯意识,“这美掠过我们苦寂的意识王国,摇落了一切空中楼阁,犹如一只惊夜的夜枭,叫出了乡民几个世纪的悲苦”⑬。莫言近乎冷酷的故事叙述得云淡风轻,却在仔细品味后令人心惊。十年前“我”和暖,两人一起荡秋千,结果绳子断了,槐刺扎进了暖的右眼,在此之前,莫言有句话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秋千架,默立在月光下,阴森森,像个鬼门关”⑭,一种冷峻的伤痛感早已弥漫开来。秋千架是暖悲剧命运的开始,也是“我”愧疚、产生赎罪心理的根源。不过在文本中,对这个“事故”的描述结束地十分突兀,再也没有了下文。读者只知道暖嫁了个哑巴,“我”上了大学,直至“我”十年后回乡,中间存在着大量的空白,这是作者故意留下的想象而又不忍去想象的。
莫言惯用这种笔法,他总是力求以最客观的叙述方式来还原现实场景,但是读者又能从冷峻的表象下感受到潜藏的情感,《白狗秋千架》中一段“复调”结构的叙述很能体现这一特征。当解放军经过时,学生宣传队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地迎接,这种场景放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十分常见,在暖唱着《看到你们格外亲》的歌声中,部队的汽车正手忙脚乱地涉水过河,可谓是乱糟糟。在这样毫无秩序的场面下,却穿插着暖歌唱的红歌片段,其产生的效果相当复杂,它间接地体现了莫言的某种反讽式叙事情调。这样的场面、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画外音,不得不说莫言是用心良苦的。
对于鲁迅和莫言来说或,理想故乡和现实故乡似乎是相反的意象,但在他们的精神期盼上却是殊途同归。
在鲁迅的回忆中,故乡景色如画,他和少年闰土交往的点滴他都铭记于心,让他回味无穷,在这里少年儿童纯真美好的本质得到了充分的彰显。鲁迅向人们袒露了心底里最柔软的美好,他和闰土雪地里捕鸟的经历、那些闰土告诉他的他所不知道的新奇世界都是如此的温馨美丽。然而记忆有多柔软美好,现实就有多残酷丑陋,这种美好正是在与现实对比的反差中产生的。鲁迅在记忆中构建他理想故乡的原由何在?“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是在自己不同的生活感受的差异中产生出来的,是从对现实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满中产生出来的。”⑮一言概之,在与故乡残酷现实对比的巨大落差中,鲁迅以回忆的方式来讴歌人性的善良与纯真,热切地呼唤着心中的精神家园和理想社会的重塑。
莫言与鲁迅处在不同的时代,因而他们作品的面貌必然也是不同的,莫言与其他新时期的作家,如残雪、苏童等,都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些美学原则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不同的体现,人们说到莫言,总是不经意给他贴上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而在对《白狗秋千架》的研究中,我们需提起——自然主义。莫言受到过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的影响,这在他作品的精神和形式上均有体现。于精神上,莫言后来的小说中都体现了一个“种”的问题,如《红高粱》《丰乳肥臀》,“我爷爷”“我奶奶”⑯身上有着红高粱般的血样的野性,上官鲁氏演绎了一首自然母性之歌,他们都是野生自然的“纯种”,而“纯种”在血脉的传承中逐渐杂化和退化了,在莫言小说中能读到野生与驯化之间的对立。莫言显然是偏向前者的。再反过来看《白狗秋千架》,女主人公暖虽遭受厄运,但与命运做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挣扎反抗,具有极强的生命韧性,她与以上的人物一样,都是自然的、野生的,同样受到了莫言的赞颂,可以说,自然主义的精神一直贯穿在他的创作中。精神为骨,形式为肉,莫言的自然主义精神必然不会让他的写作产生鲁迅式的美化,他笔下的故乡也必然是冷峻的、现实的。
与莫言“野生—驯化”的对立对应,我们可以在《故乡》中找到“儿童—成人”的对立,少年的闰土纯真善良、活泼可爱,未被污染的心灵使得他与作者亲密无间,而成年后的闰土使作者内心悲凉,由这可延伸到《故乡》中理想故乡和现实故乡的对立。前者已经逝去,在后者的反衬下显得尤为珍贵美好,这是鲁迅渴望的精神故乡。鲁迅在回忆中寻找社会的良药,这副良药就是人的本真,莫言则在追溯民族文化心理的过程中看到了自然人性的光芒。作为返乡者,他们对故土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对故乡的变化必定有着敏锐的嗅觉,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牵动他们的神经,而作为知识分子的返乡者,他们不可能对这些变化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已经跳脱出故乡多年。他们的认知使他们可以透过这些变化看到某些事实,这些事实使他们思考甚至苦闷,自觉或不自觉,他们心中会产生一些期盼,一些设想。鲁迅的期盼设想寄托在美化的回忆中,莫言的期盼设想寄托在张狂的自然中,理想故乡和现实故乡似乎是相反的意象,实则殊途同归。
三、近乡情更惑:无法确定的身份认同
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心中,故土难离,故乡是“根”,是游子漂泊在外时情感的寄托地,也是人生失意时的庇护所。古时不少文人墨客,离乡时踌躇满志,遇到挫折后总会发出“不如归去”的感慨。故乡拥有最为宽厚博爱的胸怀,静静地等待着和接纳着外出的游子们,因此人们总是对故乡有着深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进入现代后,古人的返乡叙述传统逐渐被打破,故乡仍是作家们创作时难以逃避的话题,但由于时代的巨大变化以及作家们心境的转变,“故乡”这个词汇的含义在作家们的心中变得复杂得多。通常的情况是,作家们在外漂泊多年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后,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完全融入故乡,而是与故乡、故乡人之间产生了一层难以言说的隔膜,身处故乡但却产生了“异乡人”的感受,这是现代以来知识分子返乡后普遍的伤痛。
对鲁迅来说,故乡给他的感受是十分复杂的。在鲁迅的童年记忆中,故乡既给了他欢乐美好的体验,同时又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愤懑和痛苦,那些好的和不好的记忆共同织成了一张大网,一方面引诱他进入,另一方面又逼迫他逃离。鲁迅这种对故乡的复杂心理,致使他对回忆中美好的一面极力美化,但是那些灰暗的经历又令他心有余悸,对故乡始终无法达到心理上的认同。
鲁迅年少时对故乡的不认同感是他与故乡产生隔阂的开始,那时的他年少气盛、踌躇满志,毅然踏上了求学之路,开始了漫长的漂泊旅程。他在日本受到了现代教育,经历了著名的“幻灯片事件”,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处于“启蒙者”的位置。在《呐喊》的自序中,鲁迅讲述了一个“铁屋子寓言”,并寄寓改造国民性的愿望。在这个寓言中,铁屋子和熟睡的人即故乡和国民是一体的,鲁迅虽处于故乡之中实际上却是个“异乡人”的身份。
鲁迅一开始就义无反顾地背叛了故乡,他离乡二十余年,漂泊二十余年,无论是遭遇到什么,也不曾有回乡的打算,只是把回乡当成永远离开故乡的一个过程,“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⑰。可以说,鲁迅年少时期对故乡的不认同已经扩大成了启蒙者与故乡的对立,演变成了一种无法消除的隔阂感和无所归依的漂泊感,《故乡》揭示了“一种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的对立关系”。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故乡成了一种无法返回的地方,也就是说故乡变成了他乡”⑱。
莫言创造了“高密东北乡”这片斑斓的文学土地,他无疑是爱着他的故乡的。他也恨他的故乡,饥饿、伤痛、孤独几乎充斥了他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他曾说:“十五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⑲他甚至连鲁迅那一些关于故乡的美好体验都没有,只有厌恶和仇恨,所以他必然会选择逃离,进兵营是一个开始,之后他拿起笔写作也是为了继续远离故乡。在莫言的笔下,充满了各色的“离乡者”形象,他们或是为了逃避饥饿,或是为了躲避伤害,或是为了追求理想、爱情而离开故乡,这些人物叠加起来似乎隐现着一个曾经的莫言。然而与鲁迅不同的是,他没能彻底背叛他的故乡,他从一个“反叛者”最终变成了一个“皈依者”。在摆脱了故乡给他的痛苦之后,他陶醉于都市带给他的衣食温饱的生活,但陶醉只是短暂的,他原以为离开故乡就能彻底离开苦难,却没想到在那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都市里面潜藏着更深的悲哀与无奈,他“感受到一种无家可归的痛苦,一种无可抑制的对精神故乡的渴求。”⑳他开始回忆故乡,思考故乡,找到了那支撑起他精神之根的宝贵所在,他一步步、不自觉地重新回到了故乡,“到了一九八四年冬天,在一篇题为《白狗秋千架》的小说里,我第一次在小说中写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五个字,第一次有意识地对故乡认同。”㉑
《白狗秋千架》是莫言回归故乡的开始,如同一个犯错归家的孩童,他对故乡的神经是敏感而纤细的,让人觉得过于小心翼翼。比如在与暖相认的场景中,“我”的表现十分耐人寻味,“发窘”“谴责自己的迟钝”“嗫嚅”这些神情和心理隐藏着我内心的激动和不安。读者可以想象到“我”的神情和语气,“我”急切而小心翼翼地想得到暖的回应和承认,其实这不仅仅是寻求暖的确证,更是一个游子迫切想要得到故乡对自己的身份确证。莫言和他的故乡土地曾经是融为一体的,但即使是他,在离乡多年归来之后也免不了产生“陌生”的尴尬,也免不了与故乡产生隔阂,但因为他的忐忑,他不能如鲁迅那般直接洒脱。在《白狗秋千架》中,这种隔阂感不如《故乡》中表现得那般强烈,但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即使只通过牛仔裤、糖果、折叠伞这些细微的事物。
其实《白狗秋千架》的故事更具有现实指向性,现今城市文明快速发展,农村被挤入了发展的边缘地带。农村与城市关系的矛盾已经微妙地转化到了小说中,内化成了“我”与故乡的隔阂。暖一开始对“我”尖酸的嘲讽。白狗对我的窥探,雨中老人对我的蔑视,故乡人对我所穿的牛仔裤的偏见,这都显示了作者对农村被置于时代大潮末流的愤懑心理,进而促成了作为还乡人“我”内心的愧疚不安,“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去修补这些裂痕,但是心理上的隔阂是怎样都填补不了的,这令作者悲伤却也无可奈何。
莫言对他的故乡既爱且恨,故乡是他不可逃脱的宿命地,故乡的一切已经丝丝缕缕渗入他的血脉,他的全身无一处不与故乡有着紧密联系,他只是一个回归故乡的游子,正如故乡包容着他一样,他也包容着自己的故乡。尽管他“皈依”了故乡,但隔阂感、漂泊无依感早已延续在了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返乡体验中,显然莫言也不能例外。身处其中而不能融入,求而不得,他只能把自己的精神家园寄托在“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天地里,故乡本身对莫言而言,“那个地方会永远存在下去”,但他的精神“却注定了会飘来荡去”。㉒
中国有一句古话:父母在,不远游。这种观念是与中国几千年的宗法制度血肉相连的。进入近现代,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轰开了封建宗法社会的堡垒,西方文明的强制输入,中国人的古老观念艰难地进行着带血的现代化蜕变,西方现代价值观动摇了知识分子对故土的“愚忠”,他们纷纷离开故乡,向外探求救国之道,加之自然经济瓦解,都市文明迅速发展,城市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有志青年不断聚拢。这些人身上带着农村的刻印无法摆脱,所以他们与都市的物欲横流和畸形繁荣格格不入,而在经受了现代文明熏陶之后,当他们返回故乡,却发现自己难以再次融入了,身处故乡却是“异乡人”。由鲁迅到莫言,我们发现知识分子“还乡”产生的漂泊感一直由现代延续至今,时代不断向前推进,“异乡人”感受也会产生差异,这种差异是“现代性”的差异,是现代人对故乡的重新打量和估价。
总之,“五四”以来自鲁迅开创了“离乡—返乡—离乡”的叙述模式,并以知识分子的姿态来审视故乡,20世纪的返乡文学就再也绕不开对“故乡”的描写和反思。有鉴于此,对莫言的《白狗秋千架》与鲁迅的《故乡》进行比较研究,能够对“五四”以来文学中故乡叙事,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文版作者序)》,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页。
②⑩⑰鲁迅:《鲁迅经典文集·鲁迅小说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③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
④裴多菲的著名评句,鲁迅将它引用在散文诗《希望》中。
⑤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页。
⑥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⑦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⑧⑭莫言:《莫言文集·白狗秋千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第249页。
⑨“诗性主体”引自仇敏:《论诗性主体》,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文艺学博士学位论文。
⑪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版,第65页。
⑫[法]普鲁斯特著,李恒基、徐继曾等译:《追忆逝水年华(安德烈·莫罗亚序)》,译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⑬孙郁:《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⑮王富仁:《精神“故乡”的失落——鲁迅<故乡>赏析》,《语文教学通讯》2000年第4期。
⑯莫言:《莫言文集·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⑱张慧瑜:《异乡人与“少年故乡”的位置——对鲁迅<故乡>的重读》,《粤海风》2009年第5期。
⑲㉑㉒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⑳莫言:《超越故乡》,《写给父亲的信》,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