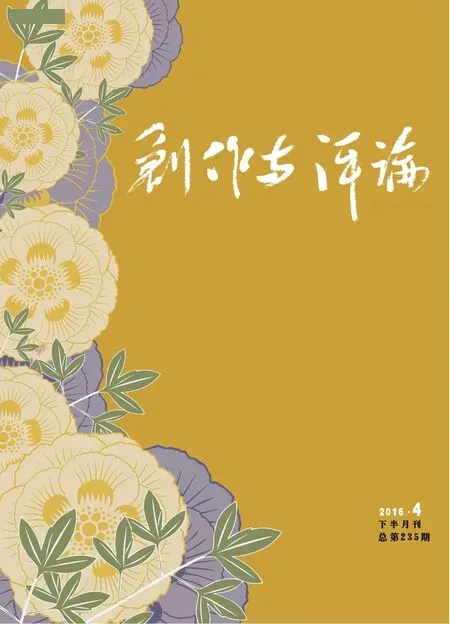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海洋书写
○王泉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海洋书写
○王泉
台湾岛形似一枚树叶,漂浮在太平洋上,因台湾海峡的阻隔,台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岛。海成为其主要的自然地理景观,让这里的人们浸染在海上升明月的空旷之美中,文人更是信手拈来,到达了“物与神游”①的境界。1990年代以来,台湾海洋散文的勃兴,预示了海洋时代的到来。蒋勋、林清玄、杨牧、廖鸿基、简媜、席慕蓉等作家的散文在书写海洋时把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博大的海洋意识之中,形成了开阖自如的艺术世界。
一、书写海洋景观与传统文化
“柔软的水承天载地的伟力,富于哲理意味,其倾注于大壑之中造成海洋,海洋生成的神话的象征意义,在先民的生活中反复运用,同陆地神话一样,升华出丰富的哲学思想,分别成为儒道释诸学说体系的构成部分。”②海洋在有形与无形之中给予人类想象的空间,因此形成了海洋文化的多样性。台湾作家身处台湾岛,自觉把周围的海洋当成人生成长的坐标,在感悟海洋文化中认同传统文化。
美学家蒋勋在诗歌《愿》中这样表达了自己对于海的感悟:“如果你是岛屿/我愿是怀抱你的海洋/如果你张起了船帆/我便是轻轻吹动的海浪。”③海洋的博大与无私奉献已经沁入到他的血脉之中,成为人生的航标。他的散文《望安即事》写海中干旱的小岛,有对古宅被冷落的唏嘘,更有对求偶云雀的特技表演的感叹,对生命奇迹的发现,也是对美的发现。
对于海,林清玄有着独特的体悟:“我们看待海的事物——包括海的本身、海流、海浪、礁石、贝壳、珊瑚,乃至海边的一粒沙——重要的不是知道它历经多少时间,而是能否在其中听到一些海的消息。”④他把从海边带回来的珊瑚礁养在淡水里,结果长出了水母。即使后来水母死了,但能见到海洋的石头复活的奇迹,也算一段因缘。他试图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东西,只要存在过,就有机会重发光芒。作家借水母的自生自灭,道出了人生无常、随遇而安的佛家思想。
杨牧的《设定一个起点》从不同的角度看海洋,给予海洋时空意义上的观照。“现在和过去重叠,海水融为一体,潮汐随月阴晴起落,发出的石子散布滩上,累积,向前无限延长;风从四方吹到,起点和终点同时存在于我自己的心,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超越了航海人指北针的限定。”⑤“潮汐”“石子”和“风”与海洋时刻相伴,自我的想象也在这一空间中得到了无限膨胀。海洋不只是外在的存在,内心的真实跨越了时空的限制,人生便以海洋为参照物,获得了自由的发展。
小野的《海星的故乡》中澎湖的西卫海滩上成群结队的海星给予人类生命的启迪。20多年间的台湾人“就像潮间带的动物,用自己的肉足或螺壳存活下来”。⑥无论世事如何变化,台湾人总能从时代的潮起潮落中找到自己的落脚点,让生命之火延传。因此,这里的“海星”既是大自然本色的生命,又象征着台湾人自强不息奋斗的轨迹。李鼎的《冬天要去夏天去过的地方》写在小岛兰屿的冒险经历,在暴风雨中走进山洞,“听见海浪用一种安静的方式在周围环绕,更让我全身舒缓下来的是,我听见自己身体里面的心跳,在大自然产生的洞中,有着无法想象的巨大共鸣。”⑦“空”并非无,而是让人无法满足的自然之力的诱惑。大自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它告诉了人存在的空间,并让人在充分释放自我中获得自由。
李岗的《万里渔港》写海边小渔村的富足及当年拍电影《条子阿不拉》的热闹,流露出怀旧情绪。李明相的《我的柴山秘密基地》则用流浪者的心态去寻找少为人知的悠闲。无边无际的海洋与夕阳的余晖交会出动人的景色,让读者陶醉于自然美景中无法自拔。褚士莹的《东屿坪——台湾的复活岛》,突出了在美丽与萧条的奇异组合的环境中,人与自然共生的哲学意蕴。这契合了佛家“众生平等”的理念,表现了对大自然的敬畏。
廖鸿基的海洋散文在台湾别具一格,这与他的职业密不可分。“他以中年之身退出政界返回故乡当渔民,与渔民们一起出海捕鱼,是寄托了人生极高的理想。”⑧他从1990年代至今已创作出版了近百万字的散文作品。他在新世纪创作的《领土出航》描写了“单调、清冷、寂寞”的船员生活。这不是一部简单的航海志,而是以47天航程中的故事和个人潜意识中的隐痛折射出航海人心中的梦想,带给读者不一样的体验。在他的笔下,不停变幻的海洋环境,给人不一样的审美体验。“亚丁湾,如镶进陆块的一只漏斗。航入湾里,仿如跨进陆地门槛:那啜泣嚎啸的海上风雨,那与风作浪撼摇船只的手中,都被湾口那道无形的门扉拦挡在外。”⑨海洋与陆地的联合,创造出亚丁湾的独特美,也成就了航运的奇迹,自然的美与航海文明组合出人生的启示录。有评论者认为:“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廖鸿基再次提出了‘海运’——如血脉的流通作为岛屿生机之启示:岛屿所意味的绝不仅是土地本身,而是一方蕴含流动生机的领土/梦土,‘海运’所践履的是我们最为深情的‘领土’之梦,于是,以‘领土’之名,‘海运’启程。”⑩
海上航行离不开漂泊之苦,《领土出航》把航海人在时间中的煎熬之苦展示在读者面前:“一旦离岸,失去节拍的日子将无限延伸回头的距离,让自己成为一只背离花蕊的蜜蜂,再如何擅飞的翅膀,再热烈的胸膛,伸得再长的手臂,舰尖孜孜犁浪如在切割,船桨轻易地便绞断了所有和陆地的牵连。一旦离岸,时间和距离已无法估算。”⑪这样的漂泊是对意志的考验,在对时空的思考中凸显生存之道。很显然,这不同于无名氏在《海艳》和《金色的蛇夜》中的海洋书写。无名氏着眼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人性的复杂多变,而廖鸿基书写的是人在海洋面前的命运。在无名氏的笔下,海显得神秘而多情。“有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并不像铁链连着铁链,深密联系;常常的,那倒似北极黑暗海上的碎冰块,狂风冲过,冰块碰在一起了,新风新浪卷来,黑暗中,冰块又离开了。一切是斩绝、冷酷、黑暗无情。”⑫黑暗中的“冰块”象征的是人际关系的冷漠和生活中突然而至的厄运。无名氏以海况写出了世事变迁中的人情冷暖,在爱与恨、聚与散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浪漫的情思。而廖鸿基以客观写实之笔书写海员的生活,但没有流水账似的枯燥乏味。他从细节出发,阐释着“海味”人生的境界。
他在红海上寻找红海之所以“红”的原因,感觉到了穷途末路之时,才解开了对“红”的困惑。“两岸黄土山丘环抱,海底、海面平整空旷。隐约,岸线有些黄褐色山影倒映在蓝色的湾里,忽然,明白了!”⑬这才是航海者的发现,无不透露出人生的境界之美。人的一生光阴在不经意间流逝,寻找与发现的美妙往往在身心疲惫之时。“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⑭王国维借用辛弃疾之语道出了“无我之境”的美妙。这在廖鸿基的散文中得到了演绎。那便是,人与海洋在混沌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海洋的广阔无垠象征着人的冥想的无边无际,人类的海上冒险则给海洋平添了人文的景观。海洋赋予人类生命的源泉,人类的活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明,世界地理的大发现正是航海文明的成果。
他这样写上岸后的感觉:“刻意放空自己,放弃感觉,什么都无所谓。街灯于是朦胧、行人无魂、车影漂浮…然而,思想和回忆交错如潮汐涨退,一旦动念,两个世界立刻又壁垒分明。”⑮这里刻画的是航海人在长期漂泊后无法“上岸”的感觉,一种恍若隔世的深切体会。想当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正是缘于他对海洋和外面世界的心驰神往。可见,好奇心激发了人类走向海洋的梦想,也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
总的来看,《领土出航》延续了廖鸿基自己在《鲸生鲸世》《来自深海》《漂岛——一趟大洋记述》等作品的纪实风格与自传色彩,把人生的历练与海洋书写融合在一起,体现出海洋人乐观向上与豁达的胸怀,丰富了海洋书写的生态主义内涵。这样的书写可以说开辟了台湾当代海洋散文的写实风格,也为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参照。他的作品不同于《鲁滨孙漂流记》《老人与海》等西方文学靠猎奇来取悦读者,而是贴近海洋生活的实际,以散点透视揭示了人与海洋命运的息息相关。也许有人会担心这样的散文由于过于实在会使读者放弃阅读,其实不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海洋面临的危机愈来愈明显,人类生产活动对海洋的污染加剧。发达的科技在创造生产力的同时,也在将大自然的资源消耗殆尽,这一不容忽视的事实呼唤作家高度关注海洋。通过海洋纪实的书写,能够让生态意识深入人心,使大众从昔日试图靠对海洋的无尽掠夺来实现自身自由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实现与海洋的和平相处。
海洋的自然天成,使人产生了望洋兴叹之悟;海洋的无私奉献,则催人警醒。1990年代以来的台湾散文对海洋之美的描摹,并非为了满足大众旅游的需要,而是从内心出发、从生活实践出发的一种艺术真实。这样的散文往往以小见大,是作家人生理想的投影。同时,他们的海洋书写传承了传统文化追求和谐美的理念,恢复了长期以来被人类陆地意识所遮蔽的海洋视域。这样的书写有利于坚定全球化时代人类对于海洋文化的自信。长期以来,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严重制约了人类向海洋迈进的进程。随着生态主义意识在全球的迅猛崛起,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海洋。这一方面是无奈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类的觉醒。
二、海洋书写中的生命体验与家园意识
女性天性温柔,在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女性的成长又无不在生命的潮汐中起伏不定,正如海洋的神秘莫测。在以简媜和席慕蓉为代表的一些女作家的散文创作中,海洋的原型意义得到了升华。
简媜的散文集《天涯海角》以海洋为背景,书写家族的历史、台湾的历史及个人的奇遇,再现了时代变迁中的女性对于童年和故乡的留恋之情。《浪子:献给先驱》追寻简氏家族从大陆迁徙到台湾的历程,将迷雾一层层拨开。“仿佛一只蜘蛛回到昔年海边,寻找当年被风吹落大海的那张网般困难,我探求先祖轨迹,只得到五字诀。”⑯这是时代的宿命,还是命运使然?“五字诀”代表家族的秘密,却无法锁定时代瞬息万变的轨迹。海洋才是通向家族的密码,作家借海边的“网”,象征人生的机缘与挑战,捕捉历史缝隙遗留的族人的坚韧,凸显了生命的一次次轮回。她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与简氏家族冒险到台的经历进行交叉叙述,从而将家园的兴盛与国家的强大联系在一起,升华出家国同构的哲思。这篇散文以自己创作的诗歌《浪子之歌》收尾,突出了海洋对简氏家族的诱惑。“蓝色海洋,鸥鸟回飞,白浪装饰着海岸/海中有一座小岛与你对望,问名字/答曰‘龟屿’/你因此埋一个吉兆在心底当作秘密”⑰这显然不同于拉家常式的絮叨,它在情绪的自然流动中隐现着对自己家族的崇拜与感激之情。
《朝露:献给1895年抗日英魂》从漳州市一块简大狮的石碑中寻找家族的集体记忆。当神圣的文物与周围堆满的垃圾相伴时,英雄的没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作家在淡淡的忧伤中追忆发生在台湾海域的近代中日之战,如泣如诉。简大狮的义举与悲惨结局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但历史也会像海洋一样,也有潮起潮落之时,昔日中华民族之痛应成为今日国人不能忘却的记忆。
《天涯海角:给福尔摩沙》是一曲写给投海自尽的母亲的哀歌。第一部分《春之哀歌》以一名叫“春”的妇女的自述,把女性的献身精神与大海融为一体,激越而悲怆,令人感慨。
潜藏海底,我隐居在红珊瑚隙,以海草结庐,采紫苔铺塌;居鲸与豚鱼已分头清理海路,以迎接婴之破腹而生。我安静地躺卧,不食不饮,不喜不惧。咸波中,我红润的女体逐渐溶解,化成鱼群身上斑斓的纹彩。繁华洗尽,我素朴如一颗海底的人泪。⑱
台湾曾经是荷兰的殖民地,“福尔摩沙”(Formosa)是欧洲人对台湾的旧称。在这里,简媜以女人死后化身为鱼在海底繁衍的神话,隐喻了台湾人曾经蒙受的被掠夺与侵占之痛,展现了台湾沉痛的历史。同时,借海洋的美丽与丰饶表现出生态女性主义的诉求。“不少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视自然/大地为[地母](Mother Earth),如默茜(C. Merchant)、葛瑞(E.Gray)和鲁诗(R. Ruether)等,虽然他们的论点有些差异,但是皆觉得自然犹如母亲一样生育、滋养、保护着万物。”⑲在这篇散文中,女性与大海融为一体,显示出博大的情怀。而生活在水泥森林中的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台湾曾经的苦难与古老的海洋民族,这令作家深感忧虑。
这篇散文的第二部分《兰屿古谣》借太平洋上红人头的传说,叙述了雅美族人手持鬼头刀在海上捕鱼的习俗,神秘而令人神往。但都市化的噩梦时刻都在威胁着他们自给自足的生活,古老的信仰在现代化面前显得多么的脆弱。第三部分《港都夜曲》和第四部分《台北摇滚》则是后现代生活的写照,与前面的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第五部分《夏之独白》以抒情见长,在独白中发出了“我要借母亲的灵魂越过海洋而去”⑳的呼声。面对现代文明的大潮,作家痛感到了海洋面临的危机。“雅美族人有很独特的空间概念。雅美人所画的地图,位居中央的并不是兰屿岛,而是大海,兰屿岛与小兰屿、巴丹群岛及其他想象的岛屿则环绕中心的海洋排列。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所谓现代人的自我中心观,无论哪一个国家绘制的地图一定都是把自己的国家置于世界的中心。一生都生息于小岛上的雅美老人似乎认为世界就是一个一个像兰屿一样的小岛。”㉑可见,雅美人给我们开启的是一个面向大海的理想王国。简媜以雅美族的信仰来反衬出现代人的愚昧,凸显批判的锋芒。同时,她在追溯海洋文化中反观现代文明的弊端,显现出强烈的家园意识。时代在前进,对传统和历史的漠视导致了现代人的狂妄自大,终究会失去赖以生存的海洋与精神家园。
《烟波蓝:给少女与梦》这样写道:
海洋在我体内骚动,以纯情少女的姿态。
那姿态从忸怩渐渐转为固执,不准备跟任何人妥协,仿佛从地心边界向上速冲的一股势力,野蛮地粉碎古老的珊瑚礁聚落,驱赶繁殖中之鲸群,向上蹿升,再蹿升,欲掴上天的脸。却在冲破海平面时忽然回身向广袤的四方散去,娇纵地把自己掼向瘦骨嶙峋砾岸。浪,因而有哭泣的声音。㉒
海洋是狂暴的,同时在躁动不安中孕育了奇特的生命,这与人类生命的孕育过程具有同构性。在这里,“海洋”象征自然生命的经久不息。作家借“海洋”写两个少女在追求艺术过程中的煎熬,演绎出女性生命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就这样,女性的成长在自我与社会、艺术与现实的博弈中得到了诠释。
简媜的另一部散文集《女儿红》也不乏书写海洋的篇章。《在密室看海》写一对姐妹的童年记忆。潮湿的老屋,无助的妈妈,黑的海,都把她们推向命运的边缘。“夜使她超越六岁孩子的视界,向上攀升、盘旋、俯瞰,看到成人世界凌乱不堪的景致,她的感官活络起来,攫住那近乎绝望的黑,捕获令人有晕眩感的怒吼,最后,鲜明地记住一个少妇与双胞胎的女儿被不知名的力量扔在黑色海滩的处境。她后来隐约明白,接着发生的事是她自己触动宿命关键,遂使一生无法出脱暗海,注定独自仰望永夜的星空。”㉓茫茫无际的夜与海象征女性成长的艰难。面对成人世界的驳杂,女孩看到了自己的宿命,这是作家感性世界里的经验,也是她表达理想诉求的诱因。儿童有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女孩更是有着天生的依赖感。但残酷的生活反过来也拯救了女孩,使她们比男孩成熟得早。简媜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女性生命的悲怆与自我救赎。妹与姐不同,具有叛逆的性格。从小就能觉察到“在妈妈巧手布置的家里,有一个幽灵男童存在。”㉔这里暗示了妹妹朦胧的性幻想。成年后的妹妹放荡不羁,也印证了她的早熟。这篇散文借姐妹不同的性格,写出了女性的两面性。一方面,她们迫于传统和现实的压力,表现出柔弱而被动的一面;另一方面,她们在适应时代与环境中学会了以柔克刚、任性而为,成为现实生活中把握自我命运的强者。
“唯有水才能保持着美而睡去;唯有水能静止地保持着倒影而死去。水在倒映着忠于伟大的回忆,忠于唯一的映象,它使各种回忆又有生命。这样便产生了给予我们曾热爱的所有的人以美的那种委派的和重复的自恋。人陶醉在过去中,对于他而言任何形象都是一种回忆。”㉕简媜的散文在回忆中试图重返少女时代,其中的“海洋”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自恋色彩,逝去的青春在“海洋”的意象中得以复活,隐喻出女性不竭的生命渴望。无论书写家族历史或雅美族的传说,还是少女的成长,都在海洋的镜像世界里呈现出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交融。她追求一个与海洋共舞的世界,简氏家族以海为邻,雅美族人以海为生,少女在封闭的环境中渴望外面的世界,都是台湾人与海洋密不可分的命运写照。但现代人留恋都市的快节奏,几乎淡忘了昔日先辈奋斗的足迹,也失去了相对自由的空间。这正是世纪的忧虑,作家在海洋书写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也把问题摆在了世人的面前,令人钦佩。
此外,席慕蓉的《海洋》借一个远洋轮上的希腊水手与一个法国女教授的婚姻变故,演绎了婚姻如海洋般起伏不定的命运。希腊水手感到自己的生命只有在海洋上拼搏才变得有意义,回到海洋是他明智的选择。同样,她的另一篇散文《给我一个岛》从小岛上一个女人的惬意生活中看到了船在海上自由行走的后面对家不变的依恋之情,这里的“岛”象征着女人渴求的理想家园。可见,席慕蓉与简媜散文的海洋书写达到了异曲同工之妙。
台湾作家书写海洋,将海洋内化为自我成长的客观对应物,人生的况味与生命的体验乃至历史意识,都转化为一种海洋意识,表现了他们对人类原初生命激情的追寻,还原了人类自身的自然元素,是一种返璞归真心态的自然流露。这在21世纪的今天具有启迪意义。因为海洋,人们天各一方,形成了不同的血统;因为海洋,人们渴望探求未知的世界,人们分享了它所带来的神奇。散文作为一种灵活多样化的文体,可以比较全面地表现海洋的大千世界。令人欣慰的是,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海洋书写接纳了西方生态主义的文化,让人们看到了浪漫主义冒险精神之外的一种审美态势。台湾散文的海洋书写无论是以叙事为主,还是以抒情见长,都没有都市散文中激烈的批评。如果说骆以军和唐诺等作家的新都市散文凸显出的是后现代都市社会里人与物、人与人的冲突的话,那么,蒋勋、廖鸿基和简媜等作家的海洋散文则表露了台湾人渴望回归自然的赤子情怀。
注释:
①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赖力行:《中国古代文论史》,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17页。
②徐明德:《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型传统及流变(下)》,《大海洋》1998年诗画展特刊。
③蒋勋:《此时众生》,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④林清玄:《养着水母的秋天》,《感性的蝴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⑤杨牧:《奇来后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⑥⑦蒋勋等:《行走台湾:台湾文化人说自己的故事》,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8页、第219-220页。
⑧陈思和:《试论9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海洋题材创作》,《学术月刊》2000年第11期。
⑨⑪⑬⑮廖鸿基:《领土出航》,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93-94页、第27页、第104页、第264页。
⑩萧义玲:《海洋流域,如梦之梦》,廖鸿基:《领土出航》,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8页。
⑫无名氏:《金色的蛇夜》(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⑭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白华、林水选注:《青玉案》,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⑯⑰⑱⑳㉒简媜:《天涯海角》,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第40页、第151页、第160页、第220页。
⑲冯慧瑛:《自然与女性的辩证:生态女性主义与台湾文学/摄影》,《中外文学》1999年第5期。
㉑余光弘,李莉文主编:《台湾少数民族》,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页。
㉓㉔简媜:《女儿红》,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第42页。
㉕[法]加斯东·巴什拉著,顾嘉琛译:《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74页。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佘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