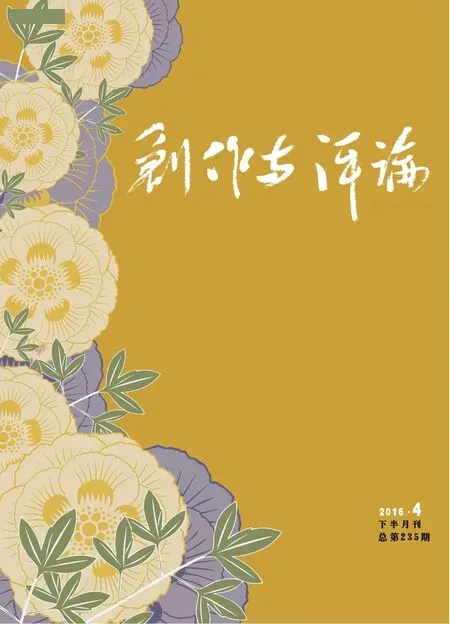中国乡镇的隐喻与暗示
——论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
○胡良桂
中国乡镇的隐喻与暗示
——论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
○胡良桂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富创造精神、最具叛逆性的作家。他成就卓著,影响广泛。他用笔、用心创作的长篇小说,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中国式的巴尔扎克。从《浮躁》《废都》到《怀念狼》,从《秦腔》《古炉》到《带灯》,几乎一部一个台阶,一部一个水准。“每一部都有突破其实很难,但他恰恰做到了,每一部都不同,而且更优质。”①
贾平凹的新作《带灯》是一部关注当下、思考现实,书写“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优秀长篇小说。它从“乡镇”一隅的地域空间,隐喻整个“中国乡镇”的整体性空间及其现代性命运。既开启了一个被当代文学史叙述所遮蔽和忽略的“中国乡镇”及其“乡镇人”群像的新领域,又呈现了一个无比鲜明的、庞杂的、正在剧变中的新乡土中国的独特审美思考与精神空间。它既是贾平凹个人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乡镇文学叙事发展中的重要开拓。
一、乡镇:一幅隐喻性的真实画卷
贾平凹在《带灯》中描绘了一幅崭新的“镇街”生活画卷。它既不像浩然的《艳阳天》以一个村庄为中心画面,描写肖长春引导广大贫下中农一道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也不是刘震云的《我不是藩金莲》以一个人物为发展线索,刻画李雪莲从丈夫告起一路连续告到县、市直至人民代表大会。《带灯》把叙述画面聚焦于乡镇的“镇街”,乡村只不过是它叙事远景,“镇街”也不止是一个自然空间,而是一个多维的、整体性叙事画面,一个小型的不同层级社会网络系统。比如樱镇就有“镇街”官方集体空间、“镇街”民间个人空间和“镇街”周边村庄空间三个部分,由此就有了“乡镇干部”“镇民”和“镇街”周边农民等三类人物群像。樱镇“镇街”又由镇中街村、镇东街村和镇西街村所组成,从而形成了一个乡镇中心驻地村所,里面除了乡镇政府及其附属机关外,还有钢材铺、肉铺、杂货店、饭馆、饺子店、米粉店、镶牙馆、私人诊所和中药铺等个体企业。由于“乡镇干部”“镇民”和“周边”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在“镇街”中彼此交集在一起,既显现出乡镇经济的繁荣景象,又构成了一个立体的、鲜活的、崭新的“中国乡镇”。
乡镇也是由一个个乡村组成的。“樱镇辖管几十个村寨”。村寨就散落在秦岭腹地,虽然既有“县上的后花园”“秦岭里的小西藏”的美誉,又有保护生态、敬畏自然的传统;既有接待过“皇帝”、寄宿过“文人骚客”的历史,又有寺庙老松、碑文篆刻的文化。但大多村寨都处在或黄土高坡,或河堤沙滩;或崇山峻岭,或沟壑深谷。那“土路似乎不是生自山上,是无数的绳索在牵着所有的山头”,把镇街和一个个村庄连接在一起,就是一条条土路,而在一条条土路和镇街之间奔波的是流动的农民。乡镇除了管理功能之外,还承担村庄与村庄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进行物资、信息、精神交流的集市功能。正是在政府乡镇所在地的管理功能和集市交流功能的作用下,《带灯》乡镇“镇街”便渐渐成为了具有一定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多元属性的复合场所。特别在逢集市的日子,乡镇“镇街”更是变得热闹非凡,盛满了各种声音。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在风的吹拂下失去了节奏语言,集市“街面上人们都在说话”,“这就是市声”。它们聚合在一起就是一幅中国乡镇民俗风情的生活画卷。
《带灯》展现了一曲中国“现实矛盾”“困境和难题”的问题画面。贾平凹说:“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解乡镇政府,知道着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②曾经一度朝气蓬勃的乡村世界如今已陷入某种空前凋敝的惨酷状态。儿童留守,土地荒芜;伤残返乡,权益无助,甚至村里有人下葬都找不到抬棺的人了。“谁好像都有冤枉,动不动就来寻政府”,就“拿头撞墙,刀片子划脸”。“维稳”就成了乡镇最关键紧迫的问题,樱镇“维稳”就有四项总体原则,具体多达28项。比如小说描写王随风的上访,既令镇政府头痛,又让人心生同情。王随风原来在县医药公司承包了三间房做生意,狠赚了一些钱。但后来医药公司职工下岗要求收回房子,而合同期又未到,在未征得王随风同意的情况下,医药公司不仅硬性单方面终止合同,还强行把她的东西扔到了外边。在双方谈判无果,王随风执意上访时,县委给镇党委施压,镇政府就采取了野蛮的手段。“村长就对王随风说:‘我可认不得你,只认你是敌人,走不走?’王随风说:‘不走!’村长一脚踢在王随风的手上,手背上蹭开一块皮,手松了,几个人就抬猪一样,抓了胳膊腿出去。”明明是遭受了冤屈的上访者,结果被当做敌人,被当成猪一样的畜牲对待。当下乡村社会的问题多么严重,王随风这类普通乡民的生存状态多么严酷。
发展是人生的梦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与利益的关系,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关系,就是把握事物内部矛盾不断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运动变化过程。《带灯》描写大工厂在樱镇的落户建设,就是发展的产物。既能给樱镇带来经济的发展,也将影响樱镇的自然环境,还会牵扯出各种利益的纠葛。因为大工厂的建设,不仅将从根本上改变樱镇的传统生存格局,而且也是一个发展自身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良机。于是,元黑眼五兄弟在准确判断大工厂的建设肯定需要大量天然河沙之后,就先下手为强地圈地占沙,把本来属于公共资源的河滩强行据为己有,办起了沙厂。而薛家的换布、拉布兄弟,则是要通过改造老街办农家乐的方式发财。可当换布得知,“元黑眼兄弟五个要办沙厂”时,换布马上意识到“办沙厂倒比农家乐钱来得快”,利润丰厚。换布兄弟托人找到县委书记秘书,给县河道管委会打招呼,镇党委书记得知县委书记秘书打的招呼,明知河道狭窄,极易发生纠纷,却同意换布办起了第二家淘沙厂。元家五兄弟就怀恨在心,却又胳膊扭不过大腿。最终因杨二猫的被打而酿成一场惨不忍睹的械斗悲剧。其结果造成死亡一人,致残五人,伤及三人,为十五年来全县最重大的恶性暴力事件。尽管可以指责元黑眼、换布的唯利是图,视钱如命。但官员之间的权力寻租,徇私枉法,贪污腐败,无疑也是造成许多百姓无辜伤亡的根本原因。
《带灯》再现了一帧精神信仰、文化生态的缺失画面。民间文化生态的演变相比急剧的社会变革与法制的修改变迁,要缓慢得多,但其显现出来的持续性与浸染性的心灵变量却巨大得多。《带灯》曾有这样的描写,以往社会的安定,早先有礼义仁智信;后来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为纲。“现在讲究法制了,过去的那些东西全不要了,而真正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又没完全建立,人人都知道了要维护自己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着。”于是,观念的超前,思维的陈旧,导致“上访者”与“镇政府”都处在一种怪谬的“错位”状态。患了“矽肺病”的打工农民不去上访,上访的尤其缠访的竟然多是有不良企图的“刁民”,而镇政府又不辨是非曲直,一律采取以钱止访、息访的思维和做法。小说中姓严的为了一棵核桃树与坡地住家“起了争端”,镇政府多次调解“都不行”,就出“三百元”来平息。“还有一个李志云的”,因特大洪灾倒了小房,按政策规定不在补贴之列,他就一直上告,镇政府又给他“面粉和被褥,还办了低保”。结果“该享用的享用了,该告还告”。不仅农民不够理性,胡搅蛮缠,镇政府也在以非正义、非法制的方式参与其中,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乡镇社会生态的恶化,让农民心生彻底失望之感。樱镇民事纠纷和访民的大量出现,不仅是干群关系紧张和经济利益冲突加剧所造成的,更是从上到下精神信仰的缺失,现代法治和公民意识匮乏的结果。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乡土情怀、文化生态在文化消费主义面前不堪一击。物质、欲望、享受成为一种可怕的“新意识形态”肆虐侵蚀着从城市到乡镇、农村的当代中国人心灵。乡村的文化生态令人忧虑。《带灯》把大工厂选址在“发现了驿站旧址”的梅李园,按带灯和竹子的大胆设想,“把驿站遗址保护和恢复起来,不就是个好的旅游点么!”可大工厂建设不仅“毁掉了梅李园”“许多石门梁、柱顶石”“栓马桩”“石狮子”都被私人拖走据为已有,而且“樱阳驿里玉井莲,花开十丈藕如船”的石刻文物,连同那“汉白玉的细腻和汉白玉上图案的精美”的井台圈,都被炸掉了。乡村文化心理结构的恶变更加可怕。作者写王中茂办婚宴,没请孩子舅舅。有人问起来,正在街上担尿桶的舅舅生气地说:“没钱的舅舅算个屁!”这人又说:“这就是中茂不对么,这么大的事不给当舅舅的说。”担尿桶的突然流一股眼泪,把尿桶担走了,脏水淋淋,巷道里都是臭气。这无疑就是樱镇民间文化生态的精神隐喻。王中茂败坏了仁义的民间文化生态,前来吃酒的客人也做出了伤风败俗的举动,把吃完饭的碗碟扔到尿窑子里。邻里亲戚是碍于仁义的传统而不得不来,但内心却充满了怨怼。看来,这民间文化的“礼”及其精神内核正在流失,那“现实的危险早已在人的本质处影响着人了”。
二、带灯:熠熠发光的幽灵化形象
带灯是贾平凹突破他以往女性形象塑造“总有一种丰绕多情与豁达坚韧,有时贤良,有时放任;有时专情,有时迷乱”③的模式,而使带灯身上具有一种崭新的精神元素:如一只黑夜“带灯”且独行的萤火虫一样幽暗明灭地闪现在樱镇的世界里。美丽又善良,刚强又柔弱,执著又犹豫;饱满而复杂,果敢而机智,粗豪而仁慈。带灯夜行而熠熠发光,虽然微弱,却超凡脱俗。
带灯是“藏污纳垢”乡镇官场的一朵奇葩。她以其独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乡镇的政治生态。带灯“农校”毕业分配到樱镇,是丈夫“在镇小学工作”;带灯清秀美丽,“读了好多的书”,别人喊她“喝酒”“打牌”,她都不去。于是,在樱镇干部眼里,带灯“还没脱学生皮”,“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她“不该来镇政府工作”等。而带灯总是对镇书记敬而远之,她以她的清高与书记的粗鄙适成反差;镇长对她施行潜规则,她毫不含糊地警告他说,“你就管好你”;副镇长好一口红炖胎盘,整烧娃娃,她一见就“胃里翻腾,喉咙里咯儿咯儿地响”。就这样一个靓丽高洁而又“不合时宜”的带灯,直到“差不多陪过三任镇党委书记,两任镇长”,才给她安排一个综治办主任。综治办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维稳”。对此,带灯仍然以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处事的机智果敢,清醒的政治头脑,深邃的人性内涵,与樱镇镇政府的其他人员,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当侯干事以种种令人发指的非人方式折磨王后生时,带灯却反复叮咛:“去了不打不骂,让把衣服穿整齐,回来走背巷。”侯干事无法理解:“咱是请他赴宴呀!”当村长对王随风凶神恶煞时,“带灯说:心慌得很,让我歇歇。却说:你跟着下去,给村长交待,才洗了胃,人还虚着,别强拉硬扯的,也别半路上再让跑了。”带灯不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农民的截访打骂、威逼利诱,总是以一种温和说理、苦口婆心的方式去化解矛盾。她既是“维稳”的得力干将,又是农民的贴心“棉袄”。建立一张乡镇干部与各村农民的“老伙计”联络图,从源头上化解矛盾,从情感上关怀农民,是带灯的一种创造性“维稳”工作。
带灯的精神世界与情感心灵是丰富的、深邃的,也是复杂的、虚幻的。作者单独以一条结构线索二十六节的篇幅,通过“给元天亮的信”把带灯浓郁的忧患意识、孤独的情感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元天亮是元老海的本族侄子,是樱镇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既能写书,又能做官;既乡音不改,又热心为家乡办事。他的传奇在樱镇“到处流传”,他的大幅照片已框在镇街的宣传栏。他成了樱镇的名片和招牌,也成了带灯的精神寄托与倾诉对象。其实,带灯与元天亮并没有见面,因为读过元天亮的作品,听到元天亮的传说,带灯就给自己的崇拜者发了一条短信,没有想到竟然收到元天亮的简单回复。“镇政府的生活常常像天心一泊的阴云时而像怪兽折腾我,时而像墨石压抑我,时而像深潭淹没我”;而丈夫的俗气还“不肯洗澡”,他们在一起也是充满着吵架的声音。于是,带灯就把自己女性的阴柔美放到与元天亮的精神交往之中。在给元天亮的短信中既坦承了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轨迹,又显现出一种自我想象的虚幻化、阴柔性。这些短信毫无例外是带灯向元天亮发出的单向性生命情思诉说,是带灯与外部世界进行精神联系和情感倾诉的虚空化对象和符号。它既传递出了带灯内心情感的荒芜、悲伤、无尽的温情与爱,又呈现着一种不受世俗所约束的蓬勃泼辣的野性精神之美。
带灯是在尽情释放自己的生命激情,在自我想象的、文字所建构的精神世界中获得抚慰和满足。元天亮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出现在带灯的眼前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化为一个精神符号,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存在,如同山间的一朵花、一片云、一缕擦肩而过又无处不在的风。在带灯眼中,“自由的生灵没有家,运行是它的心地,飘逸的生命没有家,它的归途是灵魂的如莲愉悦”。因此,带灯像不屑浮华的王宝钏一样,“在人生道路上把许多的背影看做心头至爱”,让“那条干枯泪腺里的石头瓦块”融化为汹涌的爱的河流。④可见,“给元天亮的信”已经成为带灯精神力量的源泉。无论是给元天亮描述自然中的花鸟虫鱼,还是给元天亮叙述樱镇的变化以及民生的疾苦;无论是给元天亮解析自己心中的苦恼与困惑,还是给元天亮诉说她心中对他的想象与爱慕,那“地软”始终是“你梦牵魂绕的故乡”,那“风筝”是她“给太阳送一个笑脸”;那山果记载着“农人脊背朝天”的汗水,那端午的雄黄酒、艾枝、露珠是“珍惜的良药”。这一切,都是与大自然、世界进行生命对话的精神方式,或是超越世俗生活之爱与美的艺术化生存;是抗衡现代性的物质发展主义的精神追求,还是“对这个世界构成一种更深层次的批判”。⑤由此可见,“短信”成了带灯的精神支柱,使她有力量去帮助和拯救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匍匐在地上的人们,使她有力量、有勇气去面对阴谋、陷害与种种令人不齿的恶行。从而使带灯的理想主义光芒虽然微弱却熠熠生辉。
带灯是理想主义悲剧命运的真实再现,也是“属于风过之后”金子般的先锋战士。带灯原名叫“萤”,即萤火虫,因“萤虫生腐草”之虞而易名带灯,取黑暗中自明之意。这个名字也显示了带灯的命运,拼命地燃烧和照亮,却注定是微弱无力与幽暗。因为美丽与超拔同脏乱和下旋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带灯身上也有了卑俗的一面。一方面,她独来独往,身边有一位竹子,还有一位同学是镇长,但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她,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和她的内心交流,她就是如此的孤独;另一方面,她的脾气越来越大,开始粗野骂人,还有两次不得已打了人。偶尔也会抽烟喝酒,会“移情别恋”,甚至还终于在内衣中发现了两个虮子,从此也便有了虱子。而村民与村民之间并非因为苦涩与烦闷而相互体恤,而是因贫富差距利益的不均积怨太深而恶斗,元家与薛家的械斗就是野蛮与血腥之极。带灯毕竟是一个弱女子,她一个人终究对抗不了嘈杂琐碎而又锐利残酷的现实,她的理想主义的浪漫、善良不但拯救不了别人,也救不了她自己。于是,在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都找不到自己时,她就只能成为一个疯子,成为现实的祭品,成为现时代一个真正的另类的“乡镇干部”。最终成了一个鬼魅世界借以渲泄郁勃黝黯情绪的幽灵。它既是“五四”以来启蒙主义“吃人”主题以及“人变成鬼”主题的富有时代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樱镇乡镇以及整个社会的悲剧性命运作出的形象暗示。
显然,带灯的美丽、漂亮与不同凡响,不属于过去,只属于未来;不属于现实,只属于理想。因为幽灵化的隐喻具有神秘性,具有非现实性。那么,在如此具有现实感的“西汉品格”的文字书写中,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强调幽灵化?带灯既要介入中国乡镇的新农村建设,又要承载当今困难重重的政治上的“维稳”任务。也就是说,她身上能折射出多少今天政治思想的光芒,或者她能预示出怎样的出路?小说结尾处关于萤火虫阵的描写,就作了隐喻性的回答:“带灯用双手去捉一只萤火虫,捉到了似乎萤火虫在掌心里整个手都亮透了,再一展手放去,夜里就有了一盏小小的灯忽高忽下地飞,飞过芦苇,飞过蒲草,往高空去了,光亮越来越小,像一颗遥远的微弱的星……那只萤火虫又飞来落在了带灯的头上,同时飞来的萤火虫越来越多,全落在带灯的头上,肩上,衣服上。竹子看着,带灯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这场面壮观的萤火虫阵,既是佛的意象与精神底蕴,又是带灯形象的理想性化身。陈晓明说:“带灯身上无疑有我们久违了的‘人民性’,有那种与穷苦百姓打成一片的‘阶级性’,甚至有着高度自觉的‘党性’。”⑥这些正是作者一种超越性的审美思维模式,而创造出的带灯身上所具有的美好品质,它既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也是一种审美理想的表达。恰如陀思妥耶夫斯所言,“世界将由美来拯救”。《带灯》所塑造的超越凡俗女性的、汲取天地灵气、具有神性的“带灯”形象,是反抗现代性、拯救和照亮“中国乡镇”的爱与美的天使。萤火虫阵及其所组成的“如佛”形象,既是对带灯的赞美,也是对樱镇的农民、大地与中国乡镇未来的期望。⑦
三、叙事:“海风山骨”的艺术体验
《带灯》的“西汉品格”与“海风山骨”的境界,体现为一种美与丑、实与虚、远与近的准确把握,一种此岸与彼岸、世俗与精神、现实与自然的细致描绘,一种理想与悲情、写实与象征、出场与影子的审美判断。它们虽然是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拉拉杂杂,混混沌沌”。但却做到交相辉映,因果推进;明丽轻快,疏密有致。从而使小说既隐喻含蓄,意蕴幽深,又清新自然,气韵生动。
《带灯》的结构艺术,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以樱镇“维稳”为中心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摹写与带灯写给元天亮的短信,构成了两条并行不悖的结构线索。前者是日常生活,后者是形而上线索;前者是接地气的,后者是艺术的飞升。樱镇现实生活这条线,一方面固然是在描写带灯与竹子她们综治办的“维稳”工作,但实际上是在充分展示樱镇芸芸众生在当下这个特定时代的众生相,展示他们的苦难生存状态,尤其是通过那些上访者不幸遭遇的具体状写,强有力地揭示普通百姓现实生活的惨酷凄楚,以及官员的投机逢迎,欺上瞒下。樱镇洪灾死亡十二人,镇书记瞒天过海,弄虚作假,一一排除,只剩一个还报“烈士”材料,树个典型;元家与薛家械斗伤亡惨重,他抽身而出,委过于人,让带灯与竹子受到处分;他虽在樱镇工作,却每天下午都回县城,整晚应酬,为自己升迁谋门路。而带灯的精神世界这条线也丰满鲜活,她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爱意,都被远方的乡人元天亮点燃了。带灯于元天亮,虽然以爱慕的姿态开始,但是她其实从来不求回报,为的只是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找个家园。无论元天亮是否回复,甚至是否存在,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带灯需要倾诉。而且,在这场清水静流的爱恋中,带灯焕发了超越于一个乡镇干部可能拥有的丰富才情,她的意象灵动,词句优美,是任何被俗世规矩限定的人无法达到的。于是,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带灯的短信越是浪漫美好,樱镇现实生活的苦难与惨酷越是突出。从各节的篇章上说,它们长短不一,看似独立,却内有关联。这种“短信体”的结构形式看似松散无章,没有骨架,实际上却别有韵味。
而隐性结构,是指人物群像板块系列:它是以镇书记、镇长、马副镇长、带灯、竹子、白仁宝、侯干事、刘秀珍等组成基层乡镇干部系列;以元黑眼、元斜眼、元老三、换布、拉布、曹老八、张膏药、陈大夫、马连翘等组成的镇街小镇人物系列;以“老伙计”(如刘慧芹、六斤、陈艾娃、李存存、范库荣等)、“十三个妇女”(丈夫都在大矿区染病)、“老上访户”(王后生、杨二猫、朱召财、王随风等)组成的村寨人物系列。他们或是“地位低下,工资微薄”,都能分片包干、尽职尽责,堪称“江山社稷的脊梁”“民族的精英”;还是“巴结上司”、弄虚作假,既对上访者气焰嚣张、手段残忍,又阳奉阴违、以权谋私。他们或是吃苦耐劳、精明干练,却能勤俭持家、和气生财,应是樱镇繁荣的“能人”、发展的动力;还是利益纷争、大打出手,既霸道龌龊、心胸狭窄,又械斗杀戮、你死我活。他们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却能精耕细作、知恩图报,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富裕的根本;还是家境贫困、凄苦潦倒,既抱怨社会、肆虐无信,又卑怯懦弱、虚妄阴暗。他们都生存在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城镇化的中国乡镇——樱镇,彼此联结,编织成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它隐喻了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带灯前行的处境,而带灯也并非是小说绝对的主人公或中心人物形象,她只不过是一个参与到小说的整体情境之中的叙述者或说话人。小说中竹子、马副镇长、元家兄弟、“老伙计”“老上访户”的形象都不是带灯所能代替或遮蔽的,甚至有些人物在完整性和深刻性上还超过了带灯,这实际上是人物群像板块结构大大地拓展了小说的话语空间,而兼具小说和散文的结构特点,实现了“复调”叙事结构的艺术创新。
《带灯》的诗化艺术,就是意象与象征的巧妙运用。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它是通过形象描绘表现出来的境界与情调。《带灯》“埙声”的意象叙事,既是带灯逃离现实的呐喊,又是她心灵的回声。贾平凹在小说中引入埙声,是因为“埙是古乐器……善吹一种浑厚的、幽怨的调子,发出的土声穿透力特强”。⑧《带灯》中时隐时现的埙声,就成了整部作品贯穿始终的音乐背景。自从带灯有了埙,就对它爱不释手,常常吹上一段,可镇政府的人都不喜欢,认为这埙声太过悲凉,听了“总觉得伤感和压抑”。带灯却认为,埙是土声,“这世上只有土地发出的声音能穿透墙,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于是,埙声就成了繁复小节中一条明亮的河流,使作品在混沌中不乏轻灵的格调。事实上,自从埙乐加入以后,小说的基调的确愈发悲凉,埙声缭绕,带灯那萤火虫一般的光亮也越来越暗淡,后来带灯患病,埙也不见了。带灯哀伤地感叹:“那真是它走了,不让我吹了。”埙声仿佛一开始就已经为带灯奏响了挽歌。埙声的消逝,既是带灯的生命活力的渐渐流逝,也是带灯心目中美好的田园家园的消失。而带灯的名字,萤火虫,更是作品最显性的隐喻。萤光,是烛光,这点小光,是理想的光,是理想主义者精神中微弱的照亮。它可以点亮自己,却无力改变世界。这种燃烧已不是点亮自己照亮别人的崇高,而是洁身自好,自救而已。只有聚在一起,才能温暖黑暗的寒夜;只有聚成萤火虫阵,才真的成了光。小说结尾这样描写:“这些萤火虫,一只一只并不那么光明,但成千的成万的十几万几十万的萤火虫在一起,场面十分壮观,甚至令人震撼。像是无数的铁匠铺里打铁淬出火花,但没火花刺眼,似雾似雪,似撒铂金片,模模糊糊,又灿灿烂烂,如是身在银河里。”这种隐喻,给带灯,给樱镇,给世人以希望,也是带灯精神、理想、人格与诗情的象征,是带灯命运的写照。
象征既有比喻中的暗喻成分,又有表述方式中的比附因素,它们的生发和放大,就是特定形象的一种含义和观念。《带灯》中虱子的隐喻与象征,就是一种艺术,一种创造,一种新观念的寻求和诞生。在樱镇,人的身上有虱子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带灯却不同,她不仅拒绝自己身上有虱子,而且还向镇政府建议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灭虱的动员,发硫磺皂,发洗衣粉。可樱镇人不仅不想灭,反而觉得带灯可笑。带灯就只好孤独地抗争。从不睡别人的床,勤洗澡换衣。直到那次带领妇女们去邻县打工摘苹果,结果带灯和竹子沾上了虱子,但经过紧张的处理,虱子远离了她们。最后,带灯毕竟力量微弱,而虱子的数量实在太多,她终于无力招架,只能无可奈何地妥协。不仅带灯与竹子的身上再一次生出了虱子,而且“无论将身上的衣服怎样用滚水烫,用药粉硫磺皂,即便换上新衣裤,几天之后就都会发现有虱子”。甚至带灯对于虱子也从紧张、厌恶,变为习惯和麻木。“也不觉得怎么恶心和发痒”,并自嘲“有虱子总比有病着好”。带灯与虱子进行的战斗,不仅象征一种陈腐的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也是她与现实丑恶势力和恶劣环境抗争的一个缩影。而白毛狗的象征意义,更是意味深长。带灯初到镇政府工作时,那条狗还是一条杂毛狗。因为带灯特别爱干净,所以就给狗洗澡,结果那条狗居然变成了一条白毛狗。带灯对白毛狗宠爱有加,下乡走访也常常带着狗,可是白毛狗先是被打跛了腿,又被人害掉了尾巴。白毛狗仿佛镇政府的护卫,它用吠叫吓退上访者,同时也承受着上访者对镇政府的仇恨。它屡次受伤,却始终能够坚强地存活下来,成为带灯工作中可以信赖的伙伴。当带灯患上夜游症,精神上出现了问题。这时的白毛狗也“再不白,长毛下生出了一层灰绒”。从象征隐喻的角度看,写狗也即是写人、写环境,通过一条白毛狗的描写,折射出带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只能是理想的破灭,理想主义的完结。
《带灯》的语言艺术,既有山骨般的阳刚,又有海风似的阴柔。阳刚犹如山骨一样坚硬、粗犷,冷干、固定。它是一种大气磅礴、汪洋恣肆的狂放语言。《带灯》主要以处理政事与上访为核心。于是,人们整日处于各种问题的漩涡之中,不是讲奋斗,就是谈挣钱,这种阳刚之气使得身体、自然、社会、精神等生态都遭到严重破坏,去大矿区打工的人大多得了矽肺病,旱涝灾害频发让人苦不堪言,社会贫富不均造成了暴力事件,人们在精神上更是无所适从。这些都在樱镇世界得到全面的展示,并落实在阳刚、公共的话语体系上。尤其是书记、马副镇长几乎就是公共话语的代言人,整个镇政府都充斥着大话、套话。特别是开会话语与文件话语,不是命令,就是拍板;不是训斥,就是压制。马副镇长等折磨王后生时训斥的野蛮,村长扇朱召财老婆耳光时的粗俗,镇长下令绑了闹事的田双仓语言的残忍,马副镇长对带灯说“这不是天了”的荒诞等,都是一种“山骨”般的刚性话语。而且,作者还采集了大量的民歌民谣、奇闻轶事、笑话段子、野史方志、残碑断简、地方曲艺之类穿插其中,甚至还有政府公文、领导计划、会议记录、工作日记等。比如县委县政府为市委黄书记到樱镇视察下的文件:“……书记、镇长和大工厂基建负责人就到樱镇边界上恭候迎接……讲话稿不用镇上准备,但多准备几个照相机,注意照相时多正面照,仰照,严禁俯拍,因为黄书记谢……”这些安排本来就像白花花的骨头一样坚硬。但经过作者的艺术剪裁,不仅没有生硬和不协调,反而呈现出一种艺术笔墨的味道,这是大胆的文件杂糅,既增添了作为小说的说话的谐趣,也强化了小说叙事的历史感。
阴柔就像海风一样阔大、柔软,温润、流动。它是一种温顺柔和、大气沉稳的明丽语言。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就是阴柔话语的核心。有了元天亮的信,才有带灯自己的精神“星空”,她是在写信的过程中建构起自己的心灵世界的,只有这时,她才属于她自己。在倾诉中,她虚构了时间与空间,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思想自由遨游,只有这时,她才找回了自己的生命感觉。于是,她行走在山林里,在幽谷的清风里对着远方的人说话:“我在山坡上已绿成风,我把空气净成了水,然而你再没回来。在镇街寻找你当年的足迹,使我竟然迷失了巷道,吸了一肚子你的气息。”“你是我在城里的神,我是你在山里的庙。”明丽而又精致,清新而又灵动。不仅如此,在政事叙述中,也有不少温润与明快的语言。刘秀珍夸儿子是她河边慢慢长大的树,身心在她的水中,水里有树的影子。她说儿子“是天上的太阳照射着河水,河水呼应着怎么是又清又凉的水流?”就极具诗意。⑨小说最后描写“萤火虫”:“正是傍晚,莽山已经看不见树林,苍黛色使山峦如铁如兽脊,但天的上空还灰白着。她们才一到河湾,二猫就知道了,撑了排子吱呀吱呀划过来,让她们坐好,悠悠向芦苇和蒲草深处荡了过去,而顿时成群成阵的萤火虫上下飞舞,明灭不已。”既有意境,又有韵致;既有情趣,又有意象。它诗意盎然,简约直白,充满着情感的力量,悲剧的美感。
《带灯》语言的阳刚与阴柔、山骨与海风又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是在温润与硬气之间绯徊,用柔性的笔法写出庄重的话题。比如“元家兄弟又被撂倒了两个”一节,那场在粪池边上的打斗,简直把暴力与荒诞、仇恨与滑稽、凶恶与无聊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了。这暴力写得淋漓尽致,却又如此痛楚,它完全就是一种海与风,山与骨;绝望与希望,社会伦理与个人伦理,交织在一起。从曲处能直,密处见疏;以小见大,以柔克刚中,既表现黑暗的力量,也写出了宽容与悲悯、信心与希望。这就是多种写法的综合,是各种精神的矛盾的辩证统一。
注释:
①孔令燕:《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光明日报》2013年1月22日。
②贾平凹:《带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页。
③⑥陈晓明:《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④⑦张丽军:《“新乡镇中国”的“当下现实主义”审美书写——贾平凹<带灯>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
⑤李云雷:《以“有情”之心面对“尖锐”之世——读贾平凹的<带灯>》,《小说评论》2013年第4期。
⑧贾平凹:《与穆涛七日谈》,《坐佛》,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69页。
⑨谢有顺、樊娟:《海风山骨的话语分析——关于<带灯>》,《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