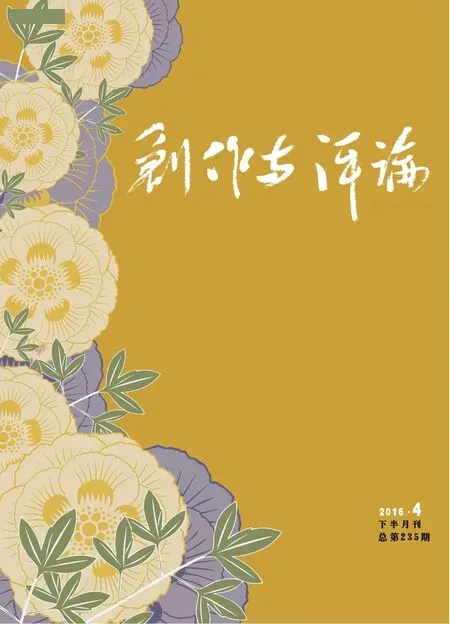变革的焦虑
——文学的生存、媒介与启蒙
○王威廉 冯娜 唐诗人
变革的焦虑
——文学的生存、媒介与启蒙
○王威廉冯娜唐诗人
一、诗人的活命
王威廉:今天很高兴能和两位朋友对话,一位是青年诗人冯娜,一位是青年批评家唐诗人。冯娜被首都师范大学邀请为驻校诗人,我想,我们今天的聊天不妨从这里开始,聊聊文学作品跟诗人、作家的生存状态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一定会影响他所写出的作品,诗人、作家为了生存,不得不游走于各种各样的机构之间,这些机构有权力的,也有市场的,它们构成的其实就是一种文学制度。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有赖于这种文学制度的生产。那么,有请冯娜,先给我们谈谈你的驻校情况吧。
冯娜:驻校诗人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高校中建立驻校诗人制度的,首都师范大学是第一家,我是他们第十二届的驻校诗人。诗人的生存状况这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少向别人主动介绍我是一个诗人,因为很多时候在大众的眼里,诗人就是李白和杜甫这些已经故去的诗人,要么就在课本上读到过的舒婷和北岛等老一辈的诗人。诗人并不是像教授这样一个的职称,也不像医生、律师这样的社会职业,几乎没有诗人作为专业写诗的人而存在,包括我也一样,我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写诗甚至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从整体境况来说,我估计90%以上(甚至更高)的诗人都有自己固定的职业,至少得有谋生的能力。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无法解决形而下的物质基础,很难要求他去建设形而上的灵魂事业。从中国目前当代的情况来看,单纯做一个诗人应该说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王威廉:我知道你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平时忙不忙?你是怎样处理工作和写作的关系的?
冯娜:之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时间被大量切割。写作至少需要一段心静的时间,工作往往会破坏这种心境,造成很大的困扰。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诗人,你又必须学会承受这种东西,如何升华日常的琐碎之物,也是对诗人的一种考验。我在中大图书馆的工作,目前是在一个分馆的馆长办公室,这个馆大概每天图书馆的入馆人次5000至8000人,我们的工作量也挺大。我个人主要承担着学生助理管理、图书馆的内外宣传、读者导等方面的工作。听起来就非常琐碎吧?也确实是如此。这些对于我来说既日常又富于挑战,作为一个诗人,我非常希望工作可以顺理成章,能有充分的时间写作。
王威廉:你写诗也写小说,你怎样看待诗歌和其他体裁的关系?
冯娜:写作都是相通的,虽然这里面有区别,但在某种深度和高度的层面都是一致的。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本质就是一个诗人。写作者只是找到的恰当的题材和文学的样式表现出来而已。我有一些画家朋友,虽然他们用画笔颜料创作,但他们也像诗人。体裁和形式可能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介质而存在。
王威廉:诗人总是带着骄傲的口吻,我们似乎不能反着说,这个诗人本质上是一个画家或小说家。你怎么看待诗歌的高贵性?
冯娜:一个诗人谈到诗歌没有足够的敬畏,谈到诗人的称谓没有足够的骄傲和自省,我觉得可能也有问题。诗歌在我的生命里,它的重要性是让我得到了另一重生活,让我的生命更丰饶更深邃。艺术也是为了让我们生命更丰富自足,让你能感到确实有一种称之为“灵魂”的东西存在于体内。诗歌的高贵也在于此。
王威廉:我想追问,小说也可以让人的生活更丰富,诗歌的独特性在哪?
冯娜:诗歌直逼人的心灵。西方谚语说狐狸知道所有的事,但刺猬知一件大事。有时觉得似乎小说家知道很多事,但诗人知道一件大事。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一只大动物,除了知道很多的小事之外,还应该洞悉更多的大事。散文写得好可以被称为散文家,小说写得好可以被叫做小说家,唯有诗人只能被称为诗人,因为诗和人是完全统一的,诗是灵魂最直接的袒露,这就是诗歌的独特性。
王威廉:问个不着边际的问题,你觉得诗人和作家这个职业会消亡吗?
冯娜:不会。只要有人类还在这颗星球上繁衍,文学也就会生生不息。只要人类的灵魂不完全可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笑),文学依然是人类内心珍贵的渴求,他们不会让其熄灭的。
二、批评的坚守
王威廉:唐诗人是个批评家,却有个很响亮的诗人的名字,父母是文学爱好者吗?
唐诗人:我父母是农民,母亲不识几个字。但我父亲可能有读过一些文艺作品吧。前几年,我带了本谢有顺老师的著作回去,他翻看了谢老师评论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的那篇,还跟我说这本小说很不错呢。不过,我印象中他其实不读文艺类书籍的,他一直喜欢研读风水堪舆类的书。
王威廉:你作为一个批评家,写过诗吗?
唐诗人:肯定写过诗的,这个年代的文学爱好者,有几个没写过诗?我喜欢古典的诗,但我觉得永远也写不过唐诗,所以就写现代诗,一直在写,现在有感觉的时候也写。但我对自己的诗非常不满意,虽然在我看来比现在刊物上的很多诗歌要好,但还是没有写出我希望的水准,所以我不以写诗为傲,更不以它为业。
王威廉:不写诗仅仅是因为写不好吗?有没有意识到诗人的生存更艰难?
唐诗人:确实有考虑。其实不仅仅是写诗,靠写小说为业,生活也很艰难。你们现在是写到一定程度了,可以不愁发表途径了,其实大多数写作爱好者,不管写什么,他们的前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在为发表发愁。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作为一个专业作家而生活,我也不可能为一个文学目标而放弃一切。我觉得,诗人也好,小说家也好,最好有一份与写作没关系的职业。现在很多作家的作品,内容永远是作家圈内和文学爱好者的故事,这是公众不爱读当下文学的一大缘由。
王威廉:从历史上来看,有没有一个时代对诗人和作家来说是生存境遇最好的?
唐诗人:1980年代或许是吧。
王威廉:李白和杜甫是怎样生存的,有没有研究过?
唐诗人:没特别研究过,但大家都明白,他们其实也为生活发愁,所以要写诗来换得皇帝或者有权位者的赏识。但是,有一个现象是,很多诗人,比如苏东坡,生活好的时候写的诗并不好,落魄的时候反而写成了最好的诗歌。
王威廉:1980年代一个人能写出一首好诗,全社会就会为他敞开大门,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其实,中国当代的文学制度,尤其是作协、文联这些组织机构,都是从苏联借鉴过来的,在过去,所有的作家都要接受这些组织机构的管理,现在肯定不是了,甚至不妨说,在今天这种恶劣的文化生态下,许多优秀的作家反而在这些组织机构里得到了生存的保障。对此,想听听你的看法?
唐诗人:对,现在的作协跟以往、跟大众以为的作协,性质已经大变了,现在加不加入作协都说明不了什么,体制内和体制外其实都差不多。现在所谓文坛,其实有好几个层面的意思。作协是一种文坛,媒体是另一种文坛,出口转内销的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还有别的比如郭敬明那套,又是另外一种文坛。这么多“文坛”,哪一种更公平?就我目前的了解,恐怕作协还更可信。当然,渠道多是好的,作家被认可的方式多了,被埋没的几率很小。
王威廉:市场经济对文学的改变究竟有多大?
唐诗人:这种改变可以有很多层面的解读。这里,我就从生存环境与精神内容层面来说吧。市场经济改变了作家的生存环境,也必然改变作家的精神内容。面对时代的变化,是随波逐流,以迎合的方式成为时代的明星,还是以拒绝的方式,坚守文学的精神取向,成为时代风气的批判者,这些都是作家面对新时代的选择。这些选择,可能是很多作家都要面对的,但生存的压力有多大,并不意味着精神上就要屈服于商业,他可能写出更具批判力的作品出来,而很多生活条件很好的作家,作品精神却越来越俗。所以,生存环境与精神内容,在文学写作这一行业,是很复杂的问题。
王威廉:在爆炸的信息碎片中,在市场的多彩泡沫中,我觉得文学批评一定要有斗争的激情,在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物之阵”里举起长矛,才能刺穿诸多意识形态的幻象。
唐诗人:写作都要有激情,作家没激情也很难写出好东西来。批评家的激情,很多人以为就是批骂,我理解的激情是对文学和对批评创作的持久之爱,只有热爱和坚守,才有批评的激情,否则就都无所谓了。当然,批评的激情,如你说的,在市场环境下,应该是举起长矛去刺穿假象、幻象。现在很多的批评,是与市场形成了合谋的。我观察到,很多青年批评家的欣赏趣味和大众的阅读趣味没什么区别,对此他们反而很欣慰,以为自己有很多支持者。我觉得,作为专业研究者,对“有很多支持者”这样的心理是要保持警惕的。
王威廉:今天的批评家主要都集中在学院了,因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存在,使得批评家其实比诗人和作家的生存更有保障。
唐诗人:确实,但如我刚才说的,在学院有保障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批评创作就会有多好的改观。我们的高校培养出来的学院,与西方传统中的学院并不一样。我们的学院也很世俗,市场和政治的诱惑,都能很轻易地粉碎学院精神。学院是一种专业精神,是要有坚守的,不是说你在学院工作就是学院派了。
王威廉:文学批评在文学的知识生产当中被边缘化,在高校,研究古代文学的看不起研究现代文学的,研究现代文学的看不起研究当代文学的,研究当代文学的看不起做文学批评的,这种古怪的学术等级,值得我们好好去反思。
唐诗人: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我觉得这里的反思,不仅仅是提出不满,更多的是思考这种“看不起”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做批评的会让其他研究者瞧不起?或许有着学术传统的缘故,比如对时间的迷恋。但与其去分析这个,还不如多思考是不是我们没有做好批评导致的?可能人家不是瞧不起这个行业,只是看不起不学无术的批评,真正有坚守、有能力的批评家,最终还是会受各个行业人士尊重的。所以,我们可以不去在乎别人的心态,但要以此为动力,做好批评,写好文章。
王威廉:首先要尊重自己的岗位,做好自己的专业。很多学者认为当代文学作品没有经过时间的洗刷和淘汰,里面的精品很少,他们会觉得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唐诗人:对,但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人,就是在做这种工作,去发现精品,没有当代文学批评,也就没有所谓发现和沉淀。
王威廉:评价的系统应该是读者、媒体与批评家三位一体的,但毫无疑问,批评家的位置要重要得多。
唐诗人:批评家有很多种,文化记者是一种,学院批评家是一种。本来,学院批评家是一种比较保守的批评,他们做的往往是历史总结性的工作,都会落后于媒体和公众的接受。但是,如今的批评家,承担的职责还包括发现,所以这种三位一体是复杂的。批评家,包括文化记者和学院的,他们发现的优秀作品,都需要媒介推广,公众的阅读文化,也需要媒介来呈现。但是,这三位一体太和谐了并不好,也就是我前面讲的“合谋”。学院批评家要用专业的眼光去批评,不能随大流。
三、媒介和传播,能改变文学吗?
王威廉:信息时代来了,纸媒衰败得触目惊心,网络几乎改变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和生产方式。
唐诗人:确实,纸媒的影响力已经很弱了,这种弱不仅仅是被新媒体压倒的弱,也有它们自身的问题,过于拒绝和过于迎合大众文化,终究会被这种文化所吞噬。所以,重要的还是坚守,坚守的不是某种载体,而是那种专业精神。因此,如今的批评,学院的声音还是最具影响力。但是,网络时代,学院的声音如何到达大众的视野?网络是杂乱的,在那么多信息的情况下,人们无法选择,于是就只好选择代表权威的官方信息了。在媒体太乱的时候,独立性的声音是很难发出来的,需要批评家去寻找这样的渠道。
王威廉:诗歌的变化其实最明显,诗歌原本是很依赖于文学杂志的,但自从网络兴起,写诗成了最便利的文学行为,似乎分行的文字都是诗了。冯娜,你有没有上网写诗?
冯娜:“上网写诗”包不包括写好诗后在网络上传播?如果包括,那在这个信息时代几乎没有诗人不触网。网络传播范围之广是病毒式的,现在你在网上贴一首诗,所有“粉丝”都可以看到,经过转发,可以读到的人数呈数倍增长。传播迅捷及时是这个数据化时代的特征,网络信息的发布基本上没有门槛,大家随便分个行都可以自称为诗人。各种口水诗、“乌青体”“食物诗”被很多人转发,炒得沸沸扬扬。好像有过调查,3000字以上的文章很难在网络上读完,分行文字会比较容易阅读。网络导致载体的改变、阅读习惯的改变,也导致了人们认知能力和思维模式的改变。网络对诗歌的冲击比小说大。
王威廉:我发现当代诗特别依赖于阐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阐释,也许好诗也不被理解;但有好的阐释,也许不起眼的句子也会变成意味丰富的作品。诗人赵丽华写过一首在网上很有名的诗,“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评论家对这首诗竟然也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你们是怎样看待当代诗歌对批评的这种依赖现象的?
唐诗人:你说诗歌对批评的依赖现象,我觉得好诗不依赖批评,靠直觉就能感受到它的好。我们说看不懂,当年的朦胧诗,有几个人说看懂了的?还比如艾略特《荒原》,那么深奥,但读了之后我们即使不明白,也能感觉到那是好诗。诗歌的力量要直抵人心,不是靠长篇大论来抵达。评论只是把评论者个人所感觉到的东西用评论的文体表达出来而已,靠评论来评价一首诗好不好是不妥的,这不代表诗本身好不好,而只是诗歌评论的好与不好。
冯娜:当代诗歌的情况跟当代艺术差不多。当代艺术依赖很多阐释,也会存在过度阐释的问题。例如一部电影网络上有很多人把一个电影细节阐释得非常繁复,但电影里可能根本不存在这么多内涵,完全属于观众再创作的过程。从丰富性上来说,读者也分为精读读者或者普通读者,我觉得这些并不是特别重要,如唐诗人说的好诗都是直接抵达的。我们写作者并不在意这些后期的阐释,在我们自身的写作逻辑和系统中,已经包含了自我阐释。可能小说家更需要这样的阐释系统存在?
王威廉:说起自我阐释,在诗人身上的确很突出,当代诗人很多是诗歌批评家,像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于坚、臧棣,等等。
冯娜:诗人直接进入诗歌评论这个过程更让人信服。有些学院派对诗歌的批评,我认为有很强的滞后性,而且这种滞后性是必然存在的。诗人置身于诗歌的当下,他们对诗歌的观察、对诗歌进展的把握都是第一现场的,这样的评论与诗歌写作产生一种更密切的呼应,更容易让人接受。
王威廉:这其中是否隐含着作为诗人的焦虑心情?他不被理解,只能亲自提刀上马。
冯娜:有自我的焦虑,也有知音少的感喟。还有可能是,在被别人阐释的过程出现了非常多的歧路,站出来自我辩白。另外,一个严肃的写作者在作品完成后的某些阶段,会对自己的写作有所反思,或者有未完成的地方再做进一步阐释。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理解。
唐诗人:诗人自己去阐释,我觉得也不可信,意图谬误的说法已经众所周知了。评论家去评论,往往不是要去还原诗人的本意。好的作品,它应该具备足够的意义空间,能够不断地被阐释,能跟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读者形成新的情感契合点。所以我觉得,诗人,或者小说家,心胸要宽阔一些,不要在乎不合本意的评论。《哈姆雷特》被弗洛伊德阐释成这样,莎士比亚会高兴吗?但因此《哈姆雷特》在理论界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冯娜:说到文学阐释和文学本身的问题,可能不单纯是写作者本人在意与否的问题。阐释有可能会使文学变成一种事件或现象而引发关注,这个涉及到传播学的范畴。文学写作是一回事,如何传播文学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时代是信息充分甚至过度化的时代,传播有时会比写作显得更加重要。你写作出来的作品不去传播它,就会被大量的东西遮蔽。好作品会被不好的覆盖和淹没,后世怎样发掘这些东西我们不得而知,但发掘在今天都已经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所以传播显得特别重要。
王威廉:网络刚刚发展的时候,我们说信息时代太好了,有才华的人一定不可能被遮蔽的,一个平等的社会来临了。目前还不到二十年,我们发现,在大海一般的信息中,这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而是一个平面的社会,因此,眼球效应主导的传播方式越来越重要了。说到这里我想起诗人余秀华,她的传播方式似乎很典型。
冯娜:余秀华走红除了她的诗歌本身之外,更多是其他因素。她的身世境遇,比较有新闻性。而且她在春节前后走红,这是一个比较值得研究的点,这个时间点暗合传播上的有效时间段。一个女诗人生活境遇不好、身体不好行动不便,还写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样的诗,都是容易引发热议的话题,大众往往饱含廉价的同情心,觉得余秀华能写出这样的诗特别了不起。单从文本来说,如果没有新闻事件般的传播力,这些诗会非常容易淹没,很多的人都在写这样的诗。在谈余秀华的同时,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另外一个诗人,许立志,一位1990年出生的年轻诗人。他跟余秀华一样来自社会底层,是一名打工者。我跟很多人一样,是许立志的自杀事件引发的关注才读到他的诗。余秀华因诗歌走红后获得了很大的帮助,可能对她现实生活有所改善,一个诗人通过诗歌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很好。而像许立志的诗歌传播却在身后。就传播的有效性而言,我们能说在余秀华身上就是有效的吗,在许立志身上就是失败的吗?也难界定。他们俩人的生命体验不一样,诗歌风格各有千秋,他们都通过诗歌反抗和控诉自己的命运和时代,殊途不同归,但我们能说余秀华就是一种成功,许立志就是一种失败吗?我们这个时代要通过文学事件才能进入文学本身,这也是这个时代的隐喻和病征。
唐诗人:我觉得余秀华的诗特别适合放在自媒体里传播和阅读。传播学有观念说,载体是会影响文体的。我们也可以想象,要是没有发明纸,没有印刷术,长篇小说是不太可能产生的。靠竹简来书写,一部《红楼梦》都要一卡车来装,即使写了也不会有传播和影响。余秀华的诗就特别适合新媒体,但你看现在各种微信号都在传播诗,为什么那些诗就没办法流行?除开冯娜刚说的那些外部因素外,还有就是诗本身的因素。
王威廉:适合手机看的诗有什么特点?
唐诗人:没做专门研究,但我感觉,这是因为她的诗句短促、有气,语言像说话一样,但又很有诗意,而精神上,有些诗又有着鸡汤的性质,有些诗又在泄愤上表达得轻巧流利。另外就是,很多诗句的字眼可以吸引人的眼球。
王威廉:载体的变化引起了阅读习惯的变化。
冯娜:传播学家伯纳德·科恩曾有这样一个著名论断:在许多场合,媒体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地成功的。大众媒体会引导受众的思维,余秀华这个事件可以看成是网络时代文学传播的一个典型案例。
王威廉:传播渠道的确会影响文学形式。有人就说,微博的一百二十个字,让我们的文学中有了一种“微博体”。
冯娜:文学本身也作为一种载体而存在。
唐诗人:报纸也在转型,但他们不会说把以前纸质版内容放在自媒体就叫转型,新媒体决定了新的思维方式,才会有新问题。我们一直在讲文学外部的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谈外部如何影响内部。不仅仅是传播,包括很多制度性的东西。在研究界,比如文化研究为什么兴起?这不是内部理论自然而然的发展,美国一段时间新批评很流行,修英语文学专业的都学这个,因此这个方向毕业出来很多人,但是这方面的岗位有限,所以他们要到其他岗位去工作。如此,就有了综合。交叉之后的研究著作,若形成了影响力,就会影响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向或者研究方向。
王威廉:文化批评的转向还隐含着文学影响力的下降,介入社会科学的话语,并向整个社会领域敞开,试图重获注意力和影响力,也是文学批评发展的内在寻求。
冯娜:我们谈了许多诗歌方面的问题,小说方面呢?
王威廉:小说家的生存状态,跟诗人和批评家还是有所不同的,也许,目前只有小说家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了,尽管这种机会也日益渺茫。像韩寒、郭敬明等人,把小说的经济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却也是无法复制和再现的。小说的传播渠道目前主要有期刊、出版、网络这三种,期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但期刊上的小说离经典艺术是最近的。出版社是纸媒时代最重要的阵地,但也是困境重重。眼下“经济效益”最好的是网络文学,你们有没有看网络小说?
冯娜:作为现象会了解,具体内容就很少看。类似《甄嬛传》这种大红大紫的作品,等稍微冷却后会去了解一下。网络小说一天能码那么多字,要保持更新率,没有办法深耕细作如琢如磨。他关注的是点击率和粉丝,当下的写作跟读者形成一个及时的反馈通道。对于我们来说,是整个作品完成之后再展现作品,而网络作家跟读者的互动非常及时频繁,甚至读者的意见也是他们作品的一部分,作家根据读者的反馈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跟美国的电视剧差不多,人物如何调整剧情怎么发展,会根据读者的反馈和收视率来调整。这种在传播的写作中传统作家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根本不可能预测读者是哪些,并根据他们的反应来写作。
王威廉:网络文学在中国格外发达,其他国家没有所谓的网络文学。在美国有通俗文学,像恐怖大王斯蒂芬·金,他在网络上销售电子书卖得很火。网络只是作为销售的平台,并没有改变小说的形态,更没有变成全民式的写作运动。
唐诗人:我们所谓的网络文学,内在是空的。这种空是说读和不读都不影响什么,比如一个阅读了几千万字数网络文学的读者,他的价值和意义追求不会有多少变化,而一个纯文学阅读者,可能会因为一本书、甚至一篇文章而改变他的人生。网络文学这样疯狂,跟我们阅读文化没有成熟有关系。我所谓的阅读文化,是说对一种文学类型的爱好,会培养我们的专业意识,是有质量追求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阅读文化是打发时间的阅读,于是最容易接触到、最方便阅读、最好理解的就最流行。现在人不是没有时间读书,而是不愿意读书,有点困难就不读,觉得这么累了这么辛劳还要在阅读上费心思是一件不必要的事情。西方阅读文化发展得比较成熟,他们的后现代是真正的后现代,即使是对娱乐性、消遣性的文化,也会愈来愈专业化。但我们不一样,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精神还是浮在我们上空的存在,但后现代物质却已经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因此,前现代的阅读心理,去面对后现代的文化产品,必然是乱象丛生。
四、启蒙:一个日益冷僻的字眼
王威廉:上个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是很强的,都是心怀天下,要启蒙民众。但大众文化铺天盖地而来,短短几年时间,启蒙竟然变成了一个冷僻的字眼。
唐诗人:启蒙是自己启蒙自己,不是别人来启蒙,或者去启蒙别人。自己启蒙自己有自觉性、懂反思了才叫完成。西方进入后现代性没什么大不了,但中国的后现代文化是一种乱七八糟的文化。没有反思的能力就去享受后现代,那是不可承受之轻。体现在阅读上,就是我想阅读就是什么,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分子来教导我。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非常自大,越不读书的人越自大,读了一点书半桶水状态的更自大。
王威廉:在信息社会中,人有种幻象,好像我什么都知道,因为我可以立刻去百度。这就是所谓的“知道分子”,知道分子面对知识分子的启蒙,他会说:对不起,你说的东西我都知道。
唐诗人:我以为,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区别就是在反思能力上。知识分子不是叛卖知识的人,而是传播思想的人,从知识到思想是有难度的。要用系统性的知识去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生产独立的意义理解和价值信念。
王威廉:知识的占有跟知识的创造是两码事。
冯娜:仅仅知道,占有的也是知识的碎片,这些碎片能不能形成一个整体,有赖于对知识的系统、深入的思考和消化。所有岛屿最终能不能相互连接,需要要寻找到能够托举它们的板块和水源,这些沉在底下、有托举力的东西才是更重要的。
王威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生存,就是“活着”的问题,早已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要活得更好。“活得更好”这种愿望似乎更容易让人迷失,因为“更好”是没有具体尺度的,欲望变得像迷雾一般弥漫了。因此,人们内心空虚,总是渴望着什么,却忘记了对文化和心灵的追寻就是救赎的捷径。
冯娜:以前是生存的焦虑,现在是生活的焦虑。我跟朋友一起从事一些文化传播方面的事情,类似一种实验。在这个实验过程中,我们早先的预期也是认为像你说的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有不少是社会精英层面的,他们应该会有一定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但实验的效果跟我们的理想差距巨大。这些人的生活落实到日常的24小时当中往往是:我这么辛苦工作赚钱,赚这么多钱是为了让我愉悦,哪怕这种愉悦很肤浅,我真的不想再理解什么更深刻的东西。人们往往显出这种高度物质化后的疲态。所谓启蒙,首先人得具备启蒙的自觉。这种自觉承担的必然是重的事物,而人的现实处境已经有太多不能承受之轻的,没有多少人具有这种自觉承受重的能力。所以知识分子显得更加重要,真正的灵魂引导也显得更加重要。
唐诗人:文化问题上,年轻人永远是主力。因为文艺跟理想跟激情有关,甚至跟情怀、情调相关,所以这天然就是青年人的东西。中年之后,若不是专业研究者,多数会转向历史、哲学、科学著作的阅读。当然,这也跟一个民族的文化习性和个人的兴趣爱好有关。但文艺确实更是年轻人的事业,所以才有文艺青年的说法。
王威廉: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她说在信息社会,我们的文化传承是一种“后喻文化”,也就是年轻人引导老年人的文化模式。举个例子,各种软件的运用,年轻人更加容易上手。但是,由于社会政治结构,话语权还是在长辈那里,这其中便有了复杂的辩证关系。
唐诗人:正因为话语权被长辈掌握着,青年人才会有不满,但现实中这种不满是难以表露的,所以他们会在文学艺术上反抗,在阅读或者写作中得到呼应和发泄。而当他们进入中年之后,曾经的反抗,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都会进入一种深重的反思和沉淀状态,因此,也就成了新一轮的长辈式文化结构。
王威廉:也许是中西两种文明的本质不同。大而化之地说,我们更加注重历史,而西方更加注重哲学。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文学跟历史,他更看重文学,因为文学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要比已然发生的历史更加重要。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也许恰恰相反。
冯娜:这样来看,可能在当下中国,大众降低了对文学的期待,同时也降低了文学的难度。大众在阅读的时候更容易接受通俗易懂的、不费脑力的作品,作为写作者要是完全认同了大众的阅读趣味,就流于通俗文化的制作。文学向大众和市场献媚的倾向,在当下十分明显。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有必要调整自身对文学的期待和对文学更高层次的理解。写作者的善变和坚守要放在一块儿地来看待。
唐诗人:你坚持一些东西才能引领时代,很多人去迎合一个时代或者迎合一批读者的趣味,但往往很快就被淹没。时代是什么?读者趣味是什么?这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与其花心思去适应本就不确定的东西,不如坚守一种自我确信的精神品格。
冯娜:其实就是各种价值的排序。文学有自身的文学价值,把它区别于商业价值和传播价值,客观看待文学的本质,坚守这种文学精神和价值形成标杆自然会引导一些人。我们现在确实存在文学价值的力量并不强大的问题。这有赖于更多具有文学信念、严肃生命力和创作力的作家们共同努力。
王威廉: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表面上似乎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实际上,人们的日常生活反而变得越来越贫乏。对财富的极度渴望,当代中国人估计会是空前绝后的。你的职业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年薪有多少,这样的价值判断与文学艺术的价值判断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我深信精神的价值、人心的判断以及艺术的力量,我也深信我的这个“深信”并不稀罕,是蕴藏在每一个人心底的种子,只要条件适宜,便会发芽生长,破土而出。
责任编辑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