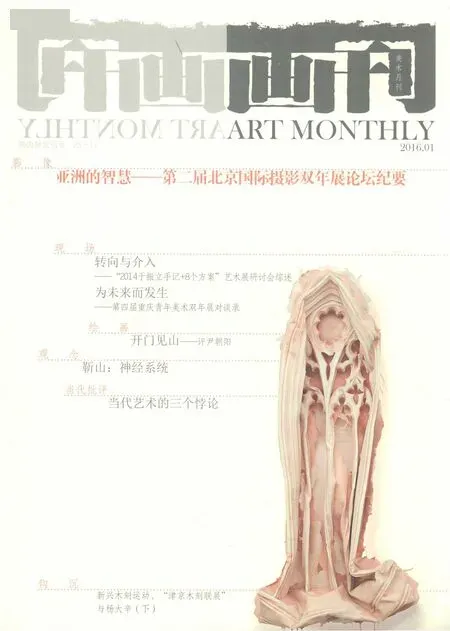贡布里希的神经元[1](上)
(英)约翰·奥尼恩斯(John Onians) 翻译:梅娜芳
理论研究
贡布里希的神经元[1](上)
(英)约翰·奥尼恩斯(John Onians) 翻译:梅娜芳
“我的方向一直是生物学的。我总是试图追寻到问题的最初点。”[2]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句话是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1909—2001年)提出来的,但事实确实如此。此话出自迪迪耶·埃里邦(Didier Eribon)尖锐的长篇访谈《毕生的兴趣:与迪迪耶·埃里邦谈艺术与科学》(1993年),此书似乎比较清楚地总结了贡布里希对其事业的看法。我说“似乎”是因为贡布里希获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在于他有这么一种能力,在他谈论或阐释某事物时,似乎解决了某些问题,判定了某些议题;但稍后,他只要改变几个句子,就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复杂情况,甚至否认我们认为他刚才提出的主张。

图1 “兔子还是鸭子?”,图片来源: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伦敦,1960年,图2。
现在的情况就是个绝佳的例子。迪迪耶·埃里邦对他的话确信不疑,并继续问道:“但在《秩序感》这同一本书中,结合文化解释、生物学解释、社会学解释和美学解释,难道没有问题吗?”贡布里希巧妙地躲开了这个语言陷阱,回避似地回答说:“这只是陈述上的问题,并不是理论上的问题。”[3]他把讨论带离了危险、沉重的理论领域,而是进入到更温和的修辞学氛围,这样,他为自己创造了足够的空间,可以朝着他喜欢的任何方向延伸话题。我们发现,这次采访更前面的对话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那时,贡布里希引入了风格具有生态学特征的观点,他还进一步解释了“生态学”一词对生物学家而言意味着什么,但他紧接着又说:“当然,我用这个词只是一个比喻。”[4]加上这么一个说明,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或随意或严谨地使用这个术语。接下去,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他赋予该词以严格的意义,并用它来反对黑格尔派的强硬对手。“但是,”他继续说,“我认为它(即生态学)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少要精确一点,请允许我们这么说,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初级生产创造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创造了特定的风格。我认为:有更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使特定的风格能够蓬勃发展。一旦这些因素发生了变化,这种艺术风格就会消亡。”[5]这是典型的贡布里希式的做法,他宣称用生态学作比喻要优于马克思主义用建筑学作比喻,因为那更“精确”,然而,这种精确完全在于生态学的比喻更开放,可以适应更多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比喻表面的精确性恰恰使它变得不那么精确,它显得过于简单、过于程式化。贡布里希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处理复杂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比喻提供不了这个空间,而生态学中的生态观念则可以。我们再一次清楚陈述了他对生态学的兴趣,但我们再一次无法确定他是真的对科学感兴趣还是只是用它作一个比喻。
有两个主要理由可以说明这种不确定性。首先,一如我们所见,这使他的方法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同时使其他人更难证明他是错误的。其次,他似乎总能感觉到人文主义者不愿过于接近科学世界的犹豫。既然他只是用科学打了个比喻,那么,无论这个比喻意味着什么,他都无需进行科学家那样的缜密实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的调查提供个人标准。我们要记住:对贡布里希而言,讨论科学和人文学科间的界限是令人振奋的,这是出于他与卡尔·波普尔的亲密关系。他和这位科学先知的友谊为他提供了科学上的特殊便利,但同时也使他意识到,科学工作者的判断异常无情。贡布里希对待生态学的态度很模棱两可,可以说,他对待科学的态度一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他的著述充分利用了科学知识和理论,但听上去还是那么不科学。波普尔学派的科学方法非常严谨,这或许会约束历史,甚至伟大艺术家的进程,但却没有束缚贡布里希,因为贡布里希更喜欢让自己成为故事的讲述者,而不是科学家。
下面我们还会完整地阐述贡布里希和科学之间的关系,但眼下我们必须先来看看他和生物学以及生物学比喻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为他带来了两方面的好处。首先,生物学允许他弄清事物的源头;其次,生物学为他提供了接受事物复杂性的解释框架。他或许不是一个生物学家,但当他想要尽力理解艺术时,他看到了生物学的优势。
贡布里希对生物学的兴趣具有很深的根源。他记得在维也纳的童年时代,父亲曾想带他去广场另一边的艺术史博物馆,但他却被自然史博物馆所吸引。当他在维也纳成为艺术史专业的学生时,他的老师是沃尔夫林、李格尔等学者的学生,而沃尔夫林和李格尔等学者的生活已经因为达尔文和神经学的发现而有所改变。当他来到英国瓦尔堡研究院——他最终成了那里的院长——的时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研究院的创立人阿比·瓦尔堡撰写传记。阿比·瓦尔堡曾于1889年记于佛罗伦萨的日记中写道,他在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找到了“一本最终能帮助我的书”[6]。贡布里希有很多理由对自然界产生兴趣。
然而,与此同时,他也有很多理由不从生物学的角度进行思考。最重要的理由在于他充分意识到这种思考会带来一定的危险。他在奥地利长大,作为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他在二十几岁时经历的反犹太主义,三十几岁时经历的纳粹主义,使他对生物学尤其是遗传生物学心怀警惕。在埃里邦的访谈中,在谈到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时,他说:“因为他基本上是个生物学家,我怀疑他到死都是种族主义者。”紧接着,他又用典型的顽皮方式补充了这么说的证据,因为康拉德·洛伦茨去世前曾在维也纳遇到贡布里希,并告诉贡布里希,他认为犹太人在哪都是最聪明的人,“这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的看法”[7]。
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他从来不提对DNA的发现,从来不讨论DNA的潜在含义,但他避而不谈大脑及其运作,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他的回避很有体系,所以肯定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只有几次提到了“大脑”或“视觉皮层”这个局部区域,这可能是一时疏忽。无论如何,如此系统的回避肯定遵循了一定的原则,我怀疑这是一项令人敬畏的原则。他更愿意把大脑看成是细节隐晦不清的“黑盒子”,或者是容纳之物过于神圣的“至圣所”(Holy of Holies)。更确切地说,他更愿意那样看待人类的大脑。当他偶尔几次用到“大脑”一词时,指的都是机械性刺激或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回应,这可能不是出于偶然。他在《艺术与错觉》(Art and
Illusion,1960年)中描述了廷伯根(Niko Tinbergen)对刺鱼的研究,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写道:“当红色邮车隔开一段距离驶过窗前的时候,廷伯根的鱼缸里的刺鱼总会摆出某种姿势,因为在它们的头脑中,红色是表示危险和对抗的。”[8]但他不喜欢用生物学或机械的方式看待人类的思维。
他害怕人类与动物或者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同化,紧接着上面所引句子之后有一段话,最能说明他的这种害怕。在解释了康拉德·洛伦茨和廷伯根对鸟类和鱼类等动物如何对人造物作出回应的证明之后,他指出:这些动物拥有很多与人造物相同的特质,但进化使它们习惯于对人造物做出反应。在暗示了我们在处理艺术时也会有类似的反应之后,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保留意见:
我不相信通过研究海鸥,拉斐尔的秘密就会有得到揭示的一天。我完全赞成那些告诫我们不要对人的天生反应做轻率推测的人的观点——不管他们是属于人种学派还是荣恩(Jung)学派。人的尊严,正像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的看法一样,恰恰在于人具有普洛修斯(Protus)神那样千变万化的能力。我们不是简单的自动售货机,向我们一投硬币就开始行动,因为我们不像刺鱼,我们有心理分析学家称之为“自我”(ego)的东西,它能检验现实,并且给来自本我(id)的各种冲动赋形。[9]
他在《艺术与错觉》的导论中讨论了李格尔,流露出他对打着科学名义的机械简化论的反感。他说:“然而被他视为科学方法的标志的这种一心专注的作风,使他成为前科学的习性(pre scientific habit)的俘虏,那是帮助极权主义原则扩散的习性,也就是编造神话的习性。‘造型意志’,即Kunstwollen,就变成机器里的幽灵,按照‘不可抗拒的规律’推动着艺术发展的车轮。”[10]他是如此反感用机械的方法解释科学,但这种反感非常理性。他在后面几页中反对简单地用进化论来解释风格的转变,从中流露出一定的嘲讽之意:
假如一切变化都是定数难逃的、完全彻底的,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资比较,没有任何情境可资设想,没有任何征候或表现可供研究,于是变化就成为变化本身的征候。为了掩盖这种重言反复,就不得不引入一些富丽堂皇的进化方案,正如李格尔,也还有他的许多后继者的做法一样。当前相信在若干历史时期中人类已发生了什么明显的生物学变化的历史学者微乎其微,人类学者更少。但是,即使是承认人类的遗传结构也许略有变化的人,也绝不赞同说人在过去的3000年中——不过100代人罢了——已经发展了像人的艺术和人的风格那么大的变化。[11]
在这基础上,贡布里希拒绝运用智人(Homo sapiens)生理学中受遗传控制的变化来解释文化变化。
有个类似的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几乎从来不提眼睛的解剖,只是偶尔才提一下视网膜,虽然他曾努力研究透视和双眼视力。同样,他也没有解释视网膜的生命中枢——视网膜中央凹。他所做的最多的就是谈论一下“中央凹的运动”,当他根据行为来讨论事物时就会倍感幸福。他在处理感知生理学时的迟疑更令人惊讶,因为他居然准备与理查德·格雷戈里合作编辑《自然和艺术中的错觉》(1973年),他在该书中编入了年轻读者科林·布莱克默分析神经活动的一篇重要文章,此文主要针对大脑神经网络的详细功能[12]。他注意到,布莱克默对人脑的一切推论都以对猫和猴子的研究为基础,或许正是这点使他不愿运用布莱克默的重要结论。也许,贡布里希只是宁愿忽视这样的研究,就像他在《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1950年)的早期版本中不曾涉及抽象艺术那样,因为他认为这有损于书中那些更具艺术创造力的作品。有些原则是贡布里希绝对不会跨越的界线,哪怕他对此深感兴趣。
幸运的是:我们无需再这么谨小慎微,现在,我们已经有望重新探讨他的一些论点,知道神经生物学和神经心理学在哪些地方支持或削弱了他的主张。我们可以以他在第一本艺术史著作——《艺术的故事》中的某些言论为例。在论史前艺术和原始艺术的第一章中,贡布里希谈论了艺术在他所说的原始人的巫术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艺术和巫术间的关联在20世纪中叶还是个陌生的观点,但正如他让读者想起的那样,这离我们自己的经验并不是那么遥远:
只要我们愿意不欺骗自己,愿意看看我们身上是不是也还保持着某些“原始”的东西,就足以解决问题。我们不讲冰河时代,且从自身开始。假设我们从今天的报纸上得到一张自己心爱的夺标者的照片,我们愿意拿一根针去戳他的眼睛吗?我们能像在报纸上别的什么地方戳了个窟窿一样无动于衷吗?我看不会的。无论我那清醒的头脑是怎样明了我对照片的所作所为无伤于我的朋友或英雄人物,我还是隐隐约约地感到对损坏相片心有抵触。不知在哪里还是存在一种荒唐的心理,觉得对相片的所作所为就是对本人的所作所为。[13]
在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贡布里希对自身经验的运用,比如,话题从原始艺术转到“我们”,再到他自己。对他而言,将有教养的现代艺术史家和原始人等同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他用“荒唐的”来描述自己的感觉就多少暗示了这一点。
然而,这种看法并不是他的新创。早在19世纪末,也就是他的老师们接受教育的那个时期,移情理论中延伸出一个特殊理论,产生了感应巫术(sympathetic magic)的概念。感应巫术是早期文明和文字出现前,人类信仰体系中的关键原则。有个我们最熟悉的例子,那就是认为损害蜡像或木像就会对雕像所代表的人物造成真正的伤害。通过移情理论的其他特征,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现象之所以如此普遍,是因为人类具有普遍的生物属性,其运作植根于人脑神经网络的遗传特性。人类精神活动的复杂性之一在于我们的大脑能够形成网络,将某个特殊的物体和其他我们经历过的,且在某个方面有所关联的任何物体联系起来。比如,神经网络不但能把某人与其外貌、姓名联系起来,还能将某人与其所拥有的物体、所认识的人、相关的场所联系起来,一旦这些联系牢牢建立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就会认为:伤害某人的雕像或名字,甚至任何与他有密切关联的东西,都如同伤害了他本人。这种作用机理可以引发某些现象,比如罗马人的除忆诅咒(damnatio memoriae)现象,即损坏某人的雕像和名字题记,就能删除某人的记忆;再比如对圣像的破坏、现代的破坏艺术,这些现象都建立在神经心理学的基础之上。有人认为这种联系具有生物学的基础,这样的观点在猿猴的相关行为中已经得到证实。比如,在黑猩猩身上已经发现了某个最能说明问题的行为:当某只黑猩猩被另一只黑猩猩伤害以后,受伤的黑猩猩报复的并不是曾经伤害它的那只,而是与后者亲近的黑猩猩。显然,在受伤的黑猩猩的神经网络中,把朋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里面可能包含了某个团体的所有成员,伤害其朋友就等于伤害最初实施伤害者。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大脑中的脑岛皮层才能体验真正的痛苦和替代性痛苦。贡布里希经常在家中阅读报纸,通过家庭环境中这种简单的反省行为,他发现了一种方法。现在,在实验室科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动物行动学家的努力下,我们已经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方法了。
除这段话以外,生物学在《艺术的故事》中也发挥了一点小小的作用。在10年后,即1960年出版的《艺术与错觉》中,虽然没有直接谈论生物学,但贡布里希多次暗指大脑和动物行为,后来,科学再次证明,其中的很多暗示都能得到证实。在该书的导论和后来的篇章中,贡布里希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兔子和鸭子的错觉暗示[14]。正如他所指,我们无法同时辨认出兔子和鸭子(图1)。他用这一观察结果来反驳错觉是个简单现象。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对神经网络另一特征的关注来进一步解释这种现象。不要过于机械化,也不要过于简单化,我们就有可能相信,大脑在工作时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能把相似的东西进行归类,比如把动物归为一类,并像书本一样在神经细胞中为每一类提供相应的空间。在极端的情况下,一组神经细胞或许只能在看到单个生物或听到它的名字时才能做出回应。视觉信息通过大脑皮层后到达颞叶。一开始,我们只能辨认出这是某种动物,然后才能判断到底是鸭子还是兔子。无论要辨认出哪种动物,都需要刺激特殊的神经组,所以当然无法同时产生两种认识。大脑的功能是组织我们的现实经历,如果同时辨认出两种动物,就会造成混乱。正如贡布里希所言,我们可以在两种选择之间迅速转移,但我们不能同时辨认出两者,有关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贡布里希对艺术活动中潜藏的机制持保留态度,这妨碍他直接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研究,但他允许那些对绘画机制几乎没有疑问的人,比如温斯顿·丘吉尔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用神经分析的方法研究自己作为业余画家的活动。怀着无可非议的赞赏之情,他引用了丘吉尔对绘画过程的敏锐看法。正如这位才华横溢的业余画家所言:
如果某个真正的权威认真探究在绘画中记忆所起的作用,那会是非常有趣的。我们首先专心致志地注视着所画的对象,转而注视着调色板,然后再注视着画布。画布所接受到的信息往往是几秒钟以前从自然对象发出的。但是它在途中(en route)经过了一个邮局。它是用代码(code)传递的。它已从光线转为颜色,它传给画布的是一种密码(cryptogram)。直到它跟画布上其他各种东西之间的关系完全得当时,这种密码才能被译解,意义才能彰明,也才能反过来再从单纯的颜料翻译成光线。不过这时候的光线已不再是自然之光,而是艺术之光了。[15]
接下去,贡布里希沿着丘吉尔的语调,但强调的却是另外的内容:“我不是温斯顿爵士吁请解释这种奥秘的研究记忆的‘真正的权威’,但是在我看来,只有在我们对他所说的那种‘代码传递’(transmission in code)所知更多之后,我们才能处理这个问题。”[16]无论丘吉尔和贡布里希之间能有多少共识——两人都在战争期间与代码有一定的接触,政治家丘吉尔显然已经注意到业余艺术家和专业艺术家的艺术记忆有一定的差别,这很可能会启发他陈述对于启蒙的渴望。幸运的是,这个特殊现象已经成了近来某些重要研究的主题。
注释:
[1]本文选自奥尼恩斯所著《神经元艺术史:从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到巴克森德尔和萨基》一书(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原文章标题为“贡布里希”。
[2]贡布里希,《毕生的兴趣:与迪迪耶·埃里邦谈艺术与科学》(Ce que l’image nous dit的英语版,巴黎,1991年),伦敦,1993年版,第133页。[3]同上,第133页。
[4]同上,第76页。
[5]同上。
[6]贡布里希,《阿比·瓦尔堡传》(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伦敦,1970年版,第69页。
[7]贡布里希,《毕生的兴趣:与迪迪耶·埃里邦谈艺术与科学》,1993年,第133页。
[8]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伦敦,1960年版,第87页。(译文出自范景中译《艺术与错觉》,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此书译文均同出此版本。——译者注)
[9]同上,第87页。
[10]同上,第16页。
[11]同上,第18页。
[12]科林·布莱克默,《困惑的大脑》,见理查德·格雷戈里、贡布里希编,《自然和艺术中的错觉》,伦敦,1973年版,第9—47页。
[13]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第15版,伦敦,1989年版,第20页。(译文出自范景中译《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译者注)
[14]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1960年版,第4—5页、第198页、第331页。
[15]同上,第34页。
[16]同上,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