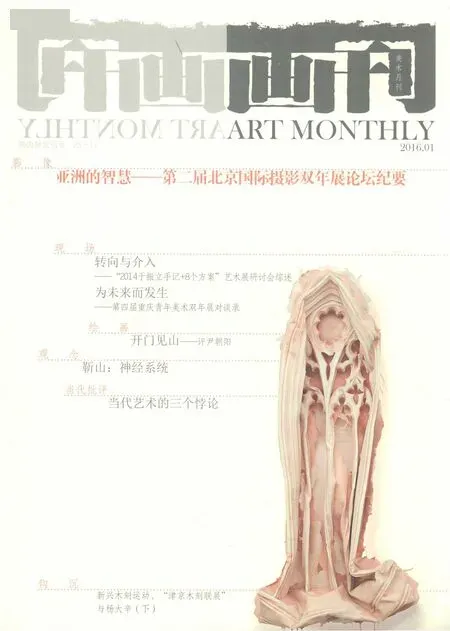转向与介入
——“2014于振立手记+8个方案”艺术展研讨会综述
本刊
现场
转向与介入
——“2014于振立手记+8个方案”艺术展研讨会综述
本刊
2015年12月26日,“2014于振立手记+8个方案”艺术展在北京宋庄艺术国际美术馆开幕。说起于振立,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从政治宣传画到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他一直是“弄潮儿”。然而,1994年,在于振立的艺术创作正是口碑与市场都运转良好的情况下,于振立却放弃一切,退居故乡大连的大黑山。是修行还是逃逸?是厌倦还是蛰伏?多年来,于振立对外界的诸多揣测质疑丝毫不理,只是专注于画画、读书、营建工作室,同时,也致力于扶持大连的当代艺术,时至今日,于振立已经被大连的当代艺术界视为导师。这次在北京的展览由吴鸿策划,展出于振立2014年的《手记》以及8位(组)大连艺术家为其提供的展示方案。展览同期举办了研讨会,策展人吴鸿与批评家杭春晓、盛葳、段君,和媒体人曲振伟及诸位参展艺术家参与了讨论。
于振立的“万神殿”
研讨会上,吴鸿首先介绍了于振立的艺术经历。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于振立以政治宣传画在全国出名。当时的宣传画从画面内容来说,脱离不了那个时代政治宣传功能的需要。但是于振立的画面,还是保持了一种比较鲜活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手法。上世纪80年代初,于振立很快转入到现代艺术浪潮中。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他的抽象表现主义时期。他的《吃喜酒的女人》,当时在全国的知名度非常高。另外,虽然当时艺术市场刚刚兴起,但于振立的作品已经有相对稳定的市场。这一阶段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此前,大家为了一个理想、一种自由精神的表达在从事艺术创作。然而很快艺术作品可以轻易地转化为商品出售,于振立产生了疑惑:到底为什么来做艺术?艺术对社会能产生什么作用?难道仅仅是作品创作出来后被一些商人买去吗?这时他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1994年回到故乡大连,并在12月26日进了大黑山,开始营建工作室。那时候交通和通讯都不便利,于振立在工作室经常几个月都见不到一个人。为打发大山里漫长孤独的时间,他大量阅读哲学、艺术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书,从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阿伦特(Hannah Arendt)、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从病理学到社会学然后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整个线索脉络清晰以后,于振立发现自己的工作方式实际是艺术和社会之间对话的过程。从那时到现在,于振立每年都会写一本手记,记录自己内心对话的过程。

于振立在大黑山

左·《2014于振立手记》封面1

右·《2014于振立手记》封面2
与此同时,营建工作室这么一项庞大的工程,靠个人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的,这个建造过程渐渐扩展成了社会行为,于振立的朋友,包括大连各界跟艺术有关或者没有关系的人都参与到建造过程中,他自己也像个老农一样掺沙和泥,由于常年劳作,于振立的双手根本不像一个艺术家的手。在大黑山上有两户农民一直帮于振立做事,两个人都姓王,人称“二王”。工作室的户外装置造型完全是“二王”来做的。工作室内部的空间是和知识界、艺术界的对话场所,工作室外面是和周边农民及普通观众对话的一个结果。吴鸿戏称工作室是“万神殿”,工作室外围的造型叫“农民迪士尼”。
曲振伟是大连《半岛晨报》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于振立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见证者。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关注于振立的工作。于振立在山上建工作室,最初是想建立一个可以居住、创作,仅供个人使用的空间,但是慢慢地,他的房子和社会发生了关系。最初是建房的材料,都是旧的,有些是城市拆迁的废料,他自己去寻找来的,有些是他向公众征集的。这期间,他与外界、与社会逐渐交往,形成了微妙的联系。比如他研究《周易》,会帮来访者算命,也会给人写写书法。他的房子建造过程中,发动了很多朋友和社会人士来参与,他自己渐渐变成了一个导演的角色。这个过程带有很强的行为性。这个房子从最初个人的居住、工作场所,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的空间。
批评家刘骁纯将于振立工作室的营建,包括工作室里发生的很多艺术活动都归结为行为艺术。刘骁纯2011年在大连有一个有关于振立工作的研讨会,接近30位批评家参与,题目是“社会雕塑与行为艺术”。但是这个研讨会上,多数批评家对于振立有深深的误解,认为他把大量时间都浪费在建工作室上,耽误了架上绘画的创作。
这么多年来,于振立在山里虽然孤独清贫,但是有作品为伴,内心是充实的。可是,2013年,栗宪庭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策划了于振立的个展。这个展览是对他一生艺术创作集大成的一个回顾,为他带来了关注和荣耀,不过,最后展览上的所有架上作品销售一空。突然之间,作品没有了,于振立的内心跌入空虚之中。
怀着这种心情,2014年成为于振立对艺术功能认识的转折期,他对自己和艺术的关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都产生了转变。这一年,在自己创作和生活条件得到些许改善之后,他拿出一笔资金成立 “大连8+1艺术基金”,这个基金有两个指向性:大连年轻艺术家和大连的当代艺术。此后于振立又陆续资助了一些艺术活动,“2014于振立手记+8个方案”展即为其体现。
由《手记》到方案
如策展人吴鸿所言,于振立及8位(组)大连青年艺术家的展览方式正是一种对话的过程,而对话、互动、交往也是大连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展览到底是如何呈现的呢?

1.《2014于振立手记》节选
展览以于振立2014年《手记》作为基础,8位(组)大连年轻艺术家,分别是“艺术教育小组”(张滨+叶洪图)、徐长健、勇胜、常佶、那新宇、孙伟、凌晨、马尚,每人(组)有一个独立的玻璃展柜,这个展柜按照展厅同比例缩小。他们根据《手记》设计各自的展示方案,呈现他们对于振立整个艺术观念的认识。我们既可以把这里的展品看成是如何展示于振立2014年《手记》的方案,同时也是他们每个人各自独立的创作。
这八位年轻艺术家有的在高校任职,有的是自由职业者,有的是职业艺术家,他们与于振立的交往时间各异,但是因为同一个主题汇集在一起,对于振立的艺术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徐长健参展的是装置《生活形式的切片》,依据展厅的空间尺度,合比例地“复制”于振立工作室的内、外物理空间,有桌椅、有台灯、有笔、有烟缸、有酒杯酒瓶等等;艺术教育小组(张滨+叶洪图)此次参展的作品是《人民日报》系列。该系列源于他们的“找自己”的想法,叶洪图生于1974年9月2日,张滨生于1974年7月6日,所谓“找自己”就是他们在自己出生那一天的《人民日报》原件上面找“叶”、“洪”、“图”和“张”、“滨”这几个字,找到之后,就在那几个字所在的位置用红色马克笔圈上红圈。他们把这张圈了红圈的报纸装裱起来,签了名,即成为作品。2015年,他们邀请于振立一起来完成在《人民日报》中找寻“于振立”的计划,并将它实施在于振立这次展览中,至此,在一个更为开放和实验的场域里来延续“寻找自己”的可能;常佶参展的是影像装置《时间平面的正面和反面》。在展台底部安放电视。电视一半播放于振立半身像和其作品叠印的影像,另一半播放影响于振立艺术观、世界观的作品和人物投影到于振立身上的影像。于振立为此方案提供了影响他的五十个艺术家、思想家或者作家名单,常佶把这些人作为正面投射到于振立的身上。再把于振立的照片做成透明,透出于振立的作品。一个“正面”和一个“背面”并置在一个影像中形成一个生命的纬度;勇胜参展的是装置《不确定之方案断想》。因作品方案想法总是不断变化,他索性便将自己反复预设的方案想法、过程都拿了出来。方案有五种:一、保鲜袋盛装手记撕下的被否定的单页纸球,和被撕毁的手记;二、通过微信、Q Q、电话、短信等现代网络形式,和可以联系上的诸人征集于振立方案展的想法。最终陈列诸想法;三、在陈列柜的四壁展示于振立2014年的《手记》标题,罗列其口中经常念叨的书名和文章;四、在展柜中放置录音笔记录下的于振立《手记》内容,音箱播放;五、否定其内容,空白页展示;那新宇的参展作品是《非处方》,作品以文本方式呈现,通过选取于振立三张具有特殊意义的图像予以改造,诠释其作品内在的批判性。作品将处方笺与药品说明书一一对应,戏拟艺术界的处方诊断,从而将于振立的思想立场置于当下艺术的批评张力之中,以此呈现一种图像学意义上的创作方法论;马尚参展的是《2014,劳作、读书、画画》,展现的是于振立2014年日常生活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劳作、读书、画画,劳作选择的是于振立经常使用的一件劳动工具——于振立母亲刚上山时,用铁丝和竹条亲手制作的打理草、木的抓挠;读书选择的是于振立2014年读过的一本;画画选择的是于振立2014年用过的一块调色板;孙伟的影像《My Dinner with Andre》,选用法国导演路易·马勒(Louis Malle)的电影《My Dinner with Andre》 (1981)的字幕。用投影打到展示柜上,全长一小时五十分钟;凌晨参展的《走进了去看》借鉴2013年杜尚奖获奖作品——拉吉法·艾卡切(Latifa Echakhch)的 《Inking》,将于振立的《手记》扫描影印到同等大小的白色纸板上,当观众走在空间外看到的是跟空间融为一体的白色纸板;走到空间的尽头回头,看到的是写满于振立《手记》的装置页面。

2.《2014于振立手记》节选

3. 《非处方》装置草图 那新宇

4.《2014,劳作、读书、画画》装置草图 马尚
展览呈现了于振立的艺术观念和思考过程,其与自己内心、与社会、与艺术的对话坦于人前。8位(组)艺术家提供的方案与《手记》及纪录片、历史照片等视觉资料,实现了直观的交流和碰撞。
转变的意义
对于展览的评价,批评家杭春晓、盛葳、段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于振立工作室外的装置
杭春晓首先从展览的性质出发,谈到于振立做这样一个展览来推荐大连的艺术家。这种表述其实构建出老一代成功艺术家推动年轻一波艺术家,是处在伟大道德上的制高点,这构成了新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于振立自身几十年的艺术行为构建的,是他在大连,在全国的影响力。但其实这种权力与展厅内作品互动的关系并不适宜。关于于振立的工作,杭春晓还提出另外一重意义,于振立20多年的累积过程构成了一种知识的“地层”。于振立早期画宣传画是服务于政治的权力机制,在上世纪80年代借助于形式的自由来摆脱这一重身份。而1994年起,他在大黑山营建工作室的过程,起初可能只是单纯的个体经验和个体事件,但持续20来年后,这个过程有新的知识生产,有新的知识经验。2013年,于振立的架上作品被买空,2014年有一个内心的空洞期。这次展出的偏偏是这一年的《手记》。其实作品清空了也未必是坏事,《手记》即是他的认知方式。他的工作室和这个展厅是作品生产的终点。艺术家借用物品来做作品,就变成了艺术家不再是作品的生产者,而是知识的生产者,作品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知识场的发生过程。相信这个房子之后还会发生语义的变化,因为新的行为、新的生活方式在里面发生,这样的知识场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动过程中,更有生长性和生产性。
盛葳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着重谈到了于振立“写作”这一行为的意义。他认为于振立实现了一种转向,他的艺术交往、艺术行为,包括写《手记》这样的行为,代表了一种“狂欢”。尤其是写作,写作最重要的不是表达了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形而上的精神,而恰恰是一种非常形而下的,非常“低级”的意义:人的身体在写作当中获得一种快感,写作这种行为本身构成了对身体的一种解放。这种说法的前提是,越来越多的人被制约于一种社会的控制之下,尤其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控制越来越极端化,我们的思想、身体、意识其实都是被控制的。艺术家的社会身份是被控制的,无论是前卫艺术还是体制内艺术家,你的身体和思想其实都被高度控制。所以于振立去大山里干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自我的一种释放,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得快感,救赎自己。他跨越了社会对身体意识的控制,至于他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建了一个什么形状的建筑,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么做,这么做首先是对他自己有意义,而不是对别人有意义。于振立还把这种行为变成一种公共化的东西,从个人“狂欢”变成集体“狂欢”。对今天的社会来说变成了一种相互对抗,或者说相互解构的关系。

上·《人民日报》 艺术教育小组(张滨、叶洪图) 装置草图

下·《时间平面的正面和反面》 常佶 影像装置草图
段君曾经拜访过于振立的工作室,他提到于振立的工作状态非常自然,跟生活融合在一起。他可以很长时间不出工作室,可以很轻松随意地创作,随时可以写、画、做,而今天,很多人的创作是过于精致化了,创作和生活完全分开。另外,大连的创作其实还是有非常的现实性、连续性,有很明确的方向,比较强调观念或者实验性、社会性,或者说社会的介入性。这次的展览是非常明确的方案艺术展,方案艺术有更强的观念上的力度,有艺术家更私密化的一些情感。
一年的《手记》,8个展示方案,展现出对于振立艺术观念进行阐释的无限可能。于振立本身是对概念、阐释非常敏感的人,从1994年上山开始,他预料到评论家可能掉入概念的漩涡,果然,有人说他是隐居,是信佛,是走道教之路。人难免被贴标签,于振立经常被人贴标签,各种不同的标签。他说自己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
今天,于振立的工作室,已经成为大连当代艺术交流与互动的重要空间。他对大连当代艺术的关注与帮助,推动了这片土地的艺术生态的变化,这种变化仍然在持续。
注:
本文根据论坛研讨会速记稿梳理而成。
展览名称:2014于振立手记+8个方案
展览时间:2015年12月26日-2016年1月16日
展览地点:北京宋庄艺术国际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