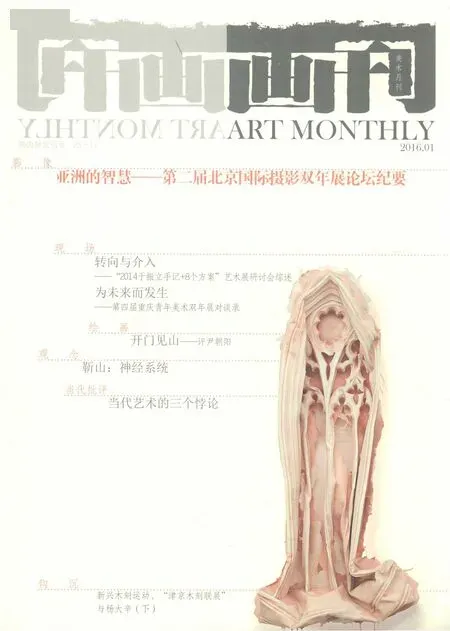亚洲的智慧
——第二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论坛纪要
本刊
影像
亚洲的智慧
——第二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论坛纪要
本刊

上·《狗村》 元性媛(Won Seoung Won ,韩国)
时间:2015年10月16日上午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报告厅
王璜生:感谢大家出席第二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论坛,论坛的题目叫做“亚洲的智慧”,由王春辰教授提出。亚洲的智慧首先应该建立在亚洲的自信、自主和自立上。回望历史,从亚细亚这个名词的产生,到边界的出现,到亚洲概念的形成,我们也许会马上联想到萨义德的论著《东方主义》,在其中有一小段话,大意是:我们无法描述自己,我们必须被描述。无论是东方,还是特指的亚洲,就在这样无法描述和被描述中存在着。从历史上讲,亚洲或者亚细亚一直是所谓西方文明主体以外的一种描述和概念,这个概念一方面指向野蛮、萎靡不振;一方面是奇观、奇异。在17、18世纪的时候,欧洲产生“中国热”、“印度热”、“亚洲热”,与其说是对东方的认识,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奇观式的想象。
今天,从亚洲的内部来看亚洲,我们会发现亚洲内部更注重自我中心,这种自我中心建立在我们各自对亚洲自身,以及亚洲与世界关系的想象中,存在一种对被描述的不满,期待着自我描述,而艰难之处即是这种无法描述。
因此,在这届摄影双年展前言,我写了一段话:“我们身处于亚洲之中,我们能自我认识多少问题,或者是认识到我们认识中的多少问题。”这就是需要亚洲的智慧,我们期待着。
李文:我是中国社科院原亚太所,现在的亚太全球战略研究院的副院长,研究亚洲问题已有20多年。虽然经常被称作是亚洲问题专家,但是亚洲的许多问题对我来讲还是非常陌生的。美国有一任国防部长拉莫斯(Donald Henry Rumsfeld)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大意是:世界上有一些事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亚洲的许多事情我知道我知道,还有一些事情是我知道我不知道,更多一些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比如,我关心朝鲜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我多次去过朝鲜,但是我现在仍然不知道;我特别想了解印度的一些古老的宗教艺术,以及种姓的状况,但是我没有机会;我去年12月份去了柬埔寨的吴哥窟,面对那么庄严的艺术品,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不知道它为何被毁灭了。
把一个陌生的亚洲转变成一个熟悉的亚洲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一是我们开放的需要。今天的中国越来越离不开亚洲、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如果不了解亚洲,亚洲对你来讲永远是陌生的,你很难融入到亚洲社会当中去。第二个是中国强大的需要,西方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是先了解世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开创了人类世界发展的新纪元。第三点是符合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或者转型的需要,人吃饱了以后需要什么呢?要有更高的精神的需要,尤其是审美方面的需要。中国经济低迷了该如何是好?中国发展的路在何方呢?路在脚下,就在文化产业软实力,就是我们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强大的精神引力。
我们艺术灵感智慧的源泉将主要来自哪里呢?将近200多年来我们一直向西方学习,刚才王璜生馆长讲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我们是被描述的、被解释的人群。亚洲应该有自己的主体、自主意识。现在我们应该开启一个亚洲各国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新时代。通过这样的活动,中国人通过各种方式汲取亚洲的美感、亚洲的智慧,我们的发展速度就会加快。
顾铮:我从自己个人的体会出发,谈谈我对亚洲的认识。
现在有人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说这个话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是一个问题。
我在这里介绍一下三种不同的亚洲观,其中两个来自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另外一个来自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
福泽谕吉活跃于明治维新时期,他提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论”。他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种先进的文化,日本只有摆脱亚洲,尤其是中国这样的“恶友”,迅速进入欧美现代国家行列才有希望。福泽谕吉在现代世界中考虑日本的存亡和发展,提出了日本在世界格局中如何定位的问题。但是接着发生的问题是:如何脱亚?如何入欧?像西方帝国主义一样通过海外殖民和武力的方式掠夺资源,加速自身发展,然后进入西方大俱乐部中去吗?20世纪上半叶日本所走过的道路,其实某种意义是重复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老路。

下· 《贫困线:新加坡,红龟粿,2013年5月,1.79美元》 赵峰(马来西亚)、林惠义(新加坡)
但是在1903年,日本另外一个国际主义者冈仓天心写了《东洋的理想》,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亚洲观。在《东洋的理想》里,他提出了“亚洲是一体的”。他认为亚洲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亚洲应该团结一体,对抗帝国主义。当时,冈仓天心和一些西方人一起努力把东方艺术介绍到西方。他认为亚洲可以为世界提供欧洲文明无法提供的爱与美的文明。显然比起福泽谕吉的急功近利,冈仓天心采取了一种文明层面挑战西方文明霸权的思想和志向。
但是亚洲一体的可能性在什么条件下具有现实性?将亚洲理想化和浪漫化的现实基础何在?我个人认为,20世纪亚洲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冈仓天心的理想亚洲观的破产。某种意义来说,孙中山的亚洲观和冈仓天心有一致的地方。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的神户作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中,孙中山提出了他著名的“大亚洲主义”。孙中山特别指出中国的革命相当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希望大家支持。他说东方文化以王道为中心,西方文化以霸道为中心,王道主张仁义道德,霸道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以正义公理感化人,讲强权以洋枪大炮压迫人,要达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做基础,讲道德、重仁义。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以文化为基础,与冈仓天心的亚洲观有某种类似性。在讲演的最后,孙中山向日本社会呼吁,你们日本民族既得了欧美霸道文化的真谛又有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究竟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臣,就要你们日本国民详尽地思考和谨慎地选择。这是孙中山对于日本的警告,很快日本作出了选择。

1.《极夜之昼》 杨泳良(中国) 2012年
在这三个不同亚洲观的前提下,我尝试用摄影的角度看看,有没有可能通过摄影对思考亚洲带来什么帮助。
我个人认为除了地理上的属性以外,亚洲无法成为一个一致的图景。亚洲内部的各国有各自不同的认同,亚洲各国互为他者,整体的亚洲被作为他者想象也是不可能的,但正因为越不可能就越导致想象和了解的欲望。这种欲望包括了凝视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洲就是一种凝视欲望的对象,所以说亚洲是情色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真切地需要摄影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摄影既是现实的镜像又预示现实的碎片化,摄影就是将世界碎片化以后再加以重组。而摄影双年展这样的展示方式,又将摄影的碎片加以集纳,这种集纳的方式既给出了可能,去了解现实、了解亚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是这种集纳也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求全、求一致的不可能。在了解亚洲的复杂性上,摄影以及摄影双年展给出了最切实的证明。
我最后的问题是:这些摄影作品说明了亚洲的什么?我认为这些作品恰恰说明了亚洲是无法说明的。而且越说明亚洲,亚洲越变得神秘。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得用摄影继续凝视亚洲,这是通过摄影我们看到的再清楚不过的问题和现实。
斯普特妮可(Sputniko):大家好,我本人是有着日本和英国的血统,我在日本长大,在伦敦学习,也经常在日本和美国之间跑来跑去。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及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一直是我艺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主题。我在美国居住工作多年以后,感觉到亚洲的文化是非常强大的文化。我看起来不像日本人,但是我是真正的日本人。我学习日本的音乐和艺术元素,学习日本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不管掺杂什么元素在里面,也会保持日本文化或者说亚洲文化的属性,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在日常生活里有许多例子,比如万圣节,我们在日本也会过万圣节,也许我们根本不知道万圣节的起源,但我们仍然会扮演不同的角色,非常疯狂地打扮;比如咖喱,我们从印度学习而来,但我们改进成了日式咖喱;比如拉面,是从中国学习的,但是日式拉面还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整个亚洲文化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可以在里面加入很多元素,加入咖喱、万圣节、人节的元素,我们也会创造新的,也是非常强大的文化。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不用从一种分裂的角度看待亚洲问题,应该秉持东西方融合的态度。

2.《直到世界尽头》 刘晓芳(中国)

3.《快乐健身》 王庆松(中国) 250cm×180cm 2013年

5.《责任与欲望》 尼尔·乔杜里(Neil Chowdhury,印度裔美国人)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作品,主要反映我的混合身份能够让我从局外的角度看待东西方这两种文化。我在日本一直待到18岁,所以在我童年的生活中都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日本流行文化,比如明星偶像和流行音乐。我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看到流行音乐的视频是那些非常非常可爱的、很顺从的女孩子的形象,她们穿着比基尼跳舞,用非常卖萌的方式取悦别人,乞求别人能够投票。我就想要打破这种非常萌的日本女性的形象,想展示不同的东西,呈现女性的力量。我做过一件作品《月球漫步机——赛琳娜的脚步》,这次展览中展出了,用视觉化的方式再创造了美国在太空探索中的历史。1969年,阿姆斯特朗在月球印上了他巨大的足迹。以后的50年里,只有12名美国的男性白人曾经在月球漫步过。一般我们想到月球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浪漫,大家都很想去。有关月球,我们创作了无数的诗歌、电影和小说等等;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到达太空,在月球上漫步。这件作品里的女孩特别热爱月球,她希望能够在月球上留下她的足迹,而且她还特别崇拜一个有着很高鞋跟的巨人形象。所以这个女孩就制造出一个月球漫步机,有着很高的鞋跟,希望能够在月球留下女性的足迹,抹掉那些男性宇航员的足迹。我对这种“DIY”自己动手的文化特别感兴趣,展现出了女性的力量。在我的网站还有一些有趣的视频,比如月经机器,可以让男性体验一下女性在月经期间的痛苦。
刘香成:我生长在香港,早期受大陆的教育,然后回到香港受英国人的教育,然后受美国人的教育,这是我的知识结构。王璜生馆长讨论东方主义的思想,描述被描述这个话题,我看到的则是,今天我们进入新的东方主义的可能。
我的摄影工作是从1977年到北京开始的,在我到中国之前,我在美国纽约看了很多很多西方怎么报道中国的例子,其中有我们大家很尊重的马克·吕布(Marc Riboud)、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很多中国喜欢摄影的朋友们,问我在他们的中国图片中看到了什么。我觉得中国人看到的、喜欢的,也是法国人希望看到的一个理想的中国。因为早期的法国思想家,看到远东的中国有一个很完美的官僚制度,以此来反对法国的国王制度。
我觉得我们会进入一个新东方主义,因为现在的中国正处在自我检讨的阶段,也正在讨论在明确国家主义还是追随西方自由主义之间寻找一个解决方案。
我有一个个人经验,印象很深刻,是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当时处在以美国主流媒体为主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美国人看到苏联解体,媒体认为这代表了冷战的结果,代表了美国的自由主义胜利了。我当时曾经在莫斯科的周围拍到一些经济衰退的场面,有一次是在垃圾场拍摄了一些纪录性的照片,发表了三张,引起了西方记者同行的注意。其实废品垃圾站是全世界都有的,但是那次莫斯科冬天垃圾站的形象在西方的媒体视觉里面,认为这个图像能证明苏联垮了。在惨痛的苏联解体的头两三年间,西方人想象着苏联人经济情况很惨,他们希望看到他们排队买黄油,看到超级市场里面没有食物可卖的画面。但是,我在前苏联生活了5年,给我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印象。令我感到最惊讶的事情是: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我看到一大批中国的农民,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替俄罗斯人种田。前苏联一千多家的农场里面干活的是中国农民。我说俄罗斯人现在没有钱,他们怎么补偿你们的工作呢?他说他们给我们拖拉机和大卡车,我们开回去。所以我很认同顾铮所说的,亚洲其实不存在一致的图景。
回到今天的中国,摄影进入一个很令人兴奋的新状态,跟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都很不一样。在当下的中国,出现这样丰富多彩的摄影,是值得研究讨论的。其中多少有着摆脱东方主义的意思,那么我们是不是在进入一种新东方主义?在今天,中国人出国学习的人数是空前的,其中有很多学生是去学习当代艺术、学习摄影、学习艺术管理。我保持一种乐观主义,期待着10年、20年后产生一种新的化学反应。

《死海》 艾维瑞·沃德曼(Aviram Valdman,以色列) 2009年
缪晓春:这次论坛是最近这段时间第一次真正讨论亚洲问题的。很有意思的是,大家讨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亚洲其实挺陌生的,我旅行过的地方,亚洲国家比欧洲国家少得多。
真的感觉有点惭愧,对自己邻近的地方那么缺少了解,但是我相信亚洲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互相是可以理解的。我举一个例子,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学生德语其实说得很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很好地沟通,远比德语流利的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学生顺畅,我想这种沟通的基础就是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沟通的话,排除政治等因素的障碍,我们在心灵上是可以顺畅沟通的。
另外,我是艺术家,做过一段时间面对现实的摄影,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从2004年开始我用三维电脑软件虚拟了一个世界,有我自己的形象,做了很多的录像作品。这个世界是我自己造的,里面没有国界、没有时间、没有民族、没有身份,什么都没有。所以做了几年这样的作品之后,我想了解周围的现实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组织了一个摄影小组,有六七个人,天天出去拍照片,两年,每天8小时,买胶卷经常是将一个器材店的胶卷全部买空。整理出来大量的照片,有些拍的时候是按照北京经纬线交接点拍摄的,也就是交接点会有对应的360度视角的照片。通过这些照片,我又建立起与现实之间比以前更紧密的联系。我每天都在看大量的照片,里面出现的图像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这次也在展览上展出了,也许对于今后还原这个社会景象会是有用的。

《朝鲜2014——阅读班的小学生》 王国锋(中国) 2009年
本间隆(Takashi Homma):我的摄影作品都是比较清晰明快的,不是沉重的风格。这次展出的作品是我在上世纪90年代做的,叫《东京郊外》,记录了当时东京郊区的风景和人物。我还出版过一本书《东京的孩子》,书里的孩子也是在东京的郊区长大的,拍摄得非常自然,即便有些孩子是来自贫穷的家庭,也还带着笑脸。另外我个人对建筑非常感兴趣,对建筑周边的环境也是。我工作生活在东京,但我的创作受了西方摄影史的影响非常大。
王川:先回应一下参加这次摄影双年展的感受,我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体会。我发现个人的创作、展示作品和参加一个展览,有的时候并不是一回事。在过去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的作品创作方式和展示方式都有了一个同以前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化,这次展览的主题又帮我明确出来一个,可能原来潜藏我意识当中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有关陌生感,对于陌生感的追随,是我创作的一种驱动。
这次展出的作品是来自于我正在制作、接近完成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关于我过去20年创作的一个汇总,当然不是一本简单的画册,有比较多的文字写作。在做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发现我所有的外出拍摄,百分之九十在我最初计划拍摄的时候没有太多想为什么要做。我通常选择从北京出发向西行。所以,目前全国有很多省份我还没有去过,而西北方的山西、陕西、甘肃我都去过七到八次以上。因为在这些地方我有大把的机会去碰到这样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告诉我,原来我们自己认为的我们文化的主体——中原文明、华夏文明这样典型的农耕文明,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和来自北方、来自西方草原文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一次又一次地融合的。我们在甘肃的永昌甚至了解到,当年罗马帝国的一支雇佣军曾流散到这个地方,和当地的文化融合以后,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现代化意义的包装而形成了所谓的骊蚠文化。过去我们说大江东去佛法西来,而在山西从北到南也可以看到佛法来了以后,是如何在拓跋氏突厥部落领导下,从大同一直到洛阳,途经山西南部的晋城地区,在那里留下的羊头山北魏石窟,这个地方名不见经传,但是我们拍摄到了一些残破的佛造像,还见到了中国其他地方不会再见到的、完美的金代的木刻建筑。在这些建筑雕塑面前,我们没办法把它们和我们所习惯认为的它们是由女真一族建造的说法对应起来。
所以在这个展览之前,我一直认为我的兴趣总体来讲,是中国的传统在当下社会中的存在形态,这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我现在特别愿意再加上一条,我觉得由于在这些地方不断遭遇这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来自于既有的和当下的现实、我们被告知的文化,和民族、和地域历史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物理空间上的,也有时间纬度上的,这种不断遭遇的陌生感,实际上是驱动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做各种探索的一个内在动力。
注:
本文根据中央美院美术馆提供的论坛速记整理稿修改而成,未经发言人审定。展览名称:陌生的亚洲:第二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
展览时间:2015年10月15日-11月29日
展览地点: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798艺术中心、Cipa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