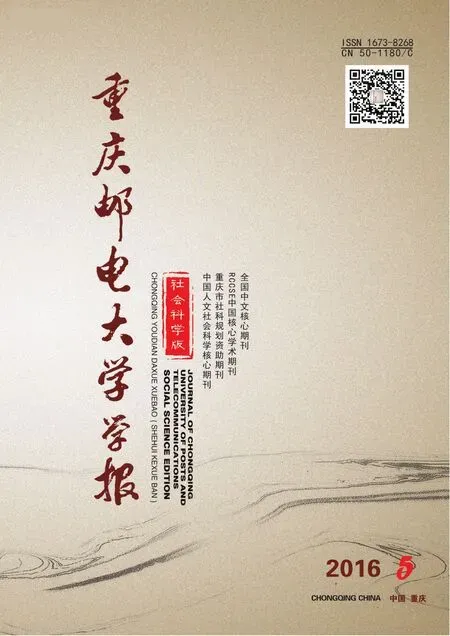刑法应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数字版权保护的“焦虑”
姚万勤
(1.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2.日本中央大学 大学院,东京 192- 0393)

刑法应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数字版权保护的“焦虑”
姚万勤1,2
(1.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2.日本中央大学 大学院,东京 192- 0393)
互联网迅猛发展致使声势浩大的大数据时代骤然降临,在社会尚未变更新理念和确立相关制度之前,如何保护数字版权凸显出较为纷扰的司法困境。与传统的著作权相比,刑法在此类问题上的规定乏善可陈,保护范围的局限未能使数字版权得到应有的重视,网络信息传播权保护缺失未能突破以传统复制权为中心的窠臼,主观营利目的的局限导致大量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难以得到制裁。因而,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变更立法、保护理念、完善罪名的相关内容成为刑法应对大数据时代数字版权保护的关键所在。
数字版权;著作权罪;复制权;传播权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不断突破人类现有认识范围,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二进制世界的固有局限,预示着一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英国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深入浅出的讲解与分析,大数据已然成为我国目前炙手可热的话题。大数据(big data),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以及知识再发现。大数据在实用层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目共睹*例如,在2009年全球大规模爆发甲型H1N1流感之前,谷歌公司的工程师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文,在文中解释了谷歌为何能够预测这场灾难的来临。因为谷歌保存了多年来所有的搜索指令记录,而且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球超过30亿条的搜索指令,如此庞大的数据资源帮助其完成了这项工作。(参见文末参考文献[1],第3页),“当世界开始迈向大数据时代时,社会也将经历类似的地壳运动”[1]绝非危言耸听的宣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高达47.9%,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之众。可以说,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数据时代就这样在世界范围内落地生根并迅速蔓延。
大数据被归结为四个典型特征,即:volume(数据量大)、velocity(数据变化速度快)、variety(数据内容庞杂)、veracity(数据的精准)[2]。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的运用与日俱增,已然成为未来社会商业活动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在大数据时代,数字网络技术在作品的创作、作品的载体、作品的复制和作品的传播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给版权保护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何通过刑法保护这种数字化版权,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以全国首例深度链接侵犯著作权案为例:
章某申请注册网站域名后创建、开设网站,通过搜索获得租用网络服务器网站,注册后以每月500元钱租用某服务器,获取账号和密码后将马克斯软件安装于该服务器。嗣后,章某将某网站提供的播放插件安装在后台,后台显示影片播放地址,点击采集其提供的影片,再点击生成链接网页,从而实现从该网上链接相关影视作品。经鉴定,章某通过该网站共计链接了900余部影视作品供他人在线浏览和下载。检察院最终以侵犯著作权罪对章某提起公诉[3]。
对章某究竟该如何处理,目前至少存在“盗窃罪说”“非法经营罪说”“侵犯著作权罪说”以及“非罪说”的对立[4],通过将播放插件安放在后台方式盗播他人影片的行为,没有逾越国家专属经营或禁止经营的禁止性规定事项,因而不属于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的规制范畴;同样,章某没有采取窃取等方式对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本身造成侵害,因而不是侵犯财产权的盗窃行为;但归根究底,章某还是通过侵犯方式获取了巨额收益,如果对于这种行为不进行相关处断显然也不妥当。即便司法机关最终以侵犯著作权罪对章某论罪处刑,但这只是本案处理结论的一种交代而已,如此处理结论对进一步防范该类案件能起到多大的威慑效果不无疑问。笔者提出该案并分析其处理结论的用意不在于探讨刑法对该类问题处理的罪名是否具有妥当性,而在于通过本案揭示的另一深层次问题——如何在大数据时代通过刑法保护数字版权。正如本案所呈现的,尽管权利人使用了包括技术保护、诉讼、甚至传统刑法保护手段阻止网络环境中的版权侵权行为,但由于大数据时代的无限开放性、无限可复制性和无限传播性等特点,海量数字作品的制作、复制以及传播行为,使得侵犯数字版权的犯罪现象更加猖獗,这不仅损害了权利者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立基于此,笔者更愿从更加深层次的角度来窥探我国现行刑法对数字版权保护的“焦虑”,以及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如何完善对数字版权的刑法保护。
二、保护的“焦虑”:现有刑法应对的不足
版权(copyright)即著作权,是指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权利(包括财产权、人身权)。言下之意,数字版权也就是各类出版物、信息资料的网络出版权,可以通过新兴的数字媒体传播内容的权利。目前,刑法对版权保护当属第217条,即“以营利为目的,违反著作权管理法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我国刑法学界理论通说认为,刑法第217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在客观方面具体表现为4种典型方式:一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二是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三是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四是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而在大数据时代,利用互联网工作、生活、学习、创作以及从事交易成为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与以往传统版权传播路径相比,漫天的网络下载、传播早已成为常态。因而,就大家“司空见惯”的侵犯数字版权的行为究竟该如何寻求刑法救济,越来越陷入司法适用的困境,我国刑法在应对数字版权保护时无不显示出不足与乏力[5]。
(一)保护范围的局限:基于《著作权法》与《刑法》的比较
我国《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了8种侵权行为,包括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传播其作品、出版图书、侵犯著作邻接权、以新技术手段间接侵权、侵犯署名权等行为。依据不同情形可以追究侵犯上述权利的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除了《著作权法》第48条第2项“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与《刑法》第217条第2项的规定完全相同,第8项在刑法第218条销售侵犯复制品罪中有所规定以外,其余各项均与《刑法》的规定不同[6]。梳理后发现,刑法着重保护的是知识产权中的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录音录像,美术作品等客体,其范围明显小于《著作权法》所确定的范围。有学者认为这是刑法基于谦抑原则的考量,将不适合用刑法规制的行为予以非罪化论处[7]。笔者认为,从社会危害性来看,未被纳入刑事法规制范围的著作权对象,并非对其侵害后表现出的社会危害性不严重,具体原因应该在于1997年新刑法制定实施后,《著作权法》对著作权领域出现的较为新型的侵权行为已适时作出调整,而《刑法》在近20年间对侵犯著作权的犯罪未经过任何修改,由此造成了《刑法》与《著作权法》在保护范围上产生脱节。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著作权的对象范围必然还会进一步扩张,尤其是数字作品不仅突破了原有的载体形式,诸多权利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和确认,通过刑法现有的规制范围更加显示出在未来大数据时代应对著作权犯罪的乏力与疲软。
(二)保护程度的欠缺:基于网络传播权的分析
在传统的著作权保护领域,《知识产权协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均明确了首次销售原则并将其适用条件赋予各国实体法进行具体规定[8]。首次销售原则,或称权利耗尽原则(the exhaustion doctrine),是指知识产权所有权人依据知识产权法控制知识产权产品的生产、使用以及销售的权利,将随着这些产品首次合法进入流通领域而丧失殆尽。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权利人控制这些产品的权利随着首次使用而被“用尽”。虽然我国在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首次销售原则,但从《刑法》第217条第1款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音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以及第3款规定的“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内容中可以明确,侵犯著作权行为具体包括“复制”和“发行”。也即,我国刑法规定的内容还是遵守了首次销售原则,对行为人通过复制和发行他人作品的行为会给予相应的处罚。而根据《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除了复制、发行、出租之外,还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显然,《刑法》对著作权人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处于缺位,由此便使数字版权的保护处于一种更加不利的状态。因为按照传统著作权制度,虽然著作权人享有对作品的发行权,但如果作品的复制件由著作权人或经著作权人许可向公众转移所有权后,著作权人便无权对作品复制件的后续流转进行控制,合法取得作品复制件的所有者可不经著作权人同意而将其再销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在网络数字环境中,网络用户在购买音乐或者电影文件后,是否有权在自己不保留备份的情况下将自己购买的文件转售给第三人?也即,首次销售原则能否适用于网络数字环境中?表面看来这仅仅属于理论探讨的范畴,但事实上会涉及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权衡。如果刑法不对首次销售原则在网络环境下的行为进行规制,那么在此种情况下会对著作权人权益造成实质性损害。当技术保护等措施在“大数据”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之时,刑法如何对网络环境下的数字版权进行保护便成为一大难题。
(三)主观目的的局限:《刑法》与《TRIPS协定》相关规定的背离
《刑法》第217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营利的目的,按照刑法理论,本罪属于典型的目的犯,但是目前较少国家在行为人主观上进行任何限定。例如,根据《TRIPS协定》第61条规定,行为人构成对著作权侵犯的主观要件只要具备“故意”即可,并没有要求主观上还必须“以营利为目的”。质言之,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复制、发行的作品是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并且对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那么该行为就具备了刑法处罚的正当根据。对主观上进行额外限制的做法,于数字版权保护百害而无一利。在大数据时代,通过主观限定的做法使对海量数据的侵权行为的保护面临着更大的困境。首先,对主观目的的证明将消耗大量司法资源。因为刑法已经明确规定了“以营利为目的”,那么在司法适用中就必须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这种目的,否则将难以对行为人论罪处刑。目前我国在网络犯罪中投入的司法资源本身就很有限,如果加大该类犯罪的证明难度,无异于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其次,在大数据的网络信息环境下,这一主观目的的限定在无形中会助长已经漫天泛滥的侵权行为,可能会放纵某些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每一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均是以获利为目的,例如,如果部分终端用户基于非营利性目的从权利人网站下载相关作品后,经非法破解并直接上传至公开网络空间供他人下载使用以赚取网络的点击量,此时权利人经济利益的损失就不能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营利目的来衡量,否则将会放纵这种犯罪行为并造成处罚的漏洞。
三、趋势前瞻:数字版权刑法保护的完善之维
虽然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TRIPS协定》,但我国刑法所确立的侵犯著作权罪与该协议规定的有关著作权的相关内容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等方面均有犯罪构成起点过高以及保护面较窄的问题[9]。因而,如何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达成保护与传播的双赢显得尤为重要。
(一)立法理念的变更:适当拓展版权的保护范围
根据是否侵害了新生法益,刑法通常将网络犯罪划分为侵害新法益的新型网络犯罪和侵害传统法益的网络化犯罪[10]。在大数据时代,网络的高度发达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法益,如数据库、计算机软件、多媒体、网络域名、数字化作品,等等。虽然与传统的著作权保护客体在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在财产性利益等方面保持了高度的相同性。因而,对于该类作品的版权保护在刑事法领域理应有所评价[11]。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我国刑法在保护传统版权范围上早就显示出愈发狭窄的弊端,更何况在大数据时代,更加难以应对新生法益的保护。具体体现在:其一,被害人在网络环境中寻求救济越发艰难,存在需保护性日益增强。与网络运行商较为强势的地位相比,著作权人通常处于相对较为弱势的地位。一旦陷入版权纠纷之中,维权之路尤为艰难。这种艰难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作品的传播途径难以控制。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我国实行自动取得著作权制度,一旦行为人在网联网上公布作品自动取得版权后,加上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可以核裂变似地迅速传播全球。这样的数字作品传播速度几乎是不可控制的;另一方面,著作权人身份认定的困境。网络虚拟化的客观现实造就了著作权人身份的相对模糊化,因为著作权人将作品上传网络时往往署上自己的笔名以及网名,在版权面临侵犯时又难以提供有效的证明,因此在最终可能使维权之路处于更加不利的状态。其二,侵犯版权的犯罪与日俱增。在大数据时代,较为快捷的传播速度将数字版权传播至较为分散的范围,这种分散传播方式无需行为人相互之间的具体接触就可完成,如此使著作权人的权益往往在瞬间就能遭受巨大损害。更有甚者,在巨大利益驱使之下,往往罔顾法律的规定而肆意侵犯他人的版权以谋求网站的点击率、下载率,从而获取丰厚的广告费等次产业利益。
拓展新生法益版权的刑法保护,首先需要在著作权法中适当改变著作权取得方式,可以将原先的自动取得变更为登记取得,基本理由有四:其一,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确立了自愿登记制度,但自愿登记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较为尴尬,因为现行法律并没有赋予自愿登记过多的法律效力,这对于著作权人保护而言依然存在不利的一面[12]。而通过法律强制规定著作权由自动取得变更为登记取得,有助于进一步促使权利人关注自己的实在权利,大大减轻了对数字版权权利人的保护难度,这对于进一步保护数字版权是极为有利的*古希腊有句法谚——“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意为法律不保护那些自己拥有权利却疏于维护和管理的人。同样的道理,如果能够将著作权的取得方式变更为登记取得,必将会减少那些因为疏于维护和管理数字版权而遭受侵权情形的发生。。其二,将自动取得变更为登记取得,有利于促进双方交易的安全,降低交易风险[13]。在自动取得著作权制度之下,权利的归属并不清晰明了,因而对于使用方的权利保护也存在较为不利的一面。当只要著作权人取得国家权力机关的登记证书,对于使用方来说,可以减少和消除权利瑕疵的顾虑,进而能够有效节约交易成本,保障交易安全[14]。其三,将自动取得变更为登记取得,使数字版权在网络传播路径中不会因为权属不明确而陷入较为被动的局面。我国著作权法根据作品形式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著作权归属制度,例如个人作品、合作作品以及委托作品等在最终的著作权归属上是存在差异的,一旦产生纠纷,在自动取得制度下,著作权的权利人也很难证明自己就是真实的权利者,而一旦变更为登记取得,即便在存疑时也较易确定著作权的最终归属。其四,可以大大降低诉讼成本。在自动取得著作权制度之下,一旦著作权归属问题产生纠纷,尤其是数字版权产生纠纷,在获取相关证据方面势必会消耗过多的人力、财力、物力。而确立著作权登记制度,其登记本身就是具有确权性质的行政行为,本身就具备民事诉讼中证据的效力,因而也就简化了证明的难度,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约了诉讼成本。
其次,数字化的版权同样包括人身权以及财产权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之下,刑法保护对象应当与《著作权法》所确立的保护范围相一致,不应厚此薄彼,未被刑法纳入规制范围的侵权行为同样具有危害性,其危害程度不亚于目前刑法规定的几种类型。具体而言,只要是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范围,刑法就不应排斥。因为刑法在属性上是“二次规范”“事后法”,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处于保障法地位便决定了刑法对其他部门法的利益不能过于漠视,尤其是值得保护的其他著作财产权种类,更应采取足够的应对之策。这是其一。其二,刑法应当反映时代的精神与发展脉络,对于落后的刑法规定应当及时予以修改、纠正。虽然一直以来过于强调成文法的稳定性,但知识产权属于较为崭新的领域,我国对其保护经历了从不重视到足够重视的发展历程,现行著作权法对版权人的利益保护愈发趋于完善,相反,一直以来,刑法在此问题上未有实质性进展,逐渐脱离了社会发展现状。因此,在此时代背景下,修改相应的刑法条文应对日益拓宽的著作权的保护对象,这是任何国家都在努力践行的现状,我国也不应置身事外。
(二)保护理念的更新:从复制权到传播权的修正
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原则是利益平衡原则,利益平衡原则一方面要求最大程度地为创造者提供激励,另一方面又要求使知识尽可能造福于社会公众[15]。我国传统知识产权法在建构版权保护时,主要是以著作权之复制权为核心。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字化作品的传播速度是其本质属性,而我国刑法以及著作权法多强调控制复制,因而产生多重悖论局面。例如,2004年,谷歌公司曾寻求与图书馆和出版商合作,大量扫描图书,欲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图书馆,使用户可以利用“谷歌图书搜索”功能在线浏览图书或获取图书相关信息。时至2009年,央视《朝闻天下》栏目报道称,谷歌数字图书馆涉嫌大范围侵权中文图书,有570位权利人的17 922部作品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已被谷歌扫描上网。谷歌公司将面临中国权利人的侵权指控。显然,谷歌公司的数字图书馆陷入困境是由于传统的版权保护框架导致的。对此,有学者指出,“控制复制就是扼杀传播,这已与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版权期待、版权法宗旨南辕北辙”[16]。笔者认为,在大数据时代,保护版权的传播权远比保护复制权意义重大。基本理由有二:首先,保护传播权能够切合大数据时代的特征,从而更加有效地保护数字版权。众所周知,大数据时代正是建构在信息迅速传播的基础之上,如果能够将版权的传播权保护到位,也就能更好地解决大数据时代版权保护无所适从的局面。其次,对传播权而不是复制权进行保护,更加有利于数字作品的利用和交流。根据我国目前《著作权法》第22条的规定,明确了在12种情形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然而,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排他性规定与浩瀚的网络资源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况且,在尽量保护优秀数字作品的知识产权时,也应尽可能地造福于人类,这样才能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共同理解。
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应适当转变保护理念——由以复制权为中心的保护体系转向以传播权为中心的保护体系。具体而言,在浩瀚的网络世界中,如果只是实施了复制数字作品的行为,那么就不能认定该行为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同样不能以犯罪论罪处刑。相反,行为人下载并广泛传播数字作品的行为才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刑法对此类行为予以规制才具有妥当性。
(三)罪名性质的革新:取消本罪中的主观目的的限定
如上文所论,在我国目前罪名体系之下,对版权的刑法保护还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盈利的目的。除此之外,还需行为人在此目的下的违法所得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点的认定,司法机关严格执行并无松懈的意思体现。例如,自2010年实施“剑网行动”以来,对主观上没有盈利目的、客观上没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行为均以非罪化处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刑法应当贯彻谦抑性原则,只有当其他手段对法益的保护都不充分时,才能由刑法以替代的形式来对法益进行保护[17],但刑法谦抑性原则只是在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较为轻微时才能予以适用。换言之,在实施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时则应排除适用该原则。对于主观上不具有营利目的的侵犯数字版权的行为,在客观上往往也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例如,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免费的海量数据下载并传播会对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样,一些盗版软件行为的泛滥不仅直接影响了国家公共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会进一步影响到公众的利益。因而对于此类行为不进行刑法控制,必将存在放纵犯罪的嫌疑。
笔者认为,在目前大数据背景下,应当取消本罪中的主观目的限制,将本罪变更为行为犯的立法体例,亦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本罪规定的行为就可构成本罪。基本理由有二:首先,取消本罪的主观目的限制,将会减少司法机关的证明负担,节约大量司法资源。例如,前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为应对传统型犯罪已经投入太多的司法资源。而对于这种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犯罪,如果存在证明难度等现实困境,案件侦破结果可能不太理想。降低该罪的主观证明难度,将会节约更多的司法资源应对诸如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关乎民生的犯罪。其次,继续保留该罪主观营利目的,不符合大数据时代版权的特征。之所以出现主观上“盈利目的”的规定有其历史性原因,因为在较早时期对版权的保护主要是以传统型的纸质作品为主,因而复制以及发行该类作品需要大量的成本,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追求营利目的也无可厚非。然而,在大数据时代,对于数字版权的侵犯需要很低廉的成本抑或根本不需要成本,因而多数国家顺应潮流取消了本罪的主观目的限制*例如,在美国1994年的司法判决中,就通过判例确立了行为人侵犯他人版权主观上不需要营利的目的。同样,在日本也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盈利的目的。。这样,只要在客观上具有侵犯数字版权的行为就可构成犯罪,因而也就增强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力度。我国亦应顺应潮流,与先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接轨。
四、结 语
正是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解构,在新秩序尚未有效建立之前,社会难免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磨合”,这种“磨合”反映在数字版权保护问题上,尤其自1997年刑法制定之后,尚未涉及到对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相关修改,更加呈现出保护不力的现状。一方面,社会迅速发展必然会导致刑法与社会生活逐渐脱节,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与进步,网络资源也随之日渐丰富,知识产权的保护形势更加严峻,而刑法由于其固有的稳定性,难免不能及时反映在数字版权的保护中,由此造成了刑法在应对知识产权犯罪时出现了保护缺位;另一方面,在相关知识产权法律面临新一轮的修改之际,刑法如何切中时弊,如何协调各方利益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知识产权则显得尤为迫切。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存在,随着其他部门法的修改和完善,刑法在制度设计上及时跟进才具有妥当性,因此,变更立法理念,更新保护理念,取消行为人主观营利的限制,对于数字版权保护同样适用且尤为关键。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一个国家重视知识创造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尤其在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的争夺才是国家傲视群雄的关键所在,缓解刑法对数字版权保护的“焦虑”,从根本上有利于国家提高综合竞争实力,有利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1]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19.
[2]冯登国.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J].计算机学报,2014(1):246-258.
[3]孙万怀.慎终如始的民刑推演——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传播性质[J].政法论坛,2015(1):96-112.
[4]骆琼.深度链接入罪须谨慎——以全国首例深度链接侵犯著作权案为视角[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14(3):35- 40.
[5]刘勇.国内Android定制手机系统中的版权困境及其应对[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39-43.
[6]罗曦.论著作权刑事保护范围[J].知识产权,2014(10):50-56.
[7]崔立红.著作权犯罪与谦抑原则的适用[J].知识产权,2007(5):65-70.
[8]唐艳.数字化作品与首次销售原则[J].知识产权,2012(1):46-52.
[9]王文华.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若干问题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44- 47.
[10] 于志刚.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J].中国社会科学,2010(3):109-126.
[11] 于志强.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制裁体系检视与未来建构[J].中国法学,2014(3):156-176.
[12] 齐爱民,彭振. 我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机制的反思与完善[J].河北法学,2013(5):10-14.
[13] 柯林霞,王增收.假冒著作权登记的界定与防治对策[J].出版发行研究,2014(8):80-83.
[14] 邹韧.著作权登记开启维权方便之门[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 06-21(09).
[15] 吕炳斌.数字时代版权保护理念的重构——从以复制权为中心到以传播权为中心[J].北方法学,2007(6):127-131.
[16] 刁胜先.我国的版权法治建设的问题与建议——以云计算为主要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3(1):16.
[17] 陈家林.外国刑法:基础理论与研究动向[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9.
(编辑:刘仲秋)
How to Deal with the “Anxiety” of Digital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Big Data Era
YAO Wanqin1,2
(1.LawSchool,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Chongqing401120,China;2.LawSchool,ChuoUniversity,Tokyo192- 0393,Japa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results in the sudden emergence of massive data era. How to protect digital copyright has been bringing more troubled judicial dilemma when the community does not yet changed new ideas and establish the relevant system.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opyright, criminal law related lacks limited regulations, which does not give due consider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digital rights. The lack of networked communication right protection is a failure of breaking away from the status quo with the traditional copy right protection as the center. And the limitation of willful profit-seeking leads to a large number of serious social harmful behaviors, which is difficult to be controlled. Therefor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big data era, the change of legislation, the protection of idea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he crime become the key to for the criminal law to deal with digital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the big data era.
digital copyright; copyright crime; reproduction right; communication right
10.3969/j.issn.1673- 8268.2016.05.006
2015- 09-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法适用公众参与机制研究(13BFX057);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创新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刑法治理模式研究(CYB14070)
姚万勤(1987-),男,安徽芜湖人,讲师,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特殊群体权利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日本中央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D923.41
A
1673- 8268(2016)05- 0030-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