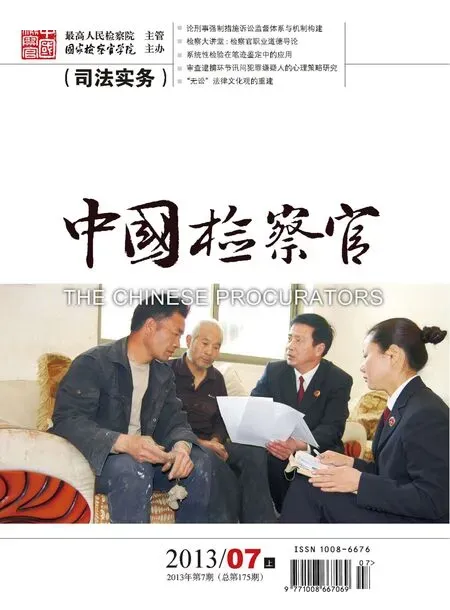论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文◎毛冠楠
论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文◎毛冠楠*
一、关于期待可能性判断标准的学说
关于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
第一,行为人标准说。该说认为,应以行为时的具体状况下的行为人自身的能力为标准。如在当时的具体状况下,不能期待该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就表明缺乏期待可能性。因为责任是就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而对行为人进行的人格非难,这就决定了要以行为人为标准。而且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本来就是为了针对行为人的人性弱点而给予救济,故有无期待可能性,理当以行为人为标准。[1]
该说受到的批评是:使刑事司法不适当的弱化;造成极端的个别化;确信犯常常没有期待可能性被认为无罪。[2]
第二,平均人标准说。该说认为,如果对处于行为人状态下的通常人、平均人,能够期待其实施合法行为,则该行为人也具有期待可能性;如果对处于行为人状态下的通常人、平均人,不能期待其实施合法行为,则该行为人也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这种观点认为,责任判断虽然是一种个别的判断,必须以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为基础,但在判断的标准上,应当以平均人为标准。
该说受到的批判是:所谓通常人、平均人,是一种不明确的观念;此说也没有考虑到对平均人能够期待而对行为人不能期待的情况,这就不符合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本意;此外,责任能力的观念就已经是以平均人的观念为基础而形成的,如果期待可能性的有无也以平均人为标准,则是概念的重复。[3]
第三,国家标准说(法规范标准说)。以上两说,都是从被期待一方提出判断标准,而国家标准说则是从期待一方提出判断标准,即主张以国家或国家的法秩序的具体要求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因为所谓期待,是指国家或法秩序对行为人的期待,而不是行为人本人的期待,因此,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只能以国家或法秩序的要求为标准,而不是以被期待的行为人或平均人为标准。
该说受到的批判是: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本来是为了针对行为人的人性弱点而给予法的救济,所以,应考虑那些不能适应国家期待的行为人,该说则未考虑这一点;而且究竟在什么场合国家或法秩序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是一个不明确的问题,因此,该说实际上未提出任何标准。[4]
第四,折衷说。第一种观点认为,“以国家标准说为前提,任何表明缺乏期待可能性的条件不能与国家的意志即法律的要求相抵触;以普通人标准为根本,结合日常生活中多数人的活动规律确认期待可能性的条件是否合理;以个人标准说为补充,从行为人的实际情况出发,考察行为人与一般人的差别,承认行为人的特殊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期待可能性的标准,应以行为人标准为主,而辅以普通人标准和国家标准。在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以行为人标准为主,参照普通人标准。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根据行为人行为的情况,可以确定行为人有无期待可能性,则不须考虑普通人标准。”
第三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标准、平均人标准说与法规范标准说事实上回答的是,实施其他合法行为的可能性达到何种程度时,行为人才有责任。就有无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而言,应以行为人的主观的、个人的事实为基础,再根据处于行为人地位的平均人标准进行判断。如果完全以平均人为标准,而不考虑行为人主观的、个人的事实,就是只照顾了一般化的正义,而没有照顾个别化的正义;如果既考虑行为人主观的、个人的情况,又以该行为人为标准,结局是任何人在当时实施该行为都是不得不实施的,否则他不会实施,这样就无法律可言。确信犯的概念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认定行为人具有实施其他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时,还应判断可能性的程度,即具有何种程度的可能性时才承担责任,这里当以国家要求或法秩序为标准,而这种要求又是以一般人的规范意识为基础的。
第五,类型人标准说。该说是有学者基于对行为人标准说的修正而提出的。日本的植田重正教授认为,“即纵令依据行为者标准说,然亦非以单纯的行为者个人为标准,而系以行为者本人所属之类型人(由于本人之年龄、性别、职业及经历等等所构成之愿望)为标准者……然有无期待可能性之判断,亦非个人的以及主观的判断,而常具备某种程度之类型性及客观性。”
二、对以上学说的评价
针对以上各说,笔者认为,第一,针对行为人标准说的几点批判,实际上并未抓住问题的关键。行为人标准使责任非难具有个别性,而主张根据行为人的个人状况为标准判断期待可能性,这一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责任判断虽然是个别化的判断,但是责任判断从行为人自身出发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只能得出行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期待可能性的结论。因为责任判断必须是将行为人与其他人相比较才能够作出,无比较也就无所谓非难。也就是说,没有参照物,行为人在主观上就没有值得非难的地方可言,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期待可能性,从而否定责任的存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行为人标准说根本就不是一种标准。对此,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期待可能性判断的标准不能取决于行为人,必须以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人作为标准。前述提到的对行为人标准说的几点批判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反而都是以承认行为人标准说是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标准为前提的。并隐含着这样一种预设,即在有些情况下该说能够正确地判断期待可能性。例如,前述对该说的第三点批判认为确信犯常常无期待可能性被认为无罪,言下之意是,确信犯之外的犯罪有可能根据行为人标准说而被认为有期待可能性从而被认为有罪,这一逻辑显然是对该说未深入了解所造成的。
持行为人标准说的大塚仁教授认为,针对行为人标准说,从来就有批判指出,站在行为人标准说的立场上,所有的行为人都会被允许,从而使刑法失去基础。但是,以行为人作为判断标准,并不是无条件地肯定行为人的主观立场的感伤主义。即使说要考虑具体场合中的行为人的情况,那也总是客观地评价行为人的能力,在行为人具有低于平均人的能力时,也应该在其能力的最大限度内予以评价。因此,即使根据行为人标准说,不能期待是责任能力者的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事态也不会像所担心的那么多,说会带来刑事司法的软弱化,只不过是杞人之忧。大塚仁教授针对行为人标准说受到的批判所作出的上述反驳并不能成立。其将责任能力与期待可能性相混淆,责任能力作为主观的能力当然必须从行为人自身进行个别的判断,但这种判断不能等同于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其所谓“行为人具有低于平均人的能力”,即是将行为人与平均人二者的责任能力相比较,而并非将平均人在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状况下实施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与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相比较。
第二,针对国家标准说的上述批判是成立的。按照该说来判断期待可能性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行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实施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必须要符合国家或法秩序的期待。该说与行为人标准说一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三,平均人标准说避免了上述两说的缺陷。该说在日本是通说与判例的立场。前述该说受到的批判,笔者认为,首先,针对第一点批判。通常人、平均人虽然是模糊的概念,但是其他学说的标准同样模糊,而且对通常人、平均人的判断只要基本符合社会的一般观念即可,不可能做到绝对地精确。其次,针对第二点批判。对行为人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原本就必须与他人相比较才能作出,即同时考虑行为人与其他人的具体情况,如果行为人也属于平均人,这一批判就不成立。最后,针对第三点批判。该点批判将责任能力等同于狭义的期待可能性,显然不正确。
由此可见,平均人标准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其缺陷实际上在其受到的第二点批判中已被涉及,即如果行为人不属于平均人或者说如果行为人由于具有某种特殊的身份从而使其期待可能性的判断不能与社会上的一般人相比较时,平均人标准说就显得不妥当。这一缺陷正好可以为类型人标准说弥补。
第四,各种折衷说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不能成为判断期待可能性标准的行为人标准说或国家标准说,因此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五,类型人标准说的首倡者植田重正教授虽然认为该说属于行为人标准说,但该说本质上是对平均人标准说的修正。内藤谦教授认为,所谓的“行为人本身所属的类型人”,可以认为接近于平均人标准说中的平均人。期待可能性有无的判断,不具有个人的、主观的因素,而应该认为具有一般程度的类型性、客观性。如果进一步解释,那么所谓“行为人本身所属的类型人”,绝对不能简单地与“平均人”的类型化同样对待。这一评价是正确的。我国有学者认为,“笔者倾向于将‘类型人标准’视为增强‘行为人标准’可操作性的一个方案,而不是将类型人标准独立出来。”这一观点与植田重正教授的观点类似,因而是不妥当的。类型人标准说作为平均人标准说的修正与行为人标准说有本质不同。
我国有学者赞同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应采用类型人标准说,其理由是:一,类型人标准说较为全面地反映社会关系中的不同人群及其属性。二,类型人标准不仅可以在决定有无期待可能性时适用,也可在判断期待可能性大小时适用。三,类型人标准能够适用于刑法实践的不同环节。对此,笔者原则上赞同。但是,类型人标准说及该学者的某些认识尚存在问题。
类型人标准说在行为人具有法律所规定的特殊身份时,其判断结论较平均人标准说合理。笔者认为,这里的行为人的特殊身份主要有两类:一是刑法分则条文对行为人可以成立单独正犯所要求具备的某些身份。主要是指特定职业身份与特定性别身份,如贪污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强奸罪中的男性身份。但是不包括一般人也可能具有的身份,如伪证罪中的证人身份。二是行为人具有的刑法总则条文所规定的未成年人的身份与限制责任能力人的身份。在我国主要是指,单纯的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犯罪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人所具有的未成年人身份;单纯的具有限制责任能力的人的身份,包括单纯的具有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身份,单纯的又聋又哑的人和盲人的残疾人身份。
在具有第一种类型身份的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场合,判断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当然不能以社会上一般的平均人为标准,而必须以具有该特定身份的同类人为标准,此时平均人标准说不妥当。
在具有第二种类型身份的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场合,则需分情况讨论。首先,单纯的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犯罪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时,判断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应以同类的未成年人为标准,而不应以社会一般的平均人为标准。其次,单纯的具有限制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违法行为时,又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受到了自身责任能力的影响,此时判断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应以具有与该行为人同等性质与程度的同类具有限制责任能力的人为标准,而不应以社会一般的平均人为标准。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未受到自身责任能力的影响,此时判断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当然应以社会一般的平均人为标准。当然,同一行为人也可能同时具有第二种类型的几种身份中的一种以上的身份,这时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可以参照以上标准进行综合考量。
三、结论
上述分析可以说明,虽然在一些场合,期待可能性的判断要受到行为人具有的特殊身份的影响,此时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应是类型人标准说。但是在有些场合,期待可能性不受任何特殊身份的影响,此时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仍应是平均人标准说,并且这是从最广义上以能够实施犯罪的所有人为对象来确定“平均人”。实际上本来意义上的平均人标准说只是将“平均人”限于社会上不具有上述特殊身份的“一般人”,因而是一种狭义的平均人标准说。此外,在不具有上述特殊身份的完全责任能力人实施的不要求特定身份的违法行为中,判断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的标准也是平均人标准说,只不过是本来意义上的狭义的平均人标准说。
当然,如果将类型人标准说的“类型人”无限扩大解释,将平均人也作为一种“类型人”,即与无责任能力者相区别的“类型人”,那么类型人标准说也可解决所有期待可能性的判断问题。但是这种无限的扩大解释显然不符合类型人标准说的本意,而且将所有的社会一般的平均人作为一种类型也失去了划分“类型人”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类型人标准说仅仅是对平均人标准说的有益的补充或修正,而不能取代平均人标准说。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应是平均人标准与类型人标准的结合。
注释:
[1]参见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2]参见马克昌著:《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6页。
[3]同[1]。
[4]参见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229页。
*河南省潢川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法学博士[465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