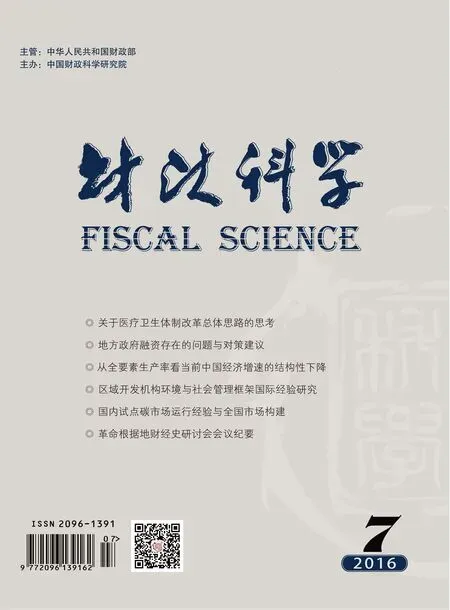从全要素生产率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结构性下降
李枢川
从全要素生产率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结构性下降
李枢川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演进的过程,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系统内生的,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区分为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其中技术进步又可以分为技术前沿的突破和对技术前沿的追赶,劳动效率分为劳动迁移和劳动分工。当前我国经济增速的结构性下降主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其中劳动效率的下降又是主要原因。
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劳动效率
对于当前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无论是决策层还是研究界,一个基本共识是下行压力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从结构性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的运行,说明研究的关注点开始从以往的需求侧转到了供给侧。
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我国近年来人口增长率和资本存量的增长并没有明显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近年来一直维持在5‰的增速,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发生在2008年至2009年。一个重要事实是,改革开放之后,劳动存量本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不大。2000年之后,劳动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超过0.5个百分点。因此,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劳动存量本身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在资本存量方面,尽管就我国资本存量在初始设定和测算方面仍然存在诸多讨论,但是陈昌兵2014年使用四个不同测算方法得到的资本存量近年来的增幅变化并不大。资本-产出比从2011年到2012年经历了一个较大的提高,但其原因在于产出增长本身出现的较大下降,而非来自资本存量。
因此,要想解释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为什么会出现结构性的下降,只能从“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缩写成“TFP”)这个概念入手。这段时期以来,决策层显然已经关注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这一词汇在中央文件中频繁出现,如2015年和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分别提到“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梳理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演进历程,理清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政策意义,有助于经济新常态下,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战。
一、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演进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生产的要素是资本(K)和劳动(L)两种,在紧凑形式的模型中,自变量可以唯一地转化为人均资本。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始于Solow(1957)。他在验证新古典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只能解释大约12.5%的总产出。因此,Solow使用外生的“残值(Residual)”来解释这个剩余的87.5%总产出,并将这个残值定义为“技术进步(A)”。1965年,Cass和Koopmans分别把Ramesy(1928)的研究引入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内生了储蓄率。但是,储蓄率的内生并没有解决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开始,Arrow等人开始努力将技术进步内生化。Arrow(1962)提出了“干中学”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进行投资的厂商可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生产率,非竞争性的知识具有外部性。在Arrow这一模型中,技术进步成为了由经济系统决定的内生变量,并且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将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
在Arrow研究的基础上,Romer(1986)和Lucas(1988)对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研究,都显示了知识或知识的积累(即人力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Aghion和Howitt(1992)发表《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增长模型》,将熊彼特主义“创造性破坏”理论引入到增长模型中,引发了将“提升产品质量的产业创新”作为研究经济长期增长基本动力的一波热潮。但是,这一类增长模型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生产率会随人口增加而增加。但是实证研究发现,即使在人口甚至是研发人员数量激增的情况下,生产率的增长水平也基本保持不变。Jones(1995)等人不再将知识资本看成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并且由于技术越进步将会越复杂,研发人员数量就需要持续的增长,但这仅能维持一个既定的TFP增长,新增的研发人员的收益将是递减的,因此TFP的长期增长率(可使用“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率”指代这一指标)将决定于人口增长率。而对于人口增长,许多经验研究都表明,人口的变化并不是独立于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其主要受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仍然是由经济系统决定的内生变量。
上述几种理论都是从技术进步(更多的是从知识存量)的角度研究TFP,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劳动本身的配置同样会影响经济增长这一事实。尽管技术进步是劳动效率改善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诸如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迁移带来的劳动效率提升就很难归因于技术的进步。这一改善同样难以进入增长方程中的劳动力总量,因此仍然属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
对于劳动效率的研究始于18世纪的Smith,他认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认为分工是由市场容量决定的。Young(1928)据此提出了著名的“杨格定理”,即市场容量决定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反过来又决定市场容量。Yang和Borland(1991)沿着Young的研究思路,提出了分工水平的不断演进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的观点,指出分工水平的不断演进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率,形成了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内生比较优势,从而扩大了市场容量,市场容量的扩大反过来又提高了分工水平,这一过程最终会使得劳动者生产率不断提高、收入不断增加以及经济的长期增长。
杨小凯、黄有光(1999)在对分工研究的同时也将制度这一变量引入到了经济增长的框架。他们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框架,并利用这一框架分析了交易费用、分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国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的降低则会提高人们的专业化水平,从而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即制度安排影响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决定了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影响一国经济绩效。而长期以来,制度一直被视为外生的因素,实际上是在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被排除出去的。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North等在分析历史案例的基础上就指出,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因,而技术进步仅是经济增长本身的表现形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制度,如分配制度、金融制度等,以及组织制度,对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至关重要,但它们是经济在运行过程中资本、劳动等要素组合生产产出时的动力或阻力,通过影响资本、劳动的配置影响经济增长。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可以假设制度对经济的潜在产出不产生短期影响。因此,本文下一部分的研究将从潜在产出的角度观察全要素生产率,并暂时忽略制度的影响。
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再认识
通过上文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演进的梳理,可以知道,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包罗万象,但是内生于一国经济系统,且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技术进步和劳动效率。这里,认为劳动效率独立于技术进步。既然全要素生产率内生于经济系统,因此它的这两个部分,只能是通过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要素才能得到发展。
对于技术进步,从Jones(1995)的研究我们知道,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必然性,技术进步的长期增长率将只决定于人口增长率。这里需要区分的是,Jones的研究更多地是着眼于高收入前沿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处于技术前沿,因此没有可借鉴的对象,只能通过技术试验带来技术进步。因此,它只能来源于人类智慧的自我进步,由于人类智慧进步从长期来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技术前沿的进步就同样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可以定义这种技术进步为“技术前沿的突破”(本文用TFP1表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一方面可以进行相关技术突破,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或者人才引进的方式对前沿技术进行追赶,因此技术进步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技术突破和对技术前沿的追赶。当然,由于并非处在技术前沿,后发国家的技术突破只会是零星的,在数量级上远远小于通过技术引进带来的对前沿技术的追赶。技术前沿追赶(TFP2)是人均资本的反函数,后发国家人均资本与前沿国家越接近,对前沿技术追赶的难度越大。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这些国家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且较早地完成了城镇化,因此这些国家通过在国内对要素配置提升劳动效率的空间较小,但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参与经济全球化提升劳动分工,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后发国家则可以同时从城镇化伴随的劳动力迁移(TFP3)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分工(TFP4)这两个方面提升劳动生产率。TFP3和TFP4都是劳动存量的函数(见图1)。

图1 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三、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降速的观察
从图2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轴经历了三次明显的变化。新世纪前后的五年(第一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轴为8%,然后在2003-2004年开始至2007年(第二阶段),经济增速不断加速,直到全球经济危机扭转其势头。这一段时间,经济平均增速超过了11%,如此之高的增速非常罕见,并且增长中轴抬升了近3个百分点,同样非常的罕见。而从2008年开始,经济增速开始阶段性下降,2008-2011年(第三阶段)经济增速中轴在10%左右,但是从2012年开始至今(第四阶段),经济增长中轴则下降到了7.5%,有近2.5个百分点的下降,这一降速非常可观。
新世纪开始,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分工、自由贸易、跨境资本流动等经济政策与互联网技术密切结合,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我国实施了与全球化进程有机结合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发挥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积极加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迅速成为最主要的全球生产中心。这一时期,劳动力迁移的速度(以当年农村人口与上年人口之差表示)总体上不断加快,城镇化不断加快,与国际上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时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经验相符。加速推进的城镇化,带来了低劳动生产率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优化了劳动的总体配置,整体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这一阶段,通过技术引进向技术前沿的追赶带来的技术进步(用设备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比例表示)比较平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由于人均GDP仍处于较低水平,向技术前沿追赶的空间巨大,因此追赶速度还未形成明显的递减。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劳动效率的改进是TFP改进的重要方面,而劳动效率的改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参与到全球化,二是劳动人口迁移下劳动要素重新配置带来的劳动效率提升。

图2 历年中国经济增速

图3 历年我国农村人口减少规模
经济增速的两次降档都发生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但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原因。危机之后,全球总需求结构出现收缩式调整,世界经济进入了增长低迷的阶段。为应对危机,中央迅速推出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通过需求管理实现了经济的V型反转。但这种方法治标而不治本,反而造成一系列后果。一是,2008年、2009年农村人口减少额迅速下降,说明经济刺激计划偏离了原先城镇化加速的轨道,这是因为推出的刺激计划明显倾向于以国资为背景的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大多数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有限。因此,这种政策本身的不平衡性为以劳动力转移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化带来了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快速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接下来几年,带来了房地产及相关市场的高速增长,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决策层采取了限制需求的方法,主要城市开始实施了各种限购措施,劳动迁移从政策层面被进一步限制。从图3来看,从2011年开始,代表真实城镇化指标的农村人口减少幅度不断下降,劳动流动带来的劳动效率提升效益在不断下降。第三,随着我国跨过人口红利的拐点,以低成本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的优势不断缩水,全球化分工带来的劳动效率提升也不断在缩水。

图4 历年我国设备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例

图5 历年我国城镇劳动生产率和全国劳动生产率增速
在技术前沿的追赶方面,可以看到设备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近几年来呈现下降趋势(见图4),这是我国人均GDP不断接近前沿国家后,追赶速度自然下降的正常反应。
总的来说,这两轮经济增长中轴的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全要素生产率中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又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也正是经济增速是结构性下降而非周期性下降的真实原因。因此,只有切实推进结构性改革,才可能实现中国中长期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包括:继续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直至最终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要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往的相关限购政策要有退出机制,通过吸纳劳动人口,实现劳动要素的合理配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关系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全局。
[1]陈昌兵.可变折旧率估计及资本存量测算[J].经济研究,2014(12).
[2]RM Solow.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12-320.
[3]Ramesy Prank.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J].Economic Journal,2010(1928),38,543-559.
[4]D Cass.Optimum Growth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5,32,233-240.
[5]TC Koopmans.On the Concept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R].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s,1963,28.
[6]K Arrow.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2,29.
[7]PM Romer.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94(5),1002-37.
[8]PM 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71.
[9]Aghion,Howitt.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J].Econometrica,1992,60,323-51.
[10]RE 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3-42.
[11]CI Jones.R&D-Based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4),759-84.
[12]Young.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Progress[J].Economic Journal,1928,38,527-542.
[13]X Yang,J Borland.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460-82.
[14]杨小凯,黄有光著,张玉纲译.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3月.
The Structural Declin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FP
Li Shuchua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e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and considers that TFP is endogenous in the economic system.So TFP can be divided in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labor productivity.Whil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onsists of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and the catch-up to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labor productivity comes from the labor migr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The structural declin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mainly due to the declin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and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is the decline of labor productivit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echnology Progress;Labor Productivity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F242
A
2096-1391(2016)07-0021-06
(责任编辑:邢荷生)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