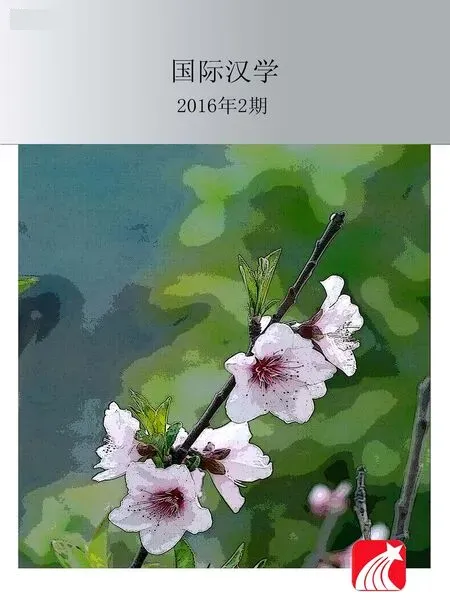纪念国学大师、《国际汉学》创刊人、原主编任继愈先生诞辰100周年专栏
《国际汉学》开卷语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她悠久的文化传统对世界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东学西传已有长达上千年的历史。汉学(Sinology,又称中国学)现已成为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中国文化属于全世界。
《国际汉学》正是为推动这项宏大的事业而诞生的。它以中国文化为其研究对象,旨在沟通海外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展示海内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报道世界各地汉学研究进展的信息,介绍重要的汉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海内外著名学者。
《国际汉学》将在世界范围内探究中国文化的产生、发展与嬗变,寻踪中国文化的外传及其影响,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中国是汉学的故乡,她理应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心。这曾经是几代中国学者的夙愿。为实现这一理想,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文化的研究,我们愿尽绵薄之力,使这份学术性集刊成为国际汉学界共同的园地。
原刊于1995年出版的《国际汉学》第一辑
任继愈先生与《国际汉学》
张西平
任继愈先生自1995年《国际汉学》创刊以来一直担任主编。正是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国际汉学》才走到今天。我清楚地记得,1992年任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了焦树安先生、我和当时书目文献出版社文史编辑室刘卓英主任开了一个小会,讨论如何创办《国际汉学》。当时,我刚刚调入国家图书馆工作,对海外汉学这门学问虽然充满好奇之心,但了解并不太多。任先生嘱咐我可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徐梵澄先生那里约稿,说他刚从印度回来,对中国文化在南亚的传播十分熟悉;又让我找蔡仲德先生,说他最近写了冯友兰先生的年表。在任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在京城四处约稿。为此,我结识了当代学术大师徐梵澄先生,走进了北大冯友兰先生生前所住的三松堂,推开了住在皂君庙的庞朴先生的书房,聆听了语言学家陈原先生的教诲。就这样,《国际汉学》第一辑的稿件很快组齐了。当时国家图书馆焦树安先生,商务印书馆吴隽深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耿昇先生以及我的好友杨煦生,都为《国际汉学》第一辑的诞生出力不小。我的德文老师、在京的德国汉学家、德国著名汉学杂志《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的主编弥维礼( Wilhelm R. Müller)博士得知《国际汉学》的出版有了困难,就慷慨解囊,支持我们。为此,任先生专门在国家图书馆的红厅接见了弥维礼先生,感谢他对中国学术的支持。1995年1月,《国际汉学》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了。
1996年我从德国访学回国后不久就开始办理调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中文学院老院长程裕祯教授希望我从国家图书馆调到北外工作时将《国际汉学》的具体编辑工作一起带到北外。当时我征求任先生的意见,他欣然答应了我的要求,并希望我到北外后像在国家图书馆一样,全力投入《国际汉学》的编辑工作,继续办好这份学术辑刊。就这样,《国际汉学》从它的诞生地—中国国家图书馆转移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我到北外后,任先生作为主编,为《国际汉学》的发展做了件非常重要的事,在他的推动下,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开始和大象出版社展开战略性合作。任先生认为《国际汉学》应有一个稳定的出版机构。为此,他亲自写信给大象出版社周常林社长,向他介绍了《国际汉学》的主旨和学术意义。1996年的深冬,京城飘起了雪花,我和大象出版社的社长周常林、总编李亚娜、副主编崔琰一起走进了任先生南沙沟的家。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会谈。任先生高度称赞了大象出版社的学术眼光,他说:“现在商业化思潮弥漫中国出版界,大象出版社能将海外汉学研究的学术出版作为全社的长期战略发展方向,非常了不起。”大象出版社和任先生有着长期合作,当时由任先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刚刚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周社长当时说:“由任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能在大象社出版,标志着大象社要长期支持海外汉学研究的出版,要在海外汉学研究出版方面使大象出版社成为全国出版社中的旗帜。”他还设想将来在大象出版社可以设国际汉学学术奖,全球的汉学研究学会也可以落脚在大象出版社。任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想法,他说:“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文化也要走向世界,要做好这一点,研究好海外汉学是很重要的。”就这样,在任先生的家中,我们确定《国际汉学》将长期在大象出版社出版,同时大象出版社还将出版由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由任先生任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室外是寒风凛冽,屋内是一派春意,在任先生带领下,《国际汉学》度过了它的严冬,迎来发展的春天。
200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迎来了她65周年华诞,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召开了“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国际研讨会”,任先生在大会做了主题发言,2004年《国际汉学》迎来她第十辑的出版,任先生亲笔题词:“广交天下学友,共促文教繁荣”;2005年在首届“世界汉语大会”上,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受国家汉办委托同时召开了“海外汉学国际研讨会”,任先生在大雨中赶到大兴国际会议中心参加了开幕式, 祝贺大会的召开;2007年6月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开始作为全国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中心,任先生专程来到北外表示祝贺。为了促进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为了支持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任先生对我们几乎是有求必应。
2007年,为了支持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申请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任先生提出,他不再担任《国际汉学》的主编,希望我来接替他主持《国际汉学》和“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当时,我诚惶诚恐。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任先生的带领下,《国际汉学》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最有影响的学术阵地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声誉。这个时候由我来接任主编一职,压力很大。在我和我的同事们的请求下,任先生同意继续担任《国际汉学》的名誉主编,以使这份杂志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任先生是《国际汉学》真正的灵魂, 在杂志创办的初期,他不仅仅审阅每辑稿件,还亲自为杂志写稿。后因他年事日高,不再过问杂志的具体事情,但他仍给我们推荐稿件,提出希望和要求。任先生一直将《国际汉学》作为他的学术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国际汉学》有今天这样的学术影响和学术地位,与他的关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2008年,他亲自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写信,建议将《国际汉学》变为正式刊物,同时支持北外海外中国汉学研究中心申请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任先生的信受到了教育部社科司的重视,社科司专门来函给北外和原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落实《国际汉学》刊号问题。正是先生的这次出面,学校将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作为独立的科研机构从中文学院独立出来。
我自己学术研究方向的转变也是在任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我主要从事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后来随着历史的重大变化,我自己的命运和学术也随着发生了变化。当时,我深深感到在中国介绍西方当代哲学尽管是很重要的,但如果只是单纯地介绍而不研究中国的文化,会使西方哲学只是作为一个外来的思想在学者的书房中,而它并未通过学者和自己生活的土地发生本质性的联系。如何寻找新的方向展开自己的学问,我处在极大的彷徨之中。当时,我刚调入北京图书馆(现称“国家图书馆”)工作,有一次向任先生请教,“如果我转入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从哪里入手比较好?”任先生沉吟了一会儿,告诉我他要考虑一下。几天后,任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如果想转入中国思想史研究,可以做一做明末清初那一段的研究工作。他说:“这一段涉及西方哲学和宗教,不少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不太熟悉,你是研究西方哲学的,进入这一段研究有一定的优势。”任先生告诉我做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思想研究有两位学者比较重要:一个是朱谦之,他研究这个时期中国哲学在欧洲的传播;一个是何兆武,他研究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他们的书我都可以找来看看。
困顿、迷茫中的我开始有了新的学术方向,我也决心尝试一下这个研究领域。于是,我一头扎进了北图的书库之中,方豪、陈垣、陈受颐、钱锺书这些名字才开始逐步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几乎用了整整10年时间,我收集到了民国以来这一研究领域里几乎所有的研究著作和论文,看到了大量原始文献,我也深深地被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吸引。此时,我才体会到任先生给我指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方向。虽然,将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困难很大,对自己的能力和学识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我第一次感受到学问和自己生活的土地的密切联系,感受到文化互动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慢慢地走出那种“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二元对峙的学术路向和思考方式。在《国际汉学》第一辑的编后记中记下了我当时的这个转变,我在后记中写道:“眼下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工作处在低谷,守护好一块纯净的学术园地可谓困难重重。与此同时,现代化的进程亦给予中国的人文科学一个千载难逢的转机,中国文化在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日益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弘扬中华文化,开辟汉学研究的新天地,这或许是我们对张横渠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新理解。我们将朝这个目标努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20年的努力,使我走进了新的研究领域,我感谢任先生给我指出的这个全新的研究方向。
在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怀念先生对《国际汉学》从创刊到发展的每一步所给予的指导、关怀。没有先生当年高瞻远瞩,将《国际汉学》创刊,就没有我们今天。2014年6月,在先生去世后不足五年,《国际汉学》被批准了正式刊号,先生在天之灵一定会露出笑容,现在《国际汉学》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国际中国文化的重要学术阵地,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们一定继承先生的学术理想,为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化研究,从更广阔的视角揭示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而不断努力。
张西平
2016年4月16日写于
北京岳各庄东路阅园小区游心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