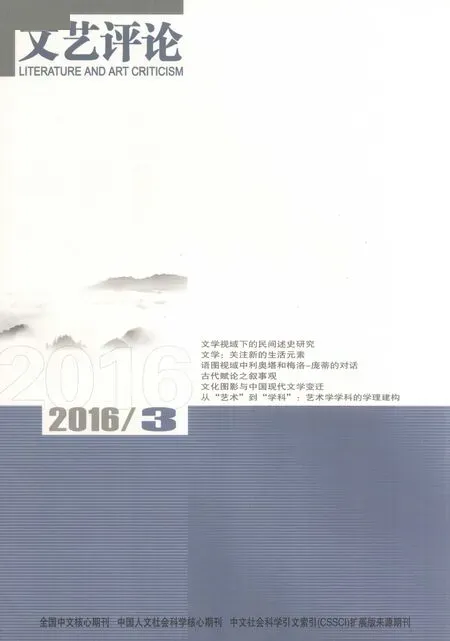古代赋论之叙事观
○周兴泰 王 萍
古典诗学
古代赋论之叙事观
○周兴泰王萍
从先秦至清代,传统赋学理论源远流长。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赋学研究呈现出日益兴盛的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传统赋学理论进行整理和研究,以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为代表。学者们注重梳理传统赋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各个阶段的不同特征,着力探讨赋的社会功用和体制特征,而对其中蕴含的叙事观念,却关注较少,甚至忽略了。兹拟从纷繁复杂的传统赋学理论中钩稽归纳出其鲜明的叙事观,概括言之,约有以下四端:
一、注重对事物的铺陈叙写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赋在体制上的突出特征就是铺陈,即对事物进行穷形尽相的铺张描绘和详细叙述,辞藻华丽绮靡,内容广博宏富。诸多文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涉及赋的铺陈叙写的特点,略举例如下:
《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曰:“教六诗: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郑玄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①
刘熙《释名》卷六《释典艺》曰:“敷布其义,谓之赋。”②
挚虞《文章流别论》曰:“赋者,敷陈之称……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③
陆机《文赋》曰:“赋体物而浏亮。”李善注曰:“赋以陈事,故曰体物。”④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⑤
钟嵘《诗品》曰:“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⑥
王昌龄《诗中密旨·诗有六义》曰:“赋者,布也。象事布文,错杂万物,以成其象,以写其情。”⑦
贾岛《二南密旨·论六义》曰:“赋者,敷也,布也。指事而陈,显著恶之殊态。外则敷本题之正体,内则布讽诵之玄情。”⑧
朱熹集注《诗集传》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⑨
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取穷物之变。如山川草木,虽各具本等意态,而随时异观,则存乎阴阳晦明风雨也。”⑩
上述诸家都注意到赋作为一种铺叙手段,具有指事而陈、象事布文的特征,其实质属于叙事艺术范畴。从音韵学的角度看,赋与“敷”“铺”“布”等字声同而义近,它不假比兴、非常直白地对所述对象进行敷陈铺排,全方位地描摹其声貌,大大提高了叙事艺术的表现力。
虽然赋颇遭后人堆砌辞藻、泛滥铺张的诟病,但却大大推动了空间立体叙事艺术的发展。清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已注意到赋擅长对杂沓多端的情事进行绘形绘影、无所不包的铺写的特性,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道:“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左右横列之法,是一种共时叙事法,赋家在空间上推而广之,动则东南西北、前后左右、远近高低、上下内外,有时甚至于进入一个杳渺无垠的世界,由此展现出一个个辽阔的空间格局,而天上人间的纷纭事物悉数摄入赋家的笔端,从而呈露出一个个壮丽宏伟的场景。先后竖叙之法,是一种历时叙事法,它按照时间序列,既具体展开情事发展的全过程,又详尽铺写过程中的每一个层面与环节,有时甚至虚拟场景,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终至一个无以复加的宏伟之境。刘氏从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肯定了赋对杂沓多端的情事进行铺排叙述的贡献。后来,朱光潜先生在论述赋之所以别于诗的问题时,称引了刘氏上述话语,并进而指出:“赋大半描写事物,事物繁复多端,所以描写起来要铺张,才能曲尽情态。”
据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曾在回答友人问作赋心得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集中反映了赋取材广阔、铺叙有序的典型特点。关于这一点,他人也多有论及。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曰:“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清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家之心,其小无内,其大无垠,故能随其所值,赋像班形。”我们不难发觉赋家以驰骋上下古今的强大想象力、容纳宇宙历史的宏阔心胸、绚丽华艳的文辞及无所不施的笔触来叙写天地间一切事物,传达出赋家内心追求巨丽、大美的审美理想。万事万物都被刻意搜罗,形诸墨楮,由此赋作文本呈现出汪博宏富、夸饰赡丽之美:“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词夸;取风云山川之形态,使其词媚;取鸟兽草木之名物,使其词赡;取金壁彩缯之容色,使其词藻;取宫室城阙之制度,使其词庄。”恰如一种“冠冕佩玉之步骤”。正是赋家以纵横之笔总览众物,才使辞赋呈现出包罗宏富、气势雄健的特征。一方面,赋家以包罗之心、宏富之辞对外部广阔世界进行铺张叙述与渲染;另一方面,赋家也对世间渺小卑微事物乃至抽象事物,如人的心灵世界进行细腻的摹写,从而造成赋体本身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兼具的双重特征,正如林联桂在《见星庐赋话》卷三中所言:“赋之有声有色,望之如火如荼,璀璨而万花齐开,叱咤则千人俱废,可谓力大于身,却复心细如发者。”
对于赋所具有的直陈铺叙的本质要素,当今学者也各有阐述,如万光治先生说:“故就实质而言,铺、敷、布、陈具有在时空两个方面把事物加以展开的意义。这些概念之被引入文学,指的即是不假比兴、直接表现事物的时空状态的艺术手法。赋既然可与敷相通假,又最早与语言表述方式发生关系,后人很自然地用它来概括文学中陈述性、叙事性和描绘性手法,并进一步用它来称谓以上述手法为主要特征的文体,这就是赋体命名的来源之一。”刘朝谦曰:“铺,有展开和叙事的双重涵义:展开也是一种展示,而且在赋是一种夸耀式的展示;展开赋予大赋的是大赋文本空间化的特征,这种空间一般是在一个中心的基础上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铺开,或者是按一种植物学、矿物学的分类框架来展开;叙事则是指陈述性的写作,其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往往具有同一性,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张力,这样的叙事方式长于体物,且使大赋文体较之骚体赋主要具有的不是情灵之性,而是物性。”两人都注重从时间叙事、空间展开两个层面来探讨赋之铺叙之义,从而得出赋之陈述性、叙事性、描绘性等重要特征。程章灿先生在分析两晋赋叙述结构的经营时说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话:“以横向的空间的顺序展开(结合时间的顺序)和以纵向的时间的顺序(结合空间的顺序),这两种极有凝聚力和涵括量的结构形式,在晋代赋家手里终于完善起来了。这是两晋赋史的一个贡献。赋凭借这两种结构形式,长期占据了长篇描写和长篇叙事的文学领域。这或许也是中国古代长篇描写诗和长篇叙事诗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认为赋就是长篇描写诗和长篇叙事诗也不无理由。”从时、空展开铺陈的层面阐述赋何以为长篇描写诗与长篇叙事诗,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诚如祝尧所言:“赋有铺叙之义,则邻于文之叙事者。”铺叙手法的运用,无疑大大增强了赋体的叙事功能。中国古代文人把汉字本身所具有的形美、音美、意美,非常娴熟地运用到赋的创作中,对外部客体世界作细腻描写与铺排式、罗列式叙述,这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把握进一步提高的结果,标志着人们艺术思维与叙事能力的日趋成熟,同时这也正是辞赋在叙述描写方面对中国叙事文学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强调主客问答的叙事结构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将“遂客主以首引”与“极声貌以穷文”并举,认为二者是赋区别于诗而自成一体的两大必不可少的要素。所谓“遂客主以首引”,指的是在赋作开篇假托主客问答对话,并引起下文,由此形成赋文的基本叙事结构,而这是辞赋对中国叙事的另一极大贡献。
荀子的《赋篇》包括《礼》《智》《云》《蚕》《箴》五篇,基本上都是先设问——“有物与此……臣愚不识,敢请之王”,后回答——王曰:“此夫……者欤?夫是之谓,请归之……”的问答格式,问语与答辞构成了赋的全篇,只有问答而尚未有具体的故事。《楚辞》的《卜居》《渔父》,以屈原与卜者詹尹、渔父的对话问答方式展开叙事,既有问答又有故事,虽说故事的因子还显单薄,但与《赋篇》相比,已有不小的进步了。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等,则进一步发展了问答对话的结构,以主客问答充当导入正文的引子,与其说问答是正文的引子,还不如说它是故事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汉大赋通常以虚拟的人物进行问答对话,以绚丽夸张的铺陈来增加自己论辩的资本,显示出很强的论辩性。如枚乘《七发》中“吴客”以七事说“太子”,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互相辩驳,扬雄《长杨赋》中“子墨客卿”与“翰林主人”相对答,班固《两都赋》中“西都宾”与“东都主人”相争论,张衡《二京赋》中“凭虚公子”与“安处先生”相问对,由此主客问答的格局成为汉大赋的定式,尽管其中的故事性越来越弱,然而它对后世赋作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如西晋左思在《三都赋》中假设“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三人为辞,唐杨夔《溺赋》中元微子与宏农子相问答,宋苏轼《赤壁赋》中苏子与客之对话等等,不一而足。刘知几《史通·杂论》指出:“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的确,自荀赋假设君臣问答以来,中国赋史已形成一种问答对话的叙事传统。这种假托人物问答对话的结构非常利于叙事的展开,于是后世赋家纷纷予以效仿,从而使赋的虚构叙事更加熟练起来。
元祝尧《古赋辨体》卷三《子虚赋》下注曰:“此赋虽两篇,实则一篇。赋之问答体。其原自《卜居》《渔父》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此体遂盛。此两赋及《两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于赋之问答对话结构有溯源穷流之意,但目光似乎又仅仅停留于汉赋,而未伸展到后世赋及其他文体上,只是皮相之论。清章学诚则比祝尧更进一步,指出假设问答的结构形式,其实早在先秦诸子的寓言故事中就已萌芽了:“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宏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的寓言故事,多采自民间并经文人润色加工,普遍采用虚构对话的形式,对话体、故事性、语言通俗的特点非常突出。如《庄子·外物》有一则寓言《儒以诗礼发冢》: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者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岁页,而以金锥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写两个儒生用儒家的诗礼去盗墓的故事。以人物对话叙写故事,生动形象,富有诙谐意味。战国时人们著书言说已经习惯了用这种对话问答体,以致成为当时社会的盛行风气。饶宗颐先生在《文学与兵家》中论道:“古之能文者,善擒纵捭阖之术,优为之赋出于纵横家,尤为的证……《汉书·艺文志》有主客赋。赋之为体,肇基于此,惜其文不可睹。然以意揣之,必立主客之分而为对问之体,以蔓衍其辞。战国时人著书惯用对话,近出土马王堆佚书,若伊尹、九主、十大经,无不如此,自是一时风气使然。至于‘客主’之名,原出兵家,继乃演而为赋体。向非孙膑兵书,则出理殆不可晓。此出土文书,所以有裨于考证也。”以出土之书论证了对话体在战国的盛行,进而得出“至于‘客主’之名,原出兵家,继乃演而为赋体”的论断,乃发前人之所未发。
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加之从先秦子书及其他各种著书中汲取丰富营养,设辞问答结构逐渐成为赋的必不可少的形体要素之一。曹明纲在《赋学概论》中认为:“设辞问对在最初的赋作中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带规律性的、固定的普遍状况,它是赋体从诗文中独立出来,在形体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基本要素。”赋以主客问答的结构展开对故事的叙述和事物的描写,从而使其自身在中国文学的叙事演进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三、主张征实与虚构的叙事原则
虚实相间是文学创作与审美的基本原则,历代文论家对此有太多的阐释。对于赋体叙事到底应该遵循征实还是虚构的原则,赋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主张:
第一,反对“虚辞”,主张“征实”,以左思、皇甫谧、刘师培为代表。晋左思《三都赋序》曰:“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巵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左思指出赋体创作必须依本求实,而不应该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那样,仅凭想象,“假称珍怪,以为润色”。应该说,左思改革赋体创作“虚辞滥说”风习的决心是好的,但如果文学创作都必须有凭有据,那就未免太生硬、无美感可言了。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虚实完美结合的典范,实中有虚,虚中见实。如果一味征实,缺乏一定的想象力,那文学的美感从何而来?左思反对一种极端,却因此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这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他对文学征实叙事一路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皇甫谧《三都赋序》曰:“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纎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夏接榱,不容以居也……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批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皇甫谧沿袭左思批评汉赋“匪本匪实”的路子而变本加厉,或曰“言过于实”,或曰“博诞空类”,或曰“虚张异类”。挚虞《文章流别论》批评汉赋“四过”(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立意甚明,其实质在于批评汉赋的虚构“背大体而害政教”。刘师培《论文杂记》曰:“赋之为体,则指类事情,不涉虚象,语皆征实,辞必类物。古‘赋’驯为‘铺’,义取铺张。循名责实,惟记事析理之文,可锡赋名。”非常明确地指出赋之所以为赋就在于赋在铺叙事情时不涉虚象、语皆征实的特征。上述诸论都可以归为赋体纪实性叙事一派。
第二,对赋的虚构叙事给予高度肯定,以司马迁和顾炎武为代表。赋发展至汉代,赋家大大提高了体认、把握、再现自然外物的能力与水平,这促使赋这种本质上为描绘性的文体向虚构夸饰方向发展。《文选》李善注宋玉《高唐赋》“假设其事,风谏淫祸也”,《登徒子好色赋》“假以为辞,讽于淫也”,已肇赋虚构性之一端。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评论:“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籍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就以“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等虚言、虚事、虚人为例论证司马相如作赋多喜假设虚构的问题。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渔父》云:“《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而太史公《屈原传》、刘向《新序》、嵇康《高士传》,或采《楚辞》《庄子》渔父之言,以为实录,非也。”注意到古赋的假设虚构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清顾炎武《日知录·假设之辞》曰:“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也。后之作者,实祖其意。”上述诸论都可归入赋体虚构性叙事一派。
第三,主张虚构与征实并重,以刘勰与刘熙载为代表。刘勰《文心雕龙·夸饰》篇主要以赋为论述对象,认为夸饰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可以获得对事物穷形尽相的描摹作用与让人称奇的审美效果。而夸饰其实就是一种虚构,适当的夸饰与虚构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必不可少,因此赋家在运用夸饰与虚构时对于度的把握至关重要。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在夸饰与征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达到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呢?刘勰为我们作出了公允而精辟的回答:“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只有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才能创作出赋体文学的典范。相反,如果过分征实,抹杀了艺术的想象力与创造性,这样的赋作必然是古板而缺少灵性的。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此处包含两层意思:一、赋体作品要描述客观事物、表现现实生活,即“象物”。但“象物”有“肖象”与“构象”之分。二、“肖象”是征实的,更容易达到;而“构象”是虚构的,但因“构象”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运用想象虚构等形象思维创造出高于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所以比“肖象”要难,而且,只有“构象”,才能给人以无穷的联想与审美愉悦,所谓“象乃生生不穷矣”。虽然刘熙载也说:“赋有以所纪之事实重者,如王无功《游北山赋》,似不过写其闲适旷达之意,然叙文中子一段抽出之,足为文献之征,乃赋中有关系处也。”并举王绩《游北山赋》为例,说明赋作有时所纪之事也必须征实。但他还是更看重虚构叙事:“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至模山范水,犹其末事。”“赋之妙用,莫过于‘设’字诀,看古作家无中生有处可见。如设言值何时、处何地、遇何人之类,未易悉举……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架虚行危、“设”字诀、不厌奇皆指虚构假设的诀窍。赋中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皆可虚构,使赋的叙事呈现出极大的虚构叙事的特征。而真正高明的叙事应该达到“须当有者尽有,更须难有者更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的“纵横自在”地出入于真实与虚构的境界。惟有如此,才能使赋之叙事更为灵活变动、宛转自如。
在赋体文学中,征实固然必不可少,但对所铺叙的事物进行创造性的想象虚构,则更为重要,这样才能使赋显现出多姿多彩的发展局面。征实与虚构作为叙事学的两大分支,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前者是对实有之事、已发生事实的叙述,后者则是对可能发生事实的叙述。前者指称现实,后者指向现实。“如果作者在可能的世界范围内描写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事和人,则是指称现实。如果作者是用虚构的方法描述不可能世界的事物,或者把现实世界的事物夸大,而使之越过了不可能世界的边界,那么这种叙述方法则叫作指向现实。或者说,是实在的就是指称现实,是虚构的就是指向现实。”然而二者的出发点却是相同的,即力图达到对事件真实本质的叙述,都可对现实起表述作用、批判作用,二者统一于叙事学之“叙述”上。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说:“叙事作品的功能不是‘表现’,而是构成一幅景象,一幅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不解之谜的、然而不可能属于摹仿范畴的景象……叙事作品不表现,它不摹仿……叙事作品中‘发生的事情’,从指物的(现实)的角度来看,是地地道道的无虚生有。‘所发生的’,仅仅是语言,是语言的历险。”其实,叙事的本质就在于建构一种景观、一个世界,就是虚构,惟有虚构的事件,才能提供引人入胜的审美愉悦,从而使叙事散发出经久不变的艺术魅力。
传统赋学理论家在叙事层面上关于赋的纪实叙事与虚构叙事的讨论,其实是在由征实与虚构两大分支组成的中国叙事传统中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它必将极大地促使我们认清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各自的本质特性及其离合情状。
四、讲究眉目朗然的叙事层次
我们知道,叙事必须讲究层次,方能有条不紊、步步推进,赋之叙事亦如此。清代赋论家在探讨作赋方法时,经常涉及到赋的层次的问题,如汪廷珍《作赋例言》曰:“题有层次,由浅入深,由虚入实,与时文无异。即无层次题,亦须以意分出来路、正位、去路,须相生而不相犯,一夹杂则无序,且气亦不清矣。”徐承埰《赋法梯程》卷首载作者之师吴晓岚撰《论赋十四则》曰:“作赋第一要诀,是分析层次,其法与时文、排律一例也。凡大题之本有事实情节者,固宜按之本事,挨次详写;即小题无甚节次,亦必想出前虚后实、前宽后紧、前浅后深之法。”二人所论,涉及辞赋作法前虚后实、前宽后紧、前浅后深等层次问题,然与叙事之关联不甚紧密。真正对赋作层次与叙事之关联问题进行过深刻论析的赋论家,要属徐斗光、侯心斋、顾莼等人。徐斗光《赋学仙丹·律赋秘诀》言:“凡赋以炼格以分层次,宜相题为之……其层次,则有如八股时文。有以古题命名者为题,古题直起,亦用总冒,后即以叙事述事为层次,事毕乃止也。”侯心斋《律赋约言》云:“又有以古事命题者,即以叙事为层次,事尽而止。然首段可用总冒,仍不妨说尽矣。”两人同时注意到以叙事述事为层次,即根据故事的发展来安排赋作的层次,这样叙事脉络就显得非常明晰。顾莼《律赋必以集·例言》云:“初学作赋,每苦无生发,以不讲层次之故也。每一题到手,须将题之前后细想一番,分作数层,然后将所限之韵配合,某层宜押某韵,某韵宜用某字,或平叙或提顿,随时变化,初无一定之质,惟期不凌躐,不重复而止。”按换韵规律分层,赋的叙事层次与韵律变化紧密结合。总之,赋在叙事时,呈现出由浅入深、由虚入实、前详后略、以叙事为层次、按八韵分层等特征,这样的叙事层次使赋的叙事既眉目朗然又摇曳灵动。如唐代陆贽《冬至日陪位听太和乐赋》依循赋题来安排赋作的结构层次,按题意层层推进,李调元《赋话》卷四评云:“先叙冬至,次叙陪位,然后叙作乐,末以听字作收煞,循题布置,浑灏流转,盖题位使然,不必尽以雕镂藻缋为工也。”与陆作就题义分层布局不同,黄滔的《馆娃宫赋》(以“上惊空壕,色施碧草”为韵),则依换韵规律来安排叙事层次,共分为四段,第一段“城”“名”“觥”“惊”同“清”韵,揭示题意,唤起全篇,作者目睹吴国荒城,由此感发“古人失而今人惊”之叹。第二段作者以“想”字贯通,“创”“状”“上”同“漾”韵,“螭”“差”“曦”“施”“迤”同“支”韵,“惑”“侧”“色”同“职”韵,对当年馆娃宫华丽辉煌的建筑与吴王骄奢淫逸的生活进行了深切细致的描摹。第三段以“殊不知”领起,“空”“栊”“蒙”同“东”韵,“隙”“石”“碧”同“陌”韵,“壕”“高”“涛”同“豪”韵,转入对今日馆娃宫及吴国衰亡破败的叙述。最后一段,“浩”“道”“草”同“皓”韵,点名赋旨,告戒统治者应借古察今,传达出作者的悲凉心境与感伤情绪。李调元《赋话》卷二谓此赋:“昔盛今衰,各以三韵叙次,布置停稳。”就明确地道出了其以韵脚转换来结构布局的特色,第二、三段各押三韵,展开吴国昔盛今衰的强烈对比,叙事层次工稳明了,情感表达亦丰富细腻。
李调元在《赋学正鹄·序目》中更是对赋的层次方法及其重要性作了充分的论证:“层次类者,赋家不二法门也。作赋如作文,有前路,有中路,有后路,有翻面,有反面,有正面,有衬面,而皆可以层次括之。不特律赋不可无层次,即周秦汉魏诸古赋,莫不步骤井然,眉目朗然。虽寥寥短篇,层次自在,特别神明于规矩之中,使人莫寻其迹耳。作赋不讲究层次,犹航断港绝潢,以蕲至于海也。学者每得一题,须得将题之前后路细想一番,分作数层,然后将官韵配合,某层宜押某韵,宜用某字,自有一定不易之节次。即题极枯窘,亦须于无层次中分出层次来。是故有叙事题之层次,咏物题之层次,言情题之层次,说理题之层次。初学必从叙事题入手,即以所叙之事为层次,事尽而篇法已完。”体裁上,不论是律赋还是古赋,题材上,不论是叙事题、咏物题,还是言情题、说理题,都必须讲究层次且各自有别,而初学者宜以所叙之事为层次进行练笔,这样赋作的叙事才会呈现出井然有序、眉目清朗之美。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明白,在纷纭繁复的传统赋学理论中除了对赋源、赋史、赋用、赋体、赋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外,还蕴藏着丰富复杂的叙事观念。赋家往往先假托一个主客问答的情境,然后在此情境下,或对对象化事物进行纪实性描述,或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虚构能力,多层面、多角度对事物进行铺张描绘与夸饰渲染,从而使赋作呈现出层次清晰、井然有序的叙事格局。正是这些丰富的叙事观念,为我们清晰梳理赋的叙事成分的演变进程与深入解读赋的叙事特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正是它们,推动着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不断向前迈进。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796页。
②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页。
④萧统编、李善《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1页。
⑥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
⑦⑧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上海: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第371页。
⑨朱熹集注《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视阈中的唐代辞赋研究”(项目编号:13CZW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南昌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