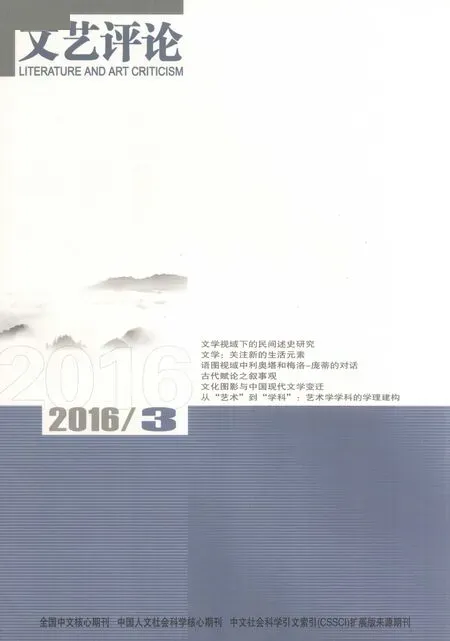“接地气”的平民非虚构写作
○任雅玲
“接地气”的平民非虚构写作
○任雅玲
一、作者“接地气”
平民非虚构作品的作者“接地气”。首先,他们来自民间,不仅不是职业作家、史学家,而且有的甚至原来都不识字,是纯粹的“草根小民”。
如《乱时候,穷时候》的作者姜淑梅1937年出生,没上过学,小时候只跟着哥哥读过几天书,60岁才开始自学认字,75岁才在女儿的指点下开始学习写作,但她却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好学精神在76岁就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每年一本,又出版了《苦菜花,甘蔗芽》《长脖子女人》,据说第四本书也已完稿。姜淑梅是个“接地气”的作者,她解放前经历过战乱、逃难,解放后经历过饥荒、文革。她从平民中来,写的就是平民的生活,用的就是平民的语言在讲他们熟悉的生活。可以说,她的个人史就是中国无数个普通百姓的历史。
《胡麻的天空》的作者秦秀英也是个“接地气”的作者。她是个农民,1947年出生的她只念过一年半小学,65岁那年她在儿媳的指点下开始做自然笔记,起初儿媳只是为了让老太太排遣寂寞,把在公园里照的各种植物的照片放在电脑里,让秦秀英画。画完后,儿媳还让她标上花名、日期、地点和天气情况。虽然六十多岁的秦秀英才开始查字典学文化,但她熟悉自己所画的那些朝夕相伴的植物、家畜等,于是68岁她就出版了《胡麻的天空》,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一个农民的世事人生和我国农村六十多年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的变迁。
当然,这些平民写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作品,也有很多客观因素在起作用,有的是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如张泽石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赖施娟是大学的教授;有的是家庭文化氛围浓郁,培养了自身良好的人文修养,如许燕吉的父亲是著名作家许地山,饶平如的父亲是有名的律师,妈妈是个能吟诗作画的才女;有的是因为有“良师”指点,如姜淑梅有个当作家的女儿指点,秦秀英有我国最早的自然笔记倡导者之一的儿媳指点。没有这些客观因素的潜在作用,这些普通百姓写出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也是很难的事情。
其次,平民非虚构作品的作者都有厚实的生活积淀,他们写的大多是他们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这些作者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阅历丰富。如《平如美棠:我们的故事》的作者饶平如1922年出生,他曾是黄埔军校学员,参加过抗战,又参加过内战,后来做过编辑、美编。1958年,因当过国民党军人,饶平如被送到安徽“劳动改造”,跟妻子分开22年。饶平如用文字和图画记录了他和妻子的爱情故事,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是时代变迁的见证。《我的朝鲜战争》的作者张泽石1929年出生,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作为战俘回国后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是在为战俘们伸张正义。《蹉跎坡旧事》的作者沈博爱1936年出生,他是湖南浏阳的中学生物教师,曾被打成右派,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入狱5年。吴国韬1942年出生,72岁出版了《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书写了他1958年至1980年间在武陵山区的教学生涯。受众通过他的执教经历可以感受到一个普通民办教师的生存艰难与人生世事,而这也恰好是我国特殊时期农村教育的缩影。
可见,平民非虚构作品的作者都是扎根生活的,“接地气”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他们有扎实深厚的生活积累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他们没有书斋气,没有先入为主的创作理念,他们在真实的生活现场浸润,书写的是更高层面上的真实的平民生存状态。这是一个具有原创力的写作群体,他们的作品虽称不上名篇佳作,但却在读者中掀起了阅读小民史的热潮。
二、文体“接地气”
因为平民非虚构作品的写作者都未经过专业的写作训练,或许正因这一点,他们在创作上更少束缚,这在文体的选择上有非常突出的体现。卡波特认为:“非虚构小说将不会被纪实小说所混淆,它是一种既通俗有趣又不规范的形式。它允许使用小说家所有的手段,但是它通常包括的既不是有说服力的客观事实,也不是诗人高度的艺术虚构,这种形式是可以通过探索达到的。”①的确,平民非虚构作品的创作手段是丰富多样的,如作者在文体的选择上就是自由而灵活的。笔者曾在《文学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一文中归纳了平民非虚构作品的文体类型,有自传体、绘画体、散文体、小说体、报告文学体、社会调查等多种类型。这里不再一一详述。在这些文体类型中,绘画体平民非虚构作品最多,最“接地气”,我们这里称之为图文互涉文体。
2.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育质量,以合理的教学计划和课程的调整是不够的。由于改革形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为每个学科体系内容陈旧的观念带来冲击。教学内容要更新,本学科的新理论和新的研究结果反映了教材和教学内容。所以他们能站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了解学科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使得创新成果。
图文互涉类平民非虚构作品都是图文并茂的,视觉形象与文字表述相得益彰。形象直观的照片或图画与质朴、通俗的语言相映衬,显示了平民非虚构作品的生动性与灵动性,为受众喜闻乐见。这类作品的体例大致有三种:一是文字与珍贵的历史照片相映衬。如张泽石的《我的朝鲜战争》、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马宏杰的《西部招妻》《最后的耍猴人》等。马宏杰是摄影师,《最后的耍猴人》是他用了12年的时间跟踪拍摄的河南新野耍猴人的故事,不仅留下了最后的耍猴人的许多珍贵照片,也记录了我国耍猴历史的兴衰,是一部耍猴人的史诗。
二是文字与手绘画相映衬。如秦秀英的《胡麻的天空》、关庚的《我的上世纪》、沈博爱的《蹉跎坡旧事》、饶平如的《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等。饶平如在妻子毛美棠去世后,手绘了18册画作回忆他们美好的爱情与婚姻生活,同时配上自创或改写的一些诗词文字,这部充满深情的作品令人感动。
三是文字与漫画相映衬。如丁午的《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李昆武的自传体长篇漫画《从小李到老李:一个中国人的一生》等。后者是漫画家李昆武的作品,作品分“多难”“转折”“兴邦”三册,书写了一个家庭在“大跃进”“文革”前后与改革开放等大历史背景下的兴衰,堪称一部“平民史诗”。
这类作品形象直观,照片与图画犹如锦上添花、画龙点睛,使文字更易于理解。也有的平民非虚构作品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如丁午的《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因为这是作者下放期间写给8岁女儿的信,为了让识字不多的女儿能够看懂信的内容,漫画家丁午的信主要以漫画为主,而文字则言简意赅,通过白描的手法叙述漫画的内容,语言幽默,富有童趣、童真,文字是对漫画最好的补充,两者配合能达到令人过目不忘的效果,更具感染力。
这些图文并茂的作品能将纷繁复杂的故事形象直观地展示出来,真实生动,有别具一格的观赏价值,可以说一图胜千言。作品中的照片或图画都能敏锐地抓取事物的特征或细节,给予受众强烈的视觉冲击,满足了受众的娱乐式阅读需求,能激发受众的阅读兴趣,加深其印象,赢得受众的共鸣与认同,更易于为受众接受。这一点已被评论者所认可,“生活图像化状况见于新世纪文学写作,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文学写作对于生活图像化的随顺,并在随顺中形成比上世纪末更为突出的图像化写作的特点”②。
的确,在当今这个读图的时代,插图本平民非虚构作品的出版与流行也是新媒体时代阅读图像化的体现,读者追求的是视觉快感,是阅读的形象与轻松。一些读者打开一本书,可能更喜欢从图片看起。有的没有时间或耐心读长篇幅的图书,一目了然的照片或图画更易于为读者接受,而且能较快地让受众进入情境,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当然,这种文体因为穿插了大量的照片、图片、绘画作品,某种程度上也打断了文字的连贯性,使内容显得零散,故事情节之间的联系被弱化。但是因为这些照片或图画直观、传神,文字通俗、生动,更能唤起受众的记忆,使受众不厌倦。
三、题材“接地气”
平民非虚构作品书写的题材都是接地气的,有生活质感,与平民百姓的历史与生活息息相关。作品不再把目光聚焦在英雄、伟人身上,而是呈现平民历史与现实生活的细节。主人公都是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普通、平常,就像邻家的爷爷奶奶或兄弟姐妹,让受众感到亲切。写作者与受众是平等的关系,没有居高临下。他们就是原汁原味地复原生活,不追求“高大全”,也不追求理性说教,真正做到了原生态地展现底层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就是“接地气”的作品。前者是作者行走在故乡梁庄的每一寸土地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她深入其中,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记录下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后者则是作者沿着梁庄人走出去的路去探寻梁庄人漂泊异乡的踪迹。作者历时两年时间,历经十多个省市,深入走访了三百四十多位在外务工的梁庄人,最后以51位梁庄人的典型经历勾勒出了当代农民命运的浩大画卷。梁鸿以务实的介入向受众再现了史诗般的人间的悲欢离合,其对民生的关切之情与对人性的深刻反思极具感染力。孟繁华曾说:“在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时代,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及命运,从而使文学再度得到民众的信任和关心。”③梁鸿就是这样一位具有责任感的学者,其两部作品的问世源于作者对故乡及故乡人的拳拳深情,是一个学者强烈的责任感促使她从精英写作转向务实的大众化写作。她在为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和农民工代言,为他们书写了真实得近乎残酷的生存寓言。试看《出梁庄记》中的一段文字:
11点左右,我们坐上出租车,到虎子那儿去。虎子住在金花路那一片的一个拆迁村里。虎子早就站在路口等我们。看见我们,一蹦一跳地要过路这边给我们开车门,被二哥骂了回去。村头是一条长长窄窄的石板小路,下面排水沟的味道时时冲上来,非常难闻。向右转,一个狭长的石板小道,宽不到三米,长却有一两百米。小道中间停着一辆三轮车,一边紧靠着墙,另一边还剩下窄窄的小缝,只是一个人的宽度。这是虎子的拉菜车。走过车,路似乎越来越窄。路的中间立着一些长长的钢管,直伸到二楼,支撑着二楼往外延伸的那些房间的地板。在这些林立的钢管下面,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拿黑黑亮亮的眼睛看着我们。
她左边是一个简易的三合板钉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黑色小锅、作业本和文具盒,旁边散落着几个薄薄的木制简易小凳。右边,楼梯的墙体石灰完全脱落,露出一种充满油腻感的黑色。她的后面是封死了的小路,尽头被一个高大的土堆严实实地堵着,几乎和这二层的楼房一样高。阳光从一线天的上方洒下来,单薄、稀少,在小女孩儿身后形成模糊的亮光,而在小女孩的前面有重重的阴影。高大、阴沉的夹缝中,这个眼睛黑亮、茫然的小女孩坐在那里,像一个孤独的、流落人间的小天使。④
这就是“接地气”的书写。我们通过梁鸿的眼睛看到了身处社会底层的梁庄农民工生活的穷苦与艰难、挣扎与困惑。然而生活的穷困还在其次,他们要面对的还有城管的驱逐、协警的追赶,生存尊严的缺失才是他们内心深处真正的痛。梁鸿走出学者的书斋,深入到尘世之中,抚摸底层民众的疾苦,关注农民的辛酸,代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务实的民间话语立场,更贴近底层民众的审美视野与文化期待,为非虚构写作开辟了一个独特的新领域。平民非虚构作品以其“在场”的方式激起了民众的阅读热情,正是这种“接地气”使文本产生了社会轰动效应。
四、传播“接地气”
新媒体时代的平民史写作的传播方式注定与传统文学的传播方式有所不同。在新媒体时代,平民非虚构作品的传播媒介也更“接地气”,网络、手机、电视等媒体都可以更便捷、更开放地发表并传播作品,尤其是网络博客、微博、微信,这些新媒介使读者与作者、文本之间的互动沟通更为便捷。许多平民非虚构作品都是先在博客上发表,引起了网友的好评,才吸引了杂志与出版社编辑的关注,发表了纸质版作品。
如赖施娟写《活路》时,就是先在网上开通了博客,在博客上记录个人与家族的变迁,因有网友的参与互动,激励她不断写下去,最后结集成书。纸质版的《活路》在每一节后面都附上了“网友评论”,把博客上作者与读者间的互动搬到了纸面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再如饶平如写《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时,是先把每个故事画成图,有一天把一张画给孙女看,孙女拍下来传给了一位同事,这位同事就把它传网上了。于是,引起了大家关注,被各种媒体采访。姜淑梅的作品最初是被其女儿发到自己的博客上,引起读者的好评和出版社编辑的关注,书出版后,获得全国多家刊物和电台的采访报道。网络给平民非虚构写作者提供了自由发表的平台,也使他们的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
赖施娟的女儿在《活路》序言中写道:“与传统传记写作还有更大不同的是:我们建议保持博客上的互动形式,即以传主的个人史写作为主文本,读者评论文本成为传记的副文本,在二者的互动中,主文本为叙事中轴,副文本表现出对主文本的多重理解,有利于主文本向纵深延伸,更大程度地表现出历史的可靠性。在这样的设想和实践中,我们将得到阅读传统传记所没有的收获:有同样经历的读者提供的新史料,进一步完善写作者的认识、思路与想法;通过博客平台,我们还找到了不少历史线索和失去联系的亲友。由此可以说,这种依靠现代技术的个人史写作,不仅是废除等级观念的新观念之下的写作,而且是建立在作者与读者沟通基础上的个人史写作,它将提供更多真实的历史与文学新资料。”⑤这里提到的“‘主文本’与‘副文本’交相延展”就很恰当地体现了新媒体时代平民非虚构作品写作模式的独特性,受众可以参与作者的创作,作者会受到读者意见的影响,作品在传播中就有不断被丰富或被改写的可能性,从中可以看出平民非虚构作品创作方式与传播方式的确发生了变化。
可见,新媒体时代是平民写作的狂欢时代,文学不再是作家的专利,它可以被每一个人用来娱乐消遣、自我表达。不仅人们的创作方式发生了改变,阅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读者与作者可以零距离接触。正是在这样文学创作与传播都“接地气”的时代,平民非虚构写作才有它的发展空间。
总之,平民非虚构写作是富有生命力的“接地气”的写作,它采用平民视角,由平民写史,与专业作家的创作有本质的差别。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但最丰富的文化资源来自民间,希望有更多的平民写作者能借助新媒体时代创作与发表的便捷优势,参与到非虚构写作中来,写出更优秀的非虚构作品。
①[美]约翰·霍格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M],仲大军、周友皋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②王纯菲《新世纪文学的图像化写作与文学的越界》[J],《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第82页。
③孟繁华《非虚构文学:走进当下中国社会的深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2日。
④梁鸿《出梁庄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⑤赖施娟《活路》序[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基金项目: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学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编号:14YJA751019)成果]
作者单位:(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