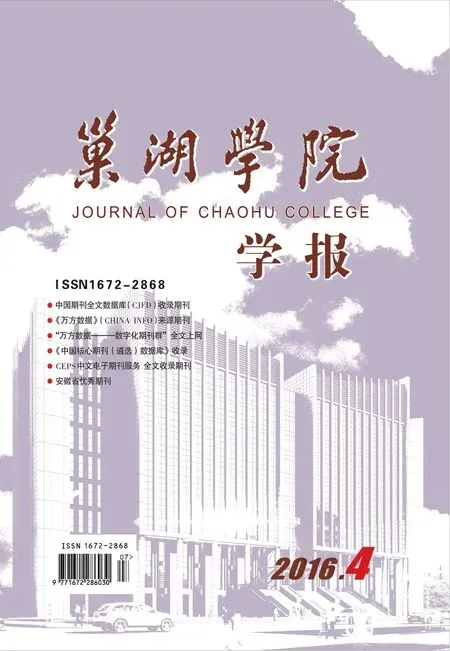巢湖放王岗一号汉墓主人吕柯即扬州刺史柯
陈立柱
(1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1)(2 安徽省淮河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00)
巢湖放王岗一号汉墓主人吕柯即扬州刺史柯
陈立柱1,2
(1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州510631)
(2安徽省淮河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合肥230000)
巢湖放王岗一号汉墓主人吕柯何许人也?文献没有明确记载。综合墓葬级别、埋葬时间与墓内文物,可知他即是启奏海昏侯刘贺与地方官吏“交通”而使其削户三千、不久死去的扬州刺史柯,人名相同,时代接近,级别相当。扬州刺史治所东汉时在九江郡历阳县地,西汉时期扬州刺史治所当亦近于此,即今巢湖市所在。
吕柯之印;扬州刺史柯;墓葬时代与级别
放王岗汉墓位于巢湖市东郊约2公里亚父村境内的放王岗上,旧传为“商汤放桀处”。岗呈南北走向,山势不高,起伏连绵数公里。岗上原有五六座大墓冢,自北向南一字展开,旧志称其中一座为桀王墓,一座为亚父墓,其余无名。1996年发掘编号为一号墓的汉墓即在岗上,称为放王岗一号汉墓,墓主人留下“吕柯之印”的印章。墓葬资料与后来发掘的北山头一号墓、二号墓资料合编为一书《巢湖汉墓》(以下简称《报告》),于200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为研究汉代环巢湖地区历史文化提供了方便。放王岗一号墓主人吕柯,《报告》编者推测 “当是西汉中期该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令长)或富甲一方的大商贾”[1],现在看来不可取。综合墓葬资料与当时历史记载,我们推定该墓的主人是汉宣帝时期的扬州刺史名柯者,他曾启奏海昏侯刘贺与地方故吏“交通”,使其遭受“削户三千”的惩罚,不久死去。
1 墓冢时代
发掘者根据出土物判定该墓年代“当在汉武帝元狩五年以后的数年中,最晚不会超出昭帝时期,即公元前118年至前74年,即西汉中期较为适宜。”[1]我们觉得未免有些拘泥。一方面,说在昭帝之前没有什么确定的根据。另一方面,武帝时代的制度风格一直影响到西汉中后期,所谓“汉武故事”在昭、宣、元、成帝时代都是遵守的,不能因为五铢钱而一定判定其当武、昭时代,除非知道此五铢钱为某一年月制定的,而五铢钱一直行用到东汉末期。根据墓葬与出土物,该墓大体定在西汉中期稍后一段时间较合适。
其一,放王岗汉墓原有高大的土堆,发现时被平整土地施工大部削去,仅墓坑东部保留有厚10—15厘米的一层红壤土,是与墓坑封土的隔层。墓坑为长方形斗坑,四壁近垂直状,整个墓坑挖在砾石层中,故四壁不甚平整。墓坑口东西长9.2米,南北宽7米,坑底长8.88米,宽6.8米,坑深4.19米。在墓坑的西壁正中有一条长斜坡式的墓道,上口残长5.8米(实际长度为7.4米),宽度为2.66米。为长方形土坑竖穴,一端附有一条长斜坡式墓道,有内外椁、内外棺即四重棺椁,这些都有楚国晚期墓葬的特点。但椁周先填木炭屑,再塞白膏泥的做法则是汉代中期以后才有的。还有,墓道下端直达墓坑底,仅与外椁底板上层面齐平,这在战国西汉前期很少见,但在西汉中后期墓葬中经常有发现。
其二,该墓出土一件陶灶,是厨房与灶体的合成物,长方形底座,正面设有两个圆形火门,灶台面有四个火眼,每个火眼上置一个罐型小陶釜。左右两侧山墙与后壁齐平,一侧山墙开有一个长方形窗户,后墙留有一圆形排气孔,其上盖有四面坡式屋顶,屋脊与正侧面坡之间以瓦楞分隔,屋面四边均有数行瓦垄。虽是手制,整体较为精细,形象生动,发掘者认为可以“为界定墓葬年代的标准器。”[1]与西汉早期刚开始出现的陶灶相比,此灶属于成熟型的陪葬明器,应当也是西汉中期以后的情况。
其三,该墓出土20枚五铢钱,而五铢钱是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开始铸造的,以后长期铸造与使用。所以该墓只能是武帝以后的。
其四,该墓出土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齐全,绝大多数保存完好,但铸造较为粗糙,几乎没有纹饰,“标志独特铸造工艺的重器未见。”[1]墓葬组合为鼎、壶、钫、甗、盆、洗、鋗、熏炉等。物品多而且组合齐全,也是西汉中期开始有的墓葬特点。
铜镜共出土四件,有“日光”镜、“昭明”镜各两面,内区铭文“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外区“内清质惟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而愿忠,然不泄”。另一铭文:内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外区有21字:“内清质以昭明,光之象夫日月,心忽扬,然雍塞而不泄”。有“日光”、“昭明”铭文的汉式镜一般认为流行于西汉中期及稍后,说明此墓不会早到前期,判断为汉代中后期较为在理。海昏侯墓出土的一枚铜镜形状、纹饰几乎与之完全相同[2],也说明这一点。
2 该墓为汉代士大夫级别的墓葬
放王岗一号汉墓出土物中有一枚 “吕柯之印”的玉质印章,是墓主身份的重要物证。吕柯何人,发掘报告作者认为于史无考。又根据出土物判定“当是西汉中期该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令长)或富甲一方的大商贾。”[1]如此判定是认为该地区为居鄛县所在,县一级别最高长官只能是县令长。而墓中有不少在作者看来是“僭越”的情况,主要是随葬物的数量惊人等,远远超过阜阳发现的汝阴侯汉墓,而与长丰发现的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相若。我们认为说是官吏应该没有问题,但其它方面还是需要再研究的。
首先,汉代巢湖市是居鄛、历阳与阜陵三县交界地带,不同时期所属当有所不同,不可肯定居鄛县城就在这里。大家都知道居鄛县城后沉入湖底(详下),说明这一判断是有问题的。
其次,该墓出土物虽然不少(3000余件),但精美尤其是上层贵族诸侯王等用物未见,与不远处的北山头一号汉墓即刘安母亲墓[3]相比,随葬物层次要低很多。墓冢出土物最多的是铜器2552件,其中箭镞就有2421件。其余铜器主要为墓主人生活用具,如炊煮器、盛储器、兵器、饰件等,即绝大多数为墓主人生前生活用具。其次为漆器,漆木器较多,占出土物的二分之一强,仅漆耳杯一类就有255件,有纹饰,绘画风格近于写实。可以看出,出土物品虽然丰富,但都是生活用器,不是上层喜好的奢侈品。两耳杯底部有用刀刻划文字,其一为“吕”,另一为“大吕”,说明为吕姓家族所有物。
再次,综合看墓主人应是一位曾经沙场的战士。墓中共出土剑三把,其中铜剑两把,放在边厢;铁剑一把,置于内棺,出土时在腰至两腿间,说明当是主人曾经用物,很是珍贵。铁剑出土时锈甚,两处已断裂,尖峰,两刃较锋利,漆鞘中段一侧饰有玉璏,表面浅浮雕一龙,龙曲颈回盼,两角翘起,身呈“S”状,卷尾,与海昏侯墓出土的玉质剑璏,形状、结构完全一样,只是纹饰作子母虎形。汉代用玉作剑饰很常见,但多为螭虎形,雕琢成龙纹的很少见。因此推测该剑很有可能是墓主人战场获胜,受到皇家赏赐而有,是以觉得宝贵,陪葬时置于身侧。铜剑贵气,平常随身佩带较多,铁剑锋利,一般多是战争用物。另外,大量铜箭镞、盾牌、马俑马具、骆驼席镇等说明,墓主人年轻时当是一位征战沙场、立过战功的军人。有的学者就认为放王岗一号汉墓文物与北方草原地带存在文化联系[4]。如果墓主曾在北方沙场征战,带回有关战利品并葬于墓中,这一切就都好理解了。汉代有军功则有爵位,累积多了就有资格成为官吏、士大夫。吕柯当是一位因军功而成为士大夫的人。这从墓中用鼎、棺椁等情况也可以看出。
放王岗一号墓共出土铜鼎八件,《报告》分为三型,其中A型两件,模铸,胎质厚重,子母敛口,磨损严重,显然是长期使用过的。C型一件,腹部无凸棱和炫纹,底部有一层因长期使用留下厚厚的烟熏。B型五件,型制基本相同,器型较小,敛口,平沿,长方形附耳,深弧度,圜底,是汉代常见的类型。可以看出A、C型时代明显偏早,B型是新铸造的。所以发掘者认为,“按照战国以来的用鼎制度,该墓实际用五鼎,墓主的身份应相当于大夫级。”[1]周代以来的用鼎制度,大体上是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本墓正是大夫级别的用鼎。有研究指出:“铜质九鼎之数虽反映一定的等级身份,但已经不是汉代区分帝、王、侯等级的核心要素。”[5]还有,本墓中四重棺椁,依《荀子·礼论》言:“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二重。”本墓四重棺椁,不合周制,但也不越制,介于诸侯与大夫之间,考虑汉代视死如生,重视阴间生活,尤其讲究棺厚椁重,则四重棺椁也是士大夫常见的配制。
墓中出土玉器总共有18件,比例偏少,反映时代特征不明显,有蝉形口含、虎形佩等,与满城汉墓、南越王墓出土配饰多以透雕龙、凤纹饰不一样,虎形配饰当是大夫级别配件的标配,以其雕刻手法较为成熟看,说是西汉中后期的也较合适。
3 墓主人吕柯即扬州刺史柯
《报告》推测该墓主人“当是西汉中期该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令长)或富甲一方的大商贾。”(《报告》第146页)但是县令长级别低,江淮地区除了寿春、舒县外,几乎都是小县,三至五百石级别的小官,不可能达到该墓主人的级别。至于说是僭越制度的富商,则没有提出什么证据。根据玉质印章“吕柯之印”、墓葬级别与时代特征等方面,我们推断他是西汉中期偏后昭宣时期的扬州刺史名柯者。
首先,两个人的名字完全一致,都叫柯。
扬州刺史柯之名,见于《汉书·武五子传》:
数年,扬州刺史柯奏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万世问贺:“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贺曰:“然。失之。”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验,请逮捕。制曰:“削户三千。”后薨。
这是汉废帝、海昏侯刘贺传的一段。当时刘贺已迁到豫章郡作海昏侯,扬州刺史柯巡行扬州诸郡,了解刘贺与前太守卒史孙万世有来往,彼此对话显示刘贺对于当年被废仍有余念,这是当今皇帝最为忌讳的,刺史职责正是查问郡国诸侯王与郡守的(详下)。了解了刘贺的情况,上奏朝廷,查验坐实,刘贺因此被朝廷削户三千,不久死去。因为刘贺,我们才知道刺史柯的情况。柯之名与吕柯之柯完全一样。颜师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刺史姓何没有写明,但名为柯则清楚。同一时代有两个名字完全一样且担任士大夫级别的官吏,在扬州任职,虽然说不可排除,但几率很小也是明显的。
其次,两人生活的时代、级别相当。
吕柯的时代在汉武帝以后、昭宣帝时期,上文已讨论。扬州刺史柯在宣帝(公元前73—49年在位)时奏事,自然是这个时期的人。刺史柯在扬州范围巡视,九江郡、豫章郡等都在巡视之列,刺史柯以后是否升职,我们不知,级别最低也达到了刺史的职位。关于西汉时期的刺史,研究者较多,综合来看其职责,颜师古注有明载:
《汉官典职仪》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涉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执,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6]
刺史主要是巡行郡国,以六条奏事,特别是郡守与诸侯王的情况,“省察治状,黜涉能否,断治冤狱”。所以刺史柯能启奏海昏侯的行状。《汉书·百官公卿表》对于刺史的情况也有叙述,“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刺史最初是一个级别不高、俸禄有限的巡查官,但位低权重,专门省察二千石的郡守与高层贵族诸侯王,对其不当行为进行纠察。所以后来很快上升为二千石的高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介绍百官时,刺史的位置排在所有地方官员之首,包括郡守之前,也说明其重要。在武帝至宣帝时期,刺史的级别与重要性的变化,可以几任西汉时期扬州刺史的情况进行考察。
一是《魏相传》:
复有诏守茂陵令,迁扬州刺史。考案郡国守相,多所贬退。相与丙吉相善,时吉为光禄大夫,与相书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愿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为霁威严。居部二岁,征为谏大夫,复为河南太守……
二是《黄霸传》:
上擢霸为扬州刺史。三岁,宣帝下诏曰:“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章有德。”……
三是《何武传》:
久之,太仆王音举武贤良方正,征对策,拜为谏大夫,迁扬州刺史。所举奏二千石长吏必先露章,服罪者为亏除,免之而已;不服,极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圣,《礼经》号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武为刺史,行部隶囚徒,有所举以属郡。圣曰:“后进生何知,乃欲乱人治!”皆无所决。武使从事廉得其罪,圣惧,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群盗,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后,圣惭服。武每奏事至京师,圣未尝不造门谢恩。……
这几任扬州刺史都在刺史柯前后,魏相稍早,从大县茂陵县令直升河南太守,因事去职,后复为茂陵令,迁扬州刺史,宣帝时官至大司农、丞相。黄霸宣帝时人,经历与魏相近,先为颍川太守,后下狱,出,通过举贤良而成为扬州刺史,以后也官至丞相。何武亦宣帝时人而年岁稍小,为扬州刺史在宣帝时,与刺史柯同。三任扬州刺史,任职前都曾做过大县的县令,魏相、黄霸甚至做过郡守。谏大夫初为八百石官员,武帝后期以后又有变迁,但在一千石以上没问题①《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何武自谏大夫迁为扬州刺史,魏相则自扬州刺史征为谏大夫,说明宣帝时期扬州刺史与谏大夫的级别相当,可以互换。黄霸由扬州刺史直接升为名郡颍川太守,也说明扬州刺史之重要,是大夫级别的官吏。刺史最初为六百石,后当在八百石至二千石之间,是以成帝时才能升为二千石,当然是大夫级别。刺史随时可以升职至二千石的郡守,主要因为权重。刺史柯后来是否升职不知道,但刺史本身已是士大夫级别了没有问题。如此,则扬州刺史柯与放王岗墓主人吕柯级别相近没有问题。
再次,扬州刺史驻地在九江郡历阳县,地近于今巢湖市,柯死葬其地可能性很大。
《后汉书·郡国志四》:“历阳,侯国,刺史治。”后汉时期扬州刺史治所办公之地在历阳县。西汉时期扬州刺史住地情况,过去学者间意见不一,有人认为没有固定住所,也有人认为有。既然东汉在历阳县设置治所,想必不是平白无故,而是西汉时期很多时候扬州刺史曾在此办公,形成惯例。历阳处在中原前往吴郡、会稽郡等扬州东南部的交通要道上,此条道路春秋时期由吴国开辟,成为中原通往东南扬州的重要通道,汉代司马迁壮行天下,经江淮至会稽走的也是这条路,在此设立扬州刺史治所,本在情理之中。那么,巢湖市在当时是否历阳县的地方?
根据我们对于西汉时期这一带情况的了解,今巢湖市处在汉阜陵县、历阳县与居鄛县的交界地带,曾经属于历阳县是不会有问题的。以下做简要讨论。
首先可以根据范增的籍贯来判断。《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说“居巢人范增”,《史记索隐》引汉荀悦《汉纪》则谓之“阜陵人也”,而《水经·泗水注》又谓范增“历阳人”。我们知道项羽大封天下诸侯时,一般都是封在自己的家乡,只有少数如刘邦者例外。如英布封为九江王,即是在自己的家乡六安(时称六)。范增封为历阳侯,历阳当即是他的家乡,后来一般认为他是巢县(今巢湖市)人,这里当为历阳与阜陵、居巢三县接界的地方。这一带不同时期可能曾分别隶属于三县,我们知道古今县境调整是经常的,是以范增会有为三县人的说法。汉代,历阳、阜陵县原县城都曾沉入湖底,中间迁地别建,县地自当有所变动。《淮南子·淑真训》言:“夫历阳之都,一夕反而为湖。”历阳县城西汉前期以前曾沉入湖底,过去有人认为在汉文帝时期,以后易地新建,可能即后来的今和县城所在地。《晋书·地理志》阜陵县条自注:“汉明帝时沦为麻湖”,说明阜陵县在东汉以后也曾别建过。至于居巢县沉入湖底事,东晋以来更是盛传不衰,“借问邑人沉水事,已知秦汉几千年。”巢湖流域属于地震频发地带,即“郯庐地震带”上,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文献记载这一带地震、地陷的情况,据《后汉书》《论衡》等记载,东汉时有人在巢湖里捡到盛满金子的酒罇等物件,今巢湖市城市风景小区建设时发现汉代墓葬,考古学者在墓棺底部的铺砖中部发现有明显隆起现象[7],这些无疑都是地震地陷才会有的现象。既然沉入湖底迁地别建,辖地就会有变化,尤其是边地。总之,今巢湖市在汉阜陵、历阳与居巢县之间不会有大问题,而居巢县城则在今姥山岛附近,今巢湖市以西,后沉入湖底(具体情况我们另有专文讨论),其东边、南边与阜陵、历阳正接界也。
还有,距放王岗墓不远的北山头一号墓,据我们研究正是刘安母亲的墓葬,这里一度还是阜陵县地。据《史记》《汉书》本传记载,刘安六岁的时候曾随父亲刘长流往蜀郡,刘长半道而死,刘安等也未至蜀郡。后汉文帝因为怕别人闲话,以及对于刘长之死愧疚,封刘安兄弟四人为侯,其中刘安封阜陵侯,时年七八岁。刘安在阜陵县为侯八年,渡过青少年时代,在这里接受母亲、师傅等的教育熏陶,所以后来才能成为当世无比的大学问家,与其父“不好学问大道,触情忘行”[8]决然不同。这一切当是母亲教导之功。十六岁时刘安改封淮南王,迁寿春,阜陵县成为其王国的一部分。北山头一号汉墓主人即“曲阳君胤”,当是汉文帝封赐给刘安母亲的,即是刘安母亲死后埋葬之地。简单一点说:巢湖北山头一号墓主人“曲阳君胤”为一50多岁女性,墓冢出土物品高贵奢华,埋葬时间在汉武帝继位之前,综合看墓主人与汉皇室有密切之关系,生活在淮南国境内,死后葬于阜陵国(县)即今巢湖市境内,得到过很多皇室馈赠之物,家族与诸侯王之间经常有往来,符合这一身份且生活于文景时期淮南国内的女性人物,淮南王刘安母亲之外没有第二人了。因为刘长后期“侯邑之在其国者,毕徙之他所”[9],即淮南国境内没有其他侯邑了。曲阳县在淮南国内,封赐给刘母当是汉文帝为补偿刘长一家而作的顺水人情。墓冢所在的地方乃刘安封为阜陵侯(八岁起)的侯国边地,刘母在侯国生活八年,教养刘安使其成长为饱学之士。刘安为淮南王(住寿春)间,母子之间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如刘安老想为父报仇,又与吴王刘濞往来)产生裂隙,母亲怀恋过去回到原阜陵国居住,并死葬其地。
由上,今巢湖市一带西汉中后期曾是扬州刺史治所所在、历阳县地,启奏海昏侯的扬州刺史柯即在此办公,后来葬于此地,即放王岗一号汉墓,留下“吕柯之印”。
刺史吕柯在此办公,死后也葬于此,是否也家于此地?书缺有间,不能详论。古人死后一般葬回本土,所谓叶落归根,但是在汉代不同的情况也是很多。如居鄛刘氏,死后葬于成德县,即今寿县与长丰交界的三义集,民国时期被发现,留下《居鄛刘君墓镇石记》等文字[10]。他是居鄛人,死后葬于成德县地,也许是觉得风水好,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在此为官。还有,曹操,官至魏王,死后葬于邺城以西的西高穴[11]。这些都不是葬回乡梓的。吕柯葬于此地之因缘,与其在此为官可能性很大,此地风水也好,至于具体情况则需要以后再研究了。

厨房与陶灶

放王岗墓铁剑玉剑格

铁剑玉璏

放王岗一号汉墓墓室结构图

放王岗一号汉墓发现“吕柯之印”章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巢湖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46、146、144、144、146、24、146.
[2]“南昌海昏侯墓发掘暨秦汉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C].南昌,2016:12-19.
[3]陈立柱.巢湖北山头一号汉墓主人只可能是刘安母亲[M]//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文物研究:第2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214-221.
[4]余雯晶.巢湖汉墓骆驼型席镇与凸瓣纹银盒初探[M]//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文物研究:第20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57-69.
[5]韩国河.侯制与“王气”——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葬的特征[N].光明日报,2016-02-06.
[6]颜师古,注.汉书:百官公卿表[M].北京:中华书局,1962:741-742.
[7]钱玉春.巢湖文明的记忆[M].合肥:黄山书社,2012:15-16.
[8]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138.
[9]贾谊.新书:淮难[M]//上海图书馆,等,编.贾谊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79.
[10]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三[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2034-2036.
[11]陈寿.三国志:魏志:魏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42-44.
责任编辑:杨松水
K878.8
A
1672-2868(2016)04-0001-06
2016-05-18
陈立柱(1963-),男,安徽灵壁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安徽省淮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先秦史及区域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