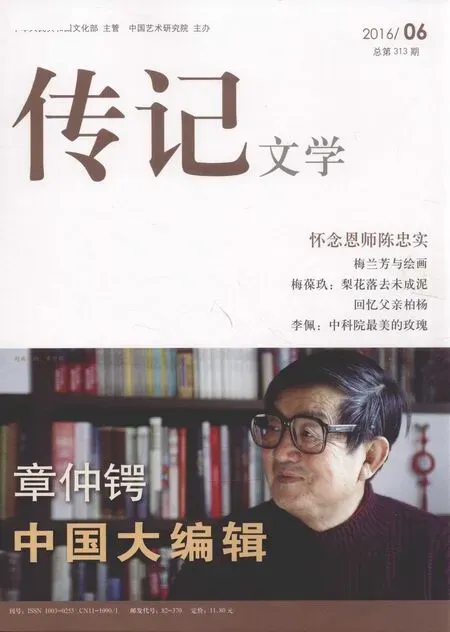苦魂三部曲:鲁迅传 (选章六)
文 张梦阳
苦魂三部曲:鲁迅传 (选章六)
文张梦阳

第十八章 鲁迅之死(下)
哭别
这时,小海婴还在三楼睡觉。1936年的大半年,他的日子也是在忧喜交错之中度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海婴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因为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更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声,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父亲的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海婴每天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他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眠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海婴自知对父亲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笑容,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黑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父亲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悄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更不敢大声叫嚷,像过去那样每出门时总要说:“爸爸再见。”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是故意不说,海婴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比什么奖赏都贵重的语言,海婴心里感到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父亲和母亲相视一笑,借此使全家人暂离愁城。
父亲的印章,现存49枚。有名章、号章及笔名章,还存有判别古籍真伪的“完”、“伪”、“善”、“翻”的单字章和“莽原社”等社团章。以石质居多,还有水晶、牙质和玉质者。外形或圆或方经过磨制者,也兼有不加磨制保持自然形态者。有一枚,上刻“只有梅花是知己”,石质,没有边款。有一枚白色木质图章。式样极其普通,呈长方形,刻有阳文“生病”二字,字体正方,刀力平平,质地一般,并非精选,刻工无名,也非名家。这块“生病”图章,海婴那时倒是常常使用的。当年上海虹口大陆新村一楼客室的里间,有一张他们一家平时吃饭的八仙桌,桌上有四只小抽屉,这只图章,就放在朝南方向、大门方位的那只抽屉中,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小圆匣印泥。海婴经常拿这只图章在纸上盖着玩,弄得手指油腻腻地尽是腥红色,这只图章也被他弄得遍身印泥,满是朱砂。30年代的上海,邮递员送信往往爱投后门,因为弄堂房子的结构,厨房紧接在后门旁边,这样,信件送到时,住户经常有人接应,可省等候时间,而前门却往往难以叫应。当时,邮递员骑自行车,技术都很高超,在弄堂里,不用下车,车速稍一减慢,扬手一掷,信件就能投入窗户以内,然后飞车就走,毫不延误。如果是挂号邮件,就得停车取章。那时挂号信件又分单挂和双挂两种。单挂号盖章后,就算收件人向邮局负责;双挂号则还有一纸回执,需要回递寄件人。这一枚“生病”图章,是父亲在逝世之前的那一年请人刻制的。当时,他已病得很重,不能像过去那样,有信必复,有稿必看了。接到信件,不愿拖延时日,以免寄信人和寄稿人牵挂,所以想出此法,在回执条上盖上“生病”二字的图章,使寄件人见此回执,就能明白情况,不致再着急催促。这也是父亲对识与不识的朋友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那时,海婴已经6岁多了,有时在楼下玩耍,遇到来信要盖此章时,往往不许旁人插手,不论邮件缓急,抢着完成自以为非常荣耀的任务。后来,很多熟人知道父亲病重,除了问候以外,一般都不愿以事务相烦,但有些人不很了解情况,所以有时偶然也见有送稿件前来请教的,碰到这种情况,母亲估计短期不及阅读,便婉言谢绝,如有持介绍信件送稿者,便在来信后面盖以“生病”二字的图章,取得对方谅解,由送信人带回。
说来也奇怪。前两三天,海婴下午放学回家,突然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他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他非常惊讶,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而这句话却非常清楚地送入他的耳鼓。他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许妈。许妈斥他:“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件事。”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1936年10月19日清晨,海婴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阳光比往常上学的时候亮得多了。他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他起床?连忙穿好衣服。楼梯轻轻响了,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去了!”海婴急促地询问:“弄为撒个能(这是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却强抑泪水,迟缓地对他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多少治疗,多少祝愿,多少人力和物力,都阻挡不住死神的降临。海婴意识到,这么不幸的一天,终于降临了。他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做一次深长的休憩。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着他的手,紧紧地贴住他,生怕再失去什么。他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父亲的床边有一些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似乎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但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不一会,来了一个日本女护士,她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伏下身去耳朵贴着父亲的胸口,听听心脏是否跳动,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左右摇动,上下振动,想用振动方法,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这一切,她做得那么专心,充满着必胜的信念,没有一丝一毫的犹疑。人们也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忽然一下苏醒,睁开那双大家都在期待着的眼睛。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离开他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他“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他的双颊了……止不住的泪水,不由地从海婴眼眶涌出,顺着脸面倾泄而下。他再没有爸爸了,在这茫茫无边的黑暗世界之中,就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人了……
10月18日下午胡风再去看鲁迅时,许广平告诉他,先生昨晚发了病,不能起床了,并叫他暂不要订房子。胡风走进房门口几步望见先生闭着眼静静地躺着,因为假牙取下了,两颊陷了下去。他晓得医生在注射,只好退了出来。
当天夜里,胡风得到冯雪峰电话,要他第二天上午赶到先生那里去。
1936年10月19日大早,胡风被捶门声惊醒了,是许广平打发内山书店一个店员来通知他:“周先生死脱啦!”胡风震惊,马上穿起衣服来,告诉梅志一声,就坐着那个店员开来的汽车赶去了。胡风坐在汽车上感到茫茫然,希望马上开到,看个究竟,同时也想到一定是事实,希望汽车一直开下去。
到了先生家,胡风急步走过客堂,上了楼,轻轻走进卧房,见先生静静地躺在床上,虽然脸型和昨天并没有大改变,但他那双智慧的眼睛已经永远地闭上了。
离床头靠窗是一张半新的旧书桌,上面杂乱地堆着些书籍、原稿,两枝“金不换”毛笔挺立在笔插里,旁边是一只有盖的瓷茶盅。这就是先生不知呕去多少心血的地方,现在显得很纷乱。桌子横头是他最近一篇文章里提到的藤制躺椅,上面多了一条薄棉垫。靠边一张方桌,满满地堆着书;床头床脚各有一架小小的书柜。壁上挂着些木刻和油画,有一张好像是凯绥·珂勒惠支女士的版画,另一张则是油绘的婴孩的画像,上面题着“海婴生后十六日肖像”字样。海婴这先生唯一的爱儿,还不到7岁,这天真的孩子似乎还不懂得人生的忧患……
房里寂静无声,只见鹿地夫妇和鹿地前妻、现在上海当记者的河野坐在卧床对面。胡风不知道鹿地他们已经来过,这时候闪过了一个念头:这是神圣的地方,这是一个最悲痛即最庄严的时间,他们竟然闯了进来坐着……另有两个青年在画着速写并着手塑下最后的面容。他们自己向胡风介绍,是曹白和他的朋友力群。曹白是先生最后倾注着好感,和他通信,在精神上支持了他的青年革命美术家,也就是先生《写于深夜里》的那个“人凡”。他们的出现冲淡了胡风对鹿地们的反感。他们是配得上代表年轻一代纯洁的心灵来为伟大的先驱者的遗容留下最后形象的。
10月19日清晨,黄源一家还在睡梦中,突然被几下轻轻的敲门声惊醒了过来。黄源睁开惺忪的眼睛,一看房间里的光色,知道时候还很早,再看看床前的小钟,也还不到7点。昨夜他们两点后才睡,今天这样早就有人来敲门,莫非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故?黄源有些惊异,于是立刻跳下了床,向门边奔去,一边问道:“谁?”
“是我。”门外应了一声,是听惯了的女佣的声音,接着又轻轻地扭了几下门上的把手。
黄源旋开了门锁,半开着门,问:“什么事?”
“楼下有人要见先生,说是有要紧事。”
这时黄源的妻子许粤华也惊醒了,下了床,走到门边来问道:“是个什么样的人?”
“没有见过的。”
黄源有些犹豫,猜不着来的是谁,有什么事。许粤华随手把晨衣交给了他,说:“你下去看看吧。”
黄源披了衣服,匆匆地跑下楼去。跑到二楼的转弯处,就见楼梯下站着一个穿藏青色学生装的青年。那个人听见了楼梯上急促的脚步声,转过身迎着黄源,但因楼梯下光线暗淡,黄源看不清他的面目。
黄源一跑到楼下,就把他引进客堂。黄源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一时想不起来。黄源也无暇思索,便靠近他身旁,直捷地问道:“有什么事?”
他低着头,哽咽着悲切地说:“鲁迅先生死了!”
一听到这句意外的霹雳似的答语,黄源好像触到了电,全身一震,眼前昏黑,一时失去了一切的感觉,木然站着。
“什么?”过了一下,黄源才定了一定神,吐出了这两个字。青年的话黄源是听清楚了的,而且好像是一把锐利的尖刀,深深地直刺到他的心中,但是他不相信。
“鲁迅先生死了!”青年依然低着头,哽咽着悲切地说。
“什么时候死的?”
“今朝5点多钟。”
黄源见他手里拿一张纸,上面有他的名字和地址,忽然转到另外一个念头,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内山书店。”接着青年催促黄源说:“汽车在外面等,请您赶快,我们一道走吧。”
“不,你先走,我换了衣服马上就来。”另一个念头抓住了黄源,犹豫地说。
“好的,我先走,您马上到他家里。”
青年说着走了,黄源直奔上楼,许粤华在房门口等着他,见他神色异样,急忙问道:“什么事?”
“周先生死了!”
许粤华听到这消息惊跳起来,连声说着:“那怎么行呢?那怎么行呢?”炼颊上是簌簌的热泪,好像一个突然被母亲偷偷地抛下的孩子似的,急得缠住黄源问,跟他进了房间。黄源竭力抑住从胸底溢涌上来的泪水和哭声,告诉她:“我们赶快换衣服走吧,车子打萧军那里转一转,我去叫他。”
不到几分钟车到了萧军住所门口,许粤华留在车里,黄源独自下去,问了一声佣人,知道萧军还在睡觉,便飞奔上楼去,房门没有下锁,黄源一推便冲了进去,见萧军睡在一个大床上,便半俯着身,说:“赶快起来,周先生死了!”
又一个霹雳打击了另一个青年。
“什么?”萧军圆睁着眼睛注视着黄源,那乱蓬蓬的头,立刻离开了枕头撑起身来。
“刚才有人来通知我,说周先生死了!”
“你诓我。”
“我怎么能用这话来诓你,赶快穿衣服,车子在外面等着。”黄源有些焦急了。
两三分钟以后,他们三个人都已坐在车上。车在早晨清寂的马路上急驶着,萧军几次要呕吐。黄源只能安慰他,说:“我不相信,他不会死的。”心里也那么想着,先生病了几月,虽然曾遭过几次险境,可是最近显然在往痊愈的途上走,决不会病死的。他们15号去看他,他的精神不是已经显得好得多了吗?昨天他们去北四川路,因为同着别的朋友,没有到他家里。在内山书店一转,老板内山先生和他们招呼了一下,并没有提到鲁迅先生的病势激变。怎么今天突然会死呢?但也许有什么意外罢,焦急与愤恨的情感在黄源胸中翻腾着,车好像走得非常地慢。
车在弄口停了下来,他们朝先生家的门口走去。这弄堂在这两年来,不知走了多少次,每次进这弄堂,想到立刻可以看见先生,哪怕是心境最恶劣的时候,也会突然变好、安静起来。但这时候却有一个可怕的命运在等着他们。萧军迈开大步在前面走,黄源好像被一颗过重的心拖着似的跟在后面。走进了后门,看见许广平站在楼梯下,她不等他们开口,就简单地说了一句:“在楼上。”
他们往二楼奔去,跑进房门,一眼看见许多人面对着床站着,回头朝床一看,他们便扑在床前,痛哭起来。
海婴紧紧偎在母亲怀里哭泣,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开始有点杂乱,不像刚才那样寂静了。日本牙科医生兼塑像家奥田杏花,赶来为父亲塑像。他先在父亲脸部搽上薄薄的一层凡士林油膏,仔细抹平,然后用现调的湿石膏敷在脸的四周,轻轻抚平,贴上纱布,待石膏凝固,轻轻地揭下模子。当他翻过面模检查质量的时候,海婴也过去望了一眼,看到石膏面模拔下父亲许多根胡子,当时感到很不舒服,仿佛从自己身上拔下许多毛发一样难受。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慢慢增多了,但大家仍动作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海婴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只见一个大汉直奔父亲床前。没有犹疑,没有停歇,没有俗套和应酬,扑到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地号啕大哭。他扑向父亲胸前的时候,一头扎下去,好久没有抬起,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发出了悲痛的呼号,倾诉着对父亲的爱戴之情。海婴看出是萧军,后边跟着的是黄源。这位重于友谊的关东大汉,不几天前,还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替他们分担忧愁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父亲的感情了。海婴不记得这情景持续了多久,也不记得是谁扶萧军起来,劝住了他的哭泣。只是这最后诀别的一幕,在他脑海中凝结,形成了一幅难忘的画面。时光虽然像流水一般逝去,但始终洗不掉这一幕难忘的悲痛场面。
胡风坐在书桌前,听许广平念给他听致送讣告的亲友名单,默默地记录下来。他这时脑子一片空白,毫无主见,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背对着房门口,不知道有谁进来或出去。冯雪峰来了,在先生额上亲了一个吻,马上把他叫到楼下客厅。这才发现孙夫人宋庆龄坐在长桌一边,她是在胡风背对房门口的时候上到房里向遗容吊唁的。胡风坐在和孙夫人相对的长桌一端,冯雪峰坐在他旁边,要他起草一个讣告。胡风激动得不能运思,只是跟着感觉写了起来。当写到“由于肉体的无情的压迫,不管他放心还是不能放心,终于不得不放下他对各种敌人刺击了一生的笔,把它交给了年青的战斗者们”的时候,胡风禁不住全身抖动,好像这才全身心地感到了这颗伟大的心灵的停止跳动,对中国人民、对进步人们会成为怎样一种不可估量的损失。一面听到好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冯雪峰的声音:“不要难过,写罢……”热泪烧得胡风看不清自己写下的字迹了。黄源在一旁默默地流泪,默默地回想着——
先生已闭上眼,安谧地躺在床上,身上盖了一条粉红色棉质夹被,脸上蒙着一张洁白的纱巾。黄源把白纱巾揭去,眼睛就红起来,先生的口眼都紧闭着,一头夹着几根银丝的黑发,浓浓的眉和须,面容虽然瘦一点,却很安祥。黄源抓住他的手,还是暖生生而柔软的,他的眼睛闭着,和熟睡着一般。他该还听到大家的哭声,为何不醒来呢!自从5月15日起病直到10月15日最后一次见面,期间他的病虽时重时轻,但他始终不相信自己会死,大家也不相信他会死,尤其是最近,虽则还有热度,但他的精神显见得很旺盛。他甚至去看过几次电影。双十节,他去上海大戏院看了改名为《复仇艳遇》的普式庚原作的《杜勃洛夫斯基》,当晚写信给黄源:“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普式庚之《复仇艳遇》,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罢。”那几天黄源忙着把《译文》付印,接着萧军又从青岛回来了,没有去看。萧军和他别了两月,回来后急于要去看他,便约他15号同去。
那天带着一个小小的高尔基木雕像,是一个新从日本回来的朋友托转交的。先生拿起雕像,看了一下,回头对他们愉快地说:“雕得不坏,很像。……”
他的爱儿海婴这时拿了一个剖开了的、萧军刚送去的石榴走进房来,许广平跟着照顾。海婴走到书桌的另一端,看到那雕像,就从椅子上爬到书桌上,说道:“这是爸爸……”
“我哪里配……”说着先生便把小像放在靠近身边的桌子上。
“你猜是谁?你知道,高……”许广平站在桌子旁边,抚着海婴说。
“高尔基……高尔基。”海婴伶俐地接着说。
先生直坐在藤椅上,仰着头直望着海婴,听见他说对了,便回头对他们笑着说:“高尔基已被他认识了。”
那天萧军刚从北方回来,谈了一些北方的情形以及沿途的见闻,声音较高。先生声音也跟着提高起来,黄源怕他吃力,默坐着很少讲话,但先生又提起了普式庚。
“《杜勃洛夫斯基》去看过了么?很好。”他问。
“又在做宣传了。”许广平笑着说。
“还没有看过原作,不知他是否完全依据原作。譬如,其中有一场小杜勃洛夫斯基叫村子里的人放火烧死关在他家里的四个官员,普式庚那时有这种想头,自然要被杀死了。”
“我有《杜勃洛夫斯基》的英译本。可惜也没有看过。”黄源说。
在归途上,萧军很愉快地说:“他好得多了。”黄源也承认。
那天晚上,电影看得很满意,回来已快12点钟。萧军坐了一会走后,黄源便捡出那本《杜勃洛夫斯基》的英译本来躺在床上看。一看便不肯放手,这影片也许是为纪念普式庚百年祭而拍摄的,所以与美国拍摄的所谓文艺电影不同,完全保持着原作的本来面目,剧情和原书简直毫无出入,而看了原书更觉得这影片好了,因此一直看到3点钟才睡觉。第二天一醒来再看,看完了才知道只有结尾稍稍不同,他预备下次见面时把这点告诉先生,但是现在却迟了……
先生生平没有什么嗜好,唯一的娱乐,恐怕就要算难得出来去看一二次影片和坐在内山书店里“漫谈”吧。但是这半年来,因了病,不能出门,连这点权利都给剥夺了。而热情依然洋溢着,他不甘寂寞,他不能无所事事地终日终夜躺着。大概是6月初吧,他的病还很重,黄源怕惊扰,不敢上楼去看他,仅在客堂里向许广平问病情。那天凑巧是星期六,过一会周建人也来了,他先上了楼,许广平邀黄源也上楼去。黄源走在前面,许广平陪着。黄源一进房门,先生从藤椅上直坐起来,看见是黄源,立刻沉下脸对许广平说:“是你阻止着不让他上楼吧。我早就听见楼下的声音。”
这时许广平很窘,黄源也很不安,于是立刻解释道:“不,许先生几次邀我上来,我想还是等一下和三先生一同上来。好了一点吧?”
“这几天已好了一点,前几天没有食欲,什么东西都无味,不想吃,只为了想维持精神才勉强吃喝一点。那时真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一没有精力,什么都完了。这几天好一点,躺着胡思乱想,又想写文章,可惜……”他自己觉得病轻了一点,愉快地说。
“不过现在也只能好好养病,把病养好了再说。”黄源想到他终天躺在藤椅上,不断地思索,有些发愁。
到晚饭时,许广平来叫吃饭。先生说:“你们到底下去吃吧。我在楼上吃。”
每到星期六,周建人从商务印书馆出来,便直接到他家里。周建人往往带了孩子先去,每次带一个,三个孩子轮流着。晚上有一餐丰盛的晚餐准备着。黄源在先生病前也常常去,有时要是在饭后不久到他家里,他一定要责问是否“躲避”吃饭。但先生平日自奉甚俭,只备几样菜蔬,一有客来,必须另外叫菜。去年夏天许粤华去日本后,先生知道黄源每天在馆子里零吃,饮食不佳,他就要黄源每星期六去家里。因此黄源有时即使有事,能挨就挨到星期六去。这样习以为常,黄源差不多每星期六分享着先生家里一星期唯一一次的丰富的晚餐。黄源甚至在先生处学会了喝酒。
但最可怀念和感谢的,不仅是这丰盛的食肴,更是先生在座时的任意谈笑。那晚没有先生在座,没有加上那精神上的粮食,虽则依然是同样丰盛的酒肴,却失去了酒肴中的至味。他们草草吃了,便上楼去看先生晚餐。
藤椅前放着一张茶几,几上的盘中盛着几碟小菜、一碗鸡汤。先生直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饭碗,但是吃得很少。他怕和大家在一起吃时禁不住要谈话,以致疲劳,但独自在楼上吃,又觉得索然无味,饭也咽不下去的样子。
“吃得很少。”黄源凄然说道。
“本来吃得不多。”他好像宽慰着黄源似的说,但黄源知道他平时饭虽吃得不多,菜可吃得不少的。如今却小小的几碟小菜还留着大半。
饭后,他依然躺在书桌边藤椅上,黄源坐在书桌前,周建人坐在另一端的书桌边。他有时吸一支纸烟,喝一点茶,许广平拿了水果来,他也吃一点。他觉得疲劳时就闭着眼睛,靠着躺椅养神。黄源和周建人都不敢提出话题,但是他的话却源源而来。许广平担心着坐在一旁。他们也担心着不敢久坐,但又不敢告辞。他在健康时,不过夜半是不放他们走的,并且看见有几个熟人在他面前,他躺着养神时不再思索,脸上露出安宁的神色,也感到几分快慰。
过了9点钟,黄源望望周建人站起来低声说:“我先走吧。”
“我也要走了。”周建人说着也站起来,望望书桌对面的先生。
先生看见他们站起来,说要走了,便又直坐起来,看看藤椅桌边上的夜明闹钟,说:“我不留你们,坐到10点同车去吧。”他的声音满贮着深情,他们又坐了下来。
周建人原先也住在北四川路附近,但这一带“特殊区域”时常不很安静,自从去年冬天又有事情发生后,就搬到法租界去了。搬家后第一个星期六到先生家里,黄源也在,他们谈到半夜。临走时,先生说:“你们都在法租界,可以同车,我不送了。”说着又对许广平说:“你送一送罢。”许广平陪他们走出大门,外面只穿一件绒绳背心。这时夜深人静,外面刮着大风,他们阻止不住她,她独自走在前面,到附近的汽车公司,付了车钱小账,笑着说:“你们同车去吧。”直到他们的车子开出以后,她才被冷风吹着回去。第二个星期六又是一个深夜,临走时许广平拿出一块二角钱塞在周建人的手里,叫他们坐汽车走,说:“对不起,今晚我不送了,请你们付一付。”
周建人推却了一下,先生便低下头,看着地板默声不响了。周建人于是不得不收下来。自后每次临走,许广平一定拿一块二角钱塞在周建人的手里。
黄源每在旁边看着这情景,心中不禁起着阵阵的酸痛。
到6月15日后,先生的病势稍轻。那时照过X光,知道是肺病。
有一天黄源下午去,先生把X光的照片拿给他看,并给他做种种的解释,最后说:“照医生说,看这照片我在五年前就该死了。然而现在却还活着,他便不知如何治法。”
医生大概每天下午4点多来,到4点钟他自己先量一次温度。许广平把温度计交给他时,他每次总对黄源说:“静默三分钟吧。”也有时说,“你们随便谈谈吧。”
黄源在他房里,几次遇见了那位须藤老医生。有一次他听听先生的肺病又用手指敲敲,说:“现在肺部很好,还可以活十年。那时少爷也大了,你太太也不必过分担心了。”
先生听了很高兴,立刻翻译给许广平听。
但是随着病逐渐好起来,先生愈益不肯“安分”了,医生常警告他不要多动,提防疲劳,静静地躺着。先生的答复是:“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最后他甚至向医生说:“我请你医病,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医生问。
“第一,是要把病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一个月可医好,我宁愿动动花两个月医好。第三,假如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
医生当然无话可说了。
那时天气渐渐热起来,他本想七、八、九三个月前往日本去养病,起初想到镰仓,那里须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觉得离东京太近,会浆在新闻记者的绕缠中。后来想到长崎,有一天黄源去,看见书桌上放着两本《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旅行指南书。但在长崎没有熟人,他觉得住旅馆太贵,住“下宿”或租“贷家”又太麻烦。“那时我一天到晚给家里的人当翻译了。”先生说。
“我想告许粤华来帮忙吧,她暑假里在东京反正天热,不该看什么书,有些事情她可帮许先生应付。”黄源说着。想到他的住所太简陋,空气既不好,一有太阳,就直逼到他的房中。他又不喜欢多移动,他的藤椅放在靠窗口,太阳逼进来,人依然躺在那里。
“不,她从东京赶去路太远,过些时再说罢。”先生婉辞拒绝了。
他一生帮助青年,指导青年,把全部的精力献给青年。他每天要分出一二小时的精力给青年复信、看稿,有的青年还要他代办书籍。他平素来往也都是青年。他为青年活着,他也活在青年中间。但他从不以青年领袖自居,从不使唤青年。即使是最接近的友人,他也不愿托付“私事”。有人以为用“捧”用“谄”可以博得先生的欢心,这是对先生的侮辱!
同时也因为热度始终未退,医生不准他远行,整个夏天他就在那蒸笼似的房子里熬着。
他患着不治的肺病,他住在无论精神与肉体都不适于他的病体的地方,但是他还工作,爱他的人,看他工作心痛,但谁能阻止他呢?
有一个酷热的下午,黄源两三点钟时到他家里。一进门就看见先生坐在客堂的书橱旁铺在地上的席子上。他穿了一身短衫裤,显着骨瘦棱棱的四肢,正弯着腰在折叠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许广平坐在旁边抢着折。不久,这部《版画选集》就出版了。
他在病中常常讲起《海上述林》,黄源也常常看见有《海上述林》的校样在他的书桌上。他曾对许广平说:“这书纪念一个朋友,同时也纪念我自己。”10 月8日黄源去,他把一本皮面精装的《海上述林》送给他,他们一同翻着看,他看到底页上有一个皱折,要许广平另换一本。他交给黄源时,微笑着说:“总算出版了。下卷也已校好。年内可出版。这书不能多送,有熟人托你买,可打八折。《译文》上能揩油登个广告么?”17日他知道《译文》上的广告已登出来,那天《海上述林》在内山书店卖去20册,他非常高兴。
听许广平说,他在17日夜里3点钟病势突变,到18日早晨已无力说话,但他到八九点钟还问报有没有来?有没有广告?许广平告诉他《译文》的广告已登出,有他的《死魂灵》,登在第一笄,此外还有些什么文章等等,他听了还不满足,说:“你把报纸同眼镜拿来!”他这样地关心《译文》,他最后看的文字,也是《译文》的广告,关于《海上述林》上卷的介绍。
但他却在19日的清晨5 时25分,悄悄地与他们不别而逝了!
闻讯而来的记者云集在楼下,等候发丧的消息,当务之急是组织治丧委员会。
冯雪峰与宋庆龄、沈均儒等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负责人和许广平等亲属商定治丧委员会名单,起草讣告。当天《大晚报》第二版就刊登出来了:
鲁迅先生讣告
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
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
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A.史沫特莱、沈钧儒、萧参、曹靖华、许季茀、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
治丧委员会还有一份冯雪峰手拟的9人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参。但刊出时,除日本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外,所有的中国报纸都没有刊登毛泽东的名字。
冯雪峰因为中共特派员身份不能出面,不仅没有在治丧委员会列名,整个活动中也退居幕后,代表组织尽他应尽和能尽的力量。
尾声
鲁迅葬礼的第二天,冯雪峰一个人又去看了鲁迅的坟墓。这时,只是一座小小的土堆,在苍茫的天色笼罩下显得无限孤寂。冯雪峰在土堆前默哀,沉思……
第三天,他就因事被派到扬子江上游的某地去,大约过了十天,办完事,坐着民生公司轮船所谓大菜间的舱位回上海,在那里喝茶,见桌子上有一本新出的画报,里面登有鲁迅先生的遗容和出殡盛况的照片,一个国民党小军官在看着。他突然抬起头来对着冯雪峰,好像非要人相信不可似的说:“鲁迅是一个危险分子,他不是共产党,你枪毙我!”然后把那画报推向冯雪峰。听他的口音,像是湖北人。冯雪峰没有怎样去理他,他也没有非要别人回答的意思;但冯雪峰禁不住微笑起来了。冯雪峰觉得,眼前这个军官是不足道的,而他会使人想得更远一些:鲁迅先生不仅生前使敌人害怕,就是死后也还能使敌人害怕,所以冯雪峰微笑了。
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尤其是走路时的姿势和背影又浮现在冯雪峰眼前——不管热天寒天,穿的都是橡皮胶底的黑帆布鞋,走路略带八字步,一步一步非常稳固,好像每一步都先做稳了中国武术上所说的马步那样;同时,他是目不旁观的,更是从不回头顾盼的。的确,他走路的这种坚实的姿势,也是非常性格化的。在他生前,冯雪峰不很注意,在他死后,就常在眼前浮现出来,葬礼后第二天从鲁迅坟墓回来的路上,冯雪峰就仿佛看见这个身材并不高大的人这样地在前面走着;这次坐在轮船上也这么看见。从此,只要想到鲁迅,冯雪峰就感到前面有这么一个背影。冯雪峰相信,只要热爱鲁迅的人,都会看见的,因为这个人总是在我们前面走着,从不回头,每一步都好像先做稳了马步,准备随时和人殴斗似的走着。
是的,凡是死后仍活在人民心上的人,都是人民在前进的路上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背影的人。
1937年1月,时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许寿裳利用寒假南归之机,在许广平、海婴陪同下,到上海万国公墓鲁迅墓地悼念鲁迅。这时,坟堆前竖立了一块梯形水泥墓碑,上面镶有瓷制的鲁迅先生像,下面刻着横写的字体幼稚而工整的“鲁迅先生之墓”6个字,它出自年仅7岁的海婴之手。墓的左侧是许广平亲手种植的一株松柏。
归途中,许寿裳吟成了一首感情至深的悼诗:
身后万民同雪涕,
生前孤剑独冲锋。
丹心浩气终黄土,
长夜凭谁叩晓钟。
许寿裳对身旁的许广平说:“我和鲁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交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关怀,不异于骨肉。他在我的印象中,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乃是三十余年前,他剪掉辫子后的喜悦的表情;最后的而且永远引起我的悲痛的,乃是他去世两个月前,依依惜别之情。三十五年之间,有二十年是晨夕相见的。每次相见,他总是名言百出,机智疾流,使我得到一种愉快的经验,恍如坐在春风之中。这种愉快的经验,追忆起来,实在是举不胜举。”
1937年1月中旬,万国公墓鲁迅墓前来了四个拜墓的人。他们的脸像上海的冬天一样,庄重而晦暗。这四个人是许广平和海婴、萧军和萧红。
萧红从日本一回来,就急匆匆地要去看望鲁迅先生。她踩着枯败的落叶和衰草,走进万国公墓鲁迅墓前,远远便看见墓碑上镶嵌的先生的瓷制半身像,就宛如又见到先生昔日那熟悉的面容。游子归来,亲人已逝。萧红一时难以接受这个冷酷的事实——像祖父一样疼爱自己的人,睡在这冰冷的墓地已逾百日,永远离自己而去。上海早已不是去年离开之前的上海,那时有鲁迅;现在没有鲁迅了,没有鲁迅的上海,还是过去的上海吗?无限往事像放电影一样,在萧红眼前一幕幕闪现,萧红热泪夺眶而出。泪眼朦胧中,看见先生还是那么温和地看着自己,评品着她的衣着服饰,耳畔回响起离开上海前夕,先生设家宴为她饯行时的叮咛:“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她真想在先生坟前痛痛快快大哭一场。
萧红在坟前默默地绕步,看见草地上放着一只花瓶,插着祭拜者的鲜花,有些已经枯萎了。她一眼就认出,这只花瓶曾经放在先生家客厅黑色长桌上,插着四季都不凋零的万年青。她第一次看见它时,好奇地问先生花瓶里是什么植物,先生抽着烟答道:“万年青。”她不解地问:“屋里不生火炉,也不冻死?”先生在升腾的烟雾中回答:“这花,就是‘万年青’,永远这样。”说着,把烟灰弹在花瓶旁的烟灰盒里,烟头像一朵小红花在指间开放、闪烁……
抗战以后,只有许广平绕道去过一次,别人就没有去过。那墓草长得很高了,而且荒了,还说什么花瓶,恐怕鲁迅先生的瓷制半身像也要被荒草埋没到他的胸口。
谁去剪齐墓上的荒草?我们是越走越远,那荒草却是总要记在心上的。
1937年4月23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上,刊登出一首诗,署名“萧红”——
拜墓
跟着别人的脚迹,
我走进了墓地,
又跟着别人的脚迹,
来到了你墓边。
那天是个半阴的天气,
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
我就在你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
只是说一声:久违。
我们踏着墓畔的小草,
听着附近的石匠钻刻着墓石,或是碑文的声音。
那一刻,
胸中的肺叶跳跃起来,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你的死,
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
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
我们走出墓门,
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击打着石头的声音,
我不敢去问那石匠,
将来他为着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
(完)
责任编辑/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