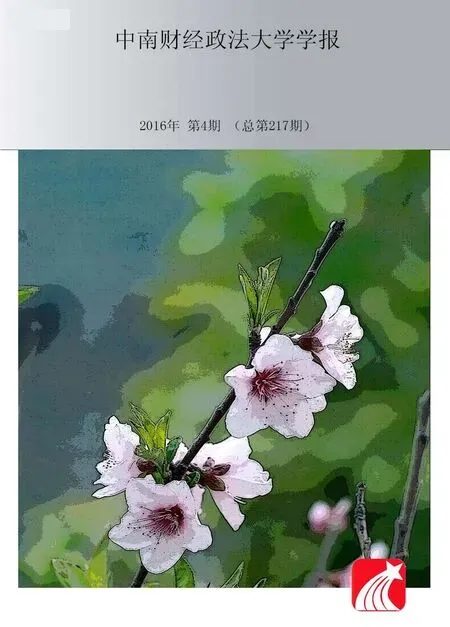经济结构变迁研究新进展
梁 俊 龙少波
(1.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2.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经济结构变迁研究新进展
梁俊1龙少波2
(1.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2.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经济部门的结构性变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近十几年来,经济结构变迁研究出现了三个重要趋势:一是从强调引起结构变迁的需求或供给单方面原因向同时强调两方面原因转变;二是从假定封闭经济以及要素的完全流动性向假定开放经济和存在要素流动障碍转变;三是从孤立地考察结构变迁问题向更多地从结构变迁视角来分析其他宏观经济问题转变。本文按照文献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对这三类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进一步的研究需要重视衡量经济结构指标的一致性,关注人为因素对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在研究中国的经济结构变迁问题时需要考虑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如所有制结构、各种形式的政府干预等。
关键词:经济结构变迁;经济增长;多部门增长模型;收入效应;价格效应
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活动的跨部门转移[1]。Kuznets、Chenery等较早对经济结构变迁的规律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产值和就业份额上升的经验事实,这被称为Kuznets事实[2][3][4](P8—13)。这种部门间的不平衡增长与Kaldor事实①不一致,而且不能被传统的平衡增长理论很好地解释[5]。学者们普遍意识到要同时对部门层面的不平衡增长与总体层面的平衡增长做出解释,必须对经济结构变迁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近十几年来,关于经济结构变迁的研究不断增多,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这些进展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结构变迁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二是在开放经济和存在要素流动障碍的背景下研究结构变迁,三是研究结构变迁与其他宏观经济问题的联系。
目前通过多部门增长模型研究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文献依然不多,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依然是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目标,因此,系统地梳理结构变迁研究的最新进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下文将分别对三类研究进行综述,在结语部分我们将对进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
一、结构变迁的原因: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
现有文献普遍认为引起结构变迁的原因主要有两类:需求方原因和供给方原因。较早的研究大多旗帜鲜明地支持其中一种,但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试图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解释结构变迁的文献正在逐渐增多,其中一些文献还试图在一个模型框架内同时对Kuznets事实和Kaldor事实进行解释。
(一)引起结构变迁的需求方原因
从需求方来解释经济结构变迁的文献认为是恩格尔效应引起了结构变迁,即认为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农产品上的支出比重会不断下降,而在非农产品上的支出比重会不断上升。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收入效应。从建模层面来看,要产生恩格尔效应需要设定具有非位似性(non-homotheticity)的偏好,其中,Kongsamut等、Echevarria、Foellmi和Zweimuller设定的非位似偏好最具代表性[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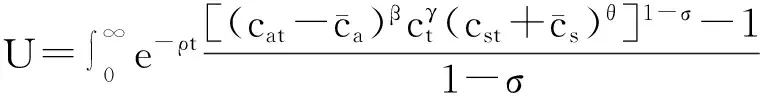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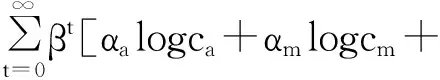
Foellmi和Zweimuller通过一种基于等级偏好(hierarchic preferences)的效用函数来产生非位似需求。在等级偏好中,产品被依次引入模型,并且每种产品的收入弹性是变化的,产品刚被引入时有较高收入弹性(奢侈品),随着收入增加,这种产品变为低收入弹性的必需品。接着新的产品又被引入,如此更替。Foellmi和Zweimuller将所有产品归入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由于不同产品有不同的收入弹性,随着产品不断被引入,劳动力将跨部门转移,出现经济结构变迁,其定量分析表明,农业的劳动力份额会不断下降,服务业的劳动力份额会不断上升,而制造业劳动力份额则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8]。该模型也能同时解释Kuznets事实和Kaldor事实,其主要不足在于它只能通过具体产品的数据来模拟结构变迁,而无法与部门层面的宏观数据结合。
总体来看,从需求方解释结构变迁的文献对引起结构变迁的原因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但存在一些过于严格的假设。比如,这类文献普遍假定的“刃锋条件”就饱受质疑,Ngai和Pissarides指出该“刃锋条件”违背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假设:偏好与技术之间完全独立,因而显得过于苛刻以至于脱离现实[9]。此外,这类文献忽视了供给方对结构变迁的影响,很多研究都表明,供给方的原因如部门间不同的生产率增长也会引起结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类研究具有一定片面性。
(二)引起结构变迁的供给方原因
另一类文献认为是供给方的特征引致经济结构变迁。具体来说,经济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和要素收入份额差异所产生的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引起了结构变迁,这种效应又被称为价格效应。该机制最早由Baumol提出[10],后经Ngai、Pissarides、Acemoglu和Guerrieri发展完善[9][11]。
Baumol将经济部门划分为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前者有不变的技术进步率,后者无技术进步[10]。劳动是唯一的投入要素,且能自由流动。如果产品的收入弹性较高,价格弹性较低,那么随着技术进步,劳动力就会向停滞部门转移,使得停滞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增大,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出现所谓的“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
Ngai和Pissarides对Baumol的研究进行了拓展,他们在模型中考虑了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要素以及多种消费品,每种消费品都会进入一个不变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substitution,CES)的效用函数[9]。不同部门的生产函数只有一个区别——技术进步率不同。他们的分析表明,当最终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时,就业份额会向低技术进步率部门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鲍莫尔病”的结论。此外,他们的模型能同时解释Kuznets事实和Kaldor事实。
以上两篇文献是从部门技术进步率差异的角度强调了引起结构变迁的供给方原因,Acemoglu和Guerrieri认为除此之外,不同部门的要素收入份额差异也会引起结构变迁。在他们的模型中,资本份额起到了放大技术进步率的作用,因而也会对结构变迁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只要各部门的资本份额不同,且各部门技术进步率与劳动收入份额之比不同,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结构就会发生变化[11]。
一些研究对Acemoglu和Guerrieri的模型进行了拓展。比如陈体标借鉴Acemoglu和Guerrieri的双层嵌套CES生产函数,通过一个同时考虑了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模型对经济增长过程中“中等收入国家增长最快,最富裕国家其次,最贫穷国家最慢”的“驼峰形”事实进行了解释[12]。徐朝阳在Acemoglu和Guerrieri的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三部门模型,除了描述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不断下降和服务部门劳动力份额不断上升的结构变迁之外,还描述了工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倒U型的结构变迁过程[13]。
总体来看,供给原因文献对需求原因文献进行了重要补充,指出部门间不同的技术进步率和要素份额差异也会引起经济结构变迁。但这类研究也只是侧重分析了供给原因单方面的影响,不能评价两类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此外,与需求原因文献假定的“刃锋条件”受到质疑类似,供给原因文献普遍假定的位似性(homotheticity)需求也饱受质疑,Ray指出,位似的需求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14]。除了以上问题,这一类文献一般只能解释各部门名义支出份额的变化,而无法解释真实支出份额的变化。可见,这一类研究也亟待补充完善。
(三)需求方和供给方原因的双重影响
以上两类文献分别关注了引起结构变迁的一方面原因,很多实证研究表明这两种原因都会起作用[15][16]。因而,只有使用同时考虑供给和需求原因的模型,才能解释早期各国以及现今发达国家经历的丰富的结构变迁模式[17](P703)。

Iscan建立了一个与Herrendorf等类似的模型,该模型也能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两种机制解释结构变迁,这两个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采用的是连续时间形式的偏好,而后者的偏好是离散时间的,此外,与Herrendorf等不同,Iscan还对模型参数进行了校准,并用该模型估计了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对美国经济结构变迁的解释程度,发现这两个因素一起解释了美国服务业就业份额上升的2/3[15]。Iscan模型的主要问题和Herrendorf等的模型一样,即要同时解释Kuznets事实和Kaldor事实,需要满足苛刻的“刃锋条件”。
一个模型若能兼顾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且能在不要求“刃锋条件”的情况下同时解释两个典型事实,显然会更合意。Boppart构建了一个这样的模型,他在模型中使用的是一种“价格独立一般线性”(price independent generalized linearity)偏好,这种偏好比戈尔曼(Gorman)偏好更一般化,并能产生非线性的恩格尔曲线[16]。他通过微观数据的估计发现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在解释经济结构变迁上几乎同样重要。
从最近的研究来看,同时从需求方和供给方来解释结构变迁已经成为了一个趋势,本文在后文将要综述的大部分文献也都兼顾了这两类原因[18][19][20][21]。这类文献能对两类原因进行比较,这相对于只考虑了单方面原因的文献而言是一个进步,但这些研究大多假定经济是封闭的,且要素流动是没有障碍的,这显然不符合很多国家的现实,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放宽这些假设能提供一个更真实的模型环境,并有利于进一步研究这些条件对结构变迁的影响。以下我们对这类文献进行梳理。
二、开放经济和存在要素流动障碍下的结构变迁
封闭经济以及要素的完全流动一直是早期研究中的典型假设,近年来,一些研究逐渐放宽这些假定,开始在有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障碍的模型条件下研究经济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一)国际贸易与结构变迁
国际贸易会对一国经济结构变迁产生影响,这类研究通常使用两国三部门模型。Matsuyama使用了一个两国三部门模型研究了制造业份额变动的情况,其中农业和制造业产品可以无成本进行外贸,服务业则没有外贸。分析表明一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另一国制造业就业份额下降,本国的制造业就业份额由于受到收入效应和贸易效应两种相反力量的影响,变动方向不确定[22]。Betts等研究了国际贸易在韩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发现国际贸易对韩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的迅速增加至关重要,但是对农业的影响不大[23]。Uy等在一个两国三部门模型框架内定量评价了收入效应、价格效应和国际贸易三种机制对韩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发现收入效应和国际贸易差不多解释了所有的农业和服务业劳动力份额的变化,以及“驼峰型”制造业劳动力份额变化趋势的上升部分(但并没有对下降部分做出很好的解释)[21]。
(二)要素流动障碍与结构变迁
一些研究还表明,要素流动障碍也会对经济结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这类文献又可分为两类:一类研究劳动力流动障碍对结构变迁的影响,另一类则研究资本流动障碍对结构变迁的影响。
第一类文献认为就业政策、换工作的高成本以及制度原因会造成劳动力流动障碍,进而影响结构变迁。Nickell等发现就业保护政策严格的国家往往有很大的工业部门,这说明,就业保护政策会阻碍劳动力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24]。Messina研究了进入壁垒的重要性,他认为欧洲有较高的服务业进入壁垒,因此服务业的劳动力份额要低于其他发达国家[25]。Lee和Wolpin衡量了1968~2000年间美国劳动力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成本,他们发现,劳动力跨部门转移的成本很高(高达一个劳动者年收入的75%),然而行业内换工作的成本很小[26]。Hayashi和Prescott研究了二战前日本劳动力转移出农业的情况,他们发现子承父业的父权制限制了日本的劳动力由农业向其他部门转移,这是二战前日本产出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27]。盖庆恩等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和非农部门的两部门模型,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流动障碍使得两部门工资水平存在差异,他们的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扭曲会阻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若消除扭曲,中国农业劳动力份额将下降26.38%[28]。
第二类文献认为所有制结构会造成资本流动障碍,进而影响结构变迁。Brandt 和Zhu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三部门模型。其中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只有劳动力,而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存在资本市场扭曲(指由资本流动障碍导致的部门间资本边际收益不相等),这种扭曲的存在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消极影响,他们通过反事实分析发现,若资本市场扭曲消除,中国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和TFP增长率将分别提高0.82个百分点和1.58个百分点[29]。Song等的研究也考虑了国有和非国有部门间的资本市场扭曲,他们通过一个两部门的世代交叠模型对资本市场扭曲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现非国有部门的融资约束以及国有和非国有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导致资本市场扭曲,他们的模型还能对中国高增长与高资本回报率并存以及对外盈余不断增加的特征事实进行解释[30]。
总体来看,考虑了开放经济和要素市场扭曲的文献显著提高了多部门模型的现实解释力。这些研究表明,除了已被广泛探讨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原因,国际贸易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也会促进或阻碍经济结构变迁的过程,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三、结构变迁与其他宏观经济问题
以往对结构变迁与其他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是相对独立的,很多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多是基于单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然而这种模型忽略了经济部门构成的变化,无法分析经济结构变迁与其他经济问题之间的联系。近年来,随着结构变迁研究的不断拓展,在多部门模型框架下研究其他宏观经济问题成为了一个新的趋势。很多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都区分了农业和非农部门,或者考虑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试图从经济结构的视角加深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认识。以下我们梳理了多部门模型在五个宏观经济问题上的应用研究。这五个问题是:农业发展、总劳动生产率变化、劳动时间的变化、经济周期和工资差距。
(一)结构变迁与农业发展
通过多部门模型研究经济发展的文献特别重视农业部门的研究。这些研究侧重从农业技术进步、农业人力资本和农场规模等角度分析穷国农业生产率或总生产率落后于富国的原因。Gollin等使用一个两部门模型分析了农业使用现代技术时机的重要性。他们的模型中农产品可以通过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两种技术进行生产,前者没有技术进步,而后者有技术进步。当现代技术的生产率低于传统技术时,所有农产品都用传统技术生产,所有的劳动力都配置在农业部门。随着现代技术进步,在某个时点,现代技术会变得比传统技术更有生产力,这时农业部门开始使用现代技术进行生产,劳动力也不断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他们的核心结论是穷富国间的大部分收入差距都源自农业部门采用现代技术时机的不同[31]。Restuccia等使用一个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对影响国家间农业就业份额差异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各国总劳动生产率差异、农业中间投入品的使用障碍和劳动力流动障碍导致各国农业就业份额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他们的定量研究还表明,如果穷国的农业部门就业份额和农业生产率水平与富国相同,那么穷富国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将是5倍,而不是实际中的34倍[32]。Lagakos 和Waugh指出穷国农业部门对高效劳动力吸引能力不足导致穷国农业部门的生产率远远落后于富国。在穷国,很多并不擅长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出于生存需要也必须进行农业生产;而在富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少数劳动力都是最擅长农业生产的高效劳动力,这使得穷富国间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异非常大。他们对模型参数校准后进行的模拟发现,穷富国间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异大约是非农部门的两倍[33]。Adampoulos 和Restucca的研究指出富国的农场规模一般较大,而穷国的农场规模一般较小,这种农场规模差异也会导致穷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富国。从机制来看,总量因素(经济层面的生产率、资本产出比和人均土地)差异和穷国扭曲性的政策造成了穷国农场规模偏小并进而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两类原因能够解释穷富国间土地规模差异和农业生产率差异的50%。他们的定量研究还发现规定农场规模上限的扭曲性政策或激进的土地税政策都会导致农场规模和农业生产率下降3%~7%[34]。
(二)结构变迁与总劳动生产率
结构变迁过程中的部门要素重置会显著影响总劳动生产率增长[7]。Bah和Brada估计了新进入欧盟的中欧国家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些中欧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份额要远低于欧盟的核心成员国,并且这些国家服务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比制造业部门低。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向服务业转移将导致人均GDP的损失,要减少这种损失就必须进行改革,使服务业更有生产力[35]。Duarte和Restuccia通过一个三部门模型研究了1956~2004年间29个国家的部门劳动生产率对结构变迁和总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穷富国间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大于制造业,于是当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时,会导致穷国劳动生产率相对富国的赶超;而当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时则会导致穷国劳动生产率进一步落后[19]。杨天宇和刘贺贺对Duarte和Restuccia的模型进行了拓展,分析了农业和非农部门间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这种更一般化的情况,并用该模型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的总劳动生产率反超印度并持续领先的原因,发现中印两国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力流动壁垒的差异,是导致印度与中国劳动生产率之比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20]。
(三)结构变迁与劳动时间
这类研究一般在模型中设定了一个家庭生产部门,该部门规模和效率的变化会引起经济结构变化和劳动时间的变化。Rogerson通过一个同时考虑了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模型研究了1956~2003年间欧洲和美国的劳动时间变化情况。为了简化分析,他把农业和制造业加总为一类,且只考虑劳动一种投入。此外,他的模型考虑了劳动供给决策和家庭生产(是市场服务的替代品),研究发现,由于欧洲的市场服务部门比美国小得多,欧洲的劳动时间相对于美国下降了45%[18]。Ngai和Pissarides在他们2007年文章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家庭生产部门。他们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模型会产生浅U型的市场劳动时间曲线,并最终将导致家庭生产部门的市场化。最初市场劳动时间的下降是由于家庭生产是市场服务更好的替代品,而随着市场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又从家庭生产部门向市场服务业转移[36]。
(四)结构变迁与经济周期
结构变迁与经济周期有很多相同特点,一些研究认为经济周期是经济活动跨部门转移的结果。比如Lilien认为,劳动力的跨部门转移需要一定时间,因此,较长的要素重置时期同样也是较长的失业时期。他还指出,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实际上是由较长的劳动力跨部门转移的时期构成的[37]。然而Herrendorf等认为经济周期和结构变迁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他们指出即使要素重置(比如企业退出行业)在衰退期比较集中,也不能认为衰退是由要素重置引起的,而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他们举了一个例子:一家钢铁厂在衰退中可能会决定永久退出这个行业,但也许这家企业只是单纯想在这个时间退出[1]。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即使结构变迁不是导致经济周期的原因,也可能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如Moro使用一个两部门模型研究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波动性,发现制造业的波动性比服务业高,原因在于制造业使用了更多中间产品,他指出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服务业比重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就会增加[38]。
(五)结构变迁与工资差距
这类研究认为不同类型劳动力具有不同的劳动禀赋,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这种禀赋差异会引起工资差距变化。李飞跃使用一个包含了现代部门(非农部门)和传统部门(农业部门)的模型分析了结构变迁与熟练、非熟练工人间工资差距的关系,他发现在技术外生的情况下,工资差距会随着结构变迁而扩大;而在技术内生,且两种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足够大时,工资差距会随着结构变迁而缩小[39]。Buera和Kaboski分析了高技术劳动(high-skilled labor)在服务业增长中的作用,他们假定服务部门有两种生产:市场生产和家庭生产,市场产品比家庭产品更复杂。模型中有两类劳动:高技术劳动与普通劳动,其中高技术劳动只能用于市场生产,且拥有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他们的分析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对市场产品以及高技术劳动的需求会增加,高技术劳动与普通劳动的工资差距会扩大,服务业的市场生产也会不断扩大[40]。
综合上述文献来看,从经济结构的视角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得到了很多总量经济分析无法得到的重要结论,加深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这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因为当部门层面的研究和总量研究得到的结论不一致时,决策者就有必要重新对经济政策进行评估,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从而有可能降低政策成本,提高政策效果。除了对以上五类问题,这种基于经济结构的分析视角对其他的宏观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地区收入差距、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设计)的分析也同样适用。
四、研究展望
近十几年来,经济结构变迁研究获得了一些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新的研究趋势上:一是从强调需求和供给单方面的原因向同时强调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原因转变;二是从假定封闭经济以及要素的完全流动性向假定开放经济以及存在要素流动障碍转变;三是从孤立地考察结构变迁问题向更多地从结构变迁视角来分析其他宏观经济问题转变。本文对这三类文献进行了综述,结合现有研究情况,我们认为有关经济结构变迁的进一步研究应该重视以下问题:
第一,要重视衡量经济结构指标的一致性。Herrendorf等指出使用生产指标(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和消费指标(消费支出份额)去衡量部门份额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他们使用生产指标来衡量韩国制造业份额变化时,发现制造业份额随人均收入增加呈现倒U型趋势;但若使用消费指标,制造业份额则基本上是一条水平线[1]。可见,在使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结构变迁时,保证模型供给方和需求方所用的部门份额指标一致非常重要。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第二,应该重视人为因素对不平衡增长的影响。经济部门的不平衡增长会引起结构变迁,从经济模型的逻辑上看这无可厚非。然而,不平衡增长会使不同群体的利益受到不同的影响,人们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可能会对经济机制的正常作用产生影响。Ray指出人们可以通过换职业、争取政治权力、甚至暴力冲突等方式来阻碍不平衡增长[41]。即使目前没有足够的数据对这些行为的影响进行定量研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影响结构变迁的原因之多,绝非现有结构变迁模型所能囊括。
第三,应该思考结构变迁研究对中国的意义。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结构性减速”期[42]。此外,“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的经济结构变迁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经济结构变迁研究多是针对发达国家,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较少。一方面,缺乏发展中国家可对比的部门层面数据限制了该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解释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模型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研究结构变迁的模型都假定劳动力和商品是自由流动的,然而在中国,由于存在户籍制度和行政区域的相对独立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是有障碍的。此外,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占据着重要地位,而现有文献研究结构变迁时很少考虑所有制结构的影响。中国还存在比发达国家更普遍的政府干预。可见,要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变迁进行更准确的描述,需要更有“中国特色”的模型。当然,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做了有价值的探索,比如Dekle和Vandenbroucke模拟了劳动力流动障碍和政府的作用,通过一个两部门模型对引起中国结构变迁的因素进行了定量评价[43]。Brandt和Zhu、Song等和陈彦斌等在多部门模型中区分了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而王勋和Anders则分析了金融抑制对经济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影响[29][30][44][5]。这些研究都为分析中国的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注释:
①Kaldor事实指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6个典型事实,即人均资本以近似不变的速率增长、人均产出以近似不变的速率增长、资本产出比接近常数、投资回报率基本不变、资本和劳动的收入份额基本不变和各国人均产出水平差距明显。
参考文献:
[1] Herrendorf,B.,Rogerson,R.,Valentinyi,A.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Z].NBER Working Paper No.18996,2011.
[2] Kuznets,S.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I.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Labor Force[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57,5(4)(supplement): 1—111.
[3] Chenery,H.B.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0,50(4): 624—654.
[4] 陈体标.技术进步、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5] 王勋, Johansson,A.金融抑制与经济结构转型[J].经济研究,2013,(1):54—67.
[6] Kongsamut,P.,Rebelo,S.,Xie,D.-Y.Beyond Balanced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1,68(4): 869—882.
[7] Echevarria,C.Changes in Sectoral Composition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7,38(2): 431—452.
[8] Foellmi,R.,Zweimuller,J.Structural Change,Engel’s Consumption Cycles,and Kaldor’s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8,55(7): 1317—1328.
[9] Ngai,L.R.,Pissarides,C.A.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97(1): 429—443.
[10] Baumol,W.J.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3): 415—426.
[11] Acemoglu,D.,Guerrieri,V.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116(3): 467—498.
[12] 陈体标.技术增长率的部门差异和经济增长率的“驼峰形”变化[J].经济研究,2008,(11): 102—111.
[13] 徐朝阳.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倒U型”产业结构变迁[J].世界经济,2010,(12): 67—88.
[14] Ray,D.Uneven Growth: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0,24(3): 45—60.
[15] Iscan,T.B.How Much Can Engel’s Law and Baumol’s Disease Explain the Rise of Service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The BE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10,10(1): 1—41.
[16] Boppart,T.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Kaldor Facts in a Growth Model with Relative Price Effects and Non-Gorman Preferences[Z].Manuscript,Stockholm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Zurich,2014.
[17] Acemoglu,D.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8] Rogerson,R.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European Labor Market Outcom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116(2): 235—259.
[19] Duarte,M.,Restuccia,D.The Role of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ggregate Productivity[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0,125(1): 129—173.
[20] 杨天宇,刘贺贺.产业结构变迁与中印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J].世界经济,2012,(5):62—80.
[21] Uy,T.,Yi,K.-M.,Zhang,J.Structural Change in an Open Econom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3,60(6): 667—682.
[22] Matsuyama,K.Structural Change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A Global View of Manufacturing Decline[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9,7(2): 478—486.
[23] Betts,C.M.,Giri,R.,Verma,R.Trade,Reform,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Korea[Z].Manuscript,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2011.
[24] Nickell,S.,Redding,S.,Swaffield,J.Educational Attainment,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and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Z].Working Paper,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2002.
[25] Messina,J.The Role of Product Market Regu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Structural Change[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6,50(7): 1863—1890.
[26] Lee,D.,Wolpin,K.I.Intersectoral Labor Mobil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Service Sector[J].Econometrica,2006,74(1): 1—46.
[27] Hayashi,F.,Prescott,E.C.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s on the Prewar Japanese Econom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116(4): 573—632.
[28] 盖庆恩,朱喜,史清华.劳动力市场扭曲、结构转变和中国劳动生产率[J].经济研究,2013,(5):87—98.
[29] Brandt,L.,Zhu,X.D.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Z].University of Toronto,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394,2010.
[30] Song,Z.,Storesletten,K.,Zilibotti,F.Growing Like Chin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1,101(1): 196—233.
[31] Gollin,D.,Parente,S.Rogerson,R.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92(2): 160—164.
[32] Restuccia,D.,Yang,D.T.,Zhu,X.D.Agriculture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Cross-country Analysi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8,55(2): 234—250.
[33] Lagakos,D.,Waugh,M.E.Selection,Agriculture,and Cross-country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2): 948—980.
[34] Adamopoulos,T.,Restuccia,D.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Farms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Z].University of Toronto,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494,2013.
[35] Bah,E.-H.,Brada,J.C.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Structural Change and Converge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2009,51(4): 421—446.
[36] Ngai,L.R.,Pissarides,C.A.Trends in Hours and Economic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8,11(2): 239—256.
[37] Lilien,D.Sectoral Shifts and Cyclical Unemploy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2,90(4): 777—793.
[38] Moro,A.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and the Decline in the US GDP Volatility[J].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12,15(3): 402—415.
[39] 李飞跃.结构变迁与工资差距[J].经济学(季刊),2011,(2): 477—492.
[40] Buera,F.,Kaboski,J.The Rise of the Service Econom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02(6): 2540—2569.
[41] Ray,D.Uneven Growth: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0,24(3): 45—60.
[42] 袁富华.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012,(3): 127—140.
[43] Dekle,R.,Vandenbroucke,G.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2012,36(1): 119—135.
[44] 陈彦斌,陈小亮,陈伟泽.利率管制与总需求结构失衡[J].经济研究,2014,(2):18—31.
(责任编辑:易会文)
收稿日期:2016-03-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与结构性改革”(13JJD790036);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简介:梁俊(1984— ),男,湖南邵阳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16)04-0003-08
龙少波(1984— )男,湖南邵阳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