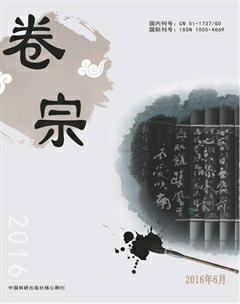柔软的力量
摘 要: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提升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抵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诱导挪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外交活动。由于挪威的特殊性和受当时环境的影响,使得美国在1945-1965年这一阶段在挪威所实行的文化外交策略更加具有“柔软”的特点。
关键词:文化外交;挪威;美国
长期以来,挪威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挪威逐渐放弃了中立的态度,并且逐步加入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寻找到了对挪威实施文化外交的契机。1945年以后,像对待欧洲的其他地区一样,美国政府在挪威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外交活动。美国在挪威进行文化外交的目标即是改变挪威对美国形象的误解,改变挪威将美国定义为一个文化肤浅民族的状况,承认其军事、经济以及文化强国地位,由此赢得挪威公众的信任,支持它的国际战略。
目前各国对于“文化外交”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对“文化外交”较为妥当的理解是:“文化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 。根据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施行文化外交的主体是政府,接收对象是外国公众,目的是利用公众舆论来为本国政府赢得支持,并影响外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在笔者看来,文化外交实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宣传性外交,一种是柔软性外交。宣传性的外交具有“强迫、灌输、压制”的特点,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会造成外国公众的反感和抵制。但柔软性外交主要是通过文化交流、电影和出版物等的形式来对外国公众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美国在1945—1965期间对挪威执行的文化外交不是强制和硬性的宣传,具有非常明显的“柔软”的特点。美国文化外交策略具有“二元性”特征,一方面,它要提升自己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又需要与共产主义制度做抗争。美国正是想通过“柔软的方式”来赢得和加强“坚硬力量”的支持,以此发展它的国际战略。
1 总体情况:“慢性”传媒盛行
美国通过一系列非官方的活動来提升其在挪威的形象,包括印刷品、电影宣传、书籍、图书馆和和翻译项目等。
在所有的这些项目中,自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的印刷品项目最高效而且最重要。因为挪威当地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文盲现象的消失和公众对报纸的大量需求,使得通过一系列印刷品来传播美国文化的方式在一段时期内比较有成效。当然,非商业性的电影宣传项目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尤其是重要的劳动阶层。但在短期后,“慢性”传媒(包括人员交换、文化展示以及学术合作项目)逐渐成为美国在挪威展开文化外交活动的主要手段,成为在挪威成功开展文化外交活动的基础。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美国在此阶段对挪威所使用的文化外交策略正如学者宁柯维奇所阐述的那样,“是文化策略,而非信息策略”。在他对美国从1938到1950年的外交策略的分析中,他将文化策略视为“慢性”传媒的一种方式,主要针对社会精英,并且由此得到他们长期的理解和尊敬。相反,信息策略主要在短期内进行,并且使用快速的、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宁柯维奇强调“慢性”传媒已经成为了美国政治领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大量的例子也都可以来证明“慢性”传媒在这一阶段盛行的现象。例如,在视美国为相对友好的国家以及在学术交流和旅游活动相对自由的地区内,公民交换项目不管是否有学术性,都在美国的文化外交中显得非常重要。有些学者已经阐述了“富布莱特法案基金项目”的重要性,而且在最近的研究当中,“美国所筹划的‘外国领导人计划也成为了促进其外交策略顺利施行的重要的外交手段”。“通过对这些本身就对美国怀有敬意的国家实行文化策略将会比使用信息策略更具有影响力”。
2 富布莱特法案基金项目
交换项目逐渐被视为更有效的、更长期的宣传方式,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建立和维持公众之间长期私人关系的重要工具,而且更因为它是更高效和更合适的文化外交策略,是对主要的传播媒介的一种重要补充。
1946 年 8 月 1 日,杜鲁门总统签署《富布莱特法案》,后来它也成为美国在挪威进行的最大的交换项目,虽然在前期(1949-1950)开展地并不是很顺利,但在后来却成为一个巨大的成功案例。从1950年到1960年,“富布莱特法案基金项目”已经成为美国在挪威开展文化外交的最重要的基石之一,而包括它在内的所有交换项目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也备受大家关注。有一种观点强调这些参与交换项目后回到挪威的学生、学者以及老师们应该在挪威的学术界对美国文化进行传播,通过有组织性的学术交流,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进行宣传。事实上,“到1968年,挪威将近有60%的社会科学家和50%的自然科学家每年至少有6个月在美国的学术机构进行科研工作”。
在1953年1月,美国教育基金会展开了一项对项目影响的调查研究。美国新闻署的激励、“富布莱特法案基金项目”的成功也使得社会研究所的大批学者深受其吸引。从美国的角度而言,这些交换项目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因为这些项目促进了国际间的理解,提升了美国的形象。另外,94%的受访人员都对在美国进修的那段生活表示“非常满意”和“满意”。绝大多数成员都对美国抱有积极的印象,他们不仅能够很好地适应美国的生活,而且对美国的身份认同感相比于在参加项目之前,有了显著的提升。
笔者通过查证,发现这些参与者在返回挪威之后,充当了重新树立美国形象的“专家”,55%的挪威公众都表示他们通过这些人更正和提升了对美国的印象,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再认为美国仅仅是一个物质发达的国家。这种传播主要是通过非正式的私人的谈话进行的。同时,4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也通过加入某些非正式的社团组织、阅读报纸及其他印刷品以及收听广播来重新建立对美国的认知。只有仅仅31%的人表示他们是靠在交换期间,阅读专业性的书籍和观看专业性的讲座来了解美国的。相反,在交换期间,通过获取非专业性的知识来改变对美国的印象却是较为普遍的,参与者在归国之后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发挥着“链式效应”——即通过非官方、非专业的交流沟通以及口口相传的方式等来传播美国的文化。
3 外国领导人计划
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目前由美国政府赞助的交流和培训项目总共有223个”,在这些项目中,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最能反映美国面向其他国家精英群体的传播策略。反观历史,20世纪50年代,在挪威进行这样的项目非常重要,尤其是没有工党组织存在的地区是美国进行文化外交的重要目标。参与这个项目的绝大多数成员并不像“富布莱特法案基金项目”那样有学历上的要求,它被视作是当时储备优秀人才干部的重要途径。因为此计划相对来说比较灵活,所以它成为美国向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进行文化外交的一条高效和合适的途径,尤其是涉及到美国国内一些比较有争议的事件和国际事件。所以一直以来,美国对于此计划也抱有较高的期望。
从1940年开始,美国在全球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就“始终坚持以各国现任和潜在的各界精英和卓越人才作为重点对象”[1]。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挪威每年大约有3到4名成员前往美国参与“领导人计划”。为了增加参与此项目的人数,美国新闻署便试图选拔更多的人来参与此项目。虽然报名参加的总体人数相对较少,但是却涵盖了主要的领域和组织,成员包括工党代表、教育领域的代表、媒体记者代表、公共服务领域的代表以及其他非官方组织的代表等。这些参与者当中也包括了一些本身就有赫赫政绩的领导人,如挪威广播系统的负责人(Kaare Fostervoll)就在事业上升阶段时参与了1952年的“领导人计划”。
著名学者史密斯说:“参与‘领导人计划一方面符合美国政府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得参与者能够为自己获取利益。”[2]。除了让参与者获取有关美国物质和文化的知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试图让这些人适应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让他们潜在地成为富有美国文化知识并且对美国抱有敬仰和同情态度的精英网络系统的成员”。
在挪威,这项计划的灵活性体现在参与者的人数分配随着计划目标的变化而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在北挪威,随着公众对中立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美国便对这一地区的“领导人计划”的人员分配和活动开展就优先考虑了。除了客观上达到增强双方理解的目标,对个人进行选拔也是为了展示美国良好的福利制度,改善他们对美国与挪威的贸易体系和美国种族关系的消极印象。
从1945年到1965年,挪威参与美国施行文化外交而开展的各种交换项目,包括“富布莱特法案基金项目”和“外国领导人计划”,学生总人数为949人,科研工作者为290人,演说家为50人,老师为141人,专家为47人以及领导人为133人。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挪威参与交换项目的国内人数之比是很高的,只有西德、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超过了挪威。这些数据说明了美国将交换项目作为在挪威进行文化外交的策略并非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将其付诸实践,并且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史密斯说:“作为美国文化外交策略的‘领导人计划在荷兰开展地非常顺利,因为荷兰这个国家相对较小,而且文化的普及程度较高,也有较为完善的教育系统,所有这些都会导致个人所能发挥的‘链式效应。”挪威与荷兰有着极高的相似性,所以史密斯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挪威。目前也有学者表示这种效应在整个大欧洲范围内同样存在。
美国著名学者克莱·G·瑞恩认为,“谁塑造心灵与想象,谁就能塑造未来”[3],通过这些交换活动,在客观上达到了一些目标。美国文化以及外交政策被不断地传播,加深了挪威公众对美国的理解。
4 挪威可否成为范例?
美国使用文化策略还是信息策略来达到其宣传目的是视具体情况而定的。笔者查阅到的史料除了提到在西欧的外交大使们的交流和信息以外,主要强调了交换项目在满足教育需求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也成为了美国维持良好国际关系的独立而重要的板块。同时,这些交换项目不仅为美国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且这些参与者都情不自禁地对他人讲起在美国的经历,存在着“链式效应”。这些文化外交活动强调了间接性文化活动的重要性,注意回避以往的政治“宣传”。同时,国家教育与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在1963年出版的两份报告同样也强调了交换项目对于外国公众学习美国物质和文化的重要作用,并且将其称赞为海外文化宣传项目重要和高效的手段[4]。同时诸多材料也表明,美国进行文化外交而使用的“慢性”传媒以及“链式效应”的重要作用,强调了这些文化活动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即“通过建立基于大众友谊和相互理解的公众舆论,进而从各国内部控制各国政府”。
在笔者看来,美国在挪威开展的文化外交活动具有典范作用,尤其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更加具有意义。美国负责教育与文化事务的前代理助理国务卿海琳娜·费伊(Helena Finn)撰文指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懂得与外国观众接触和战胜自己的意识形态敌人之间的联系,文化外交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文化外交是美国军火库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虽然这些活动对官方正式的反共产主义的宣传有所削减,但是文化外交的作用在不断发挥,赢得了目标群众的信任和理解。开展文化外交活动所要施行的策略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不仅需要考虑目标群众的构成和特点,还需要考虑资源是否充足、方式是否可行和合理。美国所需要的是挪威的认可和支持,而“认同另一个国家是需要采取合适的方式让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能适应另一个国家,并能被它所引领”[5],所以美国以柔和的方式来对待挪威。“通过这些方式和手段,目标国家的群众对美国保持着友好的态度。”
“中立国的存在有利于均势体系的稳定,因为中立国能够发挥缓冲和平衡的作用”,而挪威中立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是因为它很好的适应了美国文化外交的框架。美国文化外交策略的灵活性以及“慢性”传媒可能的作用都得到了有力的诠释,并且成为领土完整但相对较小的国家的范例,展示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是如何在超级大国的安全体系中成为大国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的”。虽然对这种间接宣传策略的选择在碰到具体情况时存在着个体的差异,但是这种策略在小国家当中所产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同时,挪威的文化宣传策略深刻影响着其他欧洲国家,对它们造成了一定的辐射作用。根据对 1954 年的参与美國的国际访问和文化项目的人数统计,来自欧洲的总人数就有 645 人[6]。
从文化外交的角度而言,挪威与西欧其他国家存在着很高的相似度,但是在当地开展这些活动也有着具体的挑战和困难,比如挪威国内对中立主义高度的偏爱、挪威人民的构成以及挪威的地理位置等。但总体而言,挪威的案例展示了,信息活动、文化策略、学术合作及交换项目在与实际直接的宣传活动的对比中,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美国在挪威进行的这种试验性文化外交,逐渐发展成为美国通过文化活动来达到政治目的、“慢性”传媒超过其他宣传方式而成为主导、“链式效应”发挥巨大作用的代表性案例。
5 结 语
为了对抗苏联,完成“世界领导者”的梦想,美国选取挪威作为它开展外交活动的重点对象,让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获取更多支持美国的力量。
在1945-1965年这一阶段,美国所使用的文化策略的“柔软性”尽显,除了常态的文化宣传方式,“慢”性媒介被美国政府大力使用,针对挪威公众的交换项目也一时盛行,“富布莱特法案基金项目”和“外国领导人计划”是所有文化外交项目中最具影响力和最有成效的两个项目。参与这些项目的公众大体都不再认为美国仅仅是一个军事和经济强国,而是一個全方位都很优秀的发达国家。同时,这些项目的参与者通过口口相传产生了“链式效应”,使得更多的公众对美国文化和体制了解地更加透彻,使美国的物质、文化及生活方式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宣传。另外,挪威作为北欧国家中的重要成员,发挥着辐射作用。挪威是美国成功开展文化外交的范例,通过挪威去影响其他欧洲国家也在美国的外交策略当中有所体现。
美国在挪威的文化外交充分地说明政治性文化策略的重要性,它展示了“慢性”传媒不仅仅可以提高双方国家长期性的理解程度,而且能够达到文化外交更多的客观目的。同时,它也展示的“柔软”的文化宣传在合适的时间会比直接性的宣传更具影响力,更能为美国赢得支持的群体和力量。
参考文献
[1]参见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resus, 2004, p.5.
[2]根据学界共识和笔者考证,认为“慢性”传媒主要包括人员交换、文化展示及学术合作等。
[3]可参考Frank Ninkovich, The Diplomacy of Ideas: US 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1938—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19.
[4]Richard Pells, Not Like US: How Europeans Have Loved, Hated, and Transformed American Cultur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61.
[5]Giles Scott-Smith, Networks of Empire: The US State Departmnets Foreign Leader Program in the Netherlands, France and Britain 1950-1970, Brussels: P.I.E Peter Lang, 2008, p.22.
[6]Geir Lundestad, ‘Research Trends and Accomplishments in Norway on United States History, in Lewis Hanke, ed., Guide to the Study of United States History outside the US 1945-1980, Volume III, White Plains, New York: Krau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85, p.256-7.
[7]数据及相关信息可参见DNSA: Sverre Lysgaard: ‘A Study of Intercultural Contact: Norwegian Fulbright Grantees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ISR,Oslo, 1954,i.
[8]IAWG, FY2012 Annual Report,http://www.iawg.gov/reports/annual/,访问日期:2015年12月。
[9]刘恩东:《美国国际访问者项目的文化外交功能分析》,《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91页。
[10]DNSA: Oslo to the Department, 3 April 1950, in RG 59, Central Files 1950-54, 511. 57-576, Box 2415.下载日期:2015年12月。
[11]同[5], p.32.
[12]Ibid, p.56.
[13]所有数据聚来源于DNSA: United States Grantee Directory Fiscal Year 1965,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966.下载时间2015年12月。
[14]同[5], p.418.
[15]Gunter Bischof, Two Sides of the Coin: TheAmericanization of Austria and Austrian Anti-America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p.162.
[16][美]克莱·G·瑞恩:《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程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17]同[5].
[18]Richard Arndt, 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lles: Potomac Books, 2005, p.57.
[19]Helena Finn, The Case for Cultural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2003, Vol. 82, No. 6, p. 15.
[20]Rafik I. Beekun and James W. Westerman, Spirituality and national culture as antecedents to ethical decisionmak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wa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 110, No. 1 September 2012, pp. 33-44.
[21]Giles Scott-Smith, Laying the Foundations: US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Promotion of American Studies in Europe, in van Minnen and Hilton, eds., Teaching and Studying US History in Europ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3.
[22]賀嘉洁:《中立国与均势的稳定——以冷战时期的“北欧平衡”为例》,《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1 年第2 期,第32页。
[23]Pederson, John Martin,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Norway and Sweden: Ide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Cold War, 1949-1961,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Lincoln,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1998, p.9.
[24]同上, p.40.
作者简介
熊世豪(1992-),男,土家族,湖北宜昌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