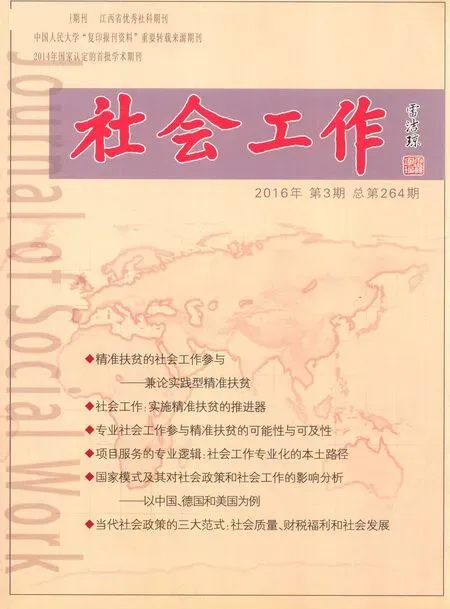残障观的多元范式与残障研究的转向
——兼评《残障权利研究》与《障碍研究》①
李学会
残障观的多元范式与残障研究的转向
——兼评《残障权利研究》与《障碍研究》①
李学会
摘要:医学模式、社会模式以及尝试超越二者的普同模式,构成了考察残障的多元范式。本文借助于台湾综合性的残障研究著作,探讨我国大陆残障研究尝试理解和转化国际残障研究中知识、理念的努力。对于中国的残障研究而言,关注残障者的主体性并反思残障研究的隐含假定是残障研究的重要任务。本文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反思框架,亦可以作为寻求突破的方向。
关键词:残障研究社会模式医学模式研究转向
李学会,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市虹口区特殊教育康复指导中心兼职科研员,讲师(上海200433)。
①本研究的初步想法得益于2014年8月在台湾国立中正大学紧凑而充实的学习。在2014年10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残障权利年会上,笔者与与会人员的交流受益匪浅,尤其是与王国羽、吴秀照、张恒豪、苏峰山等老师的交流。当然,一切文责由本人承担。
一、引言:如何认识残障
残障②笔者赞同如何称谓具有某种缺陷或者身心遭遇障碍的人士是重要的,实际上不同文化中的称谓例如残废、残疾、身心障碍等等已然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文化事实,既体现了残障人士的正名乃至于自我认同,也体现了社会再现残障的方式和文化意涵(例如张恒豪、苏峰山(2009)对战后台湾小学教科书中障碍者的分析以及李学会(2015)对全国自强模范社会形象的研究)。而且残障作为一个客观实在与其分类标准一同出现,同时具有多种实体的残障(邱大昕,2011,2013)。本文采用的是残障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同于残疾——多多少少有些医学模式的意谓,也不同于(身心)障碍——过度重视残障人士本身的社会状态而忽略了其他(权力)主体在界定残障群体“资格”发挥作用的现实。文章中在使用不同概念时,为了引述原文的完整性,保留了不同的用法。例如,台湾的残障研究,倾向于使用“障碍”一词。人士向来是社会成员中从未缺席的一部分,但如何认识、理解残障本身,深受文化观念、历史传统、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如何“合适地”描述和对待残障人士摇摆不定,进而衍生出差异巨大的法律、社会政策和社会态度。2006年联合国通过、2008年我国批准加入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为我国残障研究、残障权利倡导事业产生全球性联系提供了契机。国外的研究观点、理念、技术等等方面有了现实的传播路径,本土在地的组织以及观点拥有了国际交流的机会①《残疾人权利公约》所直接衍生的民间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途径就是,提交与政府提交审查报告相平行的影子报告。CRPD第三十三条“国家实施和监测”一章第三条予以确认:“民间社会,特别是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应当获邀参加并充分参与监测过程”。实际上,在实践中CRPD也成为权利倡导者的有力思想来源,例如“盲人高考”权利倡导中的话语动员(李学会、傅志军,2015)。。对残障群体的权利而言,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挑战。互联网、智能通讯设备大大弥补了残障人士在某些功能上的不足,甚至成为身体机能的某种延伸;同时,残障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国际上新的做法、理念等等有关权利、行为、政策等的具体突破都可以比较快速地传递到残障群体中,这对残障群体的权利倡导来说,无疑是一种良好的示范和合法性来源。长期以来,我国残障研究囿于经验现象的描述和一般对策的阐述,研究所依据的理论范式以及方法的科学性相对受到忽视。学术研究虽然滞后于一线的残障组织对于《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反应,但也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武汉大学公益法研究中心主编的《残障权利研究》(2014)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作为残障研究步入全球联系的例证,2014年瑞典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②《残障权利研究》(2014)就是在该机构与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于2012-2013年间实施的“中国残障人权利多学科研究项目”的成果。在我国倡导并切实推动开展多学科人权研究,可以说肇始于挪威人权中心和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所进行的项目。在此之前,两机构在2006年、2007年在北京举办过两次跨学科人权研究国际研讨会(张万洪,2010:导言)。在《残障权利研究》(2014)之前,同样是张万洪所主编的《我们时代的人权:多学科的视野》(2010),可以视作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发端,在国内的残障研究中同样是比较前瞻的实践。而且来自多元学科背景的现实,也让研究的主题更多样,或许也有些缺乏聚焦,这当然也与人权研究宽泛自由的领域有关。早期人权领域的研究,残障问题仅仅是一个分支,例如以2004年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英国国际发展部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的“以权利为基础促进发展国际研讨会”,尽管残疾人权利保护是一个议题,但显然不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2005)。代表国际人权发展重大事件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从文本到付诸实践,为人权研究、残障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这也好理解作为国内人权研究重镇的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中心),将研究旨趣之一转向残障研究,这不仅仅是人权研究向残障领域的扩张(残障作为研究或法律客体),更是残障作为权利主体的凸显。法学(人权)领域的有关残障的研究,代表了从研究残障的人权研究到以残障人权为研究对象的残障研究的转变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残障权利研究》(2014)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与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合办的“中国残障人权利多学科研究项目”同样也在推动残障研究的全球化。项目所支持的台湾行程部分,为两岸残障研究的接触提供了便利,也让有着一脉文化相连的两岸,在残疾人事业发展方面有了更多碰撞。由台湾障碍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国羽、林昭吟、张恒豪主编的《障碍研究:理论与政策应用》(2012)可以视作台湾学者障碍研究的总结和与西方障碍研究对话以获得本土认同所做的努力。
笔者作为参与者之一,接触了两岸三地的残障研究者、倡导者与实务者,面对丰富的资料和全新的视角,除了产生了“补课”的想法和马上行动的激情之外,也多少有些失落感。国内的残障研究,多数时间是一个边缘的领域,在学术规范性、研究的深度以及学术群体的投入方面都存在有待突破的空间③见蔡禾、周林刚等,2008,《关注弱势:城市残疾人群体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对残障研究所处的学术忽视状态似乎不是大陆所独有,王国羽(2005)也指出台湾的社会学传统缺乏对残障议题的关注,这是社会现实(例如接触障碍者的经验、社会歧视等)与学术社群(包括学术制度)两者的交互结果(亦可参见:“缺角的台湾社会学研究:身心障礙研究”,巷仔口社会学:http://twstreetcorner.org/2013/06/06/wangguoyu/)。。从主流的视角来说,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等学科的研究,多以福利视角注重从国家福利体制的角度,建构一整套面向残障群体的政策体系①见李学会、傅志军,2015,《残障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及综合取向》,《社会工作》第4期。福利的视角为残障权利模式所排斥或者批判的审视,多少是因为福利的视角下残障群体被视作福利的被动接受者,而权利模式强调残障的主体性,即便接受来自国家的福利,那也是因为这是残障群体的(社会)权利。早在礼记大同篇中就有“鳏寡孤独废者,皆有所养”的福利理念,“皆有所养”虽然赋予了国家对于残疾人的责任,但也确立了残疾人需要被施舍和帮助的边缘地位。而且福利视角下的政策实践,残障者对国家的依赖,可能会给福利接受者造成污名(卡罗·沃克尔,2006)。这也正是台湾残障权力运动先驱刘侠(2004)批判传统福利观念的原因之一。尽管对福利本身的理解可能会造成不同视角之间的冲突,但对于福利视角下的研究以及政策实践来说,保持必要的反思,而不是把来自国家的福利视为不言自明的假定是有必要的。社会政策学科中社会政策的主体与客体、受益者分析等等角度,都可以推进社会政策研究,以揭示政策实践背后的价值基础。。因此,有必要增进对现有研究的认识,增强研究的宏观视角的自觉以及完整地理解外来的知识与本土的现实。
本文立足于以上两本残障研究的著作,尝试做些梳理,尤其以台湾的研究为参照,期望能够对国内残障研究的发展有些启示。
二、变迁中的研究范式和残障定义
很久以来,残障人士通常被认为是医疗体制、社会福利、特殊教育、社会政策等领域中接受服务的客体或者研究对象,与之相应的研究更是分散在不同学科之间。伴随着残障权利运动的兴起,为具体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转变现有的研究视角正是残障成为主体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从研究障碍的学科分割到残障研究的跨领域整合,既是残障权利运动的结果,也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障碍研究》的出发点是“以障碍者为主体出发,探讨障碍者权利的建构与实践、反省社会结构造成的‘障碍’,以及社会政策层面上不同理论架构下对障碍者权益实质保障的争议”(王国羽、林昭吟、张恒豪主编,2012:8)。除了障碍研究中残障者的主体性需要凸显,实际上障碍研究本身同样需要在与西方残障研究的比较中获得主体性,这也正是该书的一个目标。因此,尽管在该书中编者把十章内容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章到第四章处理障碍研究的理论发展、分类方式与历史脉络,第五章到第十章为探讨不同层面的障碍议题与政策”,然而所有研究都内含理解残障的多元方式之于研究残障和残障研究的影响。本部分以此为思路,解读台湾残障研究的领域。
(一)医学模式
如何描述残障有多个版本,在与以往的范式决裂,为残障权利运动提供理论支持的过程中,医学模式作为一个范式被建构出来。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已经广为人知,这一范式主要从人的缺陷方面研究残疾,这些缺陷造成了个人能动性受限制,并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实现某种功能。相信专家和专业人士的作用,残疾是一个需要被避免的缺陷,康复的重点在于残疾人自身,因此需要对残疾人进行医学诊断与治疗,临床康复(Campbell,2009;Norma Leclair&Steven Leclair and Christopher R. Brigham,2009)。当然,医学模式的残障观也不是从来就建立的。张恒豪、苏峰山所撰写的“西方社会障碍历史与文化”一节回顾了西方定义、识别和干预残障的历史与文化,现代医学的出现使残障(尤其是智力与精神障碍)的划分有了新的方法,18世纪的启蒙时代,生物医学、教育、照顾的专家观点强化了专家处理障碍议题的主导权,确立了残障作为“病人”的医疗观点。19、20世纪欧洲收入残障者的机构和隔离式的学校数量迅速发展(王国羽、林昭吟、张恒豪主编,2012:14—20)。
如何认识残障就体现在具体的日常实践和政策设定之中,尽管很难从一般的话语实践中,辨识出背后的残障概念模式。而且经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医疗模式与社会模式不断转换与对立,然而,医疗模式之于残障权利来说却不是轻松去除的。王国羽的“障碍概念模式与理论发展”,回顾了定义障碍的各种努力,以及政策意涵。“世界卫生组织分类系统与障碍测量议题”,讨论了ICF制度中,除了评估残障者所具有的身体损伤,还注重环境因素的影响。世卫组织所做的残障定义改变过程,“就是逐渐脱离以医疗专业为掌控障碍论述的过程,医疗专业的判断只是障碍评估的的一部分”(王国羽、林昭吟、张恒豪主编,2012:97)。以就业观点为例,医疗模式的观点下,障碍者的“异常”被认为是劳动参与的主要障碍,必须透过医疗康复或职能训练加以矫正,以符合劳动市场的人力需求的标准(王国羽、林昭吟、张恒豪主编,2012:164)。对于残障者的就业议题,医疗模式的视角下,能否就业取决于残障者自身,雇主是否提供就业岗位以及政府是否有义务消除障碍并没有积极的义务要求。
(二)社会模式
20世纪70年代,英国反隔离身体残疾联盟(UPIAS)的活动家开创了英国残障运动史的开端。经由Mike Oliver等人对理解残障的阐释,不但被学术界所肯定,而且成为检验英国残疾政策、区分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标准。残障的社会模式成为一个强势的范式。其观点可以归结为简单的口号:“残疾来自于生活而不是来自于身体”。社会模式对于残疾政策以及残疾人自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某些政治策略消除障碍而不是局限于具体的医疗手段,引起社会变革是社会模式的行动方向;传统的医疗模式观点认为残疾问题来源于身体的缺陷,社会模式则认为问题来自于社会的压迫,新的观点无疑都有助于残疾个体的解放(汤姆·莎士比亚、尼古拉斯·沃森,2001:8-9)。
范式之转换的实际影响体现在政策价值基础的转变,具体在立法(第四章)、医疗(第五章)、劳动就业(第六章)、社区照顾(第七章)、特殊教育(第八章)、无障碍环境(第九章)、性与性别(第十章)等方面来说,台湾残障立法经历从慈善向权利的过程;残障医疗与健康照顾需要政策利害关系人的合作、高品质的服务提供以及障碍人士的参与;残障者在目前的竞争性生产体制中获得工作机会实属不易,障碍者的工作与就业需求的满足,需要在政府的政策推动下,企业、非营利组织与社区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障碍者自主选择、主导服务的机会和空间是推动障碍者社区生活的方向;特殊教育的意义需要重新思考,尽管特殊教育去特殊化有争议,但推动教育的回归刻不容缓;无障碍环境常常与障碍者具体的体验相关,因而障碍的解决方式应该是提供身心障碍者多元的选择;身心障碍者有正常的情欲需求,却容易形成社会的边缘人,残障者的性与性别议题应该被正视。
(三)医疗与社会模式之外
社会模式的基本假设以及局限性需要重新审视(汤姆·莎士比亚、尼古拉斯·沃森,2001)。英国的残疾社会模式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残损和社会意义上的残疾之间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极端的社会模式否认残损问题,拒绝降低残损的可能性和益处。残损具有社会原因,但无法解释由于先天因素、偶然事件的而导致的残损。而且残损与残疾之间的二元对立,遮蔽了由残损到残疾的社会过程。因此莎士比亚和沃森(2001)建议要超越英国残疾模式,首先要打破残损和残疾之间的对立,而是一个连续谱,残疾是一个包含生物学、心理学、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复杂概念;其次,残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生理局限,而不是仅仅被定义为残疾人的那部分群体,因此残障研究更应该揭示残损和其表现形式之间的本质联系,这些本质联系的形成过程就是社会排斥和歧视的过程。
《障碍研究》倡导超越社会与医疗模式的对立,强调障碍是一种普同经验,认识残障的视角应该回到身体经验,采用生理、社会、环境的互动模式(王国羽、林昭吟、张恒豪主编,2012:64—65)。同样以就业为例,在此种观点下,障碍的就业的确受到个人残损的障碍,同样如果社会不提供某些支持,就业困境会加剧;但更全面、真实的现实是,“障碍者就业,不仅在于就业机会的获得,更需要仔细分析其身心功能状态与职场环境的互动,进而调整适性的工作机会与提供就业支持”(王国羽、林昭吟、张恒豪主编,2012:168)。强调残障作为一种普同经验①国内也有研究者提出“常态化”模式以与医疗模式和社会模式对应,其基本观点是残疾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尤其可能伴随着老年的功能老化而成为残疾人(尚晓援,2013:导言)。正如作者所言,此种观点还有待于理论化。无论是常态化模式还是普同经验的论述,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政策实践导向。然而,与医疗模式和社会模式相比,笔者认为这两种论述都缺乏本体论上的明确阐述,因而也难以从范式层面上与之并列。,也是一种有别于医疗模式与社会模式的残障论述,而且在无障碍设施的设计理念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美国医疗社会学者左拉(Zola,Irving Kenneth)通设计的理念(王国羽,2015)。
三、残障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法选择
有意思的是,国内努力在残障研究中开拓新出路的主要依托是法学学科。与欧美、台湾不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残障研究主要分布在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等学科。正如前面所交代的,法学介入残障领域的研究,首先是以人权为突破口,从平等、正义等基本的价值出发,指出残障群体的权能不足,因此从法律(首先是建构法的精神之现实体现者——法律条文)角度确认、保障残障群体的权利就一直是法学发挥干预现实作用的方式。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掌握某种理论视角与价值偏好之后,进入具体的残障权利领域,识别存在的问题,虽然顺理成章但也不是没有问题②借鉴日本人类学家栗本慎一郎(1979:78-79)的观点,接受某一假设后,具体的“实证”研究只是寻找证据的证实性问题。。借鉴和深化不同学科的残障研究,法学的、社会学的、教育学的、经济学的、文学的等等学科视角,都是有待挖掘的学术资源。
(一)研究视角的选择
对于目前大陆的残障研究,研究者所面临的立场选择与社会情境更加复杂,首先面临的就是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③一些学科往往把此类问题归在“本土化”议题之下,到目前虽然鲜有研究者强调残障研究的本土化,但面对残障权利倡导或权利不足的中外实践对比时,往往能够从挫败感中面对差异。从一般的人权角度出发,提出别人拥有的权利我们也应该拥有,固然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但也忽视了社会情境的差异,而情境的差异恰恰是行动策略选择和政策走向的影响因素。。本文所讲的研究视角,系指主体(谁来做残障研究)与客体(残障研究的对象)的匹配。图1是笔者建构的残障研究视角的理想类型①这一理想类型的提出意在指出研究视角的具体维度,有助于具体反思研究的立场和形成自觉的研究。研究视角的取义受张恒豪(2014)的启发,不同的是本文从两个维度建构四种理想类型。这些围绕残障的视角各有利弊长短,具有不同的功能。当然,这些视角及其功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且具体的研究可以具有多重功能。随着残障者权利意识的觉醒,残障者从事研究的情形已不是个例。欧美以及港台不乏进行残障研究以及倡导的姣姣残障者,国内亦是如此。他们的研究首先是其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本身也是知识生产和文化再现的过程,更有可能导向权利倡导。在越来越多的残障者进入权利倡导和研究领域后,相信随之而来的残障者与非残障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更多讨论,这涉及到残障研究的方法论,E.Stone和M.Priestley(1996)认为非残障的残障研究者在研究时应扮演寄生物、马前卒和伙伴的角色,并在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解放(emancipatory)意义的研究范式。,之所以将研究者是否为残障者作为重要一维,在于残障这一身心状态已然成为理解残障区别的原因来源;残障研究的对象是否为残障者,重在强调研究对象的主体性。Inside-in的视角:遭受某种障碍的人研究(表达主体)的经验,这种研究的功能在于形成障碍者的自我认同;Inside-out的视角:研究者为障碍者,研究的对象主要在于非障碍者对障碍的研究,此类研究的直接功能在于权利倡导;outside-in的视角:非障碍者对障碍者的研究,突出障碍者的主体经验,功能在于障碍的文化再现;outside-out的视角:非障碍者对障碍研究的研究,不直接以障碍者为研究对象,功能在于客观知识的生产。

图1 .残障研究视角的理想类型
理解残障研究的视角,不仅仅在于能够细致地划分残障研究,更在于自觉了研究视角后,拓展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例如,《我国残障儿童受教育权保障的检视与反思》,采用的视角属于Outsideout的视角。白荣梅、王静开篇引出研究问题的话“2012年9月28日,深圳宝安区宝城小学19名家长联名写信,要求在该校就读的自闭症李某转学”(张万洪主编,2014:105)。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残障儿童通过随班就读的方式实现受教育权所遭受的障碍,随后该文利用实证数据检视了我国残障儿童受教育权的保障问题。如果采用outside-in的视角,那么实例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19名家长联名写信要求在该校就读的自闭症李某转学的行为就是一个邻避行动,从理性选择角度来说这些家长的做法并非没有正当性。至少来说,真正的融合教育,利益相关者应该知道“哪些是合适的行为”。在这样的视角下,追踪这个行动的始末,通过实证方法了解自闭症学生、自闭症学生家长、学校教师、其他学生家长以及其他部门的态度与行为,分析行动逻辑以及结果,也将是一个不错的研究。
残障者的权利是多元的,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残障权利研究更是涉猎广泛,张万洪所主编的《残障权利研究》(2014)从主题上关注了残障人的就业、教育、性与社会性别等,也从残障人角度探讨肢体残障、精神残障、视力残障等的权利。残障人的就业和教育向来是我国政府法律和政策实践的重点领域②例如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权益保障法》,之后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条例陆续出台,199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残疾人教育条例》,200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残疾人就业条例》,2012年颁布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这些条例的出台顺序反映了国家在残障权利保障的价值选择和政策优先选择。,也是研究的焦点所在。残障人的就业常常遭到各种障碍,因而就业率低以及就业质量不高。政府除了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其本身的作为同样具有示范意义。刘小楠、谢斌的《公共部门带头招录残障人士的实证研究及政策建议》,指出公共部门有责任和义务招录残障人士,这也正是国内外法律的共同要义。该研究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调查我国公共部门招录残障人士的现状,有力的展现了政府对招录残障人士的态度以及所作出的具体努力。虽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招录的残障人士的比例并不令人满意,但研究本身已经是一个残障权利确认与倡导的行动。冼志勇的《残障人就业权利法律保障体系若干问题探析》可以算是理解残障人就业困境的一个角度,法的制定与实施都值得深入检讨。残障人的就业不仅受到就业政策的影响,同样与就业之前的教育以及残障的家庭、学校等制度设置相关联。倪震的《为什么他们选择相同的职业:东市盲校的学生生活》揭示了视力障碍者的学生,在隔离的盲校中所获得信息以及信息的来源都是单一而同质的,“做一名合格的按摩师”几乎是所有围绕视力障碍者的主体对盲生的惟一期望,正是这样的制度环境让盲生从事按摩具有了路径依赖的可能。
《残障权利研究》(2014)除了关注我国残障社会政策已经干预的主要领域,更是从残障人士的具体权利出发对一些重要而相对忽视的问题进行研究,例如生育权、性权利。钱锦宇、任璐的《中国智力障碍者生育权的保护与限制研究》以outside-out的视角探讨智力障碍者的生育权,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基于法学学生对智力障碍者生育权看法的调查。智力障碍者常常是法律、政策的客体,法律上的权利主体资格也常常受到限制。倡导智力障碍者的生育权固然是一个方向,但受到的限制除了法律上的,本质上还有智力障碍者能否成为生育决策主体的问题。张金明等人的《脊髓损伤者生育权利现状调查研究》采用outside-in的视角了解了脊髓损伤者的生育需求及影响因素,他们普遍具有生育子女的愿望而且具备生育能力,但获得专业的服务却相当欠缺。
(二)研究方法的尝试
残障研究和权利倡导需要有效的方法“讲故事”、“讲道理”,有力的证据是揭示残障权利受损背后的文化偏见、政策偏差、制度设置等障碍的指引,而跨学科的尝试和多种叙事的方法可能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选择。《残障权利研究》(2014)把突出实证性作为研究特点之一,强调研究者“深入‘田野’,直面真实世界,关注残障人权利实现的迫切性问题”。因此,研究的重点在于残障权利的实践,而非残障权利的规范分析。从资料收集的方式上,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广泛使用;研究方式方面,偏向于定量的调查研究以及偏向于定性分析的民族志、现象学也成为残障研究方法的尝试。
倪震的《为什么他们选择相同的职业:东市盲校的学生生活》,探讨盲生与特定职业(按摩)的匹配,理解为何盲生把“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按摩师”作为职业期望。作者并未将之视为盲生的职业选择倾向,而是将盲生普遍选择按摩作为职业这一社会事实置于产生该事实的具体场域中。作者选取了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作为研究突破口,信息是进行决策的依据和基础,而单一的信息已经让盲生选择按摩只能是最终的、惟一的选择。民族志的观察方法带领研究者走进盲生的生活世界,隔离教育政策对盲生职业选择的影响增进了研究者的理解,虽然没有提出一般的政策或解决建议,但相信读者能够从中读出引申出政策干预的方向。陈亚亚的《女权与残障:基于身份政治的思考与观察》,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探讨残障女性的生存现状和身份认同,访谈残障女性是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和落脚点,同时也兼顾了文献分析、机构走访、网络在线观察和访谈相关从业者。从方法上保证残障女性是主体,但又与其他主体系统相联系。尽管将女权主义引入残障议题并无定论,但把性别视角引入残障议题却是需要的。马志莹的《因爱之名,以医之名?从权利角度看精神病院住院女性的体验》,则直接关注残障女性的生活体验,利用2010~2012年3个暑假对一个精神病院的参与观察所得的数据分析精神病住院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微观实践。既为我们展示了医疗模式的残障观的具体表现,也可以看到残障权利在参与者之间的拉锯、斗争与转移。可见,残障者的权利倡导单以法律的力量并不充足,需要的是权利系统中行动者的共同自觉和努力。其他的研究者都尝试采用实证的方法,关注具体的残障权利实践,这种尝试有助于理解残障权利实践的历史脉络,能够促进研究视角、理论之间的对话。
四、迈向自觉的研究与行动
(一)关注残障者的主体性
《障碍研究》和《残障权利研究》都强调残障者的主体性。从研究的视角来说,inside-in和outsidein的研究是努力的方向。激进的视角——没有残疾的人不会做与残疾有关的研究——虽然否认了残障者与非残障者之间理解的可能性,但也极力强调了残障者自身的日常生活体验,而且鼓励予以表达,这种体验的表达者正是他们自身。
但也应该看到,过度关注某一具体做法,就可能会忽视本土实践的历史脉络而陷入去背景化的认知模式,这无疑会影响倡导目标的设定和倡导策略的选择。如果要承认经验的历史性,要超越经验与理论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则关键在于经验与理论的紧密连接。通过残障的实践历史连接理论与经验,“连接理论,便有可能超越经验的简单描述性、回顾性和纯特殊性;同时,一旦连接经验,便会承认理论的历史性,避免其超时空的绝对化或意识形态化”(黄宗智,2007)。
通过经验研究辨识隐含的残障理论及其建构过程,可能是我国残障研究获得主体自觉的一个选择。例如虽然我们正在使用“医学模式”概念及理论,这是与西方的对话中确立的话语范畴。在我国残障领域的实践中,是否具有其他的模式或者怎样体现医学模式,并没有深刻的挖掘①马志莹的《因爱之名,以医之名?从权利角度看精神病院住院女性的体验》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了比较好的探索。。如果理论的建构过程缺乏经验的支持,那么要实现经验与理论的连接,就需要深入实践进行研究,以避免仅仅以“学术上正确”的观点进行研究。比较而言,西方的残障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尽管也是多学科的研究领域(Research Field),但享有关于残障范式的话语体系。直接以残障(或者残障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残障研究,更具有一个学科的取向(虽然多数研究处于社会学的视角之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残障被视作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残障研究宣称一种“新”视角,虽然摆脱不了旧有的模式,但表面了获取残障主体的努力(Titchkosky,2000)。在21世纪的前后几年里,如何理解残障正在经历着医疗模式与社会模式的相互作用。社会模式的提出与发展,显然也受早前有关残障的社会学研究从微观转向宏观的呼吁有关,把病态角色(Sick Role)、异常、态度、人际关系等概念作为“有用概念”(Useful Concepts)的微观社会学分析,更像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取向,而忽视了诸如社会结构、社会控制等维度的宏观分析(Bynder and Kong-Ming New,1976)。虽然这是40年前的呼吁,至今仍然能够为我国的残障研究提供一个反思的维度,即残障研究本身也不应该是可以忽略的反思对象。而理解那些“有用的”概念,仍然是有用地第一步。
(二)研究主体在理论和立场上的自觉
残障理论视角选择的自觉,增强范式的文化敏感性,除了强调残障者的主体性外,研究主体的自觉同样重要。残障理论与立场的重要性除了体现在观察残障的基本视角,更是引领残障研究的的起点,正如奥尔特曼(2001:70)所言:
“残疾的理论模型的意义在于它是该领域真实世界的抽象概括,在广泛的基础上定义了主要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受具体经验和细节的干扰。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和思考概念及其关系的空间,摆脱了细枝末节问题的干扰。然而,要使用理论观点,也就是将其应用在日常社会中,就需要对存疑的现象进行经验性解释。要缩小概念范畴,对形成理论的概念进行定义是第一步。在社会中,同一个概念可能由于观察者角度的差异有多重定义。一旦选定了一种定义,具有无限的具体特性的理论概念与现实的经验性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就形成了。”
这大概也正是Mike Oliver强调残障研究应具有解放性质的缘由。理论视角的选择是经验研究的指引,如果借用福柯关于微观权力实践的思想,那么理论本身也是建构残障现实一种力量,所以残障研究者辨识不同理论的价值假设与策略选择就是必要的。在目前的中国,残障者进入接受高等教育依然困难重重,但越来越多的残障者获得权利意识,已经出现一批身为残障的残障权利倡导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具有反思意识的残障研究者出现。英国的残障权利运动中,以社会模式为理论指导,离不开肢体障碍的残障研究者的身体力行。视力障碍的French,Sally也从不抹去自身作为视力障碍者的角色(French and Swain,2002),而她对视力障碍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对于我国的残障研究者来说,也值得细细体味。
(三)自觉的行动:弥合研究与倡导、实务的鸿沟
要有自觉的理论选择和研究取向,倡导实证导向的经验研究是一个现实选择。而跨学科的研究实践,合作研究就是必要的策略,也是建构学术共同体的要求。当然,合作研究并不简单(布斯等,2009),这也为编者所承认。以学术会议为依托,借助于研究项目培育合作的可能性,已经是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的努力方向。
苏峰山(2014)指出“障碍研究并非单纯的学院研究,障碍研究从一开始就深受障碍者运动所启发,也同时影响障碍者运动的方向”,道出了残障研究与权利运动的密切关系。为了相同的目的,国内残障研究者与行动倡导者(NGO)之间的接触越加广泛和紧密。残障权利的实践发展对理论指导具有迫切的需求,厘清残障研究是什么以及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并形成一些共识以桥接理论与现实的鸿沟。经过30年的发展,台湾的残障研究已经发出了走出西方框架的呼声。例如,西方残障观的发展经历了隔离、大规模机构化的过程,而台湾并没有机构化的历史,利用西方“普适的理论”理解台湾经验就会遮蔽多样的现实(王国羽、林昭吟、张恒豪主编,2012)。这对我们的启示就是,残障研究有必要与正在进行的残障实践领域保持紧密的联系,研究者与行动者虽然不可混为一谈,但缺乏实地调查的残障研究就会有落入“抽象经验主义”(米尔斯,2012)的危险。实现研究者与行动者之间的链接与转换,实际上也暗含在目前诸多的研究项目、行动倡导之中。
五、小 结
在残障事业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残障权利的实现以及残障研究都面临转型。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治理理念的推行以及残障权利意识的提高,对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提升残障研究的质量是一个艰辛而又迫切的过程。鼓励跨学科、多学科的残障研究向这一目标靠拢,当然,研究者也要避免放弃个人所长去尝试其他学科的理论或者方法,避免用跨学科的话语遮蔽了视角的多样性,以致缺乏专业视角下的问题意识和脉络梳理。如果缺乏实证的社会事实的描述,跨学科的研究就会流于一般性的分析说明和经验描述的碎片化。
强调残障研究的主体性,就要回到残障本身,探讨残障的产生(以及随社会条件的变迁)、残障面临的问题及原因、解决残障群体面临问题的政策实践等等这些“基础性的研究”,残障的身份、过程、体验以及残障群体内部的异质性都需要进一步的重新认识。如果说“人权理论探讨的并非事实,而是应然权利”(张光杰,徐品飞,2004:24),那么新的视角的研究则应该转向法的实践、政策的实践、理念的实践。明确论述残障的多元范式,首先要理解这些范式既有时间上的历史演进,也是相互竞争的模式,也就是要看到具体模式的内在不足以及适用性,每一种模式都促使其它模式重新审视它们关于残疾的假设以及方法。残障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从多学科的多元视角开拓残障研究,系统地在我国有关残障的以往研究、文化观念、政策实践的历史中,挖掘残障研究的资源,并推动残障权益保障发展,既是当代中国残障研究者的责任,也是其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1]芭芭拉·M.奥尔特曼,2001,《残疾的定义和操作化,以及在调查数据中的测量:一个更新》,载巴尼特,奥尔特曼编,2013,《残疾理论研究进展及学科发展方向》,郑晓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2005,《以权利为基础促进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黄宗智,2007,《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开放时代》第4期。
[4]卡罗·沃克尔(Carol Walker),2006,《社会政策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载杨团、关信平主编,《当代社会政策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5]赖特·米尔斯,2012,《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第3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李学会,2015,《残疾人的社会形象:对历次残疾人“全国自强模范”事迹的分析》,载张万洪主编,《残障权利研究·2015夏季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李学会、傅志军,2015,《从隔离走向融合?——我国视力障碍者高等教育的历史、特点及政策变迁》,《社会工作》第6期。
[8]栗本慎一郎,1997,《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9]刘侠,2004,《侠歌长流:刘侠回忆录》,台北:九歌。
[10]邱大昕,2011,《谁是身心障碍者:从身心障碍鑑定的演变看“国际健康功能与神细心障碍分类系统”(ICF)的实施》,《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第2期。
[11]邱大昕,2013,《谁是盲人:台湾现代盲人的鑑定、分类与构生》,《科技、医疗与社会》第16期。
[12]尚晓援,2013,《中国残疾儿童家庭经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苏峰山,2014,《障碍的社会存有论:障碍研究模式之解析》,《残障、权利与正义年度大会(2014)论文集》,武汉大学。
[14]汤姆·莎士比亚、尼古拉斯·沃森,2001,《残疾的社会模式:一个过时的意识形态?》,载巴尼特,奥尔特曼编,2013,《残疾理论研究进展及学科发展方向》,郑晓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5]托马斯·库恩,2012,《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6]王国羽,2005,《缺了一角的台湾社会研究:障碍经验的社会学讨论》,台北:“2005台湾社会学会年会暨研讨会”,(2005年11月19日~20日)。
[17]王国羽,2015,《障碍研究论述与社会参与:无障碍、通用设计、能力与差异》,《社会》第6期。
[18]王国羽、林昭吟、张恒豪主编,2012,《障碍研究:理论与政策应用》,高雄市:巨流出版社。
[19]韦恩·C·布斯、格雷戈里·G·卡洛姆、约瑟夫·M·威廉姆斯,2009,《研究是一门艺术》,陈美霞、徐华卿、许甘霖,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张光杰、徐品飞,2004,《人权是什么?——三种阐释与一个回答》,载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编,《复旦人权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1]张恒豪,苏峰山,2009,《战后台湾国小教科书中的障碍者意象分析》,《台湾社会学刊》第42期。
[22]张万洪主编,2010,《我们时代的人权:多学科的视角》,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3]张万洪主编,2014,《残障权利研究: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4]Campbell,Fiona Kumari.2009.Medical Education and Disability Studies.J Med Humanit,30,pp.221-235.
[25]French,Sally and Swain,John.2002.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abled People's Movement.In: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Work.Blackwell Companions.Blackwell,Oxford,pp.394-400.
[26]Herbert Bynder and Peter Kong-Ming New.1976.Time for a Change:From Micro-to Macro-Sociological Concepts in Disability Research.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Vol.17,No.1(Mar.),pp.45-52.
[27]Stone,Emma.and Priestley,Mark.1996.Parasites,Pawns and Partners:Disability Research and the Role of Non-Disabled Researchers.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7,No.4(Dec.),pp.699-716.
[28]Titchkosky,Tanya.2000.Disability Studies:The Old and the New.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Cahiers canadiens de sociologie,Vol.25,No.2(Spring),pp.197-224.
[29]Norma Leclair,Steven Leclair,and Christopher R.Brigham.2009.The Medical Model of Impairment.In S. Goldstein and J.Naglieri(eds.),Assessing Impairment:From Theory to Practice,Springer:pp.59-75.
编辑/杨恪鉴
基金项目:瑞典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与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合办的“中国残疾人研究”(第二期)。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6)03-0064-011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6.0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