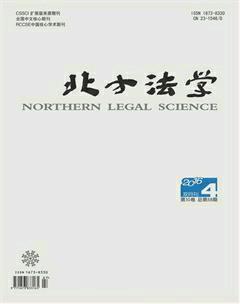《刑法》第1条:刑法的具体概念与根本原则
摘 要:刑法学应当立基于刑法的具体概念而不是抽象概念。刑法概念具体化的法条依据是《刑法》第1条。学界不把该条作为刑法的概念问题而是作为刑法概念之后的刑法根据来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刑法概念具体化的理论进路在于找到刑法内容的两个来源,明确宪法作为两个来源及其关系之根据的意义,并全面理解刑法的两大功用。《刑法》第1条的理论地位是刑法学的基石概念,其规范地位则是刑法根本原则,可名之曰“刑法正义原则”。根本原则统摄两大基本原则:第2条的法益保护原则和第3至5条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根本原则的司法实践要讲司法逻辑,控辩审对《刑法》第1条的落实各有其功能。
关键词:抽象概念 具体概念 刑法根本原则 司法逻辑
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4-0084-10
刑法教科书阐释刑法的概念一般采取“刑法是规定……的法律或法律规范”的方式,①这可谓是刑法解释共同体所获致的最大公约数意义上的共同语言。然而,这只是定义了刑法的抽象概念,并不是刑法的具体概念。正如拉伦茨所言,法学或法教义学是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的。②刑法学自然不例外,所以刑法学需要的是刑法的具体概念,如果满足于抽象概念,并以之为基石建构理论体系,那么至多只能形成一个抽象概念式的体系,即拉伦茨批判的那种“外部的体系”。③因此,刑法解释共同体应该谋求刑法的具体概念的共识。
一、刑法概念具体化的法条依据
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的区分是黑格尔提出来的。黑格尔认为不包含任何具体内容,没有任何差别的自我同一的概念就是抽象概念,它是形式逻辑下的概念。具体概念则是辩证逻辑下的概念。④任何一个具体概念,都有一般、特殊、个别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揭示了概念的辩证运动,体现了思维的辩证发展。抽象概念仅仅代表着具体概念中“一般”这个环节。具体概念并不是对抽象概念的简单否定,而是通过扬弃抽象概念,使概念从一般经由特殊上升到个别,从而使概念达到思维中的具体,使作为概念体系的理论达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由于“外部的体系”中最一般的概念,其意义空洞化极为严重——因为抽象概念的抽象程度越高,内容就越空洞,拉伦茨赞同在外部体系之外另行构建由法律原则及其具体化所组成的内部体系,这种内部体系是借助于“规定功能的概念”而实现的。在此,拉伦茨没有采用具体概念这个用语,以避免黑格尔的观念论世界观,但强调“规定功能的概念”不是抽象概念,它与黑格尔所谓具体概念具有相似功能,即它们都关切因形成抽象概念所采取之孤立化方法而被切断之意义脉络。参见前引②,第332、333—335、348、355页。 笔者认为,回避黑格尔的观念论是正确的,但连具体概念这个术语一起否弃则不应该。与抽象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具体概念;对具体概念一词,不需要完全在黑格尔意义上使用,正如也可以不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抽象概念一词;如果回避具体概念一词,会导致否定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区分本身;从文字经济性而言,具体概念一词也比规定功能的概念一词更简约。根据辩证逻辑,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不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概念,而是同一概念的不同逻辑阶段,所以概念从抽象概念上升为具体概念也发生在同一理论体系的同一逻辑过程。所谓法学的外部体系与内部体系是对概念辩证运动的否定,同时也是对理论体系(法学)与规范体系(法律)的混淆。所以,本文不采用规定功能的概念一词,而使用具体概念这个用语。
刑法学主要是对特定法秩序下的刑法问题进行体系性解答,其不同于个别性解答的功能在于解答的深刻性和融贯性。参见[德]N.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罗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刑法的具体概念是刑法学的基石概念,基石概念不仅以浓缩的方式蕴含着作为整个学科体系构建材料的信息,也具有决定整个学科体系如何展开的方法论功能。参见刘大椿:《科学哲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4页。 “一旦定义形成,为适合定义而被裁剪的事件以及起初的心理事实变为活生生的事实。正是这一现象使得定义如此重要而又如此危险,它们提供了对法律世界集中的解释,但又排除了瓦解这一定义的可能性”。[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因此,刑法的概念必须反映我国实定刑法的存在,即我国的而非外国的、当代的而非它代的、现实的而非想象的刑法,亦即必须成为我国刑法的具体概念,才堪当我国刑法学的基石,才能为体系化解答我国当下司法实践中的刑法问题奠定刑法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那么,到哪里去探寻这种具体概念的共识呢?《刑法》第1条为我们提供了法条依据,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是罕见的,我国刑法学应珍视该条,把该条作为刑法概念具体化谋求共同语言的出发点。理由如下:
首先,《刑法》第1条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实定刑法的存在性。《刑法》第1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自始以来,该条就是立法者用以表述刑法观的载体。参见高铭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所谓刑法观,在理论逻辑上就是刑法的具体概念问题。《刑法》第1条制定于1979年,修订于1997年,前后有重大变化,这些显见的立法史实反映了刑法的具体概念的发展。如果不去阐明这些重大变化的观念意义和方法意义,就无法获致刑法的具体概念,而只能使刑法学建基于刑法的抽象概念之上。
学界并没有把该条当作刑法的概念问题加以理解。刑法教科书一般将此条定性为“刑法的根据”即“制定刑法的根据”,认为包括宪法根据和实践根据两个方面,并在“刑法的概念”之后加以阐释,尽管它同刑法的概念问题一样也属于“刑法概说”的范畴。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前引①,第29页。 刑法教科书一般在定义刑法的抽象概念之后把该条作为立法史知识介述,随后在漫长的刑法学展开中再也不提该条了。这样一来,面向司法实践的刑法学体系就失去了依据该条对刑法的概念进行具体化的机会,此条的体系性地位和司法功能都无从谈起。以刑法的抽象概念为基底的刑法学,或许在许多个别问题上能够进行合乎我国刑事正义的解答,但这种解答难以具有深刻性,更何况其对我国特有刑法问题之体系性解答难有融贯性。
其次,是否在刑法的概念内阐述刑法根据,关系到对刑法根据的理解深度。“……的……”这种短语结构,表达了两个事物间的关系,但有两种关系非常不同:一是有如“我的杯子”,某个杯子虽属于“我”,但并非“我”的固有成分,丢掉这个杯子“我”还是“我”;二是有如“我的灵魂”,“我”与“我的灵魂”并不相互外在,丢掉灵魂“我”将不再是“我”。那么,当人们谈到“刑法的根据”时,实际上是在类似“我的杯子”的意义上理解“刑法的根据”。如果把刑法的根据看作刑法的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则会注意到刑法的根据与刑法概念的其他要素诸如刑法的目的、立法者的政策、刑法的形式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那么刑法的根据问题在其与刑法的概念之间构成的部分与整体的诠释学循环中将得到深入的阐释。而一旦把刑法的根据作为刑法的概念之后的问题来把握,则刑法的根据就像当下被对待的那样,成为一个孤立的知识片段,不可能被深入理解。
再次,将该条作为刑法的根据问题,也必然抹煞“根据”与“结合”的语义差别和语用功能。这在后面的讨论中会看得很清楚。
二、刑法概念具体化的理论进路
概念在思维之中运动,由抽象概念上升到具体概念。由刑法概念具体化这一显示运动的短语决定,如题所示的理论进路也充满动态性。
在刑法内容的立法表述上,《刑法》第1条的“结合”一词首先表现了刑法概念的运动。这是刑法的抽象概念走向具体概念的第一步。我国传统哲学方法论也强调运动变化,认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故万象虽“多”而皆有对,可名之为“两”;两不立则一不可见,因此讲“一”的往往只从“两”上讲。参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206页。 方法论的动态性,源于本体论的动态性。传统本体论认为,“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朱熹),“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朱熹),转引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825、826页。 “太极既为之体,则阴阳皆为其用”(黄宗羲)。转引自前引B11,第206页。
那么,刑法内容是由什么结合而成的呢?在方法论上可归为“两”。根据《刑法》第1条,其一是“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其二呢?该条在文字上付之阙如,是因为该条恰切地省略了主语。概言之,其二应归结为“立法者的刑法政策”,亦即“立法者的刑法政策”与“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相结合,决定了刑法内容的立法表述。
从语义逻辑上分析,“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包含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即我国官方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政策经验和政策需要)和我国民间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生活经验和生活需要);但从语用逻辑上分析,前一方面已为“立法者的刑法政策”所考量,所以,同“立法者的刑法政策”相结合的实际上是后一方面。在这种语用意义上,“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可化约为“刑法生活”这个术语。总之,是立法者的刑法政策与当代社会的刑法生活相结合,决定了刑法内容的立法表述。这里可以看到,立法上的“结合”只是结合过程的一步,因为立法上结合的阶段性成果只是《刑法》文本。在立法之后,即司法实践中如何活化这种结合,就进入了理论视域,留待后面探讨。
在立法结合问题上进一步动态考量,则涉及到刑法的生活性或生成性问题。所谓刑法的生活性或生成性,是指刑法的内容经由社会成员自发互动而形成之属性。应该说,任何刑法都不可能将刑法的生活性或生成性彻底剥离,但也无可否认,历史上许多时候刑法的生活性或生成性是被极大抑制的,从而刑法几乎只是刑事政策的工具。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没有刑法典,仅有的一些刑法规定正是这种单纯的政策工具。即便是1979年的刑法典,其刑法观也高度政治化,这表现为当时第1条中“结合”所涉专政和革命的具体经验等因素。改革开放将我国带入民主法制的轨道,主流刑法观渐渐发生了变化,这反映在1997年修订后的现行第1条中。最重要一点,就是顺应民主化进程,刑法内容重新回到生活基点之上。刑法内容之发生机理由计划和革命转向市场和生成,这不是对立法权的削弱,相反,是使立法权真正具有权威性的进步。当下,立法机关和社会成员借助发达的互联网而互动的立法前奏,表明现在的刑法主要是从生活的土壤中长出来的,而不是由政治的机器中造出来的。这恰是司法法律与政治法律的区别。[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造出来的东西与长出来的东西相比,一是前者简单后者复杂,人们对后者心存敬畏;二是对于造出来的东西,谁造的谁有发言权,但对于长出来的东西,人人皆可能有发言权。“指导任何人类群体的行为的具体知识,从来就不是作为一个稳定而严密的体系而存在的。它只以分散的、不完美和不稳定的形式,存在于众多个人的心智中,一切知识的分散性和不完美性,是社会科学必须首先面对的两个基本事实。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经常作为‘仅仅是人类心智的不完美因素而不屑一顾的东西,在社会科学中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事实。……相反的‘绝对主义观点,即知识,尤其是对特定环境的具体知识,仿佛是一成不变的和‘客观的,即它对所有的人都一样,这是社会科学中一些经久不衰的谬误的根源。”[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在司法实践中,辩方对于行为规范具有相当的发言权。刑法学应当关注支配被告人个人行为的观念而不是民众惯用的推测性观念,一旦满足于“平均人”这个典型的实证主义概念,参见前引B15,第219页。 就止步于“以平均人为对象的作为命令的决定规范”。参见陈家林:《论我国刑法学中的几对基础性概念》,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206页。 这种“平均人”只是抽象的存在,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一旦行为规范被抽象化即实证主义化,行为规范就必然被看作是刑法规定好了的,只须向公众单向度宣示、规诫、指引、指示的规范,参见王安异:《裁判规范还是行为规范——对滥用职权罪的功能性考察》,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4期,第118页。 而这里的公众、个人也就只是一种抽象,具体的社会成员就仅仅被作为行为规范的客体处理。因此,长出来的刑法预示着司法逻辑,而造出来的刑法则预示着执法逻辑。刑法学应及时反映刑法的生成性并尊重司法逻辑。
刑法生活和刑法政策参与刑法型构之前的法律过滤,以及两者被过滤之后互相“结合”的比重,都是宪法决定的。前面已然提及,“根据”不是“结合”。刑法教科书的传统解说把“根据宪法”看作刑法的法律根据是没错的,但把“结合……”看作刑法的实践根据就错了。“结合”的施动者与被动者在“结合”中是横向关系,而“根据”的施动者与被动者在“根据”中是纵向关系。宪法根据是立法者的刑法政策与现实社会的刑法生活及其相结合的上位概念,把“结合……”看做刑法的实践根据就犯了把刑法生活与宪法等量齐观的错误。宪法的精神是民主的精神和人权的精神。所谓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以防止少数人专制。故而,民主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宏观判断,一个人不能因为政府没有听他的就说不民主。所谓人权,是自由、平等等基本权利,人权对抗的是多数人暴政。故而,人权是一种个体主义的微观判断,一个人完全可以指摘民主政府侵犯了他的人权。根据宪法制定《刑法》,就是要体现民主与人权的精神。因此,要确保刑法生活在刑法型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控制性作用,要确保刑法政策在刑法型构中的抉择性地位和调节性作用。立法上的“根据”需要在司法中加以落实,这就是宪法的刑事司法化问题,留待后面探讨。
在立法根据问题上,也需进一步动态考量。这涉及到刑法规范的当为性与存在性的关系。在民主语境下,刑法的规范性不仅仅意味着刑法的拘束力,拉伦茨将规范性效力或规范性特质理解为拘束性。参见前引②,第132、78页。 还意味着刑法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事实。在“世界最大的刑法学输出国”德国,有存在论与规范论之争。争论焦点在于规范是由现实形成,还是规范只从规范中来。Roxin批判Welzel的存在论,但还不是彻底的规范论立场。因为对存在论的借鉴,始自19世纪的形式规范论演进到当今主流的实质规范论,即法益论。但形式的规范论依然存在。Jakobs即主张形式规范论,他认为法益是属于规范世界以外的存在世界,对于规范系统是不重要的。Jakobs坚持一元的、纯粹的、激进的规范论。Schünemann对之加以批判,指其为循环论证的法实证主义。Schünemann既反对一元的规范论,也反对一元的存在论,主张并存论。参见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4、6、7、8—19、25—27页。 笔者认为,既应区分当为与实存、价值与事实,又应将当为、价值统一于实存、事实,而不使其处于二元状态。唯有如此,才能说刑法规范按照宪法精神把刑法政策与刑法生活结合起来了。
具体而言,在当为、价值的意义上,规范是一种指令,即行为模式;在实存、事实的意义上,指令必须与特定社会事实相对应才能成为客观存在的规范。因此,规范是一种对应于大体上被社会成员所遵守、并被他们感到有约束力(有效)的社会事实的行为模式。制裁理论仅仅对这种遵从作了行为主义的外部观察,从而把规范的效力按照认知主义方式,理解为规范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客观力量。这种逻辑是不能为民主和人权理念所接受的。规范的约束力,来源于规范本身被行动者或旁观者内在地体验为有效,这种受约束的特殊体验在语言上以道义语词和短语来表现。规范被社会成员广泛感到有效,并不排除对实施违背模式之行为的人施加额外的有组织的制裁。制定法来自于立法权威,但立法权威所由来的最高权威必然以不成文法的形式存在。如果社会成员遵守立法的法律意识(形式的法律意识)与他们对正义的渴望(实质的法律意识)分裂了,立法不再被接受为有效,服从立法仅仅处于对制裁的恐惧,那么立法权也就摇摇欲坠了。参见[丹麦]阿尔夫·罗斯:《指令与规范》,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99—122页。 以上说明,对刑法生活的基本尊重与刑法政策的适度运用,是刑法规范的规范性和正当性的源泉。有学者认为,“由国家制定与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禁止人们实施犯罪行为、命令人们履行义务以免犯罪、指示司法人员如何认定犯罪和科处刑罚(包括免除刑罚处罚)的法律规范,就是刑法规范”。“犯罪后将受到刑事制裁,从而使一般人作出不实施犯罪行为的意思决定”。前引①,第30、31页。 这种刑法规范观不免有过重的行为主义外部观察意味。一般人之所以不实施犯罪,固然有害怕刑事制裁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对此种消极因素的比重不宜看得过重,因为一般人主要是因为对刑法规范的有效感才不实施犯罪的,古训说“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刑罚威慑对于预防少数潜在犯罪人犯罪才起主要作用。如果忽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刑法规范的当为性与存在性就无法统一起来。
立法者根据宪法,将刑法政策与社会的刑法生活相结合,以决定刑法内容,这是“制定”的意涵之一;另一意涵是把刑法内容通过《刑法》的形式加以表述。刑法的概念通过《刑法》的制定而从一般达到特殊,司法实践则把刑法的概念由特殊上升到个别,从而实现刑法概念真正的具体化。
《刑法》用在司法,就是第1条表述的“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由于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故《刑法》必须被看作是供控辩审共用的话语平台。所以,“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包括“为了惩罚犯罪”和“为了保护人民”两个方面。所谓“为了惩罚犯罪”,就是《刑法》的法益保护之用(“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刑法》第2条的法益保护原则用在此处,为控方奠定了话语平台。所谓“为了保护人民”,就是《刑法》的人权保障之用(“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第3至5条的罪刑法定原则用在此处,这为辩方奠定了话语平台。作为统一体的“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则用在裁判,从而为法官奠定了话语平台。
能否将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看作手段与目的关系?否。《刑法》之所以要保护人民,不是因为人民受到了犯罪的威胁或侵害,而是因为人民受到刑事权力的威胁。刑事追诉权甚或刑事审判权对社会成员的威胁,并不一定都构成犯罪,不能说只要其不构成犯罪就不需要保护人民了,更不能说只有在确定其构成犯罪之后才去保护人民。把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看作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实际上是把刑法错当作了行政法。
三、《刑法》第1条的规范地位
如前所述,在刑法学的体系中,《刑法》第1条是刑法的具体概念问题,刑法的具体概念是刑法学的基石概念(基石概念论)。这是该条的理论地位。但在刑法规范的体系中,则不能说该条是刑法的具体概念,有学者把法律概念、政策也看作法的要素(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笔者认为,它们是不能同作为法律规范表现形态的法律规则、原则并列的,因为法律概念是法学的要素,法律概念的语词载体则是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而政策或是政策性原则或是法律规范的一个解释依据。 而应说该条是刑法的根本原则(根本原则论)。这是该条的规范地位。对刑法的具体概念的阐释,为理解刑法根本原则提供了理论前提。黑格尔指出,具体概念是一种发生影响的、构建的、形成的原则,是一切生命的原则,因之同时也是彻底具体之事物。参见前引②,第334—335页。 只要去除其中的观念论成分,其关于具体概念乃是原则的思想有值得借鉴之处。相对于抽象概念的形式性和封闭性,刑法的具体概念是实质性和开放性;相对于法律规则的形式性和封闭性,刑法的根本原则也具有实质性和开放性。刑法学体系的实质性和开放性是对刑法规范体系的实质性和开放性的反映和阐释。这里的论述中至少有两个疑问仍须解答:
首先,原则是不是规范?有学者认为,“由于规范的内容是禁止做什么、允许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故刑法总则中的许多一般性、原则性规定(如《刑法》第1条、第2条),并不属于刑法规范”。前引①,第30页。 这反映了法学界的一个传统,即把规范与规则等同。参见《法学词典》编辑委员会编:《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18页;前引B24张文显主编书,第70页。 如果把法的安定性作为刑法的主导理念,参见前引①,第20页。 就易产生这种倾向。
规则是“对一个确定的具体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具体后果”的规范,原始时期的法律都只表现为法律规则。参见[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7页。 规则对于法律的基础性和重要性甚至以“共同谬见”的形式表现出来——“认为法律是一种让事实适应规则的机械体系,这是如此众多的外行人(实际上也有一些律师)对法律共同持有的谬见”。[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规则何以重要?是因为规则的社会功能在于最大程度地化简期望领域的复杂性和偶在性,把复杂性和偶在性的负担从意识中卸载下来。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191页。
但是,规则的局限性也正是在于对期望领域复杂性和偶在性的化简上。一方面,规则无视案件情境,不适应复杂社会的人性需求。古典时期后的罗马法就突破了规则体系,将衡平的概念广泛引入法定权利与义务之中,因此使一般法规的严苛得以缓和,体现了西方法律传统中“旨在使人性升华的法律改革的原则”。参见前引B30,第45—46、64页。 如波斯纳所言,规则的一个主要局限就是在解决纠纷的思维中屏蔽了纠纷的诸多潜在关联因素,于是适用规则时必定不考虑纠纷的具体情境,而这经常使规则的基础价值无法完美实现。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56—57页。 唯规则论是法律形式主义,其对于常规案件力能胜任,但对于例外案件则力所不及。如果一个国家的刑法规范观局限于唯规则论,则其刑法必然冷酷无情而难于满足对个案正义的人性需求。当下,我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就不能把规范与规则等同。另一方面,唯规则论抹煞了法律自身的活力,难以适应法律发展的需要。“作为一种活的社会制度的法律,适用中的法律,就如同社会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一样,是具体的、主观的和关乎个人的。”前引B30,第74—75页。 卢曼指出,在多变的复杂社会中,规范不稳定并非坏事,而是符合日常生活需要的规范性条件,同时也是法律发展的前提。每个社会都需要根据各自的复杂性程度为规范期望的充分多样性创建空间,把期望之间的矛盾以及对无处不在的冲突的容忍看成是社会系统的正常状态,甚至把冲突看成系统在过度复杂的环境下维持存在的前提条件。参见前引B31尼克拉斯·卢曼书,第91、78、100—101页。 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变化日新月异、目不暇接,法律不仅要维持现有秩序(稳定),也要促进秩序转型(发展),因此不能坚持唯规则论。第三,规则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遵循它,参见前引B33,第60页。 何况规则与规则之间的矛盾、冲突绝无法靠规则本身来解决。这在充满变化的改革时代尤为明显。
在当代复杂社会,“将法体系重构为不仅是法规则,而且是法原则之总体的法的结构理论,在论证理论上对应了强调权衡为一种突出的法律证立模式”。[德]乌尔弗里德·诺伊曼:《法律论证学》,张青波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不同于法律规则通常具有的“假定—处理—制裁”或者“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结构,原则“是一种用来进行法律论证的权威性出发点”。参见前引B29,第27页。 Schünemann就认为原则在刑法规范中被应用得比其他法领域广泛得多。参见前引B20,第17页。 法律原则通常具有主导性法律思想的特质,参见前引②,第353页。 它赋予法律规则以价值导向,决定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并为解决规则冲突提供价值基准。但法律原则能离开规则而直接适用吗?否。法律原则必须通过法律规则而实施,其方式有二:一是通过解释和适用规则而实施;二是通过处理规则的例外而以标准之形态实施。庞德把“标准”定义为“法律所规定的一种行为尺度”。并且他举例说,马车通过一条单轨铁道,火车的速度每小时30英里,此时“停下来,看一看和听一听”的规则是适用的;但在另一种场合,一辆重型卡车通过一条有四条铁路线的铁道,流线型火车的速度达每小时100英里,此时上述规则就不适用了,只好适用“适当注意以免他人受到不合理损害危险”之标准。参见前引B29,第29页。 在刑法规范中,也有标准现象。例如,故意杀人罪的刑法规范包含着“无正当理由不得杀人”的行为规范。参见陈子平:《刑法总论》(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页。类似的论述还可参见[美]保罗·H.罗宾逊:《刑法的结构与功能》,何秉松、王桂萍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211页。 刑法中所有行为规范其实都可作这类表述。它们由两部分构成:针对常规情境“不得怎样”的行为规则和针对例外情境“正当怎样”并不犯法的标准。“刑法规则使得人们干活时不必全副武装或保镖不离左右”,前引B33,第64页。 但在特殊情境下,杀人却可能是合法的。随着社会复杂性和民众法律需求的增加,特殊总是努力反对普遍,结果是规则和标准之间的界线模糊了。有规则就有特例,而标准就是要将特例处理制度化,就是要克服法律规则的情境不敏感性、冷漠的客观性;标准要求重视案件情境,要求获得实质正义。社会越复杂,受规制的行为越具流动性,规则之治就越需辅之以标准之治;在复杂而人道的社会里存在的法治只能是规则和标准并举之治。参见前引B33,第56—59、400页。 标准的副作用很明显,比如模糊性,但标准的副作用则是形式法治走向全面法治的必要代价。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作为形式正义的“校正正义”概念,比复仇更有助于实现公正,因为校正正义确立了司法正义不考虑个人特点之观念。但是,不能因此就一概否定个人化正义,校正正义只是从复仇到全面法治观念的进步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根据法官个人在案件中的利害关系来解决纠纷固然应予否弃,按照争议双方的个性、身份、外貌或其他个人特点而不是按照他们诉讼本身的非个人化的优劣来解决纠纷也为亚里士多德所正确地否弃,但是,以一种看来对案件特点最佳的方式,而不是运用一般规则来解决纠纷,从而得出的是实质正义而非形式正义,这是亚里士多德所没有触及的。波斯纳认为这是只要最大限度兼顾规则与标准就应予肯定和重视的个人化正义。参见前引B33,第392—398页。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要求的,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以标准为补充从而实施原则的法律规范综合体系。当然,标准越重要,法官的司法能力就要越高。参见前引B33,第399页。
其次,第1条是不是根本原则?在刑法学上,刑法原则一般被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两级,这值得商榷。刑法学认为《刑法》第3至5条表述的三项基本原则是最高的原则,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的内在统一性何在呢?必须存在高于这三项基本原则的根本原则,才能确保它们的内在统一性。这个根本原则,就是第1条表述的原则,可名之为“刑法正义原则”。当然,总则第一章章名并没有提及第1条,但这并不妨碍把第1条定性为刑法的根本原则(后面探讨)。在第1条根本原则的统摄之下,刑法的基本原则分为两翼:一翼为第2条,另一翼为第3至5条。第2条是保护性原则、追诉性原则、凸显政策性的原则,而第3条至第5条为保障性原则、辩护性原则、凸显公理性的原则。参见刘远:《论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 上面提到的两种统一性全在于第1条。第1条彰显了刑法之一“体”,第2条至第5条彰显了刑法之两“用”。这种一体两用的结构为以司法逻辑理解和架构刑法提供了前提,也合乎我国传统哲学关于太极为体、阴阳为用的本体论架构(后面探讨)。
这里要说明两点:其一,第2条何以称得上基本原则?常识认为第2条是“刑法的任务”,这并没有错,但“刑法的任务”只是该条的规范内容,并不是该条的规范地位。正如常识认为第3条的规范内容是“罪刑法定”,但要明确其规范地位,须加上“原则”二字。同理,第2条的规范地位是原则,即法益保护原则,这与说该条的规范内容是刑法任务并不矛盾。在原则—规则—标准这一刑法规范谱系中,第2条不是原则又是什么呢!可能有人质疑说,《刑法》总则第一章的标题分明是“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刑法的任务与基本原则之间以顿号隔开,规定刑法任务的第2条怎么会是基本原则呢?应该承认,此标题表述之初,立法者可能不认为刑法的任务属于基本原则。但这不要紧,因为立法者不能被视为一群特定的观念一经形成就永远不变的人,其应被视为一个组织体,该组织体的认知、意志、情感都在与时俱进,当需要赋予固有法律文字新的含义而文字本身又能承载时,立法者无需修改立法。因此,从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这种理念出发,完全可以认为刑法任务属于基本原则范畴,只是由于对刑法任务的强调才将其与其他基本原则单列。这在语言上也不存在障碍。例如,刑法学对《刑法》第22条犯罪预备就习惯于这样解释,认为“准备工具”属于“制造条件”,但“由于准备犯罪工具是犯罪预备行为最常见的形式,所以我国《刑法》第22条将其明列出来”,而“制造条件”就指“其他为实施犯罪创造便利条件的行为”。参见前引⑩高铭暄、马克昌主编书,第165页。
其二,第3至5条何以整体性地被定性为一个基本原则?将第3至5条总称为罪刑法定原则是合理的。首先,罪刑法定原则被公认为有形式和实质两个侧面,第3条着重于形式侧面,第4、5条着重于实质侧面。其次,许多大陆法系刑法学著作就只讲罪刑法定原则,并在罪刑法定原则之内讲平等和公正。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3页;[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补正版)》,钱叶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1页;前引B23大塚仁书,第67—74页;[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2页;[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80页。 再次,将第3至5条作整体性理解和把握可以避免不良后果。例如,学界关于法条竞合是否可以补充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问题,否定说强调罪刑法定原则高于罪刑相适应原则,肯定说强调罪刑相适应原则有时高于罪刑法定原则,这种讨论就把罪刑相适应与罪刑法定对立起来了;且不论孰是孰非,单说肯定说占上风时,有时可以不讲罪刑法定的观念就开始流行了,这种观念具有脱离法条竞合这个具体问题而泛滥的趋势,这对于法治实践是危险的。如果将第3至5条规定的原则统一为罪刑法定原则,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就不对罪刑法定原则构成威胁了。
四、刑法根本原则的司法实践
前面将《刑法》第1条所承载的刑法根本原则名之为“刑法正义原则”,那么刑法正义如何实现呢?这就要诉诸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的命题。不能简单地把司法法与行政法的区别归结为前者以法的安定性后者以法的合目的性为指导原理。参见前引①,第20页。 司法法处理的是诉讼双方和法官之间的三角结构,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正,而所谓公正首先意味着不偏不倚。法官的公正仰赖于“兼听则明”这一定纷止争的不二法则,而“兼听则明”本身就预设了纷争双方视角的差异和法官对分歧视域的融合。这不同于行政法。行政法虽然也追求公平正义,但行政执法毕竟主要是以行政机关的视角统制相对人的视角,“不由分说”的执法方式具有漠视视角差异的倾向;尽管当代行政法的实施也融入了一些司法化手段,如行政复议,但它毕竟不同于司法性的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无疑也只是行政法实施极为次要(至少在案件数量的意义上)的方式。而刑法的运作方式主要是司法方式,这决定了刑法规范应以司法逻辑的多重视域被理解和商谈。
在卢曼看来,法庭的双方当事人都援引对自己有利的规范,都运用合法或非法这个法律符码对已经发生的争议事项给予观察,这属于“一阶观察”;而审案法官要对争议双方所给出的已经内含合法或非法评价的对立规范给予二次评价,这属于“二阶观察”。法庭上当事人之间的唇枪舌剑,是社会各子系统从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领域不断向法律系统提交各种竞争性规范的过程,这里呈现的是各种社会规范之间在横向上的冲突关系,卢曼称之为规范的“社会维度”。法院要在之前的沟通(法条、先例、学说等)与当下的沟通(对案件的裁判)之间保持可联接性,呈现的是法律系统内部各种规范之间的纵向关系,卢曼称之为规范的“时间维度”。法律规范以程式的形式从人格、角色和价值中分化出来,并呈现出“如果……那么……”的条件形式,卢曼称之为规范的“事实维度”。卢曼指出,法律系统需要不断经历“变化—选择—稳定”的循环过程。社会维度上所呈现的规范之间的横向冲突提供了规范“变化”的契机,然后经过法庭程序这个处理“时间维度”的装置对竞争性的各种异质规范进行“选择”,最后以重新设置的条件程式的“事实维度”形式“稳定”下来。这个过程不断循环前进,就是实现“规范性行为期望的一致性一般化”这一法律功能的法律演化过程。教义学的学者们处于一个虚拟的法官视角来观察法官的观察,这种观察比法官的二阶观察具有更高的反身性,但其社会功能仍然是提高前后法律沟通之间的可联接性。参见前引B31尼克拉斯·卢曼书,第12—14页。
因此,刑法正义这一根本原则的司法实现要靠司法逻辑。这意味着:
其一,控方以刑事追诉政策对刑法进行解释性运用,其功能核心在于《刑法》第2条的法益保护原则的司法贯彻。在公诉制度下,控方属于政治权力组织,且不具有达致公正所需要的中立性条件,而是具有社会控制的行政思维倾向。法益保护是其行动动力,追诉政策是其行动指针,构成要件是其行动依据,与这三者相对应的,则分别是后果主义(或结果主义)、整体主义、形式主义。对于没有或者控方认为没有法益侵犯(包括威胁和侵害)的行为,控方是不会启动司法程序的。控方这种以法益侵犯评判为先导对案件事实进行的回溯性法律思考,即后果主义(或结果主义)。由于法益复杂多样且相互交织,后果主义常常导向整体主义。非法拘禁行为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如果是发生在截访过程中的,就像以往所显示的事实,控方往往置之不理,之所以如此,就是基于一种整体主义评判(即保护人身自由与维稳之间的权衡)。这表明,控方的整体主义评判的公正性是不可靠的,有赖于司法检视,而司法检视的启动者往往是辩方。不仅如此,控方所进行的后果主义、整体主义的评判往往是隐而不显的,而摆在司法台面上的则主要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如构成要件。控方的构成要件评判与其法益侵犯评判、政策考量是不可分割的,但前者相对于后者,无疑具有形式主义倾向。这意味着,构成要件问题、法定刑问题自然是辩方需要注意的,但更值得揭示的是,控方究竟是基于怎样的后果主义、整体主义评判而采取追诉行动的。
其二,辩方以生活中行动者的角色对控方的追诉进行反驳,其功能核心在于《刑法》第3至5条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贯彻。在司法过程中,辩方是以个体化的即作为孤立个人的社会行动者面目出现的,具有依据刑法生活进行辩解的思维倾向。真实的刑法生活世界的司法呈现有赖于辩方的过程主义、个体主义、实质主义的辩护行动。实践智慧是处理具体、可变的实际生活,从具体导至一般的善,它来自生活经验,并说明生活经验。参见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97页。 所以,辩护对于公正司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所谓过程主义,是指辩方还原行为人背景和行为环境等案件情境以对抗控方后果主义的话语方式,即便是以歪曲的形态加以还原。被告人常常会强调自己事发当时是怎么想的,或者由辩护律师加以表述。所谓个体主义,是指辩方根据个体生活思维来对抗控方整体主义的话语方式,这种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使刑法生活得以进入司法过程。科斯把“黑板经济学”转变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借助的就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因为其“交易成本”概念的出发点是生活语境中个体的人,这种方法论与哈耶克的认识论有同源之处。参见冯兴元:《科斯的遗产》;盛洪:《可惜他未圆中国之梦》;张维迎:《经济学革命者》;李韦森:《中国经济学家要让经济学回归正道》;陈斌:《交易费用看世界,产权界定最重要——悼罗纳德·科斯》;王玉霞:《“无论走多远,科斯是为我指明方向的人”》;肖耿:《在中国挖经济学的金矿》。以上文章分别载于《南方周末》2013年9月5日第14、16、17、18、29版。 所谓实质主义,是指辩方揭示控方隐而不显的价值判断以从基础上动摇控方形式主义判断的话语方式。这往往表现在辩方诉诸行为规范以检视控方的法益侵犯判断,诉诸定罪情节考量以抗衡控方的构成要件判断等等。
其三,法官在中立的立场上统合控辩双方的诉求,其核心功能在于实现刑法正义这一根本原则。通过将控方的视域与辩方的视域加以统合,在行为与后果之间、刑法生活与刑法政策之间、传统与未来之间、形式与实质之间、法益保护与罪刑法定之间进行调适,以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动态平衡。
Abstract:The criminal jurisprudence should be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its specific concepts rather than abstract ones. The provision basis to embody the concept of the criminal law is the First Clause of the Criminal Law. It is debatable that the academia interprets this Clause as the ground of the criminal law following the concept rather than the concept itself.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embody criminal concepts lies in seeking for two sources of the content of the criminal law, defi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itu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two sour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and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two funct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The theoretical status of the First Clause of the Criminal Law is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criminal jurisprudence and whose normative status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criminal law, which can be called as “the justice principle of the criminal law”.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governs two basic doctrines: one is the legal interest protection stipulated in the Second Clause and the other is the statutory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Clauses from the Third to the Fifth. Judicial practice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criminal law ought to abide by the judicial logic, and the prosecutor, the defendant and the trial also have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to perform the First Clause of the Criminal Law.
Key words:the abstract concept the specific concep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criminal law judicial logic
[作者简介]刘福元,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① [美]多丽斯·A.格拉伯:《沟通的力量——公共组织信息管理》,张熹珂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② [德]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