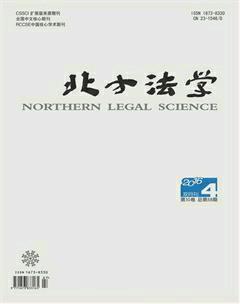刑事卷证与技术审判
牟军
摘 要:从证据手段在审判中的运用来看,以卷证为基础的欧陆主要法治国家的刑事审判可以界定为一种技术审判,而英美以口证为主要手段的刑事审判大致属于一种经验审判。我国普遍运用卷证的刑事审判也可归为一种技术审判方式,但由于对卷证的过度依赖、司法者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和刑事卷证运用的程序性制约机制的欠缺,导致我国技术审判的异化。当下推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非是对刑事卷证运用的根本否定,相反,为我国刑事卷证在审判中运用的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刑事卷证 技术审判 口证
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4-0124-14
刑事卷证是以文字为载体、以卷宗(证据卷)为形式所形成的证据材料。在我国,它包括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和起诉阶段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的陈述所制作的讯问(询问)笔录,实施侦查措施或行为过程的笔录,采集鉴定人的鉴定意见、调查过程收集的各类原始书证等系统化的书面证据材料。长期以来,“刑事法官普遍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展开庭前准备活动,普遍通过宣读案卷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法院在判决书中甚至普遍援引侦查人员所制作的案卷笔录并将其作为判决的基础,因此,中国刑事审判中实际存在一种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裁判模式”。①在我国主流学界,对案卷笔录(卷证)的运用向来持排斥或否定态度:卷证作为一种主要证据形式在法庭内外的运用,使得庭审流于形式,严重损害审判应有的独立性,有悖于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整体性的角度看,对于当代中国刑事卷证实际运用的评价又需采取客观和谨慎的态度,既要对从西方引入的主流诉讼价值观加以关注,也需对中外司法制度及其具体实践加以考察。鉴于此,笔者拟从两大法系不同证据手段的运用与刑事审判的内在联系角度出发,揭示两大法系展现的不同刑事审判风格,以此分析对刑事卷证的运用有着共同“情结”的欧陆和我国在刑事审判风格上的异同,以及我国司法改革背景之下刑事卷证的命运及可能的制度安排。
一、欧陆的刑事审判:一种实际运用卷证的技术审判方式
在我们已有的认识中,传统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审前形成或制作的案卷材料(尤其警察侦查制作的卷证材料)是被排出在刑事审判之外的,这主要源于欧陆所奉行的直接言词原则。德国学者罗科信教授认为,言词审判主义是指只有经由言词(一般而言指用德语)所陈述及提及之诉讼资料方得用为裁判之依据。[德]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 达马斯卡也认为,直接原则要求裁判者应当直接接触他据以作出判决的证据材料,所有合议庭成员都需听取证据,证人要亲自到庭作证。[美]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魏晓娜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从对该原则的上述释义看,言词原则与直接原则相近,在欧陆学理的表述上主要以直接原则来涵括。直接原则的精神实质在于裁判者应当亲自聆听原始证人的口头陈述,而不可用案卷材料等庭外书面证据代替证人的口头陈述,更不允许将这些书面材料作为最终裁判的依据。
然而,在传统欧陆主要法治国家,早期刑事司法强调充分性理由所形成的庭审直接言词原则,与逐渐兴起的现代资产阶级自由心证原则的普遍推行产生冲突。达马斯卡认为,所有的可采性规则——对于第二手材料的证明价值问题,预先作出了否定性判断——在本质上就是荒谬的。在某些情况下,传闻证据可能比原始的口头证言更可信。前引③,第273页。 正是基于证据材料证明力不应由法律规则预先加以规定,而应由法官自由判断并加以利用的务实理念,参见前引③,第272页。 当代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在法律实践中对庭前形成的案卷材料采取了较之英美法更加灵活甚至更为宽容的态度。
一方面,就案卷材料的移送及庭前准备来看,以德法为代表的欧陆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均明确规定检察官向法院提起公诉时应一并将侦控阶段形成的案卷材料移送给法院。对于移送案卷材料的条件和所涉及的案件性质及类型并无具体限制。法官在庭前通过阅卷实际为庭审调查做了准备,并对法庭的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产生“预先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案卷材料在刑事庭审中的运用来看,在法国,犯罪案中占绝大多数的轻罪和违警罪案均是庭审法官使用审前案卷材料(包括警察卷宗)的基础上对案件迅速加以处理的。Bron Mckillop, Readings and Headings in French Criminal Justice; Five Cases in the Tribunal Correctionnel, 46Am J Comp L 757(1998) 转引自左卫民:《刑事诉讼的中国图景》,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28页。 在德国,适用刑事处罚令处理的案件,检察官移送卷宗,法官在阅卷的基础上对案件进行书面审理。而对于普通刑事案件的庭审,案卷材料也可在一定限度内使用。从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包括法官预审中形成的庭前各类案卷材料,在庭审中可以作为印证、弹劾庭上口头陈述,抑或作为证人恢复记忆的证据材料加以运用。另外,在分段式或渐进式庭审中对案卷也可运用。德国学者约阿希姆·赫尔曼以一个模拟案件审理为例,论述了德国分段式庭审间隙中控辩双方可在法官主持下就案件处理方式和结果进行协商,或在接下来的庭审前主审法官可进一步研究案卷材料的情况。参见[美]弗洛伊德·菲尼、[德] 约阿希姆·赫尔曼:《一个案例 两种制度——美德刑事司法比较》,郭志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277、343页。
从上述情况看,在欧陆主要法治国家,案卷材料并不是作为口头审理方式的一种例外加以运用的,这与其秉持的直接言词原则存在较大反差。案卷材料庭内外的运用对欧陆刑事审判产生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入的。在司法实践中,将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刑事审判界定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书面审判方式并不为过。
达马斯卡曾就欧陆裁判者的司法操作演进历史与卷证运用的关系指出:“他们逐渐惯于在井然有序的文件的基础上来进行决策,这些文件过滤掉了可能营造出决策中的回旋余地的、‘杂乱的情境性和个人性细微差异。”[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由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卷证叙事的严密性和条理性,以及卷证所产生的“知识积累”效果,由于文字记录的方式和条件所受限制较小,卷证形成和制作贯穿于审前程序的全过程,可根据诉讼进程和调查案件的实际需要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卷证涵盖被告方、被害方和证人及鉴定人陈述的书面材料,也包括追诉者调查或采取侦查措施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笔录等文字材料,还包括追诉者在调查阶段收集的书证材料;除原始书证材料外,卷证中的主要笔录或书面材料长短不限、份数不限,提供者的人数不限,甚至整体卷证的卷数和厚度不限。卷证的这些特点都表明卷证信息容量大、涵盖面广,信息传递更为全面、系统和周密。 卷证的运用更可能使裁判者趋于理性而褪去个性化和情绪化的色彩,其对庭审的操控也可能更为慎密和周全。法国技术哲学大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ull)认为,一切合理而有效用的方法和手段就是技术。JElull, The Technological Order, CMitcham ed,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The Free Press, 1983, p78 转引自王秀华:《技术社会角色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据此,可将欧陆运用卷证的审判方式称为一种技术的审判。
方法和手段的有效性是衡量审判是否具有技术性的主要标准。即该尽管卷证在审判阶段的运用面临对程序正义价值和审判中心地位的冲击,但从欧陆卷证的官方属性(它决定了卷证本身的严格性和法律效力,并可作为对裁判者约束和追责的依据)和实践运用的具体价值来看,在保持卷证制作和运用相对合理的前提下,依凭卷证的技术审判效果除表现在裁判实体结果的基本可靠性外,同样突出地体现在对审判过程(环节)有效性的影响。
第一,审判目标的明确性和可预见性。技术和确定性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知识不仅以确定性终,而且也从确定性始,确定性是贯彻始终的知识。参见[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相对于不预设审判目标的经验审判而言,技术审判强调庭审须有确定性且初步可预见性的目标。这一目标实际上是庭审追求的可预知的可靠性结果(适用法律和事实认定结果)。裁判者预先接触和阅读制作严密、内容完整的卷证具有决定作用,即便这些材料多为追诉机关指控的卷证材料,从而将被动的审判变为一种主动的和可控的审判进程。 相反,“如果在一个案件从一个步骤转向下一个步骤的过程中发生了信息阻隔或丢失的情况,导致主持后一个步骤的官员无法读取前一步骤留下的书面记录,整个科层式程序就会失去方向”。前引⑧,第86页。 可见,裁判者对审判信息的预先掌握,对于具有科层制传统的欧陆国家而言尤为重要。不可否认,裁判者通过阅卷了解审判可能进程和结果而确立的审判目标,可以被视为裁判者的“先入为主”和“预断”,但这已非是哲学意义上对人认知的主观主义和片面主义的批判。从对技术审判过程及其结果有效性和可靠性掌控的角度看,这种裁判者的“先入为主”和“预断”又有存在的价值。
第二,审判的有效决策。审判的决策是对能否开启审判和以一种什么方式进行审判所做的决定。它主要解决庭前案件的过滤、筛选和繁简程序分流的问题。从技术审判的角度衡量,决策对于确定审判的指向性和针对性,提高审判的效率,减少不必要审判成本的支出,实现审判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无疑都有重要意义。显然,裁判者为审判做出上述可靠决策,需预先了解和掌握案件情况,包括案件的性质、基本事实和可能判处的刑罚轻重等,而“这种决策的正当性又来自于可以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可欲结果”。前引⑧,第31页。 所以,无论出于上述审判决策的可靠性还是正当性的需要看,裁判者事先具体和有效地掌握案件信息至关重要,官方制作并编排有序的完整卷证就具有重要作用。“卷宗里包含的文档并不是旨在帮助某一位特定官员组织其活动的官方内部文档,而是为初始决策和复核决策提供基础的信息源”。前引⑧,第76页。 如在德国,法院应当在没有非职业法官参加的情况下审查检察官的卷宗,决定是否存在充分的证据将被告人提交审判,法院是基于卷宗中的书面信息作出决定的。[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第三,开庭前周密的准备和安排。检察官移送案卷材料是欧陆各国的通行做法,在审前准备中法官必然接触和阅览案卷材料,因而审前准备的实际功能在于通过阅卷事先初步掌握全案的事实和证据情况。“法官庭前就证据准备得越充分,其就越熟悉实际上既用于实体目的又用于评估庭审证词可靠性的证据”,Mirjan RDamask, Evidence Law Adrif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72从而预判庭审中应关注的问题。当然,开庭前的这一准备活动也为法官实际驾驭庭审过程,对庭审的举证、质证和认证等证据调查环节以及控辩双方辩论事项作出预判和具体安排提供了条件。因而法官对案件的处理也更为迅速和权威。前引③,第135页。 法官只有事先细致阅览系统的卷证,通过对不同卷证材料的反复对比、推敲和细节把握才能较好熟悉和掌握证据及案情的基本情况,也才能为庭审的环节和进程作出合理规划和安排。
第四,庭审进程的稳定性。庭审过程应当稳步推进和有序进行,出现大的庭审停滞、中断、反复甚至冗长拖沓的现象。其体现了庭审结构的科学设置以及与庭前程序的连贯性,决定了庭审效率和成本投入是否合理,这是衡量技术审判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卷证运用作为实际审判方式的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刑事庭审的稳定性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这不仅得益于法官庭前阅卷,“如果对卷宗中的各种文书材料不熟悉,他(主审法官——笔者注)几乎无法有效地进行法庭询问”,前引③,第101页。 而且在于官方的卷证(尤指预审程序加工整理的卷证),尽管法官仍需在庭审中听取证人证言,但“主审法官往往会事先研究案卷并且在审判过程中反复征引案卷中所包含的材料。对证人的质证仍然只是例行公事似的进行”。前引⑧,第80页。 达马斯卡在评价不依赖书面证据的诉讼方式存在的问题时曾指出,“在诉讼程序的早期阶段获得适格证据变得很难甚至不可能,即便获得了这样的证据,在其长期埋没于卷宗之后再把它挖掘出来也很难”。前引⑧,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书,第92页。
第五,庭审方式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由卷证的运用呈现的欧陆庭审方式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庭审手段上,卷证与口证并用。基于庭审直接言词原则,欧陆庭审在形式上需通过口头方式对人证进行调查,但检察官移送卷证、法官阅览并在庭上有条件地适用卷证却是实践中的主要做法。无论以庭上的口证来支持或印证卷证,还是卷证对口证的辅助或补强,都显示了法官在庭前准备以至庭审环节运用卷证的一种安全性以及对庭审结果可靠性的保障。这也表明因有刑事卷证在庭前和庭审中的运用,刑事庭审的方式变得丰富多样,庭审方式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才得以显现。二是庭审进程上,渐进式和分段式并行。由于通过阅览、使用卷证,法官已较妥善解决庭审目标、决策、准备等各技术环节,庭审得以渐进和分段的方式进行。“在一个环节中考虑完一个特定事项之后,把其中引发出的新的要点留到下一个环节中去考察,并以此类推,环环相扣地进行下去,直到问题似乎完全澄清为止”。前引⑧,第78页。 这种类似“牙医式”的审理方式相对于集中审理方式而言,虽然比较机械和生硬,但又较为从容和稳健,有利于法官对庭审得出较客观的结论,因为“最后的环节可以致力于将所有的线索串起来,重新审视前面的阶段性结果,并冷静地做出一项裁决”。前引⑧,第78页。
第六,突出庭审的重点、难点,并与对事实情节的把握相结合。有条不紊、稳健推进的技术审判风格要求法官始终关注庭审的事实问题,分清庭审事实调查的主次、难易和轻重,切实把握庭审过程的环节。卷证的使用为庭审做到这一点打下了很好基础:一是卷证对所记载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裁剪和整理。“证据在提交给事实裁判者之前,最好应裁掉细微末节之处,消除意外之情形,依法律标准简洁安排,并将其写成文字。经过这些准备后,便能在法官办公室内以修道院般的宁静,通过仔细研究和分析书面证据完成事实认定”。Mirjan RDamask, Supra note 17,p70二是法官的阅卷凸显对事实重点和细节的关注。“案件中的事实经过了裁剪,并且按照上级所下达的相关性标准,进行了井然有序的编排”。前引⑧,第35页。 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卷证内容的进一步整理,厘清案情的要点、争点和难点,以便于庭审事实调查更为集中和有得放矢。三是庭审过程中对卷证的使用。庭审中法官通过对卷宗的宣读和引证,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第253条、第254条和第256条的规定,对于证人、鉴定人或者共同被指控人已死亡等四种特殊情形,可以宣读法官庭前的询问笔录,或者经检察官、辩护人和被告人同意的包括检警方制作的讯问笔录在内的其他笔录。对于庭内外被告人自白相矛盾的,为查明自白真实性,可宣读被告人的庭前自白;为唤起证人等的记忆需要,可以在庭上宣读警方、法官等制作的询问笔录。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第427条、第428条和第429条的规定,轻罪案件审理中,庭前调查笔录或报告具有证据能力,能够提交法庭,其证明力的状况则由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原则作出决定。《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21至328条也规定了庭外书面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诸多例外情形。 确定证据调查的范围、重点,厘清事实的情节,起到“对庭审证明活动的组织意义”。前引B24, p131
第七,庭审的范式和规格。对庭审范式和规格标准的衡量,不仅需观察庭审的动态过程,也需考量庭审的最终结果。与英美依凭法官的地位、威望以及裁决书中充分说理以支持裁决的公正性和执行力有所不同的是,在欧陆主要法治国家,裁决书形式和内容的范式与规格是影响裁判公正性和可接受性的重要因素。尽管各国在裁决书结构安排上不完全一致,但裁决书都具备被告人基本信息、案件事实、事实依据和适用法条等若干基本要素。例如在法国,法院有罪判决书包括判决理由和主文两项重要内容。法官应当在判决中对其内心确信作出表述,用诉讼案卷与庭审辩论中向其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来证明其内心确信是正确的。没有说明理由的裁判决定,或者说明理由不充分的裁判决定,或者包含有相互矛盾之理由的裁判决定,均将受到最高法院的审查。法庭的判决不得仅仅限于照抄规定什么是犯罪的法律条文,而对得到认定的、证明应当适用这些条文的任何犯罪事实不做具体说明。判决不得使用事先已经印制好的现成格式。有罪判决的主文应当表述以下内容:受到传唤到案的人被宣告犯有何种刑事犯罪,或者该人应当承担责任的是何种犯罪;受传唤到案的人被科处的刑罚以及刑罚方式,可能对其宣告的民事处罚;适用的法律条文等。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下),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0-781页。 其中事实依据(证据材料)的完整性和充分性成为裁决书具有合理范式和较高规格的重要标志。经严格审查和过滤的卷证是裁判书事实依据的主要来源。如在法国,判决所需的材料由各专业化的司法官员以案卷的形式汇集起来,经过细心的整理后交给决策者。判决做出之后,案卷整理者在先前报告的基础上起草法院的判决书。由于判决书是由训练有素的职业法官完成,对于卷证在判决书的运用也更有技巧,判决书也更具正式的风格。前引⑧,第49—50页。
从卷证对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刑事审判具体环节和结果产生的综合影响来看,卷证的运用显然造就了欧陆刑事审判的技术风格和特质。欧陆技术审判的本质在于运用卷证方法和手段的有效性,但同时因它对刑事审判结果所具有的预见性倾向和审判方式的程式化及刻板化特征,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对于欧陆运用卷证的技术审判价值需客观和综合衡量,而非以一种技术优越论的态度来掩盖它所存在的其他问题,其视为源于历史传统,适应现代欧陆刑事审判的固有规律较为稳妥。
二、英美的口证审判:经验主导的审判方式
与欧陆刑事审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美的刑事审判始终强调口证作为唯一的庭审调查对象和裁判依据,原则上排斥卷证在庭内外的运用。其主要的制度支撑:一是证据法上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在英美立法和判例中,庭外形成的言词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所声称的内容为真实的,就属于传闻证据,法庭应予以排除。至于传闻证据的范围,不仅包括他人庭上转述原始证人的陈述和证人的自书材料,也包括庭前警察、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制作的询问笔录或其他书面材料,因而庭审排拒了绝大多数书面材料的运用。二是起诉状一本主义的案件移送制度。该项制度要求检察官向法官提起刑事指控时,只能向法官提交起诉状,而不能移送原始卷宗尤其是涉及案内证据的案卷材料。裁判者应根据庭上亲历的听证和质证过程判明案情并以此作出裁判。显然,英美等国对案卷材料的禁用更为严格,不仅禁止控方的案卷材料进入法庭,而且不允许庭审法官审前接触和阅览案卷材料。
由于英美较为严格排斥案卷材料在审判阶段的运用,各类人证的提供者需以口头方式在庭上陈述并进行相应的调查和质证,因而英美的刑事审判可称为一种口证的审判方式。口证,即口头证据,是指具有合法作证资格的人(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和侦查实施者等)出席法庭,以口语的方式就自己所了解的案情进行陈述所形成的证据形式。如果将口证方式的普遍运用与英美庭审过程相联系加以考虑,它所体现的英美审判风格正是一种经验主导的审判。
“语言作为社会具有创造性的东西并不能被想象成是理性的谈论,而从根本上说是具美学特征的。……美学的语言偏向想象与感情,以最直接的形式促进经验共享”。[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1页。 语言是一种听觉和视觉融合的艺术,语言的美学特征在于语义的表达通过语音、语调、语速和肢体性动作等语言感性的外部形式来实现,接受者是在亲历中积累的经验而感知的。正因如此,以口证(口头陈述)运用为特征的英美刑事审判,对于作为既是听者又是裁判者的法官和陪审团而言,更多需要运用经验和直觉来达成对案件事实的认知。韦伯指出,“英国与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判,一直到今日为止,在极大程度上仍然是经验的裁判,尤其是依据判例来裁判。”[德] 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Ⅲ:支配社会学》,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事实上,大凡有陪审团参与或法官主要遵循口头陈述为原则的刑事审判活动,都与裁判者的经验有着密切关系。这源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对抗制庭审。对抗制庭审要求控辩双方进行面对面的语言交锋,双方需要直接举证和质证,裁判者则以耳闻目睹的方式做出裁断。“这种制度在知识创造上的最大限制就是将案件中的事实争议基本上排除在法官和法学的思考之外”。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庭审过程成为裁判者主要运用自身阅历和经验的判断过程,在特定的时空领域感性的认知多于理性的分析。二是庭审的二元制结构。达马斯卡认为,英美审判结构就像一个半人半马的怪兽——一半专业,一半外行,法官审案,陪审团提供事实。参见前引⑧,第59页。 在二元制的庭审结构中,“诉讼必须是口头的,因为在大多数案件中,陪审团是文盲;审判必须尽可能地集中,因为陪审团只能短时间集会”。[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潘华仿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在庭审过程中,“他们有很大的余地去进行自发行动和即兴发挥,也有足够的空间去作出情绪化的反应或凭借过度的激情去行动”。参见前引⑧,第36页。 就对案情和裁决事项的判断而言,陪审团主要依凭的是自身的感知能力(直觉),而非理性的思考和认知。
建立在口证基础上的经验审判,由于事实裁判者能够面对知情者,后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其注视之下,通过自身的直觉和感受实时了解鲜活的案情,案情以一种戏剧化的场景得以展现。经验审判的一个显著优势在于,庭审的言说及其结果可能更为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因为“声音的物理性质塑造了我们的情感体验”,林岗:《口述与案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而“感情和想象力比起信息与理性来,对左右公众的情感和观点有更重要的作用”。前引B30,第60页。 但司法最终需要通过对案件严密而合理的处理来实现正义的价值。立基于口证的经验审判可能产生如下问题:一是个人的情绪化导致处理案件的随意性。在强调感性和直觉的经验审判中,“有待处理的问题很难同个人的特性分割开来”。前引⑧,第36页。 如果裁判者在案件处理中的个性程度偏重,案件认知的情绪化和随意性增强,案件处理的严密性则会减弱。二是案情认知的全面性障碍。在二元法庭,法官可以通过预审程序将不可采但却可信的信息免于事实裁判者的接触,防止在其头脑中留下任何印记。前引B24, p47 这种做法虽有审判公正性的考虑,但对全面、周密地查明案情不利。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刑事审判的实际需要和卷证的固有功能,英美对案卷材料并未采取绝对排斥态度,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卷证的运用又有灵活的一面:
第一,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存在诸多例外情况或特殊情形。一是针对证据提供者的特殊身份或证据形成的特殊情形以及证据反映的内容所决定的书面材料本身的可用性;二是因证据提供者的客观原因或特殊情形而直接在庭上运用案卷材料。
第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庭外所作口供(包括警察制作的讯问笔录)本身不因其二手性而排拒于法庭之外。对于庭外口供尤其警察侦查阶段制作的讯问笔录,英国普通法并不将其作为传闻证据对待,当然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的制约。美国则将这类证据作为传闻证据规则的重要例外承认其证据的可采性。故这类嫌疑人口供不因其庭外书面材料的属性丧失证据能力。只要警方讯问方法、手段和程序合法并保障嫌疑人陈述的意志自由(陈述任意性),作为检警案卷材料中的口供笔录就具证据能力,可作为法庭证据调查的范围。如果其可靠性得到确认,将可作为裁判的主要证据。必须承认,在英美等国,检警讯问制作的口供笔录是一项重要的卷证材料,美国学者弗洛伊德菲尼根据美国加州检、警刑事司法实践经验展示一起假设盗窃、抢劫案的侦办过程形成的案卷材料,其中警察侦查活动形成材料包括:犯罪报告;对犯罪嫌疑人甲的逮捕报告;犯罪嫌疑人甲的陈述;存在逮捕犯罪嫌疑人甲的合理根据的声明;对犯罪嫌疑人乙的逮捕报告等。检察官活动形成材料包括:对被告人乙的刑事控告书;对被告人乙的起诉书;对被告人甲的刑事控告书;对被告人甲的起诉书;被告人甲的答辩协议;被告人甲的缓刑建议等。参见前引⑦,第二章。 在庭上对它的提出和采纳是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操作进行过滤的。
第三,从程序需要来看,英美预审程序对卷证的运用有一定加强。英美的预审程序旨在通过对检察官移送案件的审查,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将被告人提交庭审。因而预审的内容主要是对案件事实进行审查,包括对警察侦查阶段制作的案卷笔录以及有关证人到场陈述的审查和运用。这一审查活动不仅对庭审产生直接影响,又成为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联系的桥梁。弗洛伊德菲尼认为,美国的预审程序体现出两个特点:参见前引⑦,第50—51、370—371页。 一是预审方式因案件的性质不同而有区别。重罪案件的预审通过公开的听证方式进行,不仅被告人及其律师需在场,而且证人也需到场接受询问。由于这种方式不依赖侦查期间获取的证据,侦查活动对预审乃至庭审的影响有限。而对于轻罪案件的预审则采取书面审查方式,主要对检察官提交的警方证据卷宗进行审查,以对案件加以过滤。这种做法与英国被称为形式上预审的治安法官移送审查起诉类似,预审显然受到侦查活动的影响。二是侦查卷宗对控辩双方仍有影响。无论是重罪案还是轻罪案,在预审前检方需阅览警察移交的卷宗,确定须出庭的证人,辩方也需熟悉自己准备的卷宗。
由于受英美传统二元结构司法制度的影响,裁判者虽对传闻保持警惕态度,但随着对诉讼效率的重视以及法律实用主义精神的抬头,耗费巨大人、财、物力的陪审团审判模式逐渐萎缩,简易审判程序或法官独任审理程序已占主导性地位,从而为职业法官运用案卷材料的庭审方式提供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有效的证据开示制度、审前动议以及其他现代诉讼所熟知的诸多手段,已经缓解了自由采纳传闻证据在传统诉讼制度下可能引发的各种困难。前引③,第285—286页。
但卷证的运用仍难以像欧陆那样对型塑刑事审判的技术品质产生实质影响。这不仅在于英美对卷证在审判阶段的提出和运用有着严格限制,更在于卷证对于裁判者而言,主要还是对控辩双方证据调查和案件事实真相判断所提供的支持,以及对英美经验审判所产生的上述不利影响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其并不能改变经验审判的固有格局。
当然,也不能绝对忽视英美刑事审判经验属性的存在。“没有什么地方,技术知识能与实践知识分开,特别是在政治活动中”。前引B11,第9页。 经验与技术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融合的。只是英美刑事审判的技术风格决定于三个重要因素:
首先,严密而系统的证据规则。“当英美证据法的独特性与法庭的组成相联系时,作为普通法的守护神,陪审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非专业裁判者被挑选来裁断争议事实也就解释了这种证据制度安排的需要”。前引B24, p26 这些证据规则主要是排除性和禁止性的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等。“证据排除性规则是必要的,因为陪审团较易受骗”。前引B34,第71页。 达马斯卡也认为,“限制性的规范是为保护非专业人士免受某些有着潜在危险之信息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前引B24, p50 在英美二元制庭审结构之下,通过排除性证据规则的运用,将不真实、有瑕疵或不当乃至违法获取的证据过滤掉,使陪审团最终接触和使用的证据相对可靠并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是技术审判所追求的结果。
其次,相对合理的程序设置。英美具有竞技对抗性的刑事审判合理性不仅体现在庭审程序和方式的设计,也体现在庭前程序的设置。英美的庭前程序包括对案件起过滤作用和开展控辩双方证据交换的预审程序,也包括行之有效的庭前会议制度。如在美国,任何庭审开始前,需召开一个庭前会议,法官需要向辩方了解:(1)是否已做出努力解决该案;(2)各方预计传唤的证人数量和庭审预期持续的时间长度;(3)任何列出须解决的问题;(4)主要证据的争执;(5)未被解决的动议。D Shane Read, Winning at Tria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rial Advocacy 2007, p21 法官庭前了解的上述问题,或与庭审中呈现的证据数量和内容有关,或与庭审的进程预见有关,抑或与要解决的庭审程序性和实体性问题有关,目的都在于法官为庭审有所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心中有数。其功能与欧陆法官庭前阅卷相似。
再次,英美法官的主导作用。英美法官群体属于高度精英化的阶层,其不仅拥有丰富的司法经验,也有着高超的司法技能和手段,以及不断增强的司法知识的供给。尽管二元制庭审结构下陪审团对案件事实有独立的裁决权,但实践中法官又可基于对司法的认知实际影响陪审团的裁决。由于法官因素的存在,二元制结构之下的审判难以用纯粹的经验审判来概括,而具有一定的司法技术特征。更何况由法官单独操作的简易审判程序中,体现法官自身能力的技术审判风格得以展现。达马斯卡认为,“在英美法系法官审中排除规则的实际作用或许较之欧陆法系审判中的还要小。”前引B24, p50 法官对证据规则依赖程度减弱的同时,实际上表明法官在案件处理中对自身司法知识和技能要求的提高。
由此可见,只要刑事审判由专业司法人员操作,且具有实际的统治地位,对审判走向和结果起关键作用的仍是他的知识和技能。这就是英美刑事审判中由于法官因素的存在而不能完全排除其技术审判特点的原因所在。当然,英美的这一技术审判与欧陆建立在卷证基础上的技术审判仍是有明显差异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英美法官需要在庭审特定时空范围内就事实和法律问题独立做出决断,审判技术发挥的空间主要是在庭上,而非欧陆国家那样以庭审为轴心可以上下自由延伸。
三、我国卷证的运用:被异化了的技术审判
侦查者制卷、公诉者送卷和裁判者阅卷与用卷属于我国现实的司法场景,刑事卷证的运用覆盖于整个审判阶段,同时,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案卷材料移送和庭审书面证据调查等制度又为卷证的运用提供了制度支撑,故而我国刑事审判方式属于典型的卷证审判。从卷证制作的主体性自律和对其操作的结构性约束看,我国刑事审判类似于欧陆的技术审判。在总体上,刑事审判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直接源于法官庭前阅览和庭上运用制作严密的卷证,卷证的运用对庭前准备和庭审过程诸多技术环节产生的效果也与欧陆主要法治国家技术审判所产生的效果有一定相似性。然而,基于诉讼价值观念和诉讼传统的不同,我国与欧陆主要法治国家运用卷证的技术审判又存在明显差别:
第一,我国刑事审判存在过度依赖卷证材料的倾向。从司法实践情况看,无论刑事案件性质、影响和危害程度有何不同,也无论案件处理是在庭前,还是在庭上甚至庭后,无论案件审判进程是在一审,还是二审或再审,法院都无一例外地阅览、使用和引证卷证。对证人等的出庭作证,即便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应该出庭的情形,在实践中也未得到有效遵循。刑事卷证成为法官庭前准备的唯一手段、庭审调查的主要对象和最终裁判的直接依据。就立法而言,尽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证人在一定条件下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有关卷证运用的规定又凸显了卷证审判的特点:一是将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检察机关案件移送的复印件主义改为案卷移送主义,为庭前和庭后法官阅览和使用案卷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二是卷证材料庭审效力未作明确限制。我国至今没有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以阻却卷证庭上的证据能力,或者对各类卷证提交庭审的条件和范围作出限定,导致侦查阶段形成的各类卷证均可全部进入庭审,法庭对卷证的证明力只做形式上的审查就可作为裁判依据。三是即便证人出庭,卷证的运用仍无相应限制。证人依法应出庭作证的案件,法律并未禁止侦查阶段形成的卷证在庭审中的提出和运用,也未禁止应出庭作证的证人在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情况下排除庭前形成的证言材料。由于证人是否出庭不影响卷证庭上的运用甚或卷证可替代证人出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实际已被虚置,这也是修正案实施以来在审判实践中证人出庭比率仍处极低状况的重要原因。所以,从实践的做法和立法的制度安排来看,由于排斥了口证的运用,我国刑事审判属于一种由卷证垄断的刑事审判,即“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
以德法为代表的欧陆法治国家,刑事审判属于实际运用卷证的审判方式,其主要是基于检察官移送卷证制度和庭审中一定限度地使用卷证以及特定案件完全运用卷证等情形,但这些国家绝没有达到审判过度依赖卷证或由卷证垄断的地步,至少在普通刑事案件审判中是如此。由于坚持直接言词原则,德法等国在普通刑事案件的庭审中,侦查阶段形成的卷证材料完全被禁止在庭审中提出和运用,庭前由预审法官制作的卷证也只有在例外情形下可在庭上宣读和引用,并作为对庭审中口证的补充或弹劾而受到限制。因而欧陆法治国家对卷证的使用是适度和有节制的,卷证在审判中的运用是合理的,并有效地推动了审判的技术化进程。
我国司法实践经验表明,司法者对卷证的过度依赖除了对审判最终结果的可靠性产生相应冲击外,对审判程序价值也有不利影响:一是庭审的形式化倾向。运用卷证的审判方式意味着审判不仅比较刻板和程式化,而且存在预先设计和可预知性的因素。“在有条不紊、慎密周全的初步调查之后,在庭审中,案情几乎没有出现戏剧性变化的可能”。前引B24,p72 学界所担心的庭审流于形式、走过场、戏剧化的表演色彩浓厚的现象难以避免。二是庭审公正性的影响。一方面,庭审的形式化倾向导致庭审的不公正性。在学界看来,庭审的形式化不仅可能导致政府追诉权的滥用,被追诉人庭审对质询问权的丧失,而且对具有现代意义的控、辩、裁三方的合理诉讼构造的运行,庭审过程和结果的独立价值的实现等产生相应的消极影响。参见龙宗智:《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118页。 另一方面,刑事卷证信息的偏向性产生审判不公。在实践中,卷证主要由侦查者记录和制作完成,卷证中的大多数材料是有罪材料。裁判者接触并在庭审中直接或间接沿用这些材料,因信息本身的不对称性和不可视性可能造成对被告人审判的不公。
第二,我国审判运行至今仍缺乏以真正意义的司法职业者群体及相应的技术标准为基础。由于卷证反映案情的间接性以及卷证信息把握的复杂性而存在固有的风险,对运用卷证的司法者职业化程度及其技术标准应有严格要求。以德法为代表的欧陆法治国家运用卷证的刑事审判显然能够满足这一要求。达马斯卡在评价欧陆法官的职业素养时曾指出,“要随时准备好根据冷冰冰的卷宗来作出决策,必须具备只有在官僚组织中才能培养出来的技能和性情倾向。对于一位外行人士来说,记录在案的证词看起来像是现实的一抹了无生气的残迹”。前引⑧,第92页。 显然,对卷证进行有效的审查和运用,官僚技术人员相对于外行人士更加得心应手。德国法律界就认为,“卷宗的任何潜在的偏见性影响都会被法官的职业经验所抵消”。前引⑦,第339页。 司法者作为官僚技术阶层所具有的稳重性格,其所受的文书训练,娴熟的书面材料运用技能,都是决定其运用卷证对审判技术有效掌控的重要因素。
官僚体制下的技术官员所受专业训练和专业知识具有同构性,并具有相应的职业伦理和道德要求,因而在执行管理的技术标准上具有一致性。“作为惯习化和专业化的结果,一位职业官员的职务反应和个人反应可能会分离开来:他会获得在必要时麻醉自己心灵的能力,并且在其官方职位上做出他作为个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做出的决策”。前引⑧,第28页。 在欧陆技术审判中,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个人素质。“由于制度必须是意思单一的,以便不造成任何歧义,由数位官员做出的决策在宣布时将废弃先前的内部分歧: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现在只好压制自己的感受”。前引⑧,第28页。 专业技术人员掌握裁决标准的一致性,不仅可顺利作出裁决,而且由于排斥了个人的情感因素,裁决过程可能更富于理性,结果也可能为多方所接受。案情和卷证材料是纷繁复杂的,阅览和使用卷证更需专业技术人员达成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实践性共识,以发挥卷证对刑事审判过程和结果技术管控的能力,降低运用卷证的风险。
我国法官职业化和专业化一直是努力的目标,但至今仍未达成。除了我国长期以来法院体制行政化和政治化倾向,使得司法不独立,司法本身的专业性要求不高的原因外,也与法官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从对法官的选任看,改革开放之初不讲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而强调法官的政治素质,因而复转军人进法院成为一种普遍的司法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法治建设水平的提高,法官业务素质的权重逐渐提高。但当下对法官业务素质的要求又限于形式上和表面化,其中主要的衡量标准在于法官的学历和文凭,以及相应的法律知识熟悉和掌握程度。由于对法官素质的误读,现实中的法官并没有表现出有效掌控审判和运用卷证的能力。从欧陆职业法官运作来看,其驾驭技术审判的能力不仅在于其法律或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其综合性素质,其对法律的信仰、理解和司法中所积累的知识。“司法的知识不可能是人的理性对永恒真理的清晰发现,而只能是法官司法实践的产物,是特定制约条件下法官与请求予以裁决的事实纠纷遭遇而逐渐累积产生的一种制度化的知识”。前引B32,第154页。 对卷证的运用法律并无相应具体规定,对于卷证的形成、制作和审判阶段阅览、分析判断以及对卷证内容的把握和取舍等,实际上都需要法官利用所积累的司法知识加以处理。我国裁判者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与欧陆法治国家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在审判中对卷证类似于工匠式的操作不能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审判技术性特征,并在实体和程序标准上取得预期效果。
第三,我国尚欠缺对卷证运用的程序性制约机制。欧陆各国对刑事审判运用卷证风险的控制,除了审判的直接言词原则、庭审卷证准入机制以及裁判者职业规范等法律和体制性手段发挥作用外,从程序控制上也有具体的措施和方法:一是预审庭对刑事案卷运用的制约机制。就预审庭的设置来看,早期欧陆预审独任庭已变为现今的预审合议庭。在德国,预审程序中的主审法官并不阅卷,而是将案卷材料分配给助理法官审查,由后者提出意见并向前者报告。而意大利通过1988年修法,将预审庭法官与预审法官相分离。这一做法意在确保预审庭法官不会因曾签发搜查令或做出过审前羁押决定而导致先入为主。二是庭前阅卷对庭审影响的消解机制。在德法两国实践中,审判合议庭的阅卷采取主审法官阅卷制,这一做法有利于避免外行陪审员产生对案件事实认识的偏见。在意大利司法实践中,推行两种案卷运用制度,一种是供预审法官使用的厚厚的检察卷宗,另一种是庭审法官可以接触的所谓法官卷宗。唐治祥:《意大利刑事卷证移送制度及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2期。 后一种案卷包含的证据材料比较有限,目的在于避免侦查因素对审判活动的干预,提升庭审控辩双方的对抗性。三是司法案卷的形成机制。达马斯卡认为,职权主义审判结构要求法官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但为避免审前程序对审判的干扰,应严格禁止决策者(庭审法官)庭外的调查取证,而应由“专职官员”或“审判管理者”承担这一职责。前引⑧,第241页。 在德国和日本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官庭前制作的询问笔录等书面材料在庭上宣读的限制逐渐减少。四是案卷材料的形成机制体现一定的控辩对抗性。欧陆国家在预审法官人证调查中明确允许被告人及其律师介入进行对质询问,这种做法类似于庭审控辩对抗方式的“前置”,以此形成的法官笔录体现辩方的参与性和对抗性。意大利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则将刑事案卷分为三类,除了典型的侦查案卷外,还有审判案卷和辩方案卷。而辩方案卷又可并入初期侦查案卷之中。上述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对刑事案卷介入审判的种种制约机制,都体现出司法因素对刑事案卷运用的干预和影响,既助于防止或减少裁判者运用案卷材料产生的预断,也利于增进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导地位。
在我国,由于缺乏法律的预先规定和实践中的操作措施,审判阶段对各类案卷的运用具有粗放型特征,庭前法官对案卷的阅览和庭审及庭后的卷证运用都缺乏相应的阻断或控制机制。我国庭前程序主要包括公诉案件审查程序和庭前会议制度。由于实行案卷材料移送原则,且庭审法官集庭前案件审查及主持庭前会议的职责于一身,其可不受限制地阅览全部卷宗内容并对庭审及结果产生直接影响。从形成司法卷宗上看,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法官有权进行庭外调查(庭前调查),但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没有采取这一措施,而对侦查卷宗采取全盘接纳的做法,失去对卷证制约和控制能力。从对卷证形成过程的对抗机制来看,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阶段卷证制作中应将律师意见附卷,体现侦查卷宗全面反映案情的立法精神。但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并未得到有效遵循,侦查卷宗仍是侦查者制作的各类不利于被追诉者的单一案卷材料,且对防止人证材料片面性更为有效的询问过程辩方参与机制,无论在立法还是实践中都未得到落实。在侦查案卷材料缺乏法官和辩方的有效介入,法官阅览和运用卷证缺乏程序性控制机制的情形下,我国刑事审判的实体效果和程序保障显然存在较大风险,刑事审判的技术又从何展现?
由上观之,尽管从归类的角度可以将我国运用卷证的刑事审判视为类似于欧陆的技术审判方式,但由于裁判者对刑事卷证的过度依赖,司法者群体职业化、专业化以及卷证运用程序性制约机制的欠缺或不足,我国刑事审判实际已偏离了合理有效的技术审判方向,或可称得上是一种异化了的技术审判。这种审判方式对审判正当程序价值乃至审判结果都有明显的不利影响。
四、卷证的运用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
由于英美运用口证的刑事审判所体现的程序正当性、被告人权益有效保障及控辩平等价值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我国学界对运用卷证的刑事审判方式普遍存在固有的排斥倾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方略,则被视为从政策导向上削弱乃至排斥刑事卷证在审判中运用的重要标志。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卷证在审判运用中的种种弊端,主要还是对卷证的过度依赖和司法者职业化、专业化程度的滞后以及对卷证缺乏规制所产生的现实问题,因而对刑事卷证进行全面否定显然并不公允,也难以真正理解中央有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精神。
对于刑事卷证在我国司法中究竟可否运用的问题,有两个基本的事实依据可以做出回答。
首先,刑事卷证是被标签了的中国司法固有特征。无论是中国司法传统使然,还是早期对前苏联刑事司法方式的借鉴,我国刑事司法早已将案卷材料的运用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刑事司法早已贴上了卷证化的标签。这一现状反映的是中国司法的现实需要。从表面上看,法官长期形成的书面审理习惯及其综合素质驾驭口证审判的不适应性,书面审判方式所需人、财、物力等公器资源与现实有限司法资源的相适应性是我国运用卷证的现实基础,而法官庭前阅卷和庭审用卷客观上有利于庭审的顺利推进和提高审判效率又是法官操作卷证的动力。从更深层面来看,司法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现实条件可能又是影响乃至决定我国刑事卷证普遍运用的根本性因素。就公检法组织体制而言,由公检法三机关同质性的机构特点、共同的诉讼目标和利益,以及各自诉讼活动方式的单向性和一体化决定了三机关实际是一个具有稳固性的司法共同体。它们在诉讼中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观念和情感,其行为自然能为对方所认同和接受,这里当然包括处于审判阶段的法院对前期侦查和起诉机关活动收集和制作的案卷材料的认同和接受。而我国刑事司法组织体制和活动方式的行政化又为审判的卷证化运作提供了基础。韦伯对于近代西方职务运作的条件曾指出,以原本草案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以及制作和传输这一文书的幕僚和写手所构成的机构发挥着基础作用。参见前引B31,第23页。 现代社会官僚组织体制和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同样以文书档案的使用作为运行基础。一是法院之间(包括上下级法院之间、同级法院之间和不同区域法院之间)业务的日常运行是靠卷宗材料维系的。二是法院内部因行政层级领导关系所形成的纵向审判管理通过卷宗材料来往传递和运用起着基础作用。三是法院内部行政化的横向审判流程管理更加依赖于案卷材料运用。此外,刑事卷证的运用也存在对刑事诉讼结构的依赖。在我国职权主义结构之下,裁判者有着更大的证据调查空间,不仅在庭审中可采分段式的证据调查方式,而且也可在庭前,甚至可以在庭后进行这样的调查。按照达马斯卡的观点,这种分段式或零散型案件审理的方法对裁判者接触的证据范围和总量就不会有严格要求,从而为裁判者在庭前和庭后阅览和使用由官方所固定的证据材料提供了便利条件。前引B24, pp61—62 所以,当代中国司法体制的同质性结构及其行政化的运行方式正是刑事卷证运用赖以存在的根本性条件。
其次,运用卷证所体现的刑事审判的技术特质不能被忽视。从上述分析看,刑事卷证的运用与审判的技术性存在内在联系,也就是说,刑事卷证的合理运用能够为审判提供技术方法和手段,增强审判的技术含量。从欧陆实践来看,刑事卷证运用所产生的技术审判效果除了有助于增强审判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外,也因卷证的合理运用使得庭前准备和庭审能够有序推进,既提高了审判效率、降低了审判成本,又由于卷证适度和合理的运用而与口证形成有效互补,对庭审的公正价值及被告人权利保障有促进作用。在当代中国刑事审判中,尽管刑事卷证被过度依赖,但卷证运用所体现的审判技术含量仍有一定表现:案件的实体处理尤其案件事实的认定总体上出现差错的比率较小。庭前和庭审对卷证的阅览和引用,客观上也使审判在可控和有序的条件下运行,提高了审判效率,节约了司法成本。只是依赖卷证对审判的程序正义价值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存在明显偏废。
卷证的运用所产生的技术审判效果,还在于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反向作用。“技术在本质上既非善的也非恶的,而是既可以用以为善亦可以用以为恶”。王秀华:《技术社会角色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基于技术的这一属性,刑事审判的技术风格和特质本应具有中立性品质。技术的中立性,也为裁判者的中立性奠定了可靠基础。韦伯曾对欧陆法律职业家阶层的形成与专业技术的关系进行总结,他指出,“近代文化愈是复杂与专业化,其外在支撑的装置就愈是要求无个人之偏颇的、严正‘客观的专家,以取代旧秩序下、容易受个人之同情、喜好、恩宠、感激等念头所打动的支配者。”前引B31,第47页。 可见,技术常态化的运用可以培养运用技术人的中立性品质。相应地,在司法领域,技术审判也可对裁判者中立性品质的培育产生影响。裁判者的中立性对于以运用卷证为主的我国刑事审判的安全性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从制度理性及现实主义立场上看,当代中国刑事审判中的卷证问题实际上不是卷证能否运用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运用方法和标准)以及运用中如何进行规制的问题。中央有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及其他司法改革举措,不是对我国刑事审判运用卷证的根本排斥和否定,相反,为我国刑事卷证在审判中运用的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第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刑事卷证回归理性和适度运用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条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旨在阻断侦查活动对审判活动的固有联系,保障刑事审判应有的独立地位和价值。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在审判阶段坚持直接言词原则,引入口证的审判方式,尤其在庭审中以法官对事实和人证、物证的直接调查作为裁判依据,而避免或减少庭审单独对卷证的调查和确认以及裁判对卷证的直接引用,实现学界所强调的事实调查在法庭、证据认定在法庭、裁判作出在法庭的目标。通过口证的运用和直接言词原则的推行,实际上能够有效削弱或减少卷证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改变刑事审判依赖卷证或过度运用卷证的传统。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调庭审的主导作用,防范的是以刑事卷证作为庭审调查和裁判的直接依据,但并不禁止法官庭前或庭后阅览和参考卷证,这对于庭审的顺利推进,保证庭审口证的有效运用,实现庭审的独立价值是有益的。
第二,我国司法机构内部组织体制的改革,为运用卷证的技术审判有效运行提供了保障。如上所述,裁判者非专业性和非职业化的倾向是我国运用卷证的技术审判产生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的司法组织体制改革,为这一技术审判方式的有效运行提供了组织体制上的保障。根据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有关司法体制改革精神,涉及法院的组织体制改革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法官员额制改革。所谓法官员额制是指法院在编制内根据办案工作量、辖区人口、经济发展等因素确定的法官职数限额制度。它是对法官主体性、关键性制度安排,通过提高法官的任职门槛和职级待遇,把优秀的法官和有效的司法资源吸引到办案岗位。二是法官分类管理制。即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审判法官、法官助理和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同时,健全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提高法官的待遇,延迟优秀法官的退休年龄。三是法官的任用制改革。除了进一步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等外,着重建立从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法官制度和从基层或下级法院中逐级筛选法官的制度。上述若干司法改革举措,目的都在于提高法官队伍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实现法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保证司法组织机构运行的独立性和应有的职业主体地位。这些举措与我国审判中对法官提出的较高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要求是相适应的,当然也为推动运用卷证的技术审判有效运行提供了组织保障。
第三,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关键在于建立可控且合理的卷证制度。从与刑事审判相关联的角度看,建立可控和合理的刑事卷证制度既有利于推动技术审判的正常运行,也有助于审判中心地位的确立。就刑事卷证的实体性制度(或规则)而言,需要建立刑事卷证的证据能力规则和证明力规则。卷证的证据能力可以从卷证制作的形式条件(卷证制作人资格、卷证制作程序和卷证书面格式等),卷证内容相对可靠性的实质条件以及卷证形成的合法性条件(收集证据的方法和手段的合法性要求)等方面进行规制。同时建立一定的卷证证明力规则,以规范乃至限制卷证在庭上的实际运用及作为裁判的依据。如从卷证证明力分类的角度,对实质性卷证、辅助性卷证及宣读作为恢复记忆卷证等的庭上运用条件和审查规则做出规定。
就刑事卷证的程序性制约机制而言,鉴于长期以来对检察机关移送的卷证材料缺乏相应程序性制约和整理机制,这类卷证材料不受限制地为法官阅览和在庭上使用,导致对庭审的公正性和审判中心地位产生负面影响,因而有必要借鉴欧陆国家对卷证材料采取的庭前程序性控制手段。诸如人证形成阶段辩方有权参与的机制,庭前审查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机制,庭前或庭外司法卷宗的形成机制以及庭审合议庭成员阅览案卷的限制机制等都可在我国适当加以建立和完善,确保刑事卷证的实际运用限定在可控和合理的范围之内。
Abstract:As to the application of evidence in the trial, criminal trials based on case files in major European countries practicing ruling of law can be defined as the technical trial, while criminal trials based on oral eviden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regarded as an empiric trial. In our country, the technical trial can be defined since case files are widely used in criminal trials. However, technical trial in China has been distorted because of excessively relying on case files, the judges less professional level, and the lack of procedural restrains on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case files. At present, the trial-centered reform of litigation system is not rejection of using case files but rather aims to lay foundation for the systemic reform on application of case files in criminal trials.
Key words:criminal case files technical trial oral evidence
[作者简介]罗欢欣,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① 其中,中沙群岛主要由隐没在水中的暗沙、滩、礁等组成,黄岩岛是中沙群岛中唯一露出水面的岛礁。
② Lian A Mito, The Timor Gap Treaty as a Model for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pratly Islands,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iview, Vol 13, 1998, p727;Christopher C Joyner, The Spratly Islands Dispute: Rethinking the Interplay of Law, Diplomacy, and Geo-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13, No2, 1998, p193
③ 东沙群岛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控制下,因为同属一个中国,笔者不再另行标明。
④ Zou Keyua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aritime Boundary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ts Legal Consequences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over the Spratly Island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Vol 28, 1999, pp 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