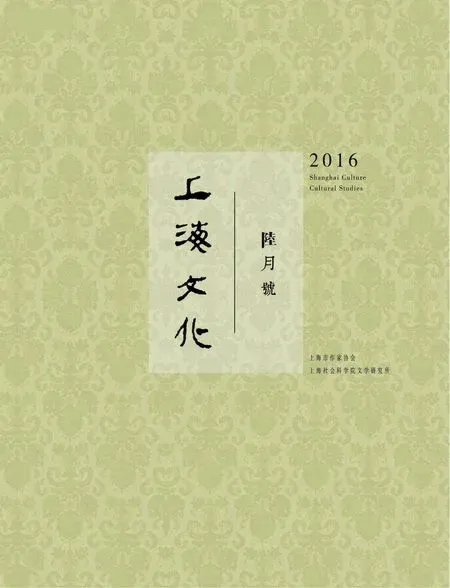神界灵光:上海盛德坛之灵魂照相活动
王宏超
神界灵光:上海盛德坛之灵魂照相活动
王宏超*
内容摘要所谓灵魂照相(Spirit photography),是指在照相术出现之后兴起的一种利用照相技术为鬼神或死去的人“照相”的现象。灵魂照相首先出现在美国,后来经由伍廷芳等人传播至中国。灵魂照相在中国与传统的扶乩巫术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上引起过很大的反响。最有名的灵魂照相事件是温州人徐班侯在遭遇船难之后,其家人利用扶乩活动为其灵魂照相。这些照片在上海盛德坛所主办的《灵学丛志》上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盛德坛此后也进行过多次的灵魂照相活动。本文聚焦于在徐班侯灵魂照相启发下,盛德坛所进行的数次灵魂照相活动,以及后来终止的原因。
关键词上海灵学会盛德坛灵魂照相扶乩
一、科学和迷信之间的“灵魂照相”
灵魂照相是乩坛利用“新技术”而进行的扶乩活动。扶乩是中国传统的方术,许地山在《扶箕迷信的研究》中说:“扶箕是一种古占法,卜者观察箕的动静来断定所问事情的行止与吉凶,后来渐次发展为书写,或与关亡术混合起来。”①许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页。扶乩与早期道教的受诰直书的现象有关,唐代又与紫姑神信仰相结合,在社会上颇为流行。扶乩主要通过文字与鬼神沟通,更早的渊源或与人类文明早期的文字巫术或文字崇拜有关。也是因为文字的媒介,扶乩更多的是在读书人中流行,或者必须有读书人的参与方能进行。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思想的东传,传统的扶乩亦“与时俱进”的进行了改变。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乩坛是上海的盛德坛,依托于上海灵学会,两者其实是“坛会合一”的组织。上海灵学会受西方心灵研究(psychical research)的影响,强调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超自然现象问题。在“科学至上”的时代,灵学会的立场颇为有趣,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或证明被“科学主义者”称之为是“迷信”的现象。而最能代表这种“科学”与“迷信”交混现象的,无疑就是“灵魂照相术”了。
灵魂照相术(Spirit photography)是指在照相术出现之后,兴起的一种利用照相技术为鬼神或死去的人“照相”的现象。灵魂照相首先出现在1860年代的美国,后来经由伍廷芳等人传播至中国。灵魂照相在中国与传统的扶乩巫术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上引起过很大的反响。最有名的灵魂照相事件是温州人徐班侯在遭遇船难之后,其家人利用扶乩活动为其灵魂进行的照相。①见拙文:《徐班侯灵魂照相事件》,《书城》2015年七月号。这些照片在上海盛德坛所主办的《灵学丛志》上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如上所述,盛德坛此后进行的多次灵魂照相活动,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极大地扩大了盛德坛以及灵学会的影响力。后来的一些乩坛,如北京悟善社,就专门模仿盛德坛的灵魂照相,也起到了扩大影响的作用。
徐班侯的灵魂照相在当时影响甚大,鲁迅对于灵学的批判,即是以此一事件为靶子。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大骂灵学:“仆审现在所出书,无不大害青年,其十恶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颤。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至于为徐班侯之灵魂照相,其状乃如鼻烟壶。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②鲁迅:《致许寿裳》(1918年3月10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0页。
《新青年》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在确立科学权威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批判鬼神迷信,“辟灵学”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辟灵学”可以说是《新青年》宣扬“德先生”的一个近因。还值得一提的是,“辟灵学”论战对于后来的“科玄论战”,亦有着持续性的影响。③黄克武:《灵学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民初知识分子对科学、宗教与迷信的再思考》,《思想史》(2),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第126页。
二、徐班侯照相的启示
1918年正月二十八日,④本文中,农历日期用汉字标示,阳历日期用阿拉伯数字标示。上海盛德坛收到由温州寄来的徐班侯灵魂照相片,照片随即在坛上传观,遂引起轰动。该日明月仙子临坛,曰:
余本不甚临坛,今日心中怦然一动,觉有异征,特来一走,乃知有奇闻也。奇闻非他,灵魂可以照相也。此事将来大可研究,吾亦乐闻此耳。⑤《记载》(1918年正月二十八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4期,1918年。
其实,在此之前,盛德坛弟子就曾在报纸上见到过有关灵魂摄影的报道,在正月二十日,就曾叩问明月仙子能否临坛摄影。明月仙子乩云:
此理玄妙,诚非常事,非有根性,难以成就。如欲其迹象著明,当另有一番研究,猝然之间,求其灵通,亦不可一语判其究竟。照相是属于一种技能,寻常人难得其妙,必兼灵学智识与照相技艺方可从事。⑥《明月仙子仙灵摄影及弹琴判词》,《灵学丛志》第1卷第4期,1918年。
因为《灵学丛志》中《记载》之栏目的内容刊发时间滞后,以上所引一月二十日的内容,实际刊发在《灵学丛志》第一卷第四期,而有关徐班侯照相的内容,刊发在第二期。所以,尚不能确定二十日有关灵魂摄影的问答,是否为乩坛有意所加,以为后来出现徐班侯照相事件之铺垫。但是,就算徐班侯照相或不是盛德坛所了解的首次灵魂照相事件,可以肯定的是,徐班侯照相是后来盛德坛一系列照相事件的直接引发者。
二月十四日,众人向常胜子、时中子叩问“灵魂照相之作为”,常胜子称:“照相事,我他日当来耍顽一耍顽亦可。”①《记载》(1918年正月二十四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4期,1918年。并在二十六日专门降乩确认允可照相。②《记载》(1918年正月二十六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4期,1918年。
常胜子是盛德坛最为活跃的乩仙之一,元代人,原名司马潜,“少时从茅山老三学道,迨二十有七时,出就俗务。与谭仲简、刘青田友善,常以阴阳相质直。及老,闲游海上,藉卜筮以为诸人当头棒喝”。③《常胜子临坛摄影照片》,《灵学丛志》第1卷第6期,1918年。
其实,这一时期,上海盛德坛尚未掌握灵魂照相的方法,二月十六日和二月十九日,常胜子与慈佑真人分别降乩论“试照仙灵法”:
将干片一张,用洁素纸包裹,外用浓黑厚纸平贴包好,置人额上或脐上。一为后天三昧火,一为先天真元气。皆可以试之。是时心中笃信观音菩萨在我光中,强固思维,约二时许(此时须在暗室中弗透光为要)。然后洗之显影,因人之思维强毅各异,而其负像遂呈各种不可思议之奇怪异状。何人最能清晰,即何人易于照仙佛也。④《常胜子试照仙灵法》(1918年二月十六日宣示),《灵学丛志》第1卷第5期,1918年。
此处所谈的“照相”,虽然也提到“暗室”、冲“洗”等拍照的要素,但就并未提到过照相设备,仅是凭借鬼神在“思维”之中所显现出的“光影”而成像。
另一乩仙慈佑真人更是谈到,动物亦能为之:
用黑套仅罩外面,使不蒙日光已可矣。即如将一有灵性之动物,亦可试之。此时可显动物心中所蓄之念,亦隐约现出,可玩也。或一时或二刻,均可。总视心之寂否为度。以驯犬最易,使之坐卧其上,便得有三处可通神明。即天渊、绛宫、地户是也。脐额尤易,动物之额不易缚住,坐卧为便。⑤《慈佑真人试照仙灵法》(1918年二月十九日宣示),《灵学丛志》第1卷第5期,1918年。
年初一二月间对于灵魂照相进行了一些探讨之后,盛德坛并没有进行实际拍照,而是一直等到了八月才开始拍照。
三、盛德坛初试照相
在刊发徐班侯照片之后,俞复的朋友丁福保怂恿一位有30多年从业经验的摄影师吴朴臣前去一试。起初,吴疑信参半。1918年八月初七晚,吴携照相器材来到上海灵学会的盛德坛。当日正值清风仙子临坛,但“仙子素行孤介,未便以此相请。”⑥俞复:《盛德坛试照仙灵记》,《灵学丛志》第1卷第6期,1918年。又见《记载》(1918年八月七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9期,1918年。接着常胜子临坛。
当俞复等人提出照相请求时,常胜子示曰:
试却可,姑试。但能否成就,试后再谈。总之,不外一诚耳。诚则或效,此与看琼苑同理,惟有缘者方能成就。缘最熟,则像,且显晰,否则黑气蒙蒙耳。⑦同上。
于是,众人开始准备拍摄,镜头所对的是“壁上琼苑幻境白纸一幅”。⑧同上。拍摄完成后,因常胜子有言在先,所拍不一定清晰,故俞复特意交代吴朴臣,“此片无论如何模糊,必持来一观。”①俞复:《盛德坛试照仙灵记》,《灵学丛志》第1卷第6期,1918年。第二天,吴朴臣告知俞复,此片显影甚难,费事甚多,若非俞复的叮嘱,他可能早就废弃此片了。最后,冲洗出的照片“不佳,但略有影耳。”②同上。俞复颇感忧虑,但拿到照片后,发现常胜子“须发伟然,道貌俨然。与五月初八日常乐金仙所绘常胜子像颇得其仿佛,乃狂喜。”③俞复:《盛德坛试照仙灵记》,《灵学丛志》第1卷第6期,1918年;常胜子灵魂照片见同期《常胜子临坛摄影照片》,《灵学丛志》第1卷第6期,1918年;常乐金仙所绘常胜子像见《明月仙子像常胜子像》,《灵学丛志》第1卷第7期,1918年。

图1 常胜子临坛摄影照片

图2 明月仙子像常胜子像
常胜子此相片,颇类似于佛教的绘画,“头上有光圈一道,此即灵光,俗绘仙佛常有之,盖有所本也。元末距今五百五十年,灵光岿然,可羡哉,可敬哉”。④《常胜子临坛摄影照片》,《灵学丛志》第1卷第6期,1918年。关于灵光,丁福保曾在《我理想中之鬼说》中加以阐述:“鬼之头上,各能放光,以便自照。其光之大小,亦与生前功德学问之深浅为正比例。其光易为烈日所夺,以致不能自见,故鬼之行动在上午者甚少,至午后则日光渐西,鬼亦渐渐出矣。”⑤丁福保:《我理想中之鬼说》,《灵学丛志》第1卷第1期,1918年。鬼见不同之人,其光之明暗亦有不同:“鬼见人之有夙根者,有功德学问者,其顶上之光亦颇巨。人为恶则其光渐小,或至于无。”⑥同上。
俞复认为这些现象均违背科学之原理,实则乃是科学所无法解释。他还非常强调在参与拍照和记录过程中,秉持了“科学”的精神,“复夙知宝爱人格,不敢以诳言弄人。且又深知此等事实,关于未来学理影响极大,尤不敢轻信以受人欺者,转以欺人。凡以上所述,皆经细心察验,足为确凿可信之保证书者也。世有好学深思之士,不欲仅封于科学已发明之故步者,盖共兴起而研究之乎”。⑦俞复:《盛德坛试照仙灵记》,《灵学丛志》第1卷第6期,1918年。
灵魂拍照的成功,让俞复异常兴奋,称之为:“盛德坛之胜绩,灵学会之灵光,五百年健在之灵魂,第一次试照之良果,两界沟通之先导,科学革命之未来。”⑧同上。
四、鬼神有形论
盛德坛及灵学会灵魂照相的“理论基础”是“鬼神有形论”。在传统观念中,都认为鬼神是无形无影的,“人每谓鬼无形、无影,神无方、无体,不可见者鬼也,不可测者神也”。①《济祖师鬼神论》,《灵学丛志》第1卷第1期,1918年1月。但盛德坛的灵魂照相却能照出“鬼影”,似乎与古人观念不同。故他们常通过扶乩形式,让乩仙临坛,论证鬼神亦是有形有影的。上海灵学会既然以“递人鬼之邮,洞幽明之隔”为己任,我们可以发现,其背后最重要的理论根基就是“有鬼论”。丁福保《我理想中之鬼说》,开篇即言:“人死为鬼,鬼有形有质,虽非人目所能见,而禽兽等则能见之也。”②丁福保:《我理想中之鬼说》,《灵学丛志》第1卷第1期,1918年。济祖师通过扶乩也曾谈到:“鬼亦有形可向,有影可照。君如不信,亦可实验。惟此时尚未得明言也。试问诸章佛痴伍博士,便可有确消息。此理昔人已先我言之。”③《济祖师鬼神论》,《灵学丛志》第1卷第1期,1918年1月。
但他同时亦说明,对于鬼神之形影方体之问题,实在超出人类可思议范围,鬼神之有形影,可以猜度鬼神有方体,但却又不能确知鬼神是有方体的,鬼神之灵妙,本就不能以方体问题来约束:
夫神无方无体一语,已为不刊之论,从无人疑之者,亦不能翻其案也。但以鬼之有形、有影征之,则无方体者未始不可有方体也。但谓其非无方体,则又不可,何也?盖吾神以不可思议之能,灵妙莫测之体,应变幻化之用,奇异诞怪之相,使世人惊骇诧奇而不敢猜度,此又可得拘泥于方体也哉?④同上。
这里他的重点是在说明鬼神的形影问题,而不愿更深地触及鬼神之方体问题。
在《常胜子灵光分影说》中,灵学会利用扶乩的形式阐述了性灵与光影的关系。人有性灵,发而为光与影,灵光是“待机而发耳。亦有不发者,无机引也”。若引而不发,常因“诚未至神未感也……诚至矣,而神临矣”。⑤《常胜子灵光分影说》,《灵学丛志》第1卷第1期,1918年。此文似专就解释灵魂摄影而作。
五、摄影师吴朴臣
丁福保是盛德坛周围最为活跃、最为知名的知识分子之一,曾作著名的《我理想中之鬼说》一文,倡导有鬼之论,他对于扶乩至为虔信,在刊发该文之前,还特地叩问乩仙进行鉴定:
时丁君仲祜因作《我理想中之鬼说》一篇,未敢自信,欲求坛上鉴定后,方刊入《丛志》。叩陈云:“‘仲尼韦编三绝,而十翼始成’,晦庵临终尚改定《大学》诚意之旨。圣贤慎重著述,往往若此。福保诠材末学,涉笔便讹,若率而付刊,既背真理,又误阅者,必成大戾。谨将拙著录副,谨请斧政,再行发刻。”⑥《记载》(1918年十二月一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3期,1918年。
从中可见其对于鬼神态度之真诚。因为与俞复有交谊,所以丁福保对于盛德坛事务参与较多。当见到徐班侯的灵魂照相后,丁福保就举荐自己的摄影师朋友吴朴臣前来盛德坛一试。
一般把1839年达盖尔银版照相术的发明作为现代照相术的开端。在此后不久,照相术就传到东方。当年的10月19日,澳门的英文报纸《广州周报》(Canton Press)就发表文章介绍达盖尔照相术。就目前资料来看,照相活动在中国的实际应用,是在1842年7月16日,鸦片战争期间来华的英国军官在镇江附近进行的拍照活动。①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1844—1879年),徐婷婷译,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年,第1-2页。随着照相技术的传入,中国人也开始关注并实践起照相活动来。如邹伯奇(1819—1869年)、罗以礼(1802—约1852年)、赖阿芳(约1839—1890年)、梁时泰(生卒年不详)、任庆泰(1850—1932年)等优秀的摄影师。②参见陈申、谢建国编著:《中国影像史》(第2卷,1839—1900年),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年。尽管和西方的摄影师有不同的审美取向,“这些最优秀的中国摄影师在技巧上已不逊色于他们的外国同行”。③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1844—1879年),第49页。吴朴臣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照相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作为摄影师,从理论上说,吴朴臣应该拥有足够的技巧,来实现灵魂照相的目的。
在灵魂照相的过程中,摄影师十分重要,就如扶手对于扶乩的重要性一样。④如以下的论文所揭示的那样,见陈明华:《扶乩的制度化与民国新兴宗教的成长——以世界红十字会道院为例(1921—1932年)》,《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明月仙子谈及照相之事时说,神仙虽自有光,但是否能拍摄到,却并非易事,取决于诚意与道缘,所以拍照最好由专人任之:
照法有数种,不一而足,未可以光限也。凡神仙能自发光,不藉人火,其像之清晰混淆,盖视乎人之诚意与否。或临照之时,虽照而神仙不在,则亦徒然而已,非但混淆,抑且无之。故非得宣允,不可凭也。有时虽未宣允,而偶时有诸形像,非常例也。总之,照相一道,照人与照鬼异,照神仙尤异。非有道缘,恐不能显。非不显也,神仙不临也。今幸有人焉,其照相一事,可专属一人,勿致临时匆促也。⑤《记载》(1918年八月十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9期,1918年。
明月仙子在其他场合也是反复交代,拍照者最好是同一人:“布设者须归一人同也,一以坚有缘,一以净器具,庶不致妄渎耳。”⑥《记载》(1918年八月十二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9期,1918年。
乩仙临坛照相,有时虽有“预告”,但多数时间都是随机而来,作为摄影师的吴朴臣,每日到坛等候。明月仙子对于吴朴臣的工作十分认可,而吴朴臣在拍摄中也极为虔诚,所以明月仙子特为吴朴臣赐名“朴诚”。⑦《记载》(1918年八月十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9期,1918年。1918年九月初七,明月仙子降乩命曰:“本坛摄务,不必逐日候此,即于逢五携镜来坛可也。”⑧《记载》(1918年九月初七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10期,1918年。之后即定下逢五拍照的惯例,这也多少减轻了一些吴朴臣的辛劳。
六、照相的“生意”
盛德坛之灵魂照相在社会上声名鹊起,也给盛德坛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也常以此作为吸引人参与之号召。如1921年10月18日,《申报》上刊载灵学会的广告云:
学会盛德坛以本月十九日为观音大士佛诞,假座新世界恭请大士降坛,宣谕救世宝训。是日下午二时起,至晚间十时止,在北部财神堂开鸾,无论何人均可前往参观。闻该会摄得灵魂照相数十种。定于是日陈列展览,并有白纸立轴一幅,能在静观五分钟内看出各种风景、人物、飞禽、走兽活动,如电光影戏云。①《灵学会在新世界开鸾》,《申报》1921年10月18日。
在《申报》的另一则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摄取鬼影”成了盛德坛招徕“生意”的最重要的“噱头”:
《灵学杂志》系宗坛出版,中华书局印行。他若颉典及鬼照种种之书,中华书局均有出售。最奇者,觇赐各种书画,光怪陆离,无不尽妙。现闻西坛订期摄取鬼影,届时必有一番热闹云。②《灵学西坛将摄取鬼影》,《申报》1923年6月8日。
灵学会在公布的第一次收支报告显示,收取的费用共有四项:会费及捐款(1035.6元)、杂志寄售款(854.2元)、杂志零售款(27.82元),以及照片售款(74.94元),虽然照片的工本费(71元)较高,照片出售这项“盈利”不多,但与杂志零售相较,出售照片还算是收入颇高的一项“生意”。③《灵学会第一次收支报告》,《灵学丛志》第1卷第10期,1918年。
灵魂照相在引来许多信奉者的同时,也引来不少请求者,他们希望为自己逝去的亲人照相,以慰哀思。第一个请求者是杨廷栋(1879—1950年)。杨廷栋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翻译家,曾留学日本,最早将卢梭《社会契约论》完整译成中文。
杨廷栋就是因为盛德坛“近于灵魂照像成绩颇著”④杨廷栋:《灵魂照像记》,《灵学丛志》第1卷第7期,1918年。而前去请求为自己已经去世28年的父亲照相的。请求之后,常胜子临坛判云:“再酌。”似乎无望。但一小时后又判云:“此事似属例外,诚意求之,亦难却也。姑开具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病状再核。”把资料都呈示之后,常胜子答应照相。拍照当日,共拍两张照片。第一张洗出后,能看出照片上人物为“半身小像,戴帽穿对襟褂……五官肖否尚难辨别,惟面形长而颏削,则固先父之遗容也”。⑤同上。第二张照片,“光颇暗淡,与生人照像迥殊。眉间额际酷与亡弟相似(先母在日,恒言亡弟之眉与先父无二)。眼角又与廷栋无异。面长颏削无须,帽与时制瓜皮帽不同,似为昔日之安睡帽。马褂似皮制而反穿者。据此言之,实有什之六七相肖”。⑥同上。但因杨父去世时,杨廷栋才13岁,距拍照之时已有28年,年岁已久,记忆不免模糊,故“虽形象在目,不免已涉惝恍,取片端视,疑非甚似,闭目凝神,又恍若酷肖。”⑦同上。此段文字所展现的矛盾心态,恰好可以说明,灵魂摄影相似与否,实取决于请求者的诚心与感情。照相成功之后,杨廷栋也不免为盛德坛之灵魂照相做些宣传,称拍照全程均是真实可信的:“照时一举一动皆亲自审究,更不应稍有疑点。是灵魂照像,已成不可诬之事实。而灵魂不灭,当然为不磨之理论。廷栋记此,非欲以神异眩人,区区之忱,盖有不能已于言者在焉。”①杨廷栋:《灵魂照像记》,《灵学丛志》第1卷第7期,1918年。
盛德坛前此的灵魂拍照,都是乩仙临坛,都是为仙人所拍,而为逝去的人拍照,是为鬼魂摄影,在盛德坛尚无旧例。杨廷栋是第一个请求者,但因最后约定的拍摄时间较晚,所以他并非第一个被拍照的家属。盛德坛的第一次鬼魂摄影,是在1918年农历的八月三十日,四川王姓叩请为其去世的父母拍照。此后又连续拍过4次:九月初七,为无锡人江姓之先母拍照;初七为安徽人黄姓之先父兄拍照;初八为扬州人张姓之先父母拍照;初九为杨廷栋之先父拍照。
接连有人请求,盛德坛似有应接不暇之累,而且有人在拍照之时,又请求加拍,均被回绝,最后,盛德坛发出禁令:“今奉镇坛使谕禁,不答游技。”②杨廷栋:《灵魂照像记》,“俞复之附记”,《灵学丛志》第1卷第7期,1918年。此后,盛德坛不再为鬼魂照相。
七、照相活动之消歇
九月二十六日,又有人叩问灵魂照相之事,土神张公武乩曰:前此乩仙已有三禁之文,禁拍照即其一也,“以后灵魂照相事,永远谢绝,不得妄渎”。③《记载》(1918年九月二十六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10期,1918年。
前此几个月,照相活动几成惯例,前期虽日期不定,但颇为连续。此时却宣布禁绝灵魂照相,实属突然。这一蹊跷的转折起自九月二十一日。当日先由土神张公武宣布新的镇坛正副使,即申本(孝廉公)和施平(茂才公),接着张公武宣示申孝廉公的谕示,虽然肯定了盛德坛的发展情况,但重点是对因社会上对盛德坛竞相仿效而带来的不良影响加以批评。
中国古代社会上乩坛很多,但就近现代社会来说,盛德坛当属最重要者。因其与上海灵学会的密切联系,以科学研究相标榜,加上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遂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盛德坛成立之后,社会上的仿效者甚多。其中鱼珠杂陈,有些乩坛借此追逐私利,亵渎神灵。二十一日坛谕认为,盛德坛影响所致,仿效者甚多,这些闻风步尘的效尤者,与盛德坛的本旨差异很大。盛德坛和灵学会亦是以“科学”为号召,强调的是科学和研究的态度,而非宣扬对于鬼神的迷信:
盖神仙意本不愿人崇奉,更不愿假为护符。故学人之迷信目此者,神仙不怒其狂,反赏其明,以遏巫觋之祸。神仙所不得不以神道设教者,劝善惩恶之旨也,非使人佞媚而流入迷信也。④《记载》(1918年九月二十一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10期,1918年。
更有甚者,借乩坛以敛财,祸端甚巨。流风所及,对于年轻人的学业和心智亦很为不利:
灵魂之学,乃高年修证之径,非少壮治己治人之时所遑及,年未半百之半,而醉心于归人之趣,其去死也不矣。年幼而暮气颓然,不可解也……今乳臭黄口,亦斤斤以乩术为能事,不驱世风于黑暗不止,谓之鬼魅世间矣。致演成北拳白莲诸创,更何堪问。①《记载》(1918年九月二十一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10期,1918年。
由此,二十一日坛谕提出了三条“禁令”:不问休咎、不判方药、不答游技。其中,第三条禁令,就是完全针对灵魂照相而言的:
现在各地已有灵魂摄影,假托灵学会名,从中取利。已出多张,竟有八仙之像,荒谬可笑。大都如绘图,并非影形,倘购得是项,一较便明。试思影形何以无显背虚实,其为叔敖衣冠,不待辨也。(李铁拐、张果老、老寿星等,竟有影片,可笑,读本坛《神光篇》便知如何,可不明言。李为金阙天尊,张为帝君,与纯阳或上或并,老寿星为南极星主,岂易狎暱,哈哈可笑)②同上。
此段文字对于了解盛德坛灵魂照相活动终止之原因,极为重要。这一坛谕之所以蹊跷,是因为许多观点与盛德坛一贯的说话相悖离。这段谈及灵魂照相的坛谕,与此前的照相活动,恰成反调。坛谕中还有一些违背日常见解的观点,比如说,盛德坛建坛以来,都希望乩坛能广泛传播,发扬光大,但二十一日坛谕却谓:
飞鸾显化,本是劝善惩恶之意,不谓去年盛德坛设立以来,各地乩坛因之大加增多,多至于林列罗织,甚为可怪。③同上。
又说:
昔日之乩坛,亦非不多。经学人不信之后,已稍杀,目为迷信,即有亦隐。盛德坛一唱于前,众乩坛同和于后,每藉口以灵学会为符,而究其旨,则大剌谬,长此以往,不特有败盛德坛名誉,抑且失乩坛之信用。扩充之,几致毁坏之矣……至不得已时,亦惟有撤销盛德坛,以灭各地假托之口。④同上。
继起者偏离了盛德坛之本旨与信誉,不是去纠正其偏颇之处,而是计划关闭盛德坛:这一说法其实也“甚为可怪”。正因为此,俞复随即发出质疑。坛谕出自“乩仙”,对于坚信鬼神实有的俞复而言,这份答词明显体现出一种极为不满的情绪。俞复提到自己听闻撤销乩坛的说法时,“不胜悚惶”,对于坛谕明显的逻辑问题,俞复对曰:
世上狡恶之人实无法以杜绝之。此辈假坛为护符,以敛钱者,即无乩坛为之假托,未尝无资以作恶之方。即使撤销盛德坛,而此等作恶之坛,未必即能销灭,况因噎废食,智者所不为。⑤《记载》(1918年九月二十二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10期,1918年。
坛谕中还批驳了所谓的“鬼神救国论”:
现值国家多故,尤宜慎惕。鬼神道张,国运可悲。⑥《记载》(1918年九月二十一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10期,1918年。
这一句话可以说是直接针对俞复而言的。针对吴稚晖所言:“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的说法,在《答吴稚晖书》中,俞复曾说:“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⑦俞复:《答吴稚晖书》,《灵学丛志》第1卷第1期,1918年1月。“鬼神救国论”,是俞复信仰扶乩之后一贯的观点。在回应坛谕的答词中,俞复曰:
必谓鬼神道张,国运可悲。此则弟子期期以为不然。盖今之败坏国家者,皆未尝知果有鬼神伺察之者也。若早令此辈略有闲居慎独自扪良心之习,则万不至无忌惮如此也。①《记载》(1918年九月二十二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10期,1918年。
在表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俞复已经在与“乩仙”直接唱反调了。
这一蹊跷变化的原因,笔者的推测是,在1918年,以《新青年》学人群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对于灵学会以及扶乩等“迷信”活动的猛烈抨击,多少分化和动摇了灵学会成员的观点和立场。在1918年八月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新青年》上密集发表的批评文章有:陈大齐《辟“灵学”》、②陈大齐:《辟“灵学”》,《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刘半农《随感录》(八)、③刘半农:《随感录》(八),《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钱玄同《随感录》(九)、④钱玄同:《随感录》(九),《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陈独秀《有鬼论质疑》、⑤陈独秀:《有鬼论质疑》,《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易白沙《诸子无鬼论》、⑥易白沙:《诸子无鬼论》,《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刘叔雅《难易乙玄君》⑦刘叔雅:《难易乙玄君》,《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等。大概某位灵学会的成员在这样的语境中,逐渐修正了原来的观点,并通过乩仙来进行了“传达”。但以俞复为代表的灵学会中坚分子,还是坚守着一贯的立场。这样,在外部的批判中,灵学会内部出现了分化,遂导致了后来灵魂照相活动的终止以及乩坛的撤销。但究竟是谁代表着坛谕所表达的立场,尚待进一步考察。
八、尾声
俞复对于灵魂照相之事还是念念不忘。
1918年九月二十八日,俞复叩问说,见无锡某处乩坛照相,有明月仙子和清风仙子之像,究竟确否。碧眼鬼仙乩曰:“明月仙子现因有要公,不来者久矣,岂复有余暇作戏耶?灵影事不止一处矣,所见闻甚有,亦未细勘详访,必问本真(即被照本身也)方知之耳。”⑧《记载》(1918年九月二十八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10期,1918年。
次日,常胜子临坛补充:“明月仙子未曾别临云云。又,清风仙子更不多涉世,故当另是一人耳。”⑨《记载》(1918年九月二十九日),《灵学丛志》第1卷第10期,1918年。乩坛否认了乩仙临坛照相的行为,其实也是重申了对于灵魂照相的禁绝态度。
盛德坛灵魂拍照之事停止之后,有关照相的讨论极少。1919年二月初十,土神张公武乩曰:“今年摄影一事,未蒙代摄二席允许,故尚未举行也,恐此举取消矣。”⑩《记载》(1919年二月十日),《灵学丛志》第2卷第1期,1919年。“代摄二席”即指明月仙子与常胜子,也是以往照相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两位乩仙。
这大概是盛德坛关于灵魂照相之事最后的说法了,自此以后,盛德坛的灵魂照相活动,真的是“取消矣”!
责任编辑:沈洁
*王宏超,男,1977年生,河南新郑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美学思想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美学)、比较美学、中国知识分子与巫术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