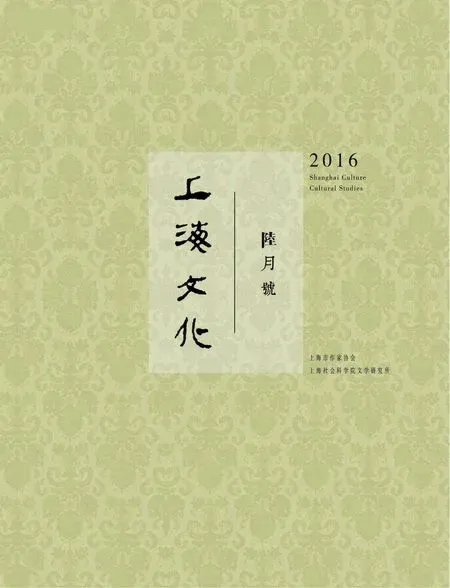刘勰的文学思想解读(下)
童庆炳
会议综述
刘勰的文学思想解读(下)
童庆炳*
内容摘要按照刘勰的文学思想,分别从“文本乎道”、“文体层面论”、“神思创作论”、“知音欣赏论”等四个方面来解读刘勰的《文心雕龙》。本文下篇涉及第三、四方面:第三,《文心雕龙》全书都涉及文学创作论,《神思》篇可视为刘勰的创作论的总纲。“神思”意谓形与心相离甚远,形在此而心在彼,是一种想象性的构思。刘勰“构象”论的加入,把“兴情”—“意象”—“言志”理解为创作的不可缺少的三阶段,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创作论。第四,刘勰鉴赏论提出的第一论点就是“知音其难”、“文情难鉴”,但紧接着又提出即“知音”不难,“文情”可鉴的论点。《知音》篇以“披文入情”或“觇文见心”提出解决文学鉴赏悖论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文心雕龙道文体神思知音
三、“神思”创作构思论
《文心雕龙》全书都涉及文学创作论,其中又以《神思》篇到《才略》篇所论述的创作问题最为集中。本节把《神思》篇看成是刘勰创作论的总纲,展开对《文心雕龙》一书创作论的阐释。“神思”的意思,按照刘勰自己的说法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解释,意谓形与心相离甚远,你的“形体”还在江湖,可精神却驰往远方庙堂之上,形在此而心在彼,这就是一种想象性的构思。
(一)“文不逮意”——“神思”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那么,刘勰的创作构思论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刘勰讲创作构思,力图解决的问题,在《神思》篇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文辞如何达到密不可分地贴切表达情意?“……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疎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这就是说,刚拿起笔的时候,觉得一切在构思的想象中都妙不可言,但刚刚才写了一半,觉得开始想象中的一半都还没有达到,感到一种挫败,这是为什么?原来想象中的情意可以凭空而翻新出奇,但落实到言辞,才发现那言辞的徵实性难于为巧的,要冲破言语的障碍,并不是容易做到的。尽管意象化成言语,言语化成意象,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有时候,意象化为言语,言语描写成形象,可以贴切到毫无间隔,可有时候那间隔则像有千里山峦障碍着。有时候觉得要表达的思想就在心里,可却要到域外去寻找。有时候觉得要表达的情思就在咫尺之近,却觉得中间横亘着万里的山河,根本摸不着边。笔者想起了巴尔扎克曾经说过的:谁不能叼着雪茄烟在树林中散步,编出几个故事来;但又有几个人能把自己编的故事惟妙惟肖地写出来而成为作家呢?的确,立意是容易的,立象也不难,难就难在言语的表现。我们可以模仿着说:谁没有一段感人的情,但要把它真实地艺术地表达出来,又有几人?其实,中国最早提出此问题的是《周易·系辞上》,其中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这里的“意”显然还是就“思想”、“意义”而言,并非说文学创作。晋代陆机《文赋》转到文学的创作构思上面来,他提出了“文不逮意”论,就应该说是属于文学构思论中遭遇到的问题了。《文赋》开篇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媸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每次读到优秀士人的创作,对他们的创作用心稍有体会。他们用言语遣词作文,那变化是很多的。但作品的美丑好坏,还是可以辨析的。每当自己也写作时,就更能体会他们的甘苦用心了。创作时常常害怕情意与物象不相称,作品不能契合情意。这是了解上的困难,是实践中遇到的困难。这里陆机提出了“物”—“意”—“文”三者的矛盾关系,就是说写作中经常遇到的是“意”不能与“物”相称,而“文”又不能与“意”相称,这就提出了创作构思中基本要解决的普遍问题。刘勰《神思》篇实际上是接着陆机说的,他希望通过“神思”来解决这个问题。《神思》篇认为这反映了“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即言语具有“徵实”的特点,不能完全表达构思中奇巧翻新的问题。所谓“徵实”即“实在”,但难道言语是实在的吗?刘勰的所谓言语的“徵实”性是否有道理呢?比如说刘勰常谈的“意”就不是实在的,“意”可以说论说文的思想,也可以说历史传纪文的“史实”,也可以说是文学创作中“情意”,一个“意”字可以随语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义涵,怎么能说它“徵实”呢?这只能说,刘勰看到了情意之“奇”与言语之“实”之间确有一定的距离,勉强可以成为一种说法。
按照现代语言学的说法,语言是一种符号,它只是具有暗示性、省略性,它无法描写现实中的一切情景与物象,更无法毫无遗漏地描写人的一切复杂而丰富的想法。这一点法国著名作家萨特说得很有道理:“实际上,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到,一件精神产品自然而然是暗示性的。即便作者旨在完整无遗地表现对象,他永远不可能说出一切,他知道的总比说的多。这是因为语言的省略。”①萨特:《什么是文学?》,《萨特读本》,桂裕芳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4页。春天来到的时候,如果我们听到了一声布谷鸟的叫声,那么春天的感觉尽在不言中了。“神思”要解决的难题就是使我们情意与景象、物象完全地契合,拒绝“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状况的发生。
刘勰又是从哪些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二)“积学”与“虚静”——主体修养的双向建构
为了解决“神思”活动的基本问题,刘勰首先着眼于主体的双向建构,即用力的方面和不用力的方面。用力的方面,刘勰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可以说,这些是讲儒家的道理。积累学识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明辨事理来丰富自己的才能禀赋,学习观察和研究周围世界的本领,顺着文思来寻觅文辞,这些本领的获得是解决“言不逮意”的学识和才能上的基础,是要长期用力的方面;但刘勰同时又提出主体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可以说,这些是讲道家的道理。
儒家的主体修养的建构讲“功以学成”,讲“才”、“气”、“学”、“习”(见《体性》篇),是要下死力气,包括先天的“才”、“气”,也是需要开发才能获得的,因为这是人的一种潜能,只有在学习的实践中,才能开发为现实的能力。至于“学”和“习”,那是外部的知识学问,不经实践,如何能使外部的转化为内部的呢?所以刘勰提出“因内符外”、“表里必符”的主张。所以整篇《文心雕龙》凡遇到问题时,就会有一个笼统的回答:“还宗经诰”,这就要读“五经”,重积累,以才学的功力为第一。《神思》篇举例说:“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掇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为何思之缓?这就是“积学”的要求所致。
但刘勰又认为,主体修养还要讲道家的“虚静”的道理,所以才有“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这十六字要求。这十六字意思是:酝酿文思,重在虚心安静,疏导五藏,摒弃功利和成见,有洁净精神。虚静的思想开始于老子,但真正把这思想引进艺术领域的是庄子。庄子《达生》篇有一则寓言故事:梓庆削木为,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曰,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这意思说:梓庆能削刻木头做,做成以后,看见的人无不惊叹他的鬼斧神工。鲁侯见到便问:“你用什么办法做成的呢?”梓庆回答道:“我是个做工的人,会有什么特别高明的技术!虽然如此说,我还是有一种本事。我准备做时,从不敢随便耗费精神,必定斋戒来静养心思。斋戒三天,不再怀有庆贺、赏赐、获取爵位和俸禄的想法;斋戒五天,不再心存非议、夸誉、技巧或笨拙的杂念;斋戒七天,已不为外物所动仿佛忘掉了自己的四肢和形体。正当这个时候,我的眼里已不存在公室和朝廷,精神专一而外界的扰乱全都消失殆尽。然后我便进入山林,观察各种木料的质地;选择好外形与体态与最为吻合的,这时候已形成的的形象便呈现于我的眼前,然后动手加工制作;不是这样我就停止不做。这就是用我木工的纯真本性融合木料的自然天性,制成的器物疑为鬼斧神工的原因,恐怕也就出于这一点吧!这就是道家提倡的虚静。它的最重要之处就在于可以达到“以天合天”的境界。刘勰的“十六字”秘诀应该说来源于此。“”是一种具有艺术性的形似夹钟的精致的匣子,可以视为一种艺术品。刘勰的“虚静”说与文学创作所要求的无功利的审美精神状态是一致的。
(三)“神与物游”——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交游,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神与物游”作为主客体的交游活动,在刘勰看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神与物游”是人的精神移入物象中,达成心与物交接时应有的氛围。首先,进入创作构思,要“物沿耳目”,但仅用感觉是不够的。所以刘勰提出“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意思是,神思想象开始之际,各种念头纷纷涌现,要在没有形成的文思中孕育合乎规律的内容,在不确定的文思中刻镂形象。但是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营造氛围:登山的时候要让情思充满山色,观海的时候要让情感移入于海,使情思中腾涌起海的风光,那么我的才能之多少就与风云并驾齐驱了。这里的山、海、风、云都是物,这就是与“物沿耳目”有关,但神思想象中要使情感移入物,使物皆著情感的颜色,形成一种进入创作想象的艺术氛围。这一点,前人所见不多,可以视为刘勰的理论创造。无论作者写什么,都要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相互动,使物移入于心,又使心移情于物,营造出一种物我之间的对话情境,即笔者此处所说的“氛围”。
第二,“神与物游”是主客体交接所形成的审美活动,这里的关键是一个“游”字。“游”字揭示神思想象的本质,也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游”,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旌旗之流也。流宋刊本皆同。集韵,类篇乃作旒。俗字耳。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称流也。”游就是风中旌旗的飘动,它的本质是自由自在、变动不居,如同游戏一般,具有不确定性,不可言说性。为什么这种“游”是解决“文不逮意”问题的前提呢?因为“神与物游”不是“神思”的目的,“神思”的目的是“物我交融”。因此只有在主客交游活动中,经过反复的多样的丰富的物与我的交接尝试,最终才可能达到物我交融。这样才能落实到文辞上面。
第三,刘勰提出“神与物游”实现的关键是志气、物象和辞令的一致。所以刘勰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这就是说,“神与物游”能不能实现呢?即“通”还是“塞”呢?关键是“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和“辞令管其枢机”。“志气”即作家的情感和生命力,“志”,思想情感,一般是后天形成的。“气”,即曹丕《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以气为主”的“气”,指人的生命的力。刘勰将气之“清浊”改为刚柔,具体指出生命力有刚与柔两种类型。“志气统其关键”就是指作家思想感情和个人的血气对艺术想象的制约问题。艺术想象必然有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个人生命力的投入,思想情感和生命力一方面是艺术想象的动力,一方面又对想象的性质、内容、走向、路线、范围,起支配作用。就是说,艺术想象也有一个节制问题,过分放纵,就会变成胡思乱想。刘勰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提出“物沿耳目”的确定要求,又以思想情感和生命力去“统”的问题,“统”就是控制。用什么来控制呢?用“志”和“气”。可以说前者是思想感情的控制,后者则基本上是艺术生命力的控制。如果思想感情和生命力对艺术想象控制得好,那么“神与物游”就“通”,否则就“塞”。这样刘勰就找到了文思通塞的第一个内在的原因,即主体的创作心理的原因。不仅如此,刘勰又找到了文思通塞的第二个原因,这就是“辞令管其枢机”。这里的“辞令”还不是指写出来的文字,而是指作家艺术想象中如何确切地运用语言与形象匹配的问题。在刘勰看来,想象或者说“神思”,并不是物象的单纯的在脑子中出现和变化翻腾的问题,物象的出现总是配合着一定的语言的。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神思想象也是一种思维,既然是思维,那么就必然要运用语言,甚至我们必须在进入语言的情况下才进入对物象的把握。思维与语言是同一的。例如,杜甫听说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立即想到可以返回北方了,就想用什么言辞来表达,于是四个地名进入他的想象。于是两句诗涌上心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向洛阳”。就是他神思想象时伴随出现的言语。能不能寻找到适当的言语,也是想象“通塞”的“枢机”。这样,刘勰就从创作心理(“志气”)和创作语言(辞令)的双重视角来揭示“神与物游”“通塞”的原因,深刻揭示了艺术想象的规律,为解决神思想象的基本问题奠定了基础。
(四)“窥意象而运斤”——“神思”的最后阶段,“神思”问题的完满解决
《神思》篇是从物—情—言三者关系的角度,作了全面的论述,阐明了创作主体运思的规律,集中解决了“文不逮意”的问题。以物为起点,以情为中介,以象为成熟,以言为结束,整个创作过程清晰可见。从刘勰《神思》篇“窥意象而运斤”这句话来看,他的“意象”是指创作构思的最后阶段,艺术想象中的意象和意象体系在胸中涌动等待形诸笔墨的那种艺术形象(也可以说“心象”),文与意不相称的问题也就在这最后形成的“意象”中解决了。
中华古代文化中,早就有“意象”一词。根据安徽大学教授顾祖钊的考察,自古至今的“意象”可以分为五种:①顾祖钊:《论意象五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在一般的“表意之象”或观念意象的意义上来使用,汉代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提出的意象观属于此种。②由于文艺心理学作为交叉学科的出现,心理学意义上的表象,也被翻译为“意象”,在心理学和文艺学两个学科都有学术意义,因此应当承认心理意象存在的合理性。③刘勰提出的“内心意象”,是指艺术构思的结果和艺术传达前的“心象”,在创作学中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理应继承。④叶燮提出的“意象”是一种达到艺术“至境”的意象,这是一般“表意之象”的高级形态和理想形态,一种可以与意境概念并列的艺术至境形态,也应接受。⑤还有一种“泛化意象”,是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通称“意象”。因为“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理论,一般称它为艺术形象或文学形象,为了减少理论术语的混乱,顾祖钊主张废除“泛化意象”,而代之以久已习惯的“艺术形象”或简称“形象”的称谓,这是对现代文论传统的尊重。显然,一个理论范畴的取舍应尊重历史和学术的科学性。①这些见解都是很有见地的,应该受到重视,并加以发扬。但是作者当时更重视是在阐述王充的“表意”之象。
王充的“表意”之象是什么意思呢?有两段话是这样说的:其一,“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意取名”。其二,“礼,宗庙之‘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之庙……虽知非真,示当感动,立意于象的”。第一段中的“熊麋之象”,是画在箭靶上的动物画像,而不同的动物画像,却是不同的爵位的象征。据《仪礼·乡射礼》的记载,对于不同爵位的人,其箭靶的材料、质地和画像亦有不同的规定:“天子熊侯,白质;诸侯麋侯,赤质;大夫布侯,画以虎豹;士布侯,画以鹿豕。”显然,这种画像象征着等级森严的爵位。《礼记·射义》中说:“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大夫、士。”又云:“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故天子大射,谓之‘射侯’。”久而久之,箭靶也被称为“侯”,成了人们在乡射之礼上猎取爵位的对象。不同身份的人,只能射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侯”。“射侯”也成了“男子之事”和“饰之以礼乐”的特别隆重的富有诗意的文化活动。王充这里重点说明的是:人们明明知道那些箭靶上的画像是假的,为什么还要“礼贵”它们呢?就是因为它们是“示意取名”的表意之象,由于已赋予这种“意象”以特殊的含义,因此它们就成了人们“礼贵”的对象。为了说明“意象”的象征的原理,王充又举了一个更为常见例子,即第二段话所说的“宗庙之‘主’”。宗庙中的“神主牌”,原来不过是一块一尺二寸高的木牌,由于上面写上了先祖的名字和神位,这样“立意于象”的缘故,所以,孝子虽知神主牌是假的,但在先祖的牌位前也十分感动,这就是“意象”的特殊效果。看来,王充是有意突出他所创立的“意象”概念,才这样反复说明的。而且,王充提出的这种“意象”,明显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脱离作者后而显现于人们眼前的一种艺术形象,不同于刘勰所说的作为艺术构思结果的、尚存在于作者胸中的内心之象。说它是艺术形象,一是因为它从属于“饰以礼乐”的古代诗性文化的一部分;二是因为它是人对动物形象的一种艺术把握和重塑,一种绘画的结果。第二,它是一种“表意之象”,“立意于象”是它的塑造原理。它是为表达某种观点和意思而创造的形象,并为表达某种观点和意思(即义理)服务,所以,它应当是艺术形象的一个特殊类型。第三,它是采用象征手法塑造的形象,因此又可以称为“象征意象”。所谓象征,也是一种广义的比喻,它与一般比喻的区别是:在比喻中喻矢与喻的同时出现,而象征里只有喻矢,喻的是什么,全靠人们去猜测。如“熊麋之象”究竟象征什么,是由特定的文化传统及其语境暗示的。由于王充提出的“意象”概念显示了这样三个特点,因此它更像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学术术语,不像《汉书·李广传》中的“意象”,出现得那样偶然和随意;同时与刘勰的“意象”概念也完全不同。①参见顾祖钊:《论意象五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还可参见作者论“意象”的同类文章。顾祖钊的这些见解,把王充的“观念意象”解释得很清楚,正如他说的“与刘勰的‘意象’概念也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虽然王充的“意象”论也是针对艺术来说的,但它是作品实现了的意象,属于艺术形象中的“象征形象”,的确与刘勰《神思》篇中所提出的存在于作者胸中并未在作品中实现的“意象”是有严格区别的,一个在作品中,一个停留在胸中,不可同日而语,要严格区别开来。因此,它不是刘勰胸中“意象”说的来源。
从理论上给予刘勰启发的,可能就是《周易》“卦象”。中国古代理论中,清楚地说明如何从思想感情到语言文章的首推《周易》,《周易·系辞上》谈到卦象时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故谓之象。”所以《周易》要提出“立象以尽意”。这是最早的“象”论,属于哲学,并没有转到文学上面来。到魏晋时期的王弼解释《周易》时曾说:“夫象者,出意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这就把言—象—意三者关联起来,并予以清楚的说明。但这还是属于哲学方面的论述,并没有把它引入文学理论。刘勰肯定对《周易》十分熟悉,对于王弼的理论更是印象深刻。所以他第一次真正地把“象”论引入文学理论,就是《神思》篇中的“窥意象而运斤”。这样,这个在想象极致中出现于胸中的有情有景的意象,上接“情”,下接“言”,形成了情—象—言的完整的文学构思和表达的链条,很好地解决了“文不逮意”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刘勰的“意象”还是心中构思过程未形诸文辞的“意象”,当然,这个胸中“意象”,已经是主观的“意”与虚构的“象”的融合,与文本中的艺术形象有相似之处,但又不能把它与文本中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艺术形象等同起来。因为这一胸中“意象”,似乎可以窥见,但仍然是活动着的变化着的动荡着的,随时可以作出变更,还未形诸笔墨。
以下考察刘勰《神思》篇解决“文不逮意”问题的途径。《神思》篇中说:
……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遯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枢机”(与下句的“关键”意思一致)指事物的关键。关键通了,事物的面貌就显露出来。要是关键堵塞了,那么精神涣散,事物的面貌就藏匿起来。这都是过渡性的话,下文则是达到“窥意象而运斤”或形成胸中意象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要求主体的心灵纯净专一,不要受外物的干扰,达到“虚静”境界。刘勰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陶钧”原指瓦器或制瓦器的圆转器,这里引申为“酝酿”的意思,就是说酝酿文思,可贵的是作者的心灵要进入“虚静”状态。这里的“虚静”不是指空无所有,它相当于荀子所说的“虚壹而静”,即专注、入神、空明、纯净的状态。这种进入“虚静”状态,按照刘勰的理解,需要“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疏瀹”、“澡雪”最早见于《庄子·知北游》:“老聃曰:汝齐(斋)疏瀹,澡雪而精神”,“五藏”是说人体的心、肺、肝、脾、肾。中医典籍《灵枢·九针论》:“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也。”“疏瀹五藏”,即从生理上疏通五藏;“澡雪精神”,“澡”洗涤,“雪”,洁白,“澡雪精神”,即从人的精神上纯净自己,从生理的精神的世界,都要做到极度的无功利,排除一切“污秽”的思想,那么“虚静”状态就会出现。但是,“虚静”状态又不是人顷刻之间的心理的调整,是一个长期修养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做到四点:①“积学以储宝”,长期积累,丰厚学识。②“酌理以富才”,斟酌事理,丰富才能。③“研阅以穷照”,“研阅”是指从精神的角度钻研所阅历的生活,这样对生活才能有透彻的理解。④“驯致以怿辞”,“驯”,顺也;“致”,情致,思致;即顺着情致或思致而寻找文辞。有了以上四个条件,那么,人的心就会深通玄妙的道理,这样就可调动声律文字来下笔了。以上意思笔者在上文中谈到,但未说得如此细致。此时,作者不要再东张西望,而是窥看着胸中出现的“意象”来运笔写文了。这才是创作中“御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即创作成功的关键。上述“积学以储宝”四条件的累积是“虚静”境界的原因,而“虚静”境界又是孕育胸中意象的原因,这里有着这种层层的因果关系,都是长期修养的结果。所以《神思》篇说:“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思契,不必劳情也”,因为是自然地长期修养之功,不必临时费力,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刘勰所说的“窥意象而运斤”的基本义涵,是指艺术想象中的具有审美性的意象和意象体系在胸中涌动,等待形诸笔墨的那种艺术形象的出现,这种状态的出现,意味着“文不逮意”问题的解决。
胸中“意象”这因果关系的生成,是一个长期修养的过程,是自然的过程,不是临时调动心理机能刹那间的事。笔者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中国“意象”生成的理论与西方的有关理论在文化上有着根本的区别。瑞士—英国学者布洛所谓的“距离”说,似乎也是讲审美的瞬间,包括创作的瞬间,要排除外物的干扰,远离功利的得失。布洛(1880—1934年)《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一文中,曾以举例的形式来展开他的“心理距离”说的论述。他说,假设海上起了大雾,这对于坐在某艘客轮上赶路的人来说,是一件极为伤脑筋的事情,除了怕延误行程之外,还有那难以预料的危险,如轮船触礁之类所引起的恐惧。船只的胡乱漂动,发出的警报,打乱了旅客的心神,焦急之情、紧张之感油然产生,“一切都使得这场大雾变成了海上的大恐怖”。但布洛接着说,“海上的雾也能够成为浓郁的趣味和欢乐的源泉”,那就是把“注意力”转向“客观地”形成的周围的种种风物——“围绕着你的是那仿佛由半透明色的乳汁做成的看不透帷幕(意象——引者),它使周围的一切轮廓模糊而变了形,形成一些奇形怪状的形象……”总之,大雾一时使周围美景如画,“有如强烈的亮光一闪而过,照得那些本来是最平常的、最熟悉的物体在人们的眼前突然变得光彩夺目”。他最后说:“这是一种看法上的差异,是由于距离从中作梗而造成的,这种距离就介于我们自身与我们感受之间”,他甚至说:“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距离乃是一切艺术的共同因素。”①参见蒋孔阳主编:《20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41-243页。实质上,布洛这里讲的距离,既不是时间的距离(过去很久的事),也不是空间的距离(人们此时就在轮船上),而是一种“心理距离”,更直白地说,就是“注意力”的临时转移。他提出的这个理论的实质也在“一开始就是由于使现象超脱了我们个人需要和目的的牵涉而造成的”,即摆脱了人们的功利要求而出现的。布洛的理论是不符合实际的,没有根据的,怎么能在顷刻之间由于“注意力”的临时转移,就能把“大恐怖”变成观看美景呢?这完全不可能。试想,邻居的房子起火了,眼看也要烧到自己家,而此时你却能注意力临时转移,去“欣赏”那红色火焰鲜艳的美丽的跳动,而把危险放在一边,谁做得到呢?布洛的理论完全是离开人们实践的无根之谈,是不足为凭的。如果真有什么“心理距离”也是长期修炼的结果,绝不可能是临时注意力转变的产物。所以西方文论中以摆脱功利目的为关键的“距离”说,是不切实际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勰以“虚静”境界达到的“意象”,与西方以注意力转移所看到的“意象”,是不一样的。这是文化的差异所致。中国古老文化讲究人的长期修养和锻炼,认为这样才能达到目标。刘勰说的“积学”、“藏器”、“蓄素”等,都有长期积累的意思。西方文化有讲究长期锻炼和实践的方面,但更常讲究临时性的心理调整,认为许多事情是瞬间的努力就可以达成的。对于中西方这种区别,我们必须有深刻的理解。
刘勰胸中“意象”说,对于中国诗论、艺术论都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汉代和汉代以前的诗学,基本思想就是“诗言志”。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感物”而产生“情志”,然后是“情志”以文辞表现出来。刘勰的《情采》篇,强调“情者文之经,辞者文之纬”,经纬编织然后诗成,似乎不要其他东西了。这都是汉代关于诗学理论“感物吟志”思想的另一种复制而已。所以历来谈到诗,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些理论不能说不对,但可以说都不够完善。《神思》篇“窥意象而运斤”中的胸中“意象”可以说真正反映了诗歌创作的实际,“构象”论的加入,把“兴情”—“意象”—“言志”理解为创作的不可缺少的三阶段,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创作论。这样,钟嵘《诗品序》中的“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时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戌,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顷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以展其义?非长歌以骋其情?”这些真实的说法,才有落脚点,离开这些意象,诗歌只是空洞地喊叫,这能说真的抒发感情吗?所以,从“感物言志”理论,发展为“感物”—“意象”—“言志”理论,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完整化过程,从此诗学发展进入坦途,这是极为有价值的。
四、“知音”欣赏论
“知音其难”是《知音》篇第一句:“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这一句一泻而下,似乎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势。纪昀评:“‘难’字为一篇之骨。”这是有体会之言。“知音难”、“知文难”一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感叹。《吕氏春秋》中所讲的伯牙鼓琴、钟子期为知音的故事,就是古来强调的无论是品人还是品文,要达到“知音”是很难的。刘勰谈知音难,不但因为古籍都谈到此点,更有他切身的体会。根据《梁书》记载,刘勰自写了《文心雕龙》,“自重其文”,深怕没有知音,而不能留传下去。他不得已求助于当时文坛领袖沈约。刘勰求见沈约的情形令人心酸:他背着用竹简写成的四万余字的沉甸甸的书稿,等待沈约的车出来。车出来后,就把车拦住,求见沈约。从中可想见刘勰卑躬屈膝的样子。沈约伸手取来,回家一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把《文心雕龙》放在书案上,随时翻阅。《文心雕龙》终于有了第一位知音——这就是沈约。刘勰也许有感于此,他的鉴赏论提出的第一论点就是“知音其难”、“文情难鉴”。但刘勰在提出第一个论点之后,又提出第二个论点,即“知音”不难,“文情”可鉴,所谓“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一方面是文情难鉴,可另一方面又是文情可鉴,这就提出了一个悖论。如何来解决这个悖论呢?这就是刘勰《知音》篇想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刘勰怎样来解决这个悖论呢?“披文入情”或“觇文见心”就是刘勰本篇提出的解决文学鉴赏悖论的基本思路。
(一)“知音”作为文学鉴赏的最高境界
欣赏文学作品时达到“知音”的地步,是中国古代文论欣赏论的特点。这与西方后来提出的文学接受论是不同的。接受论承认“前见”、“前理解”,对于同一作品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甚至相反的解读。当然,西方的这种文学接受论,中国古代也有,后面将要谈到。
刘勰的《知音》篇重点不在对作品的评论,而在对作品的鉴赏。应该看到,评论是对作品的判断,是要下理性的结论的,而欣赏则是对作品的感性的欣悦体认,是不必下理性的结论的。
那么,刘勰是怎么理解欣赏的呢?他的见解在哪里呢?
刘勰以“知音”作为鉴赏的篇名,这本身就可以看出,刘勰对于文学鉴赏提出了几乎难以企及的高境。所谓“知音”的事例,一般认为就是前面提到的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吕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列子·汤问》篇有相似的记载,点出了“知音”二字:“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念”属于作者,“得”属于读者,两者一定要完全相应。刘勰在《知音》篇中以对音乐的鉴赏为喻,来说明他所理解的文学鉴赏是要求追寻作品原初意义的一种高境。
中国古来的关于文学鉴赏有两种不同的阐释要求。第一种就是“知音”式的阐释要求,要求鉴赏者与创作者达到心心相印,即鉴赏者一定要追寻到创作者本来的创作企图。所谓作者在作品之中的所“念”,而鉴赏者必“得”之。作者之所“念”与鉴赏者之所“得”,两相符合,一点都不差,两者进入同一个艺术世界,同一种氛围,同一种情调,同一种情志。这种“知音”式的艺术鉴赏高境可能是从孟子的“以意逆志”理论那里来的。《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意思是说,不能因为个别的辞和句曲解整篇的意义,也就是不能断章取义,而应该根据作品的整体去领会作者的创作意图,还原其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所谓“逆”,是一个过程,就是欣赏者以己之意去迎取、追寻、探求诗篇的意义,务求最终与作者所表达的本初情志相一致相吻合,达到冥合为一的地步。第二种就是“诗无达诂”的阐释要求。“诗无达诂”是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他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提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是“训诂”,是用今言解释古言。董仲舒的意思是,《诗经》没有统一的解释,《周易》无法达到占卜的意图,《春秋》的含义无法全部表达于文辞。这“诗无达诂”的本意是为汉儒随意解释《诗经》、《周易》和《春秋》寻找理论根据的,但由于它考虑到了诗篇的多义性,读者主观的不同状况,也有其合理性。而且这种说法与《周易》的“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相吻合,因此广为后代诗论家所接受。这第二种阐释要求,就不要求欣赏者与作者的本意相一致,各人面对同一首诗,可以有不同甚至完全不同的理解。发展到后来,有的诗论家就提出“诗为活物”(明代钟惺)、“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明代谢榛)、“解诗不可泥”(清代何文焕)、“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清代赵翼)等。
刘勰的《知音》篇标举的是第一种阐释要求,也可以说是鉴赏的高境。即要求像伯牙与钟子期的那种作者与鉴赏者的关系。所以《知音》一开篇就大喊“知音其难”。达到“知音”的境界,鉴赏者要返回到作者赋予作品的本初意义,这是刘勰对于文学鉴赏的一个基本假设。现在看来,作者的写作历史属于过去,甚至是遥远的过去,要以作品的指涉去追踪过去作者写作时的种种事态原委已经不易,而要以鉴赏者的解读去坐实作者创作时的主观意图,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但刘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提出了“披文入情”说(或“觇文见心”说)。“文”与“情”的关系,是刘勰《文心雕龙》论述的一个重点。刘勰在《体性》篇中提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这个思想与《知音》篇所说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是一致的。创作是从情到文,即“为情而造文”(《情采》),也就是从隐至显,从内至外;而鉴赏则是从阅读、探求“文”的整体入手,最后返回到创作者创作的意图和情志中,也就是从显回溯到隐,从外回溯到内。这个过程可不可能呢?刘勰认为是可能的。他肯定地说:“源波讨源,虽幽必显。”尽管认为“披文入情”有种种困难,但只要掌握“术”和“律”,“知音”仍然是可能的。他于是先分析了“文情难鉴”的原因,再提出文情可鉴的规律:包括鉴赏者的起码的修养、必要的步骤、合理的方法、鉴赏的关键、鉴赏的高潮等。
(二)“披文入情”的障碍
刘勰在《知音》一开篇就认为“知音其难”,“披文入情”有种种障碍,提出了“文情难鉴”的五种原因或“披文入情”的五种障碍。
五点原因,其中三点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一点是鉴赏客体的复杂性造成的,一点是鉴赏主体的复杂性造成的。
第一,“贵古贱今”。刘勰以秦皇对待韩非、汉武对待司马相如为例,说:“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战国时期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和《孤愤》篇等文章,秦始皇读了,觉得太好了。曾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韩非子到了秦国,不久就遭到冷遇,后来竟然被秦始皇囚禁起来,最后被害。汉武帝读了《子虚赋》,也曾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觉得很遗憾。可后来把司马相如找来了,汉武帝始终视之如倡优,后者未得到重用。这就是说,离得远的人,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能客观看待,就会觉得他的文章好;一旦离得近了,各种利害关系就产生了,不能客观看待,那文章就不被看在眼里了,这就是刘勰所说的“贱同而思古”或“贵古贱今”。这一现象多有学者谈到,在刘勰之前,刘安主编《淮南子·修务》说:“世俗之人,尊古而贱今。”王充《论衡·超奇》篇说:“俗好高古而称好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密酪辛苦。”在刘勰之后,白居易《与元九书》:“夫贵古贱今,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他以韦苏州为例,韦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这些说明了“贵古贱今”、尊远贱近,是人之大情,是品人评文中普遍现象。刘勰把这一点看成是“披文入情”而达“知音”境界的一大障碍。
第二,崇己抑人。“崇己抑人”或“文人相轻”是“文情难鉴”的第二种原因。刘勰以班固、曹植为例说明此点。刘勰说:“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第一个例子是班固嗤笑傅毅的问题。刘勰可能是从曹丕《典论·论文》借鉴来的,曹的文章说:“文人相轻,自古亦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这“下笔不能自休”的嘲笑是怎么回事?查《后汉书·傅毅传》:“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点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乃依《宗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驷为主簿。及宪迁为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由此看来,傅毅虽然在文学史上似乎没有留下太多佳作,可能因为他太看重歌功颂德,没有反映现实生活,但文才还是不错的。班固自己也在朝廷上,所作的赋无非也是歌功颂德,他有什么理由嗤笑傅毅?原来傅毅曾因《洛阳赋》被拜为郎中,迁为兰台令史,但后来所作的《反都赋》内容文字重复《洛阳赋》,这才被自恃甚高的班固嗤笑为“下笔不能自休”。班固批评傅毅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背后嗤笑就显得过分了,的确是“文人相轻”。
至于陈思王曹植议论陈孔璋、丁敬礼和刘季绪三件事情,均见曹植《与杨德祖书》。对于陈琳(字孔璋),曹植说:“以孔璋之才,不闲(娴熟)于辞赋,而多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写文章)盛道仆(指曹植)赞其文,夫钟其不失听,吾亦不能忘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曹植认为陈琳对于赋体不够娴熟,硬要说自己与司马相如风格一样,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狗。而且前次,曹植也已有文章批评他,陈琳反而觉得曹植是赞美他。这件事很可叹。曹植真怕后来的人会嗤笑他。应该说曹植论陈琳之才,是很允当的,而且光明正大,不是随便议论,属于正常的文学批评。可刘勰把曹植对陈琳的批评视为“崇己抑人”、“文人相轻”,这个看法就未必是正确的。丁廙(字敬礼)是曹植的朋友,《与杨德祖书》中说:“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为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畏后世之嗤余也。”刘勰也把曹植评丁敬礼这段话当作“文人相轻”的例证,也不知他是何意思?是不是他把曹植批评陈琳与赞扬丁敬礼对比起来看,是否说曹植一方面赞扬跟自己关系好的,另一方面批评跟自己关系比较淡的人,这不太正常。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曹植的《与杨德祖书》评论当时几位作家,都是比较客观的、得当的。刘勰所举的例子并不合适,但他讲的“文人相轻”的事情的确是“文情难鉴”的原因之一。
第三,信伪迷真。“信伪迷真”是“文情难鉴”的第三种原因。刘勰以楼护为例,说:“至如君卿唇舌,而缪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咨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以上所言,并无事可考。不知刘勰当时有什么资料根据。但人们在鉴赏中“信伪迷真”的情况是有的。
以上三点为人为的原因,属于鉴赏过程中人为的障碍。鉴赏者只要端正态度,排除私念,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第四,形器易徵,文情难鉴。这一点是刘勰基于鉴赏客体的复杂性而提出的。刘勰认为,就是普通的物体,有时候都很难甄别,何况是具有情感性的文学呢。刘勰说,麒麟、凤凰和獐子、野鸡相差甚远,珠玉与碎石也大不相同,光天化日之下,谁的眼睛都可以看清楚它们的形状。然而,鲁国的家臣把麒麟当作獐子,楚国有人把野鸡认作凤凰,魏国的农夫把夜光宝珠看成怪石,宋国的旅客把燕国的碎石当成珠宝。由此可见,本来有形之器容易验明,还发生这些错误,那么文章是蕴含情感的事物,谁敢说容易分清优劣呢?事情的确是如此,文学作品作为鉴赏的客体是很复杂的,古人反复提出的“言不尽意”、“文外重旨”、“意在言外”、“韵外之旨”等情况,或本篇所说的“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等情况,说明文学作品因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优劣是很难说清楚、讲明白的。有的诗篇或诗句为什么会产生多种多样的解释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诗篇或诗句本身可能有多重所指。
第五,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文情难鉴的原因,除了鉴赏客体的复杂性以外,还有鉴赏主体方面的原因。刘勰说:“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者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这段话包含了三个意思:一是指人的性格不同,如慷慨者、蕴藉者、浮慧者、爱奇者等,对于作品的格调各有各的喜好;二是指人们所站的位置不同,不能全面地把握作品,出现“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情况;三是鉴赏者主观情绪的偏颇,合自己口味的就称赞,不合自己口味的就反感,各人持片面的见解,去衡量变化万端的作品。这就是所谓的“知多偏好,人莫圆该”。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总之,是说鉴赏者的个性和性格不同,审美趣味不同,对作品会有选择和排斥,会有不同的理解等。
上面第四、第五两点说明鉴赏客体和主体的复杂性是很难避免和克服的,这是“文情难鉴”的基本原因。
(三)“披文见情”的可能
可喜的是刘勰的论述没有停留在“知音其难”、“文情难鉴”这一命题上面,作者又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命题,这就是“知音”会有、文情可鉴,“披文见情”是可能的。刘勰如何来论证这个命题呢?刘勰提出了“术”(“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和“律”(“独有此律,不谬蹊径”)的论点,认为文情可鉴建立在鉴赏者起码的修养、观察的方面、合理的方法、鉴赏的关键、鉴赏的高潮的认识、掌握的基础之上。
刘勰从以下四点来说明“披文见情”的路径或文情可鉴的原因:
第一,鉴赏者的修养——“务先博观”。刘勰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含有多阅读、多实践、多比较的意义。“博观”,则含有多积累、多观察、多体验的意义。他的意思是,看过高山大川的人,才会知道土堆的矮小,了解大海宽广的人,才会知道水沟的狭窄。这的确是说出了鉴赏者应有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评价作品不存私心,憎恨的态度不带偏见。按照现代审美心理学的艺术投射的观点,我们在鉴赏的时候,是把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投射到鉴赏对象上面,因此往往是“所见出于所知”。为什么今天的人们能同情林黛玉,是因为我们了解自由爱情的可贵和争取之不易。在200多年前,在《红楼梦》刚刚开始流传的时候,许多人满脑子的封建思想,还是男女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观念,因此那时候对于林黛玉争取自由婚姻的理想就很难理解,更谈不到欣赏。
第二,鉴赏应考察作品的各个方面——“六观”。刘勰认为,“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这“六观”说历来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重点。有的说“六观”是鉴赏的标准,有的说“六观”是方法。其实,这种争论意义不大。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刘勰说的“六观”分别指什么,然后我们才会知道它的性质。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解释说:“一观位体,《体性》等篇论之。二观置辞,《丽辞》等篇论之。三观通变,《通变》等篇论之。四观奇正,《定势》等篇论之。五观事义,《事类》等篇论之。六观宫商,《声律》等篇论之。大较如此,其细条当参伍错综以求之。”①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17页。范文澜的解释,从思路上看,大体是正确的。解释“六观”不能局限于字面意义,要从《文心雕龙》全书来解释其意义。有的学者认为,这“六观”不涉及作品内容问题,只涉及作品形式问题。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和机械了。
“一观位体”就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纯粹是安排体裁问题。《熔裁》篇说:“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可见,观“位体”的意思就是根据文章的情理内容来确定文章体式,文采则运行于这个体式之中。“位体”似可理解为情理内容在文章体式、文辞得到何等艺术的处理问题,即整体上文章是否做到了“櫽括情理”,是否做到了“规范本体”。可见“一观位体”就包含了对文章内容的安置问题。
“二观置辞”。“置辞”问题与《丽辞》篇有联系,而且与《文心雕龙》全书中谈到的全部修辞问题都有联系。如《情采》篇提出的“文附质”和“质待文”的问题,“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的问题。又如《熔裁》篇提出“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体有本,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这也是“置辞”所包括的文辞表现情志是否做到繁略选择的问题。《章句》篇所提出的“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即如何积字成词、积词成句、积句成篇中的修辞问题,也属于“置辞”问题。还有《丽辞》所提出的对偶问题等等,都包括在“置辞”范围之内。大体说来,观“位体”更多的是考察如何处理内容方面的问题,观“置辞”则更多考察如何处理形式方面的问题。
“三观通变”。这是与《通变》篇所阐明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这种考察是把作品放到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加以把握,看看这篇作品与前人的作品有何承继关系,有何独创。如《通变》篇所讲的“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就是考察作品的作者是否根据自己体验到的感情去理解前人的作品,并加以继承,同时要考察作品是否根据自己的独特气质、性格有新的变化等。
“四观奇正”。这与《辨骚》篇、《定势》篇所提出的相关内容有密切关系。如《辨骚》提出《离骚》的特点是“酌奇而不失其正,玩华而不失其实”,即在追求奇特而不失雅正,追求华采而不失质朴。这应该是“观”作品“奇正”的一个重点。《定势》篇说:“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强调要以雅正之思想去驾驭奇特的文体,而不要为了奇特而失去雅正之思想,更是刘勰考察作品的一个方面。
“五观事义”。“事义”狭义说就是典故。考察作品如何运用典故,在古代的作品接受论中是一个重要方面。《事类》篇提出作品要“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问题,在考察作品的时候,要看它是否达到“表里相资,古今一也”的程度。
“六观宫商”。“宫商”这里指文章的声律。六朝时期随着汉语“四声”规律的发现,人们自觉地感受到汉语声律之美。因此考察作品的声律运用,也成为一个评价作品的重要层面。人们开始用很挑剔的眼光来看作品中声律安排的好与坏。《声律》篇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动静,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这些话清楚表明了刘勰对于作品声律的重视。但刘勰对于作品的声律并没有提出过于繁琐、苛刻的规定,仅提出“声得盐梅,响滑榆槿”的自然要求。所谓“观宫商”也就是对作品声律要做上述考察。
由此看来,“六观”并不是什么标准,因为标准一定要考虑到准则和严格的规定,如现在我们说的“标准时间”、“标准语”,都有严格的规定;刘勰提出的“六观”并无严格的规定。“六观”也很难说是什么方法,因为也不是解决问题的路径和程序,如我们现在说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都要循着某种路径和程序的意思,刘勰的“六观”并无这种意思。笔者的看法是,“六观”是指作品的六个方面或六个层面,意思是考察作品要从这六个方面入手。至于有的学者把“六观”与“新批评”的批评方法相类比,更是牵强附会,有“过度阐释”之嫌。
第三,鉴赏的方法——“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刘勰有没有提出鉴赏的方法呢?有。刘勰在《知音》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刘勰显然认为,创作与鉴赏的“程序”是不同的,创作者先“情动”后“辞发”,先有感情郁积于胸中,然后用文辞去加以表达;而鉴赏者则是“披文以入情”,先阅读文辞篇章,然后通过感受、领悟、分析到达对于作品所蕴含的“情”的理解。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如前文所说,刘勰非常重视“文”与“情”的关系,在《体性》篇提出了所谓的“因内符外”、“表里必符”的说法,这里就暗含了对“文”与“情”关系的理解。即认为“情”是“内”是“里”,而“文”是“外”是“表”。没有内心的“情”,谈不到外面的“文”,反之,没有外面的“文”,内心的“情”也表现不出来。根据文与情的这种关系,刘勰认为鉴赏是“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或“觇文辄见其心”,也即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用比喻的说法就是“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从江河的流水的波浪,溯源而上,最终就会发现那江河源头在哪里,这样作为源头的幽深的“情”最终就会自然显露出来。刘勰所说的这种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鉴赏者,所面对的就是前人和别人的文本,通过对文本的各种症候的感受、研究、分析,很自然地就会形成对文本的理解。但这种理解是否就是知音式的理解呢?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难说的。因为我们的理解不会、或不完全会与作者的创作意图相一致,达到心心相印的地步。但刘勰对此很有信心,他说:世代久远的作者,无法了解他们的面貌,但观察他们作品的文辞就能窥见他们的内心。未必是前人的作品过于深奥,只怕自己的见识太浅陋。弹琴的人心里想着山水,其情就在琴声中表现出来,何况把自己的情理形诸笔端,他怎么能隐藏得了呢?刘勰甚至说:读者用心去理解作品中的情理,就像人用眼睛去看物体的形状,只要眼睛明亮,那么物体的形状就无法藏匿,只要读者心思敏慧,文章的情理就无不明白了。所以,刘勰认为他的“披文见情”、“沿波讨源”的方法是可以化解“文情难鉴”而达到文情易鉴的。
第四,鉴赏的关键——弃“俗鉴”,取“妙鉴”。刘勰没有停留在鉴赏方法的阐述上,又进一步提出了这种方法是否有效,还必须掌握鉴赏的关键。在这里刘勰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这就是“俗鉴”与“妙鉴”,并论述这两者的区别。刘勰说:“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质疎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事浮浅,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翫泽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在这里,刘勰首先认为,有一种鉴赏可以说是“俗鉴”。这种“俗鉴”是怎样一种状况呢?总的说,就是“深废浅售”,即不接受深刻的作品,只欣赏浅薄的作品。他举了四个例子来说明“俗鉴”之不可取。第一个例子是庄子嘲笑人们对《折杨》的欣赏。《庄子·天地》篇:“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华》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折杨》、《皇华》都是庄子当时流行的俗曲,欣赏的人很多。可是真正有深刻内容的高言、至言则不被人欣赏。第二个例子是宋玉伤叹高雅的《白雪》无人欣赏的例子。宋玉在《对楚文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①宋玉:《对楚王问》,《文选》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99页。宋玉是用这个故事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刘勰则引这个故事来说明“俗鉴”之不可取。第三个例子是屈原抱怨自己与众不同的才华不为人所理解。他在《九章·怀沙》中说:“文质内疏,众不知余之异采。”意思是,我性格质朴疏阔,大家不了解我的独特才华。第四个例子是扬雄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才会说:“我心里喜欢深沉渊博而有绝美的文章。”总之,刘勰认为在文学鉴赏中,一味欣赏肤浅的没有深意的作品,就是“俗鉴”。那么如何拒绝这种“俗鉴”呢?刘勰提出了“妙鉴”与之对抗。他说:“良书盈箧,妙鉴乃订。”满箱子的好书,要通过“妙鉴”才能正确地加以评定。那么这“妙鉴”与“俗鉴”相比,有什么特点呢?刘勰的意思可能就是特异、深刻、享受、玩味这四点。刘勰认为“妙鉴”应“见异为知音”,这就是要看出一篇作品与另一篇作品的特异之处,像屈原的作品与《诗经》确有很大的不同,鉴赏者能“见异”,看到屈原作品的独特之处,这样才能成为屈原的“知音”。刘勰又认为“妙鉴”应是“深识见奥”,这就是鉴赏作品的深刻性问题,真正的鉴赏者应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作品的深意,这样的鉴赏才能使自己感到内心喜悦。这还不够,刘勰认为“妙鉴”应该是一种享受,读书就像过节一般,众人熙熙,如登春台,像听到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和吃到最可口的菜肴一般,高兴无比。最后“妙鉴”应该有鉴赏的高潮,这就是刘勰说的“玩绎方美”。所谓“玩绎方美”不是在读作品的时候,而是在读过作品之后,觉得余香满口,回味不尽,这才是鉴赏的高潮时刻。因为,在读作品的过程中,你为其中的人物、事件所吸引,还来不及用超然的态度来欣赏它,一定要等到作品读过之后,把书合上之后,笑也笑过了,哭也哭过了,心情已经平静了,这个时候才能够回味那文章的妙处、美处、含蓄处、淡而有味处、有深意处,有独特魅力处……这才是鉴赏的高潮。刘勰认为只有这种“妙鉴”才能达到“知音”式的理解。
刘勰从“博观”作为鉴赏者的修养,从“六观”提示鉴赏作品的方面,从“披文入情”、“沿波讨源”方法的论述,从弃“俗鉴”、取“妙鉴”的鉴赏关键的层层解说,来说明知音不难、文情可鉴,阐明了他的“知音”鉴赏论,不可谓不煞费苦心。
刘勰的《知音》篇是《文心雕龙》中构思比较完整的一篇,他先提出“文情难鉴”,分析了“文情难鉴”的种种障碍;接着又提出了文情可鉴,提出了文情可鉴的种种条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知音很难,知音不难。我们读了《知音》前半段,看他那样呼喊“知音其难”,似乎觉得他好像要推翻了他自己提出的“知音”作为鉴赏的高境,真替他捏了一把汗。可是读了《知音》的后半段,觉得他找出了种种的理论来证明“知音”并不难,又觉得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我们真是在替古人担忧。刘勰是一个高明的舞蹈家,他先向左转,然后向右转,一切都那样自然,那样优美,因为他有一个“务为折衷”的舞蹈操练思维法在帮他的忙。
责任编辑:李艳丽
*童庆炳(1936—2015年),男,福建连城人。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艺理论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诗学、文艺心理学、文艺基本理论和美学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