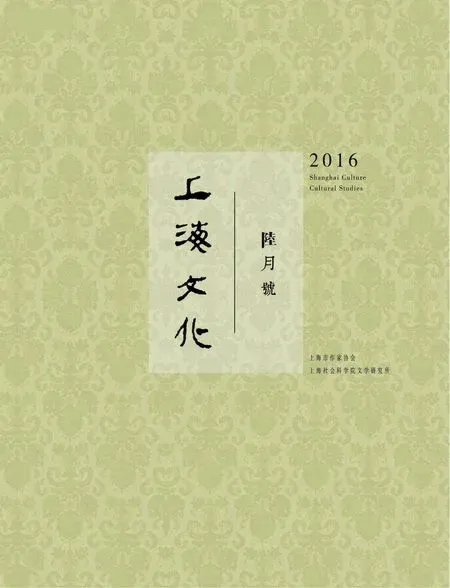婚姻自由、移风易俗与“细腻革命”
——罗汉钱故事的启示之一
张炼红
婚姻自由、移风易俗与“细腻革命”
——罗汉钱故事的启示之一
张炼红*
内容摘要罗汉钱常用作爱情信物,作者试图打开这个以新旧罗汉钱串起两代人命运的通俗故事,即从1950年赵树理为宣传婚姻法创作的评书体小说《登记》,到地方戏中移植较早、影响较大的沪剧《罗汉钱》,再到全国公映、深入人心的同名戏曲片,梳理和探析新中国大众文艺实践内外的激进政治及其在生活世界中展开的“细腻革命”,理解并反思以婚姻自由为表征的社会变革及其文艺改造中有关移风易俗的文化想象和历史影响。
关键词婚姻自由生活世界移风易俗激进政治 “细腻革命”
一
提起沪剧《罗汉钱》,中年以上的戏迷不会不知道这个戏,没看过全剧的大概也会记得丁是娥演唱的《回忆》。这段七分钟的〔反阴阳〕,宛转低回,缓缓唱出了“小飞蛾”隐忍不发的心事:
为了这个罗汉钱,甜酸苦辣都尝遍。二十年来心酸事,不敢回想埋心底。想当初还在娘家里,我与那保安有情义。偏偏是自己的婚姻难作主,一定要父母之命媒妁言。
爹娘将我另婚配,嫁与木匠成夫妻。保安哥与我藕断丝不断,一来二往情丝牵。我赠他戒指表心意,他赠我一个罗汉钱。风吹草动消息传,丈夫打骂无情面。
可怜我,受尽委屈难分说,眼泪倒流肚中咽。
二十年日月不易过,这痛苦,永生永世难忘记。①沪剧《罗汉钱》唱词,参见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本(《剧本》1952年11月号)、《华东地方戏曲丛刊》(1954年)、《中国地方戏曲集成·上海卷》(1958年)三种,前两种改动较大,集成本稍作调整,此本现已收入《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当代戏剧文学卷》(下),张炼红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唱词引文除特别注明外,皆取流传最广、约定俗成的唱词版本。
这段唱从小听到大,反反复复,听得铭心刻骨。丁派行腔的委婉舒展,表演的含蓄内敛,总是一遍遍地把人带入古井重波似的沉思情境中,哀恸深往,却能波澜不惊。
没想到的是,最近重温由沪剧《罗汉钱》改编的戏曲片,夜深人静中又听出些波澜:“我赠他戒指表心意,他赠我一个罗汉钱”,这两句堪称“戏眼”的唱词,在影片中被悄悄挪到婚前,紧随着“想当初还在娘家里,我与那保安有情义”。①此据(沪剧)戏曲艺术片《罗汉钱》唱词,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1956年摄制,1957年全国公映。这么一改,小飞蛾心爱的罗汉钱,就从婚后的私情信物,变回到婚前的定情信物。
同为男女之情,贴身信物,这下罗汉钱的性质可就改变了,经由情感道德的净化、美化、合理化而提升了。原本因私情丑事而来的“伤风败俗”,也就凭借着“反封建”的时代主题,转而成其为旨在“移风易俗”的婚姻家庭革命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基础。那么,为什么先前的各种改编、移植对此都眼开眼闭,等到拍摄电影时就得这么修正呢?
而从“伤风败俗”到“移风易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结构性的破立开合之际,在由此所连带的各种新质与旧胎之间,有形无形中到底有哪些进退、腾挪与翻转机制,使得以婚姻自由为表征的“移风易俗”的社会变革及其文艺实践成为可能?
具体落实到罗汉钱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即从最初赵树理为宣传婚姻法创作的评书体小说《登记》(1950年),到地方戏中移植较早、影响最大的沪剧《罗汉钱》(1952年),再到全国公映、深入人心的同名戏曲片(1957年),这个用新旧两枚罗汉钱串起母女两代人命运的通俗故事,如今还能否重新打开阅读空间,再从中慢慢讲出点意思来呢?②赵树理的小说《登记》发表于《说说唱唱》1950年第6期,随后由评书演员赵英颇改名《罗汉钱》播讲,并被多种文艺形式移植改编,其中1952年由张骏祥导演、丁是娥主演的沪剧《罗汉钱》最为著名,1956年拍摄戏曲片,1957年公映后更为深入人心。
二
“赵树理写的决不是简简单单、故事体的大众文学,《登记》从一枚罗汉钱下笔,布局是很精心的。”——此话出自汪曾祺,不像是随口说说的。在他眼中,赵树理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农村才子,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妩媚的作家,看人看事,常常微笑。不同于大多数评论者,他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有其独特的抒情诗意,他善于写农村的爱情,农村的女性。她们都很美,小飞蛾(《登记》)是这样,小芹(《小二黑结婚》)也是这样,甚至三仙姑(《小二黑结婚》)也是这样。这些,当然有赵树理自己的感情生活的忆念,是赵树理初恋感情的折射。但是赵树理对爱情的态度是纯真的,圣洁的”。③汪曾祺:《才子赵树理》(1997年),参见赵勇:《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红药:《话说赵树理和沈从文——记汪曾祺先生一席谈》,《文学报》,1990年10月18日。说到作者对爱情的态度时为何要加“但是”两个字,这里暂且不表。细读小说《登记》,的确能让人看到赵树理的精心与妩媚,也能体会他初到北京那些年对乡村感情生活的深深忆念。
故事发生在张家庄,艾艾姑娘与同村小晚两情相好,互赠小方戒和罗汉钱为定情信物。小飞蛾发现女儿竟然也有罗汉钱,回想当初与保安相爱却被迫嫁给张木匠后藕断丝连、挨打受罪,唯恐女儿步其后尘,就将新旧两枚罗汉钱一并藏起。年轻人的自由恋爱遭到村民非议,民事主任也横加干涉,说他们败坏风气。为息事宁人,尽早嫁出女儿,小飞蛾答应媒婆去相亲,无意中却听到对方在背后挑是非,当即愤然离去。为成全艾艾和小晚,燕燕姑娘仗义来做媒,说动了小飞蛾,答应成全女儿的婚事。民事主任出于私心,仍不肯写介绍信,区里也听信传言,不让登记。幸好此时婚姻法颁布,年轻人终于得偿所愿。
结婚登记的主角自然是年轻人(“新人”),而罗汉钱故事的灵魂,或者说“戏胆”,却还在身为母亲的小飞蛾。评论者常说赵树理小说不太在意刻画人物,尤其不注重人物心理描写,可你看他写小飞蛾写得何等经心,何等有戏。就这“小飞蛾”的绰号,也是为的说她长相出挑,活像当地梆子戏班里有名的武旦:“一出场,抬手动脚都有戏,眉毛眼睛都会说话。唱《金山寺》她装白娘娘,跑起来白罗裙满台飞,一个人撑满台,好像一只蚕蛾儿,人都叫她‘小飞蛾’。”①赵树理:《登记》,《赵树理全集》(2),北京: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以下小说引文皆出于此。而小飞蛾的俊俏,惹眼,再加上婚后传扬出来的男女私情,都让她“声名不正”,走到哪里都要被人说三道四。可话又说回来,大伙儿明里是在诋毁她、唾弃她,暗地里却还想再多看几眼,那还不是喜欢她?如果说,深藏在盒子里的罗汉钱,就是让小飞蛾百转千回、无法释怀的私情之郁结;那做出这等丑事来的小飞蛾,在众人眼里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声色牵引,哪怕嘴里多议论她几句,也会觉得莫名快意吧。
想想这样一个小飞蛾,她在传统文艺中分明勾连着两种女性形象的谱系:一面是身世凄凉、痛苦无告的“弱女”或“冤魂”谱系,另一面则是敢爱敢恨、勾魂摄魄的“尤物”或“妖魅”谱系。前者多为苦主,后者大抵“祸殃”,有时还往往一体两面,多少都担负着人世间难以为怀的一点心劫与“冤孽”(小飞蛾自语)。譬如说白娘子,她是千年修炼的蛇妖,也是身怀六甲的人妻;她水漫金山,苦斗法海,也难免涂炭生灵。当她穿戴着素白纱裙,满台飞跑着走圆场时,你就只见一身清素虚飘的白娘子,头顶着鲜红绒花,一路上东奔西杀,好不凄凄惨惨,却又怨气冲天……就此形神相照之间,更凸显出一种情感张力。
而在更多苦情戏、鬼魂戏中,由各路名角担纲的苦主、妖魅形象,也因艺人们深入骨髓的底层生活经验,加之苦打苦熬出来的旺盛饱满的艺术爆发力,使得剧中人的痛苦与绝望本身也充满了抒情和审美的蓬勃能量。尤其是民众所热爱的那些悲剧人物,越是被伤害、被牺牲、被亏欠,越是执着于边缘化、底层化的生活实践,越是坚守着被压抑、被磨砺的内心愿望,日积月累就越使人具有强劲的生命力,那就越像是幽暗里发出的光,地底下开出的花,静默中震撼人心。哪怕生命被唾弃被杀戮,不屈的精魂到底还是要来洗冤雪耻,藉此倾其深衷,了其念想。就像《六月雪》的窦娥、《红梅阁》的李慧娘、《焚香记》的敫桂英、《京娘送兄》的赵京娘……千百年来仍在舞台上闪爆出惊人之力,常常让人触目撄心,甚至于血脉贲张之际,灵魂简直都要被激颤得出窍!②参见张炼红:《细腻革命:民众生活世界与文化政治》,《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正因此,被小飞蛾隐隐集于一身的这两种谱系渊源,特别是地方戏中有关鬼魂和妖魅的深厚传统及其表现形式,都让她冤苦无告、低回宛转的生命体验变得极富形式感,这在小说移植为各种地方戏后表现得尤为充分。而赵树理原本写得也真是传神,就说元宵看灯吧,她要在各街道上飞了一遍才回去,何等热情与欢快;说相亲受辱之后,她哪里还肯任人摆布,又拿出二十多年前那“小飞蛾”的精神在前边飞,一直飞回了家,何等烈性而决绝。故事改编为沪剧《罗汉钱》时,丁是娥也从这个“飞”字把握到人物的性情特质,那就是在长期压抑境遇下依然透露出的“朝气”和“生命力”,并用她潜心琢磨的手眼身法步,真正在节节寸寸中演活了小飞蛾。1952年,沪剧《罗汉钱》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观者赞不绝口,连赵树理本人看了都很服气:“我写的小飞蛾,就是舞台上的这个人物。我就是这个想法。”①丁是娥:《我演小飞蛾》(蓝流、李涵整理),《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丁是娥口述,简慧等整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参见褚伯承:《〈罗汉钱〉唱进中南海》,上海文艺网,2008年9月27日。1952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罗汉钱》获剧本奖、演出奖和乐队奖,丁是娥、石筱英获演员一等奖,解洪元、筱爱琴获演员二等奖。文化部还特邀剧组到中南海演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观看。
三
小飞蛾也真是不简单。爱而不得,锥心刻骨。张木匠得知私情后羞恼成怒的一顿毒打,更让她长了记性。然而,也就是天长日久的屈辱,折磨,痛苦无告,使她在隐忍压抑中慢慢积蓄起一股心力。压抑越久,心事越深重,而积蓄越久则心力越饱满。这股心力的持久、深重和饱满,看来也多少保全了她天性中活泼泼的生趣,再怎么受煎熬也没有被彻底掐灭掉。而她不说话,不肯给笑脸,无非是想在孤寂和硬气中把那点生趣裹得更紧、藏得更深罢了。对一个卑微而坚韧的农村妇女来说,这也是她在赤手空拳中所能持守的起码的生命尊严。
自从她挨了这顿打之后,这个罗汉钱更成了她的宝贝。人怕伤了心:从挨打那天起,她看见张木匠好像看见了狼,没有说话先哆嗦。张木匠也莫想看上她一个笑脸……婆婆跟丈夫是一势,一天跟小飞蛾说不够两句话,路上碰着了扭着脸走。小飞蛾离娘家虽然不远,可是有嫌疑,去不得;娘家爹妈听说闺女丢了丑,也没有脸来看她。这样一来,全世界再没有一个人跟小飞蛾是一势了,小飞蛾只好一面伺候婆婆,一面偷偷地玩她那个罗汉钱……“罗汉钱!要命也是你,保命也是你!人家打死我也不舍你!咱俩死活在一起!”她有时候变得跟小孩子一样,把罗汉钱暖到手心里,贴到脸上,按到胸上,衔到口里……除了张木匠回家来那有数的几天以外,每天晚上她都是离了罗汉钱睡不着觉,直到生了艾艾,才把它存到首饰匣子里。(《登记》)
小飞蛾的隐忍自持,含蓄内敛,分明也就是骨子里的要好、要强,因此也决不会由着自己变成另一个“三仙姑”。想想这两个活在赵树理笔下的女人,小飞蛾与三仙姑,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都在生活重重压抑之下从俏媳妇熬成老女人,她们命运相似而性情迥异,同在一根藤上,各自开花落果。从为人妻、为人媳直到为人母的小飞蛾,终于咽下屈辱,收拾旧情,就此把女儿艾艾当作命根子。母性的温慈,骨肉的亲昵,也在慢慢回暖她的心。而一旦发现女儿竟然也有那惹祸的罗汉钱,她就像是惊弓之鸟,紧张、慌乱,旧伤又添新痛:
小飞蛾手里拿着两个罗汉钱,想起自己那个钱的来历来,其中酸辣苦甜什么味儿也有过:说这算件好事吧,跟着它吃了多少苦;说这算件坏事吧,想一遍也满有味。自己这个,不论好坏都算过去了;闺女这个又算件什么事呢?把它没收了吧,说不定闺女为它费了多少心;悄悄还给她吧,难道看着她走自己的伤心路吗?(《登记》)
尽管此事“想一遍也满有味”,可自己所承受的痛苦越深、挣扎越久,她就越不忍心,也不甘心眼看着女儿步其后尘。这个活泼伶俐的艾艾姑娘,不仅延续了母亲的骨血,恐怕也将用一枚新的罗汉钱延续其命运,这就更让小飞蛾觉得母女俩一体连心,也更添其舐犊护犊之情。因此,相亲时听到媒婆在背后挑是非,怂恿人家把艾艾娶过门后痛打一顿来管教(“小飞蛾那时候,还不是张木匠一顿锯梁子打过来的?”),气得她当下就拿定主意,拒绝婚事:“难道这挨打也得一辈传一辈吗?去你妈的!我的闺女用不着请你管教!”
五婶那两句话好像戳破了她的旧伤口,新事旧事,想起来再也放不下……她又前前后后想了一下:不论是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姊妹,不论是才出了阁的姑娘们,凡有像罗汉钱这一类行为的,就没有一个不挨打——婆婆打,丈夫打,寻自尽的,守活寡的……“反正挨打的根儿已经扎下了!贱骨头!不争气!许就许了吧!不留嫁给谁还不都是一样挨打?”头脑要是简单一点,打下这么个主意也就算了,可是她的头脑偏不那么简单,闭上了眼睛,就又想起张木匠打她那时候那股牛劲……“妈呀!怕煞人了!二十年来,几时想起来都是满身打哆嗦!不行!我的艾艾那里受得住这个?……”就这样反一遍、正一遍尽管想……(《登记》)
小飞蛾最大的本事也就是这么“想”。时时刻刻记着打,记着痛,也就更加抹不掉她那点心事。心事牵扯搅动着心力,她那全副心力也就在“想”中苦苦流转,如同静水流深,看似波澜不兴,其实底下始终有暗流在涌动。而当深情和屈辱,孤独和无助,日积月累地埋进她记忆,融入她生命,不断涵容与打磨,那就像是“蚌病成珠”,哪怕置身幽暗她也能暗暗发出光来。这种光,首先照亮她自己的内心和头脑,遇事“偏不那么简单”。
问题是,平日里她早已习惯了忍辱负重,倘再加上遇事“偏不那么简单”,那只会更让她迟疑不决:既舍不得女儿嫁给别人挨打受罪,可真想要成全女儿配小晚呢,又怕飞流短长糟蹋人。而她越怕惹是非,越怕村里人说闲话,也就越不能容忍闲话再来糟蹋人。正是这种源于内心和舆论双重压力而来的迟疑不决,使得村里都知道她怕事,却未必了解她怕到极点后被逼出来的那份倔强和硬扎。
与此同时,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村日常生活,也在不知不觉中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小飞蛾与张木匠的夫妻感情,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家庭生活的操持,尤其是对女儿共同的爱,而逐渐缓和起来。比如,只要一提起艾艾的婚事问题,做爹妈的总能有商有量,很是同心。再比如,张木匠有个老习惯,小飞蛾每次回娘家,他都要跟着去,起初是因为不放心,后来也就习惯成自然。因此,小飞蛾决定去东王庄相亲,顺便回趟娘家,他当然想要跟去:“二十年来老规矩,总是一道去的。”小飞蛾心里有些难受,叹口气说:“艾艾都这样大了,你快要做丈人的人了,难道我一个人回娘家,你还不放心吗?”这里的语气,亲近中带着点埋怨,絮叨中又有点俏皮。①丁是娥:《我演小飞蛾》,《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第137页。这段夫妻对话的细节,在小说《登记》中只是泛泛带过一笔,沪剧则具体用到了这场戏中,也可见戏曲处理人物关系的特别细致、得体之处。此时的张木匠一脸憨相,嘻开了嘴说:“跟惯了,还是跟跟吧!”一来一去,就让人明白了这对冤家夫妻长久磨合成的相处之道,也领会了平常日子里夫妻间自然流露出的那份亲情与常情。而当年动不动打老婆也罢,回娘家时“真像解差押犯人”也罢,这在多年以后早已成为村里人打趣张木匠的家常话,甚至当着小飞蛾的面说说笑笑,夫妻俩听了难免会有点尴尬,可这也已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习惯成自然,只不过多了点呛人的烟火气,说到底,还是连带着乡村共同生活中群己互动而来的谐趣和暖意。
正是在这样有常有变的生活世界中,在无论如何都想要好好过日子的愿望支撑下,人们就与各自分定的角色身份和生活方式,与周遭环境和人群,日久生情。长期置身于这种历史性、社会性,且已内在化的伦理秩序中,底层妇女往往会以其身心最直接的感受力、平衡力和忍耐力,在事无巨细的日常操持中体现各自的情义承担、伦理承担和道德承担。于是,在岁月的艰辛和亏欠中,在忍耐和坚持中,慢慢历练出更细腻、更柔韧也更结实的情感道德与伦理特质,居于幽暗,而能暗暗有光。从有形之劳到无形之力,从无形之力到内在之光,如同“蚌病成珠”,这里就有着个体生命与生活世界长久依存化合而来的“共命感”。
俗话说,原汤化原食。对心力饱满而个性坚韧的小飞蛾来说,生活过程的艰辛与折磨,情感体验的屈辱和压抑,恰恰成为既令她备感痛苦,又能从中得到慰藉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来源。日久天长,当痛感化作慰藉,辛酸熬出尊严,其间就会生成一种只能靠生活本身来铸就的人与人、人与生活世界“相依为命”的力量。这种力量无所不在,有形无形,重重叠叠,共同指向日常实践中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共存性的情感伦理结构。这里就有某种整体性的伦理和谐与动态平衡,一种基于“依存/冲突”关系而形成的“共命/压迫”体验结构。而生活世界作为意义寄托之地,多侧面多层次地给人以理解和创造生命意义的历史与现实情境。
与此相关,群己人我之间,一种更为持久而深往的互动关联如何可能?回想戏里戏外那些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底层妇女,以及各种意义上的被压迫者、被损害者,她们在艰辛忍耐中到底持守着什么,克服了什么,维系着什么,保存了什么?看看在艰辛忍耐之中,人们与生活世界的联系持续加深加固了还是削弱了?事实上,当人们在忍耐中有所持守、有所维系时,个体或群体想要在具体生活进程中切实改变不合理现状的“细腻革命”,也就在其将来未来之际具有越来越切近的可能性。②关于“生活世界”的初步思考,参见张炼红:《生活世界、文化自觉与价值重建》,《文汇报》(文汇学人·每周讲演)2011年9月19日。
四
再看看张家庄上的年轻人,大多却还是不经世事、六神无主的小儿女模样。不同于那个时代所常见的对青年(“新人”)的想象和刻画,在小说《登记》和沪剧《罗汉钱》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半旧半新、新旧合体的青年形象。
话说因为小飞蛾的迟疑不决,小辈们也摸不透她的心思,加之媒婆追上门来说媒,就让两情相好的年轻人越发心焦起来。可他们一时间所能想到的出路,也不过是要设法找个媒人,好向双方父母去提亲。为此,艾艾抱怨道,“我爹爹糊里糊涂,姆妈又怕多是非”,“村里长辈全是老脑筋,我想寻个介绍人到我姆妈门前去提一提亲事也寻不着”。小晚也同样担心着,“讲好闲话的一个也没,讲坏闲话的人倒不少,啥人肯来当我们的介绍人呢?”好在,村里还有个不怕惹是非的燕燕,关键时刻,仗义挺身来做媒:“介绍人我来当,向你们爹娘亲事提。我们的婚姻无人来帮助,只有你帮我来我帮你。现在我的婚姻已耽搁,再不能看你们落在苦海里,我一定从中出把力,让你们婚姻来成全。”
这里特别有意味的是,以燕燕、艾艾等年轻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生力量”,面对着周围的旧风气、老脑筋,他们并没有想到用新旧对抗的、断裂的、激进的方式来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在村里的长辈们面前,他们似乎并不觉得自己就有多么进步,进步到可以用新旧对决的方式,把婚事搞成一场义无反顾的社会革命。
尤其是燕燕,她珍视自己和小进的恋情,也能顾念体恤长辈的心情,并且格外看重她和艾艾的姐妹情谊,将心比心,急人所急。她娘寻死作活要把她许给别人家,闹得她身不由己,怕娘这把年纪真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所以就只好认命,为此还被小进误解,见面不理不睬,但她心里再难受也能忍耐住,决不和他翻脸。
不仅如此,燕燕的善良和坚韧还在于,正因为自己婚事被耽搁,心有不甘,她才更要帮艾艾,一门心思就想来成全这桩好事,也算替她自己争口气。而真想要帮这个忙,那还得入乡随俗,用村里人能接受的方式,也就是不让小飞蛾太为难的方式:你们不是说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好,那我就来做这个媒吧!她心里特有主见,而且善解人意,遇事总能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既不固执也不灰心,无论如何都要来促成艾艾与小晚的婚事。
燕燕说媒,其实是要说理。说的什么理呢,自然是要说出跟小飞蛾内心相通的情与理,也就是人之常情与常理。怎么说理才好呢,那唯有将心比心,才能情通理顺,最终说服小飞蛾“要替艾艾作主张”。因此,燕燕做媒,走的是因地制宜、以柔克刚的“妇女路线”,凭的是将心比心、推心置腹的“水磨工夫”,这样才可能有效激发起吃尽苦头的小飞蛾们支持儿女婚姻自由的“革命性”。
小说《登记》中,燕燕做媒做得直截了当。燕燕一提小晚,就被小飞蛾挡了回去:“我早就知道你说的是他!快不要提他!你们这些闺女家,以后要放稳重点!外边闲话一大堆!”燕燕不管,接着说:“闲话也不过出在小晚身上,说闲话的人又都是些老脑筋,索性把艾艾嫁给小晚,看他们还有什么说的?”小飞蛾一想:“这孩子不敢轻看!这么办了,管保以后不生闲气,挨打这件事也就再不用传给艾艾了!”几个来回,大媒就做成了。
到了沪剧《罗汉钱》中,“燕燕做媒”这场戏处理得很细腻,很流畅,很抒情,好听又好看。首先,不单是在充满生活气息的情节内容上,通过做媒来呈现燕燕和小飞蛾之间情理沟通的过程;而且,恰恰随着这个过程的逐渐展开,使得原本不太可能的事情出现了转机,因而更让人感觉情通理顺,水到渠成。其次,在与此相关的艺术处理上,唱腔先采用江南非常流行的民间小调〔紫竹调〕(原名〔支烛调〕),旋律质朴流畅,节奏从容不迫,很适合两两对唱;接着又选取沪剧基本调中簧腔类的〔流水板〕,旋律轻快活泼,擅长表达喜悦、乐观、诚挚、坦率之情,正好贴合燕燕做媒时明快敞亮的心境。于是在这样的唱腔设计和对唱形式中,燕燕和小飞蛾你来我往,彼此穿插接应,故事本身也随之而步步推进,眉目越来越清晰:
燕:燕燕也许太鲁莽,有话对你婶婶讲。
我来做个媒,保你趁心肠,人才相配门户相当。
问婶婶啊,我做媒人可像样?问婶婶呀,我做媒人可稳当?
蛾:燕燕你是小姑娘,你做媒人不像样。
燕:只要做得对,管啥像不像,我来试试也无妨。
蛾:燕燕姑娘我就听你讲一讲,我家艾艾许配那家年青郎?
燕:就是同村的李小晚。
蛾:这门亲事不稳当。
燕:攀了这门亲,
蛾:村里有人讲,年轻姑娘太荒唐。
燕:好婶婶呀,婚姻只要配相当,配相当呀,管啥人家背后讲。(转〔流水板〕)
婶婶呀,小晚艾艾早相爱,正好一对配成双,
自己看对自称心,将来勿会得怨爹娘。
别人家夫妻容易寻相骂,这一对夫妻是有说有话有商量;
亲亲热热过时光,随时回来好望爹娘,望爹娘。
假使你反对这桩亲事另匹配,将来一定会起祸殃,
拿女儿推到地狱里,爹娘存的啥心肠,啥心肠?
婶婶呀,你想一想,艾艾是你亲生养,
眼面前放着好坏两条路,你要替艾艾作主张。
蛾:话是讲得有道理,小晚艾艾配得上,
只怕村里闲话多,说我们爹娘太荒唐。
你说好来有啥用,外面闲话啥抵挡,啥抵挡?
燕:讲闲话的全是老封建,硬说小晚艾艾不正当。
索性把他俩配成双,看人家还有啥个闲话讲?有啥讲!
蛾:勿要看轻这个小姑娘,倒讲得有条有理好主张。
这样一来倒也好,一双两好免得将来闲气生。
他们本是两相爱,艾艾不会再被人打。
燕燕姑娘好灵巧,你做媒人倒也做得蛮像样。
燕:婶婶可是答应了我?
蛾:不要心急不要慌,还有你家叔叔张木匠,等他回来再商量。
燕:我晓得你不是不转弯的老脑筋,你一定会让艾艾称心如意的!①录自(沪剧)戏曲艺术片《罗汉钱》唱词。较之沪剧舞台演出本,片中“燕燕做媒”略删几句唱词,可算是该剧搬上银幕后保留最完整的一场戏,由此亦可见其重要性。
很显然,无论两人在此沟通什么,怎么沟通,其实都基于常情常理。燕燕对包办婚姻有切肤之痛,深知小飞蛾爱女心切、护犊情深,也体贴到她埋藏心底的痛苦和隐忧,所以强调艾艾与小晚人才相配、门户相当、两情相好,“自己看对自称心,将来不会得怨爹娘”。对小飞蛾来说,这既符合她挑女婿的眼光,也能去掉她怕女儿日后挨打受罪的心病。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怕人说闲话,燕燕就果断说出了令她意料不到、却又直击内心的话:“讲闲话的全是老封建,硬说小晚艾艾不正当。索性将他俩配成双,看人家还有啥个闲话讲?有啥讲!”闻听此话,小飞蛾不觉从桌前站起身来,此时镜头随之转动,窗棂外几道光影照进来,映在小飞蛾身上。只见她神情舒展,双眼发亮,轻声自语道:“勿要看轻这个小姑娘,倒讲得有条有理好主张。这样一来倒也好,一双两好免得将来闲气生。他们本是两相爱,艾艾不会再被人打。”这个主意在情理上看似简单,不过是反其道而行之,可对小飞蛾来说确实意义重大:身为家长,她这么做就是不惜冒犯众怒,真正不同于她爹娘和乡邻们所习惯的想法和做法。而燕燕做媒所蕴含的“革命性”也就在这里,就在几乎被旧风俗禁锢得透不过气来的小飞蛾身上:她承受压迫越深重,反骨反心就越强烈,而妇女翻身、解放、移风易俗的强劲动力不就来源于此?尽管,真要将这种“革命性”实践到底,更大的压力还在后头,限于篇幅,此处按住不表。
话说这场戏前后不到五分钟,环环相扣,一气呵成。眼看着两人在同一曲调回旋中你来我往,就事说理,时时倾听、沟通,处处协调、互动,恰如水流宛转,顺势铺陈而能条达到底。其间,镜头始终平静地往返于燕燕和小飞蛾的循环对唱中,不疾不徐,不温不火,却丝毫不让人感到单调乏味,且因其唱腔之美、唱词的入情入理、表演的清新质朴而格外可亲可感,不知不觉中身临其境,时有会心和共鸣。无论紫竹调的质朴流畅也好,流水板的明快欢悦也好,这种鲜明的节奏感与浓厚的抒情性决非随心所欲,而是紧紧贴合着人物对生活世界的热爱、对事体情理的投入,并能与之水乳交融。同样,顺应着这种扑面而来的抒情性和节奏感,观众也能欣然入戏,听着看着就真的会相信:不管小飞蛾原本怎么想,燕燕这么做媒确实能打消她的顾虑,说动她的心;也真是能从中看出燕燕有才情、有智慧、有章法,难怪本来听听而已的小飞蛾也会对她刮目相看,“不要看轻这个小姑娘”。可见只有当艺术形式与其内容浑然一体时,“燕燕做媒”的剧情内涵才更具有真实感与可信度。
这似乎也就意味着,如此贴切而又表现充分的艺术形式本身,与其视为一种载体、一种手段,不如说它直接就以最完整的形式感昭示出一种内在的生命力、一种感性直觉的思想力,那就是给予人们在此声色光影律动中最直接的感悟,就是在忘我投入的艺术观演过程中,体会到人世间如同天地自然般的伦常秩序感与合情合理性。于是,内心就会有一种信任与肯定:原来如此啊,就该这样啊!
五
《罗汉钱》看了几十年,有时回想“燕燕做媒”忍不住还会唱起来,越唱就越觉得有味道。就是这么明快动人的交心对唱,这么入情入理的做媒相劝,这么有心有意的水磨功夫,共同促成了两代人在所谓新旧磨合中并不对立、更非决裂的情理沟通方式。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中,这种方式的确不那么具有革命性,但由此而能更切实有效地推动人们走向“婚姻自由”的社会变革,并且走得更脚踏实地,更通情达理,那也就更安心,更持久。
而这里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问题是,“移风易俗”的社会变革到来之际,所谓新旧两代人之间的沟通互动如何可能?双方实际上共享着哪些东西?彼此又给予了何种援力?
回头再思量,这里的关键还在于“戏胆”小飞蛾。她吃尽苦头却仍不失其儿女初心,才能细细体贴到儿女情事,才会暗暗和年轻人一条心,才肯没轻没重听凭燕燕来做媒,并且句句听得进。其实说来说去,人才相配、门户相当、两情相好,这些情理何尝不是小飞蛾心中所愿?但在痛苦压抑的岁月里憋屈得太久了,种种心事、心病和心愿都被封存在沉默隐忍中,越是思前想后她就越觉得力不从心。这当口,正值时代大变动到来之际,如果说燕燕做媒是想寻求长辈对儿女婚姻自由的支持,那么小飞蛾恰恰也渴望找到某种实践的形式,来挣脱身心内外的重重禁锢,真正发出自己的心声。而此心声,既是蚌病成珠的小飞蛾对于生活压迫的率性回应,又和年轻人的愿望有共鸣,彼此于情于理能接应,那么新事物也就能果断寻到落脚点:任何一种人间新质,只有落了地,生了根,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确立其主心骨,不仅得以生,而且可以活。
新旧之间,所谓“新质发于旧胎”,看来也远非那么简单,你是你,我是我,那么想当然。再想想燕燕姑娘,不也正是新一代的小飞蛾么?在共同的心愿和切实的互动中,燕燕和小飞蛾凭借着各自细腻而丰富的生命情感体验,使得新旧磨合成为可能,真正形成了内外变革的合力。换言之,新旧两代小飞蛾,就是在对各自婚恋困境的共同承担中,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情理上的传承与联盟,一种深具内在抗争性的合力,以及在日常低调抗争中自我更新着的民众/风俗/乡村生活的“共同体”。于是,激进政治谓之“婚姻自由”的新观念、新风气才有可能逐渐融入生活世界,于潜移默化之中移风易俗。可以说,小飞蛾们的翻身、解放,本身就和这种融入并介入生活的“移风易俗”的革命性能量密不可分。当此社会变革指向底层民众用力之际,势必促其就地翻转,并在因其翻转之难而产生的整体连带中,形成犹如“鸡毛飞上天”所象征的新世相与新生活。而所谓“移风易俗”,恰是充分利用各种已有的社会和文化形式,在因地制宜的实践与翻转中,促成了更大的时代变迁与文化变异。
事实上,只有在全力维系展开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才可能有更多时间让彼此积蓄和保存有限的力量,既非抗争对决,也不顺势妥协,直到迎来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时刻。在我看来,促成“移风易俗”的真正切实而重要的变革力量,就是那种既能从民众息息相关的生活世界里汲取能量,又能以低调持续的日常实践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和行动,这也就是社会变革中建构新的生活共同体所需要的“细腻革命”。
责任编辑:沈洁
*张炼红,女,1971年生,上海浦东川沙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新中国戏曲改革与当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