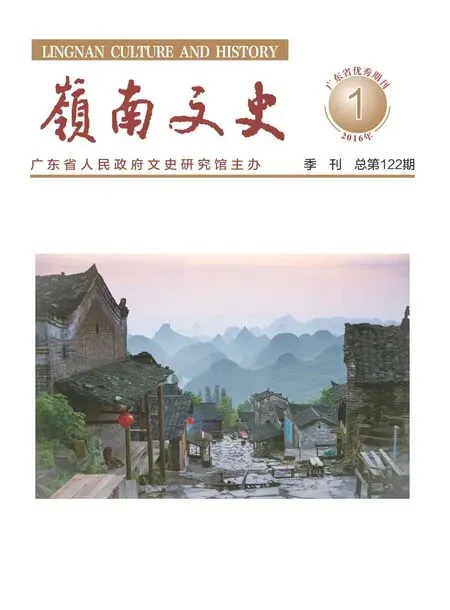18-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女性
——以珠江疍家女为例
陈 曦
18-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女性
——以珠江疍家女为例
陈 曦
18-19世纪,正值西方国家拓宽海外市场,进行资本积累之际,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布“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开放港口。西方人聚集在广州十三行经商,活动范围主要在广州河南一带和珠江航道上。故此,他们最先遇到也最为熟悉的女性群体,便是被视作珠江沿岸女性象征的疍家女。18-19世纪西方人记录与描绘的疍家女形象,较为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疍家女性的生存状况,对于了解和掌握清中晚期中国底层妇女的生存状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疍民与广州
疍民又称疍家人,亦称蛋蛮、龙人、龙户等。疍,同蜑、蜒、蛋,为东南沿海地区在船上生活居住,从事捕鱼、采珠、挖蚝等水上作业的族群统称;而在不同地区,这些居民则有不同的俗称,如广州、香港一带称为“疍家”、“艇家”,漳泉一带称为“白水郎”,福州一带则称为“曲蹄”。
关于其源与广东关系,众说纷纭。范晔《后汉书》、司马光《资治通鉴》、常琚《华阳国志》、乐史《太平寰宇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籍文献中皆有关于“蜑”的记载,[1]“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中更多次提及疍家。[2]疍学泰斗陈序经教授把30多种疍民起源说按船型、生活习性等归纳成六类,其中,宋代疍民聚居之地在两广;历史学者罗香林在《百越源流与文化》中论证古代蜑民居地经越南达两粤,其疍民源起于古越族的论证为后世学者普遍认可;梁启超观点与之相仿:“蜑族昔固洞居,而与华人杂厕者也,其由陆入水,不知仿自何时,为我族所逼,不能自存于陆地,是以及此,抑亦其自入水后,与我无争,故能阅数千年,传其种以迄今日,古百粤之族,其留纯粹之血统,以供我辈学术上研究之资料者,惟此而已。”[3]
疍民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港澳等地,尤以珠江流域为甚。鸦片战争前,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是西方人活动的主要地区,疍民是西方人外游时接触最多的群体,对此,当时来华的西方人多有描述。法国旅行家奥古斯特·博尔热(Auguste Borget,1808-1877)、法国公使随员伊凡(DR.YVAN)、英国访华使团成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常年寓居澳门的著名画家乔治·钱纳利 (George Chinnery,1774-1852)等,都用文字或图画进行过形象塑造。尤其是在广州生活40多年的美国人威廉·C·亨特 (William C. Hunter,1812-1891)在自己的著作《旧中国杂记》中更有对疍家的专门注录:“疍家,一个非常有用的阶层,他们的艇仔常年提供搭载乘客过江,前往花地或到十三行的服务。疍家一词,意为‘疍人家庭’,由上面提到的艇子组成,舱顶的中央用厚席子覆盖,用着若干支桨和一支橹行驶”。[4]
二、西方人眼中的疍家女
根据清政府当时的规定,来广州通商的西方商人不可随意出行,不可到乡间任意游行,不可进入内地贸易,只能在清政府指定的地方游玩。[5]因而在春、秋季节,西方商人定期从澳门坐船至广州十三行进行贸易经商,按例到附近游玩,海幢寺、花地湾等地成为西方人在广州主要的消遣旅游之地,他们接触到最多的中国女性,就是生活在珠江河道上的疍家女。
水上活动范围广、流动大,疍家女像男人一样在从事水上运输工作,吃苦耐劳,也给予她们密切接触西方人的机会。法国公使随员伊凡便在其《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书中描述:“一个船妇坐在船的前面,用高超的技术掌控着轻便的船桨……两个可爱的船家女随心所欲来引导我们看每一样东西”。[6]对于这些西方人,疍家女的形象就是她们这一阶层中国女性的象征。在西方人的记录与描绘中,疍家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具有娴熟的掌舵技能
疍民常年栖息水上,视水如陆,以舟为室,浮生江海。疍家的男人以捕鱼为生,渔业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疍家的女人(如图1),则常年通过搭载乘客过江、前往花地或十三行谋利,疍家女的艇子,不仅接送外国人,而且还向他们出售橘子、香蕉等多种商品,与他们进行各种生意往来。

图1:英国访华使团成员威廉·亚历山大1793年绘疍家女
伊凡认为选择在河上居住的疍家女是花城居民中最谨慎和最有艺术气质的:“当我参观珠江人口稠密的河床时,这座城市的绝妙景象令我产生不可思议的印象,我充满真挚的热情,自觉这一印象是客观的……当我们深入了解居住水上、自力更生的居民的生活细节是……我们开始对那些勤劳的人们产生兴趣”,[7]英国访华使团成员威廉·亚历山大在1793年就曾赞誉过疍家女的划船和掌舵技术:“中国所有河流和运河上,都有大量的水上人家。这些女人的划船和掌舵技术,和男人一样娴熟。”。[8]奥古斯特·博尔热则观察到:“这些船都建得十分牢固,以为乘客提供最大舒适为原则,通常两名妇女在撑船,一个划船,另一个既划船又掌舵。她们都长得非常漂亮,衣服整洁。”[9]不难发现,刚进广州城的西方人,几乎都被疍家女娴熟精湛的驾船技术、疍家船内舒适环境所吸引,而勤劳勇敢,不惧生活艰苦的疍家女形象则让西方人大加赞赏。
2.具有“自然美”的形态
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缠足”被视为重要的美德,畸形的“三寸金莲”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标准(如图2)。许多西方人的描述中,“缠足”这种严重摧残女性身体和心理的陋习,就像附在中国女性身上的特殊标签,向他们展示着中国女性被扭曲的身体特征。如格雷夫人所见:“中国的太太们有时会骑在保姆的背上,从一条村到另一条村拜访朋友,有些太太即使在自己的大花园里游玩时也会让人背着”,[10]中国人扭曲小脚的审美让他们感到匪夷所思和难以理解。

图2:佚名画师绘缠足女人制丝通草画(广东省博物馆藏)
加之东西方审美标准的不同,在他们眼中,中国中上层女性的体型缺乏曲线美,甚至被偏颇地描述为“两块肋骨简单的拼凑”,而疍家女不仅有着健康自然的身段,甚至疍家女的衣着打扮在西方人眼中也是整洁大方的。如英国人格雷夫人所见,摇撸和划桨的疍家女最常见,她们的服装质地是蓝黑的棉布,身穿束腰外衣,裤子宽而短,裤子长至小腿的一半,她们既不穿鞋子也不穿袜子。[11]英国1849年出版的瑟尔(Henry Charles Sirr,1807-1872)的《中国与中国人》一书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地位低下的女性,包括疍家或船上的女性,她们的手和胳膊匀称美丽。总体看来,作为中国的女性,她们的手、胳膊和脚是我们所看过的最美的,前提是脚处于未被扭曲的自然状态。”为了方便水上生活,疍家女常年裸足,天足有着自然的美感。
疍家女的头发不剪短而是任其生长,有时编成像男人一样的辫子(如图1),更多的疍家女子会在头顶上挽一个发髻或头巾,或者戴上帽子遮阳挡雨(如图3),[12]钱纳利画作中的疍家女便是常常戴着红色的头巾。钱纳利画作中有多幅关于疍家女“阿来”的写实人物肖像画,在他的传记中,也曾记载了他与疍家女“阿来”、“阿常”来往,为她们绘制肖像画的事情。这些流传下来的疍家女肖像画(如图4),不仅可以让人们直观地了解到疍家女的形象特征,更可以让人们直接观察疍家女与中国传统女性形象之间的差异。作为中国女性中比较特殊的一群,终年裸足是疍家女最明显的特征。她们不缠足、不束乳、不扎腰,拥有黝黑健康肤色,形体健壮,没有过多矫揉造作的打扮,在西方人眼中,有着一种“自然美”。

图3:疍家女孩

图4:钱纳利疍家女
3.具有较强的商业意识
18-19世纪,随着广州口岸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珠江航道的日益繁忙,疍民不可避免地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商业意识渐增,逐渐开始从事一些渔业之外的商业活动。有这样的记载:“有一大批的船被放置在架空的楼房底层,可能不能再下水了,成了数户人家的住房。它们的顶上盖着席子和钉在一起的木版,都是可活动。有时候这些船用来开店,广州市里生活在水边的各个阶层都可以在那买到大米、辣椒,以及一个贫穷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任何物质资料。”[13]
在这种环境下,作为家庭重要劳动力的疍家女,很多成为积极、精明的生意人。不用缠足的身体条件,使她们可以加入到当时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去,在商业运输、商品贸易和服务行业承担着重要的劳动角色。在满布船艇的珠江航道上,到处都有疍家女穿梭忙碌的身影,调船渡客、运送货物以至招揽顾客,管理运营杂货艇、柴米艇、蔬菜艇,向顾客兜售烧生蚝、鱼生粥、艇仔粥、炒蚬炒螺、花生糖等,给那些远道而来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伊凡还记载了一位疍家小女孩向其推销早餐的事:“突然,这个小女孩对我说了几句难听懂的话,并把她的早餐递给我。”[14]在毫不犹豫地品尝了小女孩递给的早餐后,伊凡给了小女孩半个比索(piastre, 埃及、西班牙、墨西哥的硬币单位)。从这位疍家小女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疍家女那种强烈的做生意的意识,以及她们那种积极主动寻找顾客的意识。
4.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国女性
疍民历代都被视为“贱民”,毫无政治地位可言,备受剥削、欺压和凌辱。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提到:“女为獭而男为龙,以其皆非人类也……然良家不与通姻,以其性凶善盗,多为水乡祸患。”[15]而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疍家女是连岸都无法靠近的下等人。疍民的生活习惯,决定了男人外出、女人掌艇的家庭分工,而守着船艇的疍家女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从事大量的劳动。“几天来,我们从不少船上看到,这些船由妇女划船或司舵,在我们是觉得奇异的。这实在不是一种异常的现象,你会看到一个女子在背上用布带缚着一个小孩,怀中又喂着一个婴儿,同时又在划桨或司舵。我好几次也观察到岸上的妇女们把婴儿缚在怀里而同时在干她们的很劳累的工作。这种不愉快的、可能引人深思的现象在使团所经过的鞑靼地区和中国北部各省从未见过。”[16]在这些文字中,无论记录者赋予这些疍家女多少同情和惋惜,都注定不会改变这些疍家女一辈子劳碌辛苦的底层命运。

法国奥古斯特·博尔热19世纪绘疍家渔民在珠江岸上[17](广东省博物馆藏)
疍民被视为“贱民”除生活来源于岸上外,还有其特殊职业有关,疍民生死与江海相依,随潮往来,艰辛的生活,使一些年轻疍家女无奈走上娼妓道路。《清稗类钞》有载:“生女,则视貌之妍媸,或自留抚蓄,或卖之邻舟,父母兄弟,仍时相过问。稍长,辄句眉敷纷,押管调丝,盖习俗相沿,有不能不为娼之势。”[18]亲自到过疍民区、近距离观察过花艇的伊凡曾这样描述:“浮城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展现着自己:白天它像个工业蜂巢,移动的蜂巢被那些勤劳和智慧的群体占据着——他们永远活跃、从不畏惧无休止劳动的严苛压榨。同是这个城市,晚上却像个富有、美丽的高级妓女,她头戴花冠,全身珠光宝气,用迷人的声音、古怪的旋律,喃喃低唱着三色堇(love-in-idleness)爱情歌曲:在夜色的掩护下,毫无矜持地进行着它那撩人情欲的交易。”[19]这些操持皮肉生意的疍家女,被称为“鱼蛋妹”、“水鸡”、“咸水妹”等,连作为女性的尊严都荡然无存,更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地位。
三、结语
目前,作为岭南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内容,疍民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范畴逐渐从历史学扩展到民族史、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专家学者或从历史角度探究疍民渊源与发展, 或从人类学、民族史、民俗学等角度研究疍民族群特殊性或人类学价值。疍家女作为疍民中特殊的一群,有着重要的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研究价值。尤其是在18-19世纪,疍家女作为西方人接触和认识中国女性的一个重要渠道,她们勤勉、吃苦耐劳、乐观开朗和积极进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西方人眼中处于深闺大院、裹着小脚蹒跚而行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因此,关注18-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疍家女形象,也就是关注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女性的认知与印象,从而可以让人们从另一个侧面、以一种异域文化视角,多维度地观察和思考清中晚期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在此基础上,可以更进一步从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出发,去思索和衡量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与演变发展。

ConwayMordauntShipley1854年绘花舫图(广东省博物馆藏)
注释:
[1]南朝·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卷86“南蛮传”记载(后简称“载”):“禀君之先,故出巫诞。巴蜀南郡蛮,本有五姓。”;晋·常琚《华阳国志》卷一载:“属有濮、宝、苴、共、奴、儴、夷、疍之蛮”;《隋书·地理志》卷三十一载:“长沙郡,又杂有夷疍”;《隋书》“南蛮传”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儴、曰俚、曰僚、曰伍”;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八载:“蜑户,县所管,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来往,捕鱼为业”;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晋时,广州南岸,周旋六十余里,不宾属者五万余户。皆蛮、蜒杂居”。
[2][15][清] 屈大均《广东新语》香港中华书局1974年印刷版本中,提及疍家相关的词条有“蛋家贼”(卷7,第250页),“舟语”(卷十八,第476页)以及“蛋家艇”(卷十八,第485页)。
[3]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四十一 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华书局,民国25年(1936),第10-11页。
[4][美]亨特著,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旧中国杂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页脚注2。
[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2年,第35页。原文为:“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来往,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中华地方官应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凡系水手及船上人等,俟管事官与地方官先行立定禁约之后,方准上岸。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不论係何品级,即听该地方民人捉拏,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
[6][7][14][19]分别见[法]伊凡:《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张小贵、杨向艳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96、98、115页。
[8][英]吴芳思:《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9][法]奥古斯特·博尔热著,钱林森等译:《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10][11][英]格雷夫人著,梅贝坚译:《在广州的十四个月》,香港:香港茉莉花出版社,2011年,第15、14页。
[12]疍家女头上戴的帽子通常用藤条编成,做工精细,涂上油漆防水,跟雨伞功能相同,而且不需要占用正在摇桨的双手。
[13][法]奥古斯特·博尔热著,钱林森等译:《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16][英]爱尼斯·安德逊:《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费振东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17]疍家人所居住的船屋,往往就地取材,把渔船拉上岸,用石头或木椿架起而成。
[18]《清稗类钞》娼妓类《潮嘉之妓》。
(作者单位:广东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