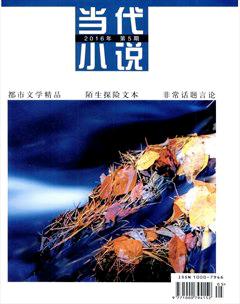“轻重”之间的灵魂质询
周园
卡尔维诺道:“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中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互相竞争: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另外一种倾向则致力于给予语言以沉重感、密度和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1页)。同样的生存体验可用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来表达——“轻逸”或“沉重”。不少作家都想写出拥有史诗品质的厚重小说,这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沉重”叙事不一定能达到一针见血之效,而“轻逸”,用洪治纲先生的话来说,即“以一种看似毫不经意的方式,将一些沉重不堪的过程轻盈而又迅捷地呈现出来”(洪治纲:《洪治纲专栏:先锋文学聚焦之十二:轻与重》,《小说评论》,2001年第6期)。恰恰包含了一种叙事智慧,能帮助读者揭下小说主人公的面纱,直抵灵魂深处,这便是“以轻击重”的妙处。从近期各类文学刊物发表的作品来看,越来越多的70后、80后小说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轻逸”的美学思维。
“轻逸”的背后往往隐匿着“沉重”的世界。第代着冬的近作《没有偏旁的生活》(《上海文学》2016年第2期)塑造了辛格笔下傻瓜吉姆佩尔式的主人公形象。小说主人公三木被邻里视作“公认的好人”,众所周知,“公认的好人”实则与傻瓜无异。算师认定五行缺水,名字却还是缺乏三点水的三木似乎命中注定一生坎坷多灾。幼年染上天花,其父不舍得花钱请大夫,幸而不治而愈,但落了满脸麻子。其貌不扬、言语不多的三木就像一块行走的“破布”,没有同学和老师的赏识,在他人的嘲笑欺侮中长大,惟一的朋友只有混混石磊,石磊却总将一桩桩恶作剧归咎于三木,木讷的三木一次次成为石磊的替罪羔羊,挨打受骂却无怨无悔。三木的青春期随着暗恋对象爱琴的远嫁省城而画上句点,为疗情伤,他迎来了不幸的婚姻,满脑子都是爱琴的音容笑貌的三木一心想跟石磊进城投奔爱琴,石磊不愿意,便编了个爱琴也遭家暴的谎言。三木信以为真,提着一把剔骨刀去了省城,紧接着便出现了被小区保安和民众追赶的持刀青年不幸溺亡的戏剧性结局,出人意料,恰又在情理之中。从故事表层来看,三木受尽邻里欺侮,尤其习惯对石磊逆来顺受,是个不折不扣的憨子。而作者实则暗处用力,凸显了三木圣人般的精神力量,就是这样一个众人眼中没有丝毫分量的窝囊废,居然对一个欺侮了他一辈子的混混的鬼话至死也笃信不移,以至于石磊最终也说了句良心话:“他胆子那么小,除了挨揍,从来没揍过人。”三木似乎心甘情愿地被他人欺侮,执拗地选择顺从与相信,这或许因为他比所有人更能看清存在的真谛,他用自己的真挚和温顺击溃了人世间的虚伪和粗暴,用自己的隐忍和善良瓦解了他人的奸诈和歹念。至此,我们发现,三木实则以一种受难者的形式,完成了对自己以及他人的精神救赎,他的“相信”,充满了伟大的救赎意味。这还是一个简单的傻瓜吗?他游离于傻瓜与圣人之间。
柏祥伟的新作《二叔的荣誉》(《福建文学》2016年第2期)讲述了以死亡交换荣誉的荒诞事件。被诊断出食道癌的二叔决定捐献遗体,造福社会。顺利拿到志愿捐献遗体纪念证的二叔在小城成了焦点人物,在关于二叔主动捐献遗体的新闻播出以后,来访者更是络绎不绝,小县城里的党政事业单位、学校企业团体都纷纷邀请二叔去做专题报告,纷至沓来的荣誉几乎将二叔塑了个“金身”,被狂热的激情笼罩着的二叔似乎红光满面了一阵子,但实则是回光返照,最终还是回天乏术,二叔枕着一摞荣誉证书安然辞世。荣誉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符号,实现的是个人最起码的尊严感,但从二叔身上,我们会发现一个颇为吊诡的现象,即便荣誉与生存对立,与死亡挂钩,二叔也甘之如饴。一次次充斥着鲜花掌声的报告会实则是带领小说飞升起来的重要情节,当二叔的病越来越严重,“在做报告的时候,极力伸长着脖子,脸上的青筋暴涨着,就像是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扼住了脖子一样。他剧烈地咳嗽着,憋得满脸通红,还在尽可能地用力发声。”而观众既为他憋得难受,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发自内心地用热烈的掌声鼓励二叔继续演讲下去。”这一经典的“看”与“被看”的模式揭示出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背后的某些晦暗成分,强化了小说的叙事感染力——看客们在围观二叔的表演,作者以及作为读者的我们在观察着这些看客的畸形心态。与其说这些荣誉是给予舅舅的奖励,不如说是促成其死亡的催命符。以死亡赢得荣誉,是作者对当代人们心灵深处的生存荒诞感以及价值缺失感的刻意发现和敏锐捕捉。
再来看刊载于同一期《福建文学》上的谢方儿所写的《麦乳精》一文。不同于诸多文革叙事“以重击重”的审美策略,《麦乳精》另辟蹊径,作者刻意淡化了文革的时代背景,以一罐小小的麦乳精来打开时光的口子,切入文革。“麦乳精”,是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里的珍馐,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四类分子”陈阿水用麦乳精换取的是两个小毛孩对其“爸爸”的尊称。当“我”向身为朝阳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舅舅泄露此事后,舅舅突然暴怒,继而要求“我”和三哥继续与阿水接触,并向他汇报阿水报复新社会的证据。“我”与“三哥”本无血缘关系,且矛盾重重,在一次次争抢麦乳精事件后,当三哥再次用曾经伸进麦乳精的右手食指指着我谩骂时,我拿起木桨将三哥打落进河水,三哥的失踪以及“我”的谎言最终将阿水推进了无底深渊。麦乳精作为叙事线索,贯穿整篇小说。作者花了大量篇幅叙述阿水用珍贵的麦乳精诱惑两个小毛孩喊其“爸爸”的荒诞事件,颇具喜剧色彩。一杯麦乳精,换得一声“爸爸”的尊称,这种“公平”交易不仅凸显了专制时代下人性被扭曲的现实景观,也展示了被戕害者犹作困兽之斗的心理突围手段,尽管并不怎么光彩,甚至有些畸形,但它撕开了极权意志钳制下人性尊严被剥夺的惨痛状态。一罐小小的麦乳精寄托着陈阿水有了儿子、并成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姐夫的精神胜利法,阿水以此令人心酸的方式获得尊严,尽管他费尽心思挣脱孤独无依的厄运,终究还是无声无息地被铅灰色的世界所淹没。
既然现实已如此让人不堪重负,作家要做的自然不是增“重”,而是要“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页)。“轻逸”美学精神的旨趣在于当面对历史之重、现实之惨淡、人性之丑陋时,作家从容不迫地将叙事从沉重的现实主义原则中解脱出来,以轻逸化的叙事思维来探索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这不仅能赋予小说天真自然的诗意,也能带领读者一道“飞升”起来。(杭州师范大学)